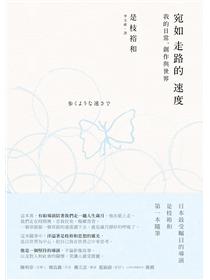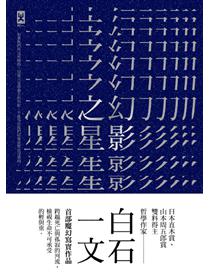★再版不斷,報章媒體盛讚不已!
★直木賞得主白石一文最新史詩傑作!
我看得見記憶,而這些記憶正是現實──
身為國際知名作家的哥哥驟然辭世,死因成謎。古賀純一從兄長遺物中找到謎樣的遺書及名為「特納之心」的隨筆,隨處綴有古賀一家歷史的隨筆,卻與純一的記憶大相逕庭。在追尋兄長死因及家族歷史的過程中,更多的謎題接踵而來.......
作者簡介:
白石一文 Kazufumi Shiraishi
一九五八年生於福岡縣,畢業自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系。二〇○○年於「文藝春秋」工作時發表了《一瞬之光》,獲得各大報章雜誌讚譽,以新銳之姿出道。○九年以《この胸に深々と突き刺さる矢を抜け》獲得山本周五郎賞,隔年一○年又以《不可或缺的人》獲直木賞,巧妙的劇情鋪陳與真摯探討生命意義的思考性作品風格在現代日本文學界中散發出獨一無二的存在感。另著有《不自由的心》、《近在身邊的遠方》、《關於我的命運》、《神秘》、《愛是謊言》、《ここは私たちのいない場所》、《光のない海》等多部著作。
譯者簡介:
王靜怡
一九八○年生,高雄市人。台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畢業,興趣為閱讀、寫作以及電玩。目前為專職譯者,譯有「偵探.日暮旅人」系列、「劇團!Theatre」系列、《空之中》、《海之底》、「諸神的差使」系列等書。
章節試閱
絕望並非存在於未來,而是聚積的過去,擱在當事人的去路之上。面對眼前如牆壁一般高高堆起的過去,我們心生畏怯,因此恐懼,因而絕望。然而,其實那都是早已結束的往事,未來就像窗外那片萬里無雲的晴空一般無限延伸,前方並沒有任何事物阻撓我們。我們畏懼過去及過去產生的幻影,因而不禁把視線從對於人類而言尚不確實──換個說法,即是蘊含著無限可能性──的未來移開;這才是絕望的真面目。
摘錄自我的哥哥.手塚迅留下的備忘錄
※ ※ ※
第一部
1
我的哥哥能夠閉著眼睛直線走路。
「聽好了,純一,首先,你要把眼前的風景牢牢地記在腦子裡。這麼一來,就算蒙著眼,你也可以在路中央走上幾百步。沒什麼好怕的,瞧,我可以這樣一直走下去。如何?純一,就像哥哥說的一樣,對吧?重點在於集中力,如此而已。」
我看得見記憶,而這些記憶正是現實──打從小時候,哥哥便常如此誇口。
然而,如今看來,那只是哥哥獨有的自信過剩;換個說法,只是膽大妄為的產物。
或許哥哥並不是能夠閉著眼睛走路,而是他完全不怕因為看不見腳邊而絆倒。
仔細想想,我從沒見過像哥哥那樣嚴苛地看待人類的矛盾態度的人。哥哥那種比常人倍加刻薄的言行並非出於他的理智,同樣是出於某種愚蠢的勇氣,換句話說,即是不顧後果的魯莽。
比方說,哥哥曾嚴詞批判這個國家的眾多遊戲機和軟體公司,說它們是破壞小孩想像力與創造力的元凶;他也曾因為電視廣告中的藝人們笑著推薦他們根本沒用過的產品而大為憤慨;美麗的女星宣稱自己愛用平價化妝品,不會喝酒的男星穿著和服津津有味地將日本酒一飲而盡,從未吃過便祕藥的偶像大力推薦便祕藥──哥哥似乎完全無法容忍這類欺瞞。
當以履行政見為由而持續參拜靖國神社的首相召開國是會議,針對承認女系天皇之誕生的皇室典範改正案聽取報告時,哥哥不顧自己封筆已久,竟突然在某部月刊上發表評論文,唾罵該首相蔑視「國體本義」、「不忠不義」,這件事在當時也震驚了整個社會。
在回程的飛機上,我把哥哥的骨灰放在膝蓋上,不停地思考哥哥死亡的理由。當然,我不可能想得出具體的理由,因為我和哥哥已經有十年沒有通過任何信件或電話了。
不過,我似乎隱約明白哥哥為何而死。
因為耽溺於擬真遊戲而犯下難解罪行的青少年越來越多,要不了多久,這個國家的未來就會葬送在現在的小孩手上──這種煩惱,這種誇張又毫無意義,但是對於哥哥而言卻是不容忽視的嚴肅煩惱在日積月累之下,將他逼上了死路。
哥哥的聰敏機智是眾所公認的,但相對地,他對於這個世上的繁文縟節一竅不通。不知何故,哥哥無論長到幾歲,都無法理解人類社會的這些無關緊要的不成文規定。對於有天才之譽的人們而言,這或許是種極為常見的狀況吧!
──上天賜予天才挑戰無解之謎的莽勇。
我記得哥哥曾經在某處寫下這句話。
我小時候看著哥哥,總是這麼想:我們無法理解天才的腦子裡在想什麼,是因為他們總是在思考全體人類無須理解的事。
他就像是個想把金屬變成糧食,拚命研究如何讓釘子或腳踏車可以食用的科學家。的確,倘若人類能夠吃金屬,確實是種劃時代的演進;然而,想當然耳,絕大多數的人並不想吃金屬,也沒有必要吃金屬。
哥哥享年五十四歲。
五十四歲算不算早逝,我不清楚。我比哥哥小五歲,今年四十九;易地而處,我並不認為哥哥的死算是早逝。我覺得人能夠活個五十年,已經足夠了。換作是我,就算明天腦部或心臟突然發生病變,一命嗚呼,我應該也不會像年輕時那樣感到悔恨。當一個人不再有說什麼也要活下去的念頭,對他而言,任何時候都是死得其時了。
同樣是在飛機上的事,如果要以一句話概括哥哥五十四年的人生,我想最適合的應該就是「過猶不及」。
哥哥正是個過剩的人。
而過剩往往有害無益。過剩的知性、過剩的才能、過剩的美貌、過剩的家世、過剩的財力、過剩的愛、過剩的恨,甚至是過剩的靈異體質,只要是冠上過剩兩字的狀態,一定會使人陷入不幸。人類無法控制過剩的事物。
過剩甚至可以殺人。
凡事都該避免「過剩」,我認為這是多數人類在這個世界上生存下去的重要關鍵。
哥哥過剩的是什麼?
知性?才能?愛情?憤怒?
我在飛機上不停地思考哥哥死亡的理由及這個問題。
直到剛才,坐進停在機場停車場的轎車駕駛座時,我才找到答案。
沒錯,對於哥哥而言,過剩的正是他本身。
從機場到我家,走都市高速道路大約是三十分鐘的車程。
我住的城市位於沿海地區,呈東西向橫長形狀,機場在東端,而我家在西端。不過,由於是個和東京完全無法比擬的小都市,只要開個三十分鐘就能到家了。
再過三天就是十一月,今年終於只剩兩個月了。我常在想,一年為什麼這麼長?總共有十二個月,縱然屬於同一年,也往往記不得半年以前發生的事。一年只要有六個月便足矣,倘若是六個月,倒還勉強記得住。
打從孩提時代起,我便認為春夏算一年,秋冬算一年才好,西曆也從二○○六年改成四○一二年即可。思及人類在地球上的肆虐,這個數字比較有說服力。
若是如此,哥哥就是一百零八歲,而我也已經九十八歲了。哥哥和我都很長壽,不是嗎?老實說,我覺得自己活得太長了。
回家之前,我順道去了附近的超市一趟。
時值假日中午,平常幾乎都是客滿的狹窄停車場還有些許空位。我把車子開進左右都是空位的停車格,並把骨灰罈留在助手座上,逕自下了車。就算是砸車竊賊,應該也不會瘋狂到偷走別人骨灰的地步吧!
不過,店裡的人卻不少。雖然還不到大排長龍的地步,但是六個收銀台前都有好幾個客人。我把購物籃放在手推車上,從灰色西裝的內袋拿出一張折起的紙片,並打開來。那是放在飛機座位上的機上雜誌頁面,被我撕下來的。我把頁面的內容裝進腦子裡,將手推車推向味噌.醬油陳列架。
我在排放各種味噌的一角尋找八丁味噌,只有下頭那一排擺了一款。我拿了兩袋兩百公克裝的味噌,放進購物籃裡。根據機上雜誌的食譜,四人份需要兩百克的八丁味噌。我不只是要拿來煮今天自己吃的晚餐,還要多煮一些留到明天,給公司的員工當午餐吃;考量他們旺盛的食欲,大概要八人份才夠。我本來還擔心超市裡買不到這一帶並不常見的八丁味噌,幸好找到了。
我匆匆忙忙地找齊其他材料。和味噌同樣是四百克的白雙糖,還有蛋、蒟蒻、烤豆腐、角麩、白蘿蔔及芋頭。最後,我又在生鮮區買了豬肉。黑豬五花肉一塊,一公克五百圓。只要吃過黑豬肉,就再也無法接受其他的豬肉了;而黑豬又以五花肉最為美味。食譜上說把肉切成約三公分大的丁,每三塊用竹籤串成一串,加以燉煮。為了慎重起見,我也買了竹籤;上個禮拜和員工一起炸肉串時,好像把竹籤用光了。
我提著兩只變得意外地重的塑膠袋,回到了車上。
回到家一看,時間已經過了下午一點。
今天是星期日,所有員工都不在。「所有員工」四字聽起來似乎為數者眾,其實包含兼職的事務員在內不過四個人,而其餘三人也只是全天班的工讀生而已。
──智子香皂社有限公司。
我從懸掛著這個小招牌的倉庫入口走進家中。
我把過世的爸媽蓋的四十幾年兩層樓房簡單地改建成住宅兼辦公室,所謂的倉庫只有十坪大,是我將小庭院和半個可停兩台車的停車場打掉,以連著主屋的形式增建的。
倉庫裡,有許多紙箱堆放在作業台的另一頭。
商品終於送來了。最近訂單太多,根本消化不完。大阪的智子香皂工廠也全線運轉進行生產,但依然追不上一張接著一張的訂單。大略目測之下,紙箱共有五十個,一箱裝著兩百個香皂,總計一萬個。即使有一萬個,也撐不了兩星期。
這種一個要價八百圓的香皂居然如此暢銷,我至今仍然不敢相信;不過,根據智子所言,「聽說這個國家的過敏人口包含症狀輕微的人在內,已經高達國民的一到兩成,我的香皂會大賣是正常的。」
創立公司,正式開始營業至今,不過一年半;但今年上半年的營收已經接近一億圓了。
或許是因為健康雜誌及女性雜誌爭相報導的緣故吧!從去年年底開始,訂單倏然暴增,經由網路或電話訂購的單位數目也跟著水漲船高。過去大多是慕名而來的個人顧客,頂多是十個、二十個小量販賣;但是自去年年底以來,卻轉變為一次一百個、兩百個的大量訂單。當然,這是因為客層拓展到藥妝店與雜貨店,不再局限於個人之故。目前,我的公司是「智子香皂」的唯一經銷商,要購買香皂只能經由這裡。
多虧了熱門商品的獨占銷售權,「智子香皂社有限公司」賺了不少錢。
從骨灰開始,我把後車廂的波士頓包和裝有食材的塑膠袋逐一搬進了與倉庫相連的辦公室,並把食材放入辦公室廚房裡的冰箱。一樓原本就是客廳.飯廳.廚房三合一的格局,由於改建時沒有多餘的資金將廚房移到二樓,所以至今我仍然是在原來的廚房煮飯燒菜。
約有十坪大的辦公室裡放著五套辦公桌椅,以及放置文件用的鐵櫃和會客沙發組。這些東西都是中古貨,只有每個人桌上的電腦是新的。應員工要求,上個月把所有電腦都換成新機種了。
我把骨灰安置於會客沙發組的茶几上,拿起自己桌上的成疊訂單,迅速地瀏覽一遍。主任山形每天都會打電話向我報告,因此我不在的這三天裡,業務並未受到耽擱。
上週四,我突然接到醫院的通知,趕往東京;隔天下午,哥哥斷了氣,遺體在傍晚運到了他的公寓裡。我獨自替他守靈,並在昨天星期日將他火化。昨晚我在哥哥的公寓裡多留一夜,整理遺物,今早用宅配把較為重要的東西寄到這裡,之後便直接前往羽田了。
這三天過得手忙腳亂,但不知何故,我並不怎麼疲勞。
我拿著骨灰罈和包包,走上二樓。
我的房間在二樓,是個約四坪大的西式房間,我從孩提時代便開始使用了。除此之外,就是哥哥從前的房間、爸媽的寢室、一坪半大的儲物間和廁所。想當然耳,浴室和盥洗室依然在一樓。
我換了件衣服,捧著剛才擱在床上的骨灰罈,來到曾是爸媽寢室的五坪大房間。房裡有張爸爸寫字時用的折疊式和几,我把它立起來,放在和室窗邊,並將除去白布後的骨灰罈安置在桌上。
我到樓下的廚房拿了只威士忌無腳杯和粗鹽來代替香爐,在無腳杯裡裝了一半的鹽,插上葬儀社給我的線香,點燃了火。我端坐在骨灰罈的正前方,閉眼合掌,但是心中並沒有任何感慨。就在我睜開眼睛,放下手時──
──這麼一提,哥哥把爸媽的佛壇移到哪兒去了?
我想起了這件事。
由於事隔已久,許多人都以為哥哥是早熟的天才,其實他以小說家成名的時期出奇地晚。處女作獲得大獎並登上銷售排行榜冠軍時,哥哥已經二十七歲了。當時,哥哥和百子姊已經結婚,新居就在東京郊外百子姊的娘家附近,生活大多倚賴百子姊當醫生的收入,而哥哥自己也一面打工,一面寫小說。
爸爸過世以後,是媽媽守著這個家的佛壇;哥哥應該是在媽媽死後將佛壇移到東京的。第二部小說比處女作更加轟動,使得哥哥一躍而成時代的寵兒;欣慰地看著兒子站在聚光燈下的媽媽卻在某一天突然心臟病發,與父親相聚去了。當時哥哥二十八歲,而我則是二十三歲,正值大學中輟的三年後。
媽媽死後,轉眼間已經過了二十五年。
當時,哥哥把供奉爸媽牌位的佛壇移到東京的住處,不知現在佛壇在哪兒?
昨晚我在哥哥的公寓裡整理遺物時,居然將佛壇的存在忘得一乾二淨;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在那個簡陋的房間裡完全不見佛壇的蹤影。
會不會是在已經過世的百子姊家?不過,哥哥和百子姊離婚的時候,我和哥哥還有來往;換句話說,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夫妻分手後,搬離家中的妻子不可能一直守著夫家的佛壇;照這麼看來,離婚成立時,哥哥當然帶著佛壇離開了。
說歸說,我也記不清當時的事了。哥哥和百子姊究竟是在幾年前分手的?是十三年前?還是十五年前?我記得當時哥哥尚未滿四十歲,而我年近三十五,自己也有麻煩事纏身,沒有餘力關心哥哥的離婚問題。哥哥搬家之後,我不記得自己曾去過他的新家;我們同樣住在東京,有急事時固然會見面,但都是在外頭短暫會面而已。哥哥和我都是不愛被人窺探私生活的人,縱使是親兄弟也一樣。當時雖然尚未完全斷絕往來,但是我和哥哥已經不像從前那樣無話不談了。
我就著正坐姿勢迷迷糊糊地望著線香的紅色火點,片刻過後,肩膀一帶開始發冷了。
東京的夜晚很冷。哥哥的公寓裡除了空調以外,沒有其他暖氣;守靈的那一晚,我不能在為了防止遺體腐爛而放置乾冰的房間裡開空調,可是又沒有其他房間供我睡覺,所以我只能瑟縮地過了一夜。離開短短三天,位於南方的此地也倏然變得秋意濃厚了嗎?
我站了起來,擱下燃燒中的線香,離開了房間。我回到自己的寢室,坐在床上,看了時鐘一眼,時間正好是兩點半。趕往墨田區的醫院探視陷入昏迷的哥哥那一晚自然不用提,隔天的守靈夜,還有昨晚,我幾乎都沒有闔眼。雖然我並不怎麼疲倦,但是回到熟悉的床上之後,體內便立刻湧現了睡意。
先小睡到傍晚吧!之後再用買來的食材烹調機上雜誌介紹的「名古屋風味噌黑輪」──我如此盤算。
2
小八、小典、阿鳶和佳江小姐個個食欲旺盛,把燉了一夜的味噌黑輪一掃而空。
作業台中央的大鍋即將見底時,越光新米炊好了,我替各人的專用碗公盛了一大碗白飯,又分別放上一顆預留的水煮蛋,遞給每個人。
用筷子搗碎水煮蛋,再淋上鍋裡剩餘的味噌湯,就是名古屋名產「赤茶泡飯」。我先示範,大家如法炮製,接著便一面大快朵頤熱呼呼的白飯,一面異口同聲地稱讚:「好吃,好吃。」
我是照著機上雜誌的食譜燉煮的,老實說,費了不少工夫。基底的味噌湯頭,是把買來的八丁味噌放進搗缽裡搗碎,並在鍋裡加入同樣分量的白雙糖和六百C.C.的酒,用小火慢慢熬煮,以免燒焦,並隨時添加高湯,直到濃度達到一般味噌湯的兩倍。
湯頭的製作與調味已是相當困難,更加麻煩的是材料必須分開熬煮。
蒟蒻搓鹽之後先水煮一遍,再用味噌湯頭熬煮一小時;水煮蛋也要一小時;五花肉切丁三公分,每三塊串成一串,約須兩小時;烤豆腐二十分鐘;泡過水的芋頭慢火燉煮一小時,直到變軟為止;白蘿蔔切片兩公分,熬煮一小時。如此這般,食譜上說將所有食材分開熬煮,是重現行家滋味的祕訣;而我既然要做了,當然不能偷工減料。
結果,直到昨晚十一點過後,全部的食材才在大鍋裡會合。我試吃了幾塊燉料,但由於先前的烹調過程搞得我筋疲力盡,縱使下午已經小睡過兩小時,還是草草吃了幾口就睡著了。
不過,不枉我如此大費周章,今天的午餐大受員工好評。近來反應如此良好的,好像只有做了成堆的梭子蟹奶油可樂餅給他們吃的那一次了。
在我的公司,一週六個工作天裡,至少會有三天像這樣圍著作業台一起享用親手烹調的午餐。掌廚的通常是我,材料費當然也是由我負擔。換句話說,我是這個中小企業的經營者兼員工餐廳的大廚。對於這個慣例,起先員工們有些困惑,但是吃了幾次我親手做的料理以後,態度便有了一百八十度轉變。不到兩個月,所有員工都變得非常期待圍桌吃飯的午休時間了。
想當然耳,理由很單純,就是因為我做的料理美味無比。
我從學生時代就開始下廚,資歷已經很長了;我自信手藝並不輸給專業廚師。料理是我唯一的興趣,應該也會成為一輩子的興趣。我常在想,只要輪流委託日本首屈一指的大廚們設計中.小學營養午餐菜單,在他們的指導之下,提供美味無比的早餐和午餐給全國各地的孩子們,現在學校裡發生的各種問題一定能夠迎刃而解。還有,企業若是真心想提高生產力,無須採用什麼成果主義、人才選拔法或自律性職能發展支援等大費周章的手法,只須把為了降低成本而委外經營的員工餐廳收回來自行管理,每天中午提供美食給所有員工,效果一定來得好上許多。
天天吃著上好食材烹調而成的美味料理,心靈便會沉澱下來,集中力也會因而提升。
對於這些一年半前雇用的員工,料理也發揮了莫大的功效。
主任小八,亦即山形八男,二十六歲;小典,亦即內村典子,二十三歲;阿鳶,亦即飛松隆志,二十一歲;還有兼職人員,負責會計工作的遠藤佳江,三十九歲──這就是員工的年齡結構;其中那三個年輕人是智子的網友,當初我雇用他們,純粹是看在智子的分上,連履歷表都沒看過。然而,這一年半以來,他們的工作表現相當良好,集中力也與日俱增。近半年內,莫說曠職,就連病假也沒人請過。這些人和智子是朋友,卻個個如此勤奮工作,無人離職,可說是相當異常。而我私下推測,支持這種異常事態的,正是每週供應三天以上的美味午餐。
一如平時,過了一點五分,作業台上已經收拾得乾乾淨淨了。
待各人回到工作崗位上之後,我向背對著我獨自拆箱、準備下午出貨的阿鳶說道:
「阿鳶,我有話跟你說,可以跟我來二樓一下嗎?」
正在用美工刀逐一拆開紙箱的阿鳶回答:
「好。」
並轉向了我。我想和員工個別談話的時候,總是會請對方到二樓去。我在哥哥從前使用的西式房間裡放了套小沙發組,充當會客室。和銀行的業務承辦人或貨運業者商談時,也都是選在二樓。
一身黑色T恤和牛仔褲的阿鳶又說:「我先去拿一下外套。」因此,我便自行橫越辦公室,先上二樓去了。
不久後,穿上外套的阿鳶也上了樓,走進會客室。
阿鳶坐在靠門的沙發上,而我則坐在靠窗的沙發上。
像這樣對坐在狹窄的房間裡,身高有一百八十七公分的阿鳶看起來十分高大;說歸說,他是根瘦竹竿,體重還不到六十公斤。如果他具備應有的體重,應該很有壓迫感吧!
「要跟我說什麼?」這類問題無論等再久,都不會從阿鳶的口中發出。不知是不是現代年輕人的通病,至少我們公司裡的三個員工在我宣稱「有話跟你說」而找他們過來的時候,絕不會主動探問是什麼事。阿鳶往沙發坐下以後,便沉默不語,啜飲著從樓下的冰箱裡拿來的寶特瓶裝綠茶。當然,他並沒有細心到順道拿一瓶上來給我的地步。
「你應該知道我是為了什麼事叫你來的吧?」
隔了一、兩分鐘後,我才開口說道。
阿鳶神情訝異,無意識地旋緊寶特瓶蓋,視線從我的臉上移開了一瞬間,並微微地端正坐姿。
「佳江小姐是在上星期三向我報告的,我原本打算在星期四找你談談,但是你也知道,我必須去東京一趟,所以才拖到現在。佳江小姐說這三個月來,我們有六百個左右的商品不見了,換算起來是三箱,價值四十八萬。她是在兩星期前發現這件事的,後來一直獨自追查原因,直到上個禮拜才查出結果。她比對票據、交貨單和銀行的匯款記錄,發現我們公司裡有員工盜賣商品,而她也找到犯人了,並且在星期三向我報告。」
說到這兒,我暫且打住。眼前的阿鳶看起來並不怎麼驚訝,而是帶著曖昧的表情望著我。
「犯人就是你。」
我說道。
阿鳶的臉龐微微泛紅,但紅暈隨即便褪去了。
接著,他露出了內斂的表情,彷彿在斟酌浮現於腦中的幾種說詞,之後才定睛凝視著我。
「不是我做的。」
並用沉著的語氣說道。
我默默無語,注視著阿鳶雙頰凹陷的臉龐,而他也毫不畏怯地回望著我。就在我們互瞪了近三十秒以後──
「不,是你做的。」
我平靜地說道。
這個時候,阿鳶的表情終於出現了較大的變化。他不可置信地張大了嘴,用責難的眼神看著我。
「古賀先生,請等一下,為什麼這麼說?我真的什麼也不知道。我怎麼可能動公司的商品?」
他的口吻顯得極為困惑。
「很遺憾,你在說謊。」
「天呀!這句話太過分了。」
阿鳶露出有些難堪的笑容,攤開雙手。
偷了東西的人被揭穿,鮮少會老實承認;因為老實的人打從一開始就不會竊取公司的物品。因此,對於阿鳶的反應,我既不意外,也不失望。
我從上衣的口袋中拿出一張折疊的紙片,將其攤開,並遞給阿鳶。阿鳶依然是一副無法釋懷的表情,但還是接過了紙片;接著,我又把一枝原子筆和刻著「飛松」的回墨印章放在桌上。
「這是你的辭呈,現在立刻用這枝筆和印章在這份文件上簽名蓋章。」
我如此下令。
阿鳶大概以為紙片上記載了什麼不動如山的鐵證吧!我感覺得出他得知只是辭呈以後鬆了口氣。
「什麼跟什麼?太不講理了。我怎麼可能簽名?如果您堅稱是我做的,請拿出證據來。您說商品不見了,究竟是怎麼回事?該不會只是沒有匯款而已吧?最近有些客人收了貨卻沒付錢。再不然,就是別人做的。搞不好是佳江姊自己做的,卻要我背黑鍋。」
我嘆了口氣。
「我知道是你做的。」
我說道。
「那就把證據拿出來。」
阿鳶又重複了一次。我越來越感到厭煩了。
「很抱歉,我是真的知道。相處了一年多,你應該也隱約察覺到我有這種本事了吧?」
我一字一句地說道。聞言,阿鳶似乎也有些畏怯了。
「如果你堅稱不是你做的,我可以把樓下的其他人叫上來,告訴他們事實,大家一起找犯人。如果這樣還是找不出來,我就報警,請他們針對盜賣公物進行調查。你應該也不想讓朋友知道這件事吧!更別說是鬧上警局了。乖乖在文件上簽名,明天以後別來了,這樣我就當作這件事沒發生過。這麼做對你也有好處。」
阿鳶垂下頭,沉默了片刻,微微搖晃雙手拿著的寶特瓶。他並不是傻瓜,他是在思考。
「我也很無奈。」
他垂著頭,喃喃說道。
「我需要香皂是有苦衷的,本來打算一有錢就把貨款補回去。我沒有惡意。」
說著,他抬起頭來,用求助般的眼神補上一句:
「求求您,我會仔細說明我的苦衷,請給我解釋的機會。我很喜歡這份工作,不想辭職。」
我觀察阿鳶的眼神,看得出他心中的欺瞞成分並不大。的確如他所言,他應該真有「苦衷」吧!
不過,我已經做出了決定。
「不必給你解釋的機會,你的行為就是偷竊,找什麼藉口都沒有用,我不會諒解的。」
阿鳶聽了我這番話,啞然無語。
「總之,快簽名吧!我不會跟你追討香皂錢。反正你大概也付不出來。」
我如此催促;阿鳶把文件扔到桌上,突然從沙發上站了起來。
「你要去哪裡?」
我用強硬的語氣說道。
「跟智子姊商量。」
「沒用的,智子也不會認同你做的事。」
「總之我要去打電話。」
從下方仰望阿鳶的臉,可看出他的臉色有些蒼白。我從上衣口袋中拿出手機。
「那我現在立刻打電話報警,可以吧?你要聯絡智子,等簽完名以後再說。」
阿鳶似乎明白我是認真的了。他再度坐下,草草簽了名,把手上的印章扔向我,逃也似地離開了會客室。
3
我一面與佳江小姐纏綿,一面回憶昨天在羽田接受手提行李檢查時的事。
我把哥哥的骨灰罈放在托盤上遞了出去,身穿制服的男性檢查員在送上X光檢查機的輸送帶之前,先畢恭畢敬地將骨灰罈放在不銹鋼台上,儘管當時已經大排長龍,卻仍然仔仔細細地合掌祝禱。
通過金屬探測門之後,我回頭一看,只見那個年約三十、身材微胖的檢查員終於放下了手,將哥哥的骨灰罈送上輸送帶。
應該是工作守則規定他這麼做的吧──我壓在佳江小姐的苗條身軀上,一面聽著她含蓄的喘氣聲,一面如此暗想。
凡事都有守則。機場每天應付大量的旅客,像昨天的我那樣抱著骨灰罈搭機的乘客想必不在少數吧!雖說骨灰罈亦屬手提行李,但若是不慎重處理,乘客或許會客訴,因此才訂下規則,接過骨灰罈的檢查員必須誠心地合掌祝禱,以免刺激對方。
即使如此,我還是很感謝那位檢查員的細心。我沒有開口道謝,而是輕輕地行了個注視禮,表達感謝之意。另一個把骨灰罈遞還給我的女性檢查員也特地用雙手捧著骨灰罈,行了一禮之後才還給我。我也深深地向她垂頭致意。
凡事都有守則,而這些守則即是從長年累積的經驗之中萃取而出的菁華。
學生時代,我曾在銀座的手相觀打過一陣子工,當時的前輩傳授我兩套萬用說詞,做為新人占卜師的守則。他告訴我,不管對方是什麼打扮,先這麼說就對了。
──雖然大家並不這麼想,其實你是個不擅於表達的人。
──在周遭的人看來,你或許很幸福,其實你也嘗過不少辛酸。
這個守則確實發揮了不小的效用。
我常在想,現代人太過輕視守則了。守則總是被當成自由與創造力的大敵,但它其實是過去的獨創集合體。對照我的經驗,打從一開始便輕視守則的人沒有半個是真的擁有獨創性的。
佳江小姐一如平時,在下班之後來到我二樓的房間,與我在床上纏綿;當我射精並將生殖器官從她的體內拔出的瞬間,放在窗邊書桌上的手機響了。
「失陪一下,我接個電話。」
我向她說道,走下了床。
我赤身裸體地走到書桌前,拿起手機;果不其然,是智子打來的。我按下通話鍵,把手機放到耳邊。
『阿鳶打電話給我。』
智子說道。「阿鳶」這個綽號原本是他在網路上用的暱稱。
「他盜賣公司的商品。很遺憾,我不能繼續雇用他了。」
『他說他的朋友有個過敏很嚴重的朋友,他拿香皂給那個人用,結果那個人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都說想要,一發不可收拾。起先他有收錢,可是後來就漸漸收不到錢了。』
「這種說詞很可疑。」
『是嗎?你真的這麼想?』
我沒有回答她的問題。
「再說,用了這種靠不正當手段弄來的東西,他的朋友反而會惡化吧?」
而是如此說道。
『話是這麼說沒錯……』
智子的聲音顯得悶悶不樂。
「阿鳶跟妳說什麼?要妳跟我說情,好讓他回來工作?」
『嗯,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他還說了什麼?」
『沒有。』
「是嗎?」
我沉默下來,智子也默默無語。
「別說這個了。妳那邊的情況如何?」
我開口說道。
『還能如何?狀況不太好。』
「是嗎?」
『姑丈呢?』
「我哥上禮拜死了。」
『手塚老師死了?』
智子的聲音有些上揚。
『這樣啊……』
她喃喃自語。
「嗯。」
『節哀順變。』
「嗯。」
之後,我們再度陷入了沉默。
絕望並非存在於未來,而是聚積的過去,擱在當事人的去路之上。面對眼前如牆壁一般高高堆起的過去,我們心生畏怯,因此恐懼,因而絕望。然而,其實那都是早已結束的往事,未來就像窗外那片萬里無雲的晴空一般無限延伸,前方並沒有任何事物阻撓我們。我們畏懼過去及過去產生的幻影,因而不禁把視線從對於人類而言尚不確實──換個說法,即是蘊含著無限可能性──的未來移開;這才是絕望的真面目。
摘錄自我的哥哥.手塚迅留下的備忘錄
※ ※ ※
第一部
1
我的哥哥能夠閉著眼睛直線走路。
「聽好了,純一,首先,你要...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1收藏
11收藏

 10二手徵求有驚喜
10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