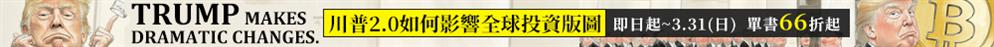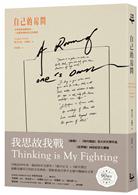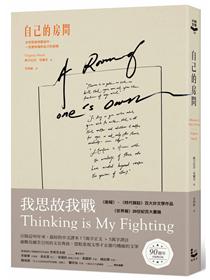三月的第三個星期一,我第一次看見鷹樹。要是我相信魔法、迷信或者宗教的話,就會把這當成一個吉兆,因為我的中間名就是馬奇。我希望大家都叫我馬奇,如果你叫我別的名字,我是不會搭理的。但媽媽堅持叫我彼得,儘管我告訴過她,我的名字是馬奇。
因此,在三月的第三個星期一,第一次見到鷹樹,可能是個吉兆──如果我相信那些不真實的東西的話。可事實上,我並不相信。人們說的很多話我都不相信,因為他們總是說些不真實的東西。凡是無法用眼睛看到、用耳朵聽到的,我一律不相信。我用真實的名字稱呼所有真實的東西。
我相信樹,因為我能夠觸摸到它們,而且每一棵樹都有真實的名字。對於我來說,它們是永恆不變的。第一次見到鷹樹那天,我十三歲零四個月又三天。那時,我平均每天爬五六棵樹,有時爬三十棵,有時爬四棵,最少的時候只爬三棵。三棵樹是我的底線,不管天晴還是下雨,生病還是健康,我每天至少要爬三棵樹。
從前,我們還住在那個門前有三級臺階的黃色房子裡時,我每天爬三棵樹,就是家門前路邊的那些。每天早上,媽媽起床之前,我都要去爬三棵樹。我想她應該不知道我在爬樹,但或許她知道也說不定,因為吃早餐前她總是叫我先洗手。即便是現在,當我遵守洗手的規矩時,也總會發現不是皮膚上沾著一些樹皮,就是指甲縫裡卡著幾根松針、幾片碎葉,大概是被她發現了吧。通常,我並不會留意這些,除非她提醒我。
洗手的時候,我就不得不注意到手上的皮膚。我的手指因爬樹而生滿老繭,指甲又髒又短,總是沾著樹皮。這是一副鳥類的爪子,一生住在樹上的鳥類的爪子。
****
三月的第三個星期一,我在爬一棵西部紅雪松,就在那個有藍色信箱的新家旁邊。那天,我沒去上學,媽媽也沒去上班,她一大早就去我週末待的地方接我。那是我回到新家的第一天。
事實上,那也是我第一次來到鄰居家的後院。當時,我們才剛認識這個鄰居──克萊頓先生。我們家的藍色信箱旁有一個黑色信箱,上面寫著他的名字──這使我比較容易記住他的名字叫克萊頓。
認識克萊頓先生九分鐘又四十二秒之後,我獲得了允許,可以爬他家後院裡的一棵樹。這是我第一次爬那棵西部紅雪松,也是我在當天爬的第二棵樹。
由於我還不清楚到底該怎麼爬,只好花了很長時間規劃路線,計算步數。這也就是為什麼我直到在這棵紅雪松上爬到五十呎的高度時才注意到了鷹樹。當時,我正忙著計算步數、規劃路線,為了以後之便。
現在,只要一閉上眼睛,我就能準確地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每一步都像照片一樣印在我的腦中。
****
爬到第二十七步的時候,我總算脫離了周圍小樹的遮蔽,視野變得清晰起來。我抬起右腿,倚靠在一根小樹枝上,測試它的承受力。但它不夠牢靠,於是我決定不再往上爬。手臂上的繃帶再次讓我分心,我很想把它扯掉,可又想起媽媽說過不許拿掉繃帶,於是只好作罷。
不管怎麼說,在思考是否要扯掉繃帶的時候,我停止了移動。我站在紅雪松的樹枝上,靜靜地看著遠方。然後,我突然意識到自己看見了什麼。
從這個角度,越過眼前層層疊疊的屋頂,我看到了河那邊的一個山谷──一個滿是樹的山谷。
起風了,小樹枝隨風搖擺。我身上撒滿了塵土與細碎的樹皮,但我依舊緊緊地抓著樹幹,直視遠方。
我看見山谷那邊有個什麼東西,不,它矗立在山谷之上。
儘管那個東西像水塔一樣巨大,但我從第一眼就知道,它是有生命的。
那是一棵樹。我從未見過如此龐大的樹。它粗壯的樹幹突兀地聳立在整片樹林之上,像一個光禿禿的圓柱體,直到樹頂才橫生出無數枝幹,在高空中展開成一個完美的樹冠。隔著一哩(可能更遠)的距離,我依然能看見樹枝上形似樹葉或鳥巢的突起。但我知道那不可能是鳥巢,因為大多數鳥只在樹冠內部築巢。這是一棵完美的樹,無與倫比,遺世獨立。
****
當時,我還不知道它叫鷹樹,只知道那是一棵很大很大的樹。
這棵樹實在非同尋常,我一看見它就忍不住想要量一量它的高度。單單是它突出於整片樹林的那一截,就起碼有五十呎。我感到體內有一股欲望在翻騰,就好像從樹根湧上來的汁液,在口腔中迴蕩。
媽媽站在這棵相形見絀的紅雪松下面,大聲喊著我的名字。我沒有聽見,因為她的聲音被風聲和我嘴裡發出來的怪聲蓋過了。我在不由自主地大聲號叫,幾乎能感受到那棵大樹也在歌唱著回應我,它在風中搖擺。
然後,我就知道該怎麼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