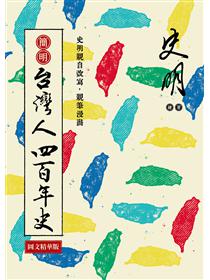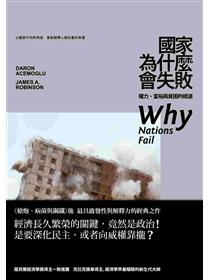撼動歐亞、終結拜占庭千年統治
無法用「民族國家」觀念來理解的龐大帝國――
鄂圖曼帝國=土耳其人統治的土耳其國家?
所謂的鄂圖曼治國體制,與伊斯蘭法有何關聯?
十四世紀初葉,在安納托利亞邊境誕生的小國――奧斯曼公國,發展成覆蓋巴爾幹、安納托利亞、阿拉伯世界、北非的大帝國――鄂圖曼帝國。至十九世紀為止,鄂圖曼帝國在橫跨約五百年的時間,管理多民族與多宗教,實現長期的安定,使得東西文明的界限日趨模糊。爾後,鄂圖曼帝國又延續了近百年,直到一九二二年方才落幕。
本書追溯的是這當中以獨特的治國機制崛起、運作,最終走向衰頹的前近代鄂圖曼帝國的五百年歷史。該機制的特性可稱為「鄂圖曼體制」,如同歐洲蔚成一大體系一般,獨一無二,且在十九世紀前的世界各個角落裡,或許都能找到類似體制的蛛絲馬跡。
■鄂圖曼帝國是專指土耳其人統治的土耳其國家嗎?
鄂圖曼帝國與土耳其共和國的關係究竟為何?
這個問題或許可以改成:「為何土耳其人以外的國家,不被視為鄂圖曼帝國的後裔?」因為巴爾幹至阿拉伯世界的廣大土地上,自鄂圖曼帝國分裂成立的各國,在歷史的某個階段都曾與帝國敵對,並在與其抗爭中建國。所以,巴爾幹或阿拉伯諸國抵死不承認自己是鄂圖曼帝國的後代子孫。此外,在十九、二十世紀的歷史中,許多國家將該國所背負的結構性問題,視為「鄂圖曼帝國的負面遺產」,將責任歸咎於過去的鄂圖曼帝國,從結果來看,也就沒有在主觀上將自己定位成帝國的「後裔」。
鄂圖曼帝國的歷史橫跨著一座分水嶺,十九世紀以前的「不屬於任何人的國家」──鄂圖曼帝國,於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步入遲暮,其後的百年,則是在現代新世界秩序下發展的「近代鄂圖曼帝國」時期。隨著光陰流轉,各民族紛紛自立國家,最後的殘山剩水則構成了「土耳其人的國家」。若細看這段歷史,土耳其共和國繼承鄂圖曼帝國一事,實則為順水推舟,情勢使然。因為到了最後,它的皈依之處就在土耳其共和國。
■「不屬於任何人」的國家之「後裔」――
無法用現代「民族國家」的觀念理解的龐大帝國!
鄂圖曼帝國統合了具有多樣性的人口,帝國內生活模式的特色就是非常無條理;在「文化馬賽克」裡生活的人們,保留各自的宗教、法律、傳統及語言。這幾乎是「民族國家」所無法想像的狀態!
若要刻意質問統治階層的民族歸屬問題,便只能說鄂圖曼帝國是由一群後天取得「奧斯曼人」之自我認同的成員所統治的國家。「奧斯曼人」的圈子裡,包含了現今的塞爾維亞人、希臘人、保加利亞人、波士尼亞人、阿爾巴尼亞人、馬其頓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庫德人、亞美尼亞人、高加索各民族、克里米亞韃靼人等等,其中也有少數的克羅埃西亞人、匈牙利人。總之,追究帝國是由哪一族人統治,在此不具任何意義。
■「鄂圖曼帝國」是像一般人理解的「伊斯蘭帝國」嗎?
伊斯蘭法對帝國的穩定來說,有何重要意義?
的確,鄂圖曼帝國懸掛著伊斯蘭的旗幟,但那頂多是他們「向伊斯蘭致敬」,用來宣揚正義或公正等普世價值及戰場上的勝利。同樣的,基督教徒亦曾經打著宗教的旗號四處征戰,雙方的所作所為如出一轍。在戰爭中,宗教縱然鼓舞了士氣,但這也不過是宗教的「利用方式」之一。
對鄂圖曼帝國而言,利用伊斯蘭法有多重的意義與優點:第一,伊斯蘭法是比鄂圖曼帝國更早建立的法制體系,欣然接納具有威信的制度,有助於統治上的安定。第二,伊斯蘭法極具彈性,所以鄂圖曼帝國中與伊斯蘭法毫無關聯的世俗規範,也能被包容在伊斯蘭法的體系底下。第三,伊斯蘭法揭示了如何統治非穆斯林的原則。
若從這個觀點看來,並非不能稱其為伊斯蘭帝國。但是,我們還是不應忽略鄂圖曼帝國是在利用伊斯蘭教及該法制體系的事實。帝國大大小小的決策都是以「伊斯蘭」為名來執行,重點就在於這「大大小小的決策」究竟所謂何事。恐怕,將鄂圖曼帝國稱呼為伊斯蘭帝國,多半意在模糊這些「大大小小的決策」的內涵。
■柔軟變化的帝國組織與鄂圖曼文化之光
從蘇丹到平民,各有豐富的享樂方式
在梅赫梅德二世、謝利姆一世、蘇雷曼一世等強大的蘇丹統治之下,帝國持續著以大宰相為中心、由官人們支配的漫長時代,在彈性的帝國組織裡,伊斯坦堡文化綻放出鄂圖曼的光芒。
十六世紀以後,隨著各式教育的普及,帝國各地開始出現以鄂圖曼語創作的詩歌,以特定人物為頌揚對象的頌詩比重逐漸加大。頌詩之所以發達,是因為想要晉升為官,檯面下私人交際的非正式社會關係日益重要。
伊斯坦堡中的富裕階層也帶起了各種消費風潮,他們大手筆興建海邊別墅、進口鬱金香和擺設宴席。至於一般民眾不僅關注宏偉建物和皇家宴席,對書籍更表現出高度的熱情,使得興建獨立圖書館比伊斯蘭經學院附屬圖書館更為興盛。十九世紀實用書需求大量增長,印刷術在鄂圖曼帝國扎下根基。之後,印刷術透過行政公文的大量印刷及官報刊行等政府需求而擴大利用,就這樣,印刷技術在鄂圖曼帝國順著社會和文化整體轉變的潮流而逐漸普及。
====================
■《鄂圖曼帝國五百年的和平》能夠帶給台灣讀者什麼啟示?
正因為鄂圖曼帝國的歷史長久以來一直被後繼諸國的民族國家所利用,以圖發展本國的民族主義,所以在這方面我們必須更加小心謹慎。如何使鄂圖曼帝國不受近代民族主義所束縛,以其本身的價值尋求歷史定位,依然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本書的啟示是:
鄂圖曼帝國應被理解為是由一群後天取得「奧斯曼人」之自我認同的成員所統治的國家,而非單純的土耳其或伊斯蘭國家。這和清帝國的「旗人」包括滿蒙漢有相似之處。今天的台灣該如何看待鄂圖曼帝國裡多元族群融合的現象?鄂圖曼帝國以伊斯蘭法同時管束穆斯林與非穆斯林,這其中有何可借鑑之處?都是非常值得深入思考的議題。
====================
■來自日本講談社的全球史鉅獻
《鄂圖曼帝國五百年的和平:跳脫土耳其視角的非伊斯蘭帝國》屬於日本講談社紀念創業一百週年,所出版的「興亡的世界史」套書第11卷。這套書的出版是希望跳脫出既定的西歐中心史觀和中國中心史觀,用更大跨距的歷史之流,尋找歷史的內在動能,思考世界史的興衰。八旗文化引進這套世界史的目的,是本著台灣史就是世界史的概念,從東亞的視角思考自身在世界史中的位置和意義。
◆本書系由21卷構成,陸續出版中――
興亡的世界史──全書系書目
01《人類文明的黎明與黃昏》
青柳正規(東京大學名譽教授)──著
02《亞歷山大的征服與神話》
森谷公俊(帝京大學教授)──著
03《草原王權的誕生》
林 俊雄(創價大學教授)──著
04《迦太基與海上商業帝國》
栗田伸子(東京學藝大學教授)、佐藤育子(日本女子大學學術研究員)──著
05《地中海世界與羅馬帝國》
本村凌二(東京大學名譽教授)──著
06《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
森安孝夫(大阪大學名譽教授)──著
07《伊斯蘭帝國的聖戰》
小杉 泰(京都大學教授)──著
08《凱爾特.最初的歐洲》
原 聖(女子美術大學教授)──著
09《義大利.海洋城市的精神》
陣內秀信(法政大學名譽教授)──著
10《蒙古帝國的漫長遺緒》
杉山正明(京都大學名譽教授)──著
11《鄂圖曼帝國五百年的和平》
林 佳世子(東京外國語大學教授)──著
12《亦近亦遠的東南亞》
石澤良昭(上智大學特任教授)──著
13《印加與西班牙的交錯》
網野徹哉(東京大學教授)──著
14《歐洲霸權的光和影》
福井憲彥(學習院大學名譽教授)──著
15《搖擺於歐亞間的沙皇們》
土肥恆之(一橋大學名譽教授)──著
16《東印度公司與亞洲的海洋》
羽田 正(東京大學教授)──著
17《大英帝國的經驗》
井野瀨久美惠(甲南大學教授)──著
18《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
平野 聰(東京大學教授)──著
19《大日本‧滿洲帝國的遺產》
姜尚中(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玄武岩(北海道大學准教授)──著
20《空中帝國──美國的二十世紀》
生井英考(立教大學教授)──著
21《人類該往何處去?》
大塚柳太郎(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應地利明(京都大學名譽教授)──等著
作者簡介:
林 佳世子
東京外國語大學研究院綜合國際學研究所教授,專長西亞社會史、鄂圖曼王朝史。御茶水女子大學文學教育學部畢業,東京大學研究院人文科學研究科博士班課程中退。著有《奧斯曼帝國的時代》(山川出版社,1997);共編著有The Ottoman State and Societies in Change: A Stud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emettuat Registers (Kegan Paul, 2004)、《記錄與表象:史料訴說的伊斯蘭世界》(東京大學出版會,2005)、《伊斯蘭世界研究手冊》(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8)、《伊斯蘭書籍的歷史》(同前,2014)。
【審訂、導讀者簡介】
林長寬
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專長伊斯蘭文化研究、中東研究、阿拉伯研究。
譯者簡介:
林姿呈
台灣大學日語系畢業,專職譯者。內容力有限公司特約譯者。譯作有《日本神社的開運御神籤集籤指南!》、《數位藝術家的素描簿vol.1:人體結構篇》。
章節試閱
〈奪得君士坦丁堡與梅赫梅德二世的征服〉
◎蘇丹執政時代的開始
自一四五一年梅赫梅德二世即位開始,先後歷經巴耶濟德二世、謝利姆一世、蘇雷曼一世統治,長達百年。在這百年之間,鄂圖曼帝國創下前所未有的巨大戰功,領土的擴張遠遠超過全面施行分封制的「本土」。本書將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介紹這四位蘇丹的時代。
四名蘇丹雖然個性截然不同,但都具備獨特的領導能力,在各自在位的年代獨領風騷。支撐四名蘇丹成功背後的力量,是早從一百五十年以前便不間斷培育累積下來、鄂圖曼帝國特有的征服與統治體制。前頭有西帕希騎兵隊與「蘇丹僕人」構成的常備軍擔任軍事的先鋒部隊活躍沙場,後勤有漸趨完善的行政司法制度。於是,鄂圖曼帝國利用在統合巴爾幹過程中所磨練出來的治理技巧,成功地將勢力擴大到涵蓋安那托利亞中部與東部的廣大土地。
四名蘇丹的治理體系朝向中央集權的方向前進,並不斷提高集權統治操作上的精度。統治手法採成文法,頒布法令,形成規範,延續後世。國力的提升成為戰場上勝利的保證,戰利品及稅收的增加充實國庫營收,給予蘇丹足夠的財政餘力,替下一場征服投注糧餉資金。鄂圖曼帝國的特徵,就在於這個以不斷征戰四方的蘇丹為核心的中央集權體制。
然而,中央集權卻也伴隨著各種副作用,而且在安那托利亞尤為顯著。前章描述的百年之中,多瑙河至巴爾幹地區大抵上都被統合在鄂圖曼體制底下。然而,安那托利亞的整合作業,卻是到十五世紀中葉以後才開始。鄂圖曼帝國常被世人誤認是「土耳其人」的國家,但是十六世紀最讓帝國焦頭爛額的問題之一,便是安那托利亞的突厥裔遊牧民。蘇丹的盛世是由華麗的戰功交織而成,同時也是與安那托利亞「突厥人」纏鬥不休的年代。
◎圍攻君士坦丁堡
驍勇善戰的蘇丹時代,以征服君士坦丁堡這件歷史重大事件揭開序幕。如前所述,拜占庭皇帝的勢力衰弱,當時他能統治的範圍僅限於一座城市的君士坦丁堡。然而,千年之都的光輝,總讓拜占庭人民期待著奇蹟發生,同時也能對入侵的敵人產生無形的心理壓力。最後,打破僵局的是剛即位不久的青年梅赫梅德二世。
一四五一年二度登基的梅赫梅德二世首先打點好周邊國家,在整頓好體制後,於博斯普魯斯海峽最狹窄的地方築城,準備圍攻君士坦丁堡。新要塞的對岸,是以前巴耶濟德一世包圍君士坦丁堡時,花了八年的時間所建立的堡壘(安那托利城堡[Anadoluhisarı]),藉此從兩邊夾擊威尼斯來自黑海沿岸殖民城市的援軍,創造對自己有利的形勢。威尼斯人是拜占庭帝國的最大的靠山,對梅赫梅德二世而言,威尼斯人的援軍是這場戰役最大的不確定因素。拜占庭帝國本身只有五千人左右的舊制軍隊,其防衛全仰賴威尼斯及熱內亞派遣的援軍、少許的傭兵以及市民的協力合作。
這是繼巴耶濟德一世、穆拉德二世之後,鄂圖曼勢力第三次圍攻君士坦丁堡。以往巴耶濟德一世採取鬆散的圍城戰術,原來預計以杜絕糧餉的策略進攻,卻出乎意料形成拉鋸戰,終告失敗。巴耶濟德一世沒有料到,君士坦丁堡腹地遼闊,足以負擔長期戒嚴的守城防衛,而且正因其規模龐大,很難從外圍滴水不漏地長期封鎖整座城市。
梅赫梅德二世記取前人教訓,決定速戰速決,擬出短期內拿下該城的作戰計劃。他特別聘用匈牙利技師製造大砲,以巨型大砲及其他最新兵器集中火力攻打陸地上的城牆,再配合十萬(也有人說是十六萬)對上至多八、九千的兵力優勢,兩者實力的差距有如雲泥。
開戰後不久,梅赫梅德二世發現自己的海軍戰力遠不及威尼斯,於是立刻放棄海戰,將海軍部隊拉上陸地,想出了橫越後方丘陵將船隻藏入金角灣內的奇計。當時金角灣的入口處早已加上鎖鏈,用來防止外敵進入灣內。這場征服戰,鄂圖曼帝國從陸海包夾,可說是一場不惜人力財力,勞師動眾的總體戰。梅赫梅德二世的親信之中有不少人持反對意見,因為一旦失敗,極有可能讓蘇丹的權威顏面盡失。但是對於擔任作戰總指揮的梅赫梅德二世而言,這是一場攸關生死的世紀決戰。
◎君士坦丁堡淪陷之日
正因如此,這場戰役的勝利對梅赫梅德二世來說,可謂意義非凡。圍城的第五十天,一四五三年五月二十九日,鄂圖曼軍於黎明前發動最後一次攻擊,軍隊蜂擁入城,拜占庭帝國亦在同一天迎來了末日。據傳,拜占庭皇帝雖然戰死,但始終找無屍首。從此以後,梅赫梅德二世被冠上「征服之父」的稱號,這場戰役的功績,成為日後梅赫梅德二世日後實行集權統治的權力基礎。
有不少義大利及拜占庭文人、鄂圖曼人士參與圍城戰,並記錄戰事發展,因此我們才能熟知關於圍城戰的細節。儘管如此,過程中還是有諸多不明之處,譬如城內街道所受的損壞程度情況不詳,關於攻陷後遭受鄂圖曼士兵肆虐行搶的天數,各種史料記載也互有出入。伊斯蘭法雖然容許士兵有權在三日內於攻陷的城內大肆搜刮掠奪,但據筆者合理的推斷,搶奪應該在一日之內就草草結束。畢竟,雖然史料記載有些地方情況慘烈,但還是有許多建築物毫無損傷,免於遭到拘捕的居民人數也不少,不過那是因為他們投靠在鄂圖曼帝國的保護傘下。另外,諸多歷史資料也都提及梅赫梅德二世不願城內遭到破壞,希望能將受損程度壓至最低。據悉,梅赫梅德二世厚待屬於他(蘇丹)的俘虜,尤其是那些拜占庭的貴族,他甚至還自掏腰包,幫受俘的貴族們支付贖金,還其自由之身。
梅赫梅德二世攻入城內後不久,隨即巡視聖索菲亞教堂,將此地改為清真寺。此外在征服後,梅赫梅德二世立刻將城內重要的教會及修道院改為穆斯林所用,作為復興整建的核心據點。這當中包括遺留至今的卡朗德哈等舊教堂,另外還有一些像阿里斯特醫院這種只能從征服後的鄂圖曼歷史資料中尋得其名的設施。仔細想想,幅員遼闊的君士坦丁堡,不會因為一日的掠奪就被摧殘殆盡,哪怕算進征服之前就已荒廢閒置的區域,鄂圖曼帝國所接手的,應是一座內部大致都還堪用的城市,這種看法應該是比較正確的。
君士坦丁堡淪陷三天後,星期五的禮拜在聖索菲亞清真寺舉行,導師由當時蘇丹的宗教近臣阿克瞻斯丁(Akşemsettin)出任。阿克瞻斯丁來自大馬士革,在圍城戰最激烈時刻「發現」先知穆罕默德的門徒阿尤布(Ayyub;土耳其語讀作「Eyup」)之墓,從而鼓舞了戰士。這個事蹟相當有名,使得鄂圖曼帝國奪得君士坦丁堡的戰果被大肆宣傳為伊斯蘭的勝利,阿克瞻斯丁寫下的勝戰捷報詞藻華麗,甚至流傳到開羅的馬木路克朝宮廷。
◎建設新都
根據帝國的史書記載,梅赫梅德二世在攻打君士坦丁堡時曾宣示:「本王寶座將設在伊斯坦堡」,昭告天下以後將以此地做為帝國首都,並連番提出具體的復興政策。
首先,梅赫梅德二世向避免淪為戰俘之身或是繳納贖金而獲得釋放的希臘居民,保障他們的安全,承諾他們可以維持舊有的「傳統與宗教信仰」。另外,對於僑居在伊斯坦堡的加拉達(Galata)地區的熱內亞商人,也擔保他們的人身安全與買賣通行自由。
另一方面,梅赫梅德二世為了振興城市,將市內建築物賜予直接參加征戰及有所貢獻之人──包含軍人、宗教學者、蘇菲教團團員等──作為生活起居使用。查看各家記錄可以發現,在取得伊斯坦堡市內不動產作為軍功獎賞的名單中,可見對征戰貢獻良多的巨砲製作家――匈牙利人烏爾班(Orban),以及第一章中所介紹的編年史作者――阿許帕夏扎德等人名。另外,梅赫梅德二世還派遣使者到帝國各地,招募願意遷居到首都的自願民眾。
然而招募移居的效果不彰,梅赫梅德二世見狀,從帝國統治下的各城邦或爾後戰勝的征服地,挑選富裕的商人及工匠,強制遣送伊斯坦堡。然而這項政策在各地卻引發了相當大的混亂。
至於復興首都建築的部分,戰爭後的第一件事,便是即刻整修城牆及興建新堡壘(耶迪庫勒[Yedikule]堡)以加強防備,預防十字軍的來襲。然而十字軍未曾現身,堅固的堡壘在此之後也無用武之地。
梅赫梅德二世於一四五七年左右,開始親自操持首都大型市集及驛站的建設,讓移居至此的商人及工匠得以在城內經商買賣;並根據伊斯蘭世界的商業習慣,將這些商辦承租給商人或工匠。由於梅赫梅德二世已事先將這些商業設施以宗教捐獻的名義贈與聖索菲亞清真寺,所以商人工匠所繳納的租金成了維持宗教設施的管理經費,此項措舉稱為宗教基金管理(vakıf)制度。
梅赫梅德二世更在其統治的後半期,拆除已成廢墟的拜占庭帝國聖使徒教堂,興建一座宏偉的清真寺――即著名的法提赫清真寺(Fatih Mosque)。聖使徒教堂為拜占庭歷代皇帝陵寢所在,梅赫梅德二世在象徵拜占庭王權之地建造象徵鄂圖曼王室權力的「征服者清真寺」――法提赫清真寺絕非偶然,想必這些行為產生的效果,早就經過他縝密的計算了。
梅赫梅德二世不僅親自下令建造清真寺,更命令手下親信軍官按照自己的財力,於都內要衝興建清真寺等建築。這些新建的清真寺地點不若法提赫清真寺顯眼,規模也比法提赫清真寺小一圈。以蘇丹為首,君臨天下的權力層級特性也同樣反映在建築上。
據悉,透過這些由蘇丹主導的建設及前述的人口政策,使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堡)在易主之後三十年內,人口恢復至約十萬人,其中約有四成是希臘正教徒、亞美尼亞教徒、猶太教徒。雖然換個角度來看,可以說「被征服以前幾乎不見蹤影的穆斯林人口迅速攀升至六成」,但在新的住民之中,還是有許多為非穆斯林。由此可知,鄂圖曼帝國統治後的復興,是以不問宗教並積極接納富商、工匠的形式來進行。自此之後,伊斯坦堡內穆斯林占六成,非穆斯林占四成的人口這樣的比例,直到進入二十世紀為止沒有太大的變動。
◎「被詛咒的伊斯坦堡」
雖然,若是從鄂圖曼帝國版圖橫跨巴爾幹及安那托利亞地區的角度來看,以伊斯坦堡為首都的決定看似順理成章。然而這在當時,似乎並非那麼理所當然。
因為在帝國裡有著一群不願在首都安居樂業的人們,這些人大多是以輕騎兵之姿在國界一帶活動的自由騎士。雖然他們名列在編入西帕希騎兵受封的名單上,但比起「蘇丹僕人」所構成的常備軍士兵或蘇丹親信團,他們更希望維持自己的獨立性,並且衷心期盼屬於他們舞台的戰爭得以持續進行下去。他們在伊斯蘭信仰中屬於異端分子,並鼓吹「聖戰」的輕騎兵精神,引起許多西帕希騎兵的共鳴。他們在征服君士坦丁堡的過程中付出心血,也共同歡慶征服的勝利和喜悅。但這些人殷殷盼望的,不是蘇丹在這場征服之後停下腳步安於現況,而是以舊都愛第尼為據點,不斷向西進軍。這種「反伊斯坦堡」情感的背後,普遍帶有不願就此承認鄂圖曼已經成為一大「帝國」,以及蘇丹仗著巨大的權威,束縛了他們的一種反抗情緒。
在這群與首都水火不容的人們之間,梅赫梅德二世的三名王子中,傑姆(Cem)最受歡迎。傑姆下令編纂的英雄傳說《薩勒圖革之書》(音譯)裡,反覆出現鄂圖曼帝國之都應為愛第尼,以及伊斯坦堡是不祥之都的論調。甚至在梅赫梅德二世時期便廣為流傳的「伊斯坦堡與聖索菲亞的傳說」中還指出,這座城市存在著災難的循環,並被日後多種鄂圖曼編年史引用。這個傳說中還暗中批判了梅赫梅德二世欲成就帝國霸業的野心,藉由羅馬王儲遭遇不幸的故事,描述人民對於滯留此地的不安,文中說到「伊斯坦堡是一座不斷被征服的不祥之都」,指出梅赫梅德二世為了重建首都只是濫用公帑,並以失敗為由處死替他監工建造清真寺的建築師等事實,作為不祥之兆。
對於今日親眼見證了伊斯坦堡榮景的人來說,這樣的反應想必令人感到難以理解吧。不過,就像蘇丹在伊斯坦堡打造的新宮殿一樣,對當時的人們來說,新時代的到來,總讓人有格格不入之感。後世稱為托卡比皇宮的新宮殿四周被高聳的城牆包圍,開放給民眾入內禮拜的空間僅有一小部分,至高無上的蘇丹可不是任何人想見就能見到的。然而,成為君士坦丁堡征服者的梅赫梅德二世,以高壓手段壓制這些騎士的不滿,任命新軍等「蘇丹僕人」擔任軍隊的骨幹,在之後的三十年間,隨其東征西討。
◎梅赫梅德二世的三十年征戰
梅赫梅德二世奪得君士坦丁堡後的三十年間,多在馬背上度過,他親自率領的遠征次數就達十八次之多。從征戰次數可以推測,多在夏季舉行的遠征,已經成為每年的例行公事。
梅赫梅德二世的目標,多半鎖定在從伊斯坦堡出發、可在一場夏季遠征抵達的範圍內。統治前期,帝國三番兩次遠征巴爾幹的塞爾維亞及希臘(色雷斯、愛琴海、伯羅奔尼薩半島)、波士尼亞等地,安那托利亞方面則主攻翠比松王國、卡拉曼公國。到了統治後期,主要面臨烏尊哈桑(Uzun Ḥasan)率領的白羊王朝和威尼斯的攻防戰。威尼斯、匈牙利與白羊王朝之間締結盟約,共同對抗鄂圖曼,因此鄂圖曼在各地的征戰都得透過充分評估國際情勢,步步為營才行。梅赫梅德二世無疑是一名兼具戰略家的才能及果敢判斷力的優秀指揮官。
儘管如此,戰爭不可能永遠百戰百勝。匈牙利軍的統領匈雅提.亞諾什手中的貝爾格勒難以攻陷,梅赫梅德二世始終未能拿下它。另外,梅赫梅德二世雖然征服翠比松王國,但是這場安那托利亞的遠征卻困難重重,最後還是靠給予新軍部屬特別的獎勵金,才勉強提振軍心返回首都。至於瓦拉幾亞(今:羅馬尼亞)的弗拉德大公(Vlad)與占據阿爾巴尼亞山區的斯坎德培,最終雖然都遭到梅赫梅德二世的驅逐,但由於他們的激烈抵抗,導致梅赫梅德二世對這兩地至多只能做到間接支配而已。此外,鄂圖曼的海軍戰力依舊不敵威尼斯等歐洲國家,這也是造成鄂圖曼與威尼斯之間演變成拉鋸戰,且未能從聖若翰騎士團手中奪得羅德島(Rhodes)的失敗主因。
但在經過三十年的征戰後,多瑙河至幼發拉底河中間這一大片區域,除了島嶼以外,幾乎全數納入了鄂圖曼帝國的版圖。梅赫梅德二世征服活動的本質,在於強勢肅清及整治這片廣大土地上零星散布的半獨立藩屬國,以及義大利諸邦的統治區,並將多數地區劃為直轄地,主動進攻、牽制那些隱身在小國背後的反抗勢力,藉以鞏固鄂圖曼帝國的「本土」區域。之後逐一在新征服地進行稅收調查,實施分封制。梅赫梅德二世直接統治的地區在十九世紀以前,大部分依舊歸屬在鄂圖曼帝國之下。
在海上,鄂圖曼也開拓出屬於自己的海域。梅赫梅德二世派遣艦隊直驅黑海北岸,將熱內亞及威尼斯的勢力逐出克里米亞半島及其鄰近海域,同時趁著克里米亞汗國發生王位爭奪的時機,逼迫其承認鄂圖曼帝國的宗主權。如此一來,黑海成為對鄂圖曼帝國而言相對安全的內海。
在這場三十年征服的過程中,塞爾維亞、波士尼亞、安那托利亞中屬於拜占庭皇室一派的翠比松王國,以及長年敵對的卡拉曼公國等國家相繼滅亡。隨著這些緩衝國的消逝,鄂圖曼帝國面臨與匈牙利背後的哈布斯堡家族,以及在埃及和敘利亞的馬木路克朝直接對峙的局面。於此同時,梅赫梅德更將遠征的目標指向伊朗及伊拉克。於是帝國與實力曾和帖木兒汗國不相上下的白羊王朝之間的抗爭,最終演變成鄂圖曼與白羊王朝的繼承國──薩法維朝──之間的敵對關係而延續下去。
(本文節錄自:第三章「蘇丹的軍旗下」)
〈奪得君士坦丁堡與梅赫梅德二世的征服〉
◎蘇丹執政時代的開始
自一四五一年梅赫梅德二世即位開始,先後歷經巴耶濟德二世、謝利姆一世、蘇雷曼一世統治,長達百年。在這百年之間,鄂圖曼帝國創下前所未有的巨大戰功,領土的擴張遠遠超過全面施行分封制的「本土」。本書將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介紹這四位蘇丹的時代。
四名蘇丹雖然個性截然不同,但都具備獨特的領導能力,在各自在位的年代獨領風騷。支撐四名蘇丹成功背後的力量,是早從一百五十年以前便不間斷培育累積下來、鄂圖曼帝國特有的征服與統治體制。前頭有西帕希騎兵隊與「...
推薦序
「近東病夫」知多少?──理解歐斯曼帝國本質
文/林長寬(國立成功大學多元文化研究中心召集人)
伊斯蘭近現代歷史中有三個西方學界所稱的「火藥帝國」(Gunpowder Empire),即歐斯曼帝國(the Osmanlıs, Ottomans, 1281-1924)(註001)、薩法維帝國(the Ṣafāwids, 1501-1722)、蒙兀兒帝國(the Mughals, 1526-1858);其中以歐斯曼帝國的帝祚最長,超過六個世紀的統治對伊斯蘭世界宗教文化之發展留下不可抹滅的印象,豐富且具多元性的輝煌文明更可謂伊斯蘭世界的代表,其融合古典伊斯蘭與拜占庭兩文明遺緒的內涵也對人類現代文明的發展有不容忽視的影響。撰寫一部歐斯曼帝國的歷史相當不容易,因為帝國從部族結構的公國(Emirate)發展成跨歐亞非「政教合一」的大帝國(Caliphate),不僅縱橫了伊斯蘭世界,更與歐洲基督教世界有相當的互動與交流關係;歐斯曼帝國境內多民族的子民,更在伊斯蘭發展史上扮演了「伊斯蘭多元化」的貢獻角色。
西方歷史學者往往視歐斯曼帝國為歐洲外在的大威脅,意謂伊斯蘭世界中第三波突厥人(Türk)勢力對基督教國家的抗戰;而就伊斯蘭歷史而言,歐斯曼帝國則象徵伊斯蘭世界第二波的政治與文化成就。歐斯曼突厥人(Osmani Türk)滅掉拜占庭帝國後,承繼其遺緒,成為地中海地區文明發展重要主角之一;然而阿拉伯歷史學者則未必認同歐斯曼人在伊斯蘭的正統性,一般仍視之為「阿拉伯伊斯蘭境域」(Arabo-Islamic Abode)的外來入侵者。當然,這主要原因是,原本阿拉伯人所主導的伊斯蘭哈里發政權被蒙古人滅掉後,突厥人取而代之,成為伊斯蘭中土(Central Lands of Islam)的主要統治者;而歐斯曼突厥人更統治了阿拉伯世界(北非、埃及、大敘利亞地區、巴勒斯坦、伊拉克、阿拉伯半島的漢志[al-Hijāz])長達三、四個世紀之久。
中世紀時,突厥人被從中亞引進阿拉伯伊斯蘭帝國內充當作傭兵(Mamlūk)後,遂被迫阿拉伯化(Arabization),之後突厥人成為伊斯蘭舞台的導演,阿拉伯人則被迫「歐斯曼化」(Osmanlization),去認同伊斯蘭文化中的突厥元素。而事實上,歐斯曼突厥人在後阿巴斯朝時期(post-‘Abbāsid period)整合了突厥、波斯、阿拉伯伊斯蘭文化與政治體制,將之帶入安那托利亞高原地區與東南歐的巴爾幹半島。歐斯曼人之所以成功,事實上是奠基於良好的領導術、健全政經體制的發展、軍事組織的制度化;基於此,歐斯曼突厥人整合併吞了後阿巴斯朝時期積弱不振的地方政權,轉化成一個與歐洲、地中海地區經濟發展有密切關係的帝國。
歐斯曼帝國興起的背景,一般研究主張源自於Ghāzī(戰士)部族軍團,而這些Ghāzī所主導的軍事活動被一些學者解讀成Jihād(聖戰)活動,因為通常征戰往往打著Jihād fī Sabīlillāh(在阿拉的道上奮戰)口號。事實上,就早期史料解讀之,Ghazāh(軍事掠奪)活動並非純以伊斯蘭之名的「聖戰」,實質是部族勢力擴張的政治活動。無可否認,歐斯曼公國初期政權建立的模式與阿巴斯朝地方軍人政權模式大同小異,亦即突厥部族進入伊斯蘭帝國後由戰俘(或被販賣)轉化為哈里發的禁衛軍,茁壯後被哈里發授權封為地方統治者──蘇丹(Sulṭān);換言之,突厥游牧部族被中央統治者組成傭兵團(mercenary),繼而發展成地方軍閥政權
基本上,歐斯曼政權的運作是軍人當家贊助(military patronage)的政體。整個政府機器、行政系統、軍隊,甚至宗教機構皆以軍人權力為依據或後盾。歐斯曼統治者自稱為Askari,即是「軍人」之意;而被統治的人民則稱為Raya(被蓄牧者)。兩者的關係乃「收稅者」與「納稅者」,此關係則由所謂「正義圈」(Circle of Justice)來界定;而「正義圈」事實上是地方軍人與官僚,其本質亦是「稅收享受者」,有中介橋樑性質。
宗教社群是研究歐斯曼帝國歷史的一個重要議題,帝國宗教政策有承襲,也有創新。歐斯曼帝國內的子民有相當比例是非穆斯林,即所謂的Dhimmi(註002),這些非穆斯林的社群稱為millet(community)。Millet一詞源自於阿拉伯文的Millah,意指「宗教社群」,此名詞可能引用自亞美尼亞文(Aramaic),此詞在古蘭經文亦指「信仰族群」;至於在波斯文中其意義則稍有轉變,指稱「國家─群體」。歐斯曼帝國的Millet用詞有三種意涵,主要是界定宗教與政治的關係,比古蘭經文中的用法更有應用性。(註003)帝國境內的Millet屬於宗教自治社群,有自己的領導者、適用的民法、宗教法、社會福利法,以及教育制度等。除了順尼穆斯林(Sunni Muslim)社群外,帝國官方承認的Millet有希臘東政教(Greek Orthodox)、亞美尼亞教會(Armenian Church)、猶太教(Judaism)。雖然帝國境內有不少天主教徒,但蘇丹卻將他們併入亞美尼亞教會社群管理之,其原因可能是歐洲天主教會與歐斯曼帝國之間長期的敵對狀態所致。
歐斯曼突厥人在建立政權前,其經濟資源基本上是依賴軍事活動的征服掠奪。帝國建立後,經濟資源的生產逐漸轉向農業與貿易。帝國古都Busra一直是絲路貿易的終點站,該城市更是中東地區絲綢的集散地,至今依然保留了絲綢工業與貿易傳統。經由帝國不斷地擴張,一些國際貿易路線上的中心城市、港口也逐漸納入帝國的控制。到了十五世紀時,黑海與地中海沿岸地區的經貿完全由歐斯曼人主宰。後來印度洋與地中海之間、幼發拉底河與紅海之間的貿易更為帝國所控制。在農業方面,安納托利亞高原地區與歐洲的農產品成為帝國進出口的生活必需品。農業與經貿發展的結果使得歐斯曼帝國脫離傳統的游牧性國家結構,進而創造出輝煌的伊斯蘭城市化文明;而且也由於經貿路線的控制,致使帝國更積極地往外擴張,以取得農業用地。
歐斯曼帝國統治時期相當長,一般研究將歐斯曼帝國歷史分成前、後兩時期:建國至巔峰時期、衰微時期。而事實上,前半期的歷史可細分為五個階段,即(一)早期Osman I的出現到Gallipoli的佔領(1300-1350),這時期已與歐洲有所接觸;(二)與帖木兒帝國西征的衝突後五十年(1355-1402);(三)透過Mehmed II的復興時期(1403-1451);(四)帝國的鞏固與歐洲哈布斯堡王國的長期作戰(1451-1593);(五)帝國的轉型至衰微走向(1593-1730)。1730年之後,歐斯曼帝國的發展幾乎已無動力可言,國家機器停頓,同時也必須面對歐洲殖民帝國主義勢力東進的挑戰。這期間蘇丹試圖改革、歐化,但似乎已無能為力,對外屢戰屢敗而被稱為「近東病夫」(the Sick Man of Near East),與「東亞病夫」(the Sick Man of East Asia)的清帝國相對應。
歐斯曼帝國統治的理念一般認為是以伊斯蘭教義為基礎,統治者自認為神的僕人(‘Abd),也是今世(Dunya)的主人,其所使用的尊稱Ṣāḥib al-Qirān (Lord of Auspicious Conjunction)即可證明。當歐斯曼人於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時,即宣稱承繼了拜占庭帝國之地位,而在1517年打敗埃及的Mamluk政權時,更宣示其承繼阿巴斯朝哈里發的志業。無可否認地,十五、十六世紀之間的歐斯曼帝國是世界超強勢力。
宣稱是真主僕人的歐斯曼蘇丹,歷代君主的治國理念基本上有六要素:邊界戰士本質(Frontier Ghāzī)、伊朗式伊斯蘭鬥士性格(Irano-Islamic Warrior)、突厥─蒙古模式(Turko-Mongal)、拜占庭體制(Roman)、千禧救贖觀(Millenarian),以及伊朗式伊斯蘭定居文明內涵(Sedentary Irano-Islamic)等性質。這些元素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轉變。從第一階段的邊境戰士轉到第二階段的蘇非(Ṣūfī)戰士,實乃蘇非主義及道團(Ṭarīqah)宣教的結果,而歐斯曼君主通常都有一至多位的蘇非修士導師(Shaykh, Pīr)伴隨他征戰,並指導國家運作的政策。在第三階段實是隨著與帖木兒帝國(Timürate)的接觸與蒙古人西征結果,原先波斯的體制中納入蒙古─突厥元素,這是一次大整合。之後打敗了拜占庭,更納入羅馬的政治、文化理念。當歐斯曼人進入中東的阿拉伯世界後,則承繼了之前的波斯伊斯蘭帝國架構而轉入定居的農業社會;也因為如此的轉變,以前游牧部族的機動力逐漸降低,無法再進行大規模的領土擴張。此時儼然成為平和穩定的世界性大帝國,雖然有薩法維帝國擋道而無法再向東前進,但此時帝國的規模與之前的阿巴斯朝有過之而無不及,甚至更勝於波斯的薩法維帝國與印度的蒙兀兒帝國。
相較於其他兩個火藥帝國,歐斯曼帝國任用了相當多的基督宗教徒、猶太教徒於朝廷的重要職位。歐斯曼人自認為這種包容的態度是在宣揚先知穆罕默德的理念──先知穆罕默德在麥地那建立伊斯蘭社群(Ummah)時,其成員亦包含了猶太教徒與基督宗教徒。伊斯蘭前的一神信仰價值觀與基本教義被吸納入伊斯蘭,其中的密契主義與伊斯蘭的社會改革理念結合發展,成了所謂千禧年救贖的教義。歐斯曼帝國朝廷重用基督教徒,顯示出在「腐敗」的基督宗教世界,突厥人的帶來伊斯蘭教義無異是一種救贖。後來歐斯曼人進入中歐、東南歐、東歐等地區,對某些受壓制的基督宗教徒與猶太教徒而言,這些活動被詮釋成一種具解放的意涵。而在十字軍東征延續的過程中,神聖羅馬帝國與歐斯曼帝國領導者堅持自己的對外活動標榜乃「救贖」與「解放」,就連遠在東邊的薩法維帝國君王與其他基督宗教王國統治者也是如此。
歐斯曼蘇丹自稱為順尼伊斯蘭(Sunnī Islām)的捍衛者,因此宗教學者(‘Ulamā’)在帝國的宗教律法發展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為了使宗教學者能夠發揮極致功能,蘇丹朝廷設置了「Shaykh al-Islām」的職位,掌管全國的伊斯蘭事務,這可謂將宗教學者階層實質地體制化,超越之前的統治政體;相較下,這也勝於薩法維與蒙兀兒帝國在伊斯蘭事務的推動。基於對伊斯蘭的推廣,歐斯曼帝國早期即已成立Ilmiye(學院),詳細規劃Mudrasah經學教育。在Shaykh al-Islām的體制下設有二位Qāzī-Askar (army judges),其下在多個重要城市中設置都會級Qāzī。Shaykh al-Islām成員擁有司法與立法權力,與哈里發的世俗行政權相輔相成。這使得伊斯蘭價值與道德觀至今屹立不搖,即使土耳其共和國建立後採納政教分離世俗化體制,伊斯蘭對穆斯林社會生活的影響依然很大。由於伊斯蘭司法、立法體制需要相當多的專業人才運作,因此伊斯蘭經學院的教學與清真寺功能緊密結合,形成一個由中央到地方省分嚴謹的階層與網路。這種嚴謹結構是前所未有的創置,落實了伊斯蘭治國的精神。
承繼先前中世紀伊斯蘭輝煌文明,歐斯曼帝國更開啟了精緻的融合文明與深度內涵的文化。歐斯曼帝國在文學、伊斯蘭學科、建築藝術、繪畫與音樂皆有相當的成就,歐洲人為之欣羨與眼紅。從Hagia Sophia到Fatıh Jami, Sulaymaniyyah以及Blue Mosque等,清真寺建築顯示歐斯曼人善加利用拜占廷建築藝術的精華於伊斯蘭神聖空間的建構;而不少清真寺的設計者更是基督教徒,如Sinan(c.1489-1588),這突顯歐斯曼統治者的開放胸襟。比起阿拉伯穆斯林所建構的宗教神聖空間,歐斯曼人的宗教態度是理性的,心懷自由主義。也因為承繼阿巴斯朝後期的古典文學遺緒,歐斯曼人在使用波斯文與阿拉伯文於文學創作與宗教典籍編撰上,更勝非突厥裔的穆斯林。直到帝國中期之後,民間開始使用歐斯曼突厥文於文學與宗教上,才引發中央政權提倡以經過阿拉伯化、波斯化的突厥語文作為官方語言,並以阿拉伯文字母為書寫工具,即所謂的「歐斯曼突厥語文」(Osmani Turkish),直到土耳其共和國建立後,官方採用拉丁文字母取代阿拉伯文字母。這種與過去文化傳統切割的行徑導致當今土耳其文化與伊斯蘭歷史的斷裂,這也是共和國世俗化政權所造成的傷害。
整體而言,歐斯曼帝國歷史起自於邊界地區的征戰軍團,建國後吸取拜占庭文明的精華,從而將阿巴斯朝的伊斯蘭帝國體制發揮淋漓盡致。歐斯曼朝之所以被稱為火藥帝國,主要原因是整個帝國的運作以軍事擴張為主軸,而大多數前半期的君主皆兼具軍人身份;換言之,伊斯蘭宗教學者與官僚體制大臣合力鞏固軍人君王贊助的文化、政治、經濟活動。因此歐斯曼帝國可謂繼先知、正統哈里發統治之後,伊斯蘭文明一千四百年發展的具體成果。
西方學界對歐斯曼帝國的研究相當豐富,特別是歐陸方面,因為歐洲人與歐斯曼人的競爭、衝突、交流從十四世紀初即開始。換言之,歐斯曼帝國代表伊斯蘭世界與歐洲基督教世界進行源遠流長的碰撞,這期間更是經歷了十字軍東征所造成的漫長衝突;而在衝突、競爭的過程中,歐洲人與歐斯曼人皆從對方學習吸取了文化與文明精華。雖然中古歐洲基督宗教徒因為信仰關係,對歐斯曼帝國與其伊斯蘭做了相當多的研究與報導,卻總不免以負面的觀點批判之;相反地,作為伊斯蘭捍衛者的歐斯曼人,對歐洲的基督宗教並無多大興趣,往往以強調穆斯林是獨一神代理者的優越感與立場去看待歐洲的基督宗教。所謂「知己知彼必勝」,歐斯曼人「知己卻未知彼」,因此十七世紀後逐漸被歐洲的基督宗教徒超越,導致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造成帝國瓦解,其統治的阿拉伯子民亦脫離伊斯坦堡政權,獨立建國。可笑的是,至今土耳其人仍瞧不起阿拉伯人,覺得他們沒有資格宣稱是伊斯蘭捍衛者;而阿拉伯人也自視為先知繼承者(種族連結),強調他們才是伊斯蘭的真正代言人。阿拉伯人與土耳其人的衝突全是歐洲民族主義負面影響所帶來的結果。
歐斯曼帝國歷史是世界史重要的一環,是作為現代世界公民必須瞭解的歷史,而且歐斯曼帝國伊斯蘭的多元性更是今日進行宗教文化對話時所應思及的。然而,台灣有關歐斯曼帝國的書籍寥寥可數,即使有,也大多是翻譯自外文。這顯示台灣學界對歐斯曼帝國的歷史文化是相當陌生的,至今似乎未有系統性的研究成果。(註004)其實中華民國在未跟土耳其共和國斷交前,兩國關係友善密切,有相當程度的交流;而且自視為伊斯蘭捍衛者的歐斯曼蘇丹對滿清末年中國地區(Çina)伊斯蘭的發展相當關注,曾派遣宗教學者到北京牛街清真寺教授伊斯蘭,並贈送大量伊斯蘭典籍,這是有歷史資料佐證的。
相較於台灣,日本對歐斯曼帝國的研究已有相當的基礎,其政府與私人部門在這方面有不少資源的投注,當然這與日本政府的中東政策有關。日本在「中東研究」的推動已趕上歐洲腳步,培養了不少國際學者,其鄰居韓國也開始跟進,這是台灣政府相關部門應該省思的。東京外國語大學的林佳世子教授所撰寫的《歐斯曼(鄂圖曼)帝國五百年的和平》,可謂一本「歐斯曼帝國史綱」,論述觸及各層面的議題。雖然內容言簡意賅,但卻具歷史的完整性,是一本易讀的「入門書」。然而,若對中東或伊斯蘭史背景不熟悉者,則需有相關的資料輔助,方能對此書有全盤的理解。這本書試圖提出新的詮釋,對西方學界傳統的歐斯曼史觀提出質疑。作者提出一個議題讓讀者思考:如何正確地認識歐斯曼帝國,換言之,不能以早期西方學界東方學(Orientalism)的刻板理論去解讀歐斯曼帝國史。簡言之,這一本歐斯曼帝國史綱值得國人細讀之。
@註001:
究竟此帝國之名稱在中文如何音譯呢?早期在台灣的教科書翻譯為「鄂圖曼」,這是從英文的Ottoman音譯而來;而Ottoman一詞則是由阿拉伯文的‘Uthamān拉丁化而成。事實上,突厥人將阿拉伯文的‘Uthamān轉成Osman,因為突厥人無法將阿拉伯文的ﺙ(th)與ﻉ(cain)兩個字母做正確發音。因此較接近原文的音譯應該是「歐斯曼」,而不是台灣或中國兩地所音譯的「鄂圖曼」、「奧斯曼」或「奧圖曼」。這種例子如同阿拉伯國家的‘Umān(Oman)被中國人音譯成「阿曼」,而不是較接近原音的「歐曼」。事實上,台灣早期的外交部與高中教科書使用「歐曼」稱‘Umān。
@註002:
Dhimmi的阿拉伯文(或歐斯曼突厥文)原意是「受保護者」,指的是「有經書的信仰者」(People of the Book[Scripture]),意為「一神信仰者」,主要是猶太教徒、基督宗教徒、祆教徒等。Dhimmi通常要繳Jizya(人丁稅),以享受宗教自治與社群權益。
@註003:
參閱:M. O. H. Ursinus, “Millet,” The Encyclopedia of Islam, new ed. Vol. VII, Leiden: Brill, 1993, pp. 61-64.
@註004:
台灣國人每年到土耳其旅遊的人相當多,除了吃喝玩樂之外,行了一趟土耳其之旅後,對其文化與文明又理解多少呢?若檢視高中教科書對歐斯曼帝國歷史描述的篇幅,即可得知為何台灣人民對歐斯曼帝國歷史文化的理解是相當有限的。為何台灣的大學中缺乏歐斯曼帝國的研究與教學呢?一般大學所教授的「世界史」主要是在講「西洋史」,即歐美史。高中歷史教科書更分為「台灣史」、「中國史」與「世界史」編撰,實在令人納悶!難道「中國」、「台灣」不存在「世界」中嗎?「台灣史」、「中國史」的編撰絕不能脫離「世界史」或「全球史」的架構。這一點日本、歐美史學界早已認知到。
「近東病夫」知多少?──理解歐斯曼帝國本質
文/林長寬(國立成功大學多元文化研究中心召集人)
伊斯蘭近現代歷史中有三個西方學界所稱的「火藥帝國」(Gunpowder Empire),即歐斯曼帝國(the Osmanlıs, Ottomans, 1281-1924)(註001)、薩法維帝國(the Ṣafāwids, 1501-1722)、蒙兀兒帝國(the Mughals, 1526-1858);其中以歐斯曼帝國的帝祚最長,超過六個世紀的統治對伊斯蘭世界宗教文化之發展留下不可抹滅的印象,豐富且具多元性的輝煌文明更可謂伊斯蘭世界的代表,其融合古典伊斯蘭與拜占庭兩文明遺緒的內涵也對人類現代文明...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8收藏
8收藏

 51二手徵求有驚喜
51二手徵求有驚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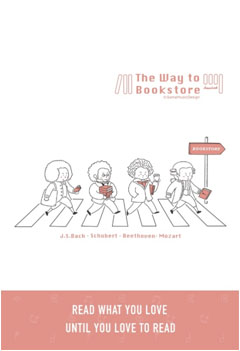





 8收藏
8收藏

 51二手徵求有驚喜
51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