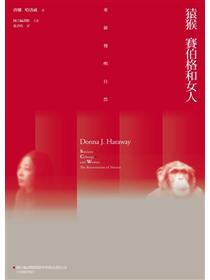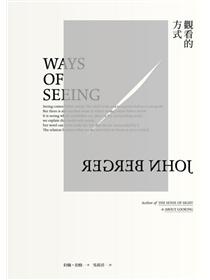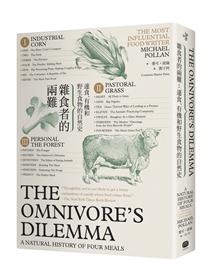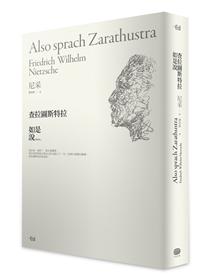太古時期,氧氣曾對生物是種毒素,直到光合作用出現改變大氣的組成
現今,人類則以另種尺度反饋地球,其每日活動的耗能堪比板塊運動
這是一部關於生態的社會理論,與人類/非人行動者的大歷史
本書讓我們澄清各種疑惑並做好準備,直面新氣候體制!
生命不只適應環境,也會調整環境,使環境有利於它們的生存。
幾十億年來,生物和環境相互作用,方才塑造出宜居的地球,
而這個自我調節的行動網絡,正是「蓋婭假說」震撼學界的創見。
然而,自地理大發現起,人類文明對環境的剝削,
已讓蓋婭對人類行動變得極度敏感。
科學家則紛紛宣稱地球已邁入新的地質年代:人類世。
面臨人類世的生態危機,該怎麼理解世界並採取行動,
才不至於落入氣候變遷懷疑論的陷阱?
本書提出反省「自然vs.文化」二分法的概念框架,
並強調氣候治理應跳脫主權國家的框架,
以納入「非人類」的行動者,重新開啟萬物的議會!
本書特色
◎否認全球暖化的川普,退出巴黎氣候協定,象徵生態運動近年來最嚴重的挫敗。環保支持者的論述與戰略是哪裡出了錯?問題恐怕出在對「自然」概念的理解,而本書則對此進行最徹底的反省!
◎質疑價值與事實截然二分的習見,科學並不完全歸科學,而是與政治息息相關。
◎跨學科的討論,自然科學、社會學、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甚至神學,對人類文明的最新階段提供多面向的觀點。
▍蓋婭並非巨型恆溫器,也不是什麼超級有機體,可以用來代替神話裡的大地之母。在我眼中,所謂「面對蓋婭」,應該是指以一種截然不同的方式,根據生物跟地球的關係來重新定義牠們,而非乞靈於某個更高或預先決定的自然秩序。
▍生命體不能獨立自存,就像細胞、細菌或人,都不是可以各自區別開來的。……生命體就像最近一本新書的書名那樣,「一切糾纏不清」。細胞本身就是多個獨立生命的重疊;我們的身體也一樣,不但需要基因,也要依靠數之不盡的小蟲子,包括那些住在我們腸道裡或皮膚表層的微生物。
▍在蓋婭尚未來臨之前,當住在現代工業社會裡的居民重新面向自然,他們看到的是必然的領域;而當他們凝視社會,他們看到的卻是自由的領域——就像哲學家說的那樣。但在蓋婭以後,這兩個領域便無法嚴格區分開來:任何生物、任何活的東西,都不再臣服於某個更高的秩序……畢竟,這些生物都互相糾纏、重疊在一起,而且都是同謀。
▍從人類世開始,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兩者已踩在相同的土壤上,亦即我們所共享的臨界區。
▍當氣候懷疑派詆毀氣候學者的科學,譴責氣候學者的舉止就像遊說集團,這些懷疑論者自己其實也集結成一個團體。他們重新分派構成世界的成分,諸如「我們能對政治有何期待」,以及「科學應當如何運作」……既然如此,氣候學者為什麼就不能照辦?
▍如果有人試圖區別科學和宗教,那麼將會出現一場屠殺,因為科學裡向來有宗教,宗教裡也一直有科學。
▍儘管「自然」一詞以不可對它有異議著稱,但這個概念卻是再模糊不過了,無論如何最不可能的便是拿它來終止衝突。
▍「自然」才是普世的、分層的、無可置喙的、系統性的、去生動的、全球的,並且對我等命運無動於衷。蓋婭並不如此。我們說過,每一個行動能力(agency)都藉修改周邊環境以追求自身利益,它們造成了錯綜複雜而又無法預料的後果。而蓋婭只是一個名字,我們不過是用它來指出這一切後果。
▍希望是行動的敵人,像希望一切會變好,與希望最壞的情況並不總是會發生。……在開始行動前,應當先把希望從我們萬分樂觀的生活領域中根除。這也是為什麼考慮再三後,我決定把這一系列演講放在但丁陰鬱的警語之下:「拋棄一切希望」。
小辭典
◎蓋婭假說(Gaia hypothesis):1960至1970年代,由發明家兼化學家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所提出,他認為地球表面的生物圈與環境構成了能自我調節的演化系統。有別於達爾文主義,洛夫洛克認為生命除了適應,也有調整環境的能力。隨後,以推動內共生學說聞名的生物學家馬古利斯(Lynn Margulis)也協助蓋婭假說的發展,她強調生命體不能獨立自存,生命體之間必然相互依賴與糾纏,遂顛覆了當時如日中天的新達爾文主義者之想像。不過,由於「蓋婭」之名取自希臘神話的大地女神,使此學說常遭到誤解,被認為帶有宗教、天意的色彩,本書作者拉圖因而試圖證明,蓋婭假說並不包含任何目的論或整體論。
◎人類世(Anthropocene):或譯人新世,由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克魯岑(Paul Crutzen)及其同僚Eugene Stoermer於2000年提出的分期概念,位於全新世之後,在此時期人類活動對地球造成了劇烈影響。查拉切西奇(Jan Zalaciewicz)則在2012年國際地質學大會提案將人類世納為正式的地質年代。關於人類世開始的時間點,專家意見頗為分歧,有人認為始於原子彈試爆的1945年,亦有人認為可追溯到18世紀末的工業革命。本書則建議將印地安人滅絕、美洲大陸林地再生(使二氧化碳濃度位於低點)的1610年,訂為人類世的起點。
作者簡介:
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
1947年出生於法國知名酒鄉伯恩(Beaune)。哲學是拉圖最初接受的學術訓練,之後於非洲服役期間對人類學產生濃厚興趣,並曾在象牙海岸從事田野工作。1975-1977年間,他在加州的沙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進行參與觀察,充分運用民族誌方法。1979年,與社會學家伍爾加(Steve Woolgar)合著《實驗室的生活》(Laboratory Life),乃上述調查的具體成果,也是新興學術領域「科技研究」(STS)的奠基之作。1982年起,拉圖任職於巴黎高等礦冶學院的創新社會學研究中心(CSI)。在CSI他與同僚發展並奠定「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的基礎。在2005年底從CSI轉至巴黎政治大學(Sciences Po.)的組織社會學研究中心(CSO),2013年起擔任巴黎政治大學媒體實驗室(Médialab)負責人。
拉圖著有作品十餘冊,包括已被譯為二十多國語言的《我們從未現代過》。這些作品既開啟研究的全新可能性,也拓展了讀者的思考與視野,充分體現出他具原創性且飽受爭議的精彩學術旅程。
譯者簡介:
陳榮泰
台大化工系、清大歷史所畢。
伍啟鴻
畢業於清大哲學所。
兩人合譯有《寄食者》、《激情的經濟學》、《巴斯德的實驗室》、《失控的佔有慾》、等書。歡迎賜教:eengthaix@gmail.com。
章節試閱
第一講 論自然(這概念)的不穩定性
與世界的關係發生突變◆被生態問題搞瘋的四種方式◆「自然/文化」的不穩定關係◆向人的天性求庇護◆向「自然世界」求援助◆偽氣候爭議的大用處◆「去跟你老闆說,科學家已經走上戰爭之路了!」◆從此我們試著從「自然」通往世界◆如何正眼面對
沒完沒了,每天一早總又要重來一次。這天是水面上升;那天是土壤瘠化;傍晚兩極浮冰加速消失;晚上八點,在兩場戰禍新聞之間,我們聽說在還沒確定如何對上千物種分類之前,牠們就已要瀕臨絕種了;每個月大氣二氧化碳的數值都比失業率還來得糟糕;每一年我們都聽說氣溫已達氣象站設站以來新高;海平面只會不斷升高;海岸線日益受到春天暴雨威脅;至於海洋,每次量測都只發現它愈來愈酸。新聞媒體說我們正活在「生態危機」的時代。
唉,談「危機」仍是一種自我安慰的方式,告訴自己「危機將會解除」,它「很快就會被我們拋諸腦後。」要是只是危機就好了!要是過去的都只是危機就好了!根據專家之言,我們該談的毋寧是「突變」:我們曾習慣某個世界,然後我們突然走向、變換到另一個世界。至於「生態」這詞,我們同樣用它求心安,好與威脅自己的麻煩保持距離:「啊,如果你談的是生態問題(écologie),那就不關我們的事囉!」就好比上個世紀談「環境」(environnement)一樣,人們用該字眼指稱那些我們可以躲在觀景窗裡遠遠端詳的自然萬物。但如今專家說,我們每一個人的體內、我們最寶貴的小小生命深處,都會觸碰到相關訊息,直接警告我們該怎麼吃喝,該如何佔用土地、如何移動、如何穿著。壞消息一個接一個,照理講我們應該會覺得自己已從單純的生態危機逐漸走到了另一種情況——甚至當稱之為我們與世界的關係所發生的深遠突變。
然而情況絕非如此。證據是:我們在聽到這一切消息時是那麼冷靜,甚至帶有令人好生敬佩的斯多葛學派模樣……如果真發生根本突變,我們早就已經徹頭徹尾著手調整自身的生活基礎。包括改變飲食、住所、交通工具、文化技術——總言之,改變我們的生產模式。假若警報器嗡嗡作響,我們總該已經即時逃出自己的窩,並依據威脅的程度發明相應的新技術。富裕國家的居民早就會像從前戰爭時那樣(比如20世紀的情況)做出許多創舉,花上四到五年的時間,藉由大規模改變生活模式把問題解決掉。然後多虧他們精力充沛的行動,夏威夷冒納羅亞(Mauna Loa)觀測站偵測到二氧化碳量早可能已經穩定下來了;濕度適當的土壤裡蚯蚓應該已是萬頭鑽動,充滿浮游生物的海洋裡群魚再度鱗光閃閃;甚至北極浮冰消融速度也可能已經減緩(除非傾斜度到達不可逆的地步,幾千年後北極冰可能滑動到新的狀態)。
無論如何,經過三十多年,我們應該已經作出行動了。危機應該已經解除了。我們可能已經帶著驕傲回頭看那段「生態大戰」的時期——那時我們差點就要投降,卻是靠大家迅捷的反應和全體動員的創造力扭轉劣勢。我們可能還已經帶著孫子,參觀這場戰役的主題博物館,期待他們目瞪口呆看著我們的進展,就像他們今天看到二次世界大戰如何啟動曼哈頓計畫,如何讓人弄清楚青黴素,或造就雷達與空運的驚人進步。
不過啊,你瞧,一個原本可能只如過眼雲煙的危機,卻成了我們與世界關係的深層質變。似乎本來在三、四十年前就能作出行動,我們卻什麼也沒做,即使有做,也不算盡力。這種情況還真是奇怪呀,我們已跨過幾道門檻,穿越一場全面戰爭,卻幾乎渾然不覺!乃至於一度迫使我們屈服的千斤重擔,如今又再度壓在我們背上——我們卻未曾真正察覺,未曾為此戰鬥過。不妨想像一下:隱身在那麼多世界大戰、殖民戰爭、核戰危機背後,20世紀(這個「典型的戰爭世紀」)還發生了另一場戰爭,一樣籠罩世界,一樣全面,一樣具殖民特性,而我們活在這樣的戰爭中,卻未曾體驗過它。我們無精打采,懶懶散散地開始關心「後代子孫的未來」(就像我們近來常說的那樣),但這一切,不正是過去世代原本就應該承擔下來的嗎?情況不應該是威脅仍然在我們眼前,而應該是威脅早就落在那些已出生的人身後了吧!對於把情況弄到這樣不可挽回的地步,我們怎能不因為自己在警報期間還如夢遊者那般前進,而多少感到有些可恥呢?
然而我們其實不缺警告,警報一直都在響。生態災難的意識一向鮮明,而且源遠流長,打從所謂的「工業時代」或「機械文明」伊始,人們就持續加以辯論、記載與求證。不能說我們對此一無所知。只能說我們有許多辦法,使自己同時既有知又無知。通常當事關自身、自我的生存,或我們所珍視者的幸福,我們寧願犯下過度防範的錯:小孩一有點感冒就去找醫生諮詢;植物遇上一點危險就準備來場殺蟲大作戰;財產有些堪慮就緊張兮兮,裝上監視器;為提防別人入侵就立刻組織前線部隊。一旦事關保護自身周遭與財物,我們就大量執行鼎鼎有名的「預警原則」——儘管我們對事情的診斷還不是很有把握,儘管專家還在對危險的強度爭論不休。然而碰上這場世界性危機,卻沒有人援引這項原則,勇敢投入行動。這一回,人類顯得老態龍鍾,他小心翼翼、過於拘泥小節,就像邊摸索邊走的盲人,用他的白杖輕敲每個障礙,一有危險徵兆就謹慎調整自己,一感到有什麼擋住路就立刻縮腳,當前面暢通時就快快前進,直到新障礙出現又開始躊躇。這樣的人類,只能說他老成持重。人們古老的德性,不管是農夫的、商人的、工匠的、勞工的還是政客的,似乎在此通通不管用了。警報響了又響,人們也一次又一次把它關掉。人們張開眼睛,人們看到、知道了,然後把眼睛閉得緊緊地往前衝!如果在讀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的《夢遊者》(The Sleepwalkers)時,我們會對1914年的歐洲人明知原因、卻仍投入一次世界大戰而感到訝異,那麼當我們回過頭知道,歐洲人(以及此後跟隨他們的所有人)對另一場大戰——一場我們知道已經發生、並且很可能已經輸掉的戰爭——的前因後果知之甚詳,卻仍奮不顧身投入,我們又怎能不驚詫呢?
......
我們有點進展了嗎?我所提出的建議就好像初期療程,很小心謹慎地為各種存在於世的方式一比高下。這使我們又回過頭詢問那些既古老又尋常的問題:誰?何處?何時?如何?為何?我們,我們這些仍稱為「人」者,究竟是誰?我們處於什麼時期?——這不是在問日曆上的時期,而是在問:時間的節奏、格律與行進方式為何?我們在哪裡?我們能接受住在哪類型的領域、土壤、位置或地方,並且我們準備和誰同住?我們是如何又為何走到當前的處境,走到被生態問題搞到抓狂的地步?我們循著什麼樣的路徑,又是基於怎樣的動機而作出決定?上述每個問題都有好幾個答案,正因為這樣,我們才如此茫然。但今天,我們之所以被徹底搞瘋,尤其是因為自然及「自然」概念這雙重的不穩定性,使這些答案變得完全無法共量。
舉例來說,如果我們對「與世界的關係為何」這個問題給出完全不同的答案,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我們可能會是誰?不妨用「地球人」(Terrien)一詞來取代原來的「人類」。那麼我們會在哪裡?在地球(Terre)之上,而不是在自然之中。說得更確切些,我們所處的土地,是與其他擁有各式需求的奇怪存在物所共享的。在何時?在一些根本的變化甚至是劇變之後,或在洪水迫近之前;這個節骨眼給人一種印象,覺得自己活在時間終結的氣氛當中——至少是覺得先前的時間已經結束。我們又可能會是如何走到那地步的?正是因為在之前那段與自然牽連在一起的時期裡,我們走錯了一個又一個岔道。在那段時期,我們給了自然許多能力,賦予它許多面向,給它一種道德、甚至是政治,但卻沒把它琢磨到能夠乘載這些的程度。我們所選擇的組構方式可能會坍塌;我們可能會分崩離析(décomposés)。
當我們意識到進步主義所憧憬的革命已經發生了,怎能不感到慌亂呢?而且導致這個革命的,並非原本假定的「生產工具所有權」上的變換,而是以驚人速度增加的碳循環活動!甚至連寫過《自然辯證法》(la Dialectique de la nature)的恩格斯也不曾想過,他自己說得有多麼對——他表示,在歷史行動的醉人狂亂中,這顆星球上的所有行動者最終都將真的動員起來。甚至連寫過《精神現象學》(Phénoménologie de l'Esprit)的黑格爾也料想不到,人類世的到來徹底翻轉了他的計畫方向——人類將不再辯證式地浸淫在絕對精神的奇遇中,而是在地史(géo-histoire)當中冒險。想像一下,當他看到精神氣息被二氧化碳給克服、超越、揚棄(aufgehoben)或毒化之時,他會說些什麼!
在評論者慨嘆「革命精神喪失」和「解放理想消逝」的時代,居然是由自然史家率先以「大加速」之名,掀開了人類世的序幕,有見及此,我們怎能不訝異?他們揭露的事情是:革命已經發生了,我們必須面對的並不是將來,而是不久以前的事。革命行動主義者被他們的發現給嚇著了。他們恍然大悟:不管我們今天做了什麼,威脅還是會伴隨我們千百年,因為在人類眾多不可逆革命行動之後接棒的,是海水持續暖化、極地反光率的變化、大洋酸度提高。這可不是逐步的變革,而是劇烈的變遷,就好比跨過傾覆點,而非只是越過海格力斯之柱。這足以把我們搞得暈頭轉向了。人們之所以對氣候問題產生懷疑,究其根本,乃源於若干極驚人的態度翻轉,包括:對進步主義本身的反抗、對將來之事的再界定,以及對領土歸屬概念的反思。這場革命沒有我們,卻衝擊著我們,同時又因我們而起;而在實際行動上,我們全都是反革命份子,全都在試著極力縮小這場革命的後果。
生活在這樣的時期也可能頗具娛樂性,只要我們能遠遠站在沒有歷史的岸邊,欣賞這齣悲劇。但如今已沒有人是局外人,因為所有的隔岸都進入了地史的劇碼中。由於觀光客不再,那種崇高的感動也就隨著觀賞者的安全感一起消失了。沒錯,這是場海難,卻不再有旁觀者。不如說,這更像《少年Pi的奇幻漂流》裡的情景:救生艇上竟(好像)有一隻孟加拉虎!可憐的遇難少年,他不再擁有堅固的隔岸可以悠哉觀賞,而必須在一隻難以馴服的野獸旁掙扎求生,既身為牠的馴服師,又充當牠的大餐!朝向我們而來的,就是我所說的蓋婭——正視她,才能避免真的發瘋。
第一講 論自然(這概念)的不穩定性
與世界的關係發生突變◆被生態問題搞瘋的四種方式◆「自然/文化」的不穩定關係◆向人的天性求庇護◆向「自然世界」求援助◆偽氣候爭議的大用處◆「去跟你老闆說,科學家已經走上戰爭之路了!」◆從此我們試著從「自然」通往世界◆如何正眼面對
沒完沒了,每天一早總又要重來一次。這天是水面上升;那天是土壤瘠化;傍晚兩極浮冰加速消失;晚上八點,在兩場戰禍新聞之間,我們聽說在還沒確定如何對上千物種分類之前,牠們就已要瀕臨絕種了;每個月大氣二氧化碳的數值都比失業率還來得糟糕;每一...
推薦序
蓋婭的終局之戰:直面真相,正視大地的臉
張君玫(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Gaia is a tough bitch.
(Lynn Margulis)
You never said you'd do anything
You made excuses for your mind
Objected core the collective
Don't you dare forget it
Don't you forget it
Don't you forget
Don't do it
(Cat Power, In Your Face)
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的《面對蓋婭》(Facing Gaia)所包含的一系列演講可以是他給當代人的忠告,結合了科學、宗教、政治和倫理的思考,我們必須擺脫他稱之為「舊的氣候政權」的壞習慣。簡言之,拉圖告訴我們,要搞政治,就要搞真的,不要搞假的。政治的真假取決為何?沒有敵對,就沒有政治。
問題當然是,為什麼拉圖要強調敵對的政治,尤其是他稱為「生態的再政治化」(repoliticization of ecology)。要理解這個呼籲,首先我們必須問的是,生態這個詞已經流行了那麼久,卻沒有造成根本的改革行動,甚至我們在聽到生態危機時,儼然麻木無感的情況,是為什麼?答案很可能就在於生態的(被)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亦即敵對狀態與意識的消弭。我們早已不知道為何而戰,沒有敵人,每個人都是敵人。如果我們還只是在講著人文和自然的二元對立瓦解,或是重新回到自然之中和諧共存,那都已經來不及了!現在是作戰的時候,但我們卻不知道該捍衛什麼。
拉圖在危言聳聽嗎?或許,這正是我們這時代人所需要的,正眼看看我們為自己和鄰人(存在)們設下的終局之戰。在第八講,也是最後一講中,拉圖說道,「活在終點的時間之中,首先是要接受會消逝時間的有限性,並停止忽略。」他甚至教大家,如果被質疑在散播末日論的危言聳聽時,該怎麼回嘴。反問是一個不錯的策略:那你呢?你活在哪個時間點上?你在哪裡?你在何時,何方,何地?拉圖反覆說著時間的終結(the end of times),以及終點的時間(the time of the end),乃至於宗教及其他發明出來的各種時間,包括不會消逝的時間(time that does not pass),對照於那不斷在消逝的時間(time that passes)。所以,你在哪裡?你活在哪種時間裡?
如果不是此時,更待何時?如果不是此地,我們可以去哪裡?我們哪裡也去不了。我們注定要活在大地上,我們是被綁在大地上的生物(the Earthbound)。大地,蓋婭,並不是一般刻板印象中的母親,和諧、慈愛、養育與寬容,而是衝突、暴力,甚至好戰和鬥爭的,如同生命。正如拉圖引述和 James Lovelock 共同鋪陳蓋婭理論的微生物學家 Lynn Margulis 的名言,「蓋婭是強悍的婊子」。而這又牽涉到性別政治的動態,尤其當這句話是出自一位反叛的女性科學家,曾經以微生物內共生(endosymbiosis)理論撼動了現代演化論中以男性科學家為主導並以較大型生物為模型的典範。蓋婭理論所受的誤解,幾乎可以說完全映照了女性在主流社會中經常遭受的誤解。「大地女神」的女性刻板印象,完全背離蓋婭神話的實質內容。但重點不在於神話的敘事,而在於我們社會中人對於力量(force)的誤解。我們習慣用區塊切割的整體和部分觀點,層級的、二元的或中心的,儘管強調關係,依然不足以掌握動態的生命觀點和力量動態。就連系統的概念也必然在此結構化的觀點中產生誤導。蓋婭是力量,換言之,不能也不會是已經完成或邁向完成的整體。蓋婭也是大地的臉,就像我們的生物圈,這個行星的薄膜,一連串不曾停歇的連結和事件。
拉圖對同代人的演講,必然也是他的自問自答,就像我們在生態突變時代中的戰爭,也必然是不同意義和意象的人類或不再是人類的大地生物的戰爭。拉圖自問,他為什麼不顧同事朋友的警告,非但沒有遠離「蓋婭」這個神話名詞╱形象╱喻說,反而以此為名做了一系列演講?答案就在細節當中。拉圖為我們同代人,或是為我們同樣注定生死綁在大地上的存有,所講述的是我們大地的臉,以及這張臉上所發生的種種不同向度的歷史事件。畢竟,我們必須認知到一件事情,這張臉,也就是蓋婭,做為我們的棲居之所,從來就不是那被我們稱為「地球」或「大地」(Earth)的一整個行星,而是這座行星淺淺的表層。
臉是一個倫理符號。對身為人類來說,有一張臉,表示值得我們在倫理上關注。對身為動物來說,直視對方的臉卻可能是一種挑釁。在關注和挑釁,並不像乍看之下如此對立,而可能是類似過程的不同向度。在關注一件事、一個人或一件事的同時,我們往往必須去挑釁那些習以為常的思考與方式。拉圖所呼籲的,生態的再政治化,相當程度上來說,也是這樣的關注與挑釁。我們必須願意去敵對,去涉入,去重新發明政治,甚至講白一點,去挑起對立。這些對立的本質,或性質,或自然,幾乎必然是反宗教的,但同時也是充滿信念的,批判的,以及引戰的,如同蓋婭。我們,無論你如何命名,如何定位,如何劃界這個我們,必須直面真相,正視大地的臉。
我們生活在終點的時間裡,但這個終點並不是任何固定的一點,也不是一直後退的地平線。這個終點的樣貌取決於你如何重新發明政治。拉圖很早就開始談論著人造物的政治,以及自然的政治,乃至於各種混合物、嵌合物和突變物的政治。在《面對蓋婭》中,拉圖對於變質區(zone métamorphique, metamorphic zone)的強調, 延續著他長久以來對於翻譯和轉化(translation)等過程的關注。我們必須重新發明政治,進行各種類別與力量之間的翻譯。因為,沒有翻譯,就沒有超越成見和框架的法律;沒有翻譯,就沒有多元存在的張力與衝突空間;沒有翻譯,就沒有能動力的重新分配;沒有翻譯,就沒有宇宙論的地圖重新繪製。沒有翻譯,就沒有政治。政治,有時候是一種翻譯和另一種翻譯的戰爭。
如同拉圖在第六講中所言,當有人把「終點的時間」(the time of the end)翻譯成「時間的終結」(the end of the times),就會發現自己處於一種頭暈目眩的變質邊緣,亦即一種誘惑,召喚你放棄所有形式與樣態的時間,揚棄有限,躍入永恆。這種誘惑在各種敘事與慣習中無所不在,造就著貌似激情的忽略,以及深深刺痛的無感。反之,蓋婭的嚴厲形象召喚另一種政治,以及另一些翻譯:你必須直面真相,杜絕永恆的誘惑。我們是有限的生命,我們活過與活著的時間也是有限的,我們是會死的大地生物。我們正處於蓋婭的終局之戰,你呢?你在哪裡?
2019年6月9日,在台北浮光書店完稿
蓋婭的終局之戰:直面真相,正視大地的臉
張君玫(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Gaia is a tough bitch.
(Lynn Margulis)
You never said you'd do anything
You made excuses for your mind
Objected core the collective
Don't you dare forget it
Don't you forget it
Don't you forget
Don't do it
(Cat Power, In Your Face)
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的《面對蓋婭》(Facing Gaia)所包含的一系列演講可以是他給當代人的忠告,結合了科學、宗教、政治和倫理的思考,我們必須擺脫他稱之為「舊的氣候政權」的壞習慣...
作者序
前言
一切都始於十多年前在我眼前上演的一段舞蹈,使我一直無法忘懷。舞者為了躲避某個使她心慌的東西,倒退著逃跑;然而,她又不時掉過頭看,一次比一次擔憂,彷彿她愈跑,背後便堆疊出愈多障礙,妨礙她前進。到後來,她被迫整個轉過身;就在那時,她停下腳步,整個人愣住。兩臂輕晃、張惶失措,她看到某東西正在逼近,比原先她想逃避的東西還要嚇人,逼得她擺出退卻的姿態。她在逃離某個恐怖東西之時又遭遇到另一個,而這東西,部分還是因她的遁逃而引起的。
我想這段舞蹈表達出時代精神。我認為它用一個(頗令我不安的)情境總結了現代人(Moderne)先是逃避、而如今又得面對的東西。避開過往古老的可怖之物,如今卻突然出現一個謎般的形象——這個恐懼的來源不再落於現代人身後,卻正在眼前。對於這個半似颶風、半似利維坦的怪物,一開始我用「世界巨靈」(Cosmocolosse)這個怪異的名字記載牠的出現。然而當我一邊讀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一邊思考著另一個極富爭議的形象,也就是他提出的蓋婭(Gaïa),兩個形象很快就融為一體。嗯,我不能夠再逃避。我必須理解這東西。牠以一種令人萬分恐慌的形貌向我走來——同時屬於神話、科學與政治的這股力量,很可能與宗教也有關係。
由於我對舞蹈一竅不通,所以我得花上好幾年的時間才找到葛納秀(Stéphanie Ganachaud)這位理想舞者演繹這段簡短的舞步。期間,由於不知怎麼處理世界巨靈這個縈繞不去的形象,我便說服了一些摯友編寫劇本,後來便成了《蓋婭全球劇團》(Gaïa Global Circus)。就在那時,出於巧合(曾經著過迷的人大概都不會覺得奇怪),吉佛講座(Gifford Lectures)的委員會找上我,邀請我2013年在愛丁堡發表六堂系列演講。講題一樣如謎般難解,叫做「自然宗教」。一個連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杜威(John Dewey)、柏格森(Henri Bergson)、鄂蘭(Hannah Arendt)以及其他人都曾應允的提議,要我怎麼拒絕它呢? 這難道不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嗎?我起初因舞蹈和戲劇而被迫開始探索的問題,現在則可藉由論證而加以發展。無論如何,這種媒體對我來說並不是太陌生。尤其我才在剛寫完的作品裡探究各類存在模式,而這些模式正日益受到蓋婭侵略影響。讀者在此所見,便是修訂、擴充並徹底將這幾場演講改寫成書的成果。
我之所以保留演講這種文類及其風格與口吻,那是因為四十年來我一路追索的「現代人的人類學」,日益呼應所謂新氣候體制(Nouveau Régime Climatique)的情境。我用這個詞總結當前的處境:現代人從前認為理所當然的物理架構,這塊讓他們的歷史不斷上演的土地,如今已變得很不穩定。彷彿原本的布景也登上舞台,要與演員一同參與戲劇情節。從此刻起,說故事的方式全都變了,到了把過去仍屬於自然的事物都放入政治當中的地步——而回過頭來,自然這個形象也就變得愈來愈難捉摸了。
多年來,我的同事與我嘗試消化「自然與科學走入政治」這件事,我們發明許多方法追蹤生態爭議,甚至描繪出這些爭議的地圖。然而,這些專業工作從來沒能撼動人們的堅定信念,大家還是繼續想像一個沒有物件的社會世界,面對另一個沒有人的自然世界——一個沒有科學家去認識的世界。然而當我們努力解開知識論與社會學裡的若干糾結,安排其中各種功能的大廈卻跨落在地上——即是說,整個再度跌落到地球(Terre)之上。我們仍在討論:人與非人可能有怎樣的關係?科學家在生產客觀性時扮演什麼角色?對未來世代可能有什麼影響?同時間,科學家自己也不斷增加新的發明,用來談論同樣的問題,但卻是在截然不同的層次上。好比說,科學家發明了「人類世」(Anthropocène)、「大加速」(grande accélération)、「星球界限」(limites planétaires)、「地史」(géohistoire)、「傾覆點」(tipping points)、「臨界區」(zones critiques)等等驚人的字眼。這些字詞看似頗為必要,而且為了理解大地如何回應我們的行動,我們勢必逐步遇上它們。
我出身的學科(「科技與社會研究」或「科學的人類學」)如今變得更加茁壯,因為大家已頗有共識,認為過去分配科學權力與政治權力的舊憲章已然作廢。這就好比說,我們確實已從「舊體制」轉入「新體制」,氣候(climat)問題於是以各種面貌蜂湧而至,以及更怪的,是氣候與政府(gouvernement)間關係的問題亦層出不窮。比起研究地理學的歷史學家,我是以更為廣泛的意義使用上述字詞——除了討論孟德斯鳩久已過氣的「氣候理論」外,這些字詞對他們來說已再無可取之處。突然間,所有人都猜測另一部《論自然法的精神》(Esprit des lois de la Nature)正要浮現;而且如果面對這新體制所釋放的力量,還想倖免於難,那就必須要著手撰寫這部作品。這本書正欲為此集體探索的工作作出一點貢獻。
在此,我把蓋婭表現成使我們得以重返地球的機會。她提供我們一個有別其他的版本,好讓我們要求科學、政治與宗教重拾過往使命,以便這些領域最終能以更謙遜樸拙、更腳踏實地的性質來界定自己。這些演講以成對的方式進行:前二講針對行動能力(puissance d'agir,即英文的「agency」),要讓不同專業與學科能夠交流,這個操作型概念不可或缺;接下來的二講介紹兩個要角,首先是蓋婭,然後是人類世;第五、六講界定出為佔據地球而互鬥的是哪些民族,以及這些民族處於怎樣的時代;最後兩講則探索關乎這些戰地的地緣政治問題。
前言
一切都始於十多年前在我眼前上演的一段舞蹈,使我一直無法忘懷。舞者為了躲避某個使她心慌的東西,倒退著逃跑;然而,她又不時掉過頭看,一次比一次擔憂,彷彿她愈跑,背後便堆疊出愈多障礙,妨礙她前進。到後來,她被迫整個轉過身;就在那時,她停下腳步,整個人愣住。兩臂輕晃、張惶失措,她看到某東西正在逼近,比原先她想逃避的東西還要嚇人,逼得她擺出退卻的姿態。她在逃離某個恐怖東西之時又遭遇到另一個,而這東西,部分還是因她的遁逃而引起的。
我想這段舞蹈表達出時代精神。我認為它用一個(頗令我不安的)情境總結...
目錄
推薦序 蓋婭的終局之戰:直面真相,正視大地的臉/張君玫
推薦序 人類世的憂鬱與療癒/洪廣冀
台灣版序 拜訪蓋婭發現者
前言
第一講 論自然(這概念)的不穩定性
與世界的關係發生突變◆被生態問題搞瘋的四種方式◆「自然/文化」的不穩定關係◆向人的天性求庇護◆向「自然世界」求援助◆偽氣候爭議的大用處◆「去跟你老闆說,科學家已經走上戰爭之路了!」◆從此我們試著從「自然」通往世界◆如何正眼面對
第二講 如何不把自然生動化,或去生動化
那些「不願面對的真相」◆描述是為了警告◆把精神集中在行動能力上◆分辨人與非人的困難◆「但它就是激動起來了啊!」◆自然法的新面貌◆論混淆原因與創造這令人遺憾的傾向◆通往將不再是宗教的自然?
第三講 蓋婭,自然的形象(總算變得世俗)
伽利略、洛夫洛克:對稱的兩位發現者◆蓋婭,一個對科學來說頗為棘手的神話名號◆以巴斯德的微生物作對照◆洛夫洛克也在大量繁殖微行動者◆如何避免系統的概念?◆生物體製造自身環境,而非適應環境◆論稍微複雜化一些的達爾文主義◆空間:歷史之子
第四講 人類世與全球(形象)的崩毀
人類世:一種創新◆思想與榔頭◆不穩定時期的爭議字眼◆瓦解人與自然形象的理想時機◆斯洛特戴克或球體形象的神學起源◆科學與全球的混淆◆泰瑞爾反對洛夫洛克◆反饋迴圈並不勾勒出全球◆另一個組構原則總算出現◆憂鬱或全球的終結
第五講 如何召集不同的(自然)民族
兩個利維坦,兩種宇宙論◆如何避免眾神之戰◆棘手的外交計畫◆召集「自然民族」是不可能的◆如何得到一次談判機會?◆論科學與宗教之衝突◆「終結」一詞意義的不確定性◆對互相競爭的集體作比較◆放棄整個自然宗教
第六講 如何(不)了結「時間終結」
1610年,決定命運的事件◆史蒂芬.圖敏與科學的反宗教◆尋找「抑制解除」的宗教根源◆「把天堂帶到地球」的奇怪計畫◆沃格林與諾斯底主義式的化成肉身◆論氣候懷疑論的末世根源◆從宗教到世俗再抵達地上◆「蓋婭民族」?◆如果別人指責你抱持「末世論述」,你該怎麼回答?
第七講 戰爭與和平之間的(自然)國家
卡斯巴.弗列德里赫的「大藩籬」◆自然之國的終結◆適當攝取施米特◆「我們在尋找地球的規範意義」◆戰爭與警察程序之間的差別◆如何轉身面對蓋婭?◆人類與「在地人」的對抗◆學會辨認競逐的領土
第八講 如何治理你爭我奪的(自然)領土
「談判劇場」,2015年5月亞曼第埃劇院◆學習召開沒有最高仲裁的集會◆擴展到非人類的締約方會議◆增加利害相關者◆勾勒臨界區◆找回國家的意義◆「願祢受讚頌!」◆終於面對蓋婭◆「是陸地,是陸地!」
參考文獻
推薦序 蓋婭的終局之戰:直面真相,正視大地的臉/張君玫
推薦序 人類世的憂鬱與療癒/洪廣冀
台灣版序 拜訪蓋婭發現者
前言
第一講 論自然(這概念)的不穩定性
與世界的關係發生突變◆被生態問題搞瘋的四種方式◆「自然/文化」的不穩定關係◆向人的天性求庇護◆向「自然世界」求援助◆偽氣候爭議的大用處◆「去跟你老闆說,科學家已經走上戰爭之路了!」◆從此我們試著從「自然」通往世界◆如何正眼面對
第二講 如何不把自然生動化,或去生動化
那些「不願面對的真相」◆描述是為了警告◆把精神集中在行動能力上◆分...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5收藏
15收藏

 73二手徵求有驚喜
73二手徵求有驚喜



 15收藏
15收藏

 73二手徵求有驚喜
73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