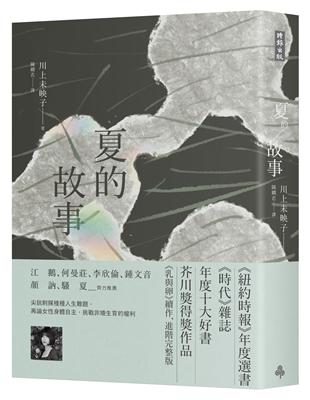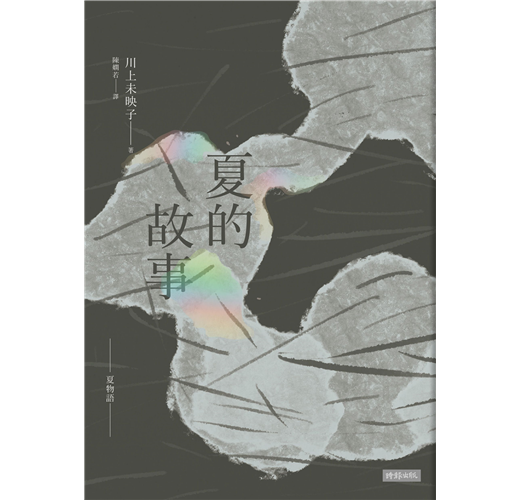《Time》雜誌Best10
《紐約時報》必讀100本書
美國圖書館協會最佳小說
授權40多國出版,娜塔莉.波曼也激推!
川上未映子壓倒性震撼全球的長篇之作!
芥川獎得獎作品《乳與卵》續作,進階完整版
尖銳刺探種種人生難題,再論女性身體自主,挑戰非婚生育的權利江鵝、何曼莊、李欣倫、鍾文音、顏訥、騷夏
上野千鶴子、村上春樹、岸政彥、桐野夏生、鴻巢友季子
台日文壇齊力推薦
.為什麼乳頭不能強大?為什麼不能很黑?在乳頭的世界裡,強而黑的巨大乳頭難道不能掌霸權嗎?這種時代會來臨嗎?會吧。
.誰有生孩子的權利?只因為沒有另一半,不能做愛,你們憑什麼說我沒有這個權利?
二○○八年的夏天,夏子在東京打工生活,朝著作家之路而努力,大阪的姊姊卷子為了進行隆乳諮商,帶著不肯開口說話的女兒綠子,來到東京在夏子租屋處借住三天兩夜。想隆乳的卷子、面臨青春期的綠子、回想親族四代共同身體特徵的夏子,三人對女性身體、美麗定義、人生必經道路,有著不同的想像與思考。
二○一六年,三十八歲的夏子終於出版了一本小說集,如願成為作家,看似朝目標邁進,但日子卻過得一成不變。此時她突然萌生了想要孩子的心念,但沒有結婚、沒有伴侶、沒有對性的渴望,這樣的人可以擁有自己的孩子嗎?於是她考慮接受第三方人工授精,為了確認自己的心意與選擇,她讀了非配偶捐精而出生的當事人的書、在網路上搜尋各類發言與資料、參與研討會,想預先了解孩子會有的各種想法,她會讓孩子感到幸福嗎?
川上未映子重寫八年前《乳與卵》夏子、卷子、綠子三人的故事,並追加八年後的夏子正面臨人生重大決定。如同八年前姊姊卷子對隆乳的篤定,夏子急切地想要見到自己的小孩、與孩子共同生活的心意也同樣堅定。小說中每位女性都面臨各種不同的問題,不禁讓人細細思索家庭、配偶、生育對女性的意義為何,而接受人工授精生育、父不詳的小孩,在心態上與非婚生子女又有何不同。可以肯定的是,無論已婚或未婚,女性其實都能擁有生與不生的選擇權。
作者簡介:
川上未映子
《紐約時報》年度選書及《時代》雜誌年度十大好書──全球暢銷小說《乳與卵》作者。生於大阪,2006年以詩人身分進入文壇,隔年出版其首部小說《我、我的牙齒,或世界》,以其詩意的文風及對於女性身體之洞察、倫理道德悖論及現代社會困境的省察而聞名。川上作品已譯介為多國語言,暢銷全球,並曾拿下日本文壇各大獎項,包含芥川獎、谷崎潤一郎獎及紫式部文學獎。現定居於日本東京。
譯者簡介:
陳嫻若
日文系畢。曾為出版社日文編輯,目前專職日文翻譯。喜歡閱讀文學,也樂於探究各領域的知識,永遠在翻譯中學習。譯作有《今天也謝謝招待了》、《森之眠魚》、《宮澤賢治短篇小說集I》、《貓式生活──徹底解讀喵星人的100種狀態》、《小熊》、《怒》、《贖罪》、《可悲的雄性生物》等。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這本書像是月之暗面,如果不翻開它,也許永遠不會相見。平成時代的日本是最多臺灣人度過美好假期的地方,極度整潔、優雅、禮貌,令人神往的日本觀光服務業,是建立在根深柢固的厭女/奴役女性的傳統上,通過川上未映子之筆,傾聽日本女性的耳語,也是一種友善回應的方式。
──何曼莊
這是本女身/聲之書。先透過不同年齡的女性,反思乳和卵的功能,其中有少女對生之恐懼、對成熟女體之厭棄,青春卻已顯現對「生」之象徵性的巨大疲憊,對照於中年女性對粉紅色乳暈的渴盼,不同世代對女體和宿命的殊異感受及觀點,在姊妹、母女的家常對談和靜默中,如夏日蟬噪聲般喧譁開來,交響成華麗辯證與深刻問難。八年後,小說家夏子進一步討論性愛恐懼、生殖議題和人工授精等議題,在看似獨白的單向表述中,潛藏著深度溝通及理解的嘗試,頗能引發當代女子的共鳴。私語、呻吟、啜泣、鼓勵或者嘆息,全收錄在諸種女子敘事聲音的《夏的故事》。
──李欣倫
這是一部精密的女性小說。透過三個女性角色交織,帶出姊妹情誼、母女情結、姨與外甥女兩代女人的新舊對望。
用「乳」與「卵」顯影:女性只有這樣的「功能性」?三個女性主角呈現各自「不得不」,和看似可以選擇,其實是沒有選擇的處境。
我特愛有一幕在公共澡堂,探討女性胸部的情節,乳頭的細部描寫令人印象深刻又感傷,作者巧妙安排一位「T」入內,讓眾人議論或走避,竟然可以如此不著痕跡點出性別議題。
主角能否扭轉女性設定?我想和扭轉階級,我認為是同一件事,也是小說主角奮力在抵抗的。「乳」與「卵」真能脫離宿命嗎?生出自己的孩子,真能擁有自己嗎?小說尾聲,我跟著新生兒的哭聲深深期待著。
──騷夏
我們無法決定自己的出生,但是卻能決定是否生育。
這光輝耀眼的非對稱,該如何弭平?
將為人母的女子們,該如何跨越這道暗渠?
如何才能這般魯莽而任性的選擇?
自己決定「生產」是什麼狀況?作者勇敢迎向這個可怕,但幾乎所有生產過的女子經歷過的問題。
──上野千鶴子(《文藝》秋季號)
這本小說質問了每一個讀者,人生種種的重要意義,
十分尖銳,但又相當迷人。
主角堅強的活著,堅強的呼吸著。
尤其是近尾聲處,也是我最鍾愛的一部分。
──村上春樹
仍在笑橋生活的卷子在故事尾聲說的那段話,任誰看了都會流淚吧。
這部作品無疑是部傑作。
──岸政彥(《文學界》8月號)
這部作品傾聽了各方的意見,是部極公平的創作。
而且也在議論生殖醫學的困難中,一面摸索著如何達成「生子」這個簡單願望的結果。
川上未映子以非凡的密度書寫出這個困難的題材。
──桐野夏生(《文學界》8月號)
本書探討的倫理問題再嚴肅不過,但是不時交織的大阪腔和臺詞,卻充滿爆笑的威力。
同時完美達成破壞與創造的川上語著實精湛。
──鴻巢友季子(《每日新聞》7 月28日書評)
名人推薦:這本書像是月之暗面,如果不翻開它,也許永遠不會相見。平成時代的日本是最多臺灣人度過美好假期的地方,極度整潔、優雅、禮貌,令人神往的日本觀光服務業,是建立在根深柢固的厭女/奴役女性的傳統上,通過川上未映子之筆,傾聽日本女性的耳語,也是一種友善回應的方式。
──何曼莊
這是本女身/聲之書。先透過不同年齡的女性,反思乳和卵的功能,其中有少女對生之恐懼、對成熟女體之厭棄,青春卻已顯現對「生」之象徵性的巨大疲憊,對照於中年女性對粉紅色乳暈的渴盼,不同世代對女體和宿命的殊異感受及觀點,在姊妹、母女...
章節試閱
1 你,家裡窮?
想知道一個人到底有多窮,只要問他老家的窗子有幾扇,就能一目了然。平日的吃穿都說不得準,想知道貧窮的程度,唯有數窗子。沒錯,貧窮就是窗子的數量。沒有窗子,或者窗子的數量越少,多半可以判斷那個人到底有多窮。
以前,我跟某個人說起這個理論時,她反駁說,不一定吧。她的說詞是這樣的,「就算是只有一扇窗,但是有可能那是一扇面對庭院、大到不行的窗子啊。家有那麼豪華的大面窗,怎麼可能算是窮人呢?」
但是,讓我來說的話,這是已經脫離貧窮的人才會有的想法。面對庭院的窗,大面窗,請問一下,庭院是什麼?豪華的窗長什麼樣子?
對貧窮世界的居民而言,根本不存在什麼大面窗或豪華窗的思維,對他們而言,窗子就是被衣櫥或收納櫃密密實實的擋住、從來沒打開過的烏黑玻璃板,或者是裝在廚房從沒旋轉過的換氣扇旁的骯髒四角框。
所以,不論是貧窮現在式的人,還是過去貧窮的人,只有窮人才會想討論貧窮,或是真正說得出貧窮的定義。而我,兩者都是,打從出生就貧窮,現在也還是個窮人。
我之所以無意識地想起或思索這件事,也許是坐在眼前的那個女孩的關係。暑假的山手線沒有想像中擁擠,人人不是玩手機就是看書,大家都平靜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
那個女孩看上去,你說她八歲也行,十歲也沒錯,她的身旁一側坐著一位年輕男子,腳邊擺著運動提包,另一側坐著兩位頭上戴著黑蝴蝶結髮箍的女孩,她似乎是一個人。
她長得又黑又瘦,可能是日晒的關係,淡色的圓形玫瑰糠疹變得特別明顯。灰色裙褲下伸出的兩條腿,與從淡藍色坦克背心旁的兩隻手臂一樣細。嘴角緊緊抿住,兩肩聳著,表情有說不出的緊張。看著她,我不禁想到小時候的自己,腦中掠過「貧窮」兩個字。
我盯著頸部開闊的淡藍色坦克背心,和本來該是白色,但是沾滿汙漬,已看不出顏色的運動鞋。我有點擔心萬一這女孩不小心張開嘴,露出牙齒,會不會看到一口蛀牙。這麼說起來,她一件隨身行李也沒帶,既沒有背包、提包,也沒有小包包。車票和錢可能放在口袋裡吧。雖然我不知道這個年紀的女孩子出門搭電車時,會做什麼打扮,但是,她手上空無一物讓我有點擔心。
看著看著,我有股衝動,覺得必須從位子站起來,移到女孩子面前,隨便跟她說說話,覺得必須與她說些只有我們才懂的話,就像在日誌角落寫下沒人懂的記號。我好像可以從她看上去粗硬的頭髮找到話題,起風時頭髮也不會亂,對吧,玫瑰疹等長大之後就會消失了,不要太在意,還是聊窗子?我家沒有看得到外面的窗,你家有窗子嗎?
一看時間,正好中午十二點。電車穿越停滯不動的夏日熱氣前進,接著傳出「下一站神田」的混濁廣播聲。到了站,車門隨著慵懶的聲響打開時,雖然才剛到中午,一個爛醉的老人連滾帶爬地上了車,幾個乘客反射性地四散走避,男子發出低微的呻吟。灰色的鬍鬚有如散開的鋼絲球,垂掛在疲憊的工作服前襟。手上捏著皺巴巴的超商塑膠袋,另一手想抓吊環卻失去平衡,跌了個踉蹌。車門關閉,電車駛動時往前一看,剛才的女孩子已經不在了。
到達東京站,出了驗票口,難以置信的人潮讓我停下腳步,那麼多人到底是從哪裡來,又到哪裡去呢?這景象不只是單純的人潮了,宛如在欣賞一場絕妙的比賽。我有點心慌,感覺似乎有人在說:只有你不懂規則。我握緊了托特包的提把,大大吐出一口氣。
十年前的夏天,我第一次來到東京車站,當時我剛滿二十歲,也像今天一樣,汗水再怎麼擦還是不斷冒出來的夏天。
我把將近十本重要作家的書,裝進高中時代在舊衣店考慮再三才買的、呆瓜一般的登山大背包裡,一般人可能認為,不如放進搬家行李一起託運,但我卻把它們當作護身符一般,片刻不離地背在背上,扛到東京來。從那天至今十年,二○○八年的現在,三十歲的我,完全不是二十歲時我所想像的未來樣子。還沒有人讀過我寫的文章(文章不時貼在部落格上,這個沒人找得到的網路角落,每天最多只有幾個人點進來),更別說它根本還沒有印刷出版。幾乎沒有任何朋友。公寓屋頂傾斜的程度,剝蝕的牆壁,每月靠著全力打工賺的十幾萬日圓維持生活,不論再怎麼寫,也不知道自己該往哪裡去的茫然,都和十年前一樣。一成不變的生活,宛如舊書店的書架上還插滿了上一代採購的書,唯一改變的只有身體裡堆滿了十年的疲憊。
看看時間,十二點十五分,結果我比約定時間提前十五分鐘到達,便靠在沁涼的大圓柱上,眺望往來的人群。在各種說話聲、無數聲響形成的嘈雜中,一大家子抱著許多行李熱熱鬧鬧的從右往左走去。然後另一對母子走過來,小男孩緊緊握著母親的手,掛到屁股旁的過大水壺不斷搖晃;不知從哪兒傳來嬰兒的哭喊聲;男女都畫了妝的一對情侶,咧著嘴快步通過。
我從皮包裡拿出電話,確定卷子沒有來電和簡訊,也就是說,卷子母女已經按照預定時間從大阪順利的搭上新幹線,按理說再過五分鐘就會到達東京站。我們約定的地點就在丸之內北口這一帶,事前已經傳了地圖也說明了方向,不過突然有些擔憂,檢查了一下今天的日期。八月二十日,就是今天沒錯。我們約好今天,八月二十日,十二點半在東京車站丸之內北口見面。
卵子為什麼要加上「子」這個字呢,是因為精子有「子」,所以只是配合它罷了。這是我今天最大的發現。去了好幾次圖書室,但是借書的手續很麻煩,更何況那裡書少,地方小、光線差,他們還會偷看我在看什麼書,所以得要快速遮住。最近我都去比較有規模的圖書館,那裡有電腦可以查,而且學校太累了。很多地方都很愚蠢。在這裡寫下愚蠢兩字雖然也很愚蠢,不過反正學校的事得過且過就行了,但是家裡的事不能隨便應付,所以不能同時想兩件事。寫字這回事,只要有筆和紙,到哪兒都能寫,不要花錢,什麼都能寫,這是個非常好的方法。Iya 這個字,可以寫成厭和嫌,厭的字形真的有討厭的感覺,所以練習厭,厭、厭。
綠子
今天從大阪來東京的卷子是我的姊姊,今年三十九歲,比我大九歲,她有個快滿十二歲的女兒,叫做綠子。卷子二十七歲時生下了她,獨自扶養她長大。
我十八歲的時候,與卷子和剛出生的綠子三個人,在大阪的公寓一起生活了好幾年。這也是因為卷子在綠子出生前,已與丈夫分手,主要是基於人手不足和經濟上的理由,在我頻繁來去後,決定三個人一起生活比較省事。所以,綠子沒有見過自己的爸爸,後來也沒聽說他們見過面,綠子就在對自己父親一無所知的狀態下長大。
直到現在,我仍然不太清楚卷子與丈夫分手的原因。我記得當時就離婚和前夫的事,跟卷子聊了很多,也還記得我心裡認為「不能這樣做」。至於,「不能這樣做」的想法到底是針對什麼,我卻想不起來了。卷子的前夫是土生土長的東京人,為了工作搬到大阪,才認識了卷子,而且很快就有了綠子。這麼說來,我還模糊的記得他操著當時大阪難得聽見的東京腔,用「君」來稱呼卷子。
我們姊妹以前與父母,四個人住在一棟小公寓的三樓。
那是個三坪和兩坪房間相連的小房子,一樓租給酒館,因為就在港口附近,只要走幾分鐘就看得到海,隨時都能看到黑色的浪頭如鉛塊般,發出巨大聲響撞擊灰色消波塊再崩裂開來的景象。不論去到哪兒,都聞得到潮水的濕氣與滔天巨浪的氣息。但這個小鎮一到夜晚,便充斥著酒醉鬧事的男人。路邊、房屋陰影處,經常能發現有人蹲在那兒。咆哮和互毆也是家常便飯,還曾經走在路上,天外飛來一輛自行車。流浪狗到處生下許多小狗,那些小狗長大又到處生下流浪狗。但是,我們在那裡住了好幾年,我上小學的時候,爸爸不知去向,所以我們三人搬到外婆住的公營社區一起生活。
與父親只相處不到七年,但是從小我就知道他是個個子矮小,身材宛如小學生的男人。
他不工作,不分日夜躺在床上,可美外婆──我們的外婆恨爸爸讓她女兒吃盡苦頭,暗地裡都叫他鼴鼠。爸爸穿著泛黃的運動上衣和衛生褲,賴在房間最裡面的萬年床墊上,從早到晚都在看電視。枕頭邊堆滿了周刊和權充菸灰缸的空啤酒罐,房間裡永遠彌漫著香菸的煙霧。他懶得換姿勢,怕麻煩,看我們的時候甚至拿小鏡子看。心情好的時候也會開玩笑,但是基本上不太說話,印象中他從來沒有陪我們玩,或是帶我們出門過。不管他是不是躺著、看電視,還是無所事事的時候,只要心情不好就會大聲叫罵,偶爾喝了酒,便會大發脾氣毆打母親,一旦動起手來,也會藉口把卷子和我打一頓,所以,我們從小就十分恐懼矮小的爸爸。
有一天放學回到家,爸爸不見了。
房間裡待洗的衣服堆積如山,雖然與平時一樣窄小又昏暗,然而光是爸爸不在,就好像一切都變得不同了。我倒抽了一口氣,移動到房間中央,試著發出聲音。剛開始只是輕喊一聲,檢查喉嚨的狀況,接著一古腦的從肚子裡發出意義不明的囈語。沒有人在,不用說話,我隨意的扭動身體,腦袋空白隨心所欲的擺動手腳,身體越動越輕盈,感覺從身體的深處湧出了一股力量。電視機上累積的灰塵、堆在水槽裡的髒碗盤,貼了膠帶的碗櫥門、刻有身高記號的木柱紋路,隨處所見的這些東西,宛如都撒上了魔術銀粉般熠熠發光。
但是,我立刻又憂愁起來。因為我明白這一切只有一下子,很快又會回到同樣的生活。爸爸只不過是難得有事出門,馬上就會回來了。我放下書包,一如往常的坐在房間角落嘆息。
但是,爸爸並沒有回來,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爸爸也沒有回來。過了幾天後,幾個男人上門來,每次都被母親趕出去。不應門的第二天早上,玄關外一定散落著許多菸頭。這種事發生了好幾次,就在爸爸未歸過了一個月的某天──媽媽把爸爸鋪在地上的棉被整個拖出房間,使勁塞進熱水器壞掉後就沒再進去過的浴室。爸爸那張塞在霉味小空間、沾染了汗臭和菸味的棉被,黃得令人吃驚。母親注視著棉被好一會兒,狠狠的朝它踢了一腳。又過了一個月,某天半夜,母親一聲聲「快起來」把卷子和我搖醒,即使在黑暗中也知道母親走投無路的表情,她帶我們上了計程車,就此逃離了那個家。
為什麼必須逃走?三更半夜的我們要到哪兒去?我既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意義。經過了一段時間,雖然也向母親探過口風,但是談論父親好像成了禁忌,終究沒能從母親口裡得到清楚的答案。那一夜莫名其妙的摸黑走了一晚上,結果卻只是從同一城市的一角到另一角,搭電車不過一小時距離,到我最愛的可美外婆家。
計程車裡,我暈車噁心,最後吐在母親清空的化妝包裡。胃裡面沒什麼可吐的,母親一面搓著我的背,一面用手拭去和胃酸一起流下來的唾液,但我滿腦子只想著書包,裡面有配合星期二課表的課本、筆記簿、貼紙,放在最下面的白簿子畫著花了幾天、昨天晚上才完成的城堡圖,側袋的口琴。垂掛在旁邊的便當袋,剛買不久、裡面放有心愛鉛筆、馬克筆、香氣珠和橡皮擦的鉛筆盒、金蔥棒球帽。我喜歡書包,晚上睡覺時都放在枕頭邊,走路時緊緊抓著肩帶,不論什麼時候都很寶貝它。我把書包當成只屬於自己的房間,而且可以隨身攜帶。
但是,我卻把它留在那裡了。還有心愛的白色運動衫、娃娃、書、飯碗,我們把它們全都留在家裡,在黑暗中奔走。我想,大概不會再回那個家了吧。我想,我再也不會背上我的背包,再也不會把鉛筆盒放在暖桌的角落,翻開筆記簿寫字,再也不會那樣削鉛筆,和靠在粗糙的牆壁上看書了吧。想到這裡,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腦中的一部分慢慢麻痺無法思考,手腳也使不上力氣,只是無意識的想著,這個我還是真正的我嗎。因為,剛才的我還在想,明天一早,我會和平常一樣醒來,到學校去,然後和平常一樣度過一天。剛才閉上眼睛睡覺的我,說什麼也想不到幾個鐘頭後,竟然會丟下一切,和母親、卷子坐上計程車在黑夜中奔馳,再也回不來了。
凝視著流過窗外的深沉黑夜,有種剛才一無所知的自己還睡在棉被中的錯覺。到了早上,發現我已經不在的我,究竟要怎麼辦好?這麼一想,突然擔心起來。我把自己的肩緊緊壓在卷子的手臂上,漸漸有些睏倦。從垂下的眼皮縫中,看得見閃著綠光的數字。離我們的家越遠,那數字則無聲的不斷增加。
這段相當於逃難投奔親人重新開始的四人生活,卻沒有持續多久。可美外婆在我十五歲那年過世,而母親早在兩年前,也就是我十三歲時撒手人寰。
突然只剩姊妹倆相依為命的我們,把從佛龕後面找到可美外婆的八萬塊當成護身符,從那時起,我們開始全力打工過活。從剛上國中,母親發現乳癌起,到可美外婆因肺腺癌隨母親而去的高中時代,我幾乎沒什麼記憶,因為打工實在太忙了。
若說還能想起什麼,就是國中春、夏、冬季長假時,我虛報年紀到工廠打工時的風景。從天花板垂掛下來的烙鐵電線與火花聲,堆積如山的紙箱。印象最深的還是從小學就進出的小酒吧,那是母親朋友經營的小店,母親白天兼做幾份工,晚上就到店裡上班。卷子讀高中時先一步在店裡洗碗打工,隨後我也在廚房幫忙,看著母親招呼酒醉的客人,一面調酒做下酒菜。卷子洗碗之外,同時又在燒肉店兼職,展現非比尋常的勤奮,當時時薪六百日圓,她一個月最高可以掙得十二萬圓(在店裡成了小小的傳奇)。高中畢業幾年後,升為正式職員,後來一直工作到倒店為止。然後懷孕、生下綠子,換了許多份兼差,現在三十九歲,她還是一星期在酒吧工作五天。也就是說卷子與單親扶養我們、拚命工作、最後生病去世的母親,過著幾乎相同的生活。
約定的時間過了快十分鐘,卷子與綠子還沒有來到會合的地點,打電話過去卷子也沒接,而且也沒有回短訊,該不會是迷路了吧。等了五分鐘再打一次時,響起喀啦喀啦的短訊通知音:
〈不知道從哪邊出去比較好,所以待在下車的月臺。〉
我在電子顯示板上查出卷子母女搭乘的新幹線車號,在賣票機買了月臺票走進驗票口。搭手扶梯升到地面時,蒸氣浴般的八月熱風直撲而來,汗水泉湧而出。我閃過等待下一班列車的群眾和在書報攤前購物的客人,繼續往前走。在第三車廂位置的長椅上看到兩人。
「啊──,好久不見。」
卷子一發現我便開心的笑了,我也跟著笑。坐在隔壁的綠子長高了好多,彷彿瞥見她的瞬間,突然長大了一倍似的。我忍不住大叫:
「天啊,綠子,你這兩條腿怎麼長的?」
把頭髮梳高綁成馬尾,穿著深藍色素面圓領T恤的綠子穿著短褲,從短褲伸出的筆直雙腿──也許是坐在椅邊的關係,看起來出奇的長。我拍了一下她的腿,綠子反射性的露出像是羞澀又像困窘的表情看著我。但卷子插話說:你看,很厲害吧。長這麼大了,嚇一跳吧。綠子霎時沉下臉,轉開視線,把放在旁邊的背包拉到身邊抱住。卷子看著我,擠出一個無奈的臉,微微搖頭,聳起肩,好像在說「看吧」。
綠子已經半年不與卷子說話了。
原因不明。某天無預警的,卷子叫她,她卻不回應。剛開始時卷子還擔心是不是心理性疾病之類,但是綠子除了不說話外,不但胃口非常好,而且正常去上學,也與朋友、老師照常說話,過著和以前一樣的生活。總而言之,綠子只有在家裡拒絕與卷子說話,是故意的舉動。不論卷子如何用盡心思想問出原因,綠子仍舊頑固的拒絕回答。
1 你,家裡窮?
想知道一個人到底有多窮,只要問他老家的窗子有幾扇,就能一目了然。平日的吃穿都說不得準,想知道貧窮的程度,唯有數窗子。沒錯,貧窮就是窗子的數量。沒有窗子,或者窗子的數量越少,多半可以判斷那個人到底有多窮。
以前,我跟某個人說起這個理論時,她反駁說,不一定吧。她的說詞是這樣的,「就算是只有一扇窗,但是有可能那是一扇面對庭院、大到不行的窗子啊。家有那麼豪華的大面窗,怎麼可能算是窮人呢?」
但是,讓我來說的話,這是已經脫離貧窮的人才會有的想法。面對庭院的窗,大面窗,請問一下,庭院是什麼?...
目錄
第一部二〇〇八年夏
1 你,家裡窮?
2 追求更高層次的美麗
3 乳房屬於誰
4 到中式飯館來的人們
5 夜裡姊妹的長談
6 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7 所有熟悉的事物
第二部二〇一六年夏~二〇一九年夏
8 你的企圖心不夠
9 小花簇擁
10 從下一個選項中做出正確的選擇
11 在腦海裡見到朋友,所以今天很開心
12 快樂的耶誕
13 複雜的命令
14 拿出勇氣
15 出生與不出生
16 夏之門
17 與其遺忘
主要參考文獻
第一部二〇〇八年夏
1 你,家裡窮?
2 追求更高層次的美麗
3 乳房屬於誰
4 到中式飯館來的人們
5 夜裡姊妹的長談
6 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7 所有熟悉的事物
第二部二〇一六年夏~二〇一九年夏
8 你的企圖心不夠
9 小花簇擁
10 從下一個選項中做出正確的選擇
11 在腦海裡見到朋友,所以今天很開心
12 快樂的耶誕
13 複雜的命令
14 拿出勇氣
15 出生與不出生
16 夏之門
17 與其遺忘
主要參考文獻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