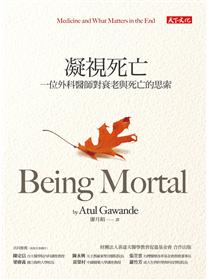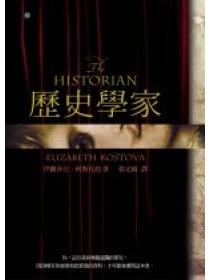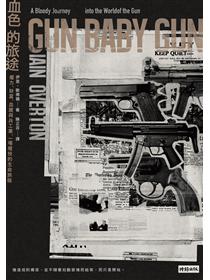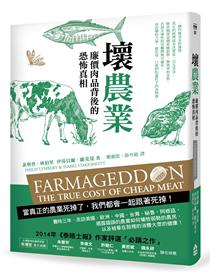我從第一天在急診室行醫,就開始做的例行祈禱:
「求求你們不要來得太晚,而且看在老天爺份上,也不要來得太早。」
在醫療上,時機就是一切。
如果你來得太遲,我沒有辦法救你;
如果你來得太早,我恐怕會看不出你哪裡有問題,因為症狀太過輕微。
有好幾種戲劇性的手段,可以在急診室引起關注。
一種是停止呼吸,另一種是昏厥並倒地。
脫衣服或是在候診室尿尿,也會產生不錯的效果。
來場癲癇發作也行。
說得殘酷一點,急診醫師的工作是「輸送肉品」。
所謂肉品,就是指你們啦。
每一年將幾萬名病人從急診室送出去,
需要決斷、效率和狡滑,外加一點兒運氣。
我(作者高曼醫師)發現,我職業生涯中的一大重要目標,
不只在於幫助需要醫療照護的人,
我還想要治療醫療體系本身,去揭露它的真面貌,
揭露它所有的長處、短處和藉口。
感人肺腑……帶您一窺急診室大門背後,
那個有時充滿戲劇性、有時平淡到乏味的,生與死僅一線之隔的世界。
—— 加拿大《國家郵報》
急診室既是生死一線之隔的地方,也是醫療糾紛的是非之地,
每個夜晚都在上演悲歡離合的人生戲劇,
有時以喜劇收場,有時以悲劇收尾。
高德曼醫師以誠懇而帶有淡淡幽默的筆調,
用一篇篇真實的故事,告訴我們:
所有你想像不到的肥皂劇情,都有可能在急診室裡活生生上演。
我寫這本書,是為了你們。
你們當中大部分人,遲早會需要像我這樣的急診醫師的服務。
你們當中很多人可能會想知道,
在急診室那道玻璃門背後的真相,
以及你們是否可以信任那裡的醫護人員……
我希望能夠帶領你們進入急診室,
展示急診室真正的運作方式,讓你們像我一樣了解急診室。
我希望經由這樣做,能揭開這份職業的神祕性,
讓你們更容易理解、以及面對「掛急診」這回事。
—— 布萊恩‧高德曼(本書作者)
作者簡介:
布萊恩‧高德曼(Brian Goldman)
在舉世少見的醫、媒兩棲職業生涯中,高德曼醫師賦予自己的任務是:解開醫學世界的神祕。《夜班急診室:急診醫師筆下的真實人生》是他的第一本著作,透過一則則精采故事,告訴大家:急診室可不像電視劇塑造的那樣。《夜班急診室》揭露了急診室裡,外人難以窺知的內部運作模式,並指出一名好的急診醫師,需要具備怎樣的觀察力、決斷力和處置力;並且坦誠檢視今天醫學界面臨的諸多問題,包括:論件計酬制、醫師為什麼會犯錯、病人與醫師之間關係的分際,醫師與藥廠之間的互惠文化……提供他獨到的洞見。
高德曼醫師在TED Talk主講的「我們能談談醫師會犯錯嗎?」(Doctors Make Mistakes. Can We Talk About That?)已吸引了超過一百萬人次瀏覽。他的最新著作是《醫師的密語》(The Secret Language of Doctors)。
譯者簡介:
楊玉齡
輔仁大學生物系畢業。曾任《牛頓》雜誌副總編輯、《天下》雜誌資深文稿編輯。目前為自由撰稿人,專事科學書籍翻譯、寫作。
著作《肝炎聖戰》(與羅時成合著)榮獲第一屆吳大猷科普創作首獎金籤獎、《台灣蛇毒傳奇》(與羅時成合著)獲行政院新聞局第二屆小太陽獎。
譯作《生物圈的未來》獲第二屆吳大猷科普譯作首獎金籤獎、《消失的湯匙》獲第六屆吳大猷科普譯作銀籤獎、《大自然的獵人》獲第一屆吳大猷科普譯作推薦獎、《雁鵝與勞倫茲》獲中國大陸第四屆全國優秀科普作品獎三等獎。另著有《一代醫人杜聰明》;譯有《基因聖戰》、《大腦開竅手冊》、《兒腦開竅手冊》、《奇蹟》、《念力:讓腦波直接操控機器的新科技‧新世界》、《幻覺》等數十冊(以上皆天下文化出版)。
章節試閱
第一章 生命的氣息
☉ 星期五夜晚,九點十五分
住在多倫多北區的我,連走帶跑的趕往我家附近的地鐵站,一步兩個臺階往下衝,生怕不能準時趕到醫院。我最恨上大夜班遲到了。我受不了看見同事對我擺臭臉,因為他操勞到晚上還不得離開,必須等遲到的我來接班。說我神經質也可以,從小我就不是會曠課的學生(雖然我經常幻想這麼做),我總是擔心不能準時。不過,我的個性很一致,如果有同事接我的班遲到,我也一樣不高興。
讓我壓力更大的,是每次接班前都會油然而生的焦慮感。雖說我看急診已經超過二十五年了,每次上班前,我還是會緊張。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即使我有這麼多的經驗,還是有些東西我不知道,有些技術我比不上同事。很少有醫師願意承認這個,但是,我可不怕說實話。
等到我的地鐵列車進站,我就開始放鬆下來。往南開到西奈山醫院不需要太久,至少我這麼想。然而,就在快抵達我要下車的車站時,列車忽然尖叫一聲,停了下來。擴音器廣播說,另外某個地方發生緊急事件,所以造成了「輕微的延誤」。我的血壓頓時升高,我咒罵這樣的等待。我最恨自己不能掌控了。謝天謝地,在漫長的十分鐘之後,列車開始慢吞吞的前進,開向我的目的地。
我快步爬上地鐵站的樓梯,進入深沉的夜色之中。我想直接衝進醫院的急診室,但還是先在Tim Hortons停下來,買一大盒一口甜甜圈,外加一大杯咖啡。喝咖啡可以讓我保持清醒;甜甜圈則是給護理師們享用,這樣她們更容易記得,在我的病人情況惡化、尤其是心臟快要停止的時候,趕緊讓我知道。
我匆匆經過莫雷街上的西奈山醫院入口,然後下了臺階,沿著走廊進入急診醫師的辦公室。我換上綠袍,抓起我的聽診器,扔了幾顆普衛醒錠到口裡(很多值夜班的醫務人員都服用普衛醒錠,以幫助頭腦保持清醒),和著咖啡吞下肚。你如果是一名五十幾歲的急診醫師,你真的需要利用各種方式保持頭腦清醒和敏銳。
我無聲的向我的病人祈禱,那是我從第一天在急診室行醫,就開始做的例行祈禱:「求求你們不要來得太晚,而且看在老天爺份上,也不要來得太早。」在醫療上,時機就是一切。如果你來得太遲,我沒有辦法救你;如果你來得太早,我恐怕會看不出你哪裡有問題,因為症狀太過輕微。
接著,在我開始值班之前,我喃喃自語的說出一句不敢大聲說出口的禱告:「拜託,不要讓我搞砸了。」
在通往急診室的走廊上,我踏進候診室,看看今天有多忙。這是一個很小的房間,三十張椅子塞在三點五公尺乘三點七公尺大的空間。病人以及他們的家屬朋友,占據了大約四分之三的椅子。一部電視機安裝在候診室靠近外門口的角落,面對著護理師。這種座位安排意味著,半數的病人及訪客除非歪著脖子,否則是看不到電視的。
我站在分隔候診室與急診室的雙扇推門外。在我右手邊,一名護理師正在檢傷站幫病人量血壓。一排病人等著要掛號。在我正前方,兩臺救護車的擔架床分別由兩組醫護人員包夾著,上頭各躺一位病人。後頭還有四位病人躺在擔架床上,形成一條隊伍,蜿蜒到相連的走廊上。嗯,今晚將會很繁忙。
☉ 夜間十點整
「高德曼醫師,請到急救室,立刻!」病房祕書的嗓音嘹亮的從擴音器裡放送出來。
一名七十二歲的老婦人,我姑且稱她為蘇菲亞,癲癇正在發作。她的手臂和腿很有節奏的抽動著,一道白色的口沫出現在她嘴邊。她的眼睛是張開的,但是眼神呆滯,直視前方。一名護理師在旁邊呼喚她,她沒有回應。
「她有肺癌,正在做化療,」一位送她來的救護員這樣告訴我。
「她有癲癇病史嗎?」
「這我就不知道了,」他邊回答,邊和另一位救護員一起將她從救護車的擔架床,轉移到我們醫院的輪床上。
「她發作多久了?」
「差不多兩分鐘,」他說。
癲癇發作是由腦內過量的活動或是同步的活動引發的短暫狀態。有癲癇,通常代表你天生具有這方面的傾向。其他原因還包括:出生時因缺氧導致腦部損傷,曾經罹患腦膜炎或是中風。另一個常見的病因則是腫瘤。蘇菲亞的肺癌令我擔憂癌細胞已經擴散到腦裡,那會是很不祥的致命發展。但是推論病因可以等一下,現階段我得先止住她的癲癇發作。發作時間拖得愈長,腦部缺氧而受損的風險就愈大。
「給她十毫克的二氮平(diazepam),」我下達指令。
一名護理師將這種鎮定劑(目前能採用的、可快速止住癲癇發作的藥物之一)抽到一管針筒裡,然後幫她注射。不出一分鐘,發作就停了,我的病人開始甦醒過來。就在發作剛剛停止的當兒,蘇菲亞的兒子走了進來。
「我是高德曼醫師,我負責照顧你母親。請問她有癲癇病史嗎?」
「沒有,」他說:「只有癌症。」
我解釋癌症可能已經擴散到他母親的腦裡,我們暫時用二氮平把發作止住了。我指示護理師,用靜脈點滴幫她注射第二種藥物,叫苯妥英(phenytoin),以防止癲癇復發。我告訴蘇菲亞的兒子,我們會把他母親安置在急救室裡,注意她的情況。
「讓我們先做一次頭部電腦斷層掃描,」我對護理師說,心裡默默盼望她腦中沒有任何癌細胞的影子。
這可不是我先前對今晚值班所期待的——良好的、輕鬆的開始。
身為急診醫師,我的首要職責是應對病人。如果你有一個傷口,一處扭傷,或是斷了一根骨頭,我的工作就是把你修補起來,然後打發你回去。如果你得了危及性命的重病,我的工作就是先保住你的性命,直到我或其他醫師想出你的問題是什麼。如果你想自殺,那麼我的工作就是阻止你得逞。
我的第二個職責是應對這個急診體系。說得殘酷一點,我的工作是「輸送肉品」。所謂肉品,就是指你們啦。每一年將大約四萬七千位病人從急診室送出去,需要決斷、效率和狡滑,外加一點兒運氣。西奈山醫院總共有四百七十二個床位,大部分時間,超過百分之九十都有人占用。要找一張空病床,一直都很困難。樓上每有一位病人不能出院,樓下急診室裡就會有一位病人沒法往樓上送,而候診室裡也會有一位病人沒法進到急診室來。
我一次只能看一位病人,但是誰也無法攔阻數不清的病人源源不斷上門來,或攔阻救護員半小時內送來半打躺在擔架床上的病人。對於這種嚴酷情況,我們稱之為受到「撞擊」或是「洪水氾濫」。有一次,一名檢傷護理師看到一整排病人從掛號處排到急診室入口,不禁嘆息道:「巴士剛剛進站。」那是我最喜歡的表達方式之一。
我們一邊和時鐘賽跑,一邊努力執行安全又有效率的急診醫療。二○○一年,美國急診醫學會發布一篇立場聲明,指出醫師每小時看診人數不應該超過二點五人。然而,有一篇由芝加哥急診醫師冉恩(Leslie Zun)撰寫的報告發現:各式各樣的行動準則要求急診醫師,每小時看診一點八人到五人之間。
平常我在剛開始值夜班的時候,效率最高,每小時可以看三到五位病人。而每天晚上協助我的,還有十到十二位護理師(包括檢傷分類護理師)、至少一位住院醫師,以及可能再多一位醫學生。照護像蘇菲亞這類緊急病人,很刺激,我很喜歡。但是當病情像她一樣嚴重的病人來到急救室,我得丟下一切事務,去照護她,於是生產線就得暫時停擺。而且就算我拚命趕工,也沒有辦法在初次看診時,就完成與病人的互動。因為通常需要好幾個鐘頭後,才能拿到病人的X光或電腦斷層掃描結果,而我也才能叫病人回家或是安排他們住院。隨著夜色漸深,我總是必須不斷再評估既有的病人,但同時還必須看新病人。到了清晨四、五點,我每小時只能再診療大約兩位新病人了。
另一個拖慢急診醫師的因素是,我們必須面對頻繁的干擾。急診室裡的每一個人,不論是護理師、病人、家屬或住院醫師,好像都認為他們可以隨時隨地和我們閒聊兩句。我就遇過當我在為病人進行骨盆檢查時,住院醫師就那樣走進來,和我大談他們的病人。
印第安納大學醫學院的急診醫師屈森(Carey Chisholm,也是美以美醫院急診創傷中心的醫師),曾經研究急診室值班期間最常見的干擾。他發現:平均而言,急診醫師一個晚上會遭到干擾五十二次。其中二十一次干擾非常嚴重,迫使急診醫師停下手邊所有的工作,開始做別的事。
在航空界大家都曉得,干擾機師會釀成很嚴重、甚至是致命的錯誤,因此航空業會盡量防範,讓干擾減到最低。但是在急診室可沒有。你可能正在試圖搶救某人的生命,護理師卻在一旁要求你下口頭醫囑,開一份止痛藥。你如果膽敢聲稱你正在忙,別人就會用一種「發什麼脾氣」的眼光看著你。
吵雜是急診室工作的另一項妨礙。西奈山醫院急診室經常會發動一波波強烈的機械警鈴攻勢。病人床邊的警鈴會發出一串由兩個音符組成的聲音,中間有稍長的停頓。那音符就和一九七五年由巴西歌手莫利斯.艾伯特演唱的經典搖滾歌曲〈感覺〉(Feelings,原為法國作曲家Louis Gaste所寫)的頭兩個音,一模一樣。每次一聽見那警鈴聲,我心中就會立刻開始播放那首歌。沒辦法,我就是會這樣。
加上人們痛苦的尖叫,精神病人的妄想哀號,以及阿茲海默症和其他失智病人一再重複的唸誦,讓人禁不住好奇,醫師怎麼有辦法像我們這樣專心工作呢?
急診室可不像電視劇塑造的模樣
情況並非一向如此。一九二三年,這所醫院剛成立,是一所擁有三十三張病床的婦產暨康復醫院。一九五三年,新的西奈山醫院在大學大道開張,位置就在知名的多倫多兒童醫院對面。一九七三年,醫院往北邊搬了一戶,到現在的位置。如今西奈山醫院已經成為訓練醫學生和住院醫師的頂級醫學機構。我們非常自豪,因為我們擁有世界級的研究機構,而且我們照護了一個日漸增長的社區,裡頭有許多複雜的病人。對此我很了解,因為我們在急診室見過很多。
一九八四年,我剛開始在西奈山醫院工作時,每次值班大約看八到十二位病人(每天從那扇玻璃門進來的病人約七十人)。那樣的年代早已成為過去。人口增長,加上鄰近關閉了好幾家醫院,意味著我們的病人數量大大攀升。現在,西奈山醫院的施瓦茨—雷斯曼急診中心,每天要看一百二十名到一百三十名急診病人(一年約合四萬七千人),而且還在增加之中。有時候,我們急診室一天看診的病人超過一百六十名。在平常的星期五大夜班,我在次日早晨七點交班前,得看三十位到四十位病人。
而且改變的不只是數量。我們所謂的劇烈程度,也就是病人的病情嚴重程度,也改變了。以前我們大部分看的病人都是心臟病發或肺炎或潰瘍。如今,最典型的西奈山急診病人可能是糖尿病、高血壓、心血管問題、腎衰竭或是癌症。先進的血管成形技術以及更好的化療,帶來利弊參半的結果。病人的壽命變長了——在我剛開始行醫時,九十幾歲的病人非常稀有,如今已變得很尋常。
隔開候診室與急診室的那扇門,「簡直就是通往另一個宇宙的門,」曾撰寫過許多本醫學書籍的佩齊(Wayne Pezzi)醫師這麼說。佩齊醫師在美國從事急診醫療已超過十年。他說,急診室可不像電視劇塑造出來的樣子,一個光鮮亮麗的、或是不斷出現很刺激的急症創傷的世界,雖說那些描述也有吻合的時刻。
「人們一想到急診室,最先想到的就是鮮血、腸子,」佩齊醫師說:「其實他們也應該要想到糞便、尿液、嘔吐物,以及從各種部位冒出來的膿液、不堪一提的骨盆分泌物,此外還要面對鬧脾氣、滔滔不絕的髒話、威脅、各種言詞辱罵,偶爾還會被人揍兩拳。事實上,急診醫師大部分所做的事,以及必須忍耐的事,都與光鮮亮麗正好相反。甚至可以說是非常噁心的事,例如幫某位病人『解除阻塞』。(我的白話翻譯是:把直腸裡的硬大便給摳出來。)」
和電視不一樣,這裡沒有源源不絕的擔架床通過推門,一隊醫護人員一邊推著擔架床奔跑,一邊忙著嘗試各種動作來搶救垂死的病人。這種場面在西奈山醫院尤其少見,因為除了特殊狀況之外,這裡並不診療槍傷或車禍傷患。那些病人通常會給送往市內其他專門處理那類型創傷的醫院。
但這並不表示西奈山醫院的病例缺乏戲劇性,只是方式不同。我們診療的病人各式各樣,從心跳停止到未知皮疹都有。少數病人面臨死亡的風險,但是大部分沒有。就某個程度而言,他們全都自認病情嚴重,否則不會跑到急診室來。在這裡,他們有時候得熬過漫長乏味的候診時光。
我會成為急診醫師,幾乎是一個意外。讀醫學院時,我對神經科學產生了興趣,也就是專門處理中風及其他腦部疾病的專科。我太喜歡這一科了,四年級的時候,我就做出一個現在想來很衝動的決定:我要成為小兒神經科醫師。我順利申請進入多倫多的兒童醫院來實習。一九七九年,我在醫學院的最後一年,我到巴爾的摩約翰霍普金斯醫院神經科,接受兩個月的輪訓。當時約翰霍普金斯有一項世界著名的神經科學住院醫師計畫。我去那兒受訓的目的,就是為了要贏得未來的指導老師的青睞。
訓練期間,我開始懷疑自己的生涯抉擇。更糟糕的是,我覺得很孤單,很想家。在我受訓的一個關鍵日子,我本來預計要上臺報告,結果卻睡過頭,錯失了在上級面前表現的機會。
我悽悽慘慘的回到多倫多。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才明白,那天早晨,我的守護天使其實是救了我。現在我知道,神經科學對我來說,是一條沒指望的路。哦,我還是可能做得不錯。但是在我靈魂深處,有某種創新的東西在攪和,好幾年後才會明朗。睡過頭,讓我免於對未來職業及生活的懊悔。
不過,我當時已經向兒童醫院提出申請,而且也獲准擔任第一年住院醫師,算是我第一年接受兒童神經科醫師的專業訓練。我不能退出。我完成那一年的訓練,然後轉到當時的新寧醫院,在那裡接受為期一年的內科住院醫師訓練。
到了那個時候,我已知道自己想要寫作。我曾嘗試寫一篇小說,但是沒能完成。一九八一年七月,我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環球郵報》的科學版。那次成功經驗讓我相信,我想要開發自己在寫作上的興趣。剛好就在那個時候,急診醫學向我招手。我認識一些住院醫師同事在當地醫院的急診室兼差、賺外快。我決定也要嘗試一下,很快就發現急診醫學非常刺激,而且能讓人獲得智能上的滿足。更棒的是,它是兼任的工作,讓我有很多時間來寫作,以及從事廣播工作。
在這一行,犯錯是會害死人的
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在我開始急診醫師生涯沒多久,我經歷到第一次以急診主治醫師身分,參與搶救心跳停止的病人。我那時是在多倫多藍領社區的西北總醫院值夜班。
就像許多壓力大的工作環境,例如執法人員、記者等等,醫學老鳥總是會觀察(和測試)新人,看他們能不能在壓力下保持冷靜,並判斷他們是否具有幽默感。資深護理師和救護員對年輕醫師的評判,往往最是嚴格。他們碰過太多自大的醫學院畢業生,這些人不懂得尊敬前輩醫護專業人員所擁有的廣博知識與經驗。
一天晚上,一名男病人心臟病發,被送進急診室。他失去心跳起碼已經十分鐘了,甚至可能更久。雖然每個人都知道他已經死了,但是急救小組還是得嘗試讓他復甦,希望奇蹟能夠發生。我在當住院醫師期間,曾經上過高級心臟救命術的課程,這是一次將理論轉化為實務的機會。身為急救小組龍頭,那天晚上我的角色是:找出我們的病人心跳停止的原因以及如何挽救。貼在我的病人胸口的電極片告訴我,他是心搏停止——沒有心律,而且將他搶救回來的機會很小。
情急之下,我趕忙讓心臟電擊去顫器充電,準備用三百焦耳的電流能量去震搖他的心臟。我把凝膠塗在電擊器上,然後壓在病人胸前,一個在胸骨右側,一個在病人左乳頭上。我大喊「clear」(離手),要所有與病人輪床接觸的人閃開,以免受到電擊。經過小心確認後,我按下電擊器上的按鈕,然而,迎接我的卻是一縷輕煙以及刺鼻的皮肉燒焦味。原來我不小心讓其中一個電極碰到一條心電圖描記器的引線,而那條引線接在病人胸口的一片貼紙上。我驚駭的發現,那片紙竟然燒了起來,雖然只有短短一下子。
一名頭髮斑白的護理師(她看起來好像在過去幾十年生涯中,每天都要抽個兩包香菸的樣子),從她那遠近兩用眼鏡片上方瞥了我一眼,一邊輕輕搖著頭說:「好啦,他就算原本沒死,現在肯定也死了。」這話引發一陣哄笑。我也跟著笑,但心裡覺得好丟臉。這是一次令人謙卑的經驗,我很高興它發生在我職業生涯的初期。
做我們這一行,犯錯是會害死人的,而這份沉重的責任並不容易面對。(我可以稍感欣慰的說,本案不是這種狀況;當時我們不管怎麼做,都無法挽回這人的生命。)有些醫師發現,很難承認自己也是凡人,也會犯錯。有些醫師發覺,去面對這個醫療體系裡有某些部分失靈,需要改進,也同樣困難。如果承認這些不足之處,他們可能就必須質疑工作裡的某些面向,而他們寧願不要去承認或檢視。
那名護理師的黑色幽默,那天確實挫了我的銳氣。我不知道,我是否需要那樣的當頭棒喝,因為我對待自己總是比別人對待我更加嚴格。但是,這個經歷至少無害。它始終是一個鮮活的記憶,關於我有可能犯下大錯,以及當我造成錯誤時,需要用哪一種態度來回應——在本案例,是用幽默和謙遜來回應。
當時我無法真正欣賞那名護理師的幽默,因為我被這種生死攸關的場面嚇呆了,就像你在幫病人插管的時候(所謂插管,就是將一條呼吸管插入病人的氣管裡)。我們做這個動作,是因為病人的肺部損害太過嚴重或是充滿液體,如果不靠人工呼吸器,無法吸入足夠維生的氧氣。我們這樣做的另一種情況是,當病人意識非常低弱,可能是因為頭部受傷或酒醉或嗑藥,以致無法防止食物或是嘔吐物從食道湧出來、灌進肺部,這種狀況稱做抽吸(aspiration)。抽吸的病人有可能當場呼吸停止,或是在幾天之後,因吸入性肺炎和休克而死亡。
在我職業生涯早期發生的另一件插曲,也對我在急診室的工作方式產生重大的影響。有一位病人因為精神問題住進某家醫院,但是他不告而別,自行離院,就是我們所謂的「逃走了」。不久之後,他進入地鐵站,跳到一列電車面前,當場死亡。我當時工作的那家醫院的救護員,將他的屍體帶回醫院,因為他必須經過正式的死亡宣告。
他們將他送到一個房間,安置在一張床上,然後用被單覆蓋起來,只露出頭部。當時我還沒有看過太多屍體,而每次凝視一具沒有生命的軀體,對我來說,總是肅穆的一刻。他的眼睛好像睡著般閉著,彷彿終於掙脫心魔,得到安息。然而,當我掀開被單時,立刻一陣反胃。我原先並不知道電車令他身首異處。救護員開了個玩笑,把他的軀體翻轉過來,因此他的頭雖然是臉朝上,但是他的身體卻是背朝上。我覺得一點都不好笑,我差點嘔吐出來。
那天晚上救護員的所作所為,非常侮辱人。我能欣賞黑色幽默,也隨時準備受人消遣,就像那天我電擊失敗,護理師對我的嘲諷。但是這個舉動,實在太超過了。說句公道話,那件事發生在超過二十年前,現在我所認識並且一起工作的救護員,都相當謙恭和敏感,而且相當專業。近年來,我從沒聽過像那樣的惡作劇。如果今天發生這種事,我會非常驚駭。沒錯,醫療工作人員可能對生老病死見怪不怪,因為我們看得太多了。但是我不認為我們應該變得如此殘酷無情,把受苦之人的自殺,當成開玩笑的材料。那樣做,我們有可能變得麻木不仁,無法碰觸自己的良心,也無法體會在急診室裡的病人及其摯愛的人所受的苦痛。我希望自己永遠不要變成那個樣子。多年前那幅可怕的影像,對我來說依然歷歷在目,它成為我的提醒者,提醒我:以醫師身分接觸他人時,要用我希望自己的親朋好友受對待的方式,來對待他們。
第一章 生命的氣息
☉ 星期五夜晚,九點十五分
住在多倫多北區的我,連走帶跑的趕往我家附近的地鐵站,一步兩個臺階往下衝,生怕不能準時趕到醫院。我最恨上大夜班遲到了。我受不了看見同事對我擺臭臉,因為他操勞到晚上還不得離開,必須等遲到的我來接班。說我神經質也可以,從小我就不是會曠課的學生(雖然我經常幻想這麼做),我總是擔心不能準時。不過,我的個性很一致,如果有同事接我的班遲到,我也一樣不高興。
讓我壓力更大的,是每次接班前都會油然而生的焦慮感。雖說我看急診已經超過二十五年了,每次上班前,我還是會緊...
作者序
前言 急診室的真實人生
有人選擇在夜晚工作,有人則是被夜晚選擇。我想我就屬於後者。
回溯到一九八二年一個春天的夜晚,也就是在我進入西奈山醫院的前兩年,我到多倫多一家社區醫院急診室兼差,這家醫院位在一處少數族裔社區的中心。那天晚上,有一名年約六十出頭的維修工人,來到急診室掛號,抱怨肚子痛、想嘔吐。
「我想大概是食物中毒,」他告訴一位急診護理師。
護理師轉告我,但是不知怎的,我的雷達突然拉起警報。雖然我那時還很沒經驗,但是有一件事我很清楚:有些病人會嚴重低估自己的症狀。這人是東歐族裔,是那種很有男子氣概、但話不多的男人,那種人往往覺得承認身體不舒服到無法工作的程度,非常丟人。如果他對護理師說他覺得有一點不舒服,他真正的症狀極可能嚴重得多。
當我幫他做檢查時,他說他吃了一份雞肉三明治,過後他只想把它吐出來。「幫我把它吐出來,可以嗎?然後我就要回去做工了,」他對我笑了一下,暗示真的沒必要大驚小怪。然而,我的直覺卻告訴我,不是這麼回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心底有一個小小的聲音響起(我在診斷病人時,常常會在心裡進行這種自我對話),這個聲音說:此人情況危急!
我拿起他的病歷,看到他有糖尿病的病史,以及高血壓和高膽固醇的問題。然後我用手觸診他的肚子。當醫師在輕壓病人的腹部時,我們是在檢查有沒有需要開刀的病徵,例如盲腸炎。那天晚上,基於某些至今我仍然不了解的原因,我把右手放到那名維修工人的腹部,一路滑到他的肚臍上,好像預料會摸到什麼致命的東西。我的發現完全如我所料。
在他腹腔中央右側,有一團規律跳動的腫塊,摸起來像是一個就快要爆炸的車胎,而且它寬達九公分。原來他有一顆動脈瘤,長在主動脈裡,而主動脈是從心臟左心室流出來供給諸多重要器官的大血管。我偵測到這顆動脈瘤的位置和肚臍差不多高,約略就在供應腎臟血流的腎動脈上面或是下方一點點。動脈瘤如果直徑超過三公分,腹腔主動脈就會膨脹起來。五公分,他就需要開刀。九公分,那他必須恐慌了——如果動脈瘤在他回家或是工作的時候爆開,他將會大量流血而死。
我需要找一位外科醫師立刻幫這人動手術,我得拿起最近的一支電話,看看是誰在待命。在我去打電話時,我經過最早叫我檢查這位病人的護理師身邊。
「食物中毒,對吧?」她問。
我盡量克制不要露出沾沾自喜的樣子。「改成腹腔主動脈瘤看看,」我說。
「噢,我的天哪!」她嚇一跳。
當時剛過清晨五點。我能把待命的外科醫師馬上弄到急診室來嗎?我那時還是新手,完全不知道他會做何反應。然而,我才向他描述不到十秒鐘,他就說:「等等。讓我猜一下。你認為這位病人有一顆主動脈瘤。」我當場呆住,他這麼快就猜到了。但在同時,我也很高興他和我看法一致。「我們最好趕緊找個血管外科醫師過去。」
最後是由他親自打電話到血管外科醫師家裡,把他叫醒。等到六點十五分,外科醫師已經趕到,準備動手術。我永遠忘不了當時的情景,在他們檢查那人的肚子時,我在一旁等待答案揭曉,看自己是否浪費了外科同事的時間。他們做完檢查後,其中一人轉身對我眨眨眼,表示讚許。啊,那可是急診醫師能夠獲得的最高禮讚。
當手術小組準備幫病人開刀時,他們問我想不想刷手,意思就是在一旁協助。這是一個尊重的信號,是認可我剛才在專業上的表現。我當然毫不猶豫,馬上接受這份邀請。
在我進入開刀房之前,外科小組對我補充說明整個狀況。他們一剖開那人的肚子時,動脈瘤就爆開了。當動脈瘤很脆弱、而且腹腔裡的氣壓和手術房的氣壓相當時,經常會發生這種情況。幸好外科小組早就預料到了。血管外科醫師很冷靜的夾住動脈瘤,然後花了兩個小時,將一片由達克龍(Dacron)製成的移植片,縫合上去。手術過後,病人被轉進加護病房。十天後,他康復出院。
那天早晨離開急診室的時候,我筋疲力盡,腎上腺素高張,而且心中充滿敬畏。要是我同意護理師最初的食物中毒判斷,我大概會建議病人多喝一點清淡液體,來減輕雞肉造成的不適。然後我會叫他回家去——等死。但是某種神祕又奇妙的力量,阻止我那麼做。
這就是急診醫師的實際生活
這件事捕捉到我在急診室上夜班會遇到的重大挑戰。我的工作和警察、救護員或消防員一樣,是在人們入睡時,提供一項基本的服務。你如果和我一樣,在急診室工作了這麼久,你就會知道應該要這樣想:除非病人出現(或自以為出現)危及生命的問題,否則不會在半夜三更離開舒適溫暖的被窩,來到急診室。而我的工作就是幫他們找出問題所在。但是不同於家庭醫師大概已經認識病人好多年了,我和病人不過剛剛碰面。我得火速了解和評估病人的狀況。
有時候,就像那名維修工人的案例,我可能必須忽略某位護理師或救護員錯誤的最初意見。要做出正確的診斷,我可能必須無視於病人口氣中的酒精味,或是他睡衣上的嘔吐臭味。通常,我得不去理會流浪漢邋遢的外表,或是焦慮的病人嘴巴的碎碎唸。
每一位病人都忍受著某種程度的痛苦,不論是真的痛苦,還是想像出來的痛苦;而急診室的醫師兩者都會碰到。每一位病人都有害怕的東西:死亡,或是改變人生的疾病,或是由一場小病釀成的很不方便的恢復期。他們剛進來時,最害怕的往往是未知。「我哪裡出了毛病,醫生?」這是最典型的問題,即使沒有真的說出口,但是它存在病人的眼神裡;當我書寫他們的病歷時,它也盤桓在空氣中。有些人甚至會問出更難回答的問題:「我快要死了嗎?」他們想知道答案。有時候我有答案,即便不是他們想要的答案或想聽見的答案。
然而,有些時候,我也不知道哪裡出了問題;有些時候,我給的是不正確的答案。但是要通過考驗,成為急診醫師,我正確的時候必須遠多於錯誤的時候。而且我必須在一團忙亂之中,在與病人相處盡可能最短的時間內,給出正確答案。並不是我不想分給病人多一點時間,而是因為我分不起;候診室裡還有滿滿的病人等在那裡。我試著在少睡、甚至不睡的情況下,動作盡量快速——這就是急診醫師的實際生活。
就算急診醫師設法做出正確的診斷,我們往往也會碰上其他的挑戰。醫院在夜間會刪減工作人員。除非病人需要緊急開刀,平日繁忙的手術室都是關閉的。X光部門也是一樣。如果有需要,我能進行簡單的X光檢查,甚至電腦斷層掃描頭部或是掃描腎結石。然而,如果我想要讓某位病人接受腹部或胸部電腦斷層掃描,我得呼叫待命的放射科醫師,然後說服她相信這個掃描不能等到天亮再做。如果我覺得病人需要緊急手術,我必須說服某位睡眼惺忪的外科醫師從床上爬起來,趕到醫院。我最好診斷得沒錯,否則外科醫師很快就會開始懷疑我的種種要求。
我因為發出警報,救了那名維修工人的命。那年我二十六歲,第一次嘗到搶救回一條生命的滋味,那人原本似乎已經被判定死刑。這件事成為我職業生涯的開端,儘管當時我還不知道。
當新人想進入醫院的急診室任職,他們最好準備大部分時間都在值夜班。部分是因為欺壓新人的慣例。不止一次,我聽到師長對住院醫師說:「我都熬過了夜班,你當然也可以。」不過,讓年輕人值夜班也揭露了另一樁明顯的事實。隨著年紀漸老,我們很多人會發現,要在太陽下山許久之後,仍然保持心態警覺和頭腦銳利,變得愈來愈困難。
回想我還是新人的時候,一九八二年,我成為約克中央醫院的大夜班人員,該院位在安大略省多倫多市北邊的里奇蒙丘,是一個所謂的臥房社區(居民白天都進市中心工作,夜晚才回來睡覺的社區)。一連好多年,我每個月都值十到十二個大夜班,通常從晚上十一點半開始,到次日早上七點半。當時我以為自己在盡了新人的責任後,就可以漸漸往上爬,輪值一些生理上比較舒服的班。
然而好玩的是,在我通向舒服的值班表的旅程中,我開始明白,其實我喜歡在夜間工作。白天當班,我很容易被各式各樣不請自來的電話擾亂,因為各個病房的祕書老是喜歡把電話轉給我。這些電話常常來自想把病人轉送急診室的醫師。但是在夜間,從來不會有這種電話。
另外,我也很喜歡日落之後到急診室來求診的病人。許多人很焦慮,有人情急到不顧一切,有人很瘋狂,也有少數人即將面臨死亡。像這樣不斷和有迫切需求的人打交道,並不容易。擔任家庭醫師,幾乎天天都會碰到範圍很廣的各種病例,從危及生命的重症,到只是需要更新處方箋的慢性輕症都有。在家庭醫師的診間裡,有潮起潮落,危機和平靜交替出現。急診室就不同了,我們碰到的病人,若非具有真正的醫藥危機,也會有其他的危機,通常是心理問題或是藥癮問題——和他們打交道,困難度不遜於和斷了手或是肚子劇痛的病人打交道,甚至更困難。
為什麼我喜歡在夜間工作,還有另一個理由。它讓我有很多時間去經營我的醫學報導生涯。從一九八○年代初期開始,我除了在多倫多市中心的西奈山醫院擔任急診醫師,同時也是醫藥記者。在我的雙重職業生涯中,我賦予自己的任務是:解開醫學世界的神祕。我先是和加拿大廣播公司(CBC)的電臺合作,然後又跟CBC的電視臺合作,最初是擔任一個半小時的時事報導節目「健康之道」(The Health Show)的特派員,後來則是擔任「全國新聞」的健康記者。
在這段過程裡,我開始寫筆記,記下醫師、護理師以及其他醫療人員之間的對話。這些對話發生在醫院走廊或是醫護人員休息室裡,都是在病人及社會大眾聽不見的地方。我決心要揭露醫療界的文化,以及醫師、護理師及其他保健專業人員對於病人與醫療體系的看法和感覺。我發現,我職業生涯中的一大重要目標,不只在於幫助需要醫療照護的人。我還想要治療醫療體系本身,去揭露它的真面貌,揭露它所有的長處、短處和藉口。就像我曾經對一名同事說的:「我想完成的任務是,把醫療界屁眼裡那根虛偽的刺給拔出來。如果容我造個新字眼,就是我要來一場『摘刺手術』(stickectomy)。」
急診室那道門背後的真相
這個目標終於在二○○七年實現:我為CBC的電臺主持「白袍與黑魔法」(White Coat, Black Art)節目,該節目揭露醫療圈裡的人心、想法和故事。也就在那個時候,我想到,可以把我在夜間急診室工作的經驗,轉化成一本書。
《夜班急診室:急診醫師筆下的真實人生》這本書要講述的,是我在西奈山醫院急診室及其他醫院值夜班時,所看過的病人。目的在於揭露急診室裡,那道將病人與醫療人員隔開的門(無論是真實的門,還是譬喻上的門)的另一側所發生的事情。另外,這本書也要講述我對醫學的態度,它深受我另一項醫藥記者生涯的影響。我從事這兩項高壓力職業的時間,幾乎一樣長。
我在本書中所描述的大夜班經驗,是把我多年來在西奈山和其他醫院值夜班時,所見過與醫治過最難忘的病人的故事,融合而成。西奈山醫院的急診室通常都是鬧哄哄的,但是在大部分的夜裡,我們不會見到大量的血和重傷害病人。因為這個緣故,自由記者索羅門(Sam Solomon)和我,還採訪了加拿大各地有精采故事要說的急診室同僚。此外,在CBC的首肯下,我也引用了一些我幫「白袍與黑魔法」節目採訪過的資料,以豐富本書的內容。
身為醫師,我必須保護病人的隱私。然而,我也有一股難以按捺的衝動,必須把急診室的真相講出來。講述深具意義的故事,同時又不得違背職業道德,需要花一點工夫。我在本書中所寫到的病人,都是以真實人物為依據。然而,我把他們的姓名和個人識別資料,做了一些更動,以保護他們的隱私。
我寫這本書,是為了你們。如果你在半夜驚醒,胸口劇痛,或是腹部有一顆火燒般的腎結石,又或者你如果半夜跌下床,摔破了骨盆,你最初的願望大概都是希望問題能夠自己解決。等你明白那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你很可能會搭車或是召救護車前往最近的醫院急診室。
急診室病人的統計數據也很驚人。有一份二○○七年的研究發現,每年、每一百位北美居民當中,就有將近四十人曾經到急診室掛號看病。這表示,你們當中大部分人遲早會需要像我這樣的醫師的服務。你們當中很多人可能會想知道,在急診室那道玻璃門背後的真相,以及你們是否可以信任那裡的工作人員。我希望能夠帶領你們進入急診室,展示急診室真正的運作方式,讓你們像我一樣了解急診室。我希望經由這樣做,能揭開這份職業的神祕性,讓你們更容易理解以及面對「掛急診」這回事。
在本書中,我會不時描述我囑咐過的檢驗和療法,例如我開的處方,或是我親自醫治的病人。然而,撰寫本書的目的純粹是為了揭露急診室的真實面貌,自娛娛人;讀者不應該把這本書視為醫療建議。若需要醫療建議,還是去看您的醫生吧。
前言 急診室的真實人生
有人選擇在夜晚工作,有人則是被夜晚選擇。我想我就屬於後者。
回溯到一九八二年一個春天的夜晚,也就是在我進入西奈山醫院的前兩年,我到多倫多一家社區醫院急診室兼差,這家醫院位在一處少數族裔社區的中心。那天晚上,有一名年約六十出頭的維修工人,來到急診室掛號,抱怨肚子痛、想嘔吐。
「我想大概是食物中毒,」他告訴一位急診護理師。
護理師轉告我,但是不知怎的,我的雷達突然拉起警報。雖然我那時還很沒經驗,但是有一件事我很清楚:有些病人會嚴重低估自己的症狀。這人是東歐族裔,是那種很有男子...
目錄
出版合作總序 樹立典範 黃達夫 4
前言 急診室的真實人生 6
第一章 生命的氣息 16
第二章 子宮的悲喜劇 40
第三章 漫漫長夜,等待,再等待 54
第四章 恐懼與嫌惡 80
第五章 「夜襲者」與「常客」 110
第六章 看緊你的住院醫師 138
第七章 夜深,人累 160
第八章 忘不了,那些逝去的名字 180
第九章 迷途的愛情 222
第十章 傾聽無言的呼救 238
第十一章 每隔幾年,就有壞事發生 250
第十二章 下班 300
感謝 322
出版合作總序 樹立典範 黃達夫 4
前言 急診室的真實人生 6
第一章 生命的氣息 16
第二章 子宮的悲喜劇 40
第三章 漫漫長夜,等待,再等待 54
第四章 恐懼與嫌惡 80
第五章 「夜襲者」與「常客」 110
第六章 看緊你的住院醫師 138
第七章 夜深,人累 160
第八章 忘不了,那些逝去的名字 180
第九章 迷途的愛情 222
第十章 傾聽無言的呼救 238
第十一章 每隔幾年,就有壞事發生 250
第十二章 下班 300
感謝 322
購物須知
關於二手書說明:
商品建檔資料為新書及二手書共用,因是二手商品,實際狀況可能已與建檔資料有差異,購買二手書時,請務必檢視商品書況、備註說明及書況影片,收到商品將以書況影片內呈現為準。若有差異時僅可提供退貨處理,無法換貨或再補寄。
商品版權法律說明:
TAAZE 單純提供網路二手書託售平台予消費者,並不涉入書本作者與原出版商間之任何糾紛;敬請各界鑒察。
退換貨說明:
二手書籍商品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二手影音商品(例如CD、DVD等),恕不提供10天猶豫期退貨。
二手商品無法提供換貨服務,僅能辦理退貨。如須退貨,請保持該商品及其附件的完整性(包含書籍封底之TAAZE物流條碼)。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
退換貨原則、
二手CD、DVD退換貨說明。
 11收藏
11收藏

 8二手徵求有驚喜
8二手徵求有驚喜




 11收藏
11收藏

 8二手徵求有驚喜
8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