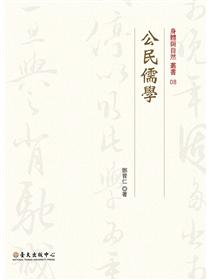提供認識中國崛起的不同視角
重新認識當代中國「革命—後革命」的歷史進程
作為中國大陸當代最重要的知識思想界參與者之一,賀照田先生在本書中延續並發展了他獨特的「知識-感覺」批判方法——「關鍵不在其經歷細節的代表性,而在於個人經歷後面的情緒感受的代表性,和把這情緒感受與時代歷史-觀念-教育結構直接辯證的整理問題的方式」。
賀照田先生談革命,並非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或主流歷史學通常著眼的角度討論,他關注的核心是革命中的「意識」、「無意識」問題。相比主流政治經濟學探討中國革命的政策、國際關係等客觀制度,主流歷史學探討毛澤東等上層政治人物的動向和自上而下的動員機制,賀照田則特別關注普通知識分子和老百姓的意識與感覺。
而本書中的「感覺」問題,包括且不限於個人與集體丶國家與社會丶歷史與當下、傳統與現代⋯⋯也就是在這種獨特的思考基礎之上,賀照田先生以史學的方法加以觀念、感覺的維度,嘗試重新梳理二十世紀中國的實踐和思想遺產。而作為近年思考成果的匯總,本書的寫作與思想亦與當今中國、世界現實緊密相關。閱讀本書,可以充分感受到思想對於歷史和現實的力量。
「實際歷史狀況常常是『病藥相發』,但在人們長期的認識意識中卻是『撥亂反正』,且這一『撥亂反正』意識對新時期的確立與展開有深刻的影響,對新時期幾十年中的眾多認知與思潮都有重要影響,因此它既是當代中國大陸諸多問題得以發生的重要意識背景,也是諸多思潮與知識的歷史-現實認知所以出現偏差的關鍵原因。相比,『撥正反亂』的歷史觀雖然也是對『撥亂反正』歷史觀的清算,但由於它是以對待歷史不夠深入、耐心為前提的,當然不能像更貼近當年『革命—後革命』實際歷史展開過程的『病藥相發』歷史理解意識,更能把我們導向更準確、深刻的歷史和現實認識。」
──賀照田
「賀照田努力於客觀、精準掌握對象,但並不認為『歷史現場』和自己無關、外在於自己,反而認為如何認識歷史其實是現實中非常重要的問題部分。就本書的主題而言,如何認識革命便是後革命時代最根本、最關鍵的問題之一。」
──鈴木將久
「我們會發現世界裡本來瀰漫了種種令人苦惱,甚至於讓人感到絕望的事情,但人類歷史這種狀況恰恰不應該讓我們拋棄理想⋯⋯我們毫無捷徑,從最困擾的地方開始思考問題才是深入現實、通往美好未來的捷徑⋯⋯在我看來,這是照田兄一貫的立場。」
──李南周
◎序作者
鈴木將久 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學系研究科教授)
李 南 周 韓國聖公會大學中國學系教授 韓國《創作與批評》季刊副主編
◎各界推薦
王智明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合聘副教授
余敏玲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林淑芬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林載爵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發行人
施 淑 淡江大學中文系榮譽教授
徐進鈺 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陳光興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主編、《人間思想》繁體字版主編
黃俊傑 台灣大學特聘講座教授
楊儒賓 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甯應斌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特聘教授
劉紀蕙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講座教授、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主任
錢永祥 《思想》總編輯、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
作者簡介:
賀照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美術學院當代藝術與社會思想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台灣社會研究學會成員,《人間思想》簡體字版主編,並先後在台灣東海大學(2007)、台灣清華大學(2008)、台灣成功大學(2009)、日本東京大學(2013)、台灣交通大學(2018)等校客座任教。主要研究中國十八世紀中葉以降政治史、思想史和中國現當代文學。個人專著論文集有《當代中國的知識感覺與觀念感覺》(上海、台北,2006)、《當中國開始深入世界》(東京,2013)、《當社會主義遭遇危機》(台北,2016)、《當代中國的思想無意識》(首爾,2018);與友人合著論文集有《人文知識思想再出發》(台北,2018)、《人文知識思想再出發是否必要?如何可能?》(台北,2019;主編的論文集有《西方現代性的曲折與展開》、《東亞現代性的曲折與展開》、《後發展國家的現代性問題》、《作為人間事件的1949》、《作為人間事件的新民主主義》、《新人・土地・國家》、《新與舊・理與時・情與勢》、《作為人間事件的社會主義改造》、《作為方法的五十年代》等近二十種。
章節試閱
啟蒙與革命的雙重變奏
前言
我相信很多讀者在看到這個文章題目時,一定會聯想到八十年代李澤厚那篇轟動一時的名文〈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不過說實話,我當初醞釀這篇文章時並沒有要和李澤厚這篇名文對話,直到給文章想題目時,「啟蒙與革命的雙重變奏」這個腦海裡浮現出的題目才讓我驚覺:我這篇文章不僅名字,而且內容都和李澤厚這篇名文有深刻的對話關係。
很有意思的是,李澤厚這篇核心焦點在對中國共產革命的歷史位置、歷史意義給以重新定位、解釋的文章,題目上出現的卻是「救亡」而非「革命」,其原因在我看來,應該不只是有的朋友推測的那樣,在題目上出現「革命」太顯眼,而還和、甚至更和李澤厚這篇文章所置身的八十年代時代思考脈絡有關。
在文革後十年對文革的不斷批判、反省中,越來越占據時代壓倒性地位的看法是把文革看作一場反現代的運動。而這一判定又引出如下問題:為什麼會在自認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階段的中國大陸,卻發生了這麼一場主導了中國大陸十年歷史的反現代運動呢?在很大的意義上,李澤厚這篇〈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所以轟動一時,就是在八十年代中後期(李這篇文章是1986年出版)很多人眼中,李澤厚這篇既歷史把握又結構透視的大文對這一問題回答得最為漂亮,不僅對革命存在的原因、意義、作用做了不乏歷史同情心的流暢解釋(因此有助於安慰和這革命歷史正面深切相關的人群,亦有助於化解在價值上對這革命、革命演變後果不認同的人們和這歷史的過度緊張),而且這既歷史又結構的流暢解釋,還印證著人們對這一革命歷史演變到後來的否定性看法確實正確(也即和這一演變直接有關的眾多現實必須改變、調整)。而這些合起來又等於為現實中人們不糾纏歷史,致力於支持時代正在進行的改革開放,支持在知識界正蔚為大觀的新啟蒙思潮,提供著歷史-結構理據。
而李澤厚這篇思緒靈動、語句有神的名文所以能用不太長的篇幅同時達至這些目標,一個核心關鍵便在他的歷史敘述、歷史理解、歷史評論,特別強調「救亡」對這「革命」的規定性。就是在他看來,中國共產革命長時間的艱苦軍事鬥爭經歷本已不利於現代價值在這革命中的扎根、生長,而這革命軍事鬥爭不得不依賴農民,不得不在落後的農村環境生存,更使得這革命遠離現代,越來越被農民深刻影響,從而使這個在起點上本是被現代前沿知識分子所發動的革命,最後被改造成了一個被農民身上的封建性和小生產者特性深刻浸染的革命。毛時代的諸多弊病,特別是文革的爆發,正是以這革命中的現代性被封建性和小生產特性深刻侵奪為前提的。是以李此文標題中的「救亡」,絕不是內容上不那麼相關的表述「策略」,而恰恰是使他大文的歷史-結構敘述、解釋得以順利證成的核心關鍵。
相比,本文標題之用「革命」,而非「救亡」等,首先便在不想預先─就把文革定性為一場反現代的運動及由此產生出的問題等─作為自己關於中國共產革命歷史認識的把握前提,而想先懸置當年這些對才過去歷史的過急蓋棺論定,以重新認真審視先前在這些視野下被把握、被分析、被定性的革命歷史,然後再慎重給出對這歷史更公平、也更準確的把握、分析。
其次,本文標題之用「革命」,還包含著我如下認識,就是:我承認李文強調的不斷的軍事鬥爭、遠離現代都市的農村環境、農民在人數上構成著革命隊伍的多數等等對這革命有深刻影響,但我不能同意的是他在看到這些方面對中國共產革命有重要影響後,並未進一步深進此革命有關經驗內在去發展、深化他的這些觀察、思考,便急著建立這些方面對此革命有根本規定性的解釋,並急著把太多問題、太多歷史現象安置進此一解釋框架。而我所以會在此點上特別質疑李文,是因為我在有關歷史研究中,發現不少李文所處理到的問題與現象實際上是不適合乃至挑戰李文的解釋邏輯的。即,李文所強調的軍事鬥爭、遠離現代都市的農村環境、農民在人數上構成著革命隊伍的多數等─這些確實是在中國共產革命中占有結構性重要地位的要素,但李文關於它們對革命有根本規定性的解釋,則過度誇大了這些要素對這一革命的塑造力。
本文和李文不同的第三方面關涉八十年代的理解與評價。李是一個很有民族責任心,很有歷史-現實感自覺的人,他說過,「自己不寫五十年前可寫的書,不寫五十年後可寫的書」(〈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後記〉),其意便在強調他最希望寫的是既基於深刻的有關中國過去與未來理解,又能有效介入時代活躍現實的著作。〈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可說是充分反映他這一寫作意識的代表之作。就是他所以寫這篇文章的現實動力,一方面在通過歷史解釋來有力支持時代的改革開放思潮、新啟蒙思潮,一方面又要化解、糾正時代這些潮流中夾雜的偏執、戾氣、極端。從這篇文章在八十年代的閱讀和接受看,這篇文章可說相當好地肩負了他賦予之的時代任務。但問題是,若現實中的時代潮流理想,那以有問題的歷史解釋為工具來支持這一時代潮流,所犧牲的還只是歷史,它還有所支持的現實足夠正確為補償;若所支援時代潮流本身已內蘊結構性偏差,還把歷史作為支持此時代潮流的工具,則其所影響的就不只是歷史認識的準確與歷史評價的公正,而還有現實開展上的代價。
相比李文對八十年代新啟蒙思潮主要肯定有所批評,本文則要用相當篇幅論及:文革後的改革開放思潮和至八十年代中葉開始蔚為大觀的新啟蒙思潮,為在中國快速推展出歷史新局面做出巨大貢獻內裡,實存在結構性偏差,且後果深遠。尤其考慮到八十年代有關偏差,本來是可以通過認真的歷史研究照亮發現的,且若當時認識到,一定會有人因之而重新審思當時時代通行的歷史-現實理解,從而構造出更周全、同樣具時代建設功能但更少歷史-現實傷害的歷史-現實認識的。可惜的是,八十年代才華如李、責任心如李,對中國近代史有深切積累、功夫如李,在這方面卻仍只是做了時代弄潮兒,成就出主要為時代大潮推波助瀾,為其合理性做漂亮歷史-結構論證的〈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而未能成為真正超越時流的諤諤之士、潮流諍友,讓人不能不為其才華、功夫可惜。
我知道近三十年後這樣來挑剔李先生這篇充滿責任感和靈動思緒的文字近於苛酷不情。(何況李是我大學時代對我影響最大的漢語思想人,雖然那時他的大部分著作我都只讀了個表面,並沒真懂。)本文所以如此,一為李先生是當代中國思想的標竿人物,對賢者人們不免會因對他們的深切寄望而求全責備;更重要的原因則在李這篇文章雖然發表快三十年了,李當年的寫作情境和文章的接受情境都已時過境遷,但李文所關涉到的一些歷史關節卻仍有一些該發之覆未被闡明,而這些未發之覆和當今時代狀況仍有其牽連。往事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本文今天仍積極於這些待發之覆,一方面固然意在對有關歷史給以更準確、更公平的理解,一方面則在這些未明之覆和今天中國的意識狀況仍有牽連所帶給我的不安。
希望以上對本文和李文糾葛的扼要交代,不是在浪費大家時間,而是可以幫助大家更多地了解本文所由作的時代相關種種,從而多些角度意會本文的討論關切和這些討論背後所流動的經驗與情感。
一
確實,如果我們不是從提到馬克思和對他某些觀點有所介紹出發,而從實際導致中國共產革命發生的歷史過程看,我們就可以清楚看到: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是從新文化運動這一歷史母體中脫胎出的,是眾聲喧嘩的新文化運動諸思想脈流中的一支,並分享著新文化運動諸思潮都分享的一些觀念與感覺。比如,對中國傳統政教理解棄如敝屣;認為中國要成功現代,必須在思想文化方面進行巨大變革;在這一變革的啟動和展開過程中,自認已經率先現代了的新知識分子的作用不僅重要,而且不能被替代等等,便都是最初作為新文化運動一支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中其他思潮共享的感覺與理解。
不過,相比共同,非常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多數思潮的如下差別: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由於其所依據的馬克思主義特別預設了無產階級(工人階級)對整個世界史的關鍵性意義,認定他們身上負有確保這世界史藍圖一定能實現的革命堅定性與徹底性,使得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信仰的知識分子們,在面對工人階級時,當然就不會有一般新文化運動知識分子在面對中國社會時的那種特別優位感。這種面對中國社會時的特別優位感,是新文化運動中以啟蒙者自命的多數知識分子們非常突出的特點。就是積極參與新文化運動的多數知識分子的共同點之一,便是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對中國所具有的建設性意義和他們所要啟蒙的中國社會的不理想都進一步絕對化。「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雖是魯迅1907年寫〈摩羅詩力說〉時所創造的表達,卻很能傳達新文化運動多數知識分子的中國社會感。在這些新知識分子,特別是其中的激烈者們看來,其時中國社會、中國人深陷「不幸」,不僅深陷「不幸」,太多人且麻木到對這些不幸無感,或有感但懦弱到不敢去抗爭。是以在這些知識分子眼中,其時中國社會、中國人的問題不只是缺少現代眼光、現代知識的問題,在精神、心理、人格、行為習慣等方面也都極為不足、不堪。否則,沒有這樣一些感覺與理解為背景,我們很難想像本是魯迅為傳達拜倫對奴隸強烈情緒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為什麼卻可成為這一時期很多新知識分子對中國社會、中國民眾的突出感受。
相比,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意義的明確認定,則使其時出自新文化運動卻又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信仰的知識分子,不能把自己的優勢位置絕對化,把中國社會的不理想絕對化,而必須直面如下張力-挑戰:一方面其時的中國工人階級確實有對自己階級的歷史意義、歷史責任從自發到自覺的問題要解決,而這保證著信仰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知識分子在中國共產革命運動,特別是興起階段時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馬克思從無產階級階級位置、階級經驗出發的關於無產階級才具有最堅決、徹底革命性的明確認定和無產階級這種堅決徹底革命性對世界史具有的關鍵意義的明確認定,使得中國真誠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又不得不細思─既然對共產主義運動至為關鍵的革命堅決性和徹底性主要由無產階級的階級位置階級經驗來保證,而並不由對馬克思主義思想上的信仰與掌握來保證,那麼,這些當時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們由於自己並不出身無產階級,因此自己要想真的擁有堅決徹底的革命性,成為一個理想的共產主義者,就必須在情感、經驗、心理上努力向工人階級看齊。而這也便意味著一個真誠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他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理想關係,一定不是一種單向的啟蒙關係,而應該是彼此雙向辯證的啟蒙關係。一方面,就幫助、教育工人階級掌握馬克思主義以獲得充分的階級自覺來說,知識分子可說是一個啟蒙者;另一方面,若想成為一個足夠理想的共產主義者,知識分子便需要認真對照工人階級的階級情感、階級經驗、階級心理來自我反省、自我改造,以把自己不僅在思想上,也在身心情感上鍛造為一個徹底的革命者。即知識分子在自覺做一個啟蒙者的同時,還要自覺地把自己作為一個被教育者、被啟蒙者。而如此也就意味著:在知識分子和社會相互關係的感覺與理解上,信仰馬克思主義並試圖身體力行的知識分子們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發軔時,便和新文化運動的一般有關狀態有著後果深遠的構造差異。
上述因馬克思主義經典革命理論帶動所帶來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發軔時就與新文化運動主流的社會感不同,隨著1920年代中期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對中國社會看法的進一步突破,差異愈發擴大。此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除順承新文化運動,繼續關注對青年知識分子的爭取與影響外,主要著重對工人階級的召喚、組織,到這時對可成為革命骨幹力量或革命助益力量的社會範圍的認定則大為擴展,認為工人階級之外的中國大部分社會階級也都具有或強或弱的革命性,有結構進中國共產革命,成為中國共產革命有機部分、或至少成為革命助力的可能。(此中非常有代表性也最為此後大家所知的文本便是毛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該文發表於1926年2月。)不僅占當時社會人口最大比重的農民的革命性被高度評價,被認為可以成為中國共產革命的基本力量,而且各式各樣的小資產階級中的大多部分也被認定為有很強的革命動力,甚至斷言民族資產階級有時也會贊助革命,至少很多時候不會反對革命。
而這一相對現代中國一般啟蒙思潮的社會理解走得更遠的─關於工人階級之外的廣大階級也都具有革命潛能、革命動力的─理解和判斷,之所以對此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在現代中國的歷史命運至為關鍵,是因為以這些判斷為起點,中國共產革命才會把自己的社會關注視野真切擴及工人階級和青年知識分子之外的廣大中國社會,並在面對這些社會階級時,不再只是一般性地宣傳、灌輸、啟蒙,而更著眼在他們身上挖掘革命動力,更著力尋找最能使他們被打動、調動的互動形式,以有針對、有實效地召喚這些階級的革命性,引導這些階級的革命性,組織這些階級的革命性,並在召喚、引導、組織這些階級革命性的同時,致力發現、發明更具有說服力、吸引力的制度形式、組織形式、社會生活形式,以及可有效支撐、護持這些制度存在、組織生活、社會生活存在的文化形式,從而在更具實效地把這些社會階級的革命潛能或可為革命所用的行動潛能、心理潛能充分調動出來的過程中,同樣有效地把這些調動起來的能量充分穩固、有機地組織結構進中國共產革命。
而這些所以會對中國共產革命的現代歷史命運至為關鍵,是因為在現代中國,被認為是共產革命理想社會基礎的現代工人階級在中國數量本就有限,而且從1920年代末開始革命便主要在沒有現代工業的農村地區進行,使這為數不多的現代工人也被和革命根據地分隔。在這種按照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將無所措手足,而世界性無產階級革命又沒有很快爆發可能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革命仍能存活下來並發展壯大,所依賴的正是─1920年代中期對中國社會的這些新認定和以這些認定為前提所開展出的豐富思想探索與實踐創造所得以綜合實現的——如何把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解對此革命需要不現成的社會現實,不斷轉變成此革命有機力量的創造:努力從中鍛造出革命的堅定認同者、積極投入者,以不斷補充進領導這革命的核心力量中國共產黨;努力從中大量陶鑄出此革命可有效依賴的基本隊伍,以構成這一革命所關鍵依託的武裝力量和群眾運動骨幹;對那些不能成為革命核心與基本力量的社會部分,也努力尋找方法使其成為革命的助力;不能成為革命的直接助力也至少樂觀其成,確實在觀念、價值上不贊成革命的也至少不去積極地反革命。
(詳全書)
啟蒙與革命的雙重變奏
前言
我相信很多讀者在看到這個文章題目時,一定會聯想到八十年代李澤厚那篇轟動一時的名文〈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不過說實話,我當初醞釀這篇文章時並沒有要和李澤厚這篇名文對話,直到給文章想題目時,「啟蒙與革命的雙重變奏」這個腦海裡浮現出的題目才讓我驚覺:我這篇文章不僅名字,而且內容都和李澤厚這篇名文有深刻的對話關係。
很有意思的是,李澤厚這篇核心焦點在對中國共產革命的歷史位置、歷史意義給以重新定位、解釋的文章,題目上出現的卻是「救亡」而非「革命」,其原因在我看來,應該不只是...
作者序
作者小引:從「撥亂反正」、「撥正反亂」到「病藥相發」
一
相比要理解二戰後西歐、北美一些發達國家的歷史與現實,現代-後現代是很重要的理解線索;要理解二戰後亞、非一些曾長期被殖民的國家、地區的歷史與現實,殖民-後殖民是很重要的理解線索;要理解二戰後中國大陸的歷史與現實,革命-後革命則是與理解上述國家、地區不可或缺的現代-後現代、殖民-後殖民地位相若的重要理解線索。
本書多數論文都聚焦處理的、對理解中國大陸革命、後革命有重要性的節點和有重要性的理解脈絡,便和革命-後革命這一理解視角,對理解二戰後中國大陸的歷史與現實所具有的重要性直接相關。這也是本書以「革命-後革命」命名的首要原因。收入本書的論文所處理的問題,分屬政治史、思想史、文學史、藝術史、精神史乃至對外關係等不同領域,我當然也期待讀者把這些文章放在這些領域中來閱讀、把握。不過,我把書命名為「革命-後革命」,也清楚表明,我同時在期待讀者把本書這些直觀看上去分屬不同領域的論文,放在「革命-後革命」歷史脈絡與理解視角、理解意識脈絡中進行閱讀、把握。
比起命名本書為「革命-後革命」很好理解的如上用意,我如此命名本書的另一層意涵要清楚說明則相當費篇幅。所以如此,是我的「革命-後革命」命名,隱含著跟中國大陸通行的理解中國大陸當代史的革命-後革命方式的尖銳對話,是以我若不清楚說明現有通行理解方式的特點何在、問題何在,我便不能清楚說明用「革命-後革命」命名本書的這另一層含義。
對中國大陸歷史有所了解的朋友都知道,中國大陸稱1978年年底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召開後的歷史時段為「新時期」。而所以自稱「新時期」並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歷史標誌點,在於十一屆三中全會徹底否定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強調的「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理解方式,把中國大陸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至現代化建設。
對中國大陸當代歷史有更多了解的朋友則進一步知道,中國大陸從「革命」到「後革命」,也就是從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認識主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實踐主導,到認識和實踐都相當徹底告別文革、相當充分進入一種「新時期」狀態,實際上是一個至少涵蓋了從1976年9月至1982年9月長達六年的歷史過程。在這六年中,在認識與實踐的很多方面都發生著巨大變化。從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和緊接著的1976年10月積極堅持文革激進理念的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國大陸被習慣稱為「四人幫」)四位激進領導人被抓捕開始,推動中國大陸距離文革認識與實踐越來越遠的變化便層出不窮。讓當時人印象深刻的歷史變化點便有:1977年7月文革中兩次被打倒、被重點批判的領導人鄧小平復出;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宣布從1966年開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文革發生、展開相始終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雖然還被高度評價,但「十一大」強調的階級鬥爭主要是批「四人幫」─也就是批文革激進派─國家實際關注重心已經轉到現代化建設中來,儘管這時的建設現代化,是想同時兼顧毛澤東時代的諸多革命理解,想真的做到「抓革命、促生產」;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不僅決定政治不再戴階級鬥爭的帽子,從1979年開始全黨工作重點完全轉到現代化建設方面來,而會議公報雖然沒有正面否定文革,但無論對之前歷史的理解還是對應該如何建設現代化的理解,都已經和毛時代的激進革命理解相告別;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為文革前半期最大的打倒、批判對象劉少奇平反;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方面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否定文革、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並對1949年至當時的歷史、現實,按照當時黨和國家核心主導者鄧小平、陳雲等的認識對歷史進行了展開檢討,對當時現實做了熱烈肯定,另一方面正式解除1977年、1978年想儘量兼顧毛時代激進革命理解和現代化追求的華國鋒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正是以如上這些年中不間斷的變動為基礎,1982年9月召開了志在「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當時中國大陸國家主導者那裡,「十二大」的召開,不僅標誌著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人事上、實踐方案上,時代都已經相當充分地完成了對毛澤東時代他們認為有問題的激進革命理解、激進革命實踐,特別是文革理解、文革實踐的─告別,而且他們所期待的全面致力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確立,至此也塵埃落定。
對中國大陸當代歷史有深入了解的朋友則還知道,對當時中國大陸國家主導者而言,上述他們大力參與的「革命-後革命」歷史過程,首先是「撥亂反正」對之前種種錯誤(「亂」)的告別,對這些錯誤所擾亂的先前種種正確(「正」)的回復。就是,「撥亂反正」所對應的理解、評價是:從1976年9月到1982年9月,特別是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到1982年9月十二大召開,並不是一般意義的從「革命」階段到革命任務基本完成後的「後革命」階段,而是這一從「革命」到「後革命」過程,及其另一面「新時期」確立過程,所以特別難得、特別有意義,所以應該給予熱烈的評價;還在於這一過程核心伴隨著─認識上對毛澤東時代(1949-1976)經驗與教訓認真、充分的分析與反省,實踐上根據這分析與反省對中國大陸方方面面所做的切實、有力的調整、改變,然後再在這些認識、實踐基礎上開新、改革開放。也就是,在這幾年歷史中集中發生的「革命-後革命」過程,為新時期中國大陸讓人矚目的成績,提供了恰當且堅實有力的基礎。
中國大陸國家關於從毛澤東時代到鄧小平時代的這樣一些認識,通過國家大力宣傳、控導,成為從那時到現在中國大陸關於自己「革命-後革命」歷史經驗過程的主流認識,也是1980、1990年代主導中國大陸知識界的籠罩性認識。非常有意思的是,經常和中國大陸國家權力關係緊張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中國大陸國家的這種「革命-後革命」理解、敘述也是基本贊同的,就是他們完全同意鄧時代對毛時代革命的告別,也贊同新時期確立時一系列「後革命」舉動,他們的有所異議、批評,實際上集中在中國大陸黨和國家的「後革命」變革在政治方面不如經濟方面走得遠。
中國大陸知識界對1976年至1982年年間的「革命-後革命」的如上籠罩性認識被打破,要等到2000年前後「新左派」的崛起所帶來的知識思想狀況的改變。「新左派」崛起後有不少左派致力於歷史的研究和重新評價,對之前的歷史認知、歷史理解有重要的拓寬、糾偏作用,也產生了一些很有貢獻的成果。但由於中國大陸「新左派」的崛起,是基於九十年代後期以來中國大陸貧富分化嚴重等現實狀況,新自由主義喧囂一時等思想狀況,因此他們難免過急、過度地從他們認為對這些問題、思潮有特別救治作用的角度、價值出發,去聚焦歷史、評述歷史,從而在面對歷史時耐心不夠,從歷史自身脈絡出發理解、評估歷史的深入程度不夠。具體到對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這段「革命-後革命」歷史的認識,很多左派所以給人一種從自身贊同價值出發選邊站的印象,即由於這些左派過急地為自己感覺親和的觀念與歷史部分辯護,對自己不感覺親和的觀念與歷史部分沒有給予足夠認真對待。而這種認識情狀,導致在中國大陸的一些左派那裡,對從毛時代到鄧時代這段「革命-後革命」歷史的認識,便成為「撥亂反正」這一流行理解的對反,認為這段歷史是在「撥正反亂」,是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由正確的社會主義轉向新自由主義。也即這一「革命-後革命」轉向,是九十年代後中國大陸新時期一系列嚴重問題所以出現的歷史與思想根源。
顯然,這種對從毛時代到鄧時代變化所做的「撥亂反正」歷史理解判定,在2000年後的中國大陸有它的現實意義,也能提醒我們特別去注意歷史中一些先前被忽略的要素與方面,但同樣顯然,這些從所處身現實的某些問題面向出發的對歷史的過度投射性解釋,也妨礙當代中國大陸左派去更展開、更深入、更公平地去理解、把握當代中國大陸歷史與現實的更多面向。
上述關於當代中國大陸「革命-後革命」、「撥亂反正」和「撥正反亂」式認識,是我本書命名「革命-後革命」,特別要對話的兩種歷史認知意識。自2001年撰寫〈後社會主義的歷史與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觀的變遷〉2一文開始,我便發現,當代中國大陸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這段「革命-後革命」歷史,固然為其後文學令人讚嘆的豐富、多樣提供著關鍵性歷史基礎,但八十年代直至2000年文學所存在的一些重要問題,追溯上去,也決定性伏基於這段歷史的「革命-後革命」方式。等到2006年撰寫〈當代史研究與當前中國大陸的思想與政治〉和〈當社會主義遭遇危機⋯⋯「潘曉討論」與當代中國大陸虛無主義的歷史與觀念構造〉的第一個版本時,我則更為清楚地發現,一些從1990年代中後期才開始被特別矚目的政治問題、精神倫理狀況問題,如果要對這些問題有深刻掌握,都需要對從毛澤東時代到鄧小平時代這段過渡歷史中的「革命-後革命」,重新做認真、深刻的考察。
這樣一些強烈經驗,推動我更為自覺也更為有規畫地投入從毛時代到鄧時代「革命-後革命」問題的研究。這些投入讓我更為了解,無論是已流行多年的關於「新時期」確立的「撥亂反正」式的歷史理解、歷史敘述,還是近年開始在一些人中流行的「撥正反亂」式的歷史理解、歷史敘述,都只適於這段時期的有限方面,眾多歷史方面若硬套這兩種歷史理解,不僅妨礙我們對這段時期的這些歷史方面獲得準確、深入的認識,而且妨礙我們對毛時代和新時期的相關聯方面有準確、深刻的理解。這些投入讓我更清晰知曉:要更深入、準確地理解、把握對當代中國大陸至為重要的「革命-後革命」問題,就必須先懸擱「撥亂反正」和「撥正反亂」兩種歷史觀,而切實了解,中國大陸「新時期」的成就確實得益於文革後對毛澤東時代經驗、教訓的諸多檢討,但這並不意味著「新時期」的成立就奠基於對毛澤東時代充分的「撥亂反正」─即對毛澤東時代的經驗、教訓做了足夠全面、深刻的把握,然後以之為基礎,發展出文革後歷史新局面。實際歷史狀況遠沒有當時許多自認為在「撥亂反正」的當事人所認為的那樣理想,而常常是有得有失。也就是,「新時期」成立固得益於對毛澤東時代經驗、教訓的多方面檢討、總結,但認為對毛澤東時代的檢討已足夠全面、深刻,「新時期」的成立是基於這充分認識基礎上的「撥亂反正」,則並非事實,而只是一些歷史當事人的主觀自認;「新時期」許多問題追根溯源,恰恰來自新時期成立時對一些重要問題究竟該如何認識把握不夠,來自對毛時代一些非常有意義的經驗、一些非常重要的視野沒有繼承與轉化。是以,一些歷史當事人自以為是的「撥亂反正」認識、實踐,回到歷史實際中去,常常並不像這些當事人自認的那麼正確,反常常是「病藥相發」即由於對病本身的把握不夠精準,對患者所具有的有利條件與潛力也缺少足夠認識,故這時治病者的藥方便不是妥帖的對症下藥。而「醫生」自以為高明的「藥」,看起來好像也對「醫」所關注的「病」有效,卻想不到由於「病」看得不準、對病人的理解也似是而非,「藥」又下得過於匆忙、過於自以為是,是以這「醫生」得意的診「病」用「藥」,常常是導致新問題、新「病」的原因。就是,「醫生」以為藥到病除的「病」往往並沒有被真的治癒,更多時候只是其表現形態被抑制,一旦壓抑狀態解除又會舊病復發,或在被抑制中轉化為另外的問題「病症」。
從「病藥相發」來看中國大陸流行的關於從毛時代到新時期的「革命-後革命」歷史理解意識,我們就會清楚看到:實際歷史狀況常常是「病藥相發」,但在人們長期的認識意識中卻是「撥亂反正」,且這一「撥亂反正」意識對新時期的確立與展開有深刻的影響,對新時期幾十年中的眾多認知與思潮都有重要影響,因此它既是當代中國大陸諸多問題得以發生的重要意識背景,也是諸多思潮與知識的歷史-現實認知所以出現偏差的關鍵原因。相比,「撥正反亂」的歷史觀雖然也是對「撥亂反正」歷史觀的清算,但由於它是以對待歷史不夠深入、耐心為前提的,當然不能像更貼近當年「革命-後革命」實際歷史展開過程的「病藥相發」歷史理解意識更能把我們導向更準確、深刻的歷史和現實認識。
是以,要在新時期歷史展開幾十年後,對當代中國大陸歷史做出根植於歷史內在的深度清理,對其中種種思潮、思考、知識做出根植歷史內在的深切反省,都離不開在和「撥亂反正」、「撥正反亂」歷史意識拉開必要距離的「病藥相發」歷史意識的導引下,對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這段對「革命-後革命」最為關鍵歷史中的實踐種種、思想觀念種種,給予重新的認真審視、細膩檢討:看哪些觀念與實踐調整是真的「撥亂反正」?即使實際是「撥亂反正」,後來關於它所以是「撥亂反正」的認識是不是正確?正確的認識應該怎樣?對正確「撥亂反正」的不正確認識是否在接下來的歷史中發揮了誤導乃至破壞作用?哪些被認為是「撥亂反正」的變革,實際卻是「病藥相發」?甚至是「撥正反亂」?為什麼會發生這樣情況?實際上是「病藥相發」、「撥正反亂」卻被當作「撥亂反正」,其引發的歷史、現實後果是什麼?等等;當然,也離不開以之為線索,對之前毛時代的思想與實踐經驗進行重新認真把握:看毛時代有哪些經驗和意識視野,應該也可以結構進新時期的歷史,或經過某種轉化可以、也應該結構進新時期歷史?更離不開追問:當發現毛時代應該被結構進新時期的思想視野和實踐經驗,實際卻未被核心掌控推動此「革命-後革命」進程的人們所意識與安排,帶給新時期的問題是什麼?此問題在新時期的歷史展開過程中是怎樣一種歷史演變形態?它帶給新時期歷史方方面面的後果是什麼?而上述這些認識展開,所帶給我們的更為細膩、展開、深入的歷史認識,當然又會為我們看待、把握在原來歷史認識情況下所出現的新時期種種觀念創新、實踐創新,提供來自歷史內在的反思視野。
而正是過去十餘年細心研究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當代中國大陸歷史,特別是其中「革命-後革命」的歷史部分,所產生的對「撥亂反正」、「撥正反亂」這兩種歷史觀的如上反省,以及跟上述兩種歷史觀直接對話的「病藥相發」歷史理解意識的產生,使我在命名本書為「革命-後革命」時,也賦予其關於當代中國大陸「革命-後革命」歷史過程究竟該如何認識的反思意涵。也就是,構成本書書名的「革命」、「革命-後革命」、「後革命」,不僅意指1949年後中國大陸歷史展開過程中時間上互相接續的三個歷史階段,而且關於究竟該如何努力,才能對「革命」、「革命-後革命」、「後革命」有更準確、深入的認識,關於為什麼在現下這個階段對既有「革命-後革命」歷史認知方式的突破特別重要等等,也是我命名本書為「革命-後革命」時,想通過這個書名指涉的。
(詳全書)
作者小引:從「撥亂反正」、「撥正反亂」到「病藥相發」
一
相比要理解二戰後西歐、北美一些發達國家的歷史與現實,現代-後現代是很重要的理解線索;要理解二戰後亞、非一些曾長期被殖民的國家、地區的歷史與現實,殖民-後殖民是很重要的理解線索;要理解二戰後中國大陸的歷史與現實,革命-後革命則是與理解上述國家、地區不可或缺的現代-後現代、殖民-後殖民地位相若的重要理解線索。
本書多數論文都聚焦處理的、對理解中國大陸革命、後革命有重要性的節點和有重要性的理解脈絡,便和革命-後革命這一理解視角,對理解二戰後...
目錄
序一 作為東亞人文思想節點的「革命-後革命」/鈴木將久
序二 刺叢裡的求索——序作為同道也作為鏡像的朋友賀照田新書《革命-後革命》/李南周
作者小引:從「撥亂反正」、「撥正反亂」到「病藥相發」
一、革命-後革命視域中的中國
啟蒙與革命的雙重變奏
當自信的梁漱溟面對革命勝利⋯⋯——梁漱溟的問題與現代中國革命的再理解
群眾路線的浮沉——理解當代中國大陸歷史的不可或缺視角
當革命遭遇危機⋯⋯——陳映真八十年代初思想湧流析論之一
鑰匙就在那陽光裡⋯⋯——革命-後革命、啟蒙-後啟蒙與當代中國大陸前衛藝術
當前中國大陸的精神倫理困境——一個歷史-思想的分析
二、當中國開始深入世界
中國革命和亞洲討論
當中國開始深入世界⋯⋯
從苦惱出發
附錄 中國革命,是過去的歷史還是正在進行中?——賀照田、李南周
對談
後記
序一 作為東亞人文思想節點的「革命-後革命」/鈴木將久
序二 刺叢裡的求索——序作為同道也作為鏡像的朋友賀照田新書《革命-後革命》/李南周
作者小引:從「撥亂反正」、「撥正反亂」到「病藥相發」
一、革命-後革命視域中的中國
啟蒙與革命的雙重變奏
當自信的梁漱溟面對革命勝利⋯⋯——梁漱溟的問題與現代中國革命的再理解
群眾路線的浮沉——理解當代中國大陸歷史的不可或缺視角
當革命遭遇危機⋯⋯——陳映真八十年代初思想湧流析論之一
鑰匙就在那陽光裡⋯⋯——革命-後革命、啟蒙-後啟蒙與當代中國大陸前衛藝術
當前...
購物須知
關於二手書說明:
商品建檔資料為新書及二手書共用,因是二手商品,實際狀況可能已與建檔資料有差異,購買二手書時,請務必檢視商品書況、備註說明及書況影片,收到商品將以書況影片內呈現為準。若有差異時僅可提供退貨處理,無法換貨或再補寄。
商品版權法律說明:
TAAZE 單純提供網路二手書託售平台予消費者,並不涉入書本作者與原出版商間之任何糾紛;敬請各界鑒察。
退換貨說明:
二手書籍商品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二手影音商品(例如CD、DVD等),恕不提供10天猶豫期退貨。
二手商品無法提供換貨服務,僅能辦理退貨。如須退貨,請保持該商品及其附件的完整性(包含書籍封底之TAAZE物流條碼)。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
退換貨原則、
二手CD、DVD退換貨說明。
 1收藏
1收藏

 4二手徵求有驚喜
4二手徵求有驚喜





 1收藏
1收藏

 4二手徵求有驚喜
4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