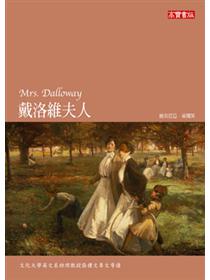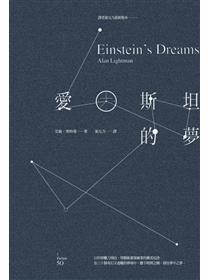《戴洛維夫人》一書,描繪戴洛維夫人從清晨為準備舉行一場宴會而外出買花,到宴會行將結束。在這一天之中,作者以克萊麗莎自己泉湧的思緒、其他人物的思維的滑移以及全知觀點的鋪陳,讓讀者藉由被割裂的片段意象中,去重拾作者企圖表達的概念及情節。
這部小說以兩個部分構成:一是時間呈現定格,讀者被引導去沉思空間中種種不同但卻是在同一時間內發生的事件,所以有時作者引導讀者站在倫敦的一條街上窺視著很多人的意識;一是空間凝結,在一個人的意識中上下移動,呈現人物一生中的各個片段。
作者簡介:
維吉尼亞吳爾芙(1882-1941)誕生於性別角色劃分嚴謹的英國維多利亞時代,自小因生為女性,無法和兄長一同接受正統的學校教育。然父親藏書豐富的圖書室和家中因文藝訪客頻繁所薰染起的文藝氣氛,直接地挑起維吉尼亞強烈的求知慾望和對文學的熱情。
1912年維吉尼亞與李奧納多吳爾芙( Leonardo Woolf)完婚,夫妻並於1917年成立出版社,憑兩人獨特的眼光,出版許多在日後大放異彩、影響深遠的作家之作品,如艾略特( T. S. Eliot)、佛洛依德( Freud)、佛斯特( E. M. Forster)及曼斯菲爾( Katherine Mansfield)。為當代文壇重量級人物。
章節試閱
戴洛維夫人說她會自己去買花。露西已幫她完成了她的工作。大門的鉸鏈得先放下來,藍伯馬雅的工人將要來了。接著,克萊麗莎‧戴洛維心想:這是個多麼美好的早晨啊──清新得像是專為送給沙灘上的孩子們一般。多麼讓人欣喜!多麼讓人熱切地想投入!門打開時鉸鏈的吱吱聲──像現在這般,一直給她一種感覺,就彷彿如在布頓時一樣,當聽到門聲時,她會立即打開法國式的窗扉,傾身,然後將頭探入戶外的空氣中。多麼新鮮,多麼平靜啊!它當然比這時的空氣寧靜,那是清晨的空氣;就像是正在拍打沙灘的浪,寒冷、刺骨,並且(對一個當時只有十八歲的女孩而言)嚴肅。她站在窗邊,感覺到有一件可怕的事情將要發生。她看著花朵,看著晨霧瀰漫的樹和禿鼻烏鴉飛起又落下,她一直看到彼得‧華爾施說:「在園子裡凝思啊」──是那樣的嗎「人和花椰菜,我選人。」──是那樣的嗎他一定在某個早晨吃早餐時說過那樣一句話,那時她正走出屋外的台階。彼得‧華爾施,他最近將從印度回來,是六月或是七月她忘記了,因為他的信件實在無趣;人們會記得的是他的話語,他的眼睛,他的小刀,他的笑容,他怪戾的性情──多麼奇怪啊!當成千上萬的事都被徹底遺忘時,她唯一記得的是如此關於甘藍菜的話。她在路緣鑲邊石上僵呆了一會兒,等待杜諾公司的小貨車經過。史克羅比‧普維斯認為她是個迷人的女人(就像住在西敏寺區的人認識他們的左鄰右舍般);她彷彿一隻快樂的小鳥,藍綠色的、輕盈、活潑;縱使她已年過半百,並且在生病後就變得蒼白。她就站在那裡,不曾看到他,挺直地等待著過馬路。從開始住在西敏寺區1到現在幾年了呢超過二十年了──人們甚至在行車途中,或夢中醒來,都會覺得克萊麗莎是個積極的、一種特別沉默,或說嚴肅的人;一種難以形容的靜謐,或是大本鐘2未敲之前的一種停懸(不過大家覺得這也許是因為流行性感冒影響到她的心臟)。
聽!鐘聲隆隆響起。一開始是一個樂音聲的警告,然後是一個無法喚回的時刻,聲波的團圈逐漸消失在空氣中。我們是如此地愚蠢啊!她在越過維多利亞街的時候這樣想著。只有天曉得為甚麼會有人如此愛著它,怎麼會有人如此看待它,把它建立起來、製造成圓的、滾動它、使它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重新開始。但那些穿著玻舊邋遢、苦難的群眾中最悲悽的人們坐在門台上(啜飲著他們痛苦的生命)也享受著它;雖然無法處理這樣的事情,她至少為著國會法案覺得積極:他們都熱愛生命。在人們眼裡、在搖晃中、在沉重的腳步中,在咆哮與吼叫的喧囂中;馬車、汽車、公共馬車、小貨車、拖著腳步到處移走的夾板廣告員;銅管樂團、琵琶桶風琴;在音樂聲、叮噹聲及頭頂上時而傳來那些奇異尖銳的飛機聲中,是她所鍾愛的生活,倫敦、六月這個時節。這是六月中旬。戰爭結束了。除了一些人,像福克斯克洛夫特太太昨晚為了小男孩的被殺害致使古老的莊園要傳給表親而肝腸寸斷;或是主持義賣會場的貝克斯波羅芙夫人手裡拿著電報,據他們說,是她最親愛的約翰被殺害了;可是這一切都結束了,感謝上天──結束了。這是六月。國王和皇后在皇宮裡。縱使時間仍非常早,到處已是敲擊聲、跳動的馬蹄聲、球板的拍打聲;主教、阿斯科特賽馬場3、壤內拉夫和其餘的一切,都被包裹在早晨灰藍的空氣網絲中。只有當白天慢慢甦醒過來時,空氣網絲才會鬆解他們。草坪上有著馳騁的馬兒,那些馬兒足尖才敲擊土地便倏地蹤身躍起,目眩的青年們、穿著透明細薄的棉布衣服而笑得開懷的女孩們,縱使跳了一整夜的舞,現在仍牽著她們可笑的毛茸茸的小狗跑步;這個時刻,縱使是年老謹慎的孀居貴婦也乘著她們的轎車出使神秘的任務;店員們也在櫥窗邊玩弄著人工寶石、鑽石和來自十八世紀可愛的古董海綠色胸針來誘惑美國人(但人們必須節約──別輕率地為了伊麗沙白買東西),而她也一樣,愚蠢、忠誠地狂愛著這些東西,和群眾一般,曾經是喬治時代的諂媚者,她,也一樣,將在這個特別的夜晚戴上閃耀著光芒的首飾;舉辦宴會。但多麼奇怪啊,當走進園子時,那種沉默;那霧氣;那喧嘩聲;那些快樂慢慢游泳的鴨子;那些蹣跚走動的袋狀小鳥;還有那個該從政府大樓裡走出來、最適合帶著蓋有皇家印章的急件盒子的休‧偉特布萊德;她的老朋友休──那值得欽佩的休!
「早安,克萊麗莎!」休說,帶點誇張地,因為他們自小就認識對方了。
「妳要去哪兒啊」
「我喜歡在倫敦散步,」戴洛維夫人說。
「這實在比在鄉間散步還好,真的。」他們是來──很下幸──看醫生的。其他的人來看畫;上歌劇院;帶女兒出來;偉特布萊德一家是來「看醫生」的。克萊麗莎曾無數次來探訪過住在療養院的艾維玲‧偉特布萊德。艾維玲又生病了嗎艾維玲的狀況現在看起來算不錯了。穿著打扮很講究、很有男子氣概並且非常英俊的休嘟起嘴說(他通常都穿得太盛裝了,不過這大概是因為他想掩飾他在法院裡的卑微工作吧!),她太大是有一些內在疾病,沒甚麼大不了的,作為一個老朋友,克萊麗莎‧戴洛維滿能瞭解的,不會要他說清楚。啊!是了,她當然問過了。多麼討厭的事啊,在覺得非常親密的此刻她竟然奇怪地意識到自己的帽子,不是一頂適合清晨的帽子,是嗎休常讓她覺得,在他慌亂帶點誇大地舉起他的帽子來使她相信她可能是個十八歲的小女生時,當然他今晚是會來參加她的宴會的,艾維玲絕對堅持他必須來。他在參加完宮廷舉辦的宴會後只會晚到一點點,因為他必須帶金姆的其中一個男孩過去。──和休在一起,她常覺得自己有點兒小氣,像個女學生,但她卻對他產生愛慕。部份是由於她已經認識他很久了,但她確實覺得休個人的特質很好。雖然理察幾乎因為他而發怒;至於彼得‧華爾施呢是從頭到尾不曾原諒她對他的喜愛。她可以記得在布頓的每一幕場景──彼得在大發雷霆;休當然沒有。雖然在任何方面他們都旗鼓相當,但休卻不像彼得那般表現得像一個積極的笨蛋;並非單純的理髮師腦袋。當休年邁的母親要他停止打獵或帶她去巴斯4,他都二話不說地照辦;他是真的很不自私。就像彼得說的,他沒有心肝,沒有頭腦,甚麼都沒有,除了一個英國紳士的風度及教養。這僅僅是她親愛的彼得最差勁的時候;同時他可以是很令人無法忍受,他可以是不可理喻,但卻讓人喜愛在這樣的早晨中和他散步。
(六月把樹木的每一片新葉都抽引出來了。居住在品林寇5的母親們在餵養她們的小孩。消息從艦隊傳到海軍部。亞靈頓街及畢卡第里街6似乎在醞釀著那特別的空氣並興奮地舉起它的葉片,燦爛地,以一種克萊麗莎鍾愛的非凡活力的波浪姿態。跳舞吧,騎馬吧,她欣賞著這一切。)他們好像已經分開了幾百年,她和彼得。她從來沒有寫過一封信給他;而他則是像一塊枯燥的木頭。突然間一個念頭閃過她的腦際,如果他現在和我在一起他會說甚麼呢──某些時候,某些影像讓她平靜地想起他,但並沒有那種陳年的苦楚;也許這是關心別人的報酬。他們在一個美好的清晨回到聖詹姆士公園的中間──是的,他們確實做了。但彼得──縱使那天再美好,那些樹和草,那個穿粉紅色衣裳的小女孩──但彼得完全沒有看進半樣事物。那天如果她叫他戴上眼鏡的話,他就會戴上,他就會觀看。是這個世界的現狀吸引著他,華格納7、波普8的詩、人們永恒的個性,還有她個人靈魂的缺點。他是如何責備她的!他們是如何爭吵的引她會嫁給首相然後站在樓梯的最高層;他稱呼她是最完美的女主人(她曾為了這樣的稱呼而在睡房裡大哭),他說她有那種完美女主人的特質。而後她仍感受得到在聖詹姆士公園內的爭辯,她仍然堅持她是對的──她一直是對的──沒有嫁給他。在婚姻裡,兩個同居在一起、每日在同一間屋子進進出出的人還是需要一點自由,一點獨立的空間;這就是她和理察互相給予彼此的。
(就好比說這個早上他去了哪裡呢某些委員會吧,她從來不過問是甚麼。)但是和彼得在一起時,任何事情都必須是共享的,每一件發生的事──這是令人無法忍受的。然而,當發生噴泉旁小花園的那一幕時,她必須和他分手,否則她相信他們兩人都將會被毀滅。雖然這麼多年來她內心一直承受著像被飛箭射穿了心臟那般痛楚,一種極大的痛苦。後來,有人在一場演奏會上告訴她,他已經娶了一個在航向印度的船隻上邂逅的女人──她不可能忘記那一切!那種戰慄感!
「冷漠、無情、老古板。」他這樣說她;她永遠不會明白他是多麼地在乎。那些印度女人想必是漂亮但愚笨、膚淺和傻氣的。她是在浪費她的同情,因為他還滿快樂的,他對她保證──他是絕對的快樂,縱使他從未完成任何一件他們曾經談論過的事;他的一生,都再再顯示他是一個失敗者。這是使她最生氣的。她已經走到了公園的大門。她注視著畢卡第里街的公共汽車,佇立了好一會兒。她現在再也不會評論任何人是如何如何的了。她感覺自己很年輕,但同時又有一種難以言喻的蒼老。她像一把利刀剖析著每一件事;但於此同時,她又彷彿置身事外,冷眼旁觀。當她看著那些計程車時,她有一種永無止境的疏離感,遠遠地,遠至海的深處,而且孤獨。
她常常覺得:有了這種情緒甚至活著一天都非常非常地危險。並非她自覺聰明,或自命不凡。她無法想像她是如何以弗洛林‧丹尼爾教給她的一丁點兒知識一路走來!她甚麼都不懂,沒有語言,沒有歷史;她現在幾乎不看書,除了在床上看回憶錄;然而對她而言這一切都深深吸引著她的注意。所有這一切,包括計程車駛過;而她不會提起彼得,她也不會提起她自己,下會說「我是這個」或「我是那個」。
她繼續走著,心想:她唯一的天賦是幾乎可以憑直覺地去認識一個人。若把她和某人一起關在一個房間裡,她馬上會像貓一樣地弓背發怒;要不然她就會低聲咕嚕咕嚕地叫。德翁賽家中、貝斯家中、有中國白鸚的家中,她曾經看過它們全都燈火通明;記得修維雅、費樂德、莎莉‧石敦──這些屋子的主人,整個晚上跳著舞;還有那些拖著沉重的身軀經過、開往市場或穿越公園、駛向家中的四輪馬車。她記得有一次曾經丟了一枚銅板到蜿蜒的溪流裡。每個人都記得。她最愛的是此刻,在此地,在她眼前,這計程車中的胖婦人。當她走向包德街時,她反覆地問自己:有關係嗎真的有關係嗎儘管她終將無法避免死亡又如何呢即使沒有她,所有這一切仍會繼續的。她就因此而感到氣憤嗎抑或是相信死亡是絕對的結束而不能使人感到安慰但就在倫敦的某條街道上,在萬物的潮汐間──在這裡,在那裡,她活下來了,彼得活下來了,活在彼此之中。她成為家中的樹的一部份,屋子的一部份;醜陋地,蔓延在每一小片、每一碎塊,以及部份她從未見過的人當中。在熟知她的人們眼中,她就像霧,被他們高高舉起,就像樹木托起霧氣。但它很快就消散了,她的生命,她自己。然而當她看入哈查德的商店櫥窗時,她又在夢想著甚麼呢她在企圖尋回甚麼呢她在敞開的書本裡讀到關於鄉野灰白的破曉曙光,是怎麼樣的一番景象呢
戴洛維夫人說她會自己去買花。露西已幫她完成了她的工作。大門的鉸鏈得先放下來,藍伯馬雅的工人將要來了。接著,克萊麗莎‧戴洛維心想:這是個多麼美好的早晨啊──清新得像是專為送給沙灘上的孩子們一般。多麼讓人欣喜!多麼讓人熱切地想投入!門打開時鉸鏈的吱吱聲──像現在這般,一直給她一種感覺,就彷彿如在布頓時一樣,當聽到門聲時,她會立即打開法國式的窗扉,傾身,然後將頭探入戶外的空氣中。多麼新鮮,多麼平靜啊!它當然比這時的空氣寧靜,那是清晨的空氣;就像是正在拍打沙灘的浪,寒冷、刺骨,並且(對一個當時只有十八歲的...
推薦序
維吉尼亞吳爾芙與《戴洛威夫人》導論﹕游移於邊界的靈魂文化大學英文系助理教授張禮文2002年電影《時時刻刻》的上映,再次喚起社會大眾對維吉尼亞吳爾芙(1882-1941)及其小說《達洛威夫人》的關注與好奇。誕生於性別角色劃分嚴謹的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維吉尼亞正如其在〈自己的房間〉(“ A Roomof One’s Own”1929)一文中所虛構的「茱迪斯莎士比亞」一般,因為生為女性,無法和兄長一同接受正統的學校教育。然父親藏書豐富的圖書室和家中因文藝訪客頻繁所薰染起的文藝氣氛,直接地挑起維吉尼亞強烈的求知慾望和對文學的熱情。
1904年維吉尼亞與手足共組「布魯斯柏里藝文圈」( Bloomsbury Group),吸引無數哲學、美學、藝術、以及文學界的同好,創造一個眾生喧嘩的異言堂。集團中滿是才華洋溢的青年知識份子,思想先進且創新、言論大膽地挑戰舊有的制度和價值觀念。
1912年維吉尼亞與集團中的李奧納多吳爾芙( Leonardo Woolf)完婚,夫妻並於1917年成立出版社,憑兩人獨特的眼光,出版許多在日後大放異彩、影響深遠的作家之作品,如艾略特( T. S. Eliot)、佛洛依德( Freud)、佛斯特( E. M. Forster)及曼斯菲爾( Katherine Mansfield)。吳爾芙敏感纖細的觀察力和對傳統寫作僵化的疑慮,在「布魯斯柏里藝文圈」和當代文人雅士的密集接觸之後,迅速地轉化為她對心理學及意識流創作技巧的高度興趣。在其〈現代小說〉(“ Modern Fiction”1925)一文中,吳爾芙指出傳統小說線性的敘事方式以及精密的佈局,無法真切地刻畫人類流動的意識及網狀的生命連結,亦無法捕捉人心剎那之間的感動、頓悟,和複雜的內心活動。從這個角度看來,她認為威爾斯( H. G. Wells)、貝內特( Arnold Bennett)、與蓋斯沃其( John Galsworthy)的作品趨向物質化(materialistic)﹔因為過度著重外在事物的具體呈現,使他們忽略了筆下角色對環境的認知與反應。相比之下,喬伊斯( James Joyce)的小說顯得性靈化(spiritual),亦更貼近生命的本質。吳爾芙文中並表示﹕「生命並非一組對稱排列的車燈,而是一圈光暈、一種半透明的罩子,環繞著我們,從意識出始至其終結。」理想的小說不應著重在情節的鋪張或角色性格描繪,而是在俯拾即是的意象之中、在持續流動的意識之中、在自由游移於不同時空的靈魂之中。吳爾芙的第一部小說《出航》( The Voyage Out1915)紀錄少女瑞秋探索自我的旅程﹔主題創新,但敘事手法仍趨保守。
第二部長篇小說《夜與日》( Nightand Day1919)依舊沿襲傳統全知全能敘述方式呈現故事情節。但自第三本小說《雅各的房間》( Jacob’s Room1922)開始,吳爾芙注入大量的反傳統手法,藉由交錯不同的敘事角度、不同角色的內在獨白、以及跳躍式的意識流動,從鬆散的、片段的、與夾雜空隙的結構中,描繪主人翁雅各的一生。歷時兩年寫作,在1925年正式出版的《戴洛威夫人》中,吳爾芙的意識流技巧臻於成熟﹕沒有情節、章節的故事,充斥著不同人物的瞬間感覺、自由聯想、直接或間接的內心獨白、和流洩湧現的多重意象。表面是記述倫敦國會議員之妻,戴洛威夫人,1923年六月在倫敦的某一天,但其中卻織匯上百個形形色色的角色﹔各主題看似無關卻又不規則地相互聯結,從戴洛威夫人的宴會到女性次等地位、一次世界大戰戰前與戰後的英國社會、異性戀霸權中的同性情慾、及理智與瘋狂的權力對峙﹔時間跳躍數十年﹔空間亦隨各角色之意識而流轉四處。正如吳爾芙在日記中所言﹕「我在這本小說所要表達的東西太多了,從生到死、從理智到瘋狂﹔我要批判當今的社會制度,並揭露它的整個運作方式。」整部小說精采地展現了吳爾芙的「隧道理論」(tunnelingprocess)。作者摒棄傳統小說對人物的經營,致力挖掘不同角色背後不為人知的洞穴,並打通各洞穴、串聯起錯綜複雜卻四通八達的隧道,交疊現在與過去的雙重時空、交織外在事件與內在意識,並巧妙地藉由鬆動、轉換主體與客體的位置,聯繫不同角色的經驗於同一時空之中。例如,故事初始時公務車的引擎爆破聲吸引了戴洛威夫人和眾人的注意,敘述焦點由戴洛威夫人流轉到在場行人的意識裡,同時也順勢牽引出另一條敘述主線,將同為觀眾的塞普提姆斯帶入故事。又,在彼得華爾施稍早短暫拜訪戴洛威夫人的一幕,意識在曾為情人的兩角之間輪轉﹔兩人時為主體,時為客體,互為主體亦互為客體,唯有仔細的讀者方能細細拼湊出最接近真相的全貌。像是結合當代的立體派及印象派畫風一般,小說中單一事件不再呈現單一平面事實,反由不同觀者的不同角度共構多面向的立體事實﹔同一時間裡,觀者是自我主體,也是其他觀者眼中的客體,多層次的意識將人與人之間的複雜網路脈絡表露無疑。原名為《時時刻刻》,《戴洛威夫人》透露除了英國國會塔頂的大本鐘( The Big Ben)所代表的「物理時間」在支配人的外在生活,尚有「心理時間」流動於人的內在意識和潛意識之中。大本鐘按時響起,鐘聲時時刻刻地提醒人們遵循強固的規律與現存體制。大本鐘所劃定的時間並非真實所在,因為真實乃存在於主觀意識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間所產生的認知上。然而,大本鐘所設定的標準,象徵社會中所有不容質疑的權威和保守勢力——亦即小說中威廉布拉得邵爵士所言之「神聖的均衡」——毫不留情地劃定界線,或有形、或無形,在不同的地方掌控著生存在團體中的每一個個體,箝制每個人的思想與行為,沒有任何越界脫軌的空間。退伍軍人塞普提姆斯即是權威之下的犧牲者之一。戰爭的殘酷與好友的戰亡,讓塞普提姆斯成為徘徊在理智邊界的「瘋子」,其幻想、幻聽、與幻覺的徵兆,加上狂言狂語的行為,再再挑戰既定的社會習俗與秩序。他熱愛生命,但「陽光多麼炙熱」,亦即權威的力量太大,讓戰後心理受創的塞普提姆斯無法以權威所限定的社會符碼和他人進行所謂的「理性」溝通。也因此在保守人士如威廉爵士的眼中,塞普提姆斯是個異類,是具有威脅性的他者( Other),必須送進療養院進行休養,直到他重新循規蹈矩地進入「均衡」的殿堂中。在躍入死亡前,塞普提姆斯大喊﹕「我會把它交給你﹗」實際上,塞普提姆斯並未屈服權威。肉體的殞滅諷刺地解放了長期被強權壓榨的靈魂。他交出去的只是軀殼,而死亡也是唯一的方式可以讓他在保有自由心靈的同時,對強權壓迫發出無聲卻嚴正的抗議。他的死亡代表一種反抗,但同時也是彼得華爾施所說的,代表「文明的其中一項勝利」。
塞普提姆斯的死訊,不啻為正在舉辦晚宴的克萊麗莎戴洛威帶來不小的震撼。戴洛威夫人和塞普提姆斯乍看之下是兩個毫不相關的個體,不論在年齡、性別、或社會階級,皆有不同﹔但後者的死亡卻觸動了前者心靈一角,促其頓悟生與死、強權與弱勢、正常與失常、個體與群體之間的微妙關係。對克萊麗莎來說,塞普提姆斯充其量是個剛結束自己生命的小人物,但她卻深刻且近乎精準地將陌生年輕人的死亡,與威廉爵士所代表的權威畫上等號。年輕時的克萊麗莎也曾對生命充滿熱情與活力,也曾和同性友人莎莉之間產生曖昧情愫,但父權社會對於傳統女人角色的期待,漸漸地閹割了克萊麗莎的女性自主意識,將她塑成一個符合標準的「家庭天使」( Angelinthe House),溫柔、純淨、並且忠實扮演父權所安排的角色。社會經驗告訴她女人是永遠的「他者」,如同「狂人」。
唯有選擇異性戀婚姻,選擇為人妻、為人母的角色,她才能在奉父權體制為圭臬的社會,以附屬品的身分安然存在,像面鏡子永遠反射男性的完整主體。塞普提姆斯就像是克萊麗莎的另外一個自我,而這個因後天社會化而退居幕後的隱性自我,渴望使用父權規範之外的的語言,期盼能有一天卸下多重的社會面具,為「自己」而活,以真實的自我面對大眾。但在社會尚未準備好收納「不同的聲音」與「不同的女性形象」的同時,克萊麗莎選擇一條和塞普提姆斯不一樣的路。她知道唯有進入體制內的婚姻制度、暫時藏身在「戴洛威夫人」的社會角色背後,走入人群且使用體制內的溝通符號,她才有機會得以模糊、甚或消弭彊界的劃分。一方面她為塞普提姆斯的死亡感到欣慰,終究這個善感的年輕人「不再害怕太陽的炙熱」,不需要再受現實桎梏綑綁。另一方面,她也知道「她必須回到人群中」,必須邀請那些「邪惡」、卻掌控社會秩序的權威人士,以議員夫人的身分交際應酬。但是,縱使舞台上眾人看到的是「戴洛威夫人」,克萊麗莎並沒有從世界上消失,她隨時可頓入閣樓那屬於她自己的小房間,面對她自己。相較於塞普提姆斯的鍾於自我,克萊麗莎採取一種妥協、折衷的方式,以雙面生活迎合社會的期望並護衛自己的本性。某個程度看來,或許克萊麗莎正如同在彼得的內心獨白中所言,是個虛假、太過關心階級與社會的世俗人。然不能否認的是,不論是外在喧囂的宴會或是既定的權威符碼,都沒有全然淹沒克萊麗莎原有的聲音或扼殺她隱遁的靈魂。反觀同為上流階級的布拉得紹夫人,在「十五年前她就已經沉淪了…她的意識走入他的(布拉得邵爵士)…她的屈服是快速的。」自始至終,我們不曾聽聞布拉得紹夫人的本名,因為「她」已經不再存在了。存在的,是一副沒有靈魂的軀殼,永遠宣示對父權體制的忠實。大本鐘的沉重鐘聲將外在時間組織、規格化,有人全然抵抗(如塞普提姆斯),有人全然接收(如布拉得紹夫人),但克萊麗莎戴洛威選擇中界地帶(liminalzone),跟著物理時間走,卻也讓流動的自我主觀意識馳騁於不同的內在時空之中。同樣地,雖然在「神聖的均衡」壓迫之下,肉體死亡是一種心靈解脫,但唯有肉體在群體中活著,個體才有可能改變舊的制度、重劃疆界、進而創造新的世界。世界不可能為個人而轉動,因此,游移於外在事件與內在意識的靈魂不僅要學習與自己的孤寂相處,也該學習使用、解構、進而建構群體的共通符碼。除了克萊麗莎與塞普提姆斯之外,小說中從多重的流動敘事聲音,亦牽帶出其他許多值得討論的角色,就有待讀者去細細品味了。
維吉尼亞吳爾芙與《戴洛威夫人》導論﹕游移於邊界的靈魂文化大學英文系助理教授張禮文2002年電影《時時刻刻》的上映,再次喚起社會大眾對維吉尼亞吳爾芙(1882-1941)及其小說《達洛威夫人》的關注與好奇。誕生於性別角色劃分嚴謹的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維吉尼亞正如其在〈自己的房間〉(“ A Roomof One’s Own”1929)一文中所虛構的「茱迪斯莎士比亞」一般,因為生為女性,無法和兄長一同接受正統的學校教育。然父親藏書豐富的圖書室和家中因文藝訪客頻繁所薰染起的文藝氣氛,直接地挑起維吉尼亞強烈的求知慾望和對文學的熱情。
1904年維吉尼...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32收藏
32收藏

 19二手徵求有驚喜
19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