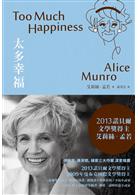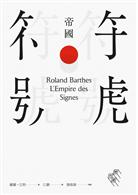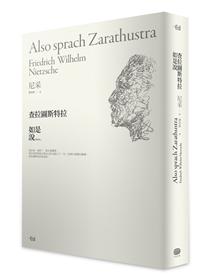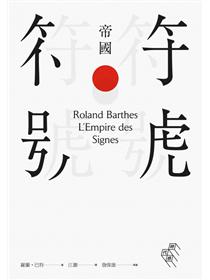張愛玲也許不是時下「正確」定義裡的女性主義者,
但在《怨女》中,她從未停止對女性命運的嚴肅思考。
──【美國哈佛大學講座教授】王德威
張愛玲逝世15週年全新改版
本書內容與舊版相同
十八歲的銀娣是出了名的「麻油西施」,由於父母早逝,拮据的哥哥和嫂子一直想把她早點嫁出去。其實銀娣心裡有喜歡的人,但那人似乎不會有多大出息。仔細思量,如果成了哥嫂的窮親戚,人家一定會說她嫁得不好。
沒有錢的苦處她是受夠了,於是,銀娣終於同意姚家瞎子少爺的這門親事。雖然她嫁的人永遠不會看見她,但今後一生一世都會像在戲台上過,腳底下是電燈,一舉一動都有音樂伴奏。
但這時候的銀娣當然不會知道,她未來的人生舞台是荊棘遍地,而她的少爺也不只是看不見她而已……
《怨女》是張愛玲創作晚期的代表作之一,不僅被改編成電影,更備受國內外文壇重視。這本由短篇小說〈金鎖記〉擴充改寫而成的長篇小說,描繪大時代下女人被命運撥弄而扭曲的一生,從青春年少的充滿憧憬,一直到被現實環境壓迫的人生幻滅,在張愛玲臻至化境的文字中,讓人唏噓也讓人心驚。
作者簡介:
關於張愛玲
本名張煐,一九二○年生於上海。二十歲時便以一系列小說令文壇為之驚豔。她的作品主要以上海、南京和香港為故事場景,在荒涼的氛圍中鋪張男女的感情糾葛以及時代的繁華和傾頹。
有人說張愛玲是當代的曹雪芹,文學評論權威夏志清教授更將她的作品與魯迅、茅盾等大師等量齊觀,而日後許多作家都不諱言受到「張派」文風的深刻影響。
張愛玲晚年獨居美國洛杉磯,深居簡出的生活更增添她的神秘色彩,但研究張愛玲的風潮從未止息,並不斷有知名導演取材其作品,近年李安改拍〈色,戒〉,更是轟動各界的代表佳作。
一九九五年九月張愛玲逝於洛杉磯公寓,享年七十四歲。她的友人依照她的遺願,在她生日那天將她的骨灰撒在太平洋,結束了她傳奇的一生。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名家推薦:
【美國哈佛大學講座教授】王德威、【劇作家】王蕙玲【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林幸謙【加州柏克萊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林郁庭【文史作家】蔡登山◎共同推薦
「《金鎖記》的七巧那樣決絕乖戾,其實是張愛玲人像畫廊中的例外。反倒是銀娣,陷身於不清不楚的生命情境,才真正演出了人生的脆弱與寒涼……對張而言,銀娣的悲劇應不在於她接受命運的擺弄,而在於她始終企圖超越她所受的束縛。」 ──【美國哈佛大學講座教授】王德威
「她領你遊走在夜色的弄堂,人性幽微的暗巷。 她轉身消失,卻把你留下。 你兀自在其中徘徊。 不待瞎子撥動三弦唱出命運,百年上海的滋味就從方塊字的隔窗裏飄散出來……」 ──【劇作家】王蕙玲
從〈金鎖記〉到《怨女》,張愛玲以隱匿屏蔽的敘事講述了分裂的他者/主體如何挪用自我的匱乏去建構女性文本。此類壓抑性質的公眾神話,長期被驅入/隱匿在歷史敘述之中,並被各種道德規範的名目所修飾掩蔽;通過她的女性修辭,張愛玲深入歷史-社會尋找女性書寫的模式,重新定義女性身份與慾望的符號。──【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林幸謙
「《怨女》成於中年旅美期間,改寫自張愛玲英文原著Roug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同竄紅上海的短篇〈金鎖記〉,皆敘述蓬門碧玉嫁入豪邸含怨以終的故事。隔了歲月與時空的美學距離,原為西方讀者書寫的《怨女》以長篇格局展現張氏走出中國、進入世界文學史的企圖,實不可小覷。」 ──【加州柏克萊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林郁庭
「寫出一個女人的憧憬、掙扎、失落與絕望,層層地剝去繁華的外衣,較之《金鎖記》,更見人性的蒼涼!」──【文史作家】蔡登山
名人推薦:名家推薦:
【美國哈佛大學講座教授】王德威、【劇作家】王蕙玲【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林幸謙【加州柏克萊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林郁庭【文史作家】蔡登山◎共同推薦
「《金鎖記》的七巧那樣決絕乖戾,其實是張愛玲人像畫廊中的例外。反倒是銀娣,陷身於不清不楚的生命情境,才真正演出了人生的脆弱與寒涼……對張而言,銀娣的悲劇應不在於她接受命運的擺弄,而在於她始終企圖超越她所受的束縛。」 ──【美國哈佛大學講座教授】王德威
「她領你遊走在夜色的弄堂,人性幽微的暗巷。 她轉身消失,卻把你留下。 你...
章節試閱
一
上海那時候睡得早,尤其是城裏,還沒有裝電燈。夏夜八點鐘左右,黃昏剛澄淀下來,天上反而亮了,碧藍的天,下面房子墨黑,是沉澱物,人聲嗡嗡也跟著低了下去。
小店都上了排門,石子路上只有他一個人踉踉蹌蹌走著,逍遙自在,從街這邊穿到那邊,哼著京戲,時而夾著個「梯格隆地咚」,代表胡琴。天熱,把辮子盤在頭頂上,短衫一路敞開到底,裸露著胸脯,帶著把芭蕉扇,刮喇刮喇在衣衫下面搧著背脊。走過一家店家,板門上留著個方洞沒關上,天氣太熱,需要通風,洞裏只看見一把芭蕉扇在黃色的燈光中搖來搖去。看著頭暈,緊靠著牆走,在黑暗中忽然有一條長而涼的東西在他背上游下去,他直跳起來。第二次跳得更高,想把它抖掉,又扭過去拿扇子撣。他終於明白過來,是辮子滑落下來。
「操那!」
用芭蕉扇大聲拍打著屁股,踱著方步唱了起來,掩飾他的窘態。
「孤王酒醉桃花宮,韓素梅生來好貌容。」
一句話提醒了自己,他轉過身來四面看了看,往回走過幾家門面,揀中一家,蓬蓬蓬拍門。
「大姑娘!大姑娘!」
「誰?」樓上有個男人發聲喊。
「大姑娘!買麻油,大姑娘!」
叫了好幾聲沒人應。
「關門了,明天來。」這次是個女孩子,不耐煩地。
他退後幾步往上看,樓窗口沒有人。劣質玻璃四角黃濁,映著燈光,一排窗戶似乎凸出來做半球形,使那黯舊的木屋顯得玲瓏剔透,像玩具一樣。
「大姑娘!老主顧了,大姑娘!」
蓬蓬蓬儘著打門。樓上半天沒有聲音,但是從門縫裏可以看見裏面漸漸亮起來,有人拿著燈走進店堂,門洞上的木板啦塔一聲推了上去,一股子刺鼻的刨花味夾著汗酸氣,她露了露臉又縮回去,燈光從下頦底下往上照著,更托出兩片薄薄的紅嘴唇的式樣。離得這樣近,又是在黑暗中突然現了一現,沒有真實感,但是那張臉他太熟悉了,短短的臉配著長頸項與削肩,前劉海剪成人字式,黑鴉鴉連著鬢角披下來,眼梢往上掃,油燈照著,像個金面具,眉心豎著個梭形的紫紅痕。她大概也知道這一點紅多麼俏皮,一夏天都很少看見她沒有揪痧。
「這麼晚還買什麼油?快點,瓶拿來。」她伸出手來,被他一把抓住了。
「拉拉手。大姑娘,拉拉手。」
「死人!」她尖聲叫起來。「殺千刀!」
他吃吃笑著,滿足地喃喃地自言自語,「麻油西施。」
她一隻手扭來扭去,烏籐鑲銀手鐲在門洞口上磕著。他想把鐲子裏掖著的一條手帕扯下來,鐲子太緊,抽不出來,被她往後一掣,把他的手也帶了進去,還握著她的手不放。
「可憐可憐我吧,大姑娘,我想死你了,大姑娘。」
「死人,你放不放手?」她蹬著腳,把油燈湊到他手上。錫碟子上結了層煤烟的黑殼子,架在白木燈台上,他手一縮,差點被他打翻了。
「噯喲,噯喲!大姑娘你怎麼心這麼狠?」
「鬧什麼呀?」她哥哥在樓上喊。
「這死人拉牢我的手。死人你當我什麼人?死人你張開眼睛看看!爛浮尸,路倒尸。」
她嫂子從窗戶裏伸出頭來。「是誰?──走了。」
「是我拿燈燙了他一下,才跑了。」
「是誰?」
「還有誰?那死人木匠。今天倒楣,碰見鬼了。豬玀,癟三,自己不撒泡尿照照。」
「好了,好了,」她哥哥說。「算了,大家鄰居。」
「大家鄰居,好意思的?半夜三更找上門來。下趟有臉再來,看我不拿門閂打他。今天便宜他了,癟三,死人眼睛不生。」
她罵得高興,從他的娘操到祖宗八代,幾條街上都聽得見。她哥哥終於說,「好了好了,還要哇啦哇啦,還怕人家不曉得?又不是什麼有臉的事。」
「你要臉?」她馬上掉過來向樓上叫喊。「你要臉?你們背後鬼頭鬼腦的事當人不知道?怎麼怪人家看不起我。」
「還要哇啦哇啦。怎麼年紀輕輕的女孩子不怕難為情?」炳發已經把聲音低了下來,銀娣反而把喉嚨提高了一個調門,一提起他們這回吵鬧的事馬上氣往上湧︰
「你怕難為情?你曉得怕難為情?還說我哇啦哇啦,不是我鬧,你連自己妹妹都要賣。爺娘的臉都給你丟盡了,還說我不要臉。我都冤枉死了在這裏──我要是知道,會給他們相了去?」
炳發突然一欠身像要站起來,赤裸的背脊吮吸著籐椅子,吧!一聲響。但是他正在洗腳,兩隻長腿站在一隻三隻腳的紅漆小木盆裏。
「好了好了,」他老婆低聲勸他。「讓她去,女孩子反正是人家的人,早點嫁掉她就是了。女大不中留,留來留去反成仇。等會給人家說得不好聽,留著做活招牌。」
炳發用一條絲絲縷縷的破毛巾擦腳,不作聲。
「告訴你,我倒真有點担心,總有一天鬧出花頭來。」
他怔了一怔。「怎麼?你看見什麼沒有?」
「喏,就像今天晚上。惹得這些人一天到晚轉來轉去。我是沒工夫看著她,拖著這些個孩子,要不然自己上櫃台,大家省心。」
「其實去年攀給王家也還不錯,八仙橋開了爿分店。」他歪了歪下頦,向八仙橋那邊指了指。
「也是你不好,應當是你哥哥做主的事,怎麼能由她,嫌人家這樣那樣。講起來沒有爺娘;耽誤了她,人家怪你做哥哥的。下次你主意捏得牢點。」
他又不作聲了。也是因為辦嫁妝這筆花費,情願一年年耽擱下來。她又不是不知道。朱漆腳盆有隻鵝頸長柄,兩面浮雕著鵝頭的側影,高豎在他跟前,一隻雙圈鵝眼定定地瞅著他,正與她不約而同。她瞅了半天,終於拎起腳盆,下樓去潑水,正遇見銀娣上來。在狹窄的樓梯上,姑嫂狹路相逢,只當不看見。
銀娣回到自己的小房間裏,熱得像蒸籠一樣。木屋吸收了一天的熱氣,這時候直噴出來。她把汗濕的前劉海往後一掠,解開元寶領,領口的黑緞闊滾條洗得快破了,邊上毛茸茸的。藍夏布衫長齊膝蓋,匝緊了黏貼在身上,窄袖、小袴腳管,現在時興這樣。她有點頭痛,在枕頭底下摸出一隻大錢,在一碗水裏浸了浸,坐下來對鏡子刮痧,拇指正好嵌在錢眼裏,伏手。熟練地一長劃到底,一連幾劃,頸項上漸漸出現三道紫紅色斑斑點點的闊條紋,才舒服了些。頸項背後也應當刮,不過自己沒法子動手,又不願意找她嫂子。
上回那件事,都是她嫂嫂搗的鬼。是她嫂嫂認識的一個吳家嬸嬸來做媒,說給一個做官人家做姨太太。說得好聽,明知他們柴家的女兒不肯給人做小,不過這家的少爺是個瞎子,沒法子配親,所以娶這姨太太就跟太太一樣。銀娣又哭又鬧,哭她的爹娘,鬧著要尋死,這才不提了。這吳家嬸嬸是女傭出身,常到老東家與他們那些親戚人家走動,賣翠花,賣鑲邊,帶著做媒,接生,向女傭們推銷花會。她跟炳發老婆是邀會認識的。有一次替柴家兜來一票生意,有個太太替生病的孩子許願,許下一個月二十斤燈油,炳發至今還每個月挑担油送到廟裏去。
這次她來找炳發老婆,隔了沒有幾天又帶了兩個女人來,銀娣當時就覺得奇怪,她們走過櫃台,老盯著她看。炳發老婆留她們在店堂後面喝茶,聽著彷彿是北方口音,也沒多坐。臨走炳發老婆定要給她們僱人力車,叫銀娣「拿幾隻角子給我。」她只好從錢台裏拿了,走出櫃台交給她。兩個客人站在街邊推讓,一個抓住銀娣的手不讓她給錢,乘機看了看手指手心。
「姑娘小心,不要踏在泥潭子裏。」吳家嬸嬸彎下腰去替她拎起袴腳來,露出一隻三寸金蓮。
她早就疑心了。照炳發老婆說,這兩個是那許願的太太的女傭,剛巧順路一同來的。月底吳家嬸嬸又來過,炳發老婆隨即第一次向她提起姚家那瞎子少爺。她猜那兩個女人一定是姚家的傭人,派來相看的。買姨太太向來要看手看腳,手上有沒有皮膚病,腳樣與大小。她氣得跟哥哥嫂嫂大吵了一場,給別人聽見了還當她知道,情願給他們相看,說不成又還當是人家看不中。
她哥哥嫂子大概倒是從來沒想到在她身上賺筆錢,一直當她是賠錢貨,做二房至少不用辦嫁妝。至今他們似乎也沒有拿她當做一條財路,而是她攔著不讓他們發筆現成的小財。她在家裏越來越難做人了。
附近這些男人背後講她,拿她派給這個那個,彼此開玩笑,當她的面倒又沒有話說。有兩個膽子大的伏在櫃台上微笑,兩隻眼睛涎澄澄的。她裝滿一瓶油,在櫃台上一秤,放下來。
「一角洋錢。」
「嘖,嘖!為什麼這麼兇?」
她向空中望著,金色的臉漠然,眉心一點紅,像個神像。她突然吐出兩個字,「死人!」一扭頭吃吃笑起來。
他心癢難搔地走了。
只限於此,徒然叫人議論,所以雖然是出名的麻油西施,媒人並沒有踏穿她家的門檻。十八歲還沒定親,現在連自己家裏人都串通了害她。漂亮有什麼用處,像是身邊帶著珠寶逃命,更加危險,又是沒有巿價的東西,沒法子變錢。
青色的小蜢蟲一陣陣撲著燈,沙沙地落在桌上,也許吹了燈涼快點。她坐在黑暗裏搧扇子。男人都是一樣的。有一個彷彿稍微兩樣點,對過藥店的小劉,高高的個子,長得漂亮,倒像女孩子一樣一聲不響,穿著件藏青長衫,白布襪子上一點灰塵都沒有,也不知道他怎麼收拾得這樣乾淨,住在店裏,也沒人照應。她常常看見他朝這邊看。其實他要不是膽子小,很可以藉故到柴家來兩趟,因為他和她外婆家是一個村子的人,就在上海附近鄉下。她外公外婆都還在,每次來常常彎到藥店去,給他帶個信,他難得有機會回家。
過年她和哥哥嫂子帶孩子們到外婆家拜年,本來應當年初一去的,至遲初二三,可是外婆家窮,常靠炳發幫助,所以他們直到初五才去,在村子裏玩了一天。她外婆提起小劉回來過年,已經回店裏去了。銀娣並沒有指望著在鄉下遇見他,但是仍舊覺得失望。她氣她哥哥嫂子到初五才去拜年,太勢利,看不起人,她母親在世不會這樣。想著馬上眼淚汪汪起來。
她一直喜歡藥店,一進門青石板鋪地,各種藥草乾澀的香氣在寬大黑暗的店堂裏冰著。這種店上品。前些時她嫂子坐月子,她去給她配藥,小劉迎上來點頭招呼,接了方子,始終眼睛也沒抬,微笑著也沒說什麼,背過身去開抽屜。一排排的烏木小抽屜,嵌著一色平的雲頭式白銅栓,看他高高下下一隻隻找著認著,像在一個奇妙的房子裏住家。她尤其喜歡那玩具似的小秤。回到家裏,發現有一大包白菊花另外包著,藥方上沒有的。滾水泡白菊花是去暑的,她不怎麼愛喝,一股子青草氣。但是她每天泡著喝,看著一朵朵小白花在水底胖起來,緩緩飛升到碗面。一直也沒機會謝他一聲,不能讓別人知道他拿店裏東西送人。
此外也沒有什麼了。她站起來靠在窗口。藥店板門上開著個方洞,露出紅光來,與別家不同。洞上糊上一張紅紙,寫著「如有急症請走後門」,紙背後點著一盞小油燈。她看著那通宵亮著的明淨的紅方塊,不知道怎麼感到一種悲哀,心裏倒安靜下來了。
二
大餅攤上只有一個男孩子打著赤膊睡在揉麵的木板上。腳頭的鐵絲籠裏沒有油條站著。早飯那陣子忙,忙過了。
剃頭的坐在凳子上打盹。他除了替男主顧梳辮子,額上剃出個半禿的月亮門,還租毛巾臉盆給人洗臉,剃頭担子上自備熱水。下午生意清,天又熱,他打瞌睡漸漸伏倒在臉盆架上,把臉埋在洋磁盆裏。
一個小販挑著一担子竹椅子,架得有丈來高,堆成一座小山。都是矮椅子,肥唧唧的淡青色短腿,短手臂,像小孩子的鬼。他在陰涼的那邊歇下担子,就坐在一隻椅子上盹著了。
店門口一對金字直匾一路到地,這邊是「小磨麻油生油麻醬」。銀娣坐在櫃台後面,拿隻鞋面鎖邊。這花樣針腳交錯,叫「錯到底」,她覺得比狗牙齒文細些,也別致些,這名字也很有意思,錯到底,像一齣苦戲。手汗多,針澀,眼睛也澀。太陽晒到身邊兩隻白洋磁大缸上,雖然蓋著,缸口拖著花生醬的大舌頭,蒼蠅嗡嗡的,聽著更瞌睡。
她一抬頭看見她外公外婆來了,一先一後,都舉著芭蕉扇擋著太陽。他們一定又是等米下鍋,要不然這麼熱的天,不會老遠從鄉下走了來。她只好告訴他們炳發夫婦都不在家,帶著孩子們到丈人家去了。
她一看見他們就覺得難過,老夫妻倆笑嘻嘻,腮頰紅紅的,一身褪色的淡藍布衫袴,打著補釘。她也不問他們吃過飯沒有,馬上拿抹布擦桌子,擺出兩副筷子,下廚房熱飯菜,其實已經太陽偏西了。她端出兩碗剩菜,朱漆飯桶也有隻長柄,又是那隻無所不在的鵝頭,翹得老高。她替他們裝飯,用飯勺子拍打著,堆成一個小丘,圓溜溜地突出碗外,一碗足抵兩碗。她外婆還說,「撳得重點,姑娘,撳得重點。」
老夫婦在店堂裏對坐著吃飯,太陽照進來正照在臉上,眼睛都睜不開,但是他們似乎覺都不覺得,沉默中只偶然聽見一聲碗筷叮噹響。她看著他們有一種恍惚之感,彷彿在斜陽中睡了一大覺,醒過來只覺得口乾。兩人各吃了三碗硬飯,每碗結實得像一隻拳頭打在肚子上。老太婆幫她洗碗,老頭子坐下來,把芭蕉扇蓋在臉上睡著了。
她們洗了碗回到店堂前,遠遠聽見三絃聲。算命瞎子走得慢,三絃聲斷斷續續在黑瓦白粉牆的大街小巷穿來穿去,彈的一支簡短的調子再三重複,像迴文錦卍字不斷頭。聽在銀娣耳朵裏,是在預言她的未來,彎彎曲曲的路構成一個城巿的地圖。她伸手在短衫口袋裏數銅板。她外婆也在口袋裏掏出錢來數,喃喃地說,「算個命。」老太婆大概自己覺得浪費,吃吃笑著。
「外婆你要算命?」她精明,決定等著看給她外婆算得靈不靈再說。
她們在門口等。
「算命先生!算命先生!」
她希望她們的叫聲引起小劉的注意,他知道她外婆在這裏,也許可以溜過來一會,打聽他村子裏的消息。但是他大概店裏忙,走不開。
「算命先生!」
自從有這給瞎子做妾的話,她看見街上的瞎子就有種異樣的感覺,又討厭又有點怕。瞎子走近了,她不禁退後一步。老太婆托著他肘彎攙他過門檻。他沒有小孩帶路,想必他實在熟悉這地段。年紀不過三十幾歲,穿著件舊熟羅長衫,像個裁縫。臉黃黃的,是個獅子臉,一條條橫肉向下掛著,把一雙小眼睛也往下拖著,那副酸溜溜的笑容也像裁縫與一切受女人氣的行業。
老太婆替他端了張椅子出來,擱在店門口。「先生,坐!」
「噢,噢!」他捏著喉嚨,像唱彈詞的女腔道白。他先把一隻手按在椅背上,緩緩坐下身去。
老太婆給自己端張椅子坐在他對面,幾乎膝蓋碰膝蓋,唯恐漏掉一個字沒聽見。她告訴了他時辰八字,他喃喃地自己咕噥了兩句,然後馬上調起絃子,唱起她的身世來,熟極而流。銀娣站在她外婆背後,唱得太快,有許多都沒聽懂,只聽見「算得你年交十四春,堂前定必喪慈親。算得你年交十五春,無端又動紅鸞星。」她不知道外婆的母親什麼時候死的,但是彷彿聽見說是從小定親,十七歲出嫁。算得不靈,她幸而沒有叫他算,白糟蹋錢。她覺得奇怪,老婦人似乎並沒有聽出什麼錯誤。她是個算命的老手,聽慣那一套,決不會不懂。她不住地點頭,嘴裏「唔,唔,」鼓勵他說下去。對於歷年發生的事件非常滿意,彷彿一切都不出她所料。
她兩個兒子都不成器。算命的說她有一個兒子可以「靠老終身」,有十年老運。
「還有呢?還有呢?」她平靜地追問。「那麼我終身結果到底怎樣?」
銀娣實在詫異,到了她這年紀,還另有一個終身結果?
算命的嘆了口氣。「終身結果倒是好的哩!」他又唱了兩句,將剛才應許她的話又重複了一遍。
「還有呢?」平靜地,毫不放鬆。「還有呢?」
銀娣替她覺得難為情。算命的微窘地笑了一聲,說︰「還有倒也沒有了呢,老太太。」
她很不情願地付了錢,攙他出店。這次銀娣知道小劉明明看見她們,也不打招呼。她又氣又疑心,難道是聽見什麼人說她?是為了她那天晚上罵那木匠,還是為那回相親的事?
「太陽都在你這邊,」她外婆說。是不是拿他們的店和對過藥店比?倒像是她也看見了小劉也不理他?
「不曉得你哥哥什麼時候回來,」老太婆坐定下來說。「我有話跟他們說。」她大模大樣添上了一句。她除了借錢難得有別的事來找他們,所以非常得意,到底忍不住要告訴銀娣。「小劉先生的娘昨天到我們那裏來。小劉先生人真好,不聲不響的,脾氣又好。」
銀娣馬上明白了。
她繼續自言自語,「他這行生意不錯,店裏人緣又好,都說他寡婦母親福氣,總算這兒子給她養著了。雖然他們家道不算好,一口飯總有得吃的。家裏人又少,姐姐已經出嫁了,妹妹也就快了。他娘好說話。」
銀娣只顧做鞋,把針在頭髮上擦了擦。
「姑娘,我們就你一個外孫女兒,住得近多麼好。你不要怕難為情,可憐你沒有母親,跟外婆說也是一樣的,告訴外婆不要緊。」
「告訴外婆什麼?」
「你跟外婆不用怕難為情。」
「外婆今天怎麼了?不知道你說些什麼。」
老太婆呷呷地笑了,也就沒往下說。她顯然是願意的。
算命的兜了個圈子又回來了。遠遠聽見三絃琤琮響,她在喜悅中若有所失。她不必再想知道未來,她的命運已經注定了。
她要跟他母親住在鄉下種菜,她倒沒想到這一點。他一年只能回來幾天。澆糞的黃泥地,刨鬆了像糞一樣纍纍的,直伸展到天邊。住在個黃泥牆的茅屋裏,伺候一個老婦人,一年到頭只看見季候變化,太陽影子移動,一天天時間過去,而時間這東西一心一意,就光想把她也變成個老婦人。
小劉不像是會鑽營的人。他要是做一輩子夥計,她成了她哥嫂的窮親戚,和外婆一樣。人家一定說她嫁得不好,她長得再醜些也不過如此。終身大事,一經決定再也無法挽回,尤其是女孩子,尤其是美麗的女孩子。越美麗,到了這時候越悲哀,不但她自己,就連旁邊看著的人,往往都有種說不出來的惋惜。漂亮的女孩子不論出身高低,總是前途不可限量,或者應當說不可測,她本身具有命運的神秘性。一結了婚,就死了個皇后,或是死了個名妓,誰也不知道是哪個。
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她外婆再問炳發什麼時候回來,她回說︰「他們不回來吃晚飯。」老夫婦不能等那麼久,只好回去了,明天再來。
他們剛走沒多少時候,炳發夫婦帶孩子們回來了,聽見說他們來過,很不高興。炳發老婆說他們沒多少日子前頭剛來要過錢。吃一頓飯的工夫,她不住地批評他們過日子怎樣沒算計,又禁不起騙,還要顧兩個不成器的兒子。
銀娣沒說什麼。她心事很重。劉家這門親事他們要是不答應怎麼樣?這不是鬧的事。一定要嫁,與不肯又不同。給她嫂嫂講出去,又不是好話。
一
上海那時候睡得早,尤其是城裏,還沒有裝電燈。夏夜八點鐘左右,黃昏剛澄淀下來,天上反而亮了,碧藍的天,下面房子墨黑,是沉澱物,人聲嗡嗡也跟著低了下去。
小店都上了排門,石子路上只有他一個人踉踉蹌蹌走著,逍遙自在,從街這邊穿到那邊,哼著京戲,時而夾著個「梯格隆地咚」,代表胡琴。天熱,把辮子盤在頭頂上,短衫一路敞開到底,裸露著胸脯,帶著把芭蕉扇,刮喇刮喇在衣衫下面搧著背脊。走過一家店家,板門上留著個方洞沒關上,天氣太熱,需要通風,洞裏只看見一把芭蕉扇在黃色的燈光中搖來搖去。看著頭暈,緊靠著牆走...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