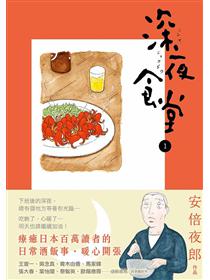這些寫於一九八八年再度遷居巴黎之後的散文,是真實歐洲歲月和人文寫照,是作者虔心的祈禱文,也是最激動深情的信仰。
絕無僅有的聲音,極致純粹的優美文字,使人感到些微痛苦,也使人上癮。
華文界最動人的散文家 陳玉慧的抒情經典
比波特萊爾更憂鬱,比莒哈絲更傳奇……
如果廿一世紀仍然存活著波西米亞,那麼她便是真正的波西米亞,沒有人像她擁有那樣的精神遊牧生活,但你也不能肯定,陳玉慧是個人類,她也有可能是個外星人,降落於此人世間;她的下筆行文如此與眾不同,她的聲音也絕無僅有,極致的純粹和美感,使人感到些微痛苦,也使人上癮。
18歲就放下一切、隻身來到巴黎的陳玉慧,將徬徨少年時的心情在散文中盡情流露,而巴黎那個繁華優雅又憂鬱之城,也形塑了她多年散文書寫的背景和氛圍;孤獨與異鄉,也一直是她創作散文最動人的主題。陳玉慧多年前便因此被贈與了一個綽號「憂鬱之母」,並被封為「憂鬱派」的始祖。
《巴黎踢踏透》便是那些年的散文結集,主要寫於一九八八年陳玉慧再度遷居巴黎以後的歲月,即使幾年後她在德國定居,告別孤單和憂鬱,重看這些心靈記錄,作家仍覺得當年能寫下這些散文真是「蒙神寵眷」。
本書以1997年出版之散文集《我的靈魂感到巨大的餓》(已絕版)內容為主體,這些憂鬱期間的紀事,作者認為有自療的成分在,可以說是作者心靈面貌的呈現。開啟了對生命的質問;並另外加入最新創作一萬多字。陳玉慧表示,「我愛寫散文,因為散文的性格繁複但又簡單,正如我的性格。外冷內熱,柔中帶剛,面貌多端?我熱衷散文文體,因為愛怎麼寫就怎麼寫,但其實,最自由的形式往往最難,我在散文創作中裡學習自由的約制。」
在此書中,敘述者不是旁人,便是靈魂本身。這是全新的文學形式,將散文、日記體與短篇小說融為一體,成為獨一無二的一種「詩性散文」。
作者簡介:
陳玉慧,華文界少見的全方位作家,精通英法德多國外語,長期旅居歐洲,被稱為「台
灣的世界之窗」。亦是少見的跨界創作人,不但是作家,還是編劇演員和導演,甚至編過舞作,也是採訪風格獨一無二的傑出新聞記者,現任《聯合報》歐洲特派員,以及多家重要德語媒體的特約撰稿人。
她不但寫暢銷小說如徵婚啟事或海神家族,也得過許多華文界重要文學大獎,散文風格獨具,曾被藝術家林懷民譽為當代華文界最動人的散文家,同時,她也編劇,寫過無數轟動一時的戲劇劇本。近年,因為作品被翻譯成德文,曾巡迴德國十多個城市以德語演講朗誦自己的作品。
她曾經是演員,多年前在西班牙巡迴演出,不但擅長編劇,且精於導演,曾在歐美及台灣導過十餘齣戲劇作品,包括改編自己的小說。今年才被美國知名大學編撰的國際女性戲劇導演一書(International Women Stage Directors),列為亞洲最重要的女導演之一。
陳玉慧重要著作包括《海神家族》、《慕尼黑白》、《我的抒情歐洲》、《遇見大師流淚》、《你是否愛過》、《書迷》等。其中長篇小說《海神家族》並榮獲2006年第一屆紅樓夢獎決審團獎,2008年台灣國家文學館長篇小說金典獎。
章節試閱
巴黎踢踏透 Paris,Tic Tac Toe!
法國現代美術名家蘇菲卡兒(Sophie Calle)和波東斯基曾經都是我的鄰居,在我看來,這二人真的太明瞭巴黎做為城市所涵蓋「大而無當」的美學和意義。
有一次波東斯基說:巴黎鐵塔大而無當,但只有巴黎才會出現這種大而無當之美。波東斯基養了一屋子貓,為了展覽奔波世界各地,經常不在家。而我第一次去找蘇菲卡兒,應徵她的室友,她看著我說,在你搬來前,我要給你看一樣東西,她帶我到客廳一角,那是一堆迷你墓碑,她說,那是我的墳墓。
巴黎正像她的象徵艾菲爾鐵塔,是一個意義之城。她不像柏林無法逃避歷史苦痛和傷痕;也不像羅馬,重重覆蓋著古代的輝煌和毀敗;她更不像挑戰時代尖端的紐約,或者敢於觸發禁忌既狂又狷的倫敦。她的渾沌或混亂(chaos)是獨一無二的,她緊張而敏感,卻極端鎮定,而且並沒有多數亞洲城市所帶有那麼一點海市蜃樓的迷惑,巴黎像沒落的男爵寡婦,巴黎像瀕臨純種的動物科。你去過巴黎周邊的郊區(Ban1ieue)嗎?巴黎的郊區破舊而醜陋,近乎絕望。巴黎郊區的存在,似乎只為了不打擾巴黎的優雅從容,以及襯托巴黎的高貴和繁華。
巴黎是詩意之城,適合路過的詩人,或者班雅明說的閒逛者(Flâneur),不適合失意落魄的人,也不適合久居。而巴黎彷彿在說,路過是性感的,是後現代的,閒逛者為類型學或結構主義提供良好註解。巴黎不是一個直截了當的城市,她不平滑(到處還有供馬車行走的石子路),永遠拐彎抹角,她比較合適當情婦,更甚於妻子。久居巴黎只會沾染寂寞和孤獨,巴黎人帶有隱居者對人的潔癖,巴黎人臉上有一種因深沈憂愁而產生的不經意之苦痛,他們以冷漠的表情掩飾著,彷彿是一種對寂寞的極端嫌惡,這種嫌惡的感染力很強,巴黎人沒有好脾氣,但巴黎人以禮貌表達他們的抗議,對人生和憂鬱的抗議。
巴黎是電影之城,一個充滿無窮想像力和希望的城市,一個發明電影的城市。一百年前,盧米埃兄弟在這個城市放映人類第一部電影,火車衝著觀眾的方向駛來,嚇跑了當時無數觀看的人。今天在巴黎,每天都有數百部電影上映,在這裏看電影像參加一種人生儀式,巴黎的電影觀眾有別世界其他城市的電影觀眾,沒有人中途進場,沒有人吃爆米花或零食,沒有人敢在放映電影途中與鄰座交談,如果有人敢這麼做,立刻會遭來大聲的「Chut」(噓)!巴黎的電影觀眾熱情、嚴肅有文化修養,對電影就像對紅酒一樣挑剔,巴黎人將電影當成古典藝術一般崇拜著,只有巴黎才會出現《電影筆記》(Les Cahiers Du Cinema)。在旅遊業仍不發達的年代,很多人從法國電影去認識巴黎,他們所了解的巴黎是虛構的巴黎,只有巴黎才符合那種虛構的美。
巴黎是觀光之城,同時也是一個販賣懷舊和時尚的城市,象徵BelleEpoque的蒙馬特,土魯斯.羅迭(Toulouse Lautre)醞釀靈感之地,伊迪絲.琵雅芙(Edith Pief)、JosephineBaker和尹夫.蒙東(YvesMontand)的歌唱舞台。散發無聊文人氣息的拉丁區,每天都有人專程坐在聖傑曼或蒙巴納斯以前老派文人喝咖啡的位子上,在香榭大道上充斥著東南亞來的採購團,採購像朝聖。巴黎是荷馬史詩《奧德賽》中的女魔,你來到巴黎,你情不自禁地受到引誘。巴黎是競技場,是馬戲團,是一個精緻絕倫的超級市場,你走進巴黎,你成為商品的一部分。觀光客不斷以驚人的暴力破壞巴黎景觀,但政客和商人也設法以金錢重建巴黎的夢幻。
巴黎是欲望之城,巴黎是一個欲望的花園,是Ville Damour,一個不耐寂寞的城市,一個猥褻和開放的城市,每個街頭角落都有尋覓愛情的人(Dragueurs)。
巴黎是個性愛神話的發源地,一個最容易邂逅的搖籃。亨利.米勒難以想像今日的巴黎,性愛販賣電腦化及數位化,你很容易在巴黎滿足肉體的空虛,誰管你的靈魂?克里希大道上到半夜都賣熱騰騰的牛角麵包,然後你可以在緊鄰的酒吧看陰陽人色情秀,無論異性戀、同性戀或女同性戀或雙性戀者甚至色情虐待狂都可以各得其所。不然是八十法朗的Pigalle,坐在爾賽宮的沙發椅上,看女人在地板上自慰。布隆尼森林裏,妓女像野生動物園事的動物,開車的人下車在樹後草地交媾,還有聖丹尼街,都是誰走過街上提公事包下班的男人,瘦小的突尼貨店老闆,高壯的水手,尾隨光著身體只披一件毛皮大衣的女人上樓。老建築瀰漫著欲望的煎熬,都是人的味道,但人的味道最臭,巴黎充滿並且聚集著欲望之氣,偶爾夾雜流露著名牌香水味,那混合氣味很難揮去,也揮之不去。
巴黎是孤獨之城,巴黎是一個憂愁的城市。巴黎提供但巴黎也索取,巴黎裝模作樣,讓人疲乏,但巴黎也令人想念,無法拋棄。巴黎是一個會讓你在婚禮中哭出來的城市,是一個會讓你和你的心理醫生吵架的城市,是一個隔絕的城市,不同的移民各自擁有自己的重鎮,他們在街上建築鄉愁,把店就蓋成他們想要的樣子,賣他們想賣的東西,他們在自己空間裡找回自己童年的夢想,他們在隔絕中建構幻想和人生。就像波特萊爾的憂鬱眼神,就像莫泊桑坐在艾菲爾鐵塔上喝咖啡,只有在巴黎鐵塔上,你才能把鐵塔忘掉,把巴黎忘掉。
但巴黎絕對令人難忘,巴黎就是巴黎,有時令人情不自禁,有時令人傷心欲絕,更有時令人欣喜若狂,血脈僨張。但很多時候,巴黎令人感到淡淡的悲哀,那是因為生活令人悲傷,而巴黎無情地向人顯示人們的各種面目及、永恆真理。
巴黎,對我而言,就是楚浮《四百擊》裡偷牛奶的少年Jean-Pierre Léaud,是我生平第一天抵達巴黎,在閣樓裡聽到音樂,那些可以讓人起舞的聲音, Paris,Tic Tac Toe!
時間之臉
新認識的朋友的狗死了,她三天沒出門並重新拾起里爾克詩集,仔細地讀著關於死亡的那一章,而突然淚流滿面,剛好有人打電話給她,她問對方:如果人死後可以去天堂,那麼一隻狗呢?
沒有人知道一隻狗死後可以去那裡。
周日中午,五腳羊街裡的巷口,一家殯儀館門前,老邁的女人問:是否有人陪她過街?這裡的確不會有車輛行駛進來,特別在周日,某位中年男士向她解釋,但她堅持著,用一種非常卑微的目光,他終於忍不住扶著她走過去,而她緊緊地抓住他的手臂,步履異常緩慢,長得像義大利人的中年男子似乎一時覺得很尷尬。
親愛的,你,我的眼光再也看不到的你,溫柔高雅的你,呼吸於一種調節於甜蜜與沉悶氣氛中的你,太多重複的旅程,但我已不再害怕了,我只是想哭,為什麼愈來愈習慣於沉默……是不是死亡的衝動也可以伴隨在對你的熱切盼望之中,噢,親愛的你。
在巴黎,一位法屬地馬廷尼克島出生的混血青年,每天用香檳宴客,穿著名的強保.高提耶的男性時裝,過著奢侈豪華的生活,有一天警察逮捕了他,原來他在三年中為了錢財,總共殺死了十七名獨身年老的婦人。他說,出門去殺死那些老婦人就像去上班一樣。
而姓都彭的矮小婦女,雙腳彎曲,行動不便,她必須一個人去離家八百公尺的超級市場購物,她買了通心粉、奶油、植物油、番茄汁、麵包、栗子果醬、草莓果醬、衛生紙、衛生紙和衛生紙,一位年輕的中國女孩要幫她提到家,她不停地說謝謝,謝謝,高興地說不出別的話。
她有個遠房親戚在紐倫堡,一個經過二次世界大戰的女人,總是憂心忡忡地在貯藏食物,已經那麼久沒有戰爭了,她仍然在地窖裡準備了十二斤的麵粉七斤的糖和麥片,她還怕不夠,由於過度憂慮,上個月她自殺了。
另外一名高大的金髮女人大約五十歲,她老是坐在地下鐵走道出口,浮腫的臉浮腫的腿,她向人們說早安,「早安,您有一、兩塊法郎可以給我嗎?」有時候心情好,她就地打起一團灰黑的毛線,有時候心情不好,心情不好她的臉就更浮腫了,一個長得和她有點像的男人,穿得跟她一樣髒的衣服,講一樣髒的話,充滿酒味地站在她旁邊。
有一對情侶走在法國南部大城的街上,停了下來,其中一個說:「我愛你。」說完這句話他們彼此噗哧大笑,又繼續往前走了。
在希臘旅行時,她夢到她父親寫信說他很孤單。她想起數年前父親曾說過幾年後要去養老院度其餘生,父親大人,她悲傷地提起筆:好久沒有您的消息,最近好嗎?
聖經裡並不曾記載關於狗的事,關於狗是否能得永生,她一直找不到答案,而她又領養了一隻新的小狗,給牠取名Joy。
你不覺得這個女人很貪心嗎?你看她的男人,男人的頭髮。他們在露天咖啡座上喝同一杯綠色的薄荷酒,幾乎忘了在旁的嬰兒車裡有一張哭喪臉孔的小孩。
美國威斯康辛州這幾個月有龍捲風,幾個農莊都被整屋捲走了,大難餘生的約翰生夫婦對著電視台的訪問,穿得像個中學生的孕婦,毫無表情地敘述著災害,好像在背誦課本上記載的課文。
台北信義路的銀翼餐廳,二個老人為了爭先付帳,面紅耳赤地大吵了一頓,幾乎要打了起來,他們不知道在個人主義盛行的歐洲沒有人會為付帳而吵架,而一位歐洲人卻為老人的行為深受感動。
看日本人演的新歌劇時,老劇場裡的嶄新紅色座椅上,年老的女士故意和一位穿著艷麗的年輕女士起爭執,根據某一種心理學分析,這也許是害怕死亡的潛能反應。
一個女人這樣形容她愛的人:他有一組電腦和二隻鸚鵡,他會唱聲樂家才會唱的那些歌和做很好喝的湯,每天喝二至三瓶的啤酒,看三個小時以上的電視,周末一定去拜訪他的父母,他有時在家不接電話或不開門。
住在慕尼黑的他開始經營廣告生意,他有個女人姓吻,Kiss,那女人有兩個叫他叔叔的小孩。你知道如何成為一名成功的實業家嗎?他說,首先你必得問自己:如果我將在六個月內死去,我會做什麼?當你知道你一定會做什麼之後,就全力去做它,假設自己還有六個月好活。再來,你必得告訴自己:無論如何工作,我就是不會疲倦,因為我就是不會疲倦。他說這就是成功的方法,他把新成立的公司叫Kiss,到目前為止還沒賺到錢。
這個住在台灣的女人宗教信仰愈來愈虔誠了,她喃喃地唸著神的名字,一心行善,遠離惡事,不再參加無益的茶會活動,潛心研究神的言語,尋求神的力量……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和死去的狗做靈魂的溝通呢?在連續幾次夢見她的狗回來找她後,她傷心地問了許多人,可能可以去找一個懂得做靈魂溝通的人?她認真地思考著,就算有人可以替她和狗做靈魂對話,然而已經漸漸忘卻牠的吠叫聲的她,如何分辨她的狗的意思呢……
你到底愛我嗎?風什麼時候又會吹起呢?海浪什麼時候停止呢?如果有一天我發現我不再愛你了呢?天空為什麼那麼藍?白雲為什麼那麼白呢?如果你不愛我,如果你不愛我,我當然愛你,如果我愛你,請你小心一點。
在史坦堡有一個湖,湖上有一個小小的島,從前,有個公主住在那裡,整個小島栽滿了玫瑰花,史坦堡的王子愛上了玫瑰公主,他常常搭船去赴約會,據說他們非常相愛,有一天王子突然死於湖中,大家都很震驚,沒有人知道死因為何,當天,當玫瑰公主知道這個消息的同時,她也自殺了……這是一個從前的故事,很久很久的從前,在西德的史坦堡湖。
也許她會愛她新的小狗,Joy,她願意愛喬依,這是時間的問題,她會愛牠,
為了紀念那隻逝世的狗,她還在讀里爾克:死亡是存在我們每個人心裡的一粒果實。
我不知道為什麼愛你們
總是夢見戲馬上要上演了,我是那齣戲的導演,卻坐在塞車中的計程車裡,無法前進,所有的車子裡也都沒有司機,或者是找不到劇場的所在,不停地在陌生的街巷裡跑,繞來繞去,就是找不到,或者自己是隱形人,我不斷地發話,但沒有人注意到我。
做夢的時候我在黑暗的控制室裡,我一直躺在地板上,半個小時,身上蓋著道具用的棉被,而我仍然哆嗦著。重物在地板上移動的聲音持續不斷,我知道是搬運工運來的佈景已上了舞台,我知道,樓下的排練室裡,一些演員正在練習鋼琴曲和歌唱,聽過無數次無數次的歌,我知道,我都知道,但是我想逃避,想走。
戲還有三天就要上演。
上帝是孤獨的,所以祂創造了世界。祂是藝術家。
演員甲生平第一次演戲,戰戰兢兢,常常流汗,已經一個禮拜必須服用鎮靜劑才能入眠。
演員乙突然失去聲音,他一直深信自己就是飾演的那個角色,但他現在只面對鏡子發呆,為什麼,為什麼,語言真的是誤會的泉源?
演員丙昨天下午告訴我,他的孿生兄弟去世了,是不是可以退出演出,目前他心中的念頭無非也想去死。
當然,跑龍套的角色還缺一名,很多人的戲服做得太緊,佈景裝台已經延誤了二天,舞台監督非常擔心演員連走位都沒有時間,燈光設計也在抱怨他的燈具不夠,走貓道非常危險。
戲還有二天就要上演。
你知道嗎?一個女演員失蹤了,怎麼樣也找不到她,還有音效師發現拷貝的帶子上突然出現一段空白,小道具抗議工資不公不幹了。
我坐在第八排第七號,你聽得到我嗎?觀眾席上只有我,常常在黑暗中,舞台上的燈光吸引我,我在創造舞台上的世界。
那個角色,對,那個角色,他走進來了,穿錯鞋子並且忘了關門,我請他重來一次,但他仍然忘了關門。
你的聲音必須更迫切堅持,像一個面臨棄城軍隊的將軍,而你的態度不夠明確,手勢過於曖昧,請聽我說,他真的是個詩人,熱血澎湃的詩人。讓我們重新開始,從上一個Cue……
他為什麼忘了上場?請到後台叫他,演員丁因為小睡片刻,以至於忘了上台,你知道嗎?
他每天坐夜車往返南北,因為除了演戲,他還接了一檔工地秀。
燈光三秒請準備,音樂Fade in請準備,如果我能將第三場的戲重排一次
,如果我能將第三場的戲重排一次,道具組做的大道具太重了,誰搬得動?也許,一切都已太遲?
戲還有一天就要上演。
我總覺得演員戊的衣服顏色實在太淡了,但是服裝設計師說他沒有預算,況且昨天已有過爭執。
也許應該取消記者的訪談,時間不多了,而他們總是問一樣的問題,為什麼要導這齣戲?我會說因為我喜歡,然後他們會再問我為什麼選這個劇本,不過,沒有人會問我為什麼吃白菜、青菜或空心菜。
演員己失戀了。今天早上才去墮了胎,中午便趕來彩排,她傷心地連手都在發抖,剛才,剛才我在走廊上看見她在哭,化完妝的臉掛著兩行黑淚。
怎麼去愛?
戲還有一個小時就要上演。
從小立志當演員的庚感冒了,而他必須穿無袖汗衫,躺在一具棺材的道具中大半場戲。
請放輕鬆,請安靜,請找個角落安靜一下,導演我祖母要來可不可以給我一張票,導演有一個許小姐要找你,請看著我,你必須提醒你自己,這世界上只有你才能演好你的角色,無論你是什麼角色。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來這裡?為什麼我愛你們?也許只是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
這是台詞,親愛的觀眾,戲已經開始演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愛你們,曲終人散的時候,道具和佈景都要搬離、銷毀,燈光再也不會以同樣方式亮著,戲服會開始發霉,所有的問題消失,在那個時候,在那個時候,請相信我,我總是突然又老了幾歲,我總是突然又覺得……孤獨。
巴黎踢踏透 Paris,Tic Tac Toe!
法國現代美術名家蘇菲卡兒(Sophie Calle)和波東斯基曾經都是我的鄰居,在我看來,這二人真的太明瞭巴黎做為城市所涵蓋「大而無當」的美學和意義。
有一次波東斯基說:巴黎鐵塔大而無當,但只有巴黎才會出現這種大而無當之美。波東斯基養了一屋子貓,為了展覽奔波世界各地,經常不在家。而我第一次去找蘇菲卡兒,應徵她的室友,她看著我說,在你搬來前,我要給你看一樣東西,她帶我到客廳一角,那是一堆迷你墓碑,她說,那是我的墳墓。
巴黎正像她的象徵艾菲爾鐵塔,是一個意義之城。她不像柏林無法逃避...
作者序
跋
靈魂的敘述者 ◎Michael Cornelius
德國今年冬天非常冷,街上沒有一個人,我在想一個問題:靈魂有溫度嗎?靈魂是不是溫暖,當幸福來的時候?靈魂會不會發燒,當愛情降臨的時候?或者靈魂感到寒涼,當一切轉為疑問的時候?
法國作家瑪格麗特.莒哈絲死的那天,我坐在飛機上望著大西洋,機艙上的液晶顯示板顯示氣溫零下六十三度,目下所及的機身四周圍繞著白沙漠般的雲。我翻閱著一本雜誌,其中Francis Giacobetti所拍攝的一組照片深深地吸引著我,那是一組以特殊攝影機拍攝出來的照片,拍攝的是一群世界知名人士的眼睛和手,而眼睛只有瞳孔的部分,放大的瞳孔。
達賴喇嘛的瞳孔看著我,無與倫比的瞳孔,帶著一種桔色,幾乎像土星表面的顏色,而土星正是憂鬱的星球。眼睛是我們身體中唯一具有顏色的部分,眼睛是發光的內在生活,是我們靈魂的「指紋」。
「我描寫愛情,是的,愛情,但並不是溫柔。」莒哈絲說,她的眼睛我從來沒看過,「我不喜歡溫柔的人,我自己便非常粗魯,當我愛一個人的時候,我便對這個人有著激情和渴望,但是溫柔卻排除了激情和渴望。」莒哈絲的心很孤獨,她的文學作品純粹,是從苦苦憂鬱中提煉出來的純粹,「過度的表演不會帶給內文任何具體的東西,相反地,它減少了直接和不可分離的深度,削弱內文的肌和血。」
我必須再度想到靈魂:「我的靈魂感到巨大的餓」,陳玉慧這麼寫。靈魂吞噬一切,一切這世界所能提供的,然而還不夠,靈魂永遠還是感到飢餓,太多是難以消化的,對靈魂來說,過於平淡、或者殘酷,甚至不足。「我看著這個世界,就用我被強暴時的那雙眼睛。」你可以時時刻刻在陳玉慧的下筆行文中感受,她在書中所發出的聲音是一種絕無僅有的聲音,非常的純粹和美感,使人感到些微痛苦,也使人上癮,想不斷地再聽下去、再讀下去。在這憂鬱的汪洋大海中,靈魂並不訴苦也不自憐,有時甚至帶著強烈的幽默和自嘲,那種幽默似乎只能從一個看過死亡的眼睛中所流露出來,是一種明白世界是何種重量的自嘲。這是陳玉慧的文字,像是皮膚上的紋身,無可更改,像梵谷畫裡的色彩,梵谷花了整整一個月才調出來的黃色。
「我看著這個世界,就用我被強暴時的那雙眼睛。」任何人如果這麼寫作,絕不會有興趣去花時間雕琢文字、或者尋找謎般的譬喻——目前所謂現代文學所盛行,並如流行病般所四處感染的寫作風格。而陳玉慧的散文具有銳刀般的透徹,沒有一個字多餘。
這本書中有幾篇散文讓我感到害怕,這種純粹的寫作方式和思維讓我感到害怕。陳玉慧的句子像布紐爾電影中切割眼睛的鏡頭,文辭如硫酸般地觸及知覺,思維像向下挖掘般地進入記憶。這種害怕沉默無聲,但是回音如此嘹亮地迴繞著我們的靈魂。如果你以作者的眼睛去看這個世界,則一切彷彿你第一次看到彩色,而過去的世界全都是黑白。那麼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怎麼還能從謊言假象、虛偽的愛、愚昧遲鈍中存活下來,而且還能不發瘋?這害怕是一種突然的認知,好像在感情世界中,我們一向如死者般行經這個世界,如果我們像作者這麼誠實,去面對所有生命必須面對的問題,那麼我們只會得到一個愚笨的答案:「我不
知道」,怎麼去愛?為什麼活著?親愛的讀者,我相信,我們的靈魂缺乏勇氣去回答它。
什麼是我們生活的本質?我們在生命中留下午麼痕跡?什麼是我們的自我?指紋嗎?還是我們發出來的聲音嗎?我們的氣味?我們的夢?我們的靈魂又留下午麼?靈魂,這個看不到也難以解釋的什麼,我們以為便是的自我之家。理想的境界可能是在別人的靈魂留下痕跡,這便是愛。或者轉化入一個新的生命,這便是轉世。以上便是《我》書的內容,在書中靈魂便是敘述者,這敘述者「靈魂」脫離出作者的自身存在,並能自由自在地超越時間、地點去敘述事件,「靈魂」能潛入讀者的意識之泉,而同時,也能脫離肉體,客觀地觀察外界。這是全新的文學形式,融入散文、日記體、短篇小說所成為的一種「詩性散文」。
〈時間之臉〉可能是我所知道最現代的一篇,許多珍貴的真實碎片,被編排成一個collage,寫作對作者而言,變成影像的剪接,剪接所有由意識流出並與靈魂聯繫的影像,剪接成一種具有旋律的文學形式,而其中只留下一條如希臘神話中的「紅線」,一個叫阿提安的女人,她為了能夠離開迷宮,一邊前進一邊留下紅線。在〈時間之臉〉中,貫穿全文的紅線是孤獨和質疑,這位「靈魂敘述者」在看似毫不相關的時空短景中,傳達的不祇是悲喜交集的荒謬時刻,還有無窮的詩意。文章中總是不時冒出一個女人,她的狗才剛死去,她問一隻狗死後能去天堂嗎?狗也有靈魂嗎?女人讀著里爾克的詩,關於死亡的詩篇。在文章結束前,女人說,就算有人可以為她和逝去的狗做靈魂溝通,她仍不確定她能在溝通中明瞭狗的意思,因為逐漸地,她已遺忘了狗的吠叫聲。「死亡是存在我們每個人心裡的一粒果實」,里爾克的詩成為〈時間之臉〉的結束語。
〈時間之臉〉有一張驚人的悲傷面孔,這世上沒有任何值得期待的了,唯一剩下的是因平凡生命存在而產生的悲傷及苦楚。如果說作者的創作帶有強烈「失根」的風格,乃是與她過去長年變遷的生活有關,這種說法則過於簡單,不過誰又能想像多年來作者的戲劇導演、作家及駐外特派員的生涯?住過紐約、巴黎、慕尼黑及台北等不同的城市?這本書不祇是作者近十年生活的記錄,不祇是一個個人的剪影,也是現代台灣人孤獨處境的呈現。文中傳達的孤獨、無家以及無條件的憂鬱感,存在世界各個角落,流亡或流浪是一種精神狀態,你不一定必須在國外生活才能感受到孤獨或無家,你很可能在自己的土地上便覺得活得像異鄉人。
誰能肯定陳玉慧是一個真正的人類,她也有可能是一個外星人,以一種非常奇特的觀看方式以及非常大的愛來描述著這時代中的荒涼。作者來到這個我們活著的世界,發現了一個不為人知的地球,寫作是她尋求聯繫時所向外界不斷發出的訊息,也成為我們前往這失落之地的導引。
「在記憶中我似乎已有一千年那麼老」,波特萊爾在《惡之華》中的〈Spleen〉
那一首中這麼寫著,這些黑色的詩選是獻給人類一千年以來的憂鬱狀態,而一千年以來,幾乎所有西方最重要的精神導師如亞里斯多德、莎士比亞、莫札特等無以計數的人,都深深身處過憂鬱之境,也就是說,若沒有經過那黑色的憂鬱狀態,也許人類至今的許許多多偉大作品便無法完成。「一個悲哀的日子可以像一百年那麼長,如果在人世間果真有地獄的話,那便是人心裡的憂鬱之苦。」四百年前伯頓在他的《憂鬱的解剖》中這麼說,憂鬱有許多名字,如悲傷、煩悶、厭倦、厭世等,有許多德文名字甚至無法翻譯成中文(weltekel、schwermut、weltschmerz,或者像法文的tristesse),有人說,憂鬱是一種令人感到悲傷的幸福,這種幸福可以像美國早逝的詩人濟慈在他的大理石墓誌銘上所說的,「在這裡安息的人,他的名字寫在水上。」當他死於一八二一年時,才二十五歲。
〈我不知道為什麼愛你們〉也是一篇極美的小品,這篇散文是作者在台北國家劇院導演後寫的手記,精鍊簡潔而充滿詩意,描繪導演在首演前的內心世界及舞台後不為人知的「戲劇人生」。一位接工地秀而必須南北奔波的演員,因為過於疲累而小睡片刻,以至於忘了上場;剛剛墮過胎的女演員,中午便趕來彩排,她在排戲時,連手都在傷心地發抖;燈光道具都不符合要求,戲服也做得太緊,然而戲便要開始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來這裡?為什麼我愛你們?也許只是為了證明我的存在?」這段台詞可能是作者悲哀的人生質疑,但是她同時也有幽默的指陳,「上帝是孤獨的,所以祂創造了世界,祂是藝術家。」
受折磨的世界靈魂如果有什麼話語,這本書便是世界之魂的語言。這語言具有神奇的魔力,令人想聽下去,那甜美的憂鬱之聲,噢,我但願擁有一副鰭,讓我能游進那悲傷之海,我的靈魂也感到巨大的餓。
(本序文作者為德國人,作家,現任雜誌編輯,也是本書作者的丈夫。)
跋
靈魂的敘述者 ◎Michael Cornelius
德國今年冬天非常冷,街上沒有一個人,我在想一個問題:靈魂有溫度嗎?靈魂是不是溫暖,當幸福來的時候?靈魂會不會發燒,當愛情降臨的時候?或者靈魂感到寒涼,當一切轉為疑問的時候?
法國作家瑪格麗特.莒哈絲死的那天,我坐在飛機上望著大西洋,機艙上的液晶顯示板顯示氣溫零下六十三度,目下所及的機身四周圍繞著白沙漠般的雲。我翻閱著一本雜誌,其中Francis Giacobetti所拍攝的一組照片深深地吸引著...
目錄
目次
【序文】靈魂的敘述者/Michael Cornelius
輯A
重返記憶莊園
尼采,你看到了嗎
夢想
要去不來梅的女人
情感的名字
藍光
問神
因為記憶
德文字
給W的一封信
輯B
親愛的你
時間之臉
蜘蛛網
有人在山上喚著你的名字
巧克力
看戲那邊晚上0℃
一條路已從這世界消失
現在是白天還是晚上
飛蛇
毛小姐和她的朋友
旋轉木馬
永遠
低頭走過那條路
背叛海的沙灘
輯C
我的靈魂感到巨大的餓
台北蒙太奇
夏天的愛與恨
七○年代的愛情生活
我不知道為什麼愛你們
成家
我的男人上輩子是我的妾
心的旅行
【自跋】我愛寫散文
目次
【序文】靈魂的敘述者/Michael Cornelius
輯A
重返記憶莊園
尼采,你看到了嗎
夢想
要去不來梅的女人
情感的名字
藍光
問神
因為記憶
德文字
給W的一封信
輯B
親愛的你
時間之臉
蜘蛛網
有人在山上喚著你的名字
巧克力
看戲那邊晚上0℃
一條路已從這世界消失
現在是白天還是晚上
飛蛇
毛小姐和她的朋友
旋轉木馬
永遠
低頭走過那條路
背叛海的沙灘
輯C
我的靈魂感到巨大的餓
台北蒙太奇
夏天的愛...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5收藏
15收藏

 8二手徵求有驚喜
8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