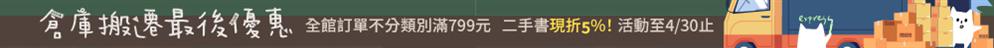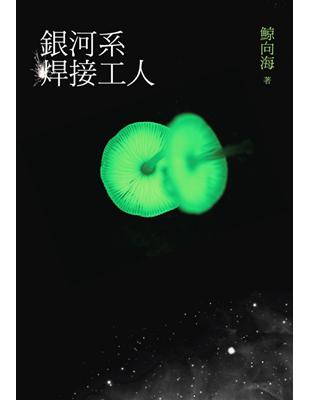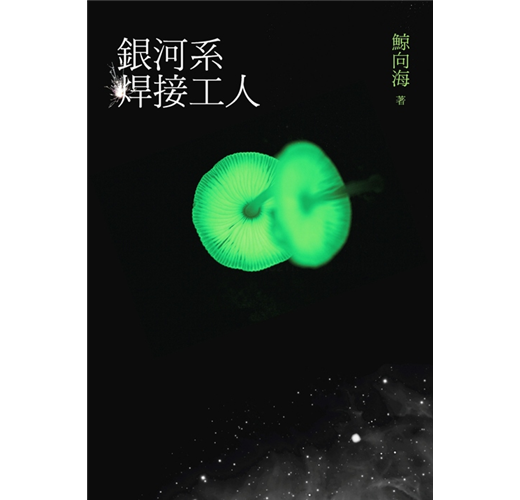序
銀河系焊接工人
無聊(長出犄角)
我跟我的朋友都是很無聊的人,我們都希望追求日常生活裡的靈光。
(假日早晨吧,常常還躺在睡夢中,夢裡仍是一些不可告人的鏡頭。三島由紀夫說:「大部分的作家都是頭腦十分平凡,但表現像個野人;我則是表現得正常,但內心卻是變態的。」從窗口往下望,那蜿蜒的街道,火炬燃盡的路燈,在在都讓我彷彿看見芥川龍之介所寫〈地獄變〉的森然景象,潑墨的黑煙與金粉的火星在我內心深處驚人地蔓延。)
文學的動機或者是源自於無聊(所謂化腐朽為神奇,意思就是你要先腐朽才行)。因為只有當你能夠發呆空想,才有辦法發現一些有趣的事情。寫作是原本眼看一望無際的無聊與膚淺,然而只要在任何一處靜心往下挖掘,就可以抵達深刻,往往就這樣意外擴張了的那種深情。
(常有傳聞〔也有人提出反對的統計數據〕,醫生的自殺率比一般人口來的高,又說精神科醫師正是自殺率最高的醫師之一。一個已經變成病人的醫生,還能夠替人看病嗎?我想是可以的,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優良醫生,即使等一下自己就要去跳樓了,還是被期勉應先診治好因想跳樓而被送來急診的病人──這就是「醫生」這門行業的瘋狂之處吧。)
雖然我的朋友安慰我說:「你真是不可思議,你如果是無聊,我們真的是無恥了。」我的戀人卻淡淡表示:「特別寫文章強調自己的無聊,本身就是一件無聊的事情。」
(沒有什麼特別需要的時候,我也曾像大多數人一般慷慨,輕閉雙眼默默祝禱「世界和平」──這垃圾一般的願望,多麼善良正義啊,適用於任何時刻,且鐵定永遠不會實現,可不斷回收利用。)
每次讀童話故事都覺得永久不衰的幸福確鑿是很無聊的。文明核爆的時代,無聊是無所不在的災難,像是輻射塵一樣飄散。然而在面對真正的災難時,便會懷念起過往的無聊日子是多麼幸福。
即使是身為最無聊的人,「我何嘗不想親吻潮浪,不想被鍛鍊成金剛/最後我只選擇了吃西瓜/偶爾也羞悔這些喪志的事……」我仍試著寫出有趣的作品,用一種遵循自我品味的方式,希冀大家在無聊時,會想到我寫的東西。最好能夠翻轉「無聊」本身的意義,使無聊失去了無聊的感覺。最後最後,當你聽到別人談論說:「鯨向海的散文真無聊……」你將不再能輕淺判斷那是什麼意思,因為無聊已經長出犄角。
(掩面)祕密交往
由於生性害羞,卻熱愛與其他的孤獨交通,所以我經常處在一種掩面的狀態,與人祕密交往。
曾有一位同為創作者的讀者特地向我聲明:「我是絕對不會坐在馬桶上讀你的詩集的!」藉此對我表達敬意。其實我並不介意耶,我想如果我的作品也具備健胃整腸的功能,可以幫助別人順利解便的話,也是功德一件。我跟他約定,下次如果輪到他出書,務必為我寫下警語:「請勿在大便時閱讀。」我就能學會尊重他的書了,但性格優雅的他激烈反對在自己書上寫下這種字句。於是我暗暗決定,下次如果我再有新書出版,我一定要在扉頁簽字感念他:「先謝謝你,我的朋友,我知道你不會,但我特許你在上大號時讀此書。」
此外,還曾有另一位讀者拿著《大雄》找我簽名,對我心疼訴說他帶著這本詩集去環島旅行,途中被雨淋濕了的驚險過程。書翻開來果然看到雨漬,一時內心也是感動的(當時便想,就算你不小心沾到的是其他的液體,也感謝你的愛用……)
就是這樣充滿祕密的念頭,使我生性害羞。
又像是有時看著窗外突然想起楊佳嫻的詩:「烏鴉提煉的陰天啊/侵蝕我們的頭冠」……彷彿回答了幾百年前另外一個女詩人的疑問:「獨自怎生得黑?」雖然我想單純沒有注意美白也會有這種效應,楊佳嫻卻對此意境有獨到領悟曾再三激動詮釋:「我怎麼自己一個人生得這麼黑?」「我是怎麼搞得自己一個人什麼都沒做卻弄到這麼黑?」「怎麼我自己一個人卻從整個世界黑掉了?」
好吧,所以大家終於明白為何需要掩面了,因為真面目往往非常不堪。然而,真正的感情就是你可以在對方面前盡情顯露你真正的不堪並且毫不覺得不堪,不是嗎?
對收藏舊書的人來說,稀有的舊書宛如稀有的礦石魔物,使擁有者獲得與眾不同的力量,這可說是一種證明獨特性的方式。因此,文學書籍雖然在新書市場上滯銷,卻在舊書市場遭人巧取豪奪。這固然是不少作者的傷心處,自己的傑作,廣大的讀者再也無緣讀到,只能成為夢幻逸品。不過因為我自己也頗熱愛收藏舊書,所以當我知道上一本不堪(?)的散文集《沿海岸線徵友》不幸絕版了,反而有種興奮感覺(有自虐的嫌疑)。此外,為了裝熟,強要與人併桌,我還硬把其中某幾篇散文偷渡到這第二本來,當作與讀者相認的暗號……(但這樣到底神祕在哪裡呢?)
一位編輯朋友曾說:「我早就不期待作家本人會和他的文字一致了,這樣才能夠去承受那必然的落差。」和我交往過的人也早就發現,沒有人可以永遠保持神思飛馳的狀態,當我越是遠離了美好的靈感,降落在其床上,坐在他們的對面時,越是不堪一擊。還好他們總是包容了我粗魯的吃相與睡姿,我不寫詩時的脆弱。
很多時候只能這樣,明明人生有那麼多沉默厚實的鼓面,都等待我們去敲打出聲;我們不想平心而論我們捶胸吶喊著為何我要平心而論我的心事如此激烈突出!事實是,我們都選擇了繼續遮掩自己的祕密。
歌德說:「是詩來做我的,不是我去做詩的。」我想有時候那不僅是「詩」,也可以是「愛」(羞)……總有某些烤箱因動了真感情而焚燒整座房屋,人生總是始料未及的。
不管是用愛還是用詩來祕密交往,出現在人家夢裡我總是感到很害羞,謝謝你們保證我的純潔。
夢和情詩和對不起
到了最後,我們發現夢和情詩,是騙人的,重點是對不起。
卡夫卡說的嗎?寫作的甜蜜是源自於我們替魔鬼勞動的報償。或許真是這樣,寫作才總是令人充滿愧疚之意──有時是藝術的缺憾使我們感受到整個世界的完整,有時卻是世界的缺憾使我們感動於藝術的完整(攤手)。
看到我家的貓正悠閒地躺在客廳的沙發上,毛茸茸的一團,十分溫煦的樣子。突然想到,以牠波斯品種聞名的皮毛,也許會讓人忍不住產生想要圍在脖子上炫耀的慾望吧,比之那些同樣因為擁有漂亮的獸毛而被豢養在人工飼料廠等待時機成熟就被莫名殺掉的貂浣熊狐狸獺兔等等動物們,牠能夠這樣隨意躺下展示自己的皮毛,應該是很幸福的啊。我當然不會讓牠看到我從網路下載的,關於我的同類們,大舉殺害牠的同類們,以換取時尚虛榮的影片(牠幸福得不需要了解自己這樣居然是幸福的)。還記得電視上一個愛好皮草的貴婦,面對記者訪問的鏡頭時,曾理直氣壯地說:「美麗的事物是不可以被禁止的!」這種悲慘由我自己承受就可以了。
還好在這本散文集裡的夢與情詩,都不需要犧牲任何動物的生命為代價(是的,我家的阿肥仍然好端端地熟睡著),真要說有什麼因此犧牲了,大概也只有我自己的生命而已(因為是一本花了好幾年才寫完的散文哪。)
如果你決意翻開來看,夢肯定是有的(剛好開頭就是一系幻覺的行列),情詩也是有的(到處都是詩的變形,愛的偷渡),至於對不起是怎麼回事呢?絕對不是不喜歡我的散文的人我在這邊向你們道歉(不喜歡就滾開!),而是裡面如果有被我諷刺乃至於得罪的人,請接受我的一拜,呃──我有時對不起詩,有時對不起醫學,對不起我自己,許多散文寫來寫去都是隱隱在表達這些不能表達的愧疚之意(淚濕了,去拿拖把)。
當上一本散文絕版時才姍姍來遲出版了這一本,對不起,我是一個被動的寫作者。常有種錯覺是,在空洞無夢的現實世界裡,彷彿只要抱擁著電腦,啟動網路連線,便無所不能,擁有了一切。無論遠行何方就算淪落地獄,需索什麼似乎都可以從自己的手指底下傾洩而出,用游標滑移散步建構而成。這種完美的幸福正是我們應恐懼的──它們太容易被破壞了,一個不知哪裡轉寄來的病毒或一點點不明白的物理障礙,居然便輕易地失去了美好感動的所有;恍若空中樓閣,天使一瞬斷翅墜毀人間。
謝謝出版社主動接洽,否則這些散文大概也就是這樣默默在網路上變成荒煙蔓草,毀壞於時代的大硬碟之中吧。
我的散文並沒有註明時序年份(約莫都是上一本散文集之後所寫),頗有時空錯亂之感,卻也盼望因此有超越時空的可能。我的書寫一向有許多奇怪的堅持與怪僻(星座論述者會自動連結到我的處女星座上,不過聽說星座也已經位移了),在此預先說幾聲對不起(顯示為不C而且有禮貌),識者或許此刻將鍵結到我的詩句:
所謂夢和情詩和對不起
都是易碎品
沿海岸線徵友,每一個細節都是鯨魚
我喜歡回到家之後把鑰匙插入鎖孔的感覺,喜歡醫師服鈕釦解開的感覺,喜歡弄鬆皮帶褲子脫下來的感覺,喜歡把襪子除去的感覺,喜歡坐下來登入電腦的感覺,喜歡好多事情可以做又什麼都不急著做的感覺,喜歡現在的感覺……
●
今日搭捷運,又是上下班的顛峰時刻,被人潮排擠在車廂之外,逼逼聲已經響到了不耐煩,我繼續努力縮小身軀,想混入車廂之中……最後門無情地關上了,車還是開走了。有些事情真的勉強不得,或許猜錯車廂,或許排錯隊伍,或許身旁的人比你更勇猛善戰;車門關上瞬間,那些擠上車的人看著我的同情眼神再悲天憫人也沒用。垂頭喪氣之時,突然,又來了一班加班車,瞬間雲淡風清,空盪盪的車廂(原來這才是我的車啊)我隨興挑了個角落的位置坐下,蹺腳,悠閒地拿出背包裡的書,開始讀詩。
●
看診時,遇到一個有感情困擾的男孩跟我說:「上大學那年,我充滿願景地,要交一個最漂亮的女朋友;半年之後,卻交到一個男朋友……」這樣的開場固然不尋常,然而深究下去,無論同性或異性戀,所要面臨的考驗都是類似的。
●
媽媽說我小時候(大概五歲)有次和爸爸在公園鬼混,因為長太可愛了(?),被某星探發掘。對方建議我可以到電影或電視公司去試鏡,演一部類似「我的爸爸是礦工」之類的片(真的有這部嗎)。我果然去了,去了一次,在期待的眾人面前發呆嚇傻……後來就沒有再繼續下去。要是當初真的去演,我可能也是小鯨鯨或者小小鯨之流吧(遠目)。
●
電影《花樣年華》裡,蘇麗珍告訴周慕雲:「我們不會和他們一樣的。」誰是我們?誰是他們?有位天才善感的詩人朋友告訴我,他寧可跟那些人一樣,就不用如此痛苦了。
●
冬盡的午後,凋殘的荷梗宛如無數戰戟肅穆地捍衛著最後的池塘。意外在植物園的野薔薇豎牌上讀到杜牧的詩:,「菱透浮萍綠錦池/夏鶯千囀弄薔薇/盡日無人看微雨/鴛鴦相對浴紅衣」……內心突然春光乍洩,變得好溫柔。
●
到某日本料理店去吃飯,離開時進入冥想狀態,居然忘了付帳……後來,還是特地走了回去。到了店裡,有點慚愧地說:「抱歉我剛剛吃完飯沒有付錢。」店員淡然:「喔,對耶,你沒付,那一共是……」然後我又默默離開了那家店,臨走前看了一眼玻璃門上的自己的形象……額角的夜空也沒多閃爍一顆星,人當然也沒有變帥。
●
友人忽然很感慨地說:「其實我想到你都不是無聊的時候而是悲哀的時候。」我想我一定有一張很靠悲的臉。
●
醫院附近有一公園,光天化日下少年們常結集在其附屬的籃球場耍帥。直到黃昏衰退,星光湧現,人群都散去了,宛如廢墟,卻成為我一人的操場;在此地噴汗跑步,偶爾大聲吼叫──如果病人看到我變身為獸的模樣,想必可以恍然我如何在黑暗之中慢慢聚集了能量,白晝才能自在地出入他們的瘋狂境界吧。
●
真正的戀人不會覺得對方很無聊或擔心自己讓對方覺得很無聊,真正的戀人會覺得真的好無聊喔但還好我們在一起使得一切都有了樂趣。
●
散文就這樣透露了我的生活細碎,如琥珀如果醬封存了我的時間,而精神分析的觀點來說,為什麼我選擇描繪這些片段而不是其他的那些,其實每一個細節都宛如鯨魚般不可輕忽(真的嗎?)
銀河系焊接工人
我雖習醫,卻屬於靈感的勞動階級。
我閱讀速度不快,觀賞電影的習性也頗零碎(因此很少去電影院遵從導演的意志乖乖看完一部電影,反而嗜好自己在家操控光碟機調度好幾部電影的畫面次序)。往往隨性翻開小說與散文集,各自讀不到其中一兩頁就忽然開始寫起詩來;經常看著武俠片頂多二十分鐘就換成冷門的歐洲電影,過三十分鐘又改播放百老匯歌舞秀。更常見的狀況是,一邊使用msn一邊瀏覽臉書,google、youtube、BBS三者視窗同時開啟。是的,因為偏愛享受繁複紛呈的多元局部並置,我很忙。
我告訴我的朋友我這樣的癖好,他們對於我不求完整的破碎流離生活感到很好奇,因為幾乎每個人都習慣一次看完一部小說或一部電影的,他們問我:你不知道結局不會一顆心懸在那裡嗎?
後來我知道了,我注重的一向更是氛圍與意境,瞬間蒙太奇的飛躍,帶來新異的存在感與自由思索的動力。我不介意是否獲取了「完整的知識」因而比昨日之我更「進步」了,生活並不需要特意等待一部電影劇終才能延續,生命也不用靠讀盡一本小說才能演化,經常一首詩的一小節便耗去我好幾個小時的流連游移,msn的一行話語臉書一則莫名塗鴉可以帶給我持久的感觸。
我喜歡閒散的巧合,人生本不是計畫性的,某些刻意追求「完整結局」的小說或電影,嚴格來說都是缺乏詩意的(對我來說),美好的作品不妨偶然一些曖昧一點──維根斯坦不也認為,概念之不精確不完整,非但不是一種缺陷,反而恰恰是一種美德?所有的書(電影),其實都是人生這部書(電影)的片段罷了。我們怎麼可能真正知道了結局?
此時代太多選擇了,太多支離破碎的無數資訊卻不學無術。再偉大的事情也都變得枝微末節。這樣的泡沫氣氛卻反而有助於想像力的重新連署布局,造成一種此斷代特有的寫作狀態。很多時候我都覺得自己像是一個焊接工人,從事著純情的文字勞作(不是純愛系或草食系喔),把一些別人眼中的爛事壞感無聊的東西寫在一起成為優雅的或者頑皮的紀念,把夢和情詩和對不起等等易碎品用文字膠著起來,是我的理想境界。把一些不思議的事物團聚在一起,而不讓他們知道彼此,卻掩面祕密交往,是我寫作的樂趣。
寫作是神性的勞動,那些思想的煙火,在半空中辛勤鍊字,照亮最底層,不可見人之事。詩是幽靈之間的擁抱,浮動而曖昧。散文則是靈光狂想的焊接,固著意義,顯示清出的座標。
使一些遠方近處,微微泛漾、悸動的閃光,得以焊接成更燦爛耀眼的什麼,讓這個時代的黑暗有突出物,果真如此,我願是那銀河系的焊接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