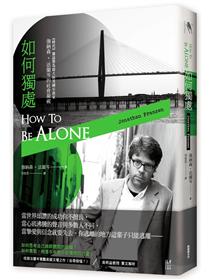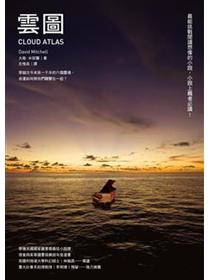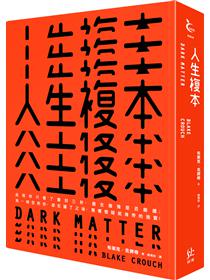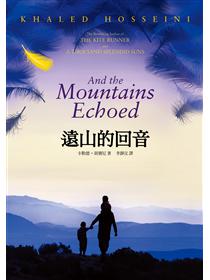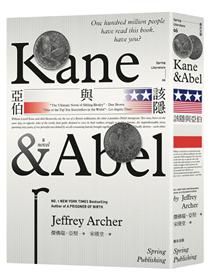每晚,他都會夢見我
我上床睡覺、做夢的時候,他醒來
我清醒時的生活,他則當成他的夢……
帶有村上春樹風格的魅力之作!
如果可以拿一個願望交換
你願意埋葬現實,還是拋棄夢境?
曼布克獎 決選作品
布萊克小說紀念獎 決選作品
三宅詠爾從未見過父親,甚至連父親的名字也不知道,為了解開身世之謎,十九歲的他離開鄉下來到東京,在茫茫人海中尋找未曾謀面的父親。他的腳步走過憤怒城市的底層社會,也走向無可避免的命運。
他不懂為何單純的尋父之旅,恐怖事件總在他身旁上演?數字「9」到底有什麼祕密?他要經歷多少黑暗才能找回失落的過去?透過想像、夢境、電玩和手稿重述記憶,我們看見人性的多重面向,也和主角一同進入熠熠生輝的奇異冒險。
在《九號夢》中,米契爾展現恢弘野心,結合驚悚和當代日本流行元素,讓敘事穿梭在虛幻與現實間,挑戰想像力的極限。
作者簡介:
大衛‧米契爾/作者
一九六九年出生於英格蘭,肯特大學比較文學碩士,英國最重要的新生代作家。曾在日本廣島擔任工程系學生的英文教師八年。
他深受保羅.奧斯特、村上春樹等作家影響,從中培育出原創、獨特的風格。他的第一本小說《靈魂代筆》即鋒芒畢露,轟動歐美文學界,被評選為「三十五歲以下作家年度最佳著作」,獲頒《週日郵報》萊斯文學獎,並入圍《衛報》小說新人獎決選。
第二本小說《九號夢》仍然令人驚豔,以虛實交錯的敘事手法挑戰想像力的極限,入圍曼布克獎及布萊克小說紀念獎決選名單,並於二○○三年獲選葛蘭塔小說新秀獎。其他作品有《雅各的千秋之年》、《黑天鵝綠》(Black Swam Green)、《雲圖》等。
他的作品四度入圍曼布克獎,曾獲萊斯文學獎、英國國家圖書獎最佳小說獎、倫敦南岸文學獎與大英國協作家獎。二○○七年以傑出的文學成就被美國《時代》雜誌遴選為「影響世界最重要的一百位藝文人物」。目前定居愛爾蘭。
譯者簡介:
廖月娟
1966年生,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碩士。曾獲誠品好讀報告2006年度最佳翻譯人、2007年金鼎獎最佳翻譯人獎、2008年吳大猷科普翻譯銀籤獎,主要翻譯領域為醫學人文、文學與歷史。
文學譯作包括曼特爾《狼廳》系列、米契爾的《雅各的千秋之年》、安.泰勒《學著說再見》、納博科夫《幽冥的火》與《說吧,記憶》等。
各界推薦
媒體推薦:
如果你想把現實從裡到外翻轉出來查看,仔細地切割、剖析,這本小說不但會讓你上癮,如迷宮般的無限可能還可能使你的大腦爆炸。
――《大誌雜誌》(The Big Issue)
米契爾以非凡的手法呈現五彩繽紛的東京——從情欲橫流的愛情賓館到黑幫殺人計畫……他是個極富才華的作家,精於融合各種元素,創造一個又一個令人著迷的角色。
――《觀察者報》(Observer)
米契爾是神奇的文字建築師,把燠熱、嘈雜的東京化為一個想像之都。
――《泰晤士報》(The Times)
敘述變化和步調使米契爾在當代英國小說家中獨樹一格。他的幻想風格尤其突出,無人可及。
――《愛爾蘭時報》(Irish Times)
小說每每以柳暗花明的驚奇、曲折離奇的敘事和別出心裁的聲音讓讀者樂在其中……米契爾就是營造這種樂趣的天才小說家。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書評
這本小說讓我對英國小說的未來充滿希望……本書融合夢境、想像、拼貼,包括奇幻迷離的電玩世界到黑幫血拼,甚至還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自殺魚雷。結構巧妙,懾人心弦。本書可謂二十一世紀小說的代表作。
――《獨立報》(Independent)年度選書
米契爾的小說讓人不時想起德里羅、村上春樹、科幻小說,特別是不斷對現實與非現實的探索。
――《書單》(Booklist)
初讀米契爾的小說就教我愛不釋手……讀第二次,更有回味無窮之感。
――拜雅特(A. S. Byatt)
這本小說融合驚悚小說、悲劇、幻想、電玩及躁動不安的現代東京圖像。
――《衛報》(The Guardian)
米契爾寫出一本前所未有的小說。有趣、溫柔又震懾人心,把成長小說提升到全新的境界。
――《新聞週刊》(Newsweek)
透過作者萬花筒般的眼睛,我們感受到現代東京的脈動。這個小說就像一個夢,一個讓你捨不得醒來的夢。
――《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
文字精煉、有力,不時教人拍案叫絕,充滿大膽的想像力及數位時代斷斷續續的節奏。米契爾從電影、漫畫、電玩和文學取材,他筆下的東京是個令人目眩神迷的虛擬實境與資訊迷宮。最讓人驚奇的是,在你看完這本小說,懷疑這一切是否只是一個夢,你一點都沒有上當的感覺。
――《倫敦標準晚報》(Evening Standard)
作者用創新的手法翻新古典的電玩與追尋主題……敘事如羊腸小徑般蜿蜒曲折,又如迷宮般複雜,融入許許多多的主導動機,如動作片、漫畫、動漫、幻科、奇幻、古典偵探小說、黑幫故事、成長小說、網路叛客、史詩歷險與戰爭……米契爾不可思議地將這些融合得天衣無縫,展現破格的自由,而不著痕跡。
――《獨立報》(Independent)書評
媒體推薦:如果你想把現實從裡到外翻轉出來查看,仔細地切割、剖析,這本小說不但會讓你上癮,如迷宮般的無限可能還可能使你的大腦爆炸。
――《大誌雜誌》(The Big Issue)
米契爾以非凡的手法呈現五彩繽紛的東京——從情欲橫流的愛情賓館到黑幫殺人計畫……他是個極富才華的作家,精於融合各種元素,創造一個又一個令人著迷的角色。
――《觀察者報》(Observer)
米契爾是神奇的文字建築師,把燠熱、嘈雜的東京化為一個想像之都。
――《泰晤士報》(The Times)
敘述變化和步調使米契爾在當代英國小說家中獨樹一格。他的幻想風...
章節試閱
我沒有打退堂鼓,直奔新宿車站,連我自己都覺得驚訝。只是在我穿越北道的時候,差點被救護車撞死。屋久島的紅綠燈僅供參考,東京的燈號可是攸關生死。昨晚,我在客運終點站下車時,發現東京有種口袋內裡的氣味。但我今天已經聞不到了,也許我一身上下都是這種味道了。我走上潘奧普蒂康大樓前的台階。大樓高聳入雲。過去七年,我不斷地想像這一刻,實在不敢相信我真來到這個地方。這裡就是了。旋轉門緩緩轉動。冷氣涼颼颼,我不禁起了雞皮疙瘩──如果冬天變得這麼冷,他們就會打開暖氣。大理石地板白得像是漂白後的骨頭。棕櫚樹栽種在銅甕之中。一個獨腿男子拄著枴杖從光潔的地板走過。橡膠摩擦地板,吱嘎吱嘎,夾雜金屬撞擊的鏘啷鏘啷。眼前冒出像長號一樣大的花,花朵大得可吞噬嬰兒。我左腳的棒球鞋底也發出令人尷尬的唧唧聲。九個訪客坐在一排完全相同的皮製扶手椅上。他們看起來和我差不多年紀,很可能都是複製人,工蜂一樣的複製人。每一個人都在想:「真是令人尷尬的唧唧聲。」我走到電梯門口,在樓層簡介的牌子上尋找大杉與房杉法律事務所。想想今天的收穫吧。到了晚餐時分,或許我已在我父親家門外按鈴。「小子,你要去哪裡?」
我轉過身去。
接待處的警衛狠狠地瞪我。那群複製人的十八隻眼睛都投射過來。「你是文盲嗎?」他用指關節敲擊一個牌子,寫著:訪客請到接待處登記。我後退,向他鞠躬、致歉。他雙臂交叉。「所以呢?」
「我有事要去大杉與房杉事務所。我要找他們的律師。」
他的帽子上繡著「潘奧普蒂康保全」的字樣。「你怎麼可以這樣大搖大擺地走進來。你跟哪一位預約的?」
「預約?」
「預約,『預定』的『預』,『約會』的『約』啊。」
那群複製人十八個鼻孔都嗅到了羞辱的氣味。
「我希望見到加藤明子小姐。」
「加藤小姐知道你要來見她嗎?」
「她不曉得,因為──」
「所以,你沒有預約。」
「請聽我說──」
「你聽我說。這裡可不是超市,進駐這棟大樓的都是私人企業。這些企業的業務很多都是機密。你不能隨便闖進來。除非是來這裡上班的、事先約好的訪客或有其他正當理由,否則任何人都不能進入電梯。明白了嗎?」
十八隻複製人的耳朵都偵測到我的鄉下口音。
「我能請你幫我預約嗎?」
我又錯了。那個警衛跟我吹鬍子瞪眼睛。有一個複製人在竊笑,等於是火上加油。「你是聾子,沒聽到我方才說的嗎?我是警衛,不是接待員。我的工作是把無聊人士、推銷員、閒雜人等趕出去,而不是帶他們進來。」
我必須停損了。「我無意冒犯,只是──」
太遲了。「小子,你給我聽著。」警衛摘下眼鏡,擦亮鏡片。「你的口音告訴我,你不是本地人,所以你必須好好聽我解釋,了解我們在東京是怎麼工作的。你最好在我真的生氣之前就趕快溜。你必須跟加藤小姐約定一個時間,約定時間的前五分鐘再來這裡。你必須在我這裡登記,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我會和大杉與房杉法律事務所的接待員確認你預約的時間無誤。之後,我才會讓你進電梯。我說的你都了解了嗎?」
我深呼吸。
警衛啪一聲翻開報紙。
雨後的濕氣和塵土又使東京變得黏膩。路上的積水在高熱的氣溫之下蒸發殆盡。一個街頭藝人在高歌,唱得荒腔走板,使路人想偷走他的零錢,用他的吉他往他的頭砸下去。我朝向新宿地下鐵入口。行人步伐快慢不一,被太陽曬得頭昏眼花。我父親家的電鈴就在東京街道指南的某個方格,但我還沒找到。我被一小塊掏不出來的耳屎搞得心浮氣躁。我討厭這個城市。我經過一家劍道館,竹劍撞擊聲像骨折啪啪啪地從窗格傳出。人行道上有雙鞋子,似乎主人突然從人間蒸發,隨風而逝。挫折感與無力的罪惡感在我心中翻騰。我似乎毀了某種無形的約定。但這是跟誰訂的約呢?公車和卡車阻塞了城市的動脈,行人在車陣的縫隙鑽來鑽去。在我瘋狂為恐龍著迷的時期,我曾在書上看到一個理論:恐龍會大滅絕是因牠們的糞便堆積如山,最後在惡臭之下窒息而死。踏遍東京每一條大街小巷之後,我發現這樣的理論並不荒謬。我厭惡這座城市到處張貼的廣告、膠囊般的小房間、隧道、自來水、潛水艇、空氣,我討厭每個角落都有塊「私人土地,禁止通行」的牌子,我痛恨每一扇門張貼的「僅限會員」告示。我願化成一個核子彈頭,將這座糞堆般的城市化為灰燼,從此從地表上消失。
***
自慰通常能讓我一夜好眠。我正常嗎?沒聽過十九歲的人會失眠。我不是戰俘、詩人,也不是科學家,甚至不會為了愛情輾轉反側。不過,我倒是欲火難耐。這城市有五百萬個女人,正朝向處於性欲巔峰期的我。女人應該把赤裸裸的自己用氣泡墊的信封裝起來,郵遞給我──像痲瘋病人般孤單的我。讓我想想。今晚,誰會乘坐愛情篷車來找我呢?啤酒廣告上,泳衣濕透的姬姬.光?還是千代雪的媽媽,那一身華麗搖滾打扮的輕熟女?朱彼特咖啡館的女服務生?《札克斯.歐米茄與不祥的紅月》一書中那個長得像昆蟲的女人?我想,還是找我的老相好姬姬吧。我東摸摸,西摸摸,在找衛生紙。
我在找火柴,想點燃一根 Mild Seven 當事後菸,但遍尋不著,只好用瓦斯爐。一頭哥斯拉終於在我手中癱倒。現在,我反倒比平時還清醒。姬姬今晚頗讓人失望。不會掌握最好的時間點。對我來說,她是不是太年輕了?富士沖印的時鐘顯示:一點四十九分。現在做什麼好?洗澡?練吉他?我這禮拜收到了兩封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信。回覆其中的一封?哪一封呢?挑比較簡單的那封吧。我最後還是沒見到加藤明子,因此給她寫了封信。她的回信只有一頁。我把她的回信和另一封放在塑膠袋中,存放在冰箱冷凍庫。起初,我把這封信放在安壽相片旁的架子上,但那封信好像一直在嘲笑我。信終於來了……什麼時候收到的呢?禮拜二。文太郎把信交給我時,唸出信封上的字。「大杉與房杉法律事務所。唉喲,你在追女律師嗎?小子,小心點,否則你那話兒可能會被貼上法院封條。要不要聽我講跟律師有關的笑話?你可知道鯰魚和律師有什麼差別?猜猜看嘛。不知道?一個卑鄙無恥、喜歡待在陰暗的底層,以渣滓為食,另一個就是鯰魚。」我告訴他,這笑話我聽過了,然後從堆滿錄影帶的樓梯飛奔上樓,回到我的膠囊房間。我告訴自己,儘管她回了信,恐怕希望不大,沒想到加藤明子的「不」像是一記響亮的耳光。這封信,我每一個字都會背了,字字命中我的要害,最致命的如下:洩露客戶的個人資料等於是背叛客戶的信任。任何一個負責任的律師都不會這樣做。這女的真絕。此外,本人不得不拒絕幫你的信函轉交給客戶。畢竟這位客戶已明白表示,他不想收到這封信。說得夠清楚了,甚至不給我再度出擊的餘地。最後,如果來日你決定透過法律程序,強制要求本事務所披露你的生父資料,本人在這個早期階段提供的協助顯然將構成利益衝突。請勿苦苦追問,相信此回覆已表明本事務所的立場。的確,一清二楚。A計畫沒搞頭了。
上野車站的代理站長青山先生的腦袋瓜像鉚釘頭一樣禿,人中有一小撮希特勒式的鬍子。這日是禮拜二,我在上野車站失物招領處上班的第一天。「我可比你想的忙很多。」他在跟我說話,視線卻一直黏在桌上的文件上。「不過,我再怎麼忙,還是會找新進人員來個別談話。」兩句話之間的沉默足足有一哩那麼長。「你知道我是誰了。」他的鋼筆沙沙地摩擦紙面。「你叫──」他看了一下資料,「三宅詠爾。」他抬起頭來看著我,等我點點頭。我點頭。「三宅。」他叫我的名字,那語氣好像在說什麼食品添加物。「曾在蜜柑果園工作──」他把手中的文件翻來翻去,我認出自己的筆跡,「在九州南部偏遠地方的一個島,那裡很有田園風光。」青山頭上的牆面上掛著歷代站長的肖像。我想像這些人每天早上都要先吵一架,爭論該輪誰復活,在這間辦公室發號施令,帶領大夥兒度過煩悶的一天。辦公室有股陳年索引卡片的氣味,那些卡片已被陽光曬得褪色了。電腦主機在嗡嗡叫。高爾夫球棒閃閃發亮。「誰雇用你的?那個叫佐佐木的女人?」我點點頭。有人敲門。他的祕書端茶進來。「我正在跟新進人員說話,丸井太太!」青山咬牙切齒地說:「我在十點三十五分就要喝的茶,已經變成十點四十五分,是不是?」丸井太太低頭道歉,然後退下。「三宅,你到窗邊,往外看,告訴我你看到什麼。」
我照他的話做。「先生,我看到一個擦窗戶的工人。」
他對諷刺無動於衷。「工人下面呢?」
電車在車站飯店的陰影中進進出出。上午的乘客、行李搬運工、像無頭蒼蠅般繞來繞去的人、迷路的人、遲到的人、準備接人的人、被接的人、月台清掃機。「下面是上野車站。」
「三宅,你說,上野車站是什麼?」
我被這個問題搞糊塗了。
「上野車站是──」青山發表他的宏論:「一部至為精密的機器,可說是地表上調校得最精準的時鐘,真是舉世無雙。而這間既防火又防盜的辦公室,就是這個時鐘的中樞。這個控制台幾乎可以……操控一切。三宅,上野車站就是我們的人生。你好好為它服務,它也會好好報答你。你的職業生涯從此像列車時刻表一樣按部就班。你實在是有福之人,才能做這部機器的一個小齒輪。我也是從這種基層的工作慢慢往上爬的,但是謹守準時、勤奮、正直──」電話鈴響,我像不存在似的。青山的臉瞬間變得光彩煥發,似乎瓦數調高了,聲音也變得嘹亮。「先生!實在榮幸……是的……的確如此……的確如此……真的。這樣的提議太好了。在下可否斗膽說一句……是的,先生,當然……會員資格仲介?那是無價之寶啊……好極了……在下有個提議……好的。時間改成禮拜五?的確……我們都非常期待您的批評、指教。謝謝……正是……在下可否──」青山掛上話筒,對著電話發愣。
過了幾秒,我輕咳一聲,禮貌地提醒他。
青山這才抬起頭來。「我方才說到哪裡了?」
「小齒輪和正直。」
「正直。」但他的心思已經不在這裡了。他閉上眼睛,捏自己的鼻梁。「你的試用期是六個月。三月,你就有機會參加日本鐵道公司的考試。所以,是那個叫佐佐木的女人雇用你的。別把這女人當作模範。她不過是一個男人婆,就算結婚了,也不辭職。她老公死了──的確可憐,不過,在這世上每一分每一秒都有人死去。她想用男人的工作來彌補自己的損失。好了,三宅,你先糾正你的口音吧。可以多聽NHK電台廣播。把你腦袋裡的垃圾清乾淨。在我高中時代,我們學校訓練出來的每一個人都是人中龍虎。現在畢業的,都變成了孔雀。你可以走了。」
我退下,關上門之前,對他一鞠躬,他卻盯著一片虛空。辦公室外空無一人。茶盤就擱在一旁。我竟然掀開茶壺蓋子,往裡面吐了一口口水。這該是跟工作壓力有關。
失物招領處這工作還算不錯。日本鐵道員工的連身工作服雖然不夠帥氣,但我六點整就可下班,從上野站走幾步路就可轉乘北千住線。我在流星附近的梅島站下車。在六個月的試用期間,我領的是週薪。每個禮拜都能進帳也挺好的。我真幸運。這工作是文太郎幫我找的。上禮拜五,我從潘奧普蒂康回來,他說,有個熟人跟他提到一個工作機會,不知道我有沒有興趣?我說,當然有。不久,我就和佐佐木太太面談。她是嚴厲的老鳥,等於是我阿嬤在東京的翻版。談了大約半小時,她就決定用我了。我早上編列失物清冊,把列車長和清潔人員在列車到站時撿到的物品依照日期/時間/車次記錄好,再依照一定順序放到金屬架上。失物招領處的主管是佐佐木太太,貴重物品都歸她負責,像是皮夾、信用卡、珠寶,她在邊間的辦公室逐一記錄、保管,而且必須向警方登記。須賀教我把那些不值錢的東西堆放在後面的辦公室。「這裡光線很差,是吧?」須賀說:「你可從拾獲的東西看出月份。十一月到翌年二月,會撿到一堆雪橇和滑雪板。三月,畢業證書。六月,結婚賀禮。七月,泳衣堆積如山。只要下一場大雨,就有好幾百支遺失的傘。雖然這工作不能讓人熱血澎湃,伊姆猴,總比在修車場當黑手或是送披薩來得好。」下午,我都在櫃台服務,等候失主前來認領或接聽電話。當然,交通尖峰時刻最忙,但到了三、四點過後,我就輕鬆了。最常來造訪的是我的回憶。
***
我躺在床上,盯著上方,利用天花板的方格當棋盤思索騎士的走法。我走著,走著,走到最後忘了走過哪些格子,只得重來。試了三次之後,覺得窮極無聊,不玩了。如果睡不著,不如想想信件的事。另一封信,也是極其要緊的信。那封信什麼時候到的?禮拜四。就是昨天。不,應該是前天。我下班回到流星的時候已累到虛脫。有人把三十六顆保齡球丟在九號月台上,不巧是離失物招領處最遠的月台。須賀又施展隱遁神功,我只好把那些保齡球一個個拖回來。後來,有支球隊來認領了,說他們一直在東京中央車站等這一批球。我漸漸了解,失物招領處拾獲的東西無奇不有。佐佐木太太有一次用推車推了具人體的骨骸進來,骨骸塞在一只背包裡。一個醫學生來認領了。他說,他去參加教授餞別會之後,坐車時把背包留在車上,忘了帶走。不管怎麼說,這日我回到流星的時候,已汗流浹背。文太郎坐在櫃台後方的高腳凳上吃綠茶冰淇淋,一邊拿著放放大鏡細看一張紙。「老弟,」他說:「要不要看看我兒子?」奇怪,文太郎說,他還沒有小孩,哪來的兒子?接著,他得意洋洋地把手中那張印得黑黑的、一團模糊的紙給我看。我皺著眉頭。「看,這超音波多神奇!」他說:「這是子宮裡面!」我盯著文太郎的肚子。他兩眼發亮。「別鬧了!我們已經為他取好名字了。其實,名字是我老婆取的。不過,我也同意了。想不想知道是什麼名字?」
「當然囉。」我說。
「『航大』,『航行』的『航』,『偉大』的『大』。偉大的航行。」
「這名字很酷。」我真心讚美。
文太郎從各個角度打量航大的模樣。「看到他的鼻子了嗎?這是他的腳。好可愛,是不是?」
「可愛極了。這個像蝦子的東西是什麼?」
「我們就是看到這個,才知道寶寶是男的。」
「說的也是。」
「這裡還有一封信是你的。我也許幫你釘個信箱,但如此一來,就會失去用蒸氣拆封房客私人信件的樂趣了。」他交給我一個看起來很普通的白色信封,上面蓋的郵戳是宮崎,由鹿兒島的金錢舅舅轉寄過來的。我把信封撕開,裡面有三張皺巴巴的信紙。電視畫面上的是直升機相撞、大樓爆炸。布魯斯.威利摘下太陽眼鏡,斜眼瞄了這一片火海。我展信來讀,看到第一行,知道是誰寄來的,連忙把信塞進夾克口袋,爬上樓去,不想讓文太郎看到我那震驚的臉。
***
宮崎山診所
八月二十五日
詠爾:
我該如何起頭呢?我先寫了一封措辭激烈的信,後來換了哀怨的語氣再寫一封,然後又寫了封輕鬆有趣的,開頭說:「你好,我是你媽,很高興認識你。」接著,又用道歉起頭再寫一封。這些信全都被揉成一團,在房間另一頭的垃圾桶旁邊。我射門的技巧真是差勁。
今夏真熱,不是嗎?梅雨沒來,我就知道會熱死了。(我想,屋久島還在下雨。那裡一年到頭都在下雨。)所以,現在的你已將近二十歲了。二十歲。那些時光都到哪裡去了?想知道下個月我就多老了嗎?我太老了,無法跟任何人說。我目前在這裡接受精神方面的治療,並戒除酒癮。我從未想過要回九州,至少這山間的空氣很涼爽。我的治療師建議我寫信給你。一開始,我不想寫,但她比我要頑固,一直要我寫。其實,我是想寫信給你,但過了這麼久了,不寫還是容易得多。但我還是有個故事可講給你聽(不只是一連串的回憶)。我的治療師說,如果我講出來,讓你知曉,往事不會再來傷害我。若你不介意,就讓我出於自私寫出來。
很久以前,我還是個年輕媽媽,和幼年的你和安壽住在東京。公寓的錢是你父親出的,但這個故事和他無關,甚至也跟安壽不相干。這只是你我兩人的故事。那時,我看起來就像是個幸福人妻,跟一個有錢男人在東京高級地段住在九樓樓中樓式的公寓,陽台擺了很多花卉盆景。男人的襯衫不用我洗,他老婆會洗。我承認,在我離開屋久島的時候,你和安壽並不在我的計畫當中。不管怎麼說,二十年前,我在東京過得挺好的,遠勝過待在屋久島的蜜柑園當農婦。島上的人說,我媽(也就是你阿嬤)在背地裡安排好我的婚事,要把我嫁給馬場新太郎。我敢說,現在的他和二十五年前一樣,是個沒用的傢伙。
難啊,我要怎麼寫才好?
那時,我心裡很苦。我才二十三歲,每個人都稱讚我是個美人兒。年輕媽媽只能和其他年輕媽媽為伴,然而如果和她們格格不入,她們就會變成全世界最惡毒的族群。她們發現我是被人包養的「小三」之後,說我不要臉,對她們會有不良影響,甚至請求大樓管理人要我搬走。你父親的權勢足以阻止此事,但之後她們再也不願意跟我說話。如你所知,那時屋久島的人根本沒有人知道你的存在。我一想到故鄉的人在我背後對我指指點點,就痛苦難耐。
這時,你父親又有了新歡。對女人來說,嬰兒本不是性感的附屬品。雙胞胎只會讓男人雙倍倒胃口。結局很難看──我想,你不會想知道那些細節的(即使你想,我也不想再想起那段過去)。當初我懷孕時,他口口聲聲說,他會好好照顧我們。我實在太年輕、天真,不知道他說的是錢。他就像所有軟弱的男人,以為只要裝糊塗,所有的人都會原諒他。他的律師接手之後,我再沒見過他(我發誓我再也不想看到他那張臉)。我可以住在東京那間公寓,但不能賣掉。那時正值經濟膨脹時期,每六個月房價就會翻倍。你則剛滿週歲。
我不是個好女人(我從來就不是個良家婦女,但至少我有自知之明)。有些女人是天生的好母親,即使還沒當上母親,已充滿母愛。我從來就不是適合當母親的人,即使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依然如此。我討厭小孩。我用你父親的律師寄來的生活費請了個非法入境的菲律賓保母,我才能逃離公寓。我常坐在咖啡店,看人來人往。像我這個年紀的年輕女人,有的在銀行上班,有的喜歡插花,有的在購物。在我懷孕之前,我總認為這些日常瑣事窮極無聊。
兩年後,我在另一家酒吧找到工作,但我意興闌珊,畢竟我已經釣到了有錢男人。每次回家,你和安壽總會提醒我,有錢男人已離我而去。(尿布、嚎哭和無眠的夜。)一天早上,你發燒了,家裡只剩我們母子倆。保母帶安壽去幼稚園,不是我們家附近那家──年輕媽媽組成的黨羽杯葛我們,向那家幼稚園威脅,不准他們收你們姊弟,我只好把你們送到遠一點的幼稚園。你哭得聲嘶力竭,不知是因為發燒,還是因為安壽不在。我已經工作了一整夜,因此我配著伏特加吞下幾顆藥丸,不管你了。之後,我聽到你敲擊門板的聲音。當然,這時你已經會走路了。我的偏頭痛不讓我睡。我失控了。我對你嘶吼,要你滾開。當然,你只有哭得更大聲。我尖叫。接著是靜默。然後,我聽到你說了一個字眼,你一定是在幼稚園學的。
「爹地。」
我心碎了。
我平靜地做了個決定:我要把你從陽台丟下去。
新的墨水,新的鋼筆。方才那枝筆竟然就在這個節骨眼壞了。是的,我很平靜:決定把你從陽台丟下去。這十個字解釋我們之後的生活。我不是說,我有理由這麼做,也不是想我想這麼做,而是指我打算那麼做。真的。要寫下這些,實在很難。
事情是這樣的:我打開臥室那道向外開的門,把你從打過蠟的木頭平台扔出去。你從樓梯邊緣滑了出去,掉到我的視線之外。我呆住了,我只能讓你掉下去,無法挽回,就算我是超人也無能為力。你掉下去的時候,沒有哭。砰。我聽到你像一袋掉到樓下的書,那就是你落地的聲音。我等著你嚎啕大哭。我等著,等著。接著,時間以三倍的速度往前推進,以彌補方才的遲緩。你躺在樓下,耳朵噴出鮮血。我看得到你。(直到現在,不管我在哪裡,每次下樓都可以看到你。)我陷入歇斯底里。救護人員對我大叫,我才不再喃喃自語。我放下電話時,你猜,我看到了什麼?你坐起來,舔自己指頭上的血。
救護人員說,孩子的身體軟綿綿的,就像布娃娃,因此你才沒摔成重傷。醫生說,你是個幸運的寶寶,但他要說的應該是我這個做母親的很幸運吧。我說,你爬過樓梯的護欄什麼的,但我渾身酒氣,說什麼也沒人相信。真的,我們母子倆都太幸運了。我知道,我打算殺了你,往後就在監獄了此殘生。真不敢相信,我終於寫出來了。事發三天後,我拿一個月的薪水把保母打發走,我告訴她,我要帶你去你阿嬤那裡。以我的精神狀況,實在不適合照顧你和安壽。之後的事,你都知道了。
我寫出這些,不是為了搏得你的同情或請你原諒。我跟你說這個故事的用意遠超過這些。往事使我無法成眠,只有說給你聽,我才能舒服一點。我真的想好起來。
你可從這皺巴巴的信紙看出端倪,不是嗎?我把這些事寫出來之後,就把信紙揉成一團,想要丟進垃圾桶。我甚至懶得對準。可是,你知道嗎?那團信紙竟然進去了,甚至沒擦到桶邊。天曉得?或許冥冥之中,自有定數。我要把這封信從鈴木醫生辦公室門底下的縫隙塞進去,免得又反悔了。如果你想打電話給我,就照信箋抬頭上印的電話號碼。你自己決定吧。但願──
我沒有打退堂鼓,直奔新宿車站,連我自己都覺得驚訝。只是在我穿越北道的時候,差點被救護車撞死。屋久島的紅綠燈僅供參考,東京的燈號可是攸關生死。昨晚,我在客運終點站下車時,發現東京有種口袋內裡的氣味。但我今天已經聞不到了,也許我一身上下都是這種味道了。我走上潘奧普蒂康大樓前的台階。大樓高聳入雲。過去七年,我不斷地想像這一刻,實在不敢相信我真來到這個地方。這裡就是了。旋轉門緩緩轉動。冷氣涼颼颼,我不禁起了雞皮疙瘩──如果冬天變得這麼冷,他們就會打開暖氣。大理石地板白得像是漂白後的骨頭。棕櫚樹栽種在銅甕...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