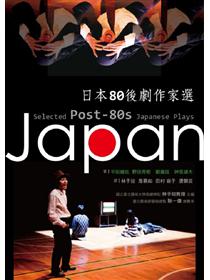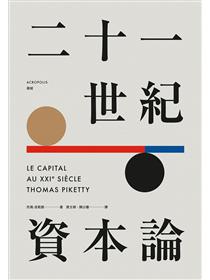蜷川幸雄在華文世界第一本中文譯作
世界的蜷川從小劇場轉型到商業劇場的歷程
1935年出生的蜷川幸雄曾為日本前衛劇場運動的健將,引領著六○年代日本小劇場運動,以反體制、反新劇的思想創作戲劇演出。但到了七○年代熱潮消退,小劇場面臨解散的命運,他開始投入製作商業劇場,第一齣戲就是挑戰莎士比亞的名作《羅密歐與茱麗葉》,從此開啟了他與莎士比亞的不解之緣。
「我們都是被時代病魔深深侵蝕的患者。現在我已經上了年紀,當導演也過了二十二年,但還是繼續地被戲劇這種病魔侵蝕。而這種病惡化的速度漸漸加快,一路奔馳倒數,直到終點。」
本書從蜷川幸雄的戲劇自傳為始,呈現日本六○年代小劇場當時氛圍,與後來成為知名演員和編劇家的同儕們過往點滴。以及他轉型走入商業劇場後所面臨的挑戰,並回憶如何開啟世界各國巡演之門。
「我這八年來從沒看過戲劇雜誌,也拒絕受訪。當我發現戲劇雜誌的評論和批評根本無法與我工作的辛勞相提並論時,我對這些就不怎麼感興趣了。」
「為了將背負著形形色色不同日常的觀眾帶進戲劇的時間,也就是進入非日常的時間和空間中,我必須驅使各種不同技巧。這就是導演的工作。」
蜷川也在本書中闡述他的戲劇理念、分析自己的作品,以及他為何起用明星、如何讓戲劇舞台進入「非日常」的世界等,鮮為人知的創作歷程。
「假如觀眾席裡坐著一千名青年,他們手裡就等於握著一千把利刃。我想,我得打造一個足以對抗千把利刃的舞台。那就是我的使命。」
最後,他提到與年輕人的溝通之道及如何產生共鳴、培養有個性演員的教育論等觀點,並回憶年少,述及影響他舞台美學的起點!
作者簡介:
蜷川幸雄(Ninagawa Yukio)
1935年出生於埼玉縣川口市。1969年以《真情滿溢的輕薄》崛起於前衛小劇場運動。1974年以《羅密歐與茱麗葉》走入商業劇場。從莎士比亞、希臘悲劇到日本劇作與文學,舞台作品題材多元,涉獵廣泛,在長達半世紀的導演生涯中,執導超過百部作品。他將歌舞伎的表演符號運用於西方經典的搬演中,形塑出獨一無二的戲劇美學,被日本人尊稱為「世界的蜷川」。
章節試閱
千把利刃(1974~1983)
走出影城的門後往右彎,馬上就看到一間名叫「太陽」的飯店。那是我們的住宿處,回到那間骯髒的小房間,我頓時全身放鬆。躺在床上,電話突然響了。接起電話,對方說他是東寶戲劇部的中根。
「我想請您導演明年五月在日生劇場的《羅密歐與茱麗葉》。」
「演員是誰?」
「羅密歐是市川染五郎(現在的松本幸四郎),茱麗葉是中野良子。」
中根製作人表示這齣戲原本計畫請法蘭高‧齊費里尼(Franco Zeffirelli,1923~,義大利電影、歌劇導演,目前為義大利政治家)來執導,但是他因故無法前來,希望我代替他來導這齣戲。他又繼續說,反正您遲早會知道的,所以原本計畫請齊費里尼導演這件事我也先告訴您。
當時我一心想導小健使用女兒節台座、在女兒節晚上表演的《哈姆雷特》,所以雖然覺得機會難得,但還是辭退了對方的好意。
在《不哭嗎?不為了一九七三年而哭嗎?》的末場演出,宣稱再也不在新宿演戲後,我拚命地思考如何讓我自己還有櫻社蛻變重生。該換腳本家?換導演?還是換演員?總之,勢必要在這三種之中有所改變。我覺得大家彼此的想像力掩護了彼此的感性。如果沒有新的邂逅,就不可能有下一步的發展。
我想起在櫻社末期曾經見過的一位青年。那應該是一九七二年的秋天吧。我進了新宿一間電影院打發時間,一個青年叫住我。我已經忘記當時演的是什麼電影了,坐下沒多久,電影就演完了。我走出大廳抽菸,正靠在牆邊發呆。
「您是蜷川先生吧?有件事我務必要請教您,可以跟我到外面來嗎?」
「可是我才剛進來,還沒看電影呢。」
我對他說。
「非常抱歉,但是我真的很想請問您。」
那個青年糾纏不休。
看到他愁眉深鎖的凝重表情,最後我也無法拒絕,跟他一起離開了電影院。
我們進了電影院附近一家地下室的陰暗咖啡廳,面對面坐著。服務生端了咖啡來,但那青年始終沒開口說話。
「你要問什麼?」
我先開了口。
那一瞬間,我感覺有個東西抵住我的側腹部,那人上半身前傾,盯著我的臉。我只能從他極不自然的姿勢,想像他在桌面下伸長的手臂。他鐵青著臉這麼對我說。
「蜷川先生,你現在能高談希望嗎?請回答我。」
我沒說話。
「蜷川先生,你能高談希望嗎?」
那青年再次開口。
「我沒有資格說希望,也不會高談什麼希望。」
我說道。
「是嗎。」
說著,那青年站起身來。抵在我側腹部的力道突然消失。青年伸出他放在桌下的手,那手裡握著一把折疊刀。
「我常看你的戲。如果你現在大言不慚地跟我高談希望,我打算一刀刺下去。還好――」
說著,他離開了咖啡廳。
假如觀眾席裡坐著一千名青年,他們手裡就等於握著一千把利刃。我想,我得打造一個足以對抗千把利刃的舞台。那就是我的使命。
隔天拍完戲後,我躺在飯店裡翻看《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文庫本。中根製作人又打了電話來。
「我現在在京都車站,能見一面嗎?」
影城正門的馬路邊林立著一間間的餐廳和咖啡廳。其中有東京演員常去的咖啡廳、有京都演員愛去的咖啡廳。京都演員們不會踏進東京演員聚集的咖啡廳,而東京演員們也不會走進京都演員常去的咖啡廳。我和中根製作人在一間剛開張的小酒館見面,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面。
中根製作人作風強勢,也很優秀。他跟一般新劇製作人不一樣。當時我對他的印象是,原來商業劇場的製作人遠比新劇製作人更優秀。
最後我還是接下了《羅密歐與茱麗葉》的導演工作。真山說我應該接下這份工作,我也期待自己能走進一個未知的新世界,或許嘗試新鮮的體驗、遇到不同風格的人,能讓自己有全新改變。我想,這麼一來我就能重回櫻社。這段過程一定能帶給我新的邂逅。
我決定執導商業劇場,帶給曾經參與櫻社的年輕人們強烈的衝擊。大家紛紛表示不滿。我們決定要當面討論我執導商業劇場這件事。大家約了時間碰面。
見面地點在參宮橋一間小酒店,這是櫻社某個成員介紹的店。那天晚上店裡臨時公休。清水邦夫、蟹江敬三、石橋蓮司、綠魔子,還有我,再加上過去曾經參與櫻社公演的工作人員和演員們,總共聚集了三十人左右吧。
我們一直討論到天亮,過程有人看著事先在筆記本上寫好的文字發言,也有人因為太過緊張,滿臉鐵青地說話。最後我們做出結論,決定解散「櫻社」。大多數人對我堅持要執導商業劇場,都抱持否定的意見。
走出小酒店,天已經亮了。那天早上有些微微寒意,天色顯得異常亮白。我一個人走向甲州街道。道路有些傾斜。蟹江站在人行道一角,對我說。
「阿錦,以後有什麼打算?」
我回答。
「沒辦法,只好繼續做商業劇場了。」
那個清晨相當寒冷,我在那裡跟蟹江道別。
每當我回憶起那天的事,很多細節都想不起來。雖然會浮現一些粗糙不悅的感覺,但這種感覺也漸漸不再真切。腦中的印象並不具體,就像一張平面圖畫紙一樣,輕薄、空白地飄到我面前。難道是我試圖要塵封那天的記憶,所以記憶氣化之後,飄散四溢了嗎?我是不是就這樣靜靜埋葬了過去的點滴,埋葬了和朋友之間的回憶呢?
商業劇場很新鮮。
我一在導演椅上坐下,馬上就有人送上咖啡。原來商業劇場會有人送咖啡啊,這就是我對商業劇場的第一印象。在現代人劇場和櫻社中我也得負責打掃、自己倒茶。看到有人端上咖啡,我覺得好感動。排練場中間放著一張導演用的舊椅子,聽說那張椅子是菊田一夫先生常用的,我並沒有用那張椅子,我總是盤腿坐在地板上排戲。
飾演羅密歐的市川染五郎一見到我便說。
「真的是蜷川先生啊,沒想到那個蜷川先生就是這個蜷川先生!」
他為什麼這麼說呢。我記得在我二十一還是二十二歲的時候,NHK電視台有一齣村上元三所寫的《江戶小鼠》連續劇,我和染五郎先生都演了那齣戲。那時候染五郎先生應該還在念高中吧。我們演的是游手好閒老愛惹事的旗本次男。我和染五郎演對手戲,戲裡兩個人經常吵架,總是針鋒相對。
「沒想到那個蜷川先生就是這個蜷川先生!」
染五郎這句話其實是想說:「沒想到年輕時跟我一起演戲的蜷川先生,竟然是現在的導演蜷川先生。」
染五郎的羅密歐演技相當出色。排練第一天,我一開始就要求所有演員丟本上場,過去商業劇場中不曾有過這種手法。很多時候直到首演日大家還記不住台詞,由此可見我這種做法有多麼奇特。整個排練場陷入驚慌。我則不斷破口大罵。
「你們就是工作態度這麼散漫,商業劇場才會被人看不起!喂!那個戴太陽眼鏡來排戲的傢伙,文藝復興時期會有太陽眼鏡嗎!給我拿掉!喂!為什麼武打場面你搞得像《殺陣師段平》(以武術師市川段平為藍本的故事)一樣,又不是在演歌舞伎。還有那邊那個傢伙,走路為什麼彎著腰左搖右擺的,你以為在演長谷川一夫的戲嗎!等一下!這句台詞為什麼說得這麼小聲?什麼,裝上麥克風後音量就剛剛好?笨蛋,誰跟你說用麥克風!哪個國家的人戴麥克風演莎士比亞!」
我不知丟了幾個菸灰缸,有時候也丟椅子。排練場就像地獄一樣。但是染五郎先生還是若無其事地排戲。終於等到羅密歐出場。
染五郎先生不知從哪裡拿來了一把真的雜草,單手拿著草出場。序幕在艾爾頓‧強的激烈搖滾樂中揭開,將近八十個群眾一陣亂鬥後的寂靜中,一個懷藏戀愛苦惱的少年,從剛剛散步的森林裡採下被朝露沾濕的野花,慢慢走了過來。
羅密歐在廣場發現了他的朋友,於是在這之前靜態的演技立刻換上不同風貌,好比一個放學後的高中生,說起煩惱時就像在玩耍,那表情充滿青春期特有的彆扭倔強。染五郎先生飾演的羅密歐快速在舞台上四處走著,一會兒跟朋友搭肩、轉眼間又走進舞台後方。好像縱身一躍就消失在舞台後方一樣。
排練場中響起熱烈的掌聲,新鮮的演技、精湛的技術。這就是歌舞伎演員。那是染五郎先生一場出色的展演。在排練第一天、第一次丟本排練,染五郎先生就能讓其他演員和工作人員都沉浸在感動的浪濤中。排練場開始變成激昂戰場。那時我心想,我應該會繼續留在商業劇場世界裡工作吧。
排完戲,走在新宿街頭,我遇到五、六個看似剛從遊行回來的年輕人,他們拿著旗竿顯得很疲累。仔細一看,原來是以往櫻社的成員。我們站著聊了幾句。從新宿車站往歌舞伎町那條路,右邊有水果店、左邊是間鞋店。大批人慢吞吞地走著,最後我們乾脆蹲在路邊繼續聊。我剛結束商業劇場的排練,而他們剛結束一場遊行抗爭。我記得那是一九七四年的四月。鬥爭早就已經落幕。
導過商業劇場後,我的風評變得很糟。有天搭電車,發現車裡垂吊的雜誌廣告上印著「給蜷川幸雄的公開質問書」。在《讀書新聞》裡也只刊載批評我的劇評,那時候我切身感覺到自己被孤立。
就在這時候,我接到一通電話,是唐十郎打來的。唐十郎這麼對我說:
「蜷川啊,我寫了一齣叫《唐版瀧之白系》的戲,你願不願意來導?」
「我讀過那齣戲,非常有趣,可是我現在風評很糟,一起工作會給您帶來麻煩,這樣對您過意不去。」
聽我說完,唐十郎接著說:
「不,那無所謂。我只是想跟你這份才能一起工作。」
千把利刃(1974~1983)
走出影城的門後往右彎,馬上就看到一間名叫「太陽」的飯店。那是我們的住宿處,回到那間骯髒的小房間,我頓時全身放鬆。躺在床上,電話突然響了。接起電話,對方說他是東寶戲劇部的中根。
「我想請您導演明年五月在日生劇場的《羅密歐與茱麗葉》。」
「演員是誰?」
「羅密歐是市川染五郎(現在的松本幸四郎),茱麗葉是中野良子。」
中根製作人表示這齣戲原本計畫請法蘭高‧齊費里尼(Franco Zeffirelli,1923~,義大利電影、歌劇導演,目前為義大利政治家)來執導,但是他因故無法前來,希望我代替他來導這...
目錄
第一章 我的戲劇自傳
從演員到導演 (一九五五~一九六五)
騷亂的新宿時代(一九六六~一九七三)
千把利刃(一九七四~一九八三)
愁緒的季節(一九八四~一九八九)
第二章 戲劇這種病
深夜對談 何謂導演
破碎的鏡子
強風將息
一切都在舞台上 與朝日劇評抗爭記
走進非日常空間的艱難和樂趣
「1991、等待」的集團創作法
總有一天要還以顏色
媒體的獵巫 辭退NHK紅牌大賽的理由
戲劇與我
藝能表演者的一體感
《雲雀卡門》的夢想
令人讚嘆的喜劇人
《馬克白》與兩位少年
導演的孤獨――仰望飯店天花板
被戲劇病魔侵襲
為了遇見新的自己
年輕工作人員給我的磨練
TANGO AT THE END OF WINTER 戲劇的文化交流
暢行世界的戲劇
我的宴會服裝
貪戀少年時的國家
年輕導演才氣縱橫的英國
倫敦的演員甄選
導演的新起點
飛天座墊之必要
人生不能無戲
繼續丟菸灰缸
無人知曉的老街劇場
以舞台觀點看建築―― 西本願寺、飛雲閣
第三章 千種眼神
溝通的訓練
令人懷念的甜美地獄
膽小的我
駒込車站的杜鵑
與音樂的濃密關係
與年輕人的共鳴
烙印
銚子高中
大人真辛苦
培養有個性的演員
育兒是成人的學校
情慾的鮮紅花朵
時間的方盒
海外的邂逅
夢幻舞台
戲劇教育論
與松田優作一致的演技論
高橋一也的表現力
對宇崎龍童的忌妒
岡本健一的甄選
我的三個東京
三首安魂曲
花柳錦之輔
鹽島昭彥
太地喜和子
另一所學校
後話
文庫版後話
第一章 我的戲劇自傳
從演員到導演 (一九五五~一九六五)
騷亂的新宿時代(一九六六~一九七三)
千把利刃(一九七四~一九八三)
愁緒的季節(一九八四~一九八九)
第二章 戲劇這種病
深夜對談 何謂導演
破碎的鏡子
強風將息
一切都在舞台上 與朝日劇評抗爭記
走進非日常空間的艱難和樂趣
「1991、等待」的集團創作法
總有一天要還以顏色
媒體的獵巫 辭退NHK紅牌大賽的理由
戲劇與我
藝能表演者的一體感
《雲雀卡門》的夢想
令人讚嘆的喜劇人
《馬克白》與兩位少年
導演的孤獨――仰望飯店天花板
被戲劇病魔侵...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8收藏
8收藏

 8二手徵求有驚喜
8二手徵求有驚喜




 8收藏
8收藏

 8二手徵求有驚喜
8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