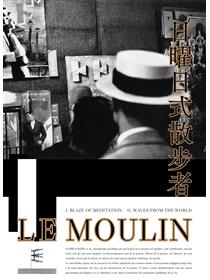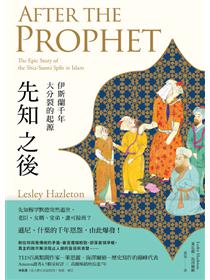獲《當代》雜誌選為「二○一四年度最佳小說」;
揉合魔幻寫實的百年招魂曲!
本書特色:
◎《老生》從庶民角度出發,記錄百年中國成長史,壯闊而深遠。
◎大陸《當代》雜誌評選為「二○一四年度最佳小說」。
◎「老生」,指一個人的一生活得太長,或僅只借用戲曲中的一個角色之意旨,更或者是指「老生常談」。書中每一個故事的人物,總有一個名字裡有「老」字或「生」字,命名之外,於小說中對生死意有所指,賦予小說人物更鮮活的魂魄。
內容簡介:
這一切似乎遠了或漸漸遠去,人的秉性是過上了好光景就容易忘卻以前的窮日子,發了財便不再提當年的偷雞摸狗,但百多十年來,我們就是這樣過來的,我們就是如此的出身和履歷,我們已經在苦味的土壤上長成了苦菜。──賈平凹
法國費米娜文學獎、紅樓夢獎、茅盾文學獎得主──賈平凹
超脫生死的百年中國史詩!
為了活得溫飽,活得安生,活出人樣,
他們做了什麼?
哪些是榮光體面?哪些又是齷齪罪過?
戰爭席捲二十世紀中國,
槍管下遍地殷紅,死亡近在咫尺。
在喪禮唱陰歌的老生,長生不死穿梭古今,
見證中國數代人的命運變遷:
游擊隊員拔槍起事、土改政策促使階級對立,
強勢幹部染指地主妻、文革引爆「人吃人」的荒謬劇。
即便村民脫貧致富,
突來瘟疫逆襲,一場繁華也成碎沫般的幻影……
賈平凹如實書寫近代中國的動亂、鬥爭、暴力與顛沛流離。透過唱師之口,捕捉細緻的農村紋理,以小人物或殘忍、或溫暖的故事,反映大中國的時代劇變。《老生》自二十世紀初寫至今日,藉由《山海經》推演歷史,將自然之原始純粹,對比當代中國的輾轉多變。《山海經》是一座山一條水的寫,《老生》是一個村一個時代的寫。故事從生之別離到死蔭幽谷;唱師口中的迢遙長路,從何處來、往哪裡去?
作者簡介:
賈平凹
原名賈平娃,一九五二年出生於中國陝西南部的丹鳳縣棣花村。現為西安市文聯專職作家。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作家協會陝西分會副主席等職。一九七二年進入西北大學中文系學習漢語言文學。一九七五年於西北大學畢業後,曾任文學編輯工作,包括陝西人民出版社文藝編輯及《長安》文學月刊編輯。
作品《滿月兒》獲一九七八年第一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臘月.正月》獲一九八四年第三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浮躁》獲一九八八年美國美孚飛馬文學獎、一九九九年《亞洲週刊》二十世紀中文小說100強,《愛的蹤跡》獲一九八九年第一屆全國優秀散文集獎,《廢都》獲一九九七年法國費米娜文學獎,《土門》獲一九九七年第五屆「西安文學獎」。《秦腔》榮獲二○○六年第一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首獎、二○○五年第四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傑出成就獎、第二屆「《當代》長篇小說年度最佳獎.專家獎」。
其他出版作品包括《帶燈》、《天狗》、《商州初錄》、《浮躁》、《妊娠》、《黑氏》、《廢都》、《白夜》、《土門》、《高老莊》、《懷念狼》、《病相報告》、《美穴地》等。
作品曾被翻譯為英、法、德、俄、日、韓、越等二十幾種語言。二○○三年榮獲法國文化交流部授予文學藝術榮譽獎。
相關著作
《帶燈》
《古爐》
《古爐(上)》
《古爐(下)》
《廢都》
章節試閱
開 頭
秦嶺裡有一條倒流著的河。
每年臘月二十三,小年一過,山裡人的風俗要回歲,就是順著這條河走。於是,走呀走,路在岸邊的石頭窩裡和荊棘叢裡,由東往西著走,以至有人便走得迷糊,恍惚裡愈走愈年輕,甚或身體也小起來,一直要走進娘的陰道,到子宮裡去了?
走到一百二十里遠的上元鎮,一座山像棒槌戳在天空,山是空空山,山上還有個石洞。這石洞太高,人爬不上去,鳥也飛不上去,但只有大貴人來了就往外流水。唱師扳著指頭計算過:當年馮玉祥帶兵北上,經庫峪繞七里峽過大庾嶺翻浙川溝,經過這裡流了一次水,到北京便把溥儀攆出了故宮。李先念從鄂豫去延安時,沿著石槽溝翻十八盤上紅岩子下核桃坪,到鎮上住過三天,流了一次水,後來當了三年國家主席。還有,梅蘭芳坐著滑竿來看金絲猴時流了一次,虛雲和尚遊歷時也流了一次。唱師說的這些事現在的鎮上人都不知道了,知道的是匡三要去西北大軍區當司令呀,頭一年冬季的車開過鎮街是流了水,水一出洞就結冰,白花花的像掛了白布簾子。而到了七年前,省長來檢查旱災,全鎮的人都嚷嚷要看石洞流水呀,但這一回,唱師在他的土窯裡不出來,手在肚皮上敲鼓點,唱:一根竹子軟溜溜啊,山山水水任我遊,遊到孝家大門口,孝家請我開歌路。人們說,唱師唱師,省長來了你不去看流水呀?!唱師不唱了,手還在肚皮上比畫,說:省長不是大貴人,石洞裡流不了水的。
果然石洞那次沒流水。
這就讓鎮上的人再一次議論了唱師,覺得他有些妖。唱師確實是有些妖,單憑他的長相,高個子,小腦袋,眼睛瓷溜溜的,沒一根鬍子,年輕人說他們小時候看見他就是現在這模樣,老年人也說他們小時候看見他也是現在這模樣。那棒槌山下的土窯,不知換過了多少次柴門,反正是唱師在土窯裡住上幾年,突然便不見了,十年八年的不見,土窯外的碾子臥成了青龍,磨子臥成了白虎,以為他已死在他鄉,他卻在某一天還掛著扁鼓拄著竹竿又回來了。走的時候是冬天,穿著草鞋,鞋殼裡塞墊了棉花,他說棉花是雲,他走雲,回來的時候是夏天,撐了一把傘,他說傘是日照。他永遠是一過中午就不進食了,只喝水,人問你怎麼只喝水呀,他說樹還不是只喝水?他能把磨棍插在窯前,一場雨後磨棍就發了芽。給孝家唱陰歌時發生過棺材裡有嘎喇喇響,他就要逮個老鼠用黑手帕包裹了在棺材上繞一繞,再把老鼠在門前一扔,說:你走!死了就死了,把貧窮和疼痛都帶走!老鼠就飛起來變成了蝙蝠,棺材裡也便沒了響動。他到鎮街人家做客,人已經去了卻還要回土窯一趟,聲明:我回去取嘴呀!他偶爾要想起外地的朋友了,就把郵票貼在胸口。
關於唱師的傳說,玄乎得可以不信,但是,唱師就是神職,一輩子在陽界陰界往來,和死人活人打交道,不要說他講的要善待你見到的有酒窩的人,因為此人托生時寧願跳進冰湖裡火海裡受盡煎熬,而不喝迷魂湯,堅持要來世上尋找過去的緣分,不要說他講的人死了其實是過了一道橋去了另一個家園,因為人是黃土和水做的,這另一個家園就在黃土和水的深處,家人會通過上墳、祭祀連同夢境仍可以保持聯繫。單就說塵世,他能講秦嶺裡的驛站棧道,響馬土匪,也懂得各處婚嫁喪葬衣食住行以及方言土語,各種飛禽走獸樹木花草的形狀、習性、聲音和顏色,甚至能詳細說出秦嶺裡最大人物匡三的家族史:匡三是從縣兵役局長到軍分區參謀長到省軍區政委再到大軍區司令,真正的西北王。匡三的大堂弟是先當的市長又到鄰省當的副省長。大堂弟的祕書也在山陰縣當了縣長。匡三的二堂弟當的是省司法廳長,媳婦是省婦聯主任。匡三的外甥是市公安局長,其妻侄是三台縣武裝部長。匡三的老表是省民政廳長,其祕書是嶺甯縣交通局長,其妻哥是省政府副祕書長。匡三的三個祕書一個是市政協主席,一個是省農業廳長,一個是林業廳長。匡三大女兒當過市婦聯主席,又當過市人大副主任。大兒子先當過山陰縣工會主席,又到市裡當副市長,現在是省政協副主席。小兒子是市外貿局長,後是省電力公司董事長,其妻是對外文化促進會會長。小女兒是省教育廳副廳長,女婿是某某部隊的師長。匡三的大外孫在北京是一家大公司的經理,二外孫是南方某市市長。這個家族共出過十二位廳局級以上的幹部,尤其秦嶺裡十個縣,先後有八位在縣的五套班子裡任過職,而一百四十三個鄉鎮裡有七十六個鄉鎮的領導也都與匡家有關係。唱師講這些故事如數家珍,還用柴棍兒在地裡畫出複雜的人物關係圖,他就喝酒,從懷裡掏出個酒壺抿上一口了,說:還想知道些什麼嗎?他的酒壺一直有酒,不時就抿一口,你不能問酒完了嗎,一問就真的酒完了,再倒不出一滴來。他並不怪嗔,還說:二百年來秦嶺的天上地下,天地之間的任何事情,你還想知道些什麼?!
要問的人再問他都有了恐懼,不問了,去找棒槌山上的放羊人,想買一隻羊或者趁太陽好,一邊在坡上晒暖暖一邊看羊群在草地上撒歡。
放羊的是父子倆,這父子倆命都硬,各自都死了老婆,第三代是個男孩,一表人才,還在縣城裡讀高中。父子倆不識數,也說不清放了多少隻羊,只是晚上把羊趕進圈了,就指著說:這一個,那一個,那一個,這一個。清楚哪一隻羊回來了,還有哪一隻沒有回來。來了人,不管來的是什麼人,父子倆遲早都會說:吃了沒?但吃了還是沒吃,他們不再有下文,會把旱菸袋從自己嘴裡水淋淋地取下來遞給你抽。來人當然不抽他們的旱菸,有一搭沒一搭地問著羊的事,眼睛就瞭見了溝對面唱師的土窯,窯門開著,是一個黑窟窿。說:哎,那唱師是多大的歲紀?老漢說:小時候他把我架到脖子上,我抱著他的頭,頭髮就是白的。來人說:那你現在多大了?老漢說:你看我兒多大?來人說:有五十吧。老漢說:我兒要是五十,那我就七十了。來人再對兒子說:你到底多大?兒子說:我爹要是七十,那我就五十呀。
這一年春上,上元鎮的天空總是停著一朵雲,這雲很白,像拴著的一顆偌大氣球,唱師出現在了鎮東口河灘上。整整十四個月的乾旱,倒流河的水有多半渴死成了沙子,唱師是騎了竹竿過的河,在地裡幹活的人沒問他是從哪兒回來的,只問天上這是什麼雲呀,他並沒回答,卻說:呀呀,這麼多的金子!到了夏天,倒流河岸的路要硬化,需要大量的沙子,一方沙子賣到六元錢,好多人才想起唱師曾經說過的話,後悔沒有早早把沙子囤起來。之後的整個夏天和秋天,唱師除了為南溝北岔的孝家去唱陰歌外,一有空老是到山上採果子,就有了一些人也跟著採果子,果子有五味子,野酸棗,珍珠果,還有八月炸瓜和獼猴桃,一邊轟著烏鴉一邊往嘴裡吃,聽見了啄木鳥在地敲木頭,也就叩牙。秋後鎮上人差不多都害起了打擺子,冷起來捂著兩床被子還渾身篩了糠似的,吃果子的人沒事。唱師還喜歡在坡上晒太陽,惹得後山林子裡的香獐子也學了樣,陽坡裡腿岔開晒起腺囊,鎮上人便因此去圍獵,得了許多麝香。
又過了一年,秦嶺外的平原上地震,波及到秦嶺,鎮上家家的門環都搖得哐啷啷響,人們全跑出門睡在野外的油毛氈棚裡。睡了七天,天天在傳著還有餘震的,還有餘震的,可餘震還是沒發生,就煩了,盼著餘震快來。終於在第八天再震了一次,並沒有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心踏實下來,才驀然發覺唱師壓根就沒有出窯洞。他是早知道地震會沒事的才一直待在土窯的?放羊的父子去了那個土窯,土窯外一叢鴿子花開了四朵,大若碗口,白得像雪,而唱師靜靜地躺在炕上,炕下的草鞋裡還臥著一隻松鼠,看見了他們,洗了一下臉,才慢悠悠地走了。原來唱師是病了。唱師是從來都不患病的,但這一次病了,又病得很重,腿腫得有桶粗,一張多麼能說會唱的嘴,皺得如嬰兒屁眼,張開著,竟說不出了話。
放羊父子拉了一隻羊到鎮街請醫生,醫生問了病情,說不用治了,醫生是治病而治不了命的。放羊父子說:他活成精了,他是人精呀!醫生說:神仙也有壽麼。讓把羊拉回去。
放羊父子嘆了一口氣,回到土窯裡等待著唱師老死,老死了把他埋葬。唱師不吃不喝了二十天,卻仍然不死。扁鼓掛在牆上,夜裡常常自鳴,那一根竹竿是放在窯門後的,天明卻走到了窯門外的石碾旁。這時間正是學校放了暑假,讀書的孩子回來了,孩子也便替了父親和爺爺守候唱師。放羊的父子要去放羊,就叮嚀著孩子:用心守著,一旦唱師嚥了氣,先不要哭,因為這時放起悲聲,死去的人容易迷糊去陰間的路,可能會變成遊魂野鬼,一定得燒了倒頭紙,給小鬼們都發散過路錢,然後就在窯外大聲喊我們,我們聽見就立馬來了。這孩子在土窯裡守候著,過一會兒去看看唱師,唱師眼閉著,以為人過去了,用手試試鼻孔,鼻孔還出氣。過一會兒再去試試鼻孔,鼻孔還是出氣。如此守過三天,唱師仍在出氣,這孩子就無聊了,想著自己古文成績不好,趁這陣可以補習補習,便讓爹請了鎮街上一位教師來 輔導,應允將來送五斤羊毛。這教師也是個飽學人,便拿了一冊《山海經》為課本,每日來一次,一次輔導兩節。
唱師靜靜地在炕上躺著,身子動不了,耳朵還靈,腦子也清白,就聽著老師給孩子講授。這時候,風就從窯門外往裡進,風進來是看不見的,看得見的是一縷縷雲絲,窯洞裡有了一種異香,招來一隻蝴蝶。唱師唱了一輩子陰歌,他能把前朝後代的故事編進唱詞裡,可他沒讀過《山海經》,連聽說過都沒有,而老師念的說的卻盡是山上海上和山上海上的事,海他是沒經過,秦嶺裡只說海吃海喝這個詞,把太大的碗也叫作大碗公,可山呀,秦嶺裡的山哪一處他沒去過呢,哪一條溝壑哪一座崖岩不認識他呢?唱師就想說話,又說不出來,連動一下舌頭的氣力也沒有了,只是出氣一陣急促一陣緩慢,再就是他感覺他的頭髮還在長,胳膊上腿上的汗毛也在長,像草一樣地長,他聽得見炕席下螞蟻在爬,蝴蝶的粉翅扇動了五十下才在空中走過一步,要出窯去。孩子也看見了那隻蝴蝶,起身要去逮,老師用鋼筆在孩子的頭上敲了一下,說:專心!蝴蝶是飛出了窯門,棲在草叢裡,卻變成了一朵花。
第一個故事
《山海經》是一本奇書,它涵蓋了中國上古時期的地理、天文、歷史、神話、氣象、動物、植物、礦藏、醫藥、宗教的諸多內容。共十八卷,其中《山經》五卷,《海經》八卷,《大荒經》四卷,《海內經》一卷。全書記載山名五千三百多處,水名二百五十餘處,動物一百二十餘種,植物五十餘種。今天學卷一,《南山經》的首山系次山系。
我念一句,你念一句。
南山經之首曰鵲山。其首曰招搖之山,臨於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狀如韭而青華,其名曰祝餘,食之不饑。有木焉,其狀如榖而黑理,其華四照,其名曰迷榖,佩之不迷。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麗之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海,其中多育沛,佩之無瘕疾。又東三百里,曰堂庭之山,多棪木,多白猿,多水玉,多黃金。又東三百八十里,曰猨翼之山,其中多怪獸,水多怪魚,多白玉,多蝮蟲,多怪蛇,多怪木,不可以上。又東三百七十里,曰杻陽之山,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白金。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謠,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孫。怪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憲翼之水。其中多玄龜,其狀如龜而鳥首虺尾,其名曰旋龜,其音如判木,佩之不聾,可以為底。又東三百里,曰柢山,多水,無草木。有魚焉,其狀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魼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鯥,冬死而夏生,食之無腫疾。又東四百里,曰亶爰之山,多水,無草木,不可以上。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為牝牡,食者不妒。又東三百里,曰基山,其陽多玉,其陰多怪木。有獸焉,其狀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其名曰猼訑,佩之不畏。有鳥焉,其狀如雞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尚鳥 付鳥 ,食之無臥。又東三百里,曰青丘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青雘。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有鳥焉,其狀如鳩,其音若呵,名曰灌灌,佩之不惑。英水出焉,南流注於即翼之澤。其中多赤鱬,其狀如魚而人面,其音如鴛鴦,食之不疥。又東三百五十里,曰箕尾之山,其尾踆於東海,多沙石。汸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淯,其中多白玉。凡鵲山之首,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其祠之禮:毛用一璋玉瘞,糈用稌米,一璧,稻米、白菅為席。
* *
有什麼要問的?
問:《山海經》的「經」,如《易經》、《道德經》,是經典的意思嗎?
答:不,是經歷。
問:所經之山,怎麼只寫山水的方位、礦產、草木和飛禽走獸呢,又都是那麼奇怪?
答:這是九州定制之前的書呀!那時人類才開始了解身處的大自然,山是什麼山,水是什麼水,山水中有什麼草木、礦產,飛禽走獸,肯定是見啥都奇怪。秦嶺裡不是也有混沌初分,老鼠咬開了天,牛辟開了地的傳說嗎?他們就是那樣認識天地的,認識老鼠和牛的。《山海經》可以說是寫人類的成長,在飽聞怪事中逐漸才走向無驚的。
問:為什麼總有「食之不饑」,「食之善走」,「食之不疥」,「食之無臥」呢?
答:虎豹鷹隼是食肉的,牛馬豬羊是食草的,上天造人的時候並沒有安排人的食物,所以人永遠是飢餓的,得自己去尋找可吃的東西,便什麼都吃,想著法兒去吃,在自然界裡突破食物鏈,一路吃了過來。人史就是吃史。
問:怎麼有了九尾四耳、其目在背的猼訑就「佩之不畏」;佩了鹿蜀就「宜子孫」,類自為牝牡,吃了就「不妒」?
答:或許是佩了猼訑後「不畏」,發現猼訑是九尾四耳,其目在背,遂之總結出耳朵能聽到四面聲音而眼能看到八方的就不會迷惑不產生畏懼。或許是佩之了鹿蜀後生育力強、子孫旺盛,發現鹿蜀是生活在「陽多赤金,陰多白玉」的山上,遂之總結出有陰有陽了,陰陽相濟了,能生育繁殖人口興旺的。或許是食了類的肉「不妒」,發現類是自為牝牡,遂之總結了妒由性生,而雄雌和諧人則安寧。我們的上古人就是在生存的過程中觀察著自然,認識著自然,適應著自然,逐步形成了中國人的思維,延續下來,也就是我們至今的處世觀念。
問:山都有神嗎?是神就祭祀嗎?
答:有一種說法,說是上天創造了萬物,就派神來。
問:祭祀「白菅為席」,為什麼用白菅而不是別的顏色呢?
答:白顏色乾淨,以示虔誠吧。沿襲到現在,喪事也叫白事,穿孝也就是穿白,裹白巾,服白衣,掛白帳,門聯也用白紙。
* *
這不對吧,之所以辦喪事用白布用紙,是黑的顏色陽氣重,人要死的時候,無常來勾魂,如果家裡人都是黑頭陽氣強盛,無常就無法靠近,亡人就可能靈魂飄散,家人們才用白布蓋頭裹身的。鵲又怎麼是山呢,是人呀,老黑的娘就叫鵲。鵲死後我去唱的陰歌,鵲還在入殮著,老黑的爹就渾身抽搐,在地上把自己窩成了一疙瘩,是我趕緊讓他戴上白帽子,他才還醒過來。
老黑的爹是個憨人,一直在王世貞家當長工,一天正在包穀地裡鋤草,突然蝗蟲來了,遮天蔽日的,老黑的爹還往天上看,蝗蟲就落在包穀稈上,頓時只見蝗蟲不見綠色,不一會兒,包穀稈大半截已不見了,殘留半尺高的包穀樁。老黑的爹嚇得跑回家,老婆正在炕上生老黑。老黑身骨子大,是先出來了腿,老黑的爹便幫著往出拽,血流了半個炕面,老黑是被拽出來了,他爹說:這娃這黑的?!鵲卻翻了一下白眼就死了。
老黑實在是長得黑,像是從磚瓦窯裡燒出的貨,人見了就忍不住摸下臉,看黑能不能染了手。
娘一死,老黑和爹都住在了王世貞家,如野地裡的樹苗子,見風是長,十五歲上已經門扇高,肩膀很寬,兩條眉毛連起來,開始跟著爹去南溝裡種罌粟。那時候王世貞正做了正陽鎮公所的黨部書記,和姨太太去鎮上過活了,留著大老婆在家經管田地和山林。大老婆喜歡老黑,每次進溝,總給老黑的褡褳裡塞幾個饃,還有一疙瘩蒜。老黑的爹說:啊給這多的!大老婆說:他長身骨子麼。拉住老黑的手,在手心放一個小桃木劍。桃木劍能避邪。
正陽鎮轄區裡的樹林子多,而且樹都長得高大,竟然有四五十丈高的樟樹和松樹。樹木高大,林子裡就有了㸳牛,野豬,還有熊,也都是些大動物。熊是喜歡在有罌粟的地方出沒,老黑的爹每次去南溝的罌粟地,總是把一副竹筒子套在胳膊上了,再讓老黑也把一副竹筒子套在胳膊上,說遇見熊了,熊會按住人的雙膊嘿嘿笑,笑得要暈過去,人就可以從竹筒子拔出胳膊逃生。爹還說,去了要悄悄的,不要弄出響聲。但老黑快活的是罌粟開花,罌粟的花是那樣豔麗,當太陽在山梁上斜照過來,把這些花映在石壁上,有了五光十色的圖影,他就莫名其妙地興奮,大聲地吼,天上的烏雲肯定要掉下一陣子雨。爹罵起老黑:你遲早會招來熊的!真的到了中秋,他們在罌粟地裡和熊遭遇了,熊是按住了老黑的胳膊,老黑的一隻腳還在踢熊的腹部,爹急喊:裝死,裝死!老黑沒有裝死,但也沒再動,熊就開始笑了,笑得沒死沒活。老黑是睜著眼看著熊笑,直到熊笑得暈過去了,他從竹筒裡拔出胳膊,說了句:笨熊!還要拿刀砍熊掌,是爹拉著他趕緊跑了。
但就在這一次,逃跑的路上,老黑的爹失腳從崖上掉下去,崖三丈高,崖下有一個樹茬,也僅僅那一個樹茬,他的頭就正好砸在上邊,等到老黑跑下去查看,爹怎麼沒頭了?再看,爹的頭被撞進了腔子裡。爹再一死,老黑成了孤兒,王世貞幫著把人埋了,給老黑說:你小人可憐,跟我去吃糧吧。吃糧就是背槍,背槍當了兵的人又叫糧子,老黑就成了正陽鎮保安隊的糧子。
老黑有了槍,槍好像就是從身上長出來的一樣,使用自如。他不用擦拭著養槍,他說槍要給餵吃的,見老鷹打老鷹,見燕子打燕子,街巷裡狗臥在路上了,他罵:避!狗不知道避開,那槍就胃口飢了,叭的放一槍,子彈是蘸了唾沫的,打過去狗頭就炸了,把一條舌頭崩出來。
那些年月,共產黨占據了陝北延安,山外的平原上到處鬧紅,秦嶺雖然還沒有兵荒馬亂,但實施了聯保制,嚴加防範。王世貞到各村寨去訓導,三月二十四日到的番禺坪。番禺坪在莽山上,那裡是一條騾馬古道,常有馱隊和腳夫經過,也正如收穫麥子也得收穫麥草一樣,莽山上的土匪也最多。這些土匪有的有槍,有的用紅布包著個柴疙瘩假裝是槍。還有一些本該是山裡的農民,農忙時在地裡刨土豆,腳夫問:老哥,問個話!回答是:你不是秦嶺人?腳夫說:你咋知道我不是秦嶺的?回答是:秦嶺人四方臉,鑼嗓子,你瘦筋筋的,還是蠻腔。腳夫說:嘿嘿,渴死了哪兒有水?回答是:我葫蘆裡有水,你來喝。腳夫看見地頭果然有裝水的葫蘆,說了幾聲謝,從背簍裡還摸出一個荷包作回報,彎腰取葫蘆時,後腦勺上挨了一鐝頭。挖土豆的取了財物,就勢在地裡挖個坑把腳夫埋了,說:你那腦袋是雞蛋殼子呀?繼續刨土豆。莽山上不安全,王世貞對老黑說:你留點神。老黑梗梗脖子,他的脖子很粗,說:誰搶我?我還想搶他哩!晚上住在番禺坪保長家,王世貞和保長在屋裡喝酒,老黑拿了槍便坐在院子裡警戒,半夜裡夜黑得像瞎子一樣黑,忽然看見院牆頭上有亮點,以為是貓,一槍就打了過去,牆那邊噗咚一聲,有人喊:打死人了!果真是打死了人。村裡幾個閒漢得知王世貞在保長家,又聽說王世貞是個胖子,穿的褲子褲腰要比褲腿長,就趴在院牆頭往裡看稀罕,其中一個嘴裡叼著菸捲兒,子彈從那人嘴裡進去,把後腦蓋轟開了。
三個月後,番禺坪的保長到鎮公所來,說那挨了槍子的人墳上的草瘋長,蓬蓬勃勃像綠焰一樣。王世貞問老黑:你有過噩夢沒?老黑說:沒。王世貞說:你還是去墳上燒些紙吧,燒些紙了好。老黑是去了,沒有燒紙,尿了一泡,還在墳頭釘了根桃木橛。
* *
這後半年,正陽鎮出了三宗怪事。
一宗是茶姑村有個老婆婆,兒子和兒媳在山上打豬草時被土豹蜂螫死了,留下一個小孫子。小孫子一哭鬧,她就把自己的乳頭塞到小孫子嘴裡,她的奶已經乾癟,吸不出奶水,小孫子仍是哭鬧,她不停說:乖呀,聽婆話!小孫子聽不懂,家裡的一隻貓卻聽得多了,叫起她是婆。一次她和村裡人在巷道裡說天氣,貓跑來說:婆,婆。把村人嚇了一跳,覺得貓是災異,背過她就把貓勒死了。當我在茶姑村唱陰歌時,我見到這老婆婆,說起她家貓還很傷心。我離開茶姑村又往三台縣去,她就抱著小孫子跟我去了三台縣要投靠親戚。那期間地裡的包穀苗半人高,下著連陰雨,我們一塊走著,她揹了小孫子,又雙手緊緊抓了腰兩邊小孫子伸出來的腳,不停地嘮叨:把婆脖子摟緊啊,狼就從後邊奪不走了你!我又問起她家那隻貓的事,她說:人有的可以長個豬嘴,有的可以長個猴樣,貓怎麼就不能說人話呢?!我只是笑,看她的小孫子就長了個貓樣,耳朵尖尖的,眼睛突出,動不動兩隻手就搓鼻子。這小孫子後來就落戶在三台縣過風樓鎮,名字叫劉學仁,是公社幹部。
一宗是還在春末,天上就常下流星雨。下流星雨的時候天上一片光亮,地上的人都害怕被砸著,要麼往石堰根下躲,要麼趴在犁溝裡雙手抱著頭。但流星雨全落到了竺山。突然傳出落下來的流星叫隕石,省城裡有收隕石的,於是有人去竺山撿,賺了許多錢。當地一戶姓雷的人也去撿,因為起得早,到了竺山天還未亮,就坐在一個倒塌地上的枯木上吸旱菸。吸呀吸呀,把旱菸鍋子都吸燙了,往枯木上彈菸灰,沒想枯木卻動起來,才知自己坐在一條蟒蛇上。蟒蛇並沒有傷害他,他卻嚇昏了,天明被人發現揹回家,還沒有醒,從此人成了植物。
竺山有了大蟒蛇,山民就圍山搜捕,終於殺了那條長蟲。據說殺蟒蛇的那條溝,草木全部枯死,此後過溝風帶著哨子,還有一股腥味。
還有一宗那就是匡三的事了。現在秦嶺裡到處流傳著關於匡三司令的革命故事,但誰還能知道匡三小時候的事呢?匡三自小就是嘴大,他能把拳頭一下子塞進去,秦嶺裡俗話說嘴大吃四方,匡三的爹卻總抱怨匡三把家吃窮了。他確實吃得多,別人家的孩子一頓吃兩碗小米乾飯,他吃過四碗了還不丟筷子,每頓都是他爹說:夠了!把碗筷奪了去。家裡把什麼都變賣了,全顧了吃喝,日子過不下去了,他爹曾在匡三睡覺時要用繩子勒,但沒有勒死,父子倆從此一塊去要飯。匡三知道爹不愛惦他,他也和爹做對頭,爹說白,他說黑,爹說月亮是圓的,他說是扁的。要飯走到大路口,爹要進這個村子,他偏要去那個村子,意見不統一,便各要各的。村子裡家家有狗,爹遲早拿根棍,匡三不怕狗,狗向他撲,他也向狗撲,狗就搖尾巴不動了。他要飯時常拿人家簷簸上的柿餅或者到地裡偷拔蘿蔔,被人追攆,他把要飯籃子一扔能跳下三丈高的地塄也能跳過齊肩的院牆。到了十三歲,爹死了,臨死前擔心死後兒子會把他埋在河邊省事,但知道兒子和他對著幹,就反話正說:兒呀,爹這氣一嚥,你把爹不要葬到高山上去,捲張席就埋在河邊吧。爹一死,匡三卻稱,十多年了,從未順聽爹的話,這一次就聽爹的吧。匡三把爹用席捲了埋在倒流河邊。秋末河裡發大水,墳被沖得一乾二淨。
這事讓王世貞笑話了半年,他說:生兒要是生這樣的兒,真他娘的不如養頭豬!
其實,王世貞說這話,是他就沒有兒。
因為沒有兒,王世貞才娶了個姨太太。這姨太太曾在戲班子裡幹過,人長得稀樣,還拉一手好胡琴,娶過來仍是多少年了也懷不上,但王世貞一有煩心事,姨太太就給他拉秦腔曲牌。有一回,王世貞和姨太太又在後院的葡萄樹下吃酒拉琴,傍晚天涼,王世貞讓老黑去辦公室把中山服拿來要披上,老黑就去取中山服。中山服是王世貞的正裝,整個正陽鎮也只有他黨部書記穿,老黑取了中山服,忍不住自己穿了一下,還站在鏡子前照,沒想就被姨太太一扭頭瞧見了,當下有些不高興。待老黑把中山服拿來往王世貞身上披,姨太太琴停了,說:撣撣土!老黑說:中山服上沒有土。姨太太說:你身上有土!王世貞不曉得事由,老黑卻心裡明白,忙把中山服從王世貞身上又取下來,撣了幾下,再給王世貞披上,卻也當著姨太太面,給王世貞報告了竺山捕了大蟒蛇的事。王世貞說:有那麼大的蟒蛇?老黑說:用那蟒蛇皮給太太蒙一把二胡多好。王世貞說:是呀是呀!第二天,王世貞帶著老黑要去竺山,臨走時老黑給姨太太說:那可能是千年老蟒蛇哩!姨太太沒說話。王世貞倒說:老黑你看看,太太像不像一株花?!
到了竺山,知道帶頭捕殺蟒蛇的人叫雷布,正是植物人的兒子。老黑一進雷布家,說:喂,書記來了,蟒蛇皮呢?但雷布不在家,炕上坐著個老婆婆給一個老頭子揉搓身子,老頭子昏迷不醒,身子縮得像個嬰兒。出了後門,王世貞看見蟒蛇皮就釘在斜對面的崖壁上。崖壁距後門只有三丈,但崖壁下是條澗,深得丟一個石頭下去,半會才咚的上來響聲。老婆婆攆出來說:那蟒蛇皮不給人的,我兒把它釘在那裡讓他爹魂附體哩。老黑說:你兒咋把蟒蛇皮釘上去的?老婆婆說:先前有吊橋,釘了蟒蛇皮,我兒怕人偷,就把吊橋砍了。老黑就往前走,發現不遠處澗上還橫著一根獨木,這獨木並不是搭上去的,是一棵被雷劈了倒在那裡,已經朽了,長滿著苔蘚和蕨草。
老黑就要從獨木上過,王世貞說:這太危險!老黑說:咱需要蟒蛇皮呀!已跳上獨木,澗裡便往上湧雲霧,老黑身子晃了一下,罵了句:狗日的!蹲下一會兒再站起來,雙手把槍端著來平衡,一步,一步,走過去把蟒蛇皮拿了過來,獨木就咔嚓咔嚓斷了三截掉下澗去。
老黑勇敢,王世貞回到鎮公所要擢升老黑當排長,姨太太不同意,說老黑這人可怕,自己的命都不惜了,還會顧及別人?王世貞說:他是為了我才這麼不惜命的。老黑當了排長,揹上了盒子槍,想到自己過澗時獨木沒斷,過了澗了獨木斷了,自己是命硬,以後恐怕不僅僅當排長吧。
開 頭
秦嶺裡有一條倒流著的河。
每年臘月二十三,小年一過,山裡人的風俗要回歲,就是順著這條河走。於是,走呀走,路在岸邊的石頭窩裡和荊棘叢裡,由東往西著走,以至有人便走得迷糊,恍惚裡愈走愈年輕,甚或身體也小起來,一直要走進娘的陰道,到子宮裡去了?
走到一百二十里遠的上元鎮,一座山像棒槌戳在天空,山是空空山,山上還有個石洞。這石洞太高,人爬不上去,鳥也飛不上去,但只有大貴人來了就往外流水。唱師扳著指頭計算過:當年馮玉祥帶兵北上,經庫峪繞七里峽過大庾嶺翻浙川溝,經過這裡流了一次水,到北京便把溥儀攆出...
目錄
開頭
第一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
第三個故事
第四個故事
結尾
後記
開頭
第一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
第三個故事
第四個故事
結尾
後記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3收藏
13收藏

 17二手徵求有驚喜
17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