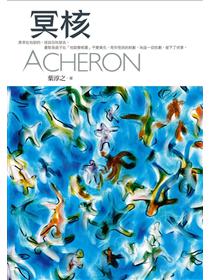最暢銷的法醫小說系列,全球銷售突破一億冊!
翻譯為三十六國語言、熱銷一百二十國
刑事鑑識與法醫探案的先驅,「CSI犯罪現場」相關熱門影集取材原點
超越《屍體會說話》,挑戰鑑識科技極限之作!
那不是一場無名火
而是來自無間煉獄的警告
要奪走我的最愛
要將我的一切付之一炬
報業大亨的農莊突然發生了一場無名火,火勢猛烈迅速燒毀了豪華宅邸,農場裡的名貴馬匹也都葬身火海。事後還在現場發現了一具女性焦屍,臉部嚴重毀損,然而令火場鑑定人員疑惑的是,判斷為起火點的浴室沒有條件引發大火,現場也找不到任何助燃劑的痕跡。此時警方傳來消息,女法醫凱‧史卡佩塔的宿敵,也是她曾協助逮捕的殺人犯嘉莉‧葛里珊從精神療養中心逃脫。掙脫牢籠的她逐步實行策劃多年的報復計畫,滿腔復仇烈火直衝史卡佩塔而來……
縱火案接連發生,甚至可以回溯過去幾年未破的火災命案。相同的模式一再出現--無法解釋的猛烈大火、遭到謀害的焦屍。凶手再次犯案是意料中的事,但這一次卻是致命的一擊……
作者簡介:
派翠西亞.康薇爾Patricia Cornwell
一九五六年出生於邁阿密。她的職業生涯從主跑社會新聞的記者開始,一九八四年在維吉尼亞州的法醫部門擔任檢驗紀錄員。一九八四年~八六年間,康薇爾根據自身的法醫工作經驗寫下了三本小說,然而一開始的出書過程並不順利。
後來,康薇爾聽從建議,推翻原本以男性偵探為主角的構想,改以女法醫為主軸,終於在一九九○年出版了她的第一本推理小說《屍體會說話》,結果一炮而紅,為她風光贏得一九九○年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約翰.克雷西獎。一九九一年,此書榮獲一九九一年美國推理作家協會愛倫坡最佳首作、國際推理讀者協會麥卡維帝獎最佳首作、鮑查大會安東尼獎最佳首作,以及一九九一年法國Roman d’Aventures大獎。
相關著作
《致命暴露》
《死亡的理由》
《波特墓園》
《鑑識死角》
《人體農場》
《失落的指紋》
《殘骸線索》
《肉體證據》
《屍體會說話》
《黑色通告》
《獵殺史卡佩塔》
《肉體證據》
譯者簡介:
王瑞徽
淡大法語系畢,曾任編輯、廣告文案,現專事翻譯。譯作包括雷.布萊伯利、派翠西亞.康薇爾、約翰.波恩等人作品。
各界推薦
得獎紀錄:
最暢銷的法醫小說系列,全球銷售突破一億冊!
翻譯為三十六國語言、熱銷一百二十國
刑事鑑識與法醫探案的先驅,「CSI犯罪現場」相關熱門影集取材原點
作者 派翠西亞.康薇爾(Patricia Cornwell)
文學史上首位甫出道便在一年內囊括五項歐美重量級獎項的作家——
1990年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約翰.克雷西獎
1991年國際推理讀者協會麥卡維帝獎最佳首作
1991年美國推理作家協會愛倫坡獎最佳首作
1991年鮑查大會安東尼獎最佳首作
1991年法國Roman d’Aventures大獎
得獎紀錄:最暢銷的法醫小說系列,全球銷售突破一億冊!
翻譯為三十六國語言、熱銷一百二十國
刑事鑑識與法醫探案的先驅,「CSI犯罪現場」相關熱門影集取材原點
作者 派翠西亞.康薇爾(Patricia Cornwell)
文學史上首位甫出道便在一年內囊括五項歐美重量級獎項的作家——
1990年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約翰.克雷西獎
1991年國際推理讀者協會麥卡維帝獎最佳首作
1991年美國推理作家協會愛倫坡獎最佳首作
1991年鮑查大會安東尼獎最佳首作
1991年法國Roman d’Aventures大獎
章節試閱
班頓在我廚房裡脫去他的跑鞋。我向他跑過去,內心滿是驚恐、怨憎的情緒和可怖的記憶。嘉莉‧葛里珊寄給我的那封信夾雜在大疊郵件和文件裡頭,一直擱在那裡直到剛才我想泡杯肉桂茶喝的時候才發現。這天是六月八日週日下午五點三十二分,我正在位於維吉尼亞州里奇蒙市的家裡。
「我就猜想她會寄到妳辦公室去。」班頓說。
他從容彎下身,脫掉白色耐吉運動襪。
「蘿絲一向不看標示有私人和機密字樣的信件。」我心悸的說。其實他早就知道了。
「也許她應該看,因為妳的仰慕者似乎不少。」他的嘲諷話語凌厲得像會割傷人的紙張。
我看著他蒼白光裸的腳踏在地板上,手肘撐著膝蓋,頭低垂著。汗水沿著他以這年齡來說算是相當健美的肩膀和手臂滴下,我的目光順著他的膝蓋、小腿到了還印著襪子織痕的細小腳踝。他用手指梳了下濕漉的灰髮,往後靠著椅背。
「老天,」他拿毛巾抹著臉和頸子說。「我實在不適合蹚這種渾水,我太老了。」
他深吸一口氣,將逐漸高漲的怒意徐徐吐出。我送他當做聖誕禮物的百年靈不鏽鋼太空系列手錶擱在桌上。他把它拿起來戴上。
「該死,這些人簡直比癌症更可怕。拿給我瞧瞧。」他說。
這封信是用奇怪的紅色印刷字體書寫的,信紙頂端有個長尾羽鳥類的粗糙章印,底下是謎樣的拉丁字ergo,意思是「因此」,想不出有任何意義。我打開那張簡單的白色打字紙,捏著一角放在他面前的法國橡木古董早餐桌上。他沒有碰觸這張很可能成為證物的信紙,只是謹慎瀏覽嘉莉所寫的字句,然後在腦中的暴力檔案庫搜尋著進行比對。
「郵戳是紐約,當然在紐約一直有關於她受審的新聞報導,」我說,加以合理化然後又予以否定。「就在兩週前有一篇精采的文章。因此任何人都可能從那裡得知嘉莉‧葛里珊的名字,至於我的住址,早就是公開資料了。所以說這封信或許不是她寄來的,也許只是某個狂人。」
「也可能是她寄的。」他繼續讀信。
「她怎麼可能從法庭精神醫院裡寄出這樣一封信,卻沒被人察覺?」我說,恐懼由心底深處竄升。
「要知道,在聖伊莉莎白之家、貝勒育之家、米哈德森,或者寇比之家,」他頭也不抬的說,「嘉莉‧葛里珊、約翰‧辛克萊兄弟、馬克‧大衛‧查普曼這些人並不是罪犯,而是病患。他們在蹲感化院或者法庭精神療養中心的時候,照樣享有和我們相同的公民權益,可以上網開設孌童狂留言版,透過電子郵件販賣連續殺人犯作案秘笈,還有寄侮辱信件給首席法醫。」
他越說越激動,憤憤的把信舉到我面前。
「嘉莉‧葛里珊在嘲笑妳,首席法醫大人,F B I 則是在嘲笑我。」他說。
「是F I B。」我含糊回了句。換個時空我或許會覺得這很好笑。
衛斯禮站了起來,把毛巾撂在肩頭。
「就假設是她吧。」我說。
「本來就是。」他篤定的說。
「好吧。那麼這封信的目的一定不只是嘲弄,班頓。」
「當然。她在提醒我們,她跟露西曾經是情人,這是媒體大眾還不知道的,」他說。「可以肯定的是,嘉莉‧葛里珊還沒過足傷天害理的癮。」
我無法忍受聽到她的名字。令我氣惱的是,此時此刻她就在我屋子裡。就好像她和我們一起坐在早餐桌邊,空氣中充滿她那邪惡腐臭的氣息。我回想她露出訕笑、目光灼灼的神情。不知在經過五年和一群精神失常人犯廝混的牢獄生活之後,她變成了什麼模樣。嘉莉並不瘋狂,她從來就談不上瘋狂,她是性格異常、病態型人格、沒有良知意識的暴力分子。
我望著窗外庭院隨風擺晃的日本楓樹,和那道幾乎遮不了鄰居視線的殘缺石牆。電話突兀的響起,我遲疑著要不要接聽。
「我是史卡佩塔醫生,」我對著話筒說,邊瞄著班頓。他還在研究那張紅字信籤。
「嗨,」彼德‧馬里諾熟悉的聲音傳來。「是我。」
他是里奇蒙警局隊長,我和他熟得立即聽出了他是誰。我準備聽壞消息。
「怎麼了?」我說。
「昨晚華倫登的一座馬場發生大火,也許妳已經看了新聞報導,」他說。「馬廄起火,將近二十隻名貴馬匹連同房子全部燒光,燒得一點不剩。」
我不懂他的用意,「馬里諾,你打電話來告訴我火災做什麼?再說北維吉尼亞又不是你的轄區。」
「現在是了。」他說。
我等待他進一步說明,感覺廚房頓時狹窄得無法呼吸。
「A T F 剛剛宣布組成N R T。」他說。
「也就是我們。」我說。
「對啦,妳跟我,明天一早就去。」
每當發生教堂或大樓火災、爆炸案或者和「菸酒槍械管制局」管轄業務有關的災難時,管制局便會成立「國家應變小組」。馬里諾和我並不屬於菸酒槍械管制局,不過在情況危急的時候也常被徵召。我曾經參與過紐約世貿中心、奧克拉荷馬市爆炸案和環球航空八○○班機墜機事件等災難處理工作,也曾經到瓦可協助辨識大衛教派的信徒屍體,以及鑑識被郵彈殺手毀容的受害者遺體。基於這些悲慘經驗,我知道菸酒槍械管制局只有在涉及死亡事件的時候才會召喚我。加上馬里諾,表示案情屬於凶殺性質。
「有多少死者?」我伸手拿電話留言夾板。
「問題不在死了多少人,醫生,而是死者是誰。那座農場的所有人是報業鉅子坎尼斯‧史帕克,別無分號。看來他的命大概不保了。」
「噢,天啊,」我低聲自語,整個世界突然一片暗寂。「確定嗎?」
「至少是失蹤了。」
「可以告訴我為什麼現在才對我提這件事嗎?」
我沒來由地惱火,並且遷怒在他身上。因為維吉尼亞州的所有不明屍體都歸我管,我應該早在馬里諾通知我以前就接獲通報才對。我很氣我的北維吉尼亞辦公室同事沒有打電話到我家裡通知我。
「別責怪費爾法克斯郡的同事了,」馬里諾猜透了我的心事。「是佛奎爾郡要求管制局由這裡接手的,所以就這樣囉。」
我還是覺得不妥,只是情況如此,不能不照辦。
「我猜大概還沒發現屍體吧。」我說,迅速做著筆記。
「猜對了。這個好玩的任務就交給妳了。」
我停頓下來,筆擱在電話留言紙上。「馬里諾,這只是普通住宅的火災,就算有縱火嫌疑而且涉及名人,我不懂菸酒槍械管制局為何會對這案子感興趣。」
「威士忌、機關槍,加上昂貴馬匹交易,這可是大生意哩。」馬里諾回答。
「好極了。」我喃喃唸著。
「是啊,這肯定是場惡夢。消防隊長晚一點會打電話給妳。還有妳最好趕緊打包行李,直升機天亮前就會來接我們。時機不對,一向都這樣。我想妳可以和妳的寶貝假期吻別嘍。」
班頓和我計畫今晚開車到希爾頓海岬去海邊度假一週。今年我們忙得少有機會獨處,而且關係鬧得有點僵。我掛斷電話,不知道該如何面對他。
「對不起,」我對他說。「我想你一定也猜到了,又有重大案件發生。」
我望著他,不知該說什麼。他繼續讀嘉莉的信,沒看我。
「我明天一早就得離開,過幾天我或許能去島上找你。」我說。
他沒聽進去,因為他不想聽這些。
「請你諒解。」我說。
他沒聽見似的,我知道他非常失望。
「妳最近在處理那些殘骸案件,」他看著信說。「愛爾蘭和本地的幾樁肢解案。信裡寫的鋸斷骨頭。也許她邊幻想著露西邊自慰,每晚在被子裡達到好幾次高潮。誰知道呢?」
他的視線停在信紙上,似乎在自言自語。
「她是在告訴我們她們兩個依然有關係,嘉莉和露西,」他繼續說。「她利用我們是企圖讓自己脫離干係,表示那些犯罪案件發生的時候她並不在場,是其他人犯的案。多重人格,既不獨特也沒什麼創意的瘋子。我原本以為她很特別的。」
「她絕對有能力面對審判。」我回了句,又惱火起來。
「這我們都很清楚,」他拿起一瓶愛維養礦泉水喝。「小露露這稱呼又是怎麼來的?」
我有些結巴,「是她進幼稚園以前我給她的暱稱,後來她漸漸的不喜歡人家這樣叫她,但我有時候還是會說溜嘴。」我停頓,回想她那時候的模樣。「她大概把這暱稱告訴了嘉莉吧。」
「這並不奇怪,有一陣子露西和嘉莉的確很親密,」衛斯禮點出事實。「她是露西的初戀,我們也都知道人永遠不會忘了初戀情人,無論那個人有多爛。」
「大部分人不會找個瘋子當初戀情人。」我說,依然無法相信我的外甥女露西這麼做了。
「瘋子就在我們當中,凱,」他又開始說教。「搭飛機時坐在妳身邊的那個散發智慧和魅力的人,排隊時站在妳後面的人,跑到後台找妳的人,在網路上和妳搭訕的人。他們就像兄弟姊妹、同學、兒女、情人,看起來跟妳我沒兩樣。露西沒得選擇,她根本不是嘉莉‧葛里珊的對手。」
後院的草坪長了太多苜蓿。今年春天冷得不太尋常,對玫瑰再適合不過了。花朵低垂著,在驟風中顫抖,淺色花瓣紛紛落地。曾經擔任調查局犯罪心理側寫小組組長,現在已退休的衛斯禮繼續他的分析。
「嘉莉想要高特的照片,犯罪現場照片、解剖照片。妳把照片給她,相對的她會告訴妳一些妳可能遺漏的案情細節和驗屍關鍵點,可能對下個月開庭時的檢察起訴有幫助。她在奚落妳,認為妳可能有所疏漏,而且多少和露西有關。」
他的老花眼鏡摺疊放在他的餐盤巾旁邊,他拿起來戴上。
「嘉莉希望妳去看她,去寇比看她。」
他凝視我,一張臉緊繃著。
「是她沒錯。」
他指著那張信紙。
「她在故弄玄虛。我知道,這是她的作風。」他極度疲憊的吐出這句。
「黑暗之光又是什麼意思?」我猛的站起,一顆心忐忑著。
「血。」他篤定的說。「妳刺中高特大腿的時候,切斷了他的腿部動脈,使得他流血致死,要不也會被列車輾死。鄧波爾‧高特。」
他再度摘下眼睛,異常激動。
「只要嘉莉‧葛里珊在,他就在,這對邪惡雙胞胎。」他補充說。
事實上他們並非雙胞胎,只是同樣染了頭髮,而且剃得短到緊貼著頭皮。我最後一次在紐約看見他們的時候他們瘦得像尚未發育,穿著充滿陽剛氣。他們共謀犯下凶殺案,我們在寶華利街逮住了她,他則死在地下鐵道裡,死在我手上。當時我根本無意見他、和他交談,或者跟他有任何接觸,因為我的職務並不包括了解罪犯心理,更別說為了法理正義而殺人了,但這是高特想要的。他安排了這結局,因為我殺了他就等於和他永遠連結在一起。我這輩子再也擺脫不了鄧波爾‧高特,儘管他死了已有五年之久。我腦中依然殘留著他血跡斑斑的屍體碎片散落在亮閃的不鏽鋼鐵軌上,老鼠從陰暗角落竄出舔食他鮮血的畫面。
惡夢中,他冰冷的藍眼珠放射著分子般的虹彩,隆隆列車聲夾帶著足以遮蔽滿月的刺眼白光。在殺了他之後的幾年當中,我一直避免替火車罹難者驗屍。由於我主管維吉尼亞州的法醫人事,有權將案件指派給我的副手們去執行。實際上我也這麼做了。我無法用平常心去看待解剖刀的森冷刀鋒,因為他布下陷阱,讓我用解剖刀刺殺他,而我也真的這麼做了。我經常在人群中看見酷似他的放浪男女,夜晚睡覺時我總是把槍放在身邊。
「班頓,你何不去洗個澡,然後我們來商量度假的事,」我說,試圖驅散那些令人難堪的記憶。「單獨在海邊悠閒的看書、散步,你會喜歡的。你不是愛死了越野單車?也許擁有一點個人空間對你是件好事。」
「必須讓露西知道,」他也站了起來。「雖說嘉莉目前受到拘禁,可是她仍在製造更多麻煩把露西拖下水,嘉莉在這封信裡頭表明得非常清楚。」
他走出廚房。
「她還能製造什麼麻煩呢?」我說,淚水湧上喉嚨。
「把妳的外甥女拖上法庭,」他停下腳步說。「公諸媒體,登上紐約時報、美聯社,甚至內幕傳真、今夜娛樂,鬧得全球皆知。聯邦調查局探員和瘋狂連續殺人犯是同性戀情侶……」
「露西已經離開調查局,不再理會他們的偏見、謊言和急於維護調查局偉大聲譽的媚俗心態。」我濕了眼眶。「她已經一無所有,他們再也找不到方法可以打擊她了。」
「凱,這事不只跟調查局有關。」他說,疲憊已極的聲音。
「班頓,別說了……」我哽咽著說。
他倚在客廳通道門邊。客廳裡燃燒著爐火,因為這天氣溫低於華氏六十度。他不喜歡我用這種態度說話,不想深入自己靈魂的陰暗面。他不想提嘉莉可能會有的惡毒行為,當然一方面也因為他擔心我。因為我必須出庭為嘉莉‧葛里珊的罪行作證,而我又是露西的阿姨。我做為證人的可信度勢必受到質疑,我的宣誓和名譽必然也隨之掃地。
「我們出去吃晚餐吧,」衛斯禮的語氣柔和許多。「妳想去哪裡?拉博蒂?還是到貝尼餐廳烤肉喝啤酒?」
「我去把湯解凍,」我抹著淚水,轉換口氣說。「我不怎麼餓,你呢?」
「過來。」他溫柔的說。
我窩進他懷裡。我們親吻時我發現他帶著鹹味,同時又一次驚訝於他身體的結實觸感。我把頭靠著他,他下巴的鬍渣摩挲著我的頭髮,顏色就像我暫時無緣見到的海灘一樣潔白。短時間內我們將無法在沙地上並肩漫步,或者在拉波拉和查理餐廳共進晚餐了。
「我最好去看看她到底有什麼要求。」我在他溫暖汗濕的頸窩裡說。
「想都別想。」
「高特的驗屍工作是在紐約進行的,我沒有照片。」
「嘉莉非常清楚法醫會如何處理高特的屍體。」
「既然這樣她為什麼還向我要?」我喃喃說著。
我倚著他,緊閉眼睛。他稍稍停頓,吻了下我的頭頂,然後輕撫我的頭髮。
「妳也知道為什麼,」他說。「她想操縱全局,把妳耍得團團轉,她最擅長這種事。她要妳替她取得照片,好看見高特面目全非的模樣,如此一來她便可以擺脫和他的關係。目前她正懷著鬼胎,妳要是回應她的需求,那就太不智了。」
「她所說的GKSWF─是什麼?電腦帳號之類的嗎?」
「我也不知道。」
「還有雉雞之地?」
「不懂。」
我們經常在這棟裡外完全由我自己設計的房子裡待著。班頓除了參與國內外重大犯罪案件的側寫工作以外,其餘時間幾乎都給了我。我知道他聽不慣我老是把我、我的掛在嘴上,儘管他也明白我們並未結婚,沒有任何一樣東西是我們共同擁有的。我已經過了人生的中點,不可能在法律上讓任何人,包括我的情人和家人在內,共享我的財物。或許這樣很自私,或許我就是個自私的人。
「明天妳走了我怎麼辦?」衛斯禮終於肯面對這話題。
「開車到希爾頓海岬然後去購物,」我回答說。「記得買足夠的黑布希和蘇格蘭威士忌。要買比平常更多的量,還有防曬係數三十五和五十的防曬乳液,還有南卡羅來納的大核桃、番茄和維答利亞甜洋蔥。」
淚水再度湧上我的眼眶,我清了清喉嚨。
「我會盡快搭飛機去跟你會合,不過我不確定華倫登的案子多久會結束。以前也發生過這種情況,我們都經歷過了,不是你沒空就是我無法配合。」
「我想問題出在,我們的生活實在不像樣。」他在我耳邊說。
「這也是我們自找的。」我回說,同時有股難以抗拒的衝動想要睡覺。
「也許吧。」
他低頭吻我,雙手溜到他最偏愛的位置。
「我們可以先上床再喝湯。」
「這次審判肯定有不妙的事發生。」我說。希望我的身體能對他起反應,可是很難。
「為了她的案子,我們全部都得回到紐約,調查局、妳、露西。沒錯,我相信五年來她一直在想著這件事,而且竭盡所能的企圖製造大麻煩。」
我離開他的懷抱,嘉莉那張尖銳憔悴的臉孔突然從我腦中的某個死角浮現。我記得那晚,在調查局位於匡提科的國家學院那座射擊練習場附近,外貌出眾的她和露西在野餐桌邊抽菸。我至今仍可以聽見她們嬌俏的相互細聲挑逗,看見她們纏綿的親吻,兩手在髮際穿梭。我記得我渾身不自在,迅速悄悄溜走,避免讓她們察覺我看見了那一幕。從此嘉莉開始進行毀掉我外甥女一生的計畫,如今這齣光怪陸離的戲已到了尾聲。
「班頓,」我說。「我必須開始整理行李了。」
「相信我,妳的行李沒問題。」
他急切的脫去我的一層層衣服,皮膚除外。他時常在我和他不同調的時候需要我。
「我無法向你保證什麼,」我細聲說。「我無法告訴你一切都會順利沒事,因為事實並非如此。那些律師和媒體不會放過露西和我的。我們會被糟蹋得體無完膚,而嘉莉則會獲判無罪。就這樣!」
我將他的臉捧在掌心。
「真相和公理,美國式正義。」我做著結論。
「別說了。」
他靜止不動,定睛凝視著我。
「別又挑起事端,」他說。「妳以前不會這麼憤世嫉俗的。」
「我不是憤世嫉俗,挑起事端的人也不是我,」我說,莫名的氣憤起來。「我沒有找上一個十一歲的小男孩,切掉他大片肌膚,然後把他赤裸裸丟在垃圾收集箱旁,頭部還嵌著顆子彈。接著又殺了一個治安官和一名獄警。接著是他的雙胞胎妹妹珍恩。記起來了嗎,班頓?還記得聖誕節前夕的中央公園嗎?雪地裡滿布腳印,噴水池被她冰凍的鮮血給染紅了!」
「我當然記得。當時我也在場,所有細節我和妳一樣清楚。」
「不對,你沒有。」
我一把抱起我的衣服,憤憤走開。
「你沒有把手伸進他們殘破的軀體裡,碰觸、測量他們的傷口,」我說。「你沒聽見他們死後所說的話。你沒看見那些家屬的臉孔,他們擠在我那狹小寒酸的辦公室裡,只等我宣布令人心碎的壞消息。你沒看見我所看見的那些,你沒有,班頓‧衛斯禮。你看見的是乾乾淨淨的檔案夾、光滑的照片跟冷冷的犯罪現場。你的時間大都花在那些凶手身上,而不是被他們剝奪了生命的人身上。也許你也睡得比我安穩吧,也許你還會做夢,因為你不怕做惡夢。」
他不發一語離開我的屋子。我說得有點過火,這些話既不公道又刻薄,而且也並非事實。衛斯禮從沒安穩睡過,經常翻來覆去的發出囈語,被子被冷汗浸透。他很少做夢,或者他已經學會忘掉夢的內容。我用鹽和胡椒罐壓住嘉莉那封信的四角,把它的摺痕攤平,她那些嘲弄和令人不安的字句成了不可隨意碰觸侵犯的證物。
用寧海德林反應劑或者盧瑪探照儀也許可以找出她留在這張廉價白紙上的指紋,信的書寫模式和以前她寄給我的信件比對,我們便可以證明她在即將接受紐約高等法院審判的關鍵時刻寫了這封充滿惡意的信件。陪審團將會明白,她在經過五年用人民納稅錢支付的精神治療之後並沒有絲毫改變。她全然沉迷於自己的作為,沒有一點悔意。
我知道班頓還在附近,因為我沒聽見他那輛BMW離去的聲音。不久後,發現他站在樹蔭下,眺望著詹姆士河的寬廣岩岸。河水酷寒,冰凍大地和卷雲的色彩在陰沉的天空下顯得晦澀不明。
「我回到屋裡以後會馬上出發到南卡羅來納。我會把公寓整理乾淨,然後去替妳買蘇格蘭威士忌,」他說,沒有回頭看我。「還有黑布希愛爾蘭威士忌。」
「你可以明天再走,」我害怕靠近他。他的一頭銀髮被偏斜的天光映得發白,一陣風將它攪得蓬亂。「我明天一早出發,你可以跟我一起走。」
他沒說話,抬頭望著一隻白頭鷲,我走出屋子以後牠就一直跟著我。班頓穿著件紅色運動夾克,可是那件潮濕的慢跑短褲還是讓他冷得發抖,兩手緊抱在胸前。他的喉頭隨著吞嚥動作起伏,痛苦從他內心某個只有我有權窺探的隱密角落放射開來。像這種時候我總不懂他為何一直守著我。
「別奢望我一成不變,班頓。」我柔聲說,這話自從我和他相愛以來說過不下百萬次。
他依然沒答腔。河水有氣無力的滾向下游,發出單調的傾瀉聲響,不情願的朝著暴猛的水壩挨近。
「我能得多少就要多少,」我解釋說。「我比大多數人需索得更多。別對我期望太高,班頓。」
那隻白頭鷲在高聳的樹頂盤旋。班頓終於開口,委屈似的。
「我也比一般人需索得更多,」他說。「因為妳也是這樣。」
「沒錯,這是相對的。」
我走向他,從他背後伸出手臂,隔著層光滑的紅色尼龍夾克環抱住他的腰。
「這點妳再清楚不過了。」他說。
我緊摟著他,用下巴磨蹭他的背脊。
「妳的鄰居在看我們,」他說。「他站在落地窗後面。妳知道妳這個高級社區裡有個偷窺狂嗎?」
他拿兩手蓋住我的手,不為什麼的逐一扳弄我的手指。
「話說回來,要是我住這裡,一定也會窺探妳。」他帶著笑意補充了句。
「你本來就住這裡。」
「不對,我只是在這裡過夜。」
「來談談明天早上的事吧。按慣例,他們大約會在五點鐘到眼科醫療中心接我,」我對他說。「所以我四點鐘就得起床……」我嘆了口氣,心想我的生活是否就這麼繼續下去。「你得留下來過夜。」
「我才不要四點鐘起床。」他說。
班頓在我廚房裡脫去他的跑鞋。我向他跑過去,內心滿是驚恐、怨憎的情緒和可怖的記憶。嘉莉‧葛里珊寄給我的那封信夾雜在大疊郵件和文件裡頭,一直擱在那裡直到剛才我想泡杯肉桂茶喝的時候才發現。這天是六月八日週日下午五點三十二分,我正在位於維吉尼亞州里奇蒙市的家裡。
「我就猜想她會寄到妳辦公室去。」班頓說。
他從容彎下身,脫掉白色耐吉運動襪。
「蘿絲一向不看標示有私人和機密字樣的信件。」我心悸的說。其實他早就知道了。
「也許她應該看,因為妳的仰慕者似乎不少。」他的嘲諷話語凌厲得像會割傷人的紙張。
我看著他蒼白...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