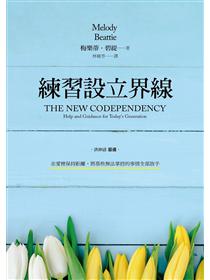VIDEO 誰說愛的形式只能有一種?
誰定義了女子該有的模樣?
十六、七歲的你/妳,在煩惱什麼呢?
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散文類教師組優選得主、
新銳作家黃庭鈺,最溫柔的女性反骨書寫
耽讀青春時光之作——
李欣倫(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作家)
許悔之(詩人.有鹿文化社長)
專文盛讚
蔣勳 推薦
「這一代的青春,比我想像的勇敢許多,享受而不耽溺,憧憬而且虔誠。」
——黃庭鈺
嗨,女孩
我想對妳說說話
說說星空和微風裡的事
妳在太空中也會感到孤獨嗎
還是,妳也落下成為了地上的一顆星
勤勞筆耕不懈的黃庭鈺,另一身分為中學國文老師,與學生們的關係緊密得如朋友、如姊妹。她一面從學生身上看見了自己過往青春年華的影子,一面心繫女孩們未來人生的際遇。遂以女校裡女老師的角色,反思自身,回溯過去:少女求學時期的青澀,投入教甄戰場的熱忱,競爭對手突如其來的無禮電話,初執教鞭的忐忑,養育孩子的甜蜜與迷惘,和關於肉身、關於自我將何去何從的探問……
課堂除了說文解字、考試,一位教師究竟還能帶給學生什麼成長的養分?從女人走回女孩,她懂,那些深埋於細胞底部的黑洞。身為一位女夫子、創作者,黃庭鈺不說教、不批判、不張狂,透過最靠近少年少女的心事角度,以溫婉的筆寫下最真誠的叮嚀、最溫暖的支持,與最體貼的祝福,領你看看世界的靜美與殘缺。
從女孩到女人,她寫下了微塵女子的生命真情
從台下到台上,她如友如姊指引學子泅泳於青春
■輯一,我想對妳說說話
課業壓力、戀愛人際煩惱、家庭經濟問題……青少年少女的心事,由黃庭鈺為妳傾聽、解憂。愛的形式不會只有一種,年輕的妳,其實不需要急著填滿青春的靜寂與空白。
■輯二,當我成為一名教師
投入教甄的沙場,順利取得教鞭,黃庭鈺最害怕的是把孩子的思想、行動捏在手裡,始終不肯放手的大人。孩子真的是父母的孩子,還是父母自我滿足的工具?
■輯三,在太空中會感到孤獨嗎
這世界雖不允許我們有病,但是如果偶有永夜,請你擁抱我的黑,好嗎……七篇散文悄聲說內心的夢魘與黑洞。
■輯四,星空和微風裡的事
寫記憶,寫生活,寫生命中如溽暑般黏人的痛苦與輕薄短小。命運的結局早已寫好,我們專心演繹自己的劇本。
■輯五,每個女子都是地上一顆星
一位女子該擁有什麼樣子?所謂的幸福又該有何樣子?墜入情愛的女子,就如地上的星,燃燒自己的光芒。
作者簡介:
黃庭鈺
章節試閱
【內文節選一】
【內文節選一】
推薦序
【推薦序1】
【推薦序1】
作者序
【後記】
【後記】
目錄
推薦序 像她這樣的一個女(夫)子──讀《時光走向女孩》◎李欣倫
推薦序 像她這樣的一個女(夫)子──讀《時光走向女孩》◎李欣倫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 退換貨原則 。
 7收藏
7收藏

 3二手徵求有驚喜
3二手徵求有驚喜



 7收藏
7收藏

 3二手徵求有驚喜
3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