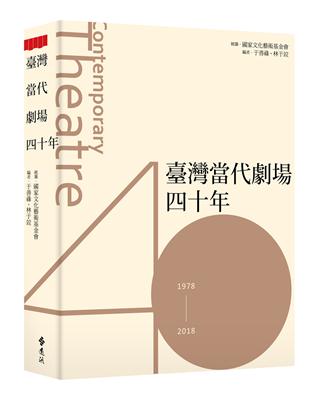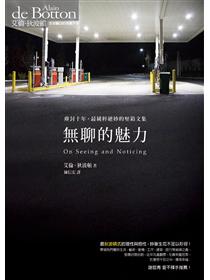行走劇場四十年的會心體驗 吳靜吉
一、開場
1.重建臺灣藝術史:鄭麗君部長的心戰喊話
文化部鄭麗君部長提出「重建臺灣藝術史」的主張,我便順水推舟,將講題定為「行走劇場四十年的會心體驗」,希望借此分享個人涉足劇場邊緣的些許經驗。
二十二年前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簡稱國藝會)成立,當時李登輝總統曾召見遠流出版公司王榮文董事長和我。他表示到國外訪問時,多數友邦都會贈送圖文並茂的藝術史,讓讀者透過精美和淺顯易懂的圖文了解一個國家。他希望王董事長和我能完成這項任務。當時王董和我曾經討論多次,但因為這項工作需要一筆可觀的經費,而且不容易募到資金,最後也就不了了之,但這個工作一直存在我心頭。
在這個論壇策辦的發想時期,與會者也斟酌該用「現代」劇場還是「當代」劇場。總而言之,這次希望用「當代劇場」為先例,日後能夠擴散到傳統戲曲、音樂、舞蹈和視覺藝術等其他藝術領域,一起建構臺灣藝術史。
2.國藝會補助歷史反思
二十二年後,國藝會也在思考長期接受政府補助,是否有益於團體發展?還是未獲補助反而表現得更好?我就以「林曼麗董事長的臺灣高鐵藝術元年——從時間到空間」為例,反思過去類似的活動。當年游錫堃擔任臺北市捷運局董事長時,召集許多人(包括邱坤良和我)提供意見。大家的共識是每一站都可藝術化或轉化為可以展演的場所,藉由藝術的生命力來協助並擴展至全臺灣。第一站就選定臺北藝術大學附近的關渡站。後來游董事長到行政院擔任副院長、再到總統府擔任祕書長,最後擔任行政院長。很可惜地,這項計畫就沒有繼續進行。這是從歷史的時間觀點來看,再從空間的觀點來看,中華管理發展基金會最近正在嘗試建構「臺灣創新地圖」,我們發現很多人回到家鄉做小型的表演或藝術空間或藝廊,或經營餐廳,餐廳裡也成為展演的空間,這都是我們今天可以做的「藝事」。
3.生命故事、文化底蘊與生命年表
我常常想「我一生當中活著有意義嗎?」出生時每個人都是孤單的,即使是雙胞胎亦然。死去時,最後的棺材裡也還是一個人,所以生跟死其實都是孤單的。
蘭陵劇坊這次演出的《演員實驗教室》,其中趙自強講的生命故事跟他的外公有關。他的外公還不到四十歲就是中將,這樣的一個人,晚年時配偶(外婆)過世,有一位女士陪伴中將的外公,許多親人都認為她只是要騙老兵的錢,搶外公的財產。趙自強的外公說他的財產早就花光,最後講了一句:「我只是孤單……」
於是我拜託趙自強凸顯「孤單」,要他「把這個孤單的訊息傳遞出去」。英國政府今年一月任命一位「孤單大臣」,因為英國六千六百萬人口中有九百萬人經常或總是感覺寂寞孤單,孤單這個字是lonely。找一個人來擔任這樣的部長,十分有趣。我雖然八十歲了,如果政府要成立這個部會,我願意擔任部長(當然是自嘲了)。
我覺得人生是有趣的,生與死之間漫長的旅程,必須創作、必須快樂、必須發揮創意、必須參與,而且要經常發揮團隊精神。在團隊合作時,會發現每一個生命故事的發展過程,都有其文化底蘊,以及影響生命故事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元素。
從2004年開始,我在政大EMBA的「領導與團隊」課程中,第一個作業就是請二百多位學生書寫他們的「個人成長年表-生命故事」,這和流水帳式自傳不同。成長年表是記述個人從出生到現在每個成長關鍵,以及關鍵在當時如何變化。此外,還有當時臺灣和世界的變化,也都有其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很多同學在尋找過去的生命故事時,會發現成長關鍵的確與彼時的文化氛圍和政治環境關係密切。這些成長年表中的片段故事就成為另一門課——「創意、戲劇與管理」的創作素材。
因此,我想以生命年表的方式,來談談我和劇場的關係。
二、行走劇場四十年的萌芽初體驗——歌仔戲和話劇的克服害羞體驗
我最早萌芽的體驗是什麼?我向來害羞,只是小時候特別害羞,害羞到跟爸爸或其他權威講話都會很緊張。太痛苦了,所以很想克服。我是怎麼做的呢?某次正好看到野台歌仔戲《樊梨花和薛丁山》演出,兩位主角一見鍾情,四眼相對,眼睛眨都不眨,完全不害羞。這讓我非常羨慕,希望日後能和他們一樣,在人群中毫不緊張。我當下以為上台演歌仔戲會有治癒害羞的作用,而開始對戲劇產生興趣,期許自己有機會上台表演以克服害羞,和群眾與權威溝通毫不焦慮臉紅。雖然壯志未酬,但仍會繼續努力。
1.第一次參加戲劇演出——小學三年級演花木蘭父親,學會觀察、模仿、轉化和「自嘲」
我小學一年級到五年級都念公館國小。三年級時,學校舉辦唯一一次的全校遊藝會,活動很多,包括舞蹈和戲劇表演,我們從課本裡尋找演出的題材,決定由小三扮演《花木蘭》課本劇。老師挑選同學時,以「能把台詞背得很好」的同學優先,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位長得比較可愛的同學,就男扮女裝扮演花木蘭,我看起來比較黑醜又憨厚,老師便推派我扮演花木蘭的爸爸。之後,我便開始仔細觀察鄰居爸爸們的共同行為,發現最主要的特徵就是翹二郎腿和抽菸,祖母因為信任我,就借菸和火柴給我。
演出時,心裡一直盤算著抽菸一事,所以我反而不緊張。時機到了,很自然地拿出香菸並點火,但我一抽就嗆到,台下笑成一團。其實我拿出香菸時,觀眾都張大眼睛、詫異開口,覺得一個小孩子怎麼可以公開抽菸?等到我被嗆到,他們才知道原來我是在演戲。那個時候我發覺運用自嘲或暴露自我弱點,可以成為喜劇來源。這次我敢上台演講,就是在暴露我自己的弱點。
2.表演教學的興趣——從小三時教六年級學姐舞蹈啟動
這兩件事情對我影響很大,之後我漸漸獲得較多戲劇演出的機會。另一個經驗,也是三年級那次的遊藝會,二姑高我三年,讀六年級,她們班女生負責舞蹈節目。依慣例,我每天都等她練完再一起回家。有時老師不在,學姐們忘記舞步時,因為我每天都相當投入在旁邊觀看,竟然記得所有舞步,所以我就教她們,而她們也很快就學會了。但一聽到老師的腳步聲,我們都會各就各位。在這個情況下,我知道我是可以當老師的,而且可以教舞蹈或戲劇等等。
3.編、導、演作的探索—家家酒的演化——在廟裡上課無聊時
之後學校因風災受損,暫時搬到廟裡上課,那個地方大家「下雨天打孩子閒著也閒著」,我就馬上「豬八戒賣肉——就地取材」,把那間廟裡的東西拿出來當道具,開始編導讓大家合演一齣戲。小孩演戲時通常都喜歡模仿老師,演出過程和結果能凝聚同學們,我也因此領悟,如果有機會,我是可以創作的。
4.在明尼蘇達讀書時,「儉腸凹肚」為何事?瑪莎.葛蘭姆和校內外演出
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唸書時,最有趣的一件事是我告訴自己,每天吃滷蛋配辣椒醬油,要把錢省下來買票看演出。記得有一次我買了第一排最貴的票,去看現代舞先驅瑪莎.葛蘭姆(MarthaGraham)的《哀慟》(Lamentation),這個作品力量很大,令我非常震撼,我在第一排會不自覺地往後退縮,給我很深的印象,也讓我親身體悟表演的感染力量有多強大。
三、行走劇場四十年的因緣際會——落腳LaMaMa的走運
1.為什麼預計在美國待兩年之前一定要到紐約
在回臺灣前我決定要滿足願望,去紐約體驗舞蹈和戲劇。戲劇不是我的本業,我心想,回臺灣後,如果當教授還搞劇場,一定會被認為是不務正業。
紐約的經驗是第二階段,那時我二十八歲,已經畢業但還差半年才能拿到正式的博士文憑,我先在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CUNYQueensCollege)任教,次年轉到耶西華大學(YeshivaUniversity)繼續教授教育心理學。既然在紐約,一定得把握機會看表演和參與演出。當時紐約有兩份報紙是主要藝文資訊來源,一是《紐約時報》(NewYorkTimes),一是《村聲》(VillageVoice)。《紐約時報》大多是報導正式的藝文活動資訊,像歌劇等等;《村聲》是周刊,報導許多外百老匯或外外百老匯(OffOffBroadway)等《紐約時報》比較不會著墨的內容。
我很想了解「到底什麼是OffOffBroadway」,抱持「山不來就我,我來就山」的心情,到了周六晚上,我必去藝術界人士聚集的格林威治村,他們常在演出後去那。有天我還沒決定要看什麼戲時,遠遠看到一個長髮及腰的熟悉面孔,原來是我小學和中學同學——葉清。我們久未見面,他從很遠就看到我,接近時開心地伸手抱我,我馬上蹲低讓他抱空,覺得自己沒有那麼開放,他大笑著說:「你看,我就知道到了美國你還是很保守。」他的朋友們都覺得我們倆都很會演戲,我那其實不是演戲,而是真情流露。
葉清原本要當銷售員,但他不知道該怎麼做,就學戲劇來增強銷售技巧。他的頭髮很長很獨特,被劇團的導演選上,說「你來獨白一段開場白」。葉清演出時,辣媽媽實驗劇團(LaMamaExperimentalTheatreClub,LaMaMaETC)的非裔創辦人艾倫.史都華(AllenStewart)正好在場。她覺得葉清深具潛力,邀請葉清到辣媽媽劇團,艾倫說:「我不能提供薪水,但可以提供免費的場地和很多協助,甚至如果你製作戲劇,也可以負責幫你完成。」
2.意外且幸運落腳LaMaMa,合創AsianAmericanRepertoryTheatre(LaMaMaChinatown)
因為要做戲才有經費來源,葉清就邀請我進入辣媽媽劇團。當時紐約人本主義心理學正夯,壓抑不敢擁抱的人,也開始擁抱;不敢講自己故事的人,也開始講故事,這是第一個因素。第二是反越戰的時代思潮。我們兩個想創化熟悉的傳統故事,述說成現代版的議題,思考以「潘金蓮」高度活潑的角色特性來表現男女性別、階級差距和文化隔閡的主題,最後決定以潘金蓮為故事主軸,這個劇叫做《餛飩湯》(WantonSoup)。為什麼取名WantonSoup呢?因當時在紐約的中國城餐廳裡,餛飩湯是點菜率非常高的餐點,也成為彼此共同的生活語言。《餛飩湯》故事敘述來自西方和東方的夫妻和小孩,Wan是丈夫的名字,Ton是太太的名字,小孩統稱為Soup,以反映上一代的權威導向、不自由和戰爭以及下一代的世界一家。比喻當時多元種族社會與世代衝突的美國環境,以及不同種族夫妻與混血孩子的和平共處。
3.《WantonSoup》創造了機會,讓來自臺灣的鄉下人遇見美國華人的文化人,遇見紐約文化人、日本劇人、聯合國大使
我們用即興創作的方式開始排練並順利演出,《紐約時報》刊登了半版的報導,《村聲》也有報導,都給予讚賞與好評,甚至有製作人主動聯繫我們,表示想把這齣戲推到百老匯繼續演出。
當《紐約時報》的ElenoreLester記者採訪時,我因為怕被學校發現「不務正業」而失去工作,希望她不要寫出我的本名(我的名字的英文是JINGJYIWU,在演出資料上我用假名Gin-GeeWOO)。結果她還是寫了我的本名,甚至報導我任教的耶西華大學。因為她是猶太人,很尊重從事劇場工作的人,也認為這是很好的事情,但我當時並不知道。
第二天我進到學校,遠遠就看到同事和學生站在布告欄前看《紐約時報》,我嚇得要死,趕快跑到辦公室準備整理東西回臺灣。意外的是,他們都跑來恭喜我。有一位同事雅各(PaulJacobs)教授跟我說,他曾經寄劇本到辣媽媽劇團,都沒有收到回應,追問我「要如何才能加入?」後來許多人把我當成資訊來源,問我「如何進去?」我說「我是糊里糊塗進去的。」
這次演出對我個人產生了許多影響。第一個影響是因為我教育心理學和創造力的背景,再加上辣媽媽的劇場知名度,就有一些教育單位聯繫我,希望能結合教育文化、戲劇舞蹈和創造力來開設工作坊,這些邀約從幼稚園到中學、大學等。這些工作坊的經驗也幫助我豐富後來蘭陵劇坊的訓練課程。
其次,因為報紙的報導,來自宜蘭鄉下的我,突然間被一些華人認識,其中有臺灣知名的藝術家,也有機會和來自臺灣的藝文人士像是楊牧、施叔青和姚一葦等交流。作家於梨華(她知名的作品是《夢回青河》)寫信給我,說她看到《紐約時報》的報導,聽說我在紐約學舞,因為她認識一位年輕有為的小說家,想到紐約跟瑪莎.葛蘭姆學舞蹈,希望我能夠幫助他。我就是因為這樣認識林懷民。之後,我們就經常見面。
還有殷允芃說「你這個人看起來不像戲劇界的人,怎麼會闖進LaMaMa,還有《紐約時報》來報導?」希望找機會讓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也覺得很慚愧,但覺得能分享經驗是件好事,也就分享了我怎麼糊里糊塗進去辣媽媽的過程。
第三個效應,是當時在紐約的亞裔美國人來找我們,他們努力地想在百老匯發展,卻一直苦無機會,看到不知道哪裡冒出來的我們,居然可以被《紐約時報》大篇幅報導,希望我們能幫忙。辣媽媽的艾倫問我:「靜吉,你們要不要組一個團?我可以幫你們向基金會申請經費。」於是,在艾倫的支持下,我們成立亞美劇場(AsianAmericanRepertoryTheater),有許多亞裔成員,包括韓國人和柬埔寨人等。艾倫暱稱之為「辣媽媽中國城」(LaMaMaChinatown),是以Chinatown的特色來命名。她幫忙申請到經費,讓十個團員每人每周五十美元,一個月共二百美元的費用。辣媽媽是頂尖的實驗劇團,現在非常知名的極簡音樂(MinimalMusic)大師菲利浦.葛拉斯(PhilipGlass)同時期也在劇團。他跟我說:「你知道嗎?我們夫婦倆就靠一周一百美元生活。」我因為有教書的正職收入,就把錢捐出來當行政費,如此這樣慢慢展開,一起做了好幾齣戲劇,同時也積極參與各種亞裔運動。
4.戲劇串連小學生、文教官員、專業人士和社區居民的橋樑——《黃河流水處處肥》的travelogue
因在辣媽媽的經驗,我大學同班同學喬龍慶邀請我為紐約一所PS23的華裔小學編導戲劇,因為這所學校百分之九十六的學生都是華裔,她希望在農曆新年有不同的演出,可以讓學生產生文化認同感。後來我用歌舞劇形式帶學生演出《黃河流水處處肥》(WhereverYellowRiverflows,Fertilityfollows),描寫華人從黃河起源的上游,一直旅行到長江流域;再到珠江流域,最後來到美國的沿途所見所聞及透過表演尋根。
我應用整體劇場的架構,讓所有想參加的學生參與。演出中運用苗族女子弄杯舞蹈、筷子舞、扇子舞、武術、功夫等等。有趣的是,女生比較擅長舞蹈,而男生喜歡打鬥,尤其那時功夫片盛行,我決定把對武打有興趣的男生都找來參加演出。我自己當前導示範,戴斗笠、穿馬褂,拿著在中國城買來的木劍,搬出以前學過的東西,「有模有樣」地展現武術,學生都很開心,也希望自己可以學我。我問「你們要不要表演?」他們說「要!」我便說「那你們要訓練自己的肢體語言。」另外,我還找了現代舞非常棒的林懷民教舞,名叫「非語文溝通」。因為林老師很認真也很嚴肅,對專業非常尊重,在他正式教舞之前,我先對學生示範一些動作和精神講話,讓他們期待有一天在舞台上可以跳得非常好。
5.戲劇扮演CivilRights文化覺醒的重要角色——《頭號香蕉的懺悔》(Confessionofano.1banana)
當時在美國的亞洲人慢慢開始組成民權運動組織,而大學生通常都是率先響應者。那時市立學院的亞洲學生成立組織,剛好在德州發生一起香港華裔年輕人被誣告強姦鄰居女士的事件。當時法官輕率審理,但有一位白人律師挺身而出為他辯護,我們也開始幫忙募款。但是後來我發現團員都非常「外黃內白」的樣子,覺得這募款沒有感覺、沒辦法心戰喊話,所以決定自己做一個二十分鐘的節目,像TED一樣,主題是《頭號香蕉的懺悔》。
我開始閱讀有關太監的書籍,用英文獨白演出一個太監的故事,講到李蓮英「如何變成太監、如何被閹割」的過程時,台下的男性本來都開著腿坐,後來都雙膝併攏,製造很好的演出效果。故事主題從生理轉換心理再到文化,最後是心戰喊話,我說「你們祖先從哪裡來?你們會不會講中文?」等等,因大部分的人都不會講中文。我就說「知道嗎?你們已經把自我的文化閹割掉了,所以無法表現你們的特殊性。」我的英語發音不標準,所以更能代表真正原汁原味的角色。因為當時的天時、地利、人和,我就這樣子過了一段獨白的時間。
6.撕毀《武則天》後,意外地受邀巡迴演講「什麼是現代劇場?」
我準備回臺灣之前寫了武則天的故事。歷史故事常常都有偏見,因為武則天的歷史是男人寫的,但我很肯定武則天,第一個理由是至少她的後宮沒有那麼多人;第二,也很重要的——她用人唯才,我開始構思武則天的舞台劇。
演出開場第一幕,我用一塊大布把每個人裹成一體,而武則天用各種不同的姿勢「點」大布內的演員,被點到的演員就離開布出來成為個體,以這種方式開場。
準備回臺灣時,很擔心自己會出事(你們看我膽子很小吧),也以為在臺灣只有把戲劇引進教學和演講,跟舞台劇演出不會產生關係,就在香港朋友家把全部文件都撕毀,毫不保留。
但在回臺時,正好在紐約認識的林懷民、殷允芃和施叔青也都回到臺灣。殷允芃在美國新聞處工作,邀請林懷去演講「什麼是現代舞?」。當時美國大使館在高雄、臺南、臺中和臺北共有四個新聞處分館,林懷民從南部場次開始。他的口才非常好,演講時台下觀眾都感動到流淚。後來殷允芃也邀請我演講「什麼是現代劇場?」,我想:「林懷民讓觀眾哭,我沒有能力讓人家哭,就決定讓大家笑。」也是從高雄開始講到臺北。最後一場在臺北美國新聞處舉辦,我安排一齣包含即興成分的短劇《鮕鮘的三分之一人生》,李昂扮演無冕皇后的記者在轎上被政大心理學系的男同學高高抬進來,效果很好,清大人文教授顧獻樑觀賞演出後很讚賞。也就是顧教授及我回臺就幫忙找好房子當鄰居的姚一葦先生,透過他們的推薦,開啟我多年後與蘭陵劇坊的機緣。
四、行走劇場四十年適逢其會——意料也意外地開啟行走元年
1978年金士傑接下周渝的耕莘實驗劇團,他們固定在耕莘文教院排練,希望找一位指導老師。顧獻樑和姚一葦推薦金士傑由陳玲玲陪同來找我,當時我的想法既單純又有些自私,「已經好久沒有運動,也沒跳舞,如果去教,親自示範時可以順便減肥,一舉兩得。」到了現場一看,嚇了一跳,竟然有一百多人參加。過程中有些人放棄或離開了,留下的核心團員是以金士傑和卓明《影響》雜誌的黃承晃、杜可風、劉若瑀(當時叫劉靜敏)和陳以亨等人。我的訓練方式和大部分團員期待的方式,以及他們熟悉的方式非常不同。金士傑根據訓練過程的痛苦感受編導了《包袱》這個作品。他覺得本來是要訓練表演的,為什麼讓我們一直在地上滾?提供耕莘文教院場地的李安德神父也問我「你們什麼時候要站起來?」到了1980年,那時已經有幾個作品,評價都不錯。
教育部的「中國話劇欣賞演出委員會」是國民黨立委李曼瑰在1962年組成,1975年後由姚一葦接手當主委,以及政戰系統的趙琦彬擔任總幹事,在1980年舉辦第一屆實驗劇展,以突破戲劇都是話劇式的狀況。姚一葦因為在紐約看過許多演出,希望從實驗的角度來嘗試不同的方式,就邀請說「靜吉,你一定要來喔!一定要參加喔!」於是大家就在劉若瑀家中以腦力激盪的方式選定「蘭陵劇坊」的名稱參加這次劇展,演出《包袱》和《荷珠新配》。
《荷珠新配》怎麼來的?有一天我問戲曲大師俞大綱先生「京劇裡面有哪一個劇本適合改編成現代喜劇?」他毫不遲疑地說《荷珠配》。國軍文藝活動中心正好演出《荷珠配》,卓明和金士傑兩個人去看完後,金士傑決定改編這個劇本演出《荷珠新配》,演出後觀眾都很喜歡,這是天時、地利、人和的時代,中國時報和聯合報也都完全支持,這齣戲受到邀請展開巡迴演出。
演出過程最緊張的一次是在1980年10月31日那場,由聯合報主辦,由副刊主編瘂弦負責,他曾在孫中山百年誕辰話劇《國父傳》演出了七十場的國父,對於舞台劇的熱愛非常可理解。當年又是臺灣最後一次舉辦許多在國外年輕人回國參加的國家建設研究會(國建會),瘂弦把這場演出視為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們得到風聲說不能演,因為那是蔣中正先生的生日,怎麼可以演妓女的故事?
趙琦彬是政戰系統出身,他跟我說:「靜吉啊,你不要理會,這件事我來處理。」他說「那天晚上,你只要看你旁邊有一個你不認識的人,你讓他快樂地投入就可以了。」趙琦彬先請警備總部的人吃飯。演出時,我看那個人的反應,李國修演趙旺,他一出場,對方就開心大笑了,我就想「喔!我今天晚上可以看戲了。」這個過程非常緊張有趣。
蘭陵劇坊後來有越來越多的創作,編導卓明把課本裡面《貓的天堂》改成劇本演出,馬汀尼演貴婦女主人,李永豐演野貓。我的訓練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每個人都是創作者」,每個人的成長故事和文化底蘊都是創作來源,還有,就是——每個人都是彼此的老師。
十年生聚中須各奔西東、各自成家立業
蘭陵運作期間,在1984年與甫回國的賴聲川合作舞台劇《摘星》,同年在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建會)申學庸處長的支持下,開辦「舞台表演人才研習會」,由我擔任主任,持續辦理五屆。許多喜愛戲劇的青年來參加,是讓許多有志於戲劇卻苦無機會的年輕人接近劇場的平台。有不少目前在藝術界的人士:像鄧安寧、許效舜、趙自強、鄧志浩、楊麗音、蔡阿炮、王耿瑜,藝術節策展人李立亨,媒體界的紀慧玲、陳文芬、李文媛、張翰揚和黃哲斌等人都是以此為起點,結業後持續發展而日漸有成。
此外,蘭陵也和其他的藝術團體共創合作,像是「明華園」以及「臨界點劇象錄」。但蘭陵每一年只有卓明跟金士傑可以導戲,其他像李國修都沒有機會。所以,蘭陵劇坊成立十年決定:要做一個暫停。必須要把團員們分家才可以各自擴展。讓人想不到的是當時無法得知「後蘭陵時代」會如何?但從蘭陵尚未停歇的1984年開始,蘭陵劇坊直接或間接地孕育了臺灣至少十五個劇團,包括李國修的「屏風表演班」、劉若瑀的「優人神鼓」、賴聲川的「表演工作坊」、李永豐的「紙風車劇團」和「綠光劇團」、趙自強的「如果兒童劇團」、謝東寧的「盜火劇團」、邱安忱的「同黨劇團」、王榮裕的「金枝演社」、廖順約的「牛古演劇團」和林于竝成立的「魚蹦興業」等。
五、行走四十年的螃蟹過河——七手八腳多元探索
這些年中,我對於臺灣表演藝術的了解還有不同面向的參與。到了後來真的是「螃蟹過河——七手八腳」的情形。
1.表演藝術團體彙編
在1991年受文建會的委託去調查與整理全臺灣的表演藝術團體,集結成《表演藝術團體彙編》,分成民族戲曲團體、音樂團體、戲劇團體、舞蹈團體四類。邱瓊瑤和陳錦誠就是當時的工作人員。某次瓊瑤到三重某個團體作問卷口訪,劇團的地點是在一間茶館。當她訪問時,旁邊的客人說:「喔,你們現在有新來一位小姐,不錯呢,要多少錢?」
那應該是第一次進行表演團體的全面普查,我們那時候從各縣市政府收集到登記立案的團體,共有兩千多個團體逐一寄發問卷,沒有寄回問卷的就用電話訪問方式來調查,最後整理成《表演藝術團體彙編》,每兩年一次,總共做了三次的研究調查。
2.藝術管理的工作坊
做彙編的調查時發現很多表演團體不會報帳,所以當時就跟文建會申請經費,請同事陳錦誠到新竹半山腰辦理工作坊,邀請藝術團體的行政人員參加,把團體申報的帳冊給文建會的會計與主計人員看,再說明正確的報帳方法,比如團體買了茶葉是要送給國外團體,但卻被誤以為是自己要喝的茶葉,茶葉要送禮或自己喝是不一樣的帳目,工作坊的效果很好,可惜只辦理一屆就沒有繼續下去。
也在這段時間,我參與了文建會的文化統計調查,發現許多地方政府的文化單位都缺乏統計資料,於是建請文建會編列預算,派文化統計專員進駐。
3.網路劇院的建構與推廣
臺灣網路環境建置十分先進,網路無國界可以隨時更新訊息。因現在的易遊網董事長專研網路平台,便在1998年開始製作網路劇院(Cyberstage.moc.gov.tw)這個平台,同時因為陳甫彥和我都在學術交流基金會(FulbrightTaiwan)工作,每年都會邀請獲得獎學金的美國教授和學生來臺教學和研究,我們可以運用他們的「母語」撰寫簡易英文,並且讓他們從參與中了
解臺灣的表演藝術。這個平台提供許多臺灣表演團隊豐富的介紹資料,以及國外藝術節的訊息,能夠讓國內外雙向更容易媒合。一方面可讓國外的策展人認識臺灣的團隊,另外,也可讓臺灣團隊了解他們適合參加的國外藝術節,把作品推向國際。這個計畫暫停了幾年,可喜的是2016年文化部網路劇院又再度活化了。
4.政策的參與——以為是守門人,實際上是守門人的助手
後來我有機會參加文建會扶植團隊評鑑委員,名義上是守門員,但實際上是守門員的助手,我通常都建議「你不要先殺,要讓他發展」。以人才培育的角度來補助,因為每年補助團體的經費都有限;可能是八十萬臺幣或一百萬臺幣,這筆經費可用來支持團體和年輕藝術家,幾年以後他可能成長茁壯,當然也可能沒有;但絕對不會白費。特別的是,有了文建會的認可,這些小團體比較能夠獲得地方政府和企業界的信任,方便申請贊助。
我是教育部藝術教育委員會的開辦委員,這個委員會主要是討論藝術教育政策和實施,也參與過一些決策,像是和其他委員共同推動藝術教授可以用作品來新聘與升等,以及音樂、舞蹈和傳統戲曲一貫制的規章,也都順利通過。
5.社區劇場——臺灣不是臺北
臺灣一直以來的文化觀點大多以臺北人觀點為主,應邀提供意見擔任評審的專家學者幾乎都是來自臺北,我就不贊成如此偏向。申學庸擔任文建會主委時,我們都認為應該發展社區劇場,邀請原本就在各地做劇場的先來提報計畫,而且要編預算讓專業人士駐團指導,並且要由中央政府提供固定薪水。劉梅英的台東劇團第一個被選上,邀請卓明擔任駐團藝術家,卓明則再邀請從巴黎回來的林原上,京劇科班出身的他曾經待過雲門舞集和蘭陵劇坊,他們一起和劉梅英成功地把臺東特有的「炮轟寒單爺」的在地文化融入戲劇創作,演出後效果很好,並且為了可以讓臺北戲劇人士看見臺東,還特別安排到兩廳院演出。
台南人劇團的前身華燈劇團也是當時選出的社區劇場。我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夠達到東西南北中、城鄉、族群等資源的平衡,真正實踐「全國」皆有戲劇的想法,希望能夠改變慣有的臺北觀點。
6.劇場的概念成為EMBA等領導與團隊相關課程主幹
我授課時,常會思考要如何教才能發揮創造力。之前在美國的經驗,讓我常常去思考「為何臺灣不能這樣做」,我授課時常用活動的方式、劇場練習等手法教課,這些應用戲劇、會心團體等技巧的課程,很重視團隊凝聚和合作的建立和認同,我年輕時參加美國辣媽媽和亞美劇場,也使用這種戲劇方法讓團員感受到自己是團體的一份子,這些都是在貫徹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理念。1994年我就以這種課程進行的方式,在陽明山童子軍訓練中心,為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辦理「入所儀式」,效果如願。
我在政治大學教EMBA的「領導與團隊」課程時也會帶入戲劇的技巧,我覺得這對他們很重要。在「領導與團隊」之後,同學們可以選修「創意、戲劇與管理」。在這門課裡,他們重組生命故事,變成創作,最後半公開演出。演出的時候,他們全家人都來看,看了之後不少人感動得交換眼淚,因為是過去的故事,記得比較清楚的大部分是悲哀的。
7.國際交流與人才交換
我做了很多國際的人才交換,在學術交流基金會(FoundationforScholarlyExchange,FSE),也就是FulbrightTaiwan進行重要改革,讓藝文人士也能夠拿獎助金赴美研究,首先跟國科會人文社會處長、經濟學家華嚴討論合作的可能,共同促成舞台藝術領域的美籍藝術家來臺教學並與臺灣藝術家共創,逐漸將藝術列入國科會補助項目。也以學術交流基金會名義,和當時的文建會以及其「文化建設基金管理委員會」還有國藝會三個機構合作,促成更多臺灣和美國藝術家的互訪。政策的靈活運用,送出許多優秀的文化人士,北藝大的幾位校長,馬水龍、劉思量、邱坤良、朱宗慶等都是Fulbright學者專家,文建會前主委陳奇祿、申學庸、陳其南、邱坤良也曾獲得FulbrightGrants。藝術家和文化人林懷民、齊邦媛、奚淞、金士傑、汪其楣、張小虹、卓明、江兆申、樊曼儂、羅青、羅燕、曾永義、王文興、吳興國、吳瑪悧、瘂弦、余光中等;藝術管理人員如黃才郎和李玉玲等,赴美交流歷程,都構成他們逐漸成為藝術界重要人士的經驗。
在我負責學術交流基金會的同期,也擔任夏威夷東西文化中心的臺灣代表,這個中心提供在校學生的獎學金以及短期研究補助,像是中視的前總經理曠湘霞、美裔臺籍人權運動者艾琳達、天下雜誌的殷允芃、江春男和前新聞局長戴瑞明等都曾獲得獎助,從這些獲獎者的名單可見其重要性。
此外,由美國企業家的洛克斐勒家族(JohnDavisionRockefeller)在1963年成立的亞洲文化協會(AsianCulturalCouncil,ACC)想要進行更多的藝術交流,就主動聯絡我希望成立臺北分會,我就推薦鍾明德擔任第一屆的執行長。
我們也曾經代表美國魯斯基金會(LuceFoundation)和國際教育協會(InstituteofInternationalEducation,IIE)選出傑出年輕文化人赴美交流。臺灣好基金會執行長、前文化部次長李應平就是其中一位。
結語:行走多年終須一別
為什麼是「會心體驗」?會心就是我們面對面、我們眼對眼,來進行交流,這是劇場界一定了解的。無論AI如何發展,會心體驗是AI無法取代的,所以這就是劇場最好的核心能力。我們可以用體驗的觀念舉一個親身的例子。2015年我陪「優人神鼓」到紐約演出,我一直想看畢卡索的雕塑展,本來很擔心會有很多人排隊買票,到了門口才發現大家都是從網路買票,只有我現場買門票,我在售票口對服務人員說:「我要買票。」在票價布告欄看到「成人二十五元一張、老人十八元」時,我就很開心跟她說:「我要買一張老人票。」她看我說:「你不要唬弄我,你看起來不像。」她講那句的時候充滿真實的感情。我跟她講說:「好,我找證據給你看。」我就想找護照給她看。但怎麼找都找不到,所以,我就說:「我站在這裡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據。」她就笑了,她說:「你來幹嘛?」我說:「我陪一個臺灣劇團來BAM演出。」她講:「啊!真好。你今天是我的客人,我邀請你免費看展。」然後就給我一張票,票上面寫的是「職員的客人」,她早有劇本,但卻能隨機應變,即興演出。這就是劇場!她是一位演員,我要看的作品其實是畢卡索的雕塑,我們的互動就是「觀眾和演員的互動」。我覺得我們可以把劇場帶到生活中,帶入工作中,變成一個別人沒有你也可以活,但沒有你卻很難活得好的元素。我想,這也是我們大家都可做的事情。
回想小時候因羨慕演員在台上不會害羞可以「自由表達」並與觀眾會心互動,從歌仔戲的啟蒙而愛上戲劇;後來因為辣媽媽和心理學經驗種下的根,返臺後整合演員的訓練方法帶進臺灣,並和蘭陵劇坊產生密切的關聯,然後隨著蘭陵成長開枝散葉,一個機緣帶動一個機緣,我覺得藝術對社會的貢獻很大,應該讓藝術盡量普及,往下扎根,這也是我至今仍願意一直出一點力量的原因,我在任何領域常常扮演「中介」功能,擔任媒合、調解、擺渡和推波助瀾的人。希望自己能把知識和經驗引介給學生和任何需要的人,讓他們因此創作、發想,然後我又能把這些收穫擺渡回來,繼續提供給其他需要的人,這就是我對於自我腳色的會心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