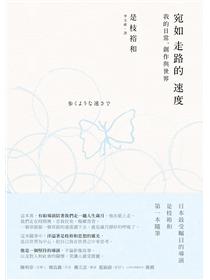借你看看我的貓
像是一個儀式,每天晚上,我輕拍床沿,雙手打在棉布床單上繃繃兩聲,發出信號,他後腿微蹲,輕巧的彈上床來,固執的沿循熟悉的路線,即便我在他正前方,他也要散步如常,從床的右下方踩一圈過來,待我拉開被子,鑽進左手臂窩。
後來我才知道斑斑那樣環床一圈,是在巡視桅桿與船帆。
撫摸著他黑亮的毛髮,他像個剛要升上一年級的小男孩,我忍不住想像他背上紅色書包,戴上黃色大盤帽的樣子,一邊用手烘烘他在冬天裡冰涼纖細的腳掌,搓搓他涼涼薄薄的耳朵。斑斑兩手搭著我,眼睛透出光芒,搜尋衣櫃可有任何溢出的衣角可供抓取,搜尋四周可有他遺漏的樂趣。
這位小朋友累了卻還不想睡,「明天再玩吧!該睡了」我親吻他的前額,聞聞他在陽光下曬出來的氣味,今天是淡淡的檀香,有時則是帶點臭味的嬰兒乳香。看著他有如一只雕工精緻的小像,絨毛在月色下變成一圈光環壟罩著他。暖意由我們相倚的皮膚向全身擴散,毛毯輕柔的裹著我的全身。流光化成水,床墊開始浮沉,家具也飄離了地板,房門鎖著,窗戶開著,我們飛過各家各戶的屋頂,遠眺城市邊緣黛黑的海水。
斑斑第一次到醫院,只有兩個掌心大,身上的斑紋未被撐開,一隻漆黑瘦怯的小獨眼貓。在強烈的冷氣房裡,瑟縮在我的胸前,像一顆溫熱的心臟,在我的胸口沉沉睡去。
「這什麼?喔……老鼠喔」牽著一隻大狗到寵物醫院回診的老先生,若有領悟的說。當年的小老鼠(那大概是身為貓,最不堪回首的人生挫折),如今小跑步時豎起尾巴那有朝氣的傻樣子,或有幾分老虎的態勢。
夜中的航行,行過白日的道路,夜歸者開鎖與夜半清痰聲特別清晰,街角的貓與狗們也跳上這夢船,來!我們有廣大的空間。我一面修整內心的雜枝與枯葉,倒掉臭水,在路邊拾撿花草,重塑新的裝飾,想想能否孵出一些新芽。在我懷裡的斑,呼嚕呼嚕的,像是一小杯燒開的熱水,我用唇口輕吻。航過整排路樹樹梢,我們打算停佇在國小的操場,到無人的教室,偷彈老師的風琴。
尤其是寒流來襲,我們能整晚都這樣倚著取暖。斑在這樣的暖被窩裡,往往能熟睡,放下所有的神經質。幾夜月光太亮,深夜醒來以為已是清晨,深眠的斑斑未被驚動,只有作夢時小腳踢向我,或是發出微弱的囈語。那囈語像是他踩過鍵盤時帶出的亂碼[]]]]]]]]]]]]]]]]]’,貓的語言。
貓能靠人類接收不到的聲波溝通,同類之間近乎無話。或許為了豢養人類,才開始發展語言。當咪被我叫喚時,會回答「嗯?」,斑斑則近年為習得的「媽」而沾沾自喜,但多數是「嗚」,柔婉百折的態勢,小兒女向父母乞憐的輕軟耳語。偶爾我們在夜半同醒,他便再以呼嚕聲,具體向我描繪他的夢,直到我們再度睡去。
忙碌須晚睡時,斑斑咪咪在我身旁各據一方,用各種伸展的姿勢,或摺疊柔軟的身體,淺眠瞌睡,等待與我回房同眠。直到深夜,我才抱起兩隻全身放鬆,因而沉重的毛球,輕拍安撫,沿途關燈入寢室。當我們同處,雖沒有開口,卻像是說了許多話,都是關於愛的話語。
彈跳是日常,阿斑全身的斑紋是從後腦往四肢散射,這讓他看起來像極一束光,沒有任何事物能阻擋一束光。斑三個月左右便來到我的生活被捧愛,從前我叫他小小貓,即便如今他已三歲多,還是叫小小貓,成為過分被溺愛因而長不大的孩子,仍活在三個月的幼貓狀態,好動調皮,玩累了便要人抱著哄著。我才明白如果擁有一個人類孩子,將會被我寵溺到無法無天,但斑斑是貓,如此就沒關係了吧!
咪咪越來越像我了,不是生活習慣而是長相。幾次我看著她凝望遠方,下巴的弧線與稜角,都想著「那不是我嗎?」。她渾圓的雙頰漸漸變成橢圓,五官拉長一些,眼神成熟一些,想是有更多話想說,從少女變成女人的臉,或者說,我們都正在老去。
冬日咪咪坐在我盤據在椅上的雙腿,心窩貼著我的小腿肚,我感受她血液流動的節拍,用鍵盤打出的每一個字,都有她的氣味。當我低頭看她,我們鼻尖相碰,作為一種親吻的替代。在斑斑加入之前,我們曾有過更為親密無間的日子,在我的第二間或第三間套房中,那是我們的少女時代。
「咪咪」是她為自己取的,她認為不俗。也曾有過其他名字,但她一概不應。
對待她,總有那種父母親對待第一個孩子,或是丈夫對待糟糠之妻的歉意與心疼。在經濟好轉之前那些不知所以的日子,都是她陪我踱過來的。沒有我,她一定可以找到其他疼愛她的主人,但沒有她,我大概不行。說大概是為了為自己保留一些尊嚴,實則沒有大概。
我們遷徙了幾次,忍受生活中似乎沒有止境的變動。某段時間身處夾層的小公寓,全無外來光,令她濕疹掉毛,但看待生活與看待我,卻全無不快。她總是歪著頭,用琥珀似的雙眼看著躊躇不安的我,像是在問我「你在煩惱什麼?」使我能瞬間發笑,至少也要能佯裝微笑,摸摸她的臉。
產後所有人只愛幼貓,她的目光轉為呆滯。在她的情侶主人面臨分手與財務危機時,貓群一一被分送,裡面有咪咪的丈夫、孩子,但咪咪是最先要被送到收容所的那一個,連夜被我搶了下來。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我一夕之間有了貓。一隻灰白黑色相間,大地色系的貓。
但那時的我們各經離散,感受過各種愛,感受不愛,如此不快樂,往後的路程像是走上公路電影的兩個人,背像過去往前走,其實擁有的燃油不多,也不知能走到哪裡,但最糟就是跳車用腿走。我常常看著這個靈慧的少女快樂的奔玩,彷彿那些失散的歲月都不存在,我們是從開天以來就並肩同行的兩者,不帶塵埃。
從此之後我看貓像人,看人像貓。
再度面臨搬家,清空大部分的置物箱,才走出房門,她返身又躲回舊房間裡,我在床頭板的夾層找到她,摸摸她的頭,告訴她其實我也很害怕。我的傾訴往往能使她堅強,因為她把我擺在自己之先,搬家的路程她十分靜定,我們就彷彿這樣下了錨。
記得國中的時候,與母親談起死,她告訴過我「如果你有一天真的很想死,記得把自己當作一台機器,用盡力氣的工作、累了就睡,什麼都不要想,度過去,不要死。」所以我幾乎有過三四年創作一片空白,因為那時我只是一台機器,只想把日子過去,等待下一秒出現的島嶼,等待下次天再晴。
所以無法寫字,也無法讀,各種飽脹的情緒滿溢胸口像是淤塞的膿血,埋藏在平滑的肌膚之下。行走如常,內心卻是碎裂。阿保美代的漫畫裡,吃夢的貓把主人的噩夢都食盡,晨起有些落在枕上的碎片像星星樣子的金平糖。那些肝膽俱廢的夜裡,或許倚著我的枕頭而睡的咪咪,正是這樣想方設法,在夜裡忙活,綴補我的失落。她在那裡,在一座靜島上,慈悲的望向泅泳的我。
我們都在等待一座島嶼,等待有天可以再讀起字,再提起筆像是買一杯手搖飲料那樣簡單。雖然漫長的日子裡,那天像是永遠不會來到。
某次咪咪生了一場大病,被誤診為腹膜炎陽性反應,鄰近的動物醫院要我帶著貓,抱著病歷表成計程車轉院。咪咪沉重得像一顆石頭,在籠裡咚咚的左搖右晃,沒有力氣伸出爪子平衡自己。當虛弱的她抬起頭,我們目光相接的時候,看見淚流滿面的我,她展現出驚訝的表情,人一般的表情。爾後她便撐起身體,極力的使自己看起來好一些。那樣生死交關的時刻,我們無聲的交會。
橫渡此次大劫,我們彷彿開啟一道共通的頻率。我時常想她,在行走間,在客運微調三十度的座椅上,我閉起眼睛,想著她的眼睛,想著她額前的黑紋如何在毛羽間游走、分岔、會合,想起在陽光中她回頭看我的樣子。
我在心裡輕輕的撫摸她背脊的細毛,像是順著月球半圈的弧度,讓手掌輕輕的覆上她溫熱的身體,想著把自己生活的毛邊與線頭,也要一起抹平下去,聽見她靈魂深處傳來的呼嚕。當我回家,她靈動的雙眼對我一閃一閃。唯有我們深知剛剛那個時刻,我們其實是在一起的。
動物的心平穩又靜定,有著比人類更澄澈的智慧。我浮動的生活也日漸將自己混成濁水,沒有澄清的一天。他們用雙眼,不假文字,勝過我用口吐出徒具雕飾的話語。那樣乾淨的心只是映出萬物本質,沒有愚痴愁苦。認識斑斑咪咪之後我從無肉不歡,到禁絕一切豬牛羊食品,如果可以,連雞肉、魚肉也要慢慢免除。因那樣具有感情的生命,不該成為食物,該擁有愉快自然的生活。生而為人,我很抱歉。
我們為了美好而耽溺,當生活由衰轉盛,當我終於能夠給她一扇觀望後山,滿眼盈綠的落地窗,還有熾烈奢侈的陽光。還有滿地的新玩具,她難掩身為一個孩子的開心,每要跟我對上眼,總要倚著牆,連續翻幾個跟斗,像是表演。她為全家表演一個星期的翻跟斗,想表示她的開心。
她的心隨著房子而敞開,當友人來探望又離去,她便染上特別鮮豔的好心情,我幾經回溯,才想起友人一進我們家門便說「哇!這是咪咪嗎?好可愛」知道自己可愛的咪咪,因著知道他人也明白,所以開心起來。
我在家忙碌的時光,咪咪乖巧的曬陽光,天冷時潛在被窩休息,中午的時候才會跳上書桌跟我打招呼,像是我小時候也會想像被窩是我的帳篷那樣,持守自己的空間。閒時換我走進房間,摸摸棉被外那隻毛毛的小手,聞聞她掌心的味道,再吻一下她的額頭。這幾個小動作串起來,幾乎就是我們的日常生活!
她是一個盡職的姊姊與母親,無論任何時候斑斑發出大叫,她一定會馬上跳下床來查看,並且盡力安慰長不大的弟弟,諸如小鼠玩具的羽毛掉了、小球掉到冰箱後面了、媽媽又剪我指甲了,任何雞毛蒜皮的挫折。
某些奢侈的午睡時光,當我起身準備忙碌,冷風灌入我剛被被褥包裹得熾熱的雙頸,我回望斑斑與咪咪仍在被中熟睡的身影,覺得辛勞有岸。當我提著沉重的身軀回家,接近門口就聽見斑斑隔門大喊「媽--媽--」也覺辛勞有岸。
斑斑三個月大時,因為眼球在雨季被感染,潰爛凸出眼眶,像煎熟的魚眼睛。一個女孩救了他,連帶撈起貓媽媽和貓哥哥,為這三隻貓尋找認養人。而今臉書仍年年回顧,提醒我女孩的溫柔的善行。
女孩與當年的男友,也是她如今的丈夫,從嘉義開著車到台中,為著確定我家適合斑斑居住。女孩看到受苦的貓總是不忍,當初看見斑斑她猶豫了一兩天,仍是硬著頭皮救了下來。她嚴格篩選認養人,再收編不親人的貓。拿出領養同意書,留下我的LINE,我們不定時的為著斑斑聯繫。
斑斑同胎的哥哥被認養之後走丟,她自責不已。可以找到那隻貓的吧?可以的!可以的吧?我們這樣彼此說了幾個月,便絕口不提,我們都知道貓真的走丟了,而且生死未卜。隔年她再來看我,斑斑已不認得她,害怕得躲起來,女孩豪氣的說「沒關係,他現在很幸福就好」。
而今女孩肚子裡也有一隻小貓,不知是妹妹或弟弟,過了年,我就要當阿姨了。
各種動物在子宮裡的樣子,人與牛與豬與貓……各種動物都是蜷縮著肉色無毛的身體,一塊矽膠似的肉,漂浮在羊水之中翻轉,扯動著臍帶。兩顆像蝌蚪一樣的黑眼睛,蹄與手都只是略有形狀,大概是降生之後才抽號分發,要人要獸都憑運氣。某些人披上獸皮,某些獸帶著人性,原來是一回事。
斑斑在夜裡睡成大字形,胚胎式深眠。開開的腿,把我擠到棉被邊,早上想跟他算帳,但他比我早起,早跑出房門玩了。
咪咪一早在窗旁看淡水後山褐黃色的樹林已經開始長出新的蔥綠,不知道她有沒有發現樹變了顏色。縱使我們都已過了少女的時候,但我們終有一個瞭望的角度,看見更遠的景色。
直待明年的新風盪入,我們要到那座山裡去看看,ssssssssssssssssf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