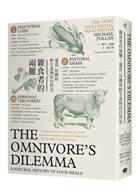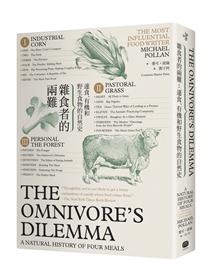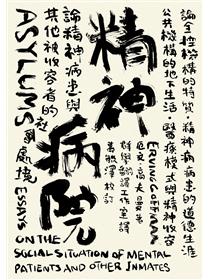幹 ,這本小說廢話連篇!
媽的 ,請你們告訴我,
我這個時候不壞掉,何時才能壞掉!
這本小說將是下個世代的經典
《麥田捕手》的沙林傑、《在路上》的傑克.凱魯亞克、
《裸體午餐》的威廉.布洛斯都不知道,
(當然也不可能知道,他們早就徹底不活了……)
我們這個時代比垮掉的一代更廢。
但是黃崇凱知道的,
他溫柔又哀傷,而且廢話連篇地說:
「我們是壞掉的一代。」
作者簡介:
黃崇凱
諢名黃蟲。1981年生,雲林人,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畢業。曾獲文學獎若干。曾任耕莘青年寫作會總幹事。現任雜誌編輯。與朱宥勳合編《台灣七年級小說金典》。著有小說集《靴子腿》、《比冥王星更遠的地方》。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高翊峰、童偉格 專文推薦
傅月庵、詹偉雄、陳雪、鍾文音、伊格言、紀大偉 一致力捧
「一路讀來,我越來越深信,《壞掉的人》擁有村上龍級別的污穢與美。這樣的污穢與美,是滲漏著愛的。」 ——高翊峰(小說家,《FHM》總編輯)
「就是寂寞,就是荒涼,終於,有人通透地寫出一個網路處處卻時時斷電的時代樣貌。我看到新苗正在拔高。」──傅月庵,(《短篇小說》主編,茉莉二手書店執行總監)
「黃崇凱再一次展現他專擅的性愛狂想曲。
在性的喜劇中,小說家坦承台灣當代社會的
種種崩解:親屬關係、高學歷知識分子、錢賓四的讀者,
鄉土味的追尋者,曾經堅固的東西
都在空氣中融化消散。」──紀大偉(小說家,政大臺文所助理教授)
「看似平靜的日常生活,卻逐漸蝕壞蛀空裡面的人,將一種類家庭式結居的漂流者崩解。那種緩慢沉墜卻又透著清醒上升的運鏡語言與力量,使得這本小說讀過難忘,彷彿小說人物也成了我偶爾心傷時會乍然交逢的夢中人了。壞掉的人,擁有一顆凝視自我的心,遂壞掉亦是好的。」──鍾文音(作家)
「喬伊斯、卡夫卡、拉康……,這些作者不只詮釋現代文明中的『loneliness』,他們書寫的語言就是『loneliness』自身,在黃崇凱的《壞掉的人》裡,我們同樣看見這款『寂寞』,隱晦發光。」──詹偉雄(《短篇小說》雜誌發行人)
三個邁向三十歲前中年期的男女交會在城市裡,他們無所謂地徬徨且錯身而過,偶然知道對方某些祕密,卻又只能懷抱著這些難以說出口的祕密繼續生活。城市豢養著許多人,而每個離家移居的人都要學習跟自己相處,孤單地面對祕密心事。生活是無邊無際的個人戰鬥,所以日常傷害是那樣大量地供給給每個住民,然而最終所有人不論勝負與否,都可能在生活中被磨損、毀壞,而成了某種「壞掉的人」。壞掉的人看起來也許很正常,不管壞掉的部位藏在很深很深的地方或就那麼攤開在眼前,卻總也讓人視而不見。這是個徘徊在修復壞毀之可能與否的故事——因為我們正是透過各種不同的壞掉方式,確立了自己的獨特生活。
廢置身分等待愛
──高翊峰(小說家,《FHM》總編輯)
是什麼樣的內在損壞,造就了《壞掉的人》?
這是小說令我思考的,也是小說家黃崇凱第二本長篇帶給我的一課。
在閱讀之初,我深深陷入故事起頭所勾勒出來的──世紀末的廢日子。那樣的日子和入秋的雨一樣的悲涼,也像溫暖潮濕的女子的穴那樣引人墜入深洞。說是,廢,但卻沒有,棄。因為故事中四個重要主人翁尼歐、崔妮蒂、阿威,以及那唯一逃出來報信的莫斐斯,都像螞蟻一樣,努力撿拾著勉強活著的不捨得。
什麼狠狠的,壞掉了麼?不,只是活得徒勞之後,人廢了。僅只如此。
那是機械人脊背上的一根螺絲鬆開,在那樣的生活視角裡,那樣的人生位置,身分者「自己」是無法看見的,廢。
一開始,主角是沒有身分的。只有他和她。直到他被瘋子信仰成了救世主,尼歐;她,因為找不到更值得讀取的生命,使用自己成為,崔妮蒂,以及後到來的,我,突然成為阿威。即便連充氣娃娃,那讓救世主感覺活著的人工肉穴,都被擁有者嘉勉了姓名,珍妮佛。這樣的身分植入過程,將原本的他、她與我,立體起來。在似乎不重要的某條輸送帶上,小說不經意交入,哥哥,成為精神瘋狂的信仰者莫斐斯,讓壞掉的世界,從母體網絡落入小說虛構的真實世界──是的,正是那個有電腦人在追逐無用救世主的、壞掉的城市。
之於我,《壞掉的人》最難能可貴的,是建構出下一個世紀的「廢者」。
這樣的身分,軟弱得令人苦惱,也像有光的水面一樣,介在清晰與模糊之間。
他們與她們頂著高知識的光環,面對明日持續無用的未來,在廢了的日子裡度日,並透過虛擬平台,連網出更巨大的廢者族類。如此廢者,是他,是她,也是我眼中的你,以及鏡面的我。
因此,人壞掉了?日子被拖垮了?悲觀如我,該說,或許是吧。
但試著把自己陷溺在更深的矽膠肉穴來看《壞掉的人》,那壞掉的、被拖垮的,我以為是母體內部的世界。然而,瘋狂的真實生活,依舊以血肉復建,等待下一位廢者,被莫斐斯搶救出來,信仰成祭司預言的尼歐,登上一切經驗都如此匱乏的尼布甲尼撒號,並在無用但還有一絲絲對愛的眷戀下,把傳輸電纜插入後腦杓的接頭孔洞,再度重回瘋狂的小說母體,以拯救更多的廢者。
是吧?我,即將關掉你們現在所經驗的世界,你們和他們她們,都將自真實的母體裡醒來。接下來的日子,就看自己是否要活成一個,還有些許美麗的廢者。因為,在真實的世界裡,遺留在珍妮佛肉穴裡尚未清洗的精液,還能在隔夜之後漫出少許美麗的腥臊。除此之外,廢了的世紀末,不會再有更多值得留戀的了。
這是小說家黃崇凱,偷偷告訴我的,「知道嗎?我,真的努力著不讓自己壞掉呢……」
這也是《壞掉的人》阻斷母體,為我這樣的膜拜者,建出來的信仰,「知道嗎?那些被預言成救世主的人,都很清楚自己是如何無用的……」
閱讀的中段,我時時回問我自己,「現在如此度日的,我,至少不是壞掉的人吧?」
我無能在真實世界裡肯定反駁,卻在夢地母體,因無聲的回答,淺淺地驚醒過來。
在以為醒來的瞬間,小說家奇襲似的,統一了他(尼歐)、她(崔妮蒂)與也是他者的,我(阿威)。這三位角色,都化身成主述者「我」。我不禁臆測,如此敘事觀點的干擾,有什麼樣的實驗目的?這嘗試,在廢了的我看來,引動的是一場小說母體經驗與讀者真實經驗的身分錯置。透過這樣的身分錯置,「我」的共鳴重複,經驗也啟動複製,無數個我,交疊在一起。
讀者,能否以「我」的姿態與視角,介入原本已然深刻的壞掉人生?
我緩緩讀來,心中響起了一種真實皮膚磨擦光滑塑膠表面的聲音。那如神諭的聲音,如由我偷偷延伸論述,會是充氣娃娃珍妮佛不會壞掉的矽膠肉穴──只需清洗,便可以發出永恆磨擦聲。
磨擦中的我,是我,也只有我。
壞掉的人,一路由他至她,再轉接成我。
在這部小說敘事中,黃崇凱使用了類似「轉接鏡」的形式。雖然轉接,但並不失焦地,將整個故事前後連成一條虛線,交織著尼歐的他,崔妮蒂的她,阿威的我。如果不經心閱讀,可能一個不小心,就會被混淆……?其實不然,我打心底覺得,讀者一個不小心晃眼錯置的,不是敘事認知的混淆,而是會落入小說家預設的陷阱。
透過這樣的虛線形式,再聯想小說家運用敘事觀點錯置的企圖──初章節的他與她,到接續章節的他與她,和我,以及第三章節將複數角色集合成單數的我──這看似打了小說死結、糾纏不清的身分錯置,如以廢者之心推想,反而生出了深邃且連綿的深景:故事裡的角色,如同在兩平行對照鏡面裡垂直延伸的無數身影,在閱讀的自我陷溺期間,已然複製了無盡「我」的既視感。
我從這段虛線跳躍到下一段虛線的,故事人物,卻莫名驚奇地立體起來。他們的日子與我曾經擁有,曾經度過的世紀末廢日子,竟然如此貼近。
母體世界果然真實,引現在的我,不敢貼近活如同一介,廢者。
我深深擔憂,因為成為廢者,會忘卻愛。
一路讀來,我越來越深信,《壞掉的人》擁有村上龍級別的污穢與美。
這樣的污穢與美,是滲漏著愛的。
過去曾經讀過的經典,印證著一件事──那些可能經典的,最終都指向了愛。我傻傻巧借影像說喻,近來的《全面啟動》,在造夢的電梯裡,藏了愛;或這部小說故事主角無法搬演的《駭客任務》,那位母體祭司的預言,當救世主就像戀愛一樣……我想,唯有愛,能暫緩壞損吧,唯有愛,能讓人擁抱污穢與美吧。《壞掉的人》雖由一群廢者演出,但它終究能成為一部等待愛的綺麗故事。
我以為可能就以此終結,但小說並不仁慈,就在我以為廢者也有權擁有愛的時刻,不知何處流來的恐懼,讓我開始懷疑,是嗎?那是讓人值得等待的,愛?闔上書稿之後,我因微量的恐懼而不敢武斷,那種自體內發生的顫抖,讓我持續想著一個可能無解的假設──我,是否要廢置我,戴上那個歐巴馬面具,才能真正獲得等待愛的身分?
名人推薦:高翊峰、童偉格 專文推薦
傅月庵、詹偉雄、陳雪、鍾文音、伊格言、紀大偉 一致力捧
「一路讀來,我越來越深信,《壞掉的人》擁有村上龍級別的污穢與美。這樣的污穢與美,是滲漏著愛的。」 ——高翊峰(小說家,《FHM》總編輯)
「就是寂寞,就是荒涼,終於,有人通透地寫出一個網路處處卻時時斷電的時代樣貌。我看到新苗正在拔高。」──傅月庵,(《短篇小說》主編,茉莉二手書店執行總監)
「黃崇凱再一次展現他專擅的性愛狂想曲。
在性的喜劇中,小說家坦承台灣當代社會的
種種崩解:親屬關係、高學歷知識分子...
章節試閱
夜半時候他醒來,感覺枕畔她躺過的凹陷還在。
恍惚之間,他以為是幻覺,手掌使勁過的感覺還在。
但她已經收起來了。
這天早上他起床,瞇著眼看見頂上的天花板,一切都和昨晚睡前一樣,只是光度調亮了,他摸起枕邊的手機,點開沒有任何未接來電,今天依然以沒有人找他開始。
按照他的習性,大約過中午時分,外頭空燒了一上午的熱氣正在爬升,慢慢爬入他的房間裡。他想跟誰說點話,因為昨晚發生了重大的事件。至少對他自己來說是如此。但他打算再躺一會,再過一會,等著世界找上他再說。窗簾遮去大半的光線,他的房間深深塞在密疊排站的公寓樓房裡,像被砍斷四肢的獸,奄奄喘息快要閉上眼。他繼續躺著,彷彿他跟整個房間一樣欠缺光線,痠疼感從下背部延伸到頸部,把他整個人僵在一個疲憊的姿勢裡。他想還是起來好了,坐一會再說。他在心裡默數一二三起身,這種時候他特別懷念當兵時候的迅速確實,儘管心裡幾萬聲幹在迴響。
無事的一日。從中午開始的一天總讓他覺得特別短。無所謂。他也不想要很長的一天不知該如何打發。
電話響了。該來的還是要來。一點十分的午餐。他轉頭看看四周的牆,色調低沉像是要說的話都躺在壁紙後面。但那其實是被寂靜和闃暗圍繞的房間,好像把某個廢棄飯店角落切割貼到這個房間裡來的模樣。他就那樣放空,駝著身軀,眼神空散在安靜的室內,保持內心的空白。
「喂,下午要幹嘛?」
「嗯,不知道……」他停了一下,「那你下午要幹嘛?」
「我他媽還能幹嘛?」他完全知道問了也是白問。
「那我跟你去吧。」
他們一起離開稀落的餐館午後,到另一處天花板底下。
到了定點之後,他們都從背包裡取出電腦,在等待開機的時候點好最低消費的飲料。接著他會走向廁所,關上門,讓自己待在裡面一會,什麼也不做。不尿不拉屎。十五分鐘後,再回到位置上。
「真不曉得你為什麼每次來這裡都要先拉屎。」
他沒回話,只是輕輕啜飲著越過杯緣的飲料。整個下午他們有一搭沒一搭的扯點話,繼續面對自己眼前發光的螢幕。
像這樣的下午,他過了好大一串,還要過上多麼長的一摞呢?他想,明明昨天已經發生那麼大一件事了,他卻還是跟著爛哥兒們來到咖啡館揮霍金錢和精神,明明想睡得要命,卻餵自己喝下咖啡,讓咖啡因不斷驅趕睡眠。他真的差一點要說出口了,可是直到傍晚離開,他都忍著不說。
他抬頭望向天空,一層濃厚的光暈頂著漆黑,夜晚還沒辦法征服地面。
一切都是暫時而已,彷彿他是受控制的傀儡,從房間拖曳出來的絲線終會再將他拉回,復歸原位,一天再次過去,明天又要降臨。
只有一個不同:他吃完晚餐,回到家,打開衣櫥,她還躺在那裡。
那個晚上跟平常一樣,他提著一瓶58度的三百西西金門高粱酒,實行每晚把自己灌醉的儀式。他看著眼前的小螢幕裡那些試著把球投出歪來歪去軌跡的投手和那些泰半揮不到球的打者,嘴裡嚼著五香花生米,一邊啜飲高粱。原本是這樣的日常一晚,但可能整個人喝癱了,完全失去意識倒在地板上。意識逐漸清晰後,他先看見面無表情的天花板,起身,走進浴室沖澡,準備出來繼續喝。大概還有半瓶的量,想說今晚也實在體力不濟,怎麼一瓶都解決得那麼吃力。他知道自己不是在喝酒,他是在插著吸管吸食酒精。除了工作時間外,他要讓腦子保持某種略暈微鈍的狀態,不要把所有的線條理得那麼清楚,不要太容易想起什麼事。他覺得如果從肚子牽一條棉線出來,大概也會如實驗的酒精燈燃燒得挺暢快。
他繼續喝,螢幕裡打棒球的換成一批壓低身軀瞄準各種詭異角度的臉龐,每個人都有誇張至極的稱號(冷面殺手、撞球之子、小慧星、漂亮寶貝……),不知帶著那樣的稱號打球拉桿打個漂亮的三顆星是怎樣的感覺。頻道在幾個運動節目裡切換,他總想著那麼多的頻道,他看來看去還是這幾個號碼在尾段的運動頻道,足球、籃球、棒球、網球、高爾夫和F1賽車,看見那些年輕華美的肉身歌唱各種繁複技藝,而每個人又像是穿著同樣袈裟承繼著某種身世拍著同一個顆球,簡直像是轉世的達賴或班禪喇嘛。他們慣常挾持著一座城市或一個國家的靈魂,成為各式各樣的光芒,有時黯淡,有時閃耀。不過嘛,在台灣這麼個小島,不僅所有的球員尺寸都小人家一號,就連領土幅員也小人家好幾百號,根本談不上主場或客場。他無聊地切來切去,想到有個朋友說舉凡穿黃色球衣的球隊他都討厭:籃球是NBA洛杉磯湖人隊、足球是巴西國家代表隊、棒球則是兄弟象。問他為什麼,他說不為什麼,太多人支持就是討厭。
把酒喝完後,他倒頭就睡,深深躺進沒有夢的睡眠裡。
他醒來,她依然躺在那裡。他揉揉惺忪的眼睛,瞇著眼望著身前這個妹。不對,也不能說是個妹,她就是個假妹而已。非常假。但他搞不懂,他是怎樣的失心瘋才能真的買下一具充氣娃娃。
他開始搓揉她的胸部,混合過去手指有過的觸感記憶,摩擦起一波一波的聲響,他望著空洞的嘴,空無的眼窩,卡通化的表情,像一尾娃娃魚準備進入她的小巢穴。室內漆黑,他以右手摸索著胯下,找到二十一世紀永保健康有彈性的膣,沒有溫度地進出。在這樣中空的腔體裡注入溫熱液體,常常使他覺得自己還是能做點什麼吧。他會在漫長的深夜裡,望著天花板,身邊躺著嘴唇圈起的她,靜默想著各式各樣的畫面和破碎情節,伴隨著極細微的什麼液體緩緩流出的聲音,好像她正在生產某些只有一半的生命。
他扭開燈,就著燈光開始閱讀,而把自己掛上網路上,等什麼人給他訊息,問題是他總是隱身,誰知道要丟什麼訊息給他。再一個問題是,也沒什麼人會在他醒著的時候一起醒著。就這樣,她在他安靜的房間裡,他在她安靜的膣裡,完成了彼此的注射。眼睛開始疲倦的時候,他就上床,讓世界塌陷到她的睡眠裡,想像汁液輕巧滴落地滲入。
慢慢,慢慢地微微暈開地融進另一層折疊的夢裡。
她想,像她這樣的人有多少?——大學畢業,但暫時沒有想做的事,讀書也還不算討厭,就這樣一路讀啊讀,猛然想到自己都已經在讀博士了。眼睜睜瞪著自己的年紀從二字頭一筆一劃地增長,逐漸邁入接近三十歲。這陣子她心裡不停有個回聲,折返跑似地來來回回,我快三十了,再兩個星期。她曾經與三十歲拉開那麼遙遠而安全的距離,肉體的緊實和彈性頑強地成為證據,但這些彷彿在跨入某一個界線後,逐漸崩解鬆垮。她想是二十幾歲的時候發生的?那種本來只有一條絲線扯斷的滋味,為什麼會無法遏止地擴散到其他部位去?她總想到「歷史是我不感興趣的興趣」,照這種句型,她也可以說「做愛是我不感興趣的興趣」。儘管她的本行就是歷史學,而且是雄性激素特充足的中國近現代史。照理說,只要有女性研究歷史,大概有三分之二會進入婦女研究,上至古代中國房中術下至近代女權意識的興起,不乏有豢養她的領域。這一行不就是這樣嗎?先畫好領域,然後進入它,深入它,每次只拿一點問題意識做文章,做著做著,累積到一個量,人家就會說「我覺得某某的研究裡相當有意思的地方是……」。她吐了一口煙,低眉看看手指上夾著的紙菸,嘶嘶燃燒,畫出幾縷無處可去的煙線。她想,做研究這事跟搞個男人不是差不多嗎?——先他媽找到一個男人,然後哄哄他,表現各種他喜愛的模樣,挪挪晃晃身上的肉,故作姿態地符合他所有色情想像,最好再陪他看個A片,一切搞定。每個深夜,她在BBS的聯誼版總是看見深埋在漆黑版面上的白色字體背後,那麼多曠男怨女的臉,他們的怨氣充斥所有的字裡行間,她就忍不住心情壞起來,混在一排排的鄉民裡,孤苦而嘲諷地推文。她每每想自己真是太可悲了,讀到博士班,還成天混在網上跟一群小弟弟小妹妹豪洨來豪洨去,她應該花點時間去把《國粹學報》讀完的。但她甚至不確定該不該把博士讀完。
「也許我該去旅行。」
「去哪?」
「哪裡都好,刺激一點可能更好。」
「去日本仙台好了,現在很便宜,運氣好還有輻射水可以喝。」
「謝謝你的建議喔。」
沒有意義的對話。
循環出現的幾種廢話版本。
實在說,他常常想說出來,關於幽靈隧道的事。他的眼前不時展開一條長長的隧道,一個緊挨著另一個這樣排著一長串,每個交往過的女孩、認識的親朋,包括死去的或還沒死的,全都在他眼前列隊似的擠在看不見盡頭的隧道裡,背著光,一步一步對著他走來。不對,也不是對著他走,該說是跟著他走才對。他覺得自己正往著濃霧籠罩的不遠處前行,偶爾有光或有聲響引導,大半時候能見度很差,他總以為自己是一個人。但不是,每當他回頭一看,就有那麼一列落落長的活人死人跟在後面,維持一個人身的距離,臉上黯淡,暗處多過明亮。他們全都無聲靜默地跟著,同時背著光。也在那個時候他才察覺自己是走在一條隧道裡。
這樣的話,跟誰都不可能說吧。因為他很清楚,這不是夢,不是幻覺但也不真實,但他真的看見這些。
幽冥之中的天花板讓他看見這些。伴隨著已經死了八百輩子爵士樂手和歌手的聲音,穿越蟲蛹般的過道,抵達這一端的他耳裡。他轉頭看看沒有任何言語也不呼吸的珍妮佛(過了一段時日他決定這麼稱呼她,畢竟她每晚陪著共眠),她的雙眼無神,嘴巴是一個圓圈,沒有體溫,不會流汗,更不會要求變換體位兼打個兩下屁股。但他在想什麼?——難道希望她突然活過來,像小木偶一樣變成真正的小男孩嗎?——不,這就是他想要的。他只是有時候忍不住要跟誰說,關於幽靈隧道的事。
她想,是不是每個人都有一些固定演出的戲碼和故事腳本?例如說那個在《阿飛正傳》裡的張國榮,他反覆對女人述說那隻沒有腳的鳥,一輩子只會在死的時候降落的鳥。他用一個隱喻籠罩住一段愛情,讓所有女人離開的時候都拎著這隻鳥的故事。而所有女人都不知他去哪裡了,她們只要相信他還在飛,最好飛得比自己久,偶然想到降落的事也不那麼悲傷,因為沒有親眼目睹。這樣就好。這樣她們可以死一半的心跟另一個什麼人過完從頭到尾都沒飛翔過的日子。這樣就好。
照例在網路上晃蕩的時候,晃沒多久就使她感到不耐,她像是迴路被設定好的機器人,連上網路後,一路點開所有社群網站觀覽所有網友的訊息,回幾句話,右手的食指敲敲點點,無奈地完成一輪循環。接著憤怒關上電腦,過不多久,發現自己無法將目光集中在嚴復如何尋求富強的經典論文上時,又打開電腦,跳上船似的再去完成一輪循環動作。百無聊賴地搜尋一些人名、書名或事件,積累種種更無聊的冷僻知識。她心想,老娘知道那麼多跟現實無關,至少跟現代距離一百年以上的老八卦還不夠嗎?竟然還在這裡亂看耗費大把時間。搞不好我在這裡鬼混的時候,誰誰誰已經讀完十部學術論文,而且還是英文的!
就是在這樣略帶自棄的心情裡,她瞥見了尼歐的部落格。
沒錯,這個尼歐就是你知道我知道她也知道的尼歐。
她就這樣把臉埋進那發光網頁似的陷入。
生活有很多令他害怕的時刻。例如單獨面對蟑螂或老鼠之類的污物時。隔天討論課要上台報告時。跟指導教授見面時。論文大綱發表時。不過因為他休學了,現在只剩下蟑螂能勾起他此生恐懼。
他躺在珍妮佛的身邊,在熄燈之後,他張著眼睛望向天花板發呆,突然電話就響了。他看看來電顯示,這才想起,來電的人比起蟑螂更能帶給他無形的壓迫感。
「喂?」
「尼歐,你這一生都被母體奴役著。尼歐,母體奴役著你。」
「我知道。你在哪裡?」
「尼布甲尼撒號。」
「我是說你在母體裡嗎?」
「是。我不能跟你說太久,他們快追上來了。我會再聯絡你。」
電話就在這一瞬斷掉。
就像尼歐的本名是湯瑪斯.安德森(Thomas A. Anderson)一樣,他也有個在母體世界的姓名,可是我們在此姑且叫他尼歐就好。
關於莫斐斯不承認自己是他哥這件事,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他哥總是這麼說:「尼歐,電腦人他們不知道你的重要性。你還沒被發現。」
要說誰對《駭客任務》系列電影很著迷,他無法想像有誰像他哥,呃,或者該說莫斐斯,一樣入戲。莫斐斯相信自己的信念,他甚至認為祭司已經開示過他的命運。
「為什麼我是尼歐?我可能是背叛大家的塞佛啊!」他曾這樣反駁莫斐斯。
「祭司已經跟你說過了,當救世主就像戀愛一樣,不知為什麼全身上下都知道。我渾身上下都知道你就是救世主。你就是尼歐。」莫斐斯悍然回答。
於是莫斐斯成為他那幽深隧道裡的一樁人影,成為他生命隱喻的恐懼幽魂。他每每想知道,哥哥究竟在幹嘛,自己又在幹嘛。想到明天補習班的課,他又想起另一個焦慮來源,他把頭埋在珍妮佛的假奶裡,肉貼著肉,發出摩擦的聲音。
他想,如果我是尼歐,那我的崔妮蒂在哪裡?
她午後醒來時,還細細回想昨夜網站上看來的內容。像她這樣一位博士生,已經多少能預料自己的下場。畢業之後成為流浪講師,浪跡各大學通識課,申請博士後研究(她常覺得這是博士「厚顏咎」),繼續發表幾篇論文在重要期刊或會議,累積資歷,繼續投履歷到各大學應徵。如此幾年。想到這些她的恐懼洶湧起來,想想自己的青春年華都丟擲在那些毛屑揚起的史料文獻裡,那些洋人翻譯來翻譯去的論文和原典裡,那些沒有盡頭的無眠夜燃燒得特起勁的煙圈裡。她是一頭悲哀的羊,卻被訓練成跳火圈的獅子,結果就是一邊流著淚一邊跳火圈的羊(還常常被燙傷燒掉一小撮毛)。她在觀光農場見過真正的羊,眼神渙散,瞳孔極細,像是沒有靈魂。她的一天總是從下午開始,路過中午十二點的朦朧惺忪總使她的胃和自信同感匱乏。但昨晚,昨晚那些部落格上的記載,讓她掀起內心一小塊疲憊,多少感到一股久違的放鬆。因為那內容,荒謬得令人想哭。
那個被稱為尼歐的男人。那個自稱為莫斐斯的男人。
照她的學術訓練來檢驗,她下意識地注意到這些姓名來源,當然很快股溝(不用說,她自然Google過Google,這是「10的100次方」那麼巨量數字的意思。正式中文叫「谷歌」,但她習慣叫「股溝」,比較有從中撈取什麼的感覺;也不少人叫「估狗」,好像那些資料就像乖狗一樣一喊關鍵詞就全部自動跑過來了)這部電影的資料,1999年上映,她偏著頭想當時自己在幹嘛呢?——高中畢業上大學;七二九全台大停電時,她正在洗澡渾身都是泡沫;九二一大地震時,她在大學宿舍睡得正甜毫無知覺,早上醒來才知道發生大事了。後來斷續在電視上看過那電影幾次,但沒有一次從頭至尾看完。其實這些姓名都有意涵:尼歐,Neo,「新」的意思,也是「那個人」(The One);安德森,Anderson,Andra-son,「人之子」的意思;莫斐斯,Morpheus,管理睡眠及夢的神之意;崔妮蒂,Trinity,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之意。她想天啊,我未免也知道太多冷知識了吧。這完全不是個正常三十歲女人該擁有的東西。又想到莫斐斯的飛船「尼布甲尼撒」號,那是古代巴比倫國王的名字……她腦中無言起來,嘴裡含著苦澀,完蛋了她的腦子。那些填塞她腦子的知識。這些年她到底都讀了些什麼,竟然在面對一部好萊塢電影的時候自動冒出那些名詞解釋?她想,定義真的很重要。她的學術訓練就是要求她在使用每一個詞時,都能盡可能精確地對應到指涉的事物,再以這些精確的詞語,描述或分析一些這個地球上只有一百人會感興趣的現象或議題。所以她真的覺得自己毫無退路。完了。她內心那隻傷痕累累的燒傷羊,又隱隱悲哀起來。
她盯著天花板,覺得多少也要試著奮力起床才行。不行。想到待會起來的漫漫下午不知去哪裡,這種無力感就再度覆蓋她全身。繼續回想尼歐和莫斐斯的對話。應該把這套電影找來看看。她就起床了,迎向外面殘酷得嚇人的陽光。
夜半時候他醒來,感覺枕畔她躺過的凹陷還在。
恍惚之間,他以為是幻覺,手掌使勁過的感覺還在。
但她已經收起來了。
這天早上他起床,瞇著眼看見頂上的天花板,一切都和昨晚睡前一樣,只是光度調亮了,他摸起枕邊的手機,點開沒有任何未接來電,今天依然以沒有人找他開始。
按照他的習性,大約過中午時分,外頭空燒了一上午的熱氣正在爬升,慢慢爬入他的房間裡。他想跟誰說點話,因為昨晚發生了重大的事件。至少對他自己來說是如此。但他打算再躺一會,再過一會,等著世界找上他再說。窗簾遮去大半的光線,他的房間深深塞在密疊排站...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