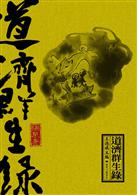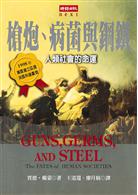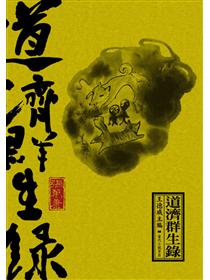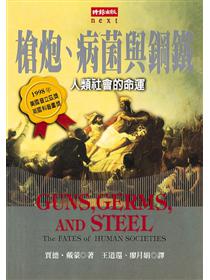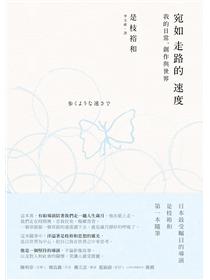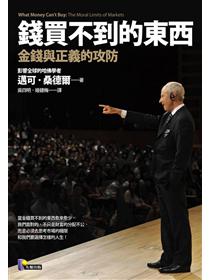1.
我辭去教職,淡出名存實亡的婚姻,變賣新店公寓,遠離混出名號的戲劇圈,和眾位豬哥軟性絕交(別找我喝酒、別找我打牌),帶著小發財便足以打發的細軟家當,穿過幽冥的辛亥隧道,來至這鳥不拉屎以亂葬岡為幕的臥龍街,成為私家偵探。
掛上招牌,印了名片,中文那面燙著楷體「私家偵探 吳誠」,另面印著“Private Eye--Chen Wu”,愈看愈發得意,反覆賞玩。搞了兩盒,沒數日便將告罄,倒不是多人需索或在紅燈下四處濫發給開車族,而是等候生意上門的空檔模仿賭徒把兩疊名片當成撲克洗牌,或以食指中指并夾作暗器練習,不過耗損率最高的是剔牙。
從奇想偶發到越獄般暗中醞釀一直到果敢實踐歷時半年,俟時機成熟才正告親友。反對聲浪一如預期傾巢而來,好似搗了蜂窩,任我掩體揮手力擋,下場仍是滿頭包。活該當災,千夫所指我早習以為常。明月高照,一干猥瑣小人刀劍在握隱身草叢,獨我一襲雪白勁裝疾風兀立曠野,時辰一到萬箭穿心,倒臥血泊中的我手裏沒有兵器,只有一支手電筒。言重了,戲劇出身的我老愛在腦海裡拍電影,胡亂編構淒絕泣血畫面,場景永遠在曠野,故事永遠是關於一名小丑的英雄情結。
這回可是來真的,決心忠於小丑本色。罅隙處處之滄海孤舟,滲入的水向是比掬出的多,人生不過爾爾。叱嗟風雲,抑或退隱於市?寧可選擇後者,不再夾窒其間以致胸懷淤血,亦不再左右巴望落得兩手空空,且大退大進,揮別婆婆媽媽,掙脫世俗枷鎖,切斷江湖連線,一個人過自己的活,何其快哉!
笑傲遺世,我瘋了嗎?
年過七旬的母親最後得知,反應最烈。不准辭職、不准提早退休、不准孟浪行事!當我囁囁吐露一一做了以上,聲嘶力竭換成搥胸頓足──母親灑狗血功夫一流,我的戲劇天分早於娘胎便師承自她──但見她淌淚夾涕揚言要壓我回學校,到校長辦公室請託伊收回成命,甚且跪求亦在所不惜!
未赴了,我說,系主任、院長、校長各個雙手微顫,捧著我遞上的辭呈,宛如天上掉下的禮物,一日內連過三級依極速件處理,執教十數載未嘗見識官僚體系這般神奇效率。他們敷衍慰留卻掩不住感激振奮,只差沒點鞭炮放煙火擊鼓列隊把我歡送出校。以上當然胡扯,我人緣不佳,可還不至惡劣到前腳踏出後邊就有人開香檳的田地。三位長官如何看待本人無預警出走我不得而知,一派瞎掰只為讓老人家死心。
母親頓時啞口,萎荏弓凹的身軀搖搖欲墜,手倚門廓,一會兒盯著她讚歎多年的義大利進口瓷磚,一會兒仰望客廳牆上老爸的畫像,瞬間更形蒼老,正欲發作,我撂下一句仍會按月寄生活費便一溜煙走人。
不孝子我真是,且不單此回,前科累累犯例一堆,所幸她老人家堅毅如山,若無超人意志怎能獨立扶家一手撐起屋頂,安然渡過風浪無數?何能招架不肖兒如我三不五時撒野耍賴竟不吐血倒地?雖已心口不同步、說話些許結巴斷續,母親仍思想澄明,聲音洪亮如沿街放送的廣播,動怒時口頭禪更熟極而流絲毫不斷續結巴。母親口頭禪多不勝數,乃一生育兒實戰的智慧結晶。「死囝仔賊」、「飼兒罔罔」、「氣死有影」、「氣到血冒湧而出」……假以時日我該自費為她出版嘉言錄,以報養育之恩。
走出家門,轉進三民路,「死囝仔賊」依稀可聞,心底一陣溫暖。
適才拎來孝敬老人家的一品香鮮蝦扁食恐怕已被丟棄垃圾桶,接下來我猜母親會打電話給正在上班的小妹,她呢,想也知道會佯裝不知情,好似晴天霹靂:「阿誠,伊起痟了嗎!」
年幼我四歲的小妹從未喚過我「哥」或「阿兄」,不僅因年齡近、孩提時作伙嬉戲感情深,且因我沒大哥樣,基因少了「為兄」的陣頭。自從各自成家,兄妹倆便聚少離多,加之我不興串門聚餐去電問安,近來更為疏分,除了節日拜拜於母親住處不得不外,鮮有見面機會和必要。親情紙薄,倒非有何難以冰釋的嫌隙,橫豎代誌演變至此,毋需欷歔,台灣很多家庭據說都淪落至此。
我以手機「知會」小妹,刻意不用市話聯絡,以免過去的事扯不完。找個不頂安靜但不至喧嘈的街角,挑了深夜時刻,若無其事地丟下炸彈:「辭職了」。彼端傳來久久的沉默,只得耐心等候,給點時間讓她消化突如其來的衝擊。「媽怎麼辦?」語氣極其冰冷。小妹一向坦直,對於我花招頻出早有防禦機制,完全省略「怎麼啦」「發生什麼事」之類制式反應。哀莫大於心死,這點可能性最大,她早不在乎任何關乎我的狗屁倒灶。
「我還是會按月給她一萬。」
「那不是我的意思。」話語方落,電話便掛了。
家人好辦,自大學便混在一塊的麻友們可沒那麼容易「按奈」。半年前我便點滴吐露退隱口風,他們起先不以為意,只當間歇性牢騷聽聽,爾後發覺事態嚴重便不斷找機會與我喝酒,不斷以勸說為由找喝酒機會。有陣子一干人車輪戰術,啤酒屋油膩矮凳上從未缺席的卻是我。平時聚會我甘居配角,不跟風、不帶頭是我奉行不悖的作風,可這會兒卻難得當上了主角。幾支嘴混聲合唱一曲勸世老歌,啤酒下肚專屬欲求不滿已婚男人的台灣藍調。
──中年危機嘛忍著點兒掐緊老二晃眼兒就過了。
──創作瓶頸嗎?切忌將寫作和人生混成一談。
──找管馬子貼身肉搏一番,不,找個女學生談戀愛待東窗事發被解聘還不遲。
最扯的應是,倦勤是吧?不想教就隨便教還不簡單。天地良心,我一向隨便教。
事情沒那麼簡單。
總是當他們搭腔搶詞忘情提點──為時僅限於剛坐下咕嚕喝下的兩瓶,一旦酒過三巡臉頰泛豬肝色後便把邀約的主題,我,給忘了──總在他們烈切分享危機處理心得時想到一句老話:友人的災難帶給我們的黑色慰藉往往甚於敵人毀滅的訊息。榮幸之至,個人生涯的巨大丕變竟為與我同等身心俱疲的哥兒們心靈注入一股宛如再造重生的能量,縱然僅僅維持一個菸臭酒臭濃濁如痰的夜晚。
偏執如我原本無意聽勸,管它朋友、親人、同事。自從妻依親到加拿大流連不返,我前一刻萬念俱灰下一秒舒爽暢快,心緒兩極晃蕩如鐘擺,從懮懮慼愀到英氣勃發,從窮途末路到海闊天空,從「蝦米攏去了」到「大幹一場」,直到發條鬆脫,鐘擺凝止於中界。猷如平生第一次學會深呼吸,吸-入-呼-出,徐徐吐納間我找到安靜,以安靜思索下一步。爾後,心底日漸埋下幽微坦蕩根深入魂的退隱之念,先如滴水般涓涓滲泌,繼而一瀉如柱勢不可擋,向親友宣告「辭了!」可絕無兜攬可茲轉念的人生哲理的渴望。
但想向他們告別,道一聲珍重。
但望另築一段未知人生,破釜沉舟放手一搏。
骰子擲出,十把啦!BG啊!不上天堂且下地獄。
我寄居於白晝和黑夜無甚兩樣的水泥洞穴,雖腳踏實地,卻不見天日。
臥龍街197巷是條死巷,宛如由盲腸內壁延伸而出的一道闌尾。裡面住了五十幾戶人家。地狹人不親,很少看到鄰居之間互動。這條死巷白天時已夠沉寂昏昧,唯一的光源來自一小片上空,到了夜晚因沒街燈更是黑壓壓,若非自住屋窗戶透出的微弱燈光,可真要伸手不見五指了。之所以落腳於此除了租金便宜外,且因為它夠隱密。為了掛牌做生意,我特意選擇自有門戶的一樓。房東為了防賊,用雨棚與鐵柵把前院遮得密不透光。看屋時問房東可否拆掉雨棚,他不假辭色地告訴我,拆掉你就不用租了。
屌斃的招牌掛在一棟中古四樓公寓底層的大門邊石柱上,長方形木板鏤刻質感的「私家偵探」。
小小招牌引來坊間動員不小、不怎麼掩飾的竊竊私語,顯然久廢的「守望相助」因怪咖入侵而再度開張。不時可見午睡方醒的公嬤叔嬸、騎著機車的少年郎、足蹬扣扣作響踏著露趾矮人鞋的美眉、早熟討打的孩童,幾乎所有周遭鄰居排好班表似地輪流徘徊於招牌近處交頭接耳,即便我出入大門,也未曾基於禮貌暫且移開視線。
某日,條子終於找上門來。身為私家偵探,自當料到。
「這是什麼?」管區仔指著木板。
「招牌。」我遞上名片,未及抹去沾在角尖的肉渣。
「有這種職業嗎?」
「沒有,我是台灣唯一,算是台灣首席私家偵探。」
笑話沒引起任何反應。只要一個,誰能找出一個值勤時帶著幽默感的警察,我自願坐牢十天。
「有執照嗎?」
「沒有。我到徵信公會申請,對方說要入會申請書、會員代表身分證影本、公司執照影本,還有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我不想入會,不想開公司,所以沒資格申請。」
「怎麼可以?」
挺著啤酒肚的條子兩隻拇指勾在肚臍下掛著手槍的皮帶上,自以為是小號的約翰偉恩。
「有犯法嗎?」
「這是做啥?」
「救人一命。」
1.
我想救的人其實是自己。
搬來這兒無異走到盡頭,亦無退路。
在一個屋簷下隱居獨住對我而言既新鮮又驚悚,完全違背醫生叮囑。無論多麼厭煩人群,盡量避免獨處,他說。偏偏我反其道而行,決心克服此生最大罩門。不想一直生活於恐懼中,決心在形式上和痼疾硬碰硬。手段看似激烈,心態卻是謙卑的。
我生於基隆八堵,家裡附近有家鐵工廠,名字忘了,雖然取名某某鐵工廠,它其實是村裡首富的造船廠。
小時常和妹妹以及老闆的小孩們在造船廠裡嬉戲,玩些什麼兒戲全忘了,只留下一幀照片︰妹妹、老闆兩個兒子和穿著深藍短褲和繫上蝴蝶結領帶的白色短袖襯衫、儼然小紳士的我站在船頭前合影。父親是個讀書人,因此常把我打扮成紳士模樣,那也是我這輩子唯一看起來像個「尖頭曼」的時期。父親因病去世後,母親變賣房產,帶著七歲的我和妹妹搬到台北。因此我對八堵的記憶少之又少,最深刻的就是那個鐵工廠。
有件事我毫無意識,先是透過家人,事後自己又添加想像而烙印為永久記憶。某日,我玩累了,躺在工廠裡的長木蹬上睡覺,期間有宵小遣入,竊走一些臭銅爛鐵,睡夢中的我渾然不曉,直到有人大喊「小偷!小偷!」方驚醒過來。事後,大人們繪聲繪影,把小偷說得很可怕,還恐嚇我︰「還好你不值錢,否則就把你偷了。」自此,我午後獨自睡在陰暗死寂的廢鐵中,身旁站著一個不懷好意的賊仔,一時拿不定主意,不知該偷小孩還是工具這個畫面一直沈澱在記憶深處,疲憊時、困頓中便會冒出來攪亂心緒。這大概就是我晚上不喜歡一個人睡覺的原因吧,就怕在無意識當中有什麼怪物怪事會發生,有人會把我所知的世界偷了,把我給偷了。
但這不是我夜裡不敢獨眠於一屋簷下的最大因素。
十九歲那年寒冬改變我一生的事件於毫無預警下發生了。事件發生之前我鮮少意識到自己或世界的存在。自小不乖不壞,不好表現也從未惹麻煩;唸書但求及格,對自己沒信心,對未來沒野心,和課本裡的「小明」恰恰相反,「小誠」毫無志向。我活在自己的內心世界,但它其實極其蕭索貧乏,沒有小王子,沒有維尼小熊,與其說它是天地,毋寧稱之為不具空間感的桎梏──軀體和魂魄猶如被鑲嵌在壓克力面板裡扁平而不具真實性的圖像。當時只隱約感覺,時間站在我這邊,我會長大,老師會老,一旦高中畢業,便得以逃脫那個教條世界,扁平的圖像自然會如咒語解封般掙脫禁錮,翩躚起飛,幻化成立體、有血肉的人。
十九歲那年大學新生的日子再好不過,英文系課業糕餅一片,班上同學陰盛陽衰(令人振奮!),校風相對自由,每位老師言行舉止都像個人,夫復何求?然而就在那年寒假、我生日前兩禮拜,一件怪事發生了。
我睡不著。
夜裡躺在床上,無論如何就是睡不著。剛開始以為只是一時怪象,試圖理出各種因素(沒運動、太過閒散、想念學校生活、家裡太悶等等),然而如此情況竟一直持續到第五天、第六天……太陽西下時,我的心也跟著隕落,兩眼透著不安,臉上被一抹陰影籠罩,心想,又是漫長無眠、數了上千隻羊亦未見效的夜晚。會過去的,會過去的,我一再安慰自己。同時,我一直想著:到底什麼毛病?什麼心事困擾著我?
記得很清楚,第七天晚上,我採取拖延戰術,看電視看到沒電視看後,拉著妹妹玩紙牌遊戲,直到她喊累了、要睡了、再玩就要翻臉為止。之後,家裡寂寥得令人發顫,彷彿在嘲笑我。不得已,只好走進臥室。先做體操,之後躺在床上做深呼吸,接著專注地數羊,羊數完後數豬……慢慢,慢慢,失去意識。
半夜,我被自己的叫聲吵醒。張開眼睛,剛開始視線模糊,好不容易才能聚焦,那情狀頗像手術過後、麻醉藥效隱隱褪去,病人逐漸恢復知覺。眼前有三個人頭,母親、妹妹和一個陌生男子,三張臉不斷搖晃,但其實是我的身體不斷搖晃。母親和中年男子各立於床頭兩邊用力壓住我,因為我彷彿《大法師》裡被惡魔附體的女孩那樣挺著腰力不斷弓起上身,還一邊「啊!啊!啊!」鬼叫著。
早上醒來,走出臥室,母親和妹妹坐在沙發上盯著我直瞧。她們憂心的眼神讓我立刻意識到那場半夜驚魂不是夢,尚於耳際幽幽繚繞、彷彿發自洪古深井的綿邈啊啊聲是真的。
母親問我好一點沒,我問她發生了什麼事。
「我也不知,就是三更半夜突然聽到從你房間傳來尖叫,我以為你受傷了,衝進去看,只見你身軀又起又躺,一直搖晃。」
「那個把我壓住的男的是誰?」
「張醫師。我半夜打電話給他,請他馬上過來。他打了一針鎮定劑後,你就睡著了。」
「他怎麼說?」
「他說可能是壓力太大。你到底有什麼心事?是不是功課太重?太重就不要讀了。還是有人在學校欺負你?失戀了?還是身體哪裡不爽快?」母親把她想得到的可能性一連串說出。
「沒有,只是最近一直睏不好。」我坐下來。
「睏不好為什麼不早點跟我說?我這安眠藥隨時有。」
近午時,我到張醫師那。步出公寓大門時,一時不適應光線,感覺一陣暈眩,眼睛半睜半瞇著。這應是鎮靜劑殘留的副作用,我想。
「怎樣,好點沒?」張醫師問。
「好點了。」
「什麼事困擾著你嗎?」
我想回答,想對醫生傾吐這些天所受的折磨,但口張開了卻說不出話,得了失語症似地啞啞咿咿。這時整個人崩潰也同時獲得解脫,像隻受傷的狗,時而嗚咽,時而哀鳴。最後,勉強說出,沒有,真的沒有,就是睡不著。
「我開些藥給你,晚上睡前吃,自然就會改善了。」
然而我的病情比家人和張醫師所能想像的還要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