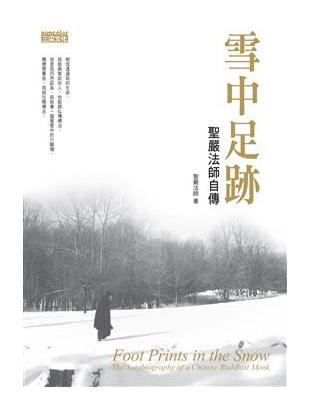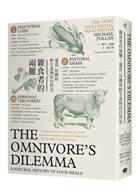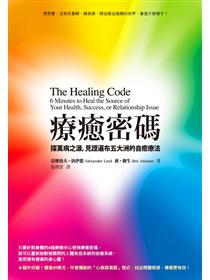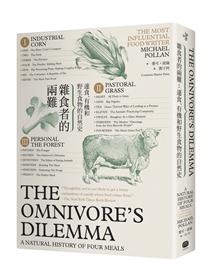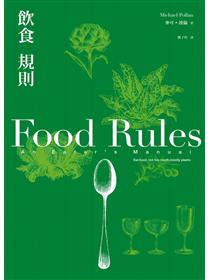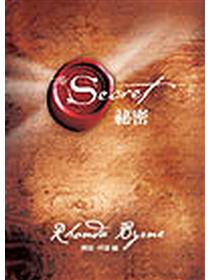第十章 棒下出孝子
東初老人主持了一場佛七,邀請了數位外地來的法師主掌法器。他在法會結束的前一天對我說:「明天我會給你剃度。」
我回答:「明天?我連僧袍也沒有。」
「什麼僧袍?當我們成為僧眾時,我們就是撿他人的破舊衣服穿。」
他詢問其他的法師,有沒有任何舊僧袍可以給我,這些法師都知道「醒世將軍」就是我,其中有些人是我在大陸時的同學。他們說:「我們會想盡辦法給他找衣服。」
他們當天晚上回去,隔天帶來了各式各樣的衣服,其中有僧袍和內衣褲,大部分都太大或太短。
我對師父說:「這些衣服都不合身。」
他說:「以往出家人都穿別人的舊衣服。如果可以修改,他們就修改。如果沒法修改,拿到什麼就穿什麼。在釋迦牟尼佛時代,出家人是到墳場撿拾那些包裹屍體用的布料,沖洗清潔後就穿上身,給你的這些衣服已經是不錯的了。」
我知道後便拿了這些衣服。有些很短,但我依然穿上身。
參加法會的信徒們都走了,只剩下兩位法師。
東初老人說:「我現在給你剃度。」
我疑惑地說:「要有人在場見證,我們應該要讓一些信眾留下來見證剃度儀式。」
東初老人嚴厲地瞪著我說:「我就知道你沒什麼好!你這麼自負!這是你第二度出家為僧,而且你已經三十歲了!當我三十歲時,我已經是方丈了。」
我實在無話可說。就在一九六○年一月六日,東初老人為我剃度,賜給我「慧空聖嚴」的法名。剃度儀式只有少數人參加,來賓就只有蓮航法師一人。
從此,我的訓練也就展開了。在剃度儀式之前,東初老人從來沒有責罵過我。當他接受我再度出家時,責罵我就是合宜的,而且往後的責罵還會更多。
我搬進文化館三個房間中最小的一間。幾天後,當我安頓好,東初老人叫我搬進大的房間。他說:「你是一位作家,又喜歡閱讀,你應該要有大的空間來閱讀和寫作。」
我高興地把我所有的東西都搬進大房間去。第二天他對我說:「你的業障很重。我恐怕你沒有足夠的福德待在大房間裡。我想你還是搬回小房間比較好。」
我有點氣惱,我才剛搬進來,但因為是他的意思,我就順從了。幾天後他來看我,說:「你知道嗎?你應該搬回大房間。你是對的,你實在需要地方來放你的書,以及足夠的空間來寫作。」
我說:「師父,不用煩心。我可以住在這個小房間,不用搬了。」
他那張方正的臉以嚴肅的態度看著我說:「這是我的命令,你該搬去大房間。」然後提起腳跟,邁著將軍般威風的步伐離開了。
我還是搬了。在我搬過去還不到半天的時間內,東初老人又出現在房門口說:「你是對的,你還是住小房間比較好。你不必把你的行李搬過去,只要人過去睡就好。」
又過了幾天,他告訴我把所有東西都搬去小房間。要搬的東西很多,花費了很長的時間。
幾天後,我們來了一位客人,那天夜已深了,東初老人來敲我的房門說:「讓我們的客人住小房間較為適宜,你何不今晚就去睡大房間呢?」
稍後他告訴我,把小房間空下來做客房比較好。所以,我應該搬去大房間。那時我生氣了,說:「為什麼你一直要我搬過來、搬過去?」我抗議著:「我已經搬了五次,我不再搬了!」
這位身形如山,曾是大陸最著名的方丈咆哮著說:「這是我的命令,我要你搬,你就得搬!」
我怯怯地走開,又開始再一次艱巨的搬遷過程。我沒有選擇,這就是師徒間的倫理,弟子對師父必須唯命是從。
東初老人依舊要我搬來搬去,我愚蠢的腦袋最後終於明白了,這就是他訓練我的一部分,所以我不再抗議了,就是照搬。當我變得只是遵行,不躊躇、不抗議和不厭惡時,東初老人就讓我住定不動了。
很快地,我投入了文化館的日常生活節奏。每天早晚都有禪坐,早課以後、晚飯以前,我們都要在菜園中作活,包括東初老人在內,鑑心師和錠心師二位尼師也住在文化館內。我們用菜根、果皮、老葉和戶外茅坑內的排泄物混合在一起做肥料,以今天的標準來說是不合衛生的,但是園中種植出肥美的蔬菜,供給我們食用。多年後,當我在農禪寺開墾廣大的菜園和果園時,東初老人的菜園還深深地留在我的腦海中。
我們的物質生活很簡單,豆腐、花生米是我們最好的佳餚,早餐我們有豆腐乳配稀飯。每星期我們會買兩塊豆腐,切成薄片,東初老人讓我們每人吃一立方吋大小的豆腐,他自己也一樣。他吃炒花生米,每餐只吃七粒。我曾問他為什麼,他說七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數字。
當我的老同學辭去《人生》雜誌的編輯後,我便接替下來,寫評論、散文,處理讀者來信,收發手稿、校正、設計和編排版面。我從零開始學起,當時我連運用各種不同字型和大小的字體都不懂,而印刷公司的工人也幫不了什麼忙。他們不做校正,其中有一些還是文盲。每次排好一頁,我就必須校對三次,但依然有錯誤發生。
更難處理的是政治方面的問題,我們不被容許刊登任何批評政府或其政策的言論,我們必須很小心地使用共產黨的「共」字,但有時工人會誤放上去。凡是觸及政治的文章,我們都要特別小心。
當雜誌印好後,我還要負責寄給訂閱者。雖然我們索取訂費,但我們常常免費寄給各佛教團體。我的單銀是台幣二百元,大約是美金五元。要支付交通費、旅費、膳食、郵寄及其他費用。
熟人勸告我:「不要再替你師父主編這份雜誌了,他付給你做主編的單銀(薪餉)相當於一個木工或水泥匠一天的工錢。」也常有人勸我去幫亡者誦經,一天就可以賺二百元。然而從過去的經驗中我知道,當你沒有時間修行卻有錢揮霍時,人很容易沉溺在壞習性中。我的努力受到嘲笑,大家說:「你是受過教育的人,但是沒有錢。你編雜誌每月才二百元,而且這錢還不是花在你自己身上。」
我告訴東初老人這些嘲諷,他說:「如果一個出家人只想著錢,那他就不應該做出家人,出家人是為了奉獻而來的。」我明白了。
東初老人鼓勵我多看經書、寫文章和進入社區民眾裡。他說:「你該去弘揚你所懂的佛法,如果你只留在寺院裡,那就太消極了。」
那時來道場的人不多,在台灣幾乎沒有人講授佛法。東初老人要我帶著佛經,去向那些等公車的民眾講解佛經內容,他要我在街上和那些陌生人分享《人生》雜誌,並做公開演講。基本上,他要我採取基督教傳播福音的方式弘法,因為他們做得非常成功,他們甚至會來寺廟裡傳播基督教的福音!
東初老人繼續不停地以種種的方式考驗我,那都是日後我才明白的。當我被派去買米和油時,他給我的錢只夠買東西,不夠坐車。一包米對我來說太重了,我扛不回來,只好求那些卡車司機載我一程。當我的師父知道這件事情後,他對我說:「很好,你給那些幫助你的人有機會做功德。」
我想,他們能做出什麼樣的功德?他們只幫過我這一次,之後他們不會再出現。但是我已學會了不要違逆東初老人,所以我什麼也沒說。
當我被派去遠地辦事,像是去台中時,東初老人只給我一半的車資。
我對他說:「錢不夠。」
他責罵說:「你真笨!這些錢夠你買半程的車票,當你上了公車或火車後,你只要假裝入睡,這樣就可以一路抵達目的地。」
東初老人要省錢,並且也想看我如何去處理這種情況。有一次,車資不足,我被趕下車來,真是個丟臉的經驗。從那次以後,我懇求車上的其他乘客幫我付不足的車資,其實也沒有多少錢。這種方式被東初老人認可,他說:「你讓那些人修行彿法。」
東初老人沒有很多錢,只靠信徒微薄的供養和印行經書的少許利潤過活。我終於明白,當他派遣我出去而不給我足夠的錢,是他訓練我的一種方法,就像是在養蜜蜂而不是養鳥。當鳥是寵物,需要人飼養時,牠們會忘記如何獨立生存;而蜜蜂不須飼養,只要蜂巢在花叢附近,牠們就會去採花粉造蜜。這樣蜜蜂不但可以獲得自己的食物,而且人們還可以拿蜂蜜去賣錢。
有一天,我的師父指示我去佛前禮拜。拜了幾天佛後,他對我說:「這是一間佛教學院,你卻什麼貢獻也沒有,去寫些文章吧!」
他要我寫的文章都是在罵人。我說:「如果我老是在罵人,那每個人都要討厭我了。」
「你可以用筆名,反正你是一位剛出家的人。你應該發聲,主持正義。」
於是我寫罵人的文章。他看了以後說:「你寫得太差,罵人罵得太過分了。」
他一篇也沒登。他說:「罵了這麼多人,你造了很大的口業,應該去禮佛懺悔。」
我又回去禮佛了。一天,他對我吼著:「你在浪費時間,向一尊木雕像頂禮,一點用都沒有。你應該去好好看一些經書。」
他吩咐我去看大部的經書,不要看那些小的。《華嚴經》有八十卷、《大涅槃經》有四十卷、《大品般若經》有六百卷,我從《大品般若經》開始讀。
幾天後,東初老人問我:「看了多少卷?」我說:「三十卷。」我是一個看書很慢的人。
他咆哮著說:「你太慢了,太多的業障阻礙,像你這樣讀書,跟蟲在爬一樣,有什麼用。快去佛前禮拜,長點智慧吧!」
所以,我又去拜佛了。幾天後東初老人再次痛罵我:「聖嚴!看看你,你這樣做毫無用處。你應該做一些實在的事情,把你自己變得有用些。你的禮拜就像是狗吃屎一樣。」
我問:「那我該怎麼辦?」
他指向一堆磚頭,那些磚都被灰泥黏在一起。他說:「那道牆上的每一塊磚都是我們的信徒捐贈的。堆放在那裡閒置著,實在是太浪費了。你去把那些磚塊重新整理好。」
我小心翼翼地把磚塊分開,放得整整齊齊,預備著東初老人隨時可以用。我花了好幾天的時間去做,覺得進展得相當好。但當東初老人看到我所做的,竟然罵我:「我叫你去整理磚塊,可是你真沒用,這些磚塊本來是好好的,但是你卻把它們弄開打碎了。你要把它們黏合好。」
我看著那堆破磚想著:真糟糕,這樣做不僅沒有意義,又太麻煩了,根本沒有辦法把這些磚塊再黏好。我抗議著說:「我不知道怎樣做,不可能把它們黏好的。」
東初老人的身影巨大,雙手交叉環抱於胸前,以嚴峻不妥協的面孔看著我,他斥責我說:「你真沒用。聽說過大海撈針嗎?那才是不可能的事。為什麼無法把磚塊黏回去,供日後使用?」
從那時起,東初老人沒有再叫我拜佛、寫文章或看經書,我必須把磚塊黏回去。我覺得那實在是浪費時間,終於鼓起勇氣,去問東初老人:「是否真的值得花時間,把這些磚黏回去?」
他回答說:「你的時間值什麼錢?你在這裡白吃白住!有什麼問題嗎?快去把這些磚塊黏好,不要浪費財物。」
這就是師父的指令,我只好繼續去處理磚頭。起初我真是束手無策,後來奇蹟般地,事情變得容易多了。我終於看出這些磚塊是怎麼拼成的,我可以一天黏回三塊。我用了十五天的時間把所有的破磚黏好。我不知道當我把它們黏好後,師父要怎麼用,我只是照著做。
當我完成後,師父吩咐我:「現在把這些磚堆起來。」
我問:「那要怎樣做?這些磚都破掉過,沒法撐得住。」但是他堅持,我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去外面休息一會兒。就在我走著走著時,一個念頭生起──我看到野芋的大片葉子。
我把幾塊磚放在一片葉子上,磚頭上面再放上一片野芋,然後再放上幾塊磚。這樣子我就可以把磚一層一層疊上去,而不會倒下來。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才把這件工作完成,每一天我都想跑走,這工作實在是太令人厭煩也太荒謬了。
當磚塊疊好時,東初老人露出了難得的歡愉。他大笑著說:「你被捉弄了!哈!哈!哈!」他非常自得其樂地說:「這些磚是沒用的,為此你一定對我氣極了!」
我悻悻地說:「我是有一點生氣。」
他說:「但是你還不錯,你的確非常有耐心。」
或許是因為我顯現了耐心,所以東初老人讓我平靜地生活了幾個月。接著有一天,他指著廚房牆壁上瓷磚脫落的地方,對我說:「聖嚴,你要把它修補好。去建築材料行,買一模一樣的瓷磚回來,把掉落了的地方補回去。」
很好!這看起來不像是太困難的工作,我經常被派去做這種小差使,我完全不知道好戲就在後頭。
我進城買了我認為是一模一樣的瓷磚。當我回去後,我的師父說:「過來看看,它們並不一樣。你要拿回去退,並買回完全相同的瓷磚。」
我仔細查看這些瓷磚,的確,雖然我買回來的新瓷磚跟舊的看起來很相似,但它們不是一模一樣的。不過你必須看得非常仔細,才能注意到這點。但這點差異又有什麼關係呢?我正要提出抗議,但一看到東初老人的面孔,我就把嘴閉住了。我只好再回去那家瓷磚行。他們很不高興看見我,我只買了三塊瓷磚,現在又要回來退貨!他們拒絕幫我找我要的瓷磚。當然,我知道這不會是個好結果,但我又能夠怎麼辦呢?我回去告訴東初老人:「師父,我找不到同樣的瓷磚。」
「為什麼找不到?」他問。
「僅僅是三塊瓷磚,瓷磚行的人拒絕去找。」
「這樣你就放棄了?你真是笨頭笨腦。去找找看是哪一間窯廠造的。」
我跑遍城裡的每家建材行,詢問一個荒謬的問題,打聽是哪一間窯廠燒出這三塊不起眼的瓷磚。沒有任何人有絲毫的興趣,這是可預料到的。我一籌莫展,並開始覺得困窘。終於運氣來了,我遇到了磚廠的工人,雖然他不能確定那些瓷磚是不是他們造的,但他告訴了我窯廠的地點。我到了窯廠,牆上掛滿了一排排的瓷磚,但是我找不到完全相同的。我問窯廠的人是否可以替我燒瓷磚。他問我要多少塊。我告訴他:「三塊。」
他說:「我們是經營批發的,我不可能只燒三塊給你!」
我懇求地說:「請幫幫忙。東初老人一定要我找到三塊跟我們廚房牆壁上一模一樣的瓷磚。」
他解釋說:「每一批出窯的瓷磚,在顏色上都會有稍微的不同。你是沒法找得到同樣顏色的。」那店員告訴我,有另一間窯廠位在很遠的地方。
我問:「我會在那裡找到一模一樣的瓷磚嗎?」
他反問:「我怎麼知道?」
我覺得沒有希望,所以回去告訴師父,這是件不可能的任務。我解釋著:「每一批瓷磚在顏色上都有稍微的不同。」完全沒抱任何此事會就此打住的希望。
他說:「昨天我打聽到這些瓷磚是哪裡來的。」
「那我該怎麼去那裡?」
「你真是白癡!一路上問就問到了啊!」
那地方很偏僻,又很遠。我花了將近一天的時間。一路上,懇求別人替我出車票錢並徒步四處尋找,最後終於找到了。我詢問這些瓷磚的事,那負責人說:「我們燒過很多瓷磚。怎麼會知道這些是不是我們燒的?你需要多少塊?」
我說:「三塊。」
他們看著我,以為我是失了心神:「你一路來到這裡,就是為了這三塊瓷磚?我們太忙了,沒時間賣你三塊瓷磚。你應該到建築材料行去找。」
我回去了,什麼也沒買到,他們一定認為我是神經病。回程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我的師父才是發瘋了,提出如此不合理的要求。
我告訴東初老人:「他們不肯賣給我三塊瓷磚。」
「你真是死腦筋。你只要問是哪一家建築材料行購買他們的產品,然後去那家店買就成了。在那窯廠時,你應該問清楚,然後直接去買回來,不就辦妥當了嘛!這不是很容易嗎?那麼我們就不需要再說這麼多了。」我覺得又累又沮喪,忍著氣說:「僅僅才幾塊瓷磚而已。」我感覺到我好像是一個三十歲的小孩。天呀!我曾是軍隊中的軍官,出版社的作家,而現在卻在全台灣到處找瓷磚。「為什麼我們不可以買三塊顏色相似的?畢竟只是廚房的瓷磚。」
他說:「你在說什麼!如果我把兩片膠布貼在你的臉上,永遠留在那裡,可以嗎?」
我一語不發地乾瞪著眼,東初老人命令我再出去找瓷磚。我四處游蕩,沒有去任何地方,腦中懸念著東初老人的無理要求。我下決心要離開這道場。
當我回來以後,逕自走入我的房間,沮喪到了極點,麻木而無知覺。東初老人探頭進來:「你一整天到哪裡去了?」我拒絕跟他說話。
他走開了,接著拿了三塊瓷磚回來,驚呼著說:「我們真是幸運!我找到了三塊從前廚房整修時留下來的瓷磚,它們夾在牆上的裂縫裡。」他看著我笑:「哈!哈!哈!你又被騙了。你是一個和尚,怎麼可以氣惱呢?我逮住你了。真是十分好玩啊!哈!哈!哈!」然後,他就離開了。
我應該火冒三丈的,但奇怪的是,我內心的沮喪消失了。他離開後,我坐在房裡,感覺很平靜,情緒一掃而空。我意會到,我並不想離開東初老人,尋找瓷磚是他對我的一種訓練。
第十五章 吃苦
一個偉大的禪師,若沒有經歷物質的貧乏和精進努力,是不會成就的。我最初出家的狼山寺院,有很多的護持者,非常富裕。但是寺裡的小和尚必須接受三年的訓練。婦女做的家務事,我們都必須學著做:清掃內外、種菜、縫衣服鞋子,還有煮飯。只有一件事不必學,就是生孩子。這種訓練的目的是讓我們去除驕傲,不要輕忽勞力工作者。和尚們要有心理準備,會到沒有信眾的地方,就像西方傳教士一樣,因此必須知道如何打理作務。勞力活動幫助學生安心,排除妄念、去除分別心或我執。如果只考慮自己,或自身的得與失,寺院生活會變得艱難。如果不能定下心來,就會受苦。如果有平常心,寺院生活便是單純的。
在禪宗語錄中,有許多著名的吃苦或做粗重勞力工作的故事。唐代有一位年輕弟子跟隨著鳥窠禪師(道林禪師的別名)修行,師父住在樹上,徒弟則住在地上,為師父送水和跑腿。徒弟希望向師父習禪以開悟,六年過去了,師父卻沒有教授他任何佛法,只是叫他跑腿。徒弟感到很沮喪,有一天,他告訴師父說他要走了。
「為什麼要走?」師父問。
「我來這裡是學佛法的,」徒弟回答:「但我只是一直在跑腿,沒有學到任何佛法,也不能開悟。所以我要走了,我要去尋找其他的善知識,教導我所需要知道的東西。」
「喔,佛法,」師父說:「我這裡有一點。」師父慢慢從僧袍裡抽出一根鬆脫的線,吹向風中。就在此時,這名弟子開悟了。
當大覺寺的董事會在準備歡迎我的時候,他們心裡也想著這則故事。他們知道我剛完成博士學位,怕我傲慢不遜,所以要我「吃點苦頭」。
我不認為有此必要,我自小就學會了吃苦,可能他們並不知道。當我到大覺寺時,他們對待我像一般普通的出家人,沒有把我當成法師。他們要我擦洗和整理寺中的房間。我把原來都是廢物的地下室清理乾淨,變成一間教室和圖書館。我赤手空拳地把後院變成一座美麗的花園。
我沒有助手,一切得自己來。其他的和尚都比我老,而且戒長,沒有幫忙。當一卡車的書從日本運來時,我想辦法從碼頭搬回寺裡,安放在地下室的圖書館中。在多年閉關後,我已習慣獨立工作。
四周環境簡陋,那時候的布朗區,到處都是彷彿就要倒塌的房子和空蕩蕩的建築物。社區的居民多是貧窮的拉丁裔和猶太人,很少有華人。這裡主要是工業區及商業區。沈家楨居士買的這個寺院,原本是間郵局的倉庫。我來時,這兒沒有臥室,我住在地下室,一間黑暗、沒有窗戶、潮濕的房間裡,好像住在山洞一樣。我在牆上挖了個洞,讓一點光線和空氣透進來。
其他的法師好多了,他們住在附近租來的公寓裡,我是唯一住在寺中的人。沒有講經,沒有權力做決定、管人或管錢。我住在寺中以接待訪客,所以基本上只是個門房而已。
大覺寺每天的作息是很熟悉的。作為一個中國僧侶,不管你在哪裡,每天的作息都是一樣。我早上四、五點起床做早課,吃早齋和打掃清潔。如果有英文課,我會去上課;如果沒課,就整理地下室。如果有訪客,我負責接待他們,累了便休息一會兒。因為這團體不大,我的時間是有彈性的。午齋過後,稍事休息,然後清理房舍和道場。我常常單獨一個人,因為白天來禮佛的人很少。如果有時間,我會打坐。我通常提前在下午五點前做晚課,然後用藥石(晚餐)。晚上時間,我用來寫作、拜佛和打坐。星期六早上,我教一小群西方人和華人禪坐。星期六下午,為週日講經布置場地,通常我們是請資深的法師來講經。我必須打掃道場的裡裡外外。
由於我是住在道場的唯一出家人,除了行政工作由日常法師負責──因為他的英文程度比我好。此外,其餘一切都是我來擔當。但這些整理寺院的雜務,並不會造成我的困擾,因為我把它當作是一種修行。
感謝沈家楨居士,我「吃苦」的時間不長。後來他提名我為寺院董事和美國佛教理事會的副理事長,並指定我為大覺寺住持。這真是特殊待遇,因為我在大覺寺的時間還不到半年,我不認為其他出家眾會受如此禮遇。
在大覺寺,我不會講英文,起初並未造成問題,因為我剛到時,大多數常來的信眾都是華人。偶爾有些好奇的西方眾會來,但他們不知道要做什麼。他們覺得像是在另一個國家,尤其我們全都在講中文。假如華人看到一個西方眾,他們通常都說:「老外來了。」我常常提醒他們,我們才是外國人,而他們是本地人!
我知道我想和西方眾接觸,此時令我回憶起與一位在日本教我禪法的老師──伴鐵牛禪師的對話,當我向他表示擔心到美國會有語言障礙時,他給了我一個開示:「禪法不是用文字教的。」
這句話幫助了我,即使我的破英文在多倫多弘法時遭到困難。在紐約,我指導禪坐,沒有期望對學者和學生講經授課。禪法的重點是直指核心,任何文字或口述都只是隔靴搔癢,目的是指導學生,幫助他們證悟禪法。必須要學生自己能離文字言說,才能明心見性。
禪宗史上有位著名的大智懷海禪師,有一次弟子問他:「你能教我如何修行嗎?」
他回答:「餓了,就吃飯;累了,就睡覺,不需要文字和語言。」
我們不要以為禪修者有很多祕密,或是他們做的事情都是神祕的。他們真實地生活,單純不複雜,沒有想太多,任何人都可以過這樣的生活。
菩提達摩來中國時,不會說中文。歷史上有一個和尚問趙州禪師說:「我非常困惑,請您給我指點?」
趙州法師只是說:「你喝粥了嗎?」
弟子回答:「有。」
趙州禪師說:「那就去洗碗。」那弟子當下開悟了。
所以當我開始與西方眾互動時,我用了類似的方法。碰到學生求助於我,我會問他:「你吃晚飯了嗎?」
如果他回答:「是的」,我就告訴他:「去洗你的盤子吧!」
我常常用這種方法和學生聊天,尤其是沒有翻譯時,因為我無法用英文講述太多佛法,所以就把事情簡單化。當學生問:「是什麼原因?」我會說:「沒有原因。」他們似乎也懂了。有一次有人在電梯裡問我:「法師,什麼是真實相?」我說:「沒這種事。」他回答說:「太好了!」
我能表達的英文範圍內,已可以回答很多問題。但沈家楨居士仍非常關切,他認為在美國如果不學英文,會非常不方便。他為我請了英文老師,支付薪水,但我已經老了,近五十歲,學習語言真是不容易。記憶力不似年輕時,所以在超過三百小時的課程後,我喊停了。因為我變得非常忙碌,而且學費實在太貴了,沈居士尊重我的決定,另外幫我找了一個課程較少的英文班。
有一天,有兩個年輕人──法蘭克林和彼得到寺裡來,問我是否會功夫。
我說:「會。」
他們問:「你會什麼樣的功夫?」
「我會太極和少林拳。」然後,我告訴他們,我不教電影裡那種身體打鬥的功夫,我說:「我教人如何運用心:首先要學習訓練念頭和穩定自心,那樣才不會為人所傷。」
他們說:「真棒!」
他們帶了一些朋友來參加第一班的課程,一開始我不知道怎樣教他們,尤其是我沒有辦法真正使用英語教學。我擔心他們會失去興趣,但我還是繼續教下去了。我請一位學生王明怡幫我做翻譯,他是紐約大學數學研究所的學生,飽受嚴重的頭痛,跟我學禪坐後,他的頭痛問題消失了。
我們的禪坐課從週六上午到下午,每週一次四個小時。剛開始,我不知要做些什麼,便去請教日常法師,沈居士曾送他去紐約上州的羅徹斯特禪中心向菲力浦.凱普樓(Philip Kapleau)學禪修。
我告訴日常法師:「我曾在中國和日本很多寺院禪修,但不知道要在西方教什麼,所以想知道凱普樓的禪中心怎麼教?」
他說:「非常簡單,他們教數息,當學員能夠熟用數息法,心沉靜下來後,就可以參禪。」
我請日常法師幫我教學,起先他很勉強。我們談了一會兒凱普樓的事,他在美國已成為知名的禪師,師父是安谷白雲(Yasutani Roshi)。
「安谷白雲的師父是誰?」我問。
「是原田祖岳(Harada Sogaku)。」他說。
我告訴他原田祖岳也是我在日本的師父伴鐵牛的師父。這說明了我是凱普樓的師兄弟,因為我們都是原田祖岳的後裔,這讓我領悟到要如何教導西方學生。日常法師得知後非常高興,並且同意幫助我。
依照他的建議,我們先教學員數息法,其他的盡量簡單。我只給予學生幾句簡單的指示,沒有其他的了。我沒有課程內容,或特定的教學計畫。
三個月結束後,只有幾位同學還留下。他們在班上認真努力,而且對於方法和理念有很好的吸收。他們覺得找到了他們的老師。
法蘭克告訴我,他將在中央公園參加一場功夫大賽。他問我:「師父,當我比賽時,你可不可以坐在旁邊?我會向所有的人介紹你是我的師父。別人會認為有師父在旁邊,我不用打就能贏了。」
我覺得很有趣:「要是你輸了,他們會向我挑戰嗎?」
「沒有人敢向你挑戰的。」他說。
我笑了笑,說:「武術的最高境界是不需要用武器或擺姿勢。當別人攻擊時,你必須把自我意識放下,對手就不知道如何攻擊你。為什麼?因為他們無從下手。這是無我、無心的道理。當自我中心仍然存在的時候,無論是進攻或防禦,對方都能夠偵察出你防守的弱點,並加以利用。如果自我不存在了,無物可防,無處可攻,對方就找不到可以攻擊你的弱點了。」
法蘭克和他的朋友注意聽著,他們立志用功練習,以達到這種境界。
我告訴他們,「要達到這種境界,禪修工夫必須臻於完美。」
一些早期武術純熟的學生,正接受警察訓練,他們認真學習,讓我很高興,覺得自己有些用。他們用單純而真誠的心學習,我也以真誠心教導他們,所以他們全部都吸收了,結果全班都很有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