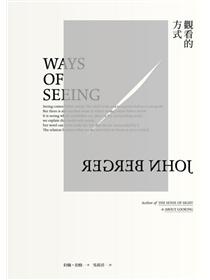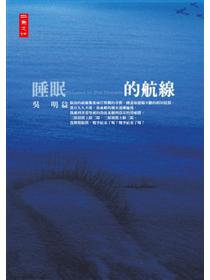本書收錄了蘇珊.桑塔格自《重點所在》(Where the Stress Falls)一書出版以來,所發表的文章。共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她為翻譯文學作品所寫的導言,第二部分是她對「九一一事件」的評論以及對攝影的思考,第三部分則是她公開發表的演說詞。
這本書的書名《同時》(At the Same Time),即是她在娜汀.葛蒂瑪講座演講的題名。桑塔格此一演講的副標題為「小說家與道德考量」,顧名思義,這篇演說的重點就在於,小說與道德。桑塔格在這篇文章中指出,「在我看來,一位堅守文學崗位的小說作家必然是一個思考道德問題的人:思考什麼是公正和不公正,什麼是更好或更壞,什麼是令人討厭和令人欣賞的,什麼是可悲的和什麼是激發歡樂和讚許的」。她並強調,這不是說教,「嚴肅的小說作家是實實在在地思考道德問題的」,在她心中,小說家是以這樣的面貌出現的:
他們講故事。他們敘述。
他們在我們可以認同的敘述作品中喚起我們的共同人性,
儘管那些生命可能遠離我們自己的生命。
他們刺激我們的想像力。他們講的故事擴大並複雜化我們的同情。
他們培養我們的道德判斷力。
作為一名小說家,同時身為一名公共知識分子,桑塔格的一言一行,提供世人一種不同於世俗的道德判斷。在二○○一年紐約遭受「九一一攻擊事件」後,桑塔格嚴詞批判了美國政府的信心喊話和悲傷管理。她認為,一個民主國家的政治意味著容忍分歧、鼓勵坦率,但此時已被心理治療取代。確實社會集體療傷是必要的,所以她說,「讓我們用一切手段一起悲傷」,但請別忘了,「我們不要一起愚蠢」。面對一再被灌輸,「我們國家是強大的」這種壯膽式的口號,桑塔格一貫地以「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態度回應:「誰會懷疑美國是強大的?但美國並非只需要強大」。
作者簡介:
蘇珊.桑塔格
1933年1月16日出生於美國紐約市。難以被歸類的傑出寫作者,不僅是一名小說家、哲學家、文學批評家、符號學家,也是電影導演、劇作家與製片。影響遍及各領域,與西蒙.波娃、漢娜.鄂蘭並列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三位女性知識分子,而有「美國最聰明的女人」的封號。
她每發表一本著作都成為了一件文化盛事。代表作品包括:1966年出版的《反詮釋》即成為大學校院經典,令她名噪一時。1977年的《論攝影》獲得國家書評人評論組首獎,至今仍為攝影理論聖經。1978年的《疾病的隱喻》肇於她與乳癌搏鬥的經驗,被女性國家書會列為七十五本「改變世界的女性著述」之一。2000年面世的小說《在美國》為她贏得美國國家書卷獎。
桑塔格一生獲獎無數,1996年獲得哈佛大學榮譽博士學位,並當選為美國文學藝術院院士,2001年獲得耶路撒冷獎,表彰其終身的文學成就,2003年再獲頒德國圖書交易會和平獎。雖然她已於2004年12月28日離世,但她提出的問題仍敲打著讀者的心靈,世界也從未停止對她的思考與懷念。
桑塔格部落格:http://www.susansontag.com/。
譯者簡介:
黃燦然
一九六三年出生於福建泉州,一九八八年畢業於廣州暨南大學,一九九○年迄今為香港《大公報》國際新聞翻譯。著有詩集《世界的隱喻》、《游泳池畔的冥想》和《我的靈魂》等,評論集《必要的角度》和《在兩大傳統的陰影下》,散文集《格拉斯的煙斗》。譯有《見證與愉悅――當代外國作家文選》、《卡瓦菲斯詩集》、《里爾克詩選》、《聶魯達詩選》、《巴列霍詩選》;卡爾維諾評論集《為什麼讀經典》(合譯)和《新千年文學備忘錄》;桑塔格評論集《蘇珊.桑塔格文選》(合譯)、《重點所在》(合譯)、《關於他人的痛苦》、《論攝影》和《同時》;拉什迪長篇小說《羞恥》和哈金長篇小說《瘋狂》。
章節試閱
一年後
自去年9月11日以來,布希政府就對美國人民說,美國正處於戰爭狀態。但這場戰爭具有特殊性質。考慮到敵人的性質,這似乎是一場看不到終結的戰爭。這是哪一種戰爭?
是有一些先例的。針對癌症、貧困和毒品這類敵人而發動的戰爭,是沒有終結的戰爭。大家都知道,永遠有癌症、貧困和毒品。也永遠會有像發動去年那場襲擊的可鄙的恐怖分子和大規模殺人者,又有一度被稱為恐怖分子(像法國抵抗運動被維琪政府稱為恐怖分子,非洲國民大會和曼德拉被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政府稱為恐怖分子)、後來被歷史正名的自由鬥士。
當一位美國總統對癌症或貧困或毒品宣戰,我們知道「戰爭」是一個隱喻。誰會認為這場戰爭──美國對恐怖主義宣布的戰爭──是一個隱喻?但它是隱喻,並且是一個帶有嚴重後果的隱喻。這場戰爭是被揭示出來而不是被實際宣布的,因為威脅被認為是不證自明的。
真正的戰爭不是隱喻。並且,真正的戰爭都有始有終。哪怕是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駭人、難解決的衝突,也有終結的一天。但這場由布希政府頒布的反恐戰爭卻永不會有終結。這就是一個徵兆,表明它不是一場戰爭,而是一種授權,用來擴大使用美國強權。
當政府對癌症或貧困或毒品宣戰,它意味著政府要求動員各種新力量來處理該問題。它還意味著不能由政府包辦一切來解決它。當政府對恐怖主義──由各種敵人形成的跨國的、基本上是祕密網路的恐怖主義──宣戰,它意味著政府可以做它想做的事情。當它想干預某個地方,它就會干預。它不能容忍限制其權力。
美國對外國「連累」的疑慮,早已有之。但是,本屆政府卻採取激進立場,認為所有國際條約都有可能損害美國的利益──因為就任何事情簽約(無論是環境問題或戰爭行為,或對待俘虜,或國際法庭),美國都要使自己受約束,遵守一些準則,這些準則有一天可能會被用來限制美國的行動自由,使美國不能任意做政府認為符合美國利益的事情。事實上,這正是條約的作用:限制簽字國對條約所涉對象任意採取行動的權利。迄今,任何受尊重的民族國家,都不曾這樣公開把條約的限制做為迴避條約的理由。
把美國的新外交政策說成是戰時採取的行動,就能夠有力地制約主流社會就實際發生的事情展開辯論。這種不願意提問題的態度,在去年9月11日襲擊事件後就已立即變得明顯起來。那些反對美國政府使用聖戰語言(善對惡、文明對野蠻)的人士遭到譴責,被指容忍這次襲擊,或至少是容忍襲擊背後的怨憤的合法性。
在「團結必勝」的口號下,呼籲反省就等於持異議,持異議就等於不愛國。這種義憤正是那些掌管布希外交政策的人求之不得的。在襲擊一週年紀念活動來臨之際,兩黨主要人物對辯論的厭惡依然很明顯──紀念活動被認為是繼續肯定美國團結一致對抗敵人。
把2001年9月11日拿來跟1941年12月7日比較,一直是揮之不去的念頭。再次,美國是一場造成很多人死亡(這一回是平民)的致命偷襲的物件,人數比死於珍珠港事件的士兵和海員更多。然而,我懷疑,在1942年12月7日,人們會覺得需要舉行大規模的紀念活動來鼓舞士氣和團結全國。那是一場真正的戰爭,一年後,那場戰爭仍在繼續著。
而目前這場戰爭,是一場幻影戰爭,一場按布希政府的意思去做的戰爭,因此需要舉行週年紀念。這種紀念,可服務於多個目的。它是一個哀悼日。它是對全國團結的肯定。但有一點卻是明白不過的:這不是一個全國反省日。據說,反省會損害我們的「道德明晰度」。有必要簡單、清楚、一致。因此,將不會有語言,但會借用那個仍有可能雄辯滔滔的過去時代的語言,例如兩黨都受用的蓋茨堡演說。但林肯那些演說不只是鼓舞人心的散文。它們是大膽的講話,在真實、可怕的戰時闡明國家的新目標。第二次就職演說敢於預言繼北方在內戰中勝利後必定形成的南北和解。林肯在蓋茨堡演說中所頌揚的自由,其關鍵是承諾把結束奴隸制做為首要任務。但是,當林肯這些偉大的演說在紀念「911」的活動中被援引時,它們就──以真正的後現代的方式──變得完全沒有意義。它們現在成為高貴的姿勢、偉大精神的姿勢。至於它們偉大的原由,則是不相干的。
這在美國反智主義的大傳統中屢見不鮮:懷疑思想,懷疑文字。而這非常適用於服務現政府的目的。宣稱去年9月11日的襲擊太恐怖、太具滅毀性、太痛苦、太悲慘,文字無法形容;宣稱文字不可能表達我們的哀傷和憤慨──躲在這些騙人的話背後,我們的領導人便有了一個完美的藉口,用已變得空洞無物的話來裝扮自己。說點什麼,可能就會惹來爭議。說話實際上有可能變成某種聲明,從而招來反駁。最好是什麼也不說。
當然,將會出現憤怒的圖像。眾多的圖像。就像老話可以再循環,一年前的圖像也可以再循環。大家都知道,一張照片勝千言。我們將重新體驗那次事件。將會採訪生還者和採訪受害者的家人。這是西方的花園的關門時間 。(我以前總覺得,最能代表目前對嚴肅和公正的重大威脅的廢話是「菁英」。現在我覺得「關門」這一說法也同樣虛假和可憎。)有些人會接受關門,另一些會拒絕,需要繼續哀悼。市政官員會大聲讀出死在雙子星大樓裡的人的姓名,這等於是美國最受稱讚的哀悼紀念碑──林纓(Maya Lin) 在華盛頓特區創造的互動黑石螢幕,螢幕上刻著(供閱讀、供觸摸)死在越南的每一個美國人的姓名──的口頭版。其他語言魔術的牙慧將陸續出現,例如剛剛宣布決定此後把河對面的紐澤西州的國際機場(聯合航空公司93班機 的死亡之旅即是從那裡升空的)稱為「紐華克自由機場」。
讓我說得更明白些。我不質疑我們確有一個邪惡、令人髮指的敵人,這敵人反對我最珍惜的東西──包括民主、多元主義、世俗主義、絕對的性別平等、不蓄鬚的男子、跳舞(各種類型)、暴露的衣著,嗯,還有玩樂。同樣地,我一刻也沒有質疑美國政府有義務像任何政府那樣保護其公民的生命。我質疑的是這種假戰爭的假宣言。這些必要的行動不應被稱為「戰爭」。沒有不終結的戰爭;卻有一個相信自己不能被挑戰的國家宣稱要擴張權力。
註:
西方的花園的關門時間:這是英國批評家西瑞爾•康諾利(Cyril Connolly)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所說的一句名言,意為美好生活的結束。
林纓(1959–):美國藝術家、建築設計師。
聯合航空公司93班機:該班機是被恐怖分子劫持來進行「911」襲擊的飛機之一,在賓夕法尼亞州墜毀。
美國絕對有權搜捕那些罪犯及其同謀。但是,這種決心不必是一場戰爭。在國外採取有限度、集中的軍事行動,不應變成國內的「戰時」。要抑制美國的敵人,尚有更好的、較少損害那些符合大家的公共利益的憲法權利和國際協議的途徑,而不必繼續乞靈於沒有終結的戰爭這一危險、使人頭腦遲鈍的概念。
攝影小結
1. 攝影首先是一種觀看方式。它不是觀看本身。
2. 它必然是「現代」的觀看方式──以先入之見偏袒各種發現和創新計畫。
3. 這種現已有漫長歷史的觀看方式,對我們期待在照片裡看到什麼起決定作用,也對我們習慣於在照片裡注意什麼起決定作用。
4. 現代觀看方式是碎片式觀看。人們覺得現實在根本上是無限的,而知識是無止境的。依此,則所有界線、所有整體的概念都必定是誤導的、蠱惑人心的;充其量是臨時性的;長遠而言幾乎總是不真實的。根據某些整體的概念來觀看現實,對塑造和形成我們的經驗有無可否認的優勢。但它也──現代觀看方式如此教導我們──否認真實事物的無限多樣性和複雜性。因此,它壓抑我們再造我們希望再造的東西──我們的社會、我們自己──的能量,確切地說,權利。真正的解放,我們被告知,是注意更多、更多。
5. 在現代社會,相機製造的影像是接觸我們沒有直接經驗的現實的主要手段。我們被預期要接受和記住我們對之沒有直接經驗事物的數目無限的影像。相機為我們定義我們認作「真實」的東西──而且它繼續把真實的邊界向前推進。攝影師如果暴露他們自己的隱蔽的真相,或暴露觀者居住地鄰近或遠方的社會中未被充分報導的社會衝突,則他就會特別受讚賞。
6. 在現代認知方式中,某一東西要變得「真實」,就要有影像。照片確認事件。照片把重要性賦予事件,使事件可記憶。一場戰爭、一場暴行、一場流行病、一場所謂的自然災害如果要成為廣受關注的對象,就必須通過各種向千百萬人散布攝影影像的系統(包括電視、網際網路、報紙、雜誌)來讓人們知道。
7. 在現代觀看方式中,現實首先是外表──而外表總是在變化。照片記錄外表。攝影的記錄是記錄變化、記錄被摧毀的過去。做為現代人(而如果我們有看照片的習慣,則按定義我們就是現代人),我們都明白所有身分都是建構。唯一無可辯駁的現實──以及我們尋找身分的最佳線索──是人們外表如何。
8. 一張照片就是一塊碎片──一次瞥視。我們累積瞥視、碎片。我們腦中都貯存著數以百計的攝影影像,它們隨時供我們回憶。所有照片都嚮往被記憶的狀況──即是說,難忘的狀況。
9. 根據把我們定義為現代人的觀點,細節的數目是無限的。照片就是細節。因此,照片似乎像生活。做現代人就是信奉細節的野蠻自主權,被細節的野蠻自主權迷住。
10. 認識首先是表示知道。表示知道如今是一種被認作藝術的認知形式。那些關於世界上大部分人受可怕的殘暴和不公正之苦的照片似乎在告訴我們──我們這些享有特權和相對安全的人──我們應激動起來;我們應要求做些事情來阻止這些恐怖。還有這樣一些照片,它們似乎要引起一種不同的注意。對這些進行中的大量作品來說,攝影不是旨在激發我們去感覺和行動的社會憂患或道德憂患的樣本,而是一個符號企業。我們張望、我們記錄、我們表示知道。這是一種更冷的觀看。這是被我們認作藝術的觀看方式。
11. 某些最出色的介入社會的攝影師的作品如果看上去太像藝術,就會受責備。而被視作藝術的攝影,也會引起類似的責備──責備它窒息關注。它向我們展示我們也許會哀嘆的事件和局勢和衝突,並要求我們泰然處之。它也許會向我們展示真正恐怖的東西,並成為對我們有膽量看什麼和有能力接受什麼的一種測試。或者,它通常──對很多最出色的當代攝影而言確是如此──只是邀請我們去凝視平庸。凝視平庸,同時也品嘗平庸,誘發那些非常發達的冷嘲熱諷的習慣,這些習慣已得到精緻的攝影展和攝影集常見的以超現實方式並置照片的確認。
12. 攝影──旅行、觀光業的最高形式──是擴大世界的主要現代手段。做為藝術的一個分支,攝影那擴大世界的企業往往擅長挖掘被認為具挑戰性、越界的題材。一幀照片也許是要告訴我們:也存在著這東西。還有那東西。還有那東西。(而這一切都是「有人性」的。)但我們該如何對待這種知識──如果它實際上是關於譬如自我、關於反常、關於畸零世界或地下世界的知識?
13. 知識也好,表示知道也好──關於這種特別地現代的體驗事物的方式,有一點我們是可以肯定的:這種觀看,以及這種觀看的碎片的累積,是沒完沒了的。
14. 沒有最後的照片。
小說家與道德考量
電視以一種極端卑賤和不真實的形式,為我們提供一種真實,而小說家有責任抑制這個真實,以維護小說事業獨有的倫理理解模式:也即我們的宇宙的特徵是很多事情同時發生。(「時間之所以存在,是為了使一切不至於同時發生……空間之所以存在,是為了使一切不至於都發生在你身上。」)
講故事即是要說:這才是重要的故事。它是把一切事物的擴散和同時發生縮減成某種線性的東西,縮減成一條小徑。
做一個有道德的人,就是給予、有責任給予某種注意。
當我們作出道德判斷,我們不只是在說這比那更好。在更根本的意義上,我們是在說這比那更重要。它是賦予一切亂糟糟擴散和同時發生的事物以秩序,並以忽略或不理會世界上發生的大部分事物為代價。
道德判斷的本質,取決於我們給予注意的能力──這種能力不可避免地有其極限,但其極限是可以擴展的。
但是,智慧,還有謙遜,也許是始於承認這樣一種想法、這樣一種震撼性的想法並在它面前低頭。這就是:想到一切事情的同時發生,以及我們的道德理解力──亦是小說家的理解力──無能力把這同時發生吸取。
也許,詩人較容易意識到這點,因為詩人並不完全相信講故事。二十世紀初無與倫比的偉大葡萄牙詩人和散文作家費爾南多•佩索亞(Fernando Pessoa)在其絕頂散文集《惶然錄》(The Book of Disquiet)中寫道:
我發現,我總是同時留意,以及總是同時思考兩樣事物。我猜大家都有點兒像這樣……就我而言,引起我注意的兩種現實都是同等地生動的。正是這,構成了我的原創性。也許也正是這,構成我的悲劇,以及使悲劇變成喜劇。
沒錯,大家都有點兒像這樣……但意識到思想的雙重性,並不好受,如果長此下去,是非常不好受的。似乎正常不過的是,人們都傾向於縮減他們所感所想的複雜性,以及關閉對存在於他們的直接經驗以外的事物的意識。
這種對延伸的意識──它吸取遠不止是此時、此刻發生的事情──的拒絕,難道不正是我們對人類之罪惡的意識總是混淆不清,以及人類有無比的能力去做壞事的要害所在嗎?由於無可爭議地存在著一些不痛苦、帶來快樂的經驗地帶,所以世間竟有如此多的悲慘和邪惡也就變成一個謎。大量敘述作品,以及力圖擺脫敘述和最終變成純粹抽象的思辨,都在質詢:為什麼存在邪惡?為什麼人們互相出賣互相殺戮?為什麼無辜者受苦?
但是,這問題也許應換一個說法:為什麼邪惡不是無所不在?更準確地說,為什麼它在某處──而不是無所不在?而如果邪惡沒有降臨在我們頭上,我們該做些什麼?也即如果被承受的痛苦是他人的痛苦,我們該做些什麼?
在聽聞1755年11月1日夷平里斯本(如果歷史學家是可信的話)並把整個社會的樂觀主義摧毀(但顯然,我不相信任何社會只有一種基本態度)的那次大地震的震撼性新聞時,偉大的伏爾泰(Voltaire) 驚詫於人們無能力理解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里斯本變成廢墟,」伏爾泰寫道,「而在巴黎這裡,我們卻在跳舞。」
我們也許會假設在二十世紀,在種族滅絕的時代,人們不會覺得以如此冷漠的態度對待同時發生在其他地方的事情有什麼不妥,或需要吃驚。難道經驗的基本結構的一部分,不正是「現在」既指「這裡」也指「那裡」嗎?然而,我敢斷言,我們對同時發生的截然相反的人類命運感到吃驚的那種能力──以及對我們沒有適當的反應感到沮喪──並不亞於二百五十年前的伏爾泰。也許我們永久的命運,是要對事件的同時發生感到吃驚──對世界在時間和空間中的無盡延伸感到吃驚,也即我們此刻在這裡,過著富足、安全的生活,不大可能餓著肚子上床或今晚被炸成碎片……而在世界其他地方,此時此刻……在格羅茲尼(Grozny) 、在納傑夫(Najaf) 、在蘇丹、在剛果、在加薩、在里約的貧民窟……
做一個旅行者──而小說家通常都是旅行者──意味著不斷被提醒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的同時性,你的世界和你去過的、又從那裡回「家」的非常不同的世界。
說「這是一個同情的問題……是想像力的局限的問題」就是開始對這一痛苦的意識作出回應。你也可以說,老是記著這個世界如此……延伸,老是記著當這在發生時那也在發生,是不「自然」的。
沒錯。
但我會回應說,這正是我們需要小說的原因:擴展我們的世界。
註:
4 伏爾泰(1694–1778):法國啟蒙思想家、作家。
5 格羅茲尼:俄羅斯聯邦車臣共和國首府。
6 納傑夫:伊拉克伊斯蘭教什葉派聖地,伊拉克戰爭主戰場之一。
一年後自去年9月11日以來,布希政府就對美國人民說,美國正處於戰爭狀態。但這場戰爭具有特殊性質。考慮到敵人的性質,這似乎是一場看不到終結的戰爭。這是哪一種戰爭?是有一些先例的。針對癌症、貧困和毒品這類敵人而發動的戰爭,是沒有終結的戰爭。大家都知道,永遠有癌症、貧困和毒品。也永遠會有像發動去年那場襲擊的可鄙的恐怖分子和大規模殺人者,又有一度被稱為恐怖分子(像法國抵抗運動被維琪政府稱為恐怖分子,非洲國民大會和曼德拉被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政府稱為恐怖分子)、後來被歷史正名的自由鬥士。當一位美國總統對癌症...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8收藏
18收藏

 54二手徵求有驚喜
54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