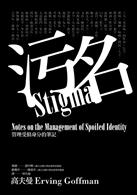鴛鴦蝴蝶派張腔同志小說極品
或許你不會知道,或許你會。在「異域」流離失所,如花般輕渺的棲身之處,就在你微微張開的手心裡。
書中十篇小說分別藏著十隻蠢動不安的靈魂,扇動著翅膀,掙扎衝破世俗規範和道德束縛。書寫同志的病和傷痛如〈他名叫伊薇蒂亞〉;連嫉妒都需要勇氣的〈雷光之夏〉;細數感情傷痕如〈花戀蝶,蝶戀花〉、〈紅〉;以戲謔的口吻探討同志婚姻的〈品名:張愛玲〉;游移在異境,遲疑踩向同性邊界的〈同窗會〉和〈賣根沙士〉;兄妹不倫之戀的〈白〉……等。而無論哪一隻靈魂,都是殘破的失敗者,都在死亡前華麗展示自己的翅膀,深切渴望一瓣柔軟的手,能輕輕拾起這些傷與痛……。
本書特色
帶有法國同志作家惹內(Jean Genet)的色彩,專寫敗德、禁忌之故事,悲傷和死亡意象重複出現,撕扯社會偽善的包容。文字又有鴛鴦蝴蝶派張腔氣味,辭藻豐富華麗,音韻節奏古典,彷彿作者就貼在我們耳邊,訴說溫軟繾綣的感傷情話。
同時選入許多作者攝影作品,有同志大遊行、舞蹈者和微小的自然景觀。透過一個邊緣者的眼睛,一幅幅凝止如畫的光影,在華麗與蒼涼的文字間緩緩浮現。
另外,封面特別邀請井十二設計研究室Wang Ivan操刀,設計出同一封面內含兩款造型。原封面為一朵充滿憂鬱氣息的靛藍色玫瑰,隨著角度折射出不同光澤;而沿著中央折線撕開,彷彿揭開作者的傷疤,一群灑滿金箔的蝴蝶隨之翻飛而起,卻也同時留下一道曲折的傷痕。一個封面,兩款造型,多重寓意,是設計迷不容錯過的經典之作。
作者簡介:
林柏宏,字戀。政大新聞系畢業,作品散見官方、民間雜誌。虛心拿過幾座文學獎,才華或許同浮雲懸漾。曾任記者、電視節目製作團隊等工作,目睹並經歷馬戲團式的生活,自此自在。披著波希米亞的外衣,過著布爾喬亞的日子,喜簡單生活。
臉書:http://www.facebook.com/altoman725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推薦序
周芬伶〈基化的藍調—林柏宏的同志新聲腔〉
第一次見柏宏是在臺中圖書館的演講,那時剛從香港回來,許是那兒的文學荒涼與人際擁擠,讓我較為惜福而不自私,對臺灣有股滿滿的文學新熱情,座中一個留大鬍子有遊民氣息的不明年紀的男子發問,一開口即知是重度文青,會後在馬路上等車時,他追出來,兩人在路邊小聊一陣。
之後再見是在《芬號500》——我將新的文學熱情化為臉書副刊,期盼能建立體制外的寫作自由學園,柏宏常來捧場,自稱是芬號起家的寫作者,這句話雖窩心,然小池塘怎容得下玉蛟龍呢?
漸漸知道柏宏不但是重度文青,還是重度表演者(能唱能演),這導致重度社會不適症,與重度同志憂鬱,原來他是苦海女神龍呢!
五年級的女同志常自比 苦海女神龍,如邱妙津、洪凌…等人,他們真的是苦,六年級雖在保守與開放之間,還能悠遊自得如陳雪,七年級就很辣了,較沒出櫃的壓力,也許是這樣,同志的文學已從上世紀末的酷兒化,在新世紀初出現「基化」的現象,也就是gay化的年代,BBOY當道,男性女傾,女性男傾,無論男女,青春小男孩當道,男的是花美男,女的是張芸京。當性別界線被穿越,表面上出現的是一大票的基兒作家,基兒不分男女,一致朝向陰柔與隱私化書寫,這些被稱為「私文學」大宗的背後不正是性別越界與文體越界嗎?純粹的異性戀作家聲勢變小,陽剛書寫也不再流行,異性戀也被基兒化了。
男性與女性書寫的極大化換來的是性別單一的終結,那所有的新世紀基兒不正該歡欣鼓舞嗎?
然而柏宏不是快樂的基兒,他很憂鬱,好像在生命中的哪一點被擊垮,像松子一樣自哀自棄,怎麼比苦海女神龍還苦啊?他說:「同志的問題還是很大!」
大在哪呢?以我對同志的粗淺瞭解,男同志的美眉與底迪;問題在他(她)們比異性戀女性還要歇斯底里與敏感,情緒的基調常是憂鬱的,他(她)們的感情被出櫃化之後,面臨的是更嚴酷的眼光,他們不被當作男人看待;也不被當作女人看待,而是非人看待。當社會認為同志不再是問題時,引來更大的問題,他們的歸類與歸屬呢,他們的人數不少,影響的也只有文學文化面,社會與政治與家庭根本是動不了的鐵板一塊。
彷如神人,有時垃圾;明明看見,卻遭刻板化。
這是柏宏書寫的背景,在基化的年代唱著沒人聽得懂的藍調。
柏宏還保留舊文青文字優美典雅的傳統,讀來有點老派,骨子底放浪到不行,百無禁忌,連宗教議題也不放過。
在基化的年代,同志書寫文字優雅,異性戀書寫則往粗暴一路走,雅言雖自愛,今人都不談,如今穢語與猥褻當道,如舞鶴、駱以軍、李昂(北港香爐)、胡淑雯、李維菁……等,一個比一個語不驚人死不休,髒話與褻語一大串,這是異性戀者的危機感造成的偏鋒現象嗎?穢語是父性語言中的暴力,找回「母語/髒話」是向父性靠攏嗎?或者誤解髒話化就是本土化,幹譙、喇塞也能當新聞標題,屌就是好,好就是不好,於是乎有表演工作坊的《母語》朝女性性器官進攻,七、八年級生左一句GY右一句屁啦,七年級作家寫髒話練習與陰毛,什麼粗野的話題都能入文。典雅的文學傳統似乎由同志文學來擔綱,如郭強生之淡雅,林俊穎之華贍,邱妙津之大氣、陳雪之頑豔,似乎從白先勇之後,文字與風格之典雅就一直由同志文學勉強支撐,連異性戀寫的同志文學勉強支撐,連異性戀寫的同志文也很華麗,華麗幾乎是同志文的代名詞,當典雅被摧毀之後,世紀初的同志文就帶有剩餘的懷舊華麗風。也許是這樣,柏宏的文字在俗麗中常會跳出讓人驚豔的語言。
男同志文學最動人的應當是性啟蒙的部份,有欲語還休的羞澀與永恆的銘記,如《白》中描寫主角與初戀男友的初夜:
與初戀男友,在我們心跳與手腳一齊慌亂的初次夜裏,交換清新愛液及紊亂的充沛體力後,無比疲軟卻情緒高張的相擁入夢。朦朧醒來,他在我耳垂呵呵浮字,他說,我們都活在一個連綿纏繞的雨季,因為這就是我們的一生。你與我的身體就像傘與主人,如果我是你的傘,你難保某天會失去我,我們只有一小段路途相陪的緣份。
初戀雖美卻只有一傘的路程,愛上異性戀(雙性戀)男子註定情感上的破洞,後來遇上威廉,長得像初戀男子的男人,展揩另一型態的三角戀,他發嗔想為他守貞,為他懷孕,卻遭到默言已對,才三十歲,他已覺自己是「失敗者」。
失敗者是此書眾多人物的命運,同志的一生就只能是纏連綿纏繞的雨季嗎?如〈他名叫伊薇蒂亞〉的跨性別者伊薇蒂亞,「阿姐,我的阿姐,伊薇蒂亞。你說過,妹仔咱這種人這款命,講好聽是跨性別者,難聽就是人妖,不妖不人,非男非女,命中註定浮浪貢,歹命一世人。」;還有〈紅〉中年向異戀修正的資深同志,連續好幾個自白「人過三十,回望自己是個失敗者,想是心中最大的悲懷」、「我決定辭職,像一個失敗者」、「我只是個失敗者」……,這個臺詞像魔咒一樣迴繞不去,只因「老是一種絕症,比死還可怕」,凡人皆怕老,同志尤甚,在青春無敵時是蝶戀花,在年老色衰時只有轉號,轉不了號的只有成為剩男剩女,他們沒有婚姻與兒女保障,老當然比死還可怕:
花(零)戀了蝶(一)一段時間後,花兒(零)難免會生膩生厭,枯薦而化為書頁中脫水乾躁的自製書籤,情或慾,消癟了去,蝶兒(一)也跟著疲倦,轉而流連野花間一叢一叢迷離虛幻的黃紅紫綠;倘若,蝶(一)戀了某一株花(零)加以追求,時而久之,蝶(一)的羽便成了標本,獨自翱翔在真空展示之中,被大頭針扎著、或被肉眼難辦的細絲栓著,花(零)不是跟著萎謝了去入土,盼成為來年春曉另一朵花(零)的絢美,就是精魂重新投了胎,變了另一隻蝶(一)。再不濟,只好悶出了果子,上餐桌待人下著,暗自祈求別餿了變廚餘給豬吃。
過去的男同文學,將同志自比為「花」已可自成一隱喻系統,從〈花月痕〉到〈孤戀花〉到〈花痴〉,但將零號與一號的關係說得如此殘酷而明白當推柏宏了,在花與蝶的關係中,往往是花兒(零號)先生厭倦,讓蝶兒消癟,(為什麼呢?花兒的賞味期太短?或者易老?)花兒老了只好轉化為蝶,或者成為眾人分食的果子,更下者成了廚餘。而這轉化可能只在短短幾年之間,同志的青春是如此短暫倉促,令人嘆息,這似乎是老調,但具有分析性。
柏宏的文字有舊文學底子,厚度較夠,在性別與情慾的探索跨度甚大,從男同到女同,從跨性別者到異國性漂流者,形成世紀初的跨性浮世繪,在手法上有新異之處如〈牆左牆右〉由牆的觀點對照左牆的中黏T與右牆的酒國名花,一個信主一個唸佛,藉由內心獨白說明她們乖違的人生,最後在K書中心認出彼此是小學同學,而似乎有了新契機,這一切似乎是神(佛)的安排?有拜有保庇,作者末了幽了神﹙佛﹚一默。〈張愛玲〉則描寫合法結婚的男同志育兒的科幻小說,他們訂製了一個名喚張愛玲的女兒,想要再有一個同樣的孩子,於是又複製一個妹妹,不料因爸爸生病,小張愛玲怕被感染逃走了。同志生子不是夢,但新親情新倫理恐怕是更大的問題。跟紀大偉的《膜》相比,在此篇看出柏宏的科幻不太科幻,想像力還是在寫實的範疇。
上個世紀末,解構與後現代將小說支解成碎片,後設與魔幻也玩到讓大家精疲力竭,新鄉土新寫實似乎是物極必返的結果,人們想聽完整的故事,而且是完整的好故事,小說家找回說故事的能力,努力說好一個故事,然而太陽底下哪有那麼多新鮮的好故事?因此拼命在文字上加料,造成文有餘而情感/情節不足的現象,我以為好的小說家能入能出,能夠創造另一個世界讓我們沉迷其中,因此想像力還是很重要,給我們驚喜,不只是華麗或粗暴!!
若真要從雞蛋裏挑骨頭,柏宏給我們的想像力與驚喜度還不夠,這種沒勁兒的作品還真是到處可見,都說新世紀了,該有新氣象,怎能沉溺於自戀或戀舊呢?作為新世紀之子應當相互期勉。
以一個新人的處女作,這本書夠豐富也到位了,但下一本呢?
媒體推薦:
本作品內容獲100年度國家文藝基金會文學類創作補助
《迷宮中的戀人》陳雪
《台北爸爸,紐約媽媽》陳俊志
《摩鐵路之城》張經宏
《狩獵家族》謝曉昀
《水兵之歌》、《人馬記事》潘弘輝
《叛逆柏林》陳思宏
中廣青春網《就在今夜》羅懿芬
露德之家秘書長 徐森杰
中部彩虹天堂 劉信詮
高中生制服聯盟召集人 徐豪謙
海馬樂團團長、藝術總監 徐灝翔
政大輕痰讀書會
共同推薦
《艷異-張愛玲與中國文學》、《雜種》周芬伶專文推薦
名人推薦:推薦序
周芬伶〈基化的藍調—林柏宏的同志新聲腔〉
第一次見柏宏是在臺中圖書館的演講,那時剛從香港回來,許是那兒的文學荒涼與人際擁擠,讓我較為惜福而不自私,對臺灣有股滿滿的文學新熱情,座中一個留大鬍子有遊民氣息的不明年紀的男子發問,一開口即知是重度文青,會後在馬路上等車時,他追出來,兩人在路邊小聊一陣。
之後再見是在《芬號500》——我將新的文學熱情化為臉書副刊,期盼能建立體制外的寫作自由學園,柏宏常來捧場,自稱是芬號起家的寫作者,這句話雖窩心,然小池塘怎容得下玉蛟龍呢?
漸漸知道柏宏不但是...
章節試閱
《花戀蝶,蝶戀花》內文連載
〈雷光之夏〉
雷來的時後,班機不偏不倚地降落在人潮散去的午后。機場一片空曠,時空單調,睡入了午后的慵懶乏味。他腳邊散佈著大包小包的行李,雖帶了一身疲憊,及旅人久桎於密閉空間的火氣,他還是抄本書,一本簡體書,書放在他翹起的二郎腿上,適切不過地,遮掩住他日益外凸的肚腩。在金門工作了一年多,養成了喫宵夜的習慣,且他大啖的,又都是熱量直逼卡路里上限的高粱、牛肉,復加上新陳代謝變慢,他吹氣球一般,君子重而不威了起來。一切壞就壞在,他耳垂處。點綴了個璀璨的假水鑽耳環,在風俗淳堯的金門,老百姓一眼即知,這是個都市人,還是有斷袖分桃之癖的,都市人。
他身形尚且玉樹瀟灑的一顰一笑,套到了現在,有種不舒服感,笨重感。他不是不清楚,但連自己都承認了,無疑直接否認了他前半生,那煙視媚行的前半生。也間接承認,他乏人問津的後半生。
光來的時候,唯恐機車沒了油,在雷面前大出窘態。出發前,他早有設想,加好了滿缸子油,但他沒估算好路之遠近,半路上也沒加油站,一切亂了套譜,處處與他作對。他暗忖,這是否為一個徵兆,先行警恫他,又不過是另一次心碎。光的小心翼翼,一旦劇化了,就是神經兮兮,總體現於,他對於細節的推敲之上,幾近乎迷信。
雷與光,自大學一別後,已有十多年沒見。雷被解雇後,在虛擬網路上的新交友平台,重逢了光。當雷直呼起,光多年之前的網路代號,lybindas,拼錯了的薰衣草,lavenders,使光陷入了百感交集。
像多年前一場煙花燦爛,被紀錄在某段影片,日後重映,回憶添了感慨的重量,哀悵也幻化作浪漫情調,足以粉飾掉所有過去曾經的缺憾。
雷的整個脊椎骨,硬僵了起來,因為他等光等太久了。然而他卻不埋怨,已是失業一族,剎那間大片的空白,使他怔恍失神,或可說自矜自憐,急切要抓住個安慰。據說,失業之苦,可比失戀。光想起了雷的說法,他上一份工作,是在駐點金門的國際公司,擔任翻譯一職,公司乃軍民合營,有柬埔寨的掃除地雷專家,新加坡的同事,中東裔的老闆,台灣方面負責掃雷的阿兵哥弟。
雷說自己沒當過兵,因為他早算好,在兵役徵召的臨門一腳,大大方方坦承自己的同志身份,此舉氣死了雷那位保守傳統的民代父親,上一次他父親勃然大怒,便是雷跑去上綜藝節目,又大大方方暢談,自己的出櫃新生活。
光對雷,仍遠遠持守一段距離,小心觀望。雷有一種犬儒式的靈活,一種包藏在知識份子裡的挑剔,或可說孤高刁蠻,未隨世故淡遠。多年前雷的伶牙俐齒,還是讓光不敢恭維。好比說,雷在網路上分別看了他照片、他視訊,光的身體部位多了贅肥,全逃不過雷的法眼,且一五一十透過對講麥克風,重點標記出來。
他也質疑,雷所說的一切是否捏造,聽來傳奇不過,遠渡重洋,在暗雷詭雷密佈的金門小島,雷為官兵專家們,進行翻譯一事?一憶及,光的想像中砲硝味四起,漫天飛埢的黃沙,嗆了光一鼻子灰,他咳,舊愛一如往事,又何嘗不是亢熱發燒後,那掏心扒肺的亂咳一氣。
想當年。他還是個菜比巴的甲車射擊士,才從運豬仔般的泊船,跨過白浪淘淘,從南台灣曝赤的陽光底下,轉至金門一冷便冷至凍餒的冬日,沒到幾天,他就開始受靶訓了。
首先,資淺的他們必須先到靶場,一行人扛沙袋拿鍬子,為靶機挖好了洞,再將早被銅油、黑漆覆蓋住鏽斑的機槍,埋入土裡,等到大家全到齊了,他們還得把風,俗稱「大顆仔」的餐車,一風塵僕僕地駛進,趕忙對連上學長使了使眼色,一夥人不動聲色,往攤車靠近,紛紛買了萬年油炸的蚵嗲、雞排,群聚於某個朔風野大的角落,滿手分不清炸油或機油,美美吃了起來。
到了某個紅綠燈口,他把機車停在路旁,撥一通手機給雷,歉聲說,再等一下就到水楠機場了,對方說沒關係沒關係,小心喔慢慢來。他心頭一暖,愛,總於曖昧時分,最令人柔腸寸斷,兩人都迫不及待,把一身最好的部份,秀給對方看。
光無邊無涯的想像力,又修正過一次。
土礪翻飛的片刻,地表好像徹底瓦解了,蕈狀的爆破土波飛濺,不及逃跑的拆彈軍士,失了足、仆了地。防護罩內,早已血肉模糊成一片,或許是被震得七孔流血吧。充斥聽覺的爆破聲,掩蓋了同袍淒厲的呼喚。如果受害者,換成慘遭人綑綁了一身引信的無辜百姓,當拆彈官兵表示,佈線太過繁複而時間太緊湊,束手無策,而奔相走避的前一刻。受害者的表情由扭曲轉為祥和,口中默禱自己生前的信仰。砰的一響,一條生靈不見了,地球仍然繼續轉動。
綠燈亮,光摧了下油門,告訴自己真是想太多。他自己的親身經驗,起個大清早,陪同營輔導長去拍攝砲兵連演息,也還沒完全甦醒的營PO仔(輔導長),問他,現在甲車上的監督官是誰,一聽是他連長,口中念念有詞,等下準備烙跑。果不其然,次次皆如此。後來,比營棧多賣了鑫鑫一口腸快去買,更扯、更為不脛而走的謠言,就是,連長的官運不夠,才會帶屎,連上出包連連,黑掉了,連長鎮不住嘛你說是不是。
到了機場,偌大的候車站前,一名警衛擎了根螢光棒,三七步站著。警衛看見光的機車,遠遠騎上了不禁止入內的上斜坡,正待發作,又懨懨地轉頭,視而不見。雷看見光,優雅自若的招起手來,兩人幾步之遙內對望,心底卻都在說,真是人事已非。他,老胖了許多。兩人卻仍是互覷笑笑,不發一語。
光眼神掃射了一遍雷的五六包行當,略略皺起眉頭。雷見狀,靈機一動道:「等下我騎車載你吧。」
光撓首搔耳,有點不好意思的道:「那這兩個行李,喏這個我揹身上,這個手提。這樣,應該就能騎到我家了吧。」
雷當然推拖了一下。但,三兩下的工夫,光就把行李上好身,雷也就沒再有所異見了。
臨出發前,雷哀嘆了口氣,道:「上次我在這,遇到一個可愛到不行的正太弟弟,沒想到現在他不在了。」
不在了?光滿臉狐疑,憋不住故又問了雷,後來方知,不過是萍水相逢,雷問路而對方好心幫雷指路,對方正對他胃口,如此而已。小小漣漪,值得他大驚小怪。光咂咂嘴,再追著問,雷你知道對方跟我們同性向呀?雷支支吾吾,語不成句。光也就心裡有個底。
安頓好之後,兩人往光的公寓騎去。
在某個街口,光趁機偷抓一把雷的胸脯,春色盈手。雷厲聲厲色,使光怯怯地收回手。下一秒,載著光的雷,冷不防加快了車速,並以一種驃騎的自在,穿梭在沙石車陣間,雷一心二用,推敲出光在他險險逼近大車後方,卻倏然一轉的分秒,不自覺地,一定會迫於緊張而摟抱他更緊些。便一再故技重施,兩人對這早是各懷不詭,反倒別有滋味在心頭。
光問雷:「欸你不是畢業於某某研究所,某某某你認識嗎?」
雷答:「當然呀!他很天兵好不好。之前我跟他一起考托福呀!他竟然花了兩次父母的辛苦錢,才考上。我一聽到差點把他給砍了。」
雷的誇張語氣宛然換了個人似的,光側頭想想,有些上了賊車之感,但好說歹說,車是自己的車,也不算賊車吧?連忙疊聲地與雷,一起說起某某某的壞話。兩人罵得興高采烈,分明是不同時期與某某結交,某某也從未幫他倆簽紅線,倒成了現成的月老。
雷使光想起了某些經驗,外島當兵,首當其衝的為金門迥異的台語口音,金門人說來,重輕全放在不同的音節,必須凝神,才能聽清楚。光雖說在金門服役,但活動範圍只在山外,再過去的金城狀況,就與一般觀光客差不多。他恍惚記得,金門的斤兩度量衡,與台斤不同。每逢金門週日島休,按規定大家需五人編為一單位,集體成行,後來也有不怕的各自解散,直到其中一員被憲兵糾舉出服儀不整,採連座處罰,大家才不敢掉以輕心。說到憲兵,光的話興又來,他自顧自樂道,
「我們以前島休,最怕碰到憲兵了。每當街上響起鐵片扣扣扣脆擊磚路的聲音,大家能鑽的鑽,能躲的躲,全跑到商家裡呀。有些商家便趁機要你買東西,你推辭不過也就買了。對呀,不成文規定哪,為了避免擾民,憲兵是不能擅自進入屋簷底下的民家,」
「還有啊……,」話匣子一打開,光不到一年的當兵生涯,又再次歷歷再現,足夠他說一輩子,「以前在山外,謠傳有個賣泡沫奶茶的女生,外號叫『金屁股』,為什麼你知道嘛?聽說她跟她媽,對一個士官長仙人跳,本來小兩口論及婚嫁,雙方家長都見過面了,婚前士官長凍未條,帶女生去開房,等他脫得精光,女生的胸罩一掉,哇靠她媽媽破門而入,拍照,索賠。士官長後來才知,女生根本未成年,認命賠了四十萬,黯然離開金門……。」
光還有那些這些夜行軍、鬼故事、離奇的逃兵傳說、島上用水桶而不用臉盆的過去,尚未一一緬懷。雷一張臉老下,就像光那些同梯的女友一般般,光噤了口,自討沒趣。
回到光的公寓,靜謐無人,機車也相對好停,畢竟是在空屋率高的台中。一推開門,電梯口的告示大喇喇寫著:
「各位住戶您好,目前本大樓電梯因故維修,若造成您的困擾,敬請見諒。 管委會上」
光忝臉不說話,尷尬瞄了雷一眼。雷一派鎮定,抓起行李就要上樓,光也順勢扛了兩袋行李。
雷變了?光一路跟在後頭,之字型樓梯間,呼吸迴響極大,畢竟兩人都已不是二十啷噹歲的小伙子。
午后的住宅區,靜得,偶有一些人家打孩子的吆喝聲、哭聲,成了唯一的背景音。金門,像是遠方的一個瞌盹,因為朦朧,在光與雷的記憶裡,客觀上同屬一地。不辨清楚就是兩個相仿的個體。
雷臉朝外,人雖然橫躺著,姿勢卻有一種撩人的媚態。他打開了褲頭的鈕釦,似睡又非睡,似矜持又擺明了勾引。他的肢體並沒有全然癱瘓的鬆。光知曉了雷的意思,欺身上去,雷推拒半天,眼神與嘴巴說的是兩個意志,過沒多久,該發生的,全都發生了。
燕好過後,雷方從四五袋行李中,掏出一個風獅爺小墜子,及一包綜合各大口味的牛肉乾。剛費了一番體力,光嘴巴饞,趁雷轉身去淋浴時,便把它拆開,細細點數,內有紅黃紫等包裝,分別為黑胡椒、咖哩、麻辣等口味。他隨性挑了一包,不由分說地吃了起來,眼神卻發現,有一張票根,脫落了牛肉乾的外包裝,杳杳掉落於地。他撿起來,是張台北往來新竹的公車票,再端詳下日期,沒多久的前天。他慢慢推估、回想,前天,他和雷在網路上相會攀談,雷不是告訴他,他人還在金門,整裝大大小小行李,先不與光閒話家常了嗎?光趁空問浸淫在水聲嘩嘩的雷:
「你前天提辭呈,還順利嗎?公司有給你該給的薪資嗎?」
雷回道:「有呀,說到這個就有氣,你知道,我那個上司。中東人。他老是看我不順眼,大概是嫉妒我跟誰都好,偏偏跟他不好吧!我還差一個月就聘約到期,不過是返台後,多給自己一天假。而且我本來就有積假呀!這樣公司馬上以逾假未歸為藉口,把我解聘了,後來,我媽也氣到打電話給我上司抗議,還爆粗口咧……。」
真的?還是假的?前一秒的歡歡愛愛,全蕩然無存,被雷淋浴時吹起的口哨,吹成了既薄又輕的空氣,像一個哈欠,像一個噴嚏,像,電梯裡一個沒人想承認的薰屁。光口頭上與雷來來往往著,身子躡手躡腳,把家裡放現金的抽屜上鎖,自己的錢包,藏在櫃子裡三五成層的衣物底下。
雷出浴間,上半身赤膊,穿一條小內褲。光煞時覺得雷的肉體,煥發出莫名的猥褻感,雷對他笑笑,悠悠哉哉便往客廳去了。光沒跟他去,反而人窩在臥房裡,悶悶不知該如何反應。兩人未語,直到天黑。
人聲雜沓的自助餐店,地上湯湯水水玷染的痕跡,發黏了起來,顏色也黑黑髒髒,盯久了會影響食慾的。眼前的雷,又好似另一個陌生路人,光有點想找出其一熟悉的角度,卻始終徒勞。雷反看光一眼,十分詫異。光只好問雷:「你來台中住我家,跟家人說過了嗎?」
雷翻撿了多為肉食的菜色,心不在焉,回道:「沒欸。」
光趁勢追問:「怕爸爸生你的氣?」
雷沒回應,臉上線條冷峻。
光轉過頭去,瞥及一對小冤家,正鬥氣冷戰。女的扠臂,臉氣鼓鼓的;男的,佯裝沒事,挑菜的手勁卻又說明了一切。光想起了,自己的年輕。
今年的夏天,不太乾脆地,與北方大陸的冷氣團一起作祟,時暖時凍,老令人摸不著頭緒。
《花戀蝶,蝶戀花》內文連載
〈雷光之夏〉
雷來的時後,班機不偏不倚地降落在人潮散去的午后。機場一片空曠,時空單調,睡入了午后的慵懶乏味。他腳邊散佈著大包小包的行李,雖帶了一身疲憊,及旅人久桎於密閉空間的火氣,他還是抄本書,一本簡體書,書放在他翹起的二郎腿上,適切不過地,遮掩住他日益外凸的肚腩。在金門工作了一年多,養成了喫宵夜的習慣,且他大啖的,又都是熱量直逼卡路里上限的高粱、牛肉,復加上新陳代謝變慢,他吹氣球一般,君子重而不威了起來。一切壞就壞在,他耳垂處。點綴了個璀璨的假水鑽耳環,在風俗淳...
目錄
目錄
周芬伶〈基化的藍調—林柏宏的同志新聲腔〉
〈自序──我曾愛過一個男孩〉
〈同窗會〉
〈他名叫伊薇蒂亞〉
〈花戀蝶,蝶戀花〉
〈牆左牆右〉
〈紅〉
〈白〉
〈雨,聲聲慢〉
〈雷光之夏〉
〈賣根沙士〉
〈品名:張愛玲〉
《花戀蝶,蝶戀花》內文連載
請見下方
目錄
周芬伶〈基化的藍調—林柏宏的同志新聲腔〉
〈自序──我曾愛過一個男孩〉
〈同窗會〉
〈他名叫伊薇蒂亞〉
〈花戀蝶,蝶戀花〉
〈牆左牆右〉
〈紅〉
〈白〉
〈雨,聲聲慢〉
〈雷光之夏〉
〈賣根沙士〉
〈品名:張愛玲〉
《花戀蝶,蝶戀花》內文連載
請見下方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