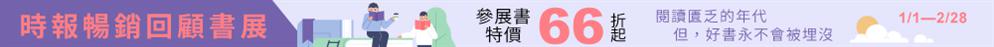附件二(內容試閱/5篇)
烏老師
烏老師是山東人。四方形鼓鼓臉,眉毛重,眼睛大,五官輪廓清晰,厚道淳樸之相,正是齊魯男人的特徵。
我讀大學時,烏老師教我們文學史。不只他一人教,好幾個老師,依照各自不同的研究方向,組合成四五人的教授小組,輪換上課。有人講重要作家,有人講文學社團,諸如此類。烏老師負責的,是最不重要的一段,一看就是別人挑剩下的。一半因為烏老師脾氣好,隨時笑眯眯,謙恭的樣子;另一半原因,烏老師是個工農兵學員。
那是八十年代中期,恢復高考後培養的第一批碩士、博士已經執掌教鞭,他們是地地道道的天之驕子,而「工農兵學員」,轉眼間變成學問差、能力弱的代替詞。沒人再去想,新培養出來的這些碩士、博士當初走進校園,第一個接過他們手中行李捲的、第一任他們的班主任,都是烏老師這樣的工農兵學員。
烏老師們吃了時代的虧,但又誰也怪不得。被人蔑視,也只能把那些鄙夷的目光和輕浮的議論吞進肚子裡,找背陰處自己慢慢消化。平日裡,還得時刻保持謙虛謹慎狀態,處處行事小心翼翼,不然會更被輕視,甚至,被罵。
學校開始新一輪職稱評定工作,教授、副教授的名額攏共沒幾個,僧多粥少。烏老師在這個學校教了小十年書,還是個講師,而他的學生中,已經好幾個教授。有天下了課,我正往宿舍晃,烏老師騎車追上來,寒暄半天,幾次欲言又止。最後終於忍不住開了口:我申報……評教授……據說……這次要聽……學生意見,你幫寫一份……話沒說完,烏老師臉已漲到通紅,大大的眼睛直往下耷拉,羞得什麼似的。
那次評定的結果,烏老師的學生中,又有幾人成功晉級副教授,烏老師落選。烏老師邀了幾個給他寫意見的學生,到實習餐廳聚餐。他說,早想感謝,可評選結果不出來,怕有賄賂之嫌,沒敢。
烏老師一如既往地笑眯眯,一如既往地教最不重要段落,一如既往地騎著那輛擦得鋥亮的自行車,在校園穿梭。隔日我們上大課,看到烏老師也在教室最後排的犄角處坐著,低著頭。上課鈴響,講課師進來,照例掃視全體同學,算是與學生互致注目禮。掃到烏老師時,講課師一愣,繼而微微頷首。我回頭看,烏老師正尷尬地笑眯眯。這位講課師,是他的學生之一。
課後我問烏老師,任務?互相聽課評判?烏老師笑眯眯地答:不是不是,來取取經。到底是博士,講得真是好。
我們畢業了,我去一家出版社報到上班。鬥轉星移,人越來越忙碌,大學生活的點點滴滴早拋到九霄雲外。一天傍晚,正在辦公室收拾東西準備回家,突然有人敲門。竟然是烏老師。
寒暄之後,烏老師幾乎是囁嚅著表達了來訪目的——又一輪職稱評定開始了,系裡說了,烏老師一把年紀,沒功勞也有苦勞,無論如何解決一個副教授。不過烏老師硬體不合格,沒有學術專著。可這麼多年下來,沒寫就是沒寫,再說什麼也來不及在一兩個月裡寫出一本專著來啊,於是系領導又說了,編一本什麼吧,系裡睜隻眼閉隻眼,照顧一下。
烏老師說完,從隨身攜帶的一個舊舊的公事包裡掏出兩個厚厚的檔案袋,袋子裡,是烏老師編的書,一本文學作品賞析集。烏老師說:我知道這書沒人買,我不能讓你為難,我準備了三萬塊錢,就算自費出書,行麼?
望著烏老師滿是期待表情的那張臉,我使勁點了點頭。烏老師臉上頓時綻放出欣喜的光澤。又從包裡掏出一個信封遞到我手上:辛苦你了……這個……一點意思……
烏老師又一次話未說完,臉紅到脖子根兒,倉皇欲逃。我一把揪住他,信封硬塞回他手裡,什麼也說不出來。這時,烏老師重重重重地歎了一口氣,臉上萬般神情瞬間滑過。
小黃
劉曉慶唱過一首歌,裡邊有句詞叫「我還是最愛我的北京」。這話擱小黃身上最合適了。不過小黃不是北京人,江南生江南長,二十二歲拎個大箱子到北京,原因說起來很文藝。
小黃上學時迷上北京的一本文化雜誌,期期不落堆在床頭,本本翻得起毛邊兒。那雜誌在網上有個論壇,她就沒日沒夜泡在裡頭玩。小黃特別有激情,每帖必回,每回必誇,而且誇得由衷。那些小黃原來常在雜誌上瞻仰到大名心生敬佩的人,也在上面玩,慢慢都被小黃的執著感動,和她成了親密網友。
小黃學電腦的,但經這論壇的薰陶,對原來專業心生厭倦,說起文化圈的事卻如數家珍。又因為論壇上的網友大多在北京,小黃的心時時刻刻向北京飛奔。轉眼該畢業了,小黃做了人生的大決定:去北京。
剛到北京時,正值論壇最興盛階段,網友們排著隊請小黃吃飯,天天一小聚,兩天一大聚,小黃那麼害羞的小姑娘,猛然間習慣了一件事:擁抱,因為每個網友在她眼裡都比兄弟姊妹還親,小黃對身體親密接觸的接受,完全發自肺腑。
網友們大多在媒體工作,所以小黃在北京雖然沒工作,但靠給朋友寫稿子,即可維持生計。多年來對文藝圈的關注,讓小黃寫東西很快上路,加上年輕聰明,又肯吃苦,勤懇好學,不恥下問,把所有網友都當成老師,沒過多久,小黃的採訪稿比很多老記者寫得都優秀。稿約越來越多,小黃再參加聚會,經常不等散席就戀戀不捨地先撤,因為還有幾千字的稿債。
冬天降臨,那個論壇仿佛隨天氣變冷而漸漸蕭條,小黃經過密集見識各種文化名人,對北京的神秘崇敬之情也慢慢打消,對人生的聚聚散散開始有了些體會,開始期盼穩定的生活。文藝圈最勢利眼,小黃雖然稿子寫得好,但沒有相關學歷,所以很難在媒體找到工作。其實也有願意接受的,但小黃起點高,一般媒體還真瞧不上。她去了一家公司,成了標準的白領麗人,但網友們都知道,小黃心裡,還是想當個好報刊的好記者。
後來小黃故鄉最大的報社招記者,她猶豫很久,聆聽每一個親密網友的意見,又做了個大決定,拎著大箱子回故鄉。上火車那一刻,小黃把來送行的網友抱來抱去,眼睛哭得腫成桃。
小黃回去後,很容易通過了考試,很快就成了報社的主力記者。因為分管文化娛樂,所以常來北京採訪演唱會之類。每次來都樂得合不攏嘴,逐個擁抱新朋老友。可一到該回去的時候,就又哭成淚人兒。有一次分別宴上,小黃借著酒力突然一拍桌子說:奶奶的,我還是最愛我的北京,我要回北京!
小黃迅速回故鄉,從那家報社辭職,又殺回北京。從那以後小黃有了明確目標:回北京,當好記者,二者缺一不可。可是世間萬事,哪件不是說來容易做來難,一晃三年過去了,小黃在北京與故鄉之間奔突無數個來回,還是沒能將兩個理想完美統一起來。北京不缺工作,但沒有小黃看得上的媒體;原來的報社隨時歡迎小黃回去,但她又捨不得北京。小黃的眉頭一天比一天緊,偶爾也開始感慨:唉,老啦老啦。
這個秋天,北京的天格外藍,小黃突然接到故鄉報社的正式邀請,請她作為報社的正式員工,籌建報社駐京辦事處,就由她常年駐紮北京。和小黃初來北京時被大家請吃飯不同,這回是小黃分期分批地請大家吃飯,每一次飯局開始,小黃照例和大家狠抱,然後亮著嗓門宣佈:這回我真算個北京人啦。
小茹
大學四年終於熬到了最後一個夏天,學分修滿,考試全過關,小茹的心野了,開始瘋玩。白天睡大覺,醒著也是懨懨的;天一擦黑就滿臉放光,躍躍欲試,沖出校園,融入北京洪流般的馬路車陣,向飯館、酒吧、夜店飛奔。
同學們都在忙正事兒,四處應聘尋求出路,小茹看似不著急,天天玩,其實心裡有更大譜兒。她可不想按部就班到公司或者什麼國營單位從小職員混起,小茹的宏偉計畫是,畢業後第一年,掙到人生的第一個一百萬。
小茹的策略是,先直接進入事業成功人士的圈子,再尋求突破口。憑的呢,就是自己年輕貌美。
事業大成功者,歲數太大,都是父輩的年齡了,而且見多識廣,身邊也不缺美女,不合適。二十啷當歲的小夥子固然也有成功的,但不穩定,積累太少。最合適的,是那些三十出頭的,在自己的行當已經打拼了十幾年,小有成就者,正是春風得意的階段,心思正活,年齡上和自己也只有十來歲的差距,正合適。
小茹天天和這些「老男人」混,跟著吃跟著喝跟著玩,享受美女待遇,處處受照顧。有時候小茹也會想,自己這樣是不是太功利了?轉念琢磨,這些老男人,也是個個有才情,風趣幽默,比那些傻不楞登的同齡同學好玩多了,至少一起玩不悶吧。想到這裡,小茹就想,自己天性就喜歡成熟的異性吧。
更何況,小茹還有一百萬的目標呢。這一宏願,小茹從不掖著藏著。一次和幾個老男人正喝泰奎拉蹦Tequila Bomb,歡笑中小茹突然發出這一豪言壯語。
「老男人」之一頗不以為然地問:你個剛畢業的小娃怎麼實現呀?願聞其詳。
小茹像在學校參加四有新人演講一樣,從容不迫答道:就說你們幾個吧,白天各自在自己的領域中吒吒風雲,晚上湊一起,就純粹喝酒玩耍,你們從來沒有想過合縱連橫。其實你們之間就存在好多生意,但你們沒這心思,也沒這時間。沒關係啊,現在有我啊!我來做這件事,我靠你們掙錢,但我掙的永遠只是小頭兒,大頭兒肯定還是你們自己的,誰跟錢有仇啊你們!說到酣處,小茹豪情萬丈,不讓鬚眉:這個時代早不是做雙鞋子掙十塊、做一百雙鞋子掙一千塊的時代了,現代社會,必須要靠合縱連橫,尋求利益最大化。
像小茹一樣有宏願的人很多,像小茹一樣腦子靈的人也很多,但是到頭來,沒幾個人實現願望,原因出在十人九懶。小茹不一樣,有理想,也真實幹,很快摸索到頭緒,將願望落在實處,起早貪黑真抓實幹起來。
「老男人」們當然由著她,凡她要求,必配合。小茹很懂事,每次提的要求,都合情合理,從不為難每個人。「老男人」們畢竟社會經驗豐富些,嘴上不說,心裡明白,小茹能做到這一點,背後下了多少苦工夫。如此一來,對小茹的照顧中,又多了些敬意。
一年過後,小茹和幾個「老男人」衝到夜店蹦迪,天快亮要散時,「老男人」要買上萬塊錢的酒單,小茹一甩頭髮說:我買過了,今天是我畢業一周年紀念日,我真的掙到了一百萬,算我請幾位老大哥。
本來要散的酒局重又開張,大家為小茹舉杯慶賀。酒至深處,小茹借著酒勁,懇請大家安靜,說有事宣佈。「其實,早就愛上你們中的一個人,但怕耽誤自己做事,更怕關係複雜你們說我俗,就一直強忍到今天,你們都不知道,包括我愛的這個人,今天,我實在忍不住了……」
老狼
對,唱歌的那個老狼。
和老狼相處二十年以上的朋友說起他,有個共同印象:好像從未聽過他抱怨什麼。老狼有張專輯叫「晴朗」,倆字兒亮堂堂的,聽著就舒坦,安他頭上真是貼。也正因此吧,老狼人緣兒特別好,要敞開大門交朋友,得累殘。好在他以低調著稱,不濫交,所以在光鮮的演藝圈那麼久,常來常往的朋友還是老幾位。
和朋友們在一起的老狼,是最隨和的一個人,也是最會照顧人的一個人。一群熟人吃飯,偶爾會有生人入夥,別人無暇他顧,總是他不時關心地跟人家碰杯酒、聊兩句。去年春節大假,他們夫婦和幾個朋友去尼泊爾旅行,隊伍中有對夫婦帶著六歲的兒子,一路下來,小男孩要求「嫁」給老狼。問為什麼,小男孩說:老狼叔叔最疼我。小男孩的媽乍聽有點不服,回想片刻,一拍腦門:還真是!這一路好像兒子老在老狼的肩上扛著。
早上老狼睡到自然醒,下午或排練,或四處逛逛,夜幕一降,他一天的黃金時段拉開了序幕。
夜裡,老狼常去朋友的酒局。老狼酒量並不大,更不饞酒,但是朋友們甭管誰組局,都盼他來。原因簡單:既是酒局,固然喜歡酒量大的,但更喜歡酒品實誠的。老狼喝酒從不偷奸耍滑,酒品太好了。
更多的夜裡,老狼會出現在檯球廳。他媳婦找不著他的時候,會把電話直接打到檯球廳,十有八九,老狼正熱火朝天地和朋友們切磋球技。「切磋球技」是個文雅說法,其實是切磋人民幣。全是熟透了的朋友,小賭怡情。輸贏很小,不是目的,只為互相擠兌看對方起急好玩。對於一個不愛去夜店,更煩卡拉OK的人,在北京城之夜,能迷上檯球這一口兒,是個不賴的愛好。
還有足球,也是他夜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歐洲杯、世界盃期間,現場直播多在夜裡,那段時間,老狼推掉一切工作和聚會,專心致志在家看球。碰上實在推不掉的事,也約到有電視的酒吧。
不過上述這些,都是老狼隨和的一面,隨和的外表下,老狼骨子裡覺得這種生活有點無可奈何。生活在北京這樣的城市,還能怎麼著?找樂唄。老狼真正最喜歡的,是外出旅行。在他看來,旅行多少有點革命的意味在裡頭,能反反日常生活的固定、機械的模式,讓人有種不安定感,讓人敏感,促人思考,能別具隻眼看待生活。
我就聽他聊過在尼泊爾,夜裡獨自在一座古城瞎轉悠,看著昏黃燈光下的古城,仿佛時光倒流回到百年之前。那種時空變幻之感,讓他新奇,讓他浮想聯翩。在撒哈拉,一望無際的大沙漠,他坐在沙堆上數星星,那種靜謐、空曠之感,讓他至今猶為嚮往。在藏區,有一次他獨自爬山登頂,夜裡在山頂宿營,感覺人隨時都有可能與整個山體徹底交匯。在馬裡,他所跟隨的車隊趕夜路,雖然一會兒戈壁,一會兒叢林,一會兒過河,但四野一片漆黑,只能靠車輪胎傳導到身體的感覺,感知地形狀況。半星亮光都不見,也沒有任何參照物,人會完全失去方向……
說起這些的老狼,才是最骨子裡的老狼,隨時神往能夠回歸野外生存的狀態,希望自己能像動物一樣機警、敏銳、強健,他覺得那樣的生活更真實,更有意思。而眼下正在經歷的城市生活,不過是在一些虛幻的假象裡苦中作樂。
卓瑪
是不是藏族小姑娘一半以上都叫卓瑪,藏族小夥子一半以上都叫扎西?我上大學頭一天,結識一個藏族同班女生,名字就是卓瑪,從此同學四年。
卓瑪是青海的藏族,不像一般藏族姑娘長得黑,但也完全不能說白淨。臉上沒有那個時候一般藏族人都有的高原紅,但整體紅紅的,不是白裡透紅,而是紅裡透紅,氣色好極了,看著就結實、健康,在一班剛剛經受了高考摧殘的豆芽菜似的漢族女生堆裡一站,有定海神針之感。
卓瑪第一次開口和我寒暄,問的竟然是:你父母是幹什麼工作的?我答:作協的。卓瑪神情一凜,沒再說什麼。我暗暗對她這問題和這神情稍有疑問,但也沒再說什麼。
後來相處得多了,對卓瑪上來就問父母這件事,不再有疑問,因為卓瑪是那麼孝順的一個姑娘。剛進校園時,所有外地同學的家信都寫得可勤了。但是兩年之後還能保持每週寫家信的,就沒幾個了,卓瑪是一個。每次接到家信時,卓瑪紅紅的臉,被興奮的情緒漲得更紅了。
卓瑪性格好,從來不慍不惱,永遠露著一口好看的白牙笑。藏族姑娘特有的那種濃密烏黑的頭髮,瞧著有股忠誠相。所以好多女生都把卓瑪引為閨中密友,找她吐露心事,找她商量該對喜歡的男孩怎麼表達。
卓瑪沒談過戀愛,自己也稀裡糊塗,當然提供不出什麼實質性的參考意見。但是不要緊,女孩子們找卓瑪、找卓瑪吐露心事、找卓瑪要參考意見,這些都是第二位的,她們看中的,是卓瑪的忠誠、貼心、嘴嚴實,不讓她說,就打死都不說。
臨近畢業時,都忙著畢業分配,整天填各種調查表。有天我正填一張家庭人員情況調查表,卓瑪在一邊看到,要過去看。剛看兩行臉漲得通紅,氣憤地沖我吼:你這個人,人品有問題。我嚇一跳,要聞其詳。卓瑪說:剛進校時我問你父母做什麼工作,你說是工人,可你現在填的是在「作協」,文化人。你撒謊,不是原來撒謊,就是現在撒謊。
時隔四年之後,我終於對她當時那一凜的神情也打消了疑問——她把「作協」聽成「做鞋」了。
畢業了,很多同學削尖腦袋設法留在北京。一些分配到外地的,隔了幾年,也用盡各種辦法重回北京。卓瑪當然是回了青海老家,因為她的父母在青海,而她又是那麼孝順的孩子。她在一所大學裡當老師,教文學理論,一教二十年。
有一年,卓瑪趁著暑假來北京找同學玩,一見當年那些閨蜜,三十多歲的人了,興奮得手拉手蹦起來,連續蹦,蹦個不停。好不容易坐穩了,大家打探卓瑪的生活狀態。出人意料的是,卓瑪不再言必談父母,而是換了言必談丈夫。丈夫長,丈夫短,丈夫讓她少吃冰東西;丈夫讓她出門要節約,多坐公車,少打車;丈夫讓她每天往家打個電話……
有人問卓瑪,你還沒說你和你丈夫怎麼認識的呢。卓瑪聽了十分不解地一愣——怎麼認識?還能怎麼認識?父母包辦的啊!這回輪到大家十分不解地一愣:這都什麼年代了,你還心甘情願讓父母包辦婚姻?還這麼理直氣壯?卓瑪又是一愣,然後掏心窩子地說:父母那麼大年紀了,比我們的人生經驗豐富多了,難道不該聽他們的麼?他們難道會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