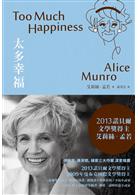黑夜裡白手起家
巴斯奇亞死時二十七歲。趴在他公寓的地板上,嘴邊有一小堆嘔吐物。他死於藥物過量。
巴斯奇亞是徹底的「白手起家」。他住在布魯克林,學校在布魯克林,十七歲,晚上跑到曼哈頓遊蕩,用噴漆在建築物外牆上留下神祕的句子。天亮,城市醒來,身上留著他的夢囈,署名SAMO。SAMO現象引起注意,《村聲》雜誌刊出專文報導。那是一九七八年,巴斯奇亞即將成為第一代由街頭走入畫廊的塗鴉藝術家。
即使現在看,巴斯奇亞給人的感覺還是很強烈。那樣的強度或許再也不會被超越了。在巴斯奇亞之後,從街頭到藝術的通路已經打開,標在藝術的地圖上。世人已經知道,在牆上塗鴉寫字,有可能名利雙收哦!事情在變得可能的同時,也在失去它的力量。在巴斯奇亞之前,不存在從街頭到藝術的任意門。因此巴斯奇亞的白手起家至少包含三重意義:出身寒微黑人家庭;沒受正規美術教育;他為自己打開一個國度,是那裡最早的藝術家。
成名後的巴斯奇亞從街頭轉移到畫室。但他的名氣更多來自畫外的世界。八零年代的藝術界,真像今天的娛樂圈,藝術家都勤於跑趴。他穿著阿瑪尼西裝作畫,濺得衣服上都是顏料,然後穿著同一套西裝去參加宴會。他自創的髮型像貓頭鷹,他說那是他的王冠,他剛加冕了自己。但戴著這王冠的巴斯奇亞,並沒有王族的霸氣。照片裡他的表情經常像個孩子。安迪沃荷和他合照,兩人戴上拳擊手套,雙手交叉胸前。和女性合照時,他常擺出宗教畫裡聖母與聖子的姿勢。白女人是聖母,黑男人是聖子。
這扮「聖母聖子」是怎麼回事?一邊是母親付出全無條件的愛,一邊是孩子回報以全無條件的信賴。八○年代的紐約,光怪陸離,絕非溫暖的娘胎。巴斯奇亞的朋友們,不是人人像他成名那麼早,都是離鄉背井出來闖,個個靈魂武裝,衝撞世法。
其中有一個女孩,和巴斯奇亞有過至少一夜情的,後來成了歌手,也是白手起家,驚世駭俗,造就新一代的傳奇。她是瑪丹娜,藝名正隱喻「聖母」。
空心人與新天后
受巴斯奇亞啟發的第一代藝術家,應該要算上奇斯哈林(KeithHaring)。雖然實際上哈林比巴斯奇亞還大兩歲。但巴斯奇亞晚上跑到街上噴漆,被《村聲》雜誌報導「發掘」時,哈林還在藝術學校裡讀書。
哈林的「發光嬰兒」(RadiantBaby)平滑、二維、扁平,延續普普風,可以順理成章嵌進藝術史裡的一格位置。從這點看,巴斯奇亞是藝術史突兀的變種。他是撞進一場派對的外人,來得意外,卻成了派對的目光焦點。
巴斯奇亞與哈林都因安迪.沃荷成名。
楚門.卡波堤對安迪.沃荷的描述相當精采。他說起一個小說裡的角色,是個聾啞人,名叫興歌先生(Mr.Singer):「這個人從來不溝通,最後被隱微地寫出是個完全空洞、沒心肝的人。但是因為他又聾又啞,他對絕望的人們象徵著些甚麼。這些人來找他,對他傾訴所有的麻煩。他們抓著他當作力量的來源,是他們生命裡近乎宗教的形象。安迪就像這個興歌先生。絕望、迷失的人來找他,尋求某種救贖,而安迪就坐著,像個聾啞人,沒甚麼可給。」
這段描述之所以精彩,是因為它驚人。安迪.沃荷,二十世紀藝術大師,時代寵兒,原來是一個空心人?周遭的人比他更慌、更沒主意,於是把他拱上了王位。說這話的卡波提是誰?他是安迪.沃荷的同代人,曾經也是紐約社交圈的一號紅人,《第凡內早餐》的作者,電影「冷血殺手」裡演他的演員得了一座奧斯卡獎。他是紐約社交圈遊戲規則的知情人,有點像《慾望城市》凱莉布朗蕭──當然是在《慾望城市》還沒變成時尚大片,凱莉還會為她的小專欄觀察紐約世情,不光只看自己和衣服牌子的時候。
八○年代的藝術家,很多力氣花在被看。作品被看,人也被看。擺出姿態來,應付從四面八方伸過來的鏡頭。成名在一夕之間,接下來迅速消耗。
說不定活得長命的辦法,是讓內部空虛掉,沒有心,像安迪沃荷那樣。
幸好藝術家微賤時有過這麼個朋友,瑪丹娜,她很快把話題轉移過去,成為新的話題天后。從此「被看」分工給娛樂圈。藝術家又可以安靜創作。
誰說抽菸很美
吳兆南與魏龍豪的相聲錄音,現在聽還是很過癮。我特別喜歡一個「戒菸記」的段子。在這段子裡,吳兆南是要戒煙的,魏龍豪是不抽煙的。戒煙的為了讓不抽煙的理解他戒煙的辛苦,首先要讓他感受抽煙有多好。於是吳兆南從買到一包菸講起,撕開塑膠膜的手感,打開盒子拉下那張錫箔紙的,到拍打盒子底部幾根煙隨機蹦出來,那種擁有挑選權的感覺……。他一個動作一個動作拆開來說,把每個動作裡的人物關係局部放大來說。
這些瑣碎的步驟,給說成了人間稀罕的享受。還真沒聽過有人這麼說抽煙的。這是多年前的段子了,兩位老演員都已經作古,不受當今的政治正確標準規範。只是從物質面把抽菸的享受處說到了頂點,接下來要怎麼戒?幸好再有魅力、再令人把持不住的物質,都有阿Q精神可以對應。吳兆南稱他的戒菸法子為「精神轉移法」,怕犯煙癮不待在家,去劇場坐在「禁止吸菸」的環境裡看戲,跟著哼哼唱唱就忘了要抽煙。
這段子說的時間,是在臺灣公賣局即將開放洋煙進口的前夕。後來兩老又有一段談抽煙的,這回是先說抽煙有害。還把宣導短片般的字句大段大段字正腔圓地念出來,聽起來反而諷刺。不知道是不是先前的段子引起政府注意,要求宣導禁煙平衡一下?不管怎樣,戒菸這主題在兩老嘴裡不減麻辣。就算是回應政府單位或是輿論反饋,就像雙口相聲之外有一個看不見的第三口,他兩老仍然是十分漂亮地回應了那第三個聲音。
要是沒有吳兆南和魏龍豪,臺灣的相聲界就太寂寞了。吳兆南的嗓音高,魏龍豪的低。吳兆南大多演機伶的角色抖包袱,魏龍豪演老實的捧哏。有時也互換。他們真是沒人能代替的,把相聲拉到藝術的層次而沒有藝術家的架子。美好的一根菸,只在他們的相聲裡聽到過。以後應該也不會有人說了吧。我不抽菸,現在公共場合禁菸的地方越來越多,有時看到朋友好不容易找到地方抽菸,很抱歉地說「不好意思等我一下」急忙掏煙,總想告訴他們去聽吳兆南和魏龍豪說的,那一根幽默又美好的菸。
不懂戲的人
《梅蘭芳》電影裡有一段戲中戲,青年梅蘭芳與十三燕合演《汾河灣》:十三燕是薛平貴,從軍多年後返鄉;梅蘭芳是柳迎春,不肯相信來人就是她的丈夫。原本,這段戲主要是薛平貴在表演,柳迎春只是背對觀眾而坐,聽薛回憶往事。梅蘭芳想改動這戲,但十三燕說:「戲在我這兒!」話語權在他手裡,鬚生主導的戲碼,旦角還得是陪襯。
第二天到了臺上,在沒有排練的情況下,梅蘭芳還是按著自己的意思,用新法演了柳迎春。當薛平貴說個沒完,柳迎春也沒閒著,她先是驚疑地回頭,繼而迴旋起身,終於正面迎向了薛平貴。夫妻相見,柳迎春由猜疑而接納,梅發明了新的身段,新的情感表現,而十三燕竟也配合得天衣無縫,像事先排練過一樣。臺下觀眾大聲叫好,一個新的詮釋就此誕生了。
在上海,人人都聽說過梅蘭芳的故事。本來沒聽說的,經過這段日子報章雜誌的宣傳,也都聽過了。因此看完電影《梅蘭芳》,誰都忍不住要行使一下話語權:實際上呀,是這樣那樣的,還有這個那個沒演出來……。人人心裡都有自己一齣《梅蘭芳》。
我也感覺有個我期望看到、卻沒展開的故事,只是不那麼具體就是了。前面說的十三燕與梅蘭芳那段戲,靈光一閃觸到一個有意思的主題:看不見的、瀰漫在舞臺上的「戲」,它大過演員個人,把臺上臺下拉在一起,卻不是誰能據為己有的。十三燕在「戲」裡時,號稱天下無敵,但「戲」的典範會轉移——典範轉移時,他還在戲裡,觀眾卻不在了。
電影裡去看梅蘭芳新戲的那些大學生,肯定不是十三燕心目中懂戲的人,不是他的目標消費者。但他們也等待著「戲」。當出現了一種戲劇表現,能溝通他們,將他們聚攏(而非推開),這些「不懂戲的人」就成了新的觀眾。這樣的事每個時代都會發生,有時正是由新的觀眾、外來的眼光,發動了典範的轉移。
當然,這些都只屬於我期待看見,卻沒拍出來的那部戲。不是電影《梅蘭芳》。
聖誕夜
化妝品市場有一條規律:經濟越不景氣,口紅賣得越好。因為市道不好時,人們雖然想著要省錢,但主要是縮減高價消費,低價的小東西還是買,而且比平日更不手軟。因為壓力越大,越想消費,買不起貴的,就買便宜的。股災不能讓女性不愛美,她們走過櫃檯,抵擋住購買白金奢華面霜的欲望,轉身又把錢花在一隻小口紅――因爲便宜,能隨身攜帶,而且立即見效。
讀雷蒙卡佛的短篇小説集《大教堂》時,老想到這個「口紅定律」。因爲《大教堂》裡的角色們,常是正在生活的一道坎上,問題看上去不大,卻是當事人眼看過不去的。最後如果能獲得解救,也往往就是經由救命稻草般的小事。例如《好事一小件》裡,一對剛喪子的夫婦接到不明的電話問:」你是不是忘了斯科蒂?」(斯科蒂是他們死去孩子的名字。)這些不斷戳到他們傷処、仿佛來自地獄的神秘電話,原來只是糕餅鋪師傅打來提醒,他們為小孩定制的生日蛋糕忘了提走了。最後誤會能解開,也是因爲麵包房的一杯咖啡、一些剛出爐的麵包圈。
如果不景氣時期,人把消費欲望分化、打散,得到以口紅為小單位的滿足,那麽人所需要的溫暖、善意、幫助,是不是也可以呢?我讀《大教堂》時常會這樣想。
聖誕夜,小球在公司哭了。「明明都確認過了呀……」一邊哭一邊說。她負責的客戶突然要求修改方案,但在聖誕夜,又已經過了下班時間,她找不到人幫她修改了。於是這個有一雙圓眼睛的、剛進公司半年的女孩,頂著一個韓系風潮的圓髮髻,趴在位子上哭了起來。
我從她的座位旁走過,覺得她真是很傷心的,妝都哭花了。在上海工作的外國人口很多,對那些來自西方國家的人而言,聖誕節比天大,工作可以等一等。上海的小白領們呢,沒法讓工作等,也沒法不受「聖誕夜」魔咒催眠而想要早下班,想特別打扮,想過特別的一天。只希望哭過之後,小球還能在後半夜遇見一件令她開心的口紅小事。
最小單位的距離
最近《三聯生活周刊》報導了一批老照片,照片的主角是同一個人,一八八一年出生在福州,名叫葉景呂。他從一九○七年開始,每年上照相館拍一張照,從十六歲到八十七歲,總共六十一張年度相片。
這些黑白相片展現了一個人緩慢變老的過程,很是動人。拍第一張照時,他還留著髮辮。接下來幾年身穿馬褂或長衫,站在相館的佈景壁畫前。後來,戴上了眼鏡。一九五○年起改穿短裝。六十歲過後,葉景呂更多拍的是半身照片,看得見時間對他眼神造成的變化。
自從數碼相機發明,拍照變得更容易。紐約有個叫凱勒的人,已經將「一日一拍」進行了八年,還在持續下去。他每天都用同樣的證件照角度,拍自己的臉,並且放上網。八年來他變化不大,也沒怎麼長胖,很令人羨慕,變的主要是髮型、眼鏡框、上衣。因此當他把八年來的照片串成動畫,連續快速播放,便產生一種奇特的效果:畫面中央的臉孔木然不動,而時間具象化為眼鏡衣服這些身外之物,風一樣不斷捲走。
一年或一天,效果完全不同。葉景呂每年走進幽暗的照相館,留下影像,是一種與時間的儀式。凱勒每天站到相機前固定一拍,則純屬數碼時代的以量取勝。即使技術上,我們能將自拍的時間距離縮到最小,也不等於記錄了整個人生。畢竟最小的距離裡,可以無限地充滿著說不出、拍不了的東西。
這讓我想起一個最近在日本引發熱議的網站。一對長距離戀人,一個在東京,一個在福岡,相隔一千公里。在相思的驅使下,兩人開始像偶像劇那樣不顧一切地朝對方奔去。這網站其實是個廣告,卻不說賣甚麼商品。站上每天更新戀人跑步的視頻,今天跑到哪裡了、互傳了什麼手機短信、戀情怎樣進展,完結篇會在聖誕夜推出,屆時才公布究竟賣的甚麼商品。
懸疑手法果然奏效,有人猜跑鞋,有人猜手機,還有人說是到處都收的VISA。
答案揭曉:安全套。即使為愛跑了一千公里,也要記得保持最後0.02毫米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