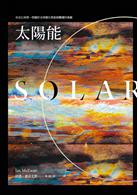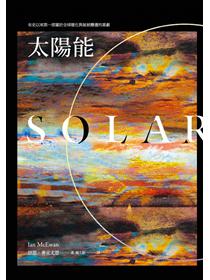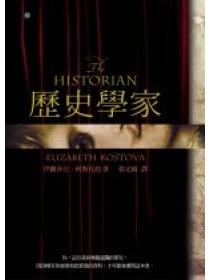普立茲小說獎得主保羅‧哈汀
美國媒體天后歐普拉
一致感動推薦
***
一個女人究竟能愛幾個孩子?
——但她努力不懈,讓他們活下來,也讓自己活下來。
透過一個令人難以忘懷的家庭所經歷的重重試煉,以二十世紀美國黑人往北移居之「大遷徙」為背景,梅錫斯娓娓道來一群孩童的故事,有愛有恨,還有新美國的應允。
一九二三年,十五歲的海蒂‧薛珀逃離喬治亞,到費城定居,望能建立更好的生活。卻嫁給了一個除了挫折以外什麼都不能給她的男人,無助地看著頭胎的雙生兒死於幾分錢就能預防的疾病。海蒂又生了九個孩子,以過人的勇氣和毅力養大,但他們從她身上得不到一絲極為渴望的溫柔。她發誓要讓孩子們有能力面對成人後一定會碰到的悲慘困境,去面對不會愛他們、一點也不和善的世界。本書分成十二條清楚易懂的支線,訴說一名母親無比的勇氣,以及美國一路走來的模樣。
梅錫斯的《海蒂十二族》優美而沉重,從頭到尾都與人驚嘆──讀來令人既愉快又悲痛,更沒想到還能讓人感到振奮,熊熊燃燒著生命力。梅錫斯初試啼聲,便引人入勝,扣人心弦,刻畫出主人翁頑強抵抗無法克服的逆境,一而再再而三地描繪出人類精神的強韌和驅動美國夢的力量,在現代小說界宣示了重要的新代言人即將登場。
作者簡介:
阿雅娜‧梅錫斯(Ayana Mathis)
梅錫斯是美國素負盛名的愛荷華創作碩士班畢業生,還獲得了哥白尼獎學金,這個獎學金之前曾提攜了麥可.康寧漢等無數文壇要角。在麥可.翁達傑的文學經紀人艾倫.勒雯(Ellen Levine, 也是 Russell Banks 的經紀人)推薦下,《海蒂十二族》迅速被美國 Knopf、英國 Hutchinson 和加拿大 HarperCollins 出版社 pre-empt 買下版權,目前已有保羅.哈丁(Paul Harding)和瑪莉蓮.羅賓遜兩位普立茲獎得主撰文推薦。
《海蒂十二族》是她的第一本小說。
譯者簡介:
嚴麗娟
台大外文系畢業,英國倫敦大學語言學碩士。現任職科技界,喜愛閱讀。
各界推薦
得獎紀錄:
各界對梅錫斯《海蒂十二族》的好評
「《海蒂十二族》以奔放而憐憫的筆調描繪出一個家庭,因著環境而更加堅強,也因著環境而四分五裂,但家人間的感情依然濃烈。文字純粹精確,非常雅致。角色充滿生命力,卻又大不相同,作者對他們有一份明斷的溫柔,讓他們更為突出。很少見到第一本小說便有這樣的成熟度。」
──加拿大作家瑪麗蓮‧羅賓遜(Marilynne Robinson)
「《海蒂十二族》從第一句起就非常優美,讓人一定要讀下去。每一頁描述的人類生活都同時卑微而充滿光榮,墮落卻得到救贖。事實上,若非從如此寬宏而充滿希望的藝術家角度來觀察,若非充滿了慈悲和愛,這些故事會令人心碎到不忍心讀下去。梅錫斯寫了一本少見的好小說。」
──普立茲小說獎得主保羅‧哈汀(Paul Harding)
「初試啼聲的小說家梅錫斯文筆中流露出的威信、清晰和勇氣令人稱奇,把讀者的心思全部吸引到海蒂後來生的九個小孩(再加一個外孫女就湊成「十二族」)生活中戲劇性十足的插曲上,充滿刺激的緊要關頭暴露出破碎的夢想,以及大遷徙後留下的痛苦……梅錫斯用銳利的洞察力寫出性向、婚姻、家人關係、骨氣、欺騙和種族主義的複雜,在一本小說中融合了承受極大痛苦的生命,卻又透露出美好。」
──Booklist書評家唐娜‧西曼(Donna Seaman)[特別推薦]
「非凡的作品……梅錫斯在她的故事中織入了自信,證實自己的寫作天分和能力。」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特別推薦]
「刻畫入裡,激動人心……就是能讓人心碎……雖然梅錫斯繼承了一些東妮.莫莉森(Toni Morrison)滿富詩意的聲調,她自己的文筆也純樸直白到動人無比,書中的結構更是頗富巧思……非常優秀的首部作品。」
──《科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特別推薦]
名人推薦:
何致和(小說家)
何景窗(散文家)
侯季然(導演)
吳億偉(文字工作者)
郝譽翔(中正大學台文所教授)
凌性傑(詩人)
陳又津(小說家)
楊索(散文家)
楊富閔(小說家)
譚光磊(版權人) 撼動人心推薦
海蒂的孩子叫她將軍,整個故事以她為中心,建起一座專屬母親的歷史舞台。熬煮草藥的老婦、妙齡少女、奮力成長的孩子們在這裡輪舞,曾經標緻的少年變成平庸男子,女兒憎恨母親,梅錫斯毫不畏懼刻畫人類靈魂的皺褶,讓我們看見在這擠壓之中如何保有尊嚴。這群人不是一直在逃,就是準備離開,展開自我拯救的大冒險。從美國南方到北方,從鄉村到城市,離開從小到大生長的家,離開父親和母親,甚至打算永遠離開這個世界。這支美國黑人的家族史,時空橫跨半個世紀,迷人的細節與靈活的場景轉換,嘩啦啦就到了盡頭。但無論他們走得多遠,這一顆顆四散星點,在我們拉開景深之後,恍如夜空中的星座輝映,為地上遙望的人們帶來救贖。──陳又津(小說家)
得獎紀錄:各界對梅錫斯《海蒂十二族》的好評
「《海蒂十二族》以奔放而憐憫的筆調描繪出一個家庭,因著環境而更加堅強,也因著環境而四分五裂,但家人間的感情依然濃烈。文字純粹精確,非常雅致。角色充滿生命力,卻又大不相同,作者對他們有一份明斷的溫柔,讓他們更為突出。很少見到第一本小說便有這樣的成熟度。」
──加拿大作家瑪麗蓮‧羅賓遜(Marilynne Robinson)
「《海蒂十二族》從第一句起就非常優美,讓人一定要讀下去。每一頁描述的人類生活都同時卑微而充滿光榮,墮落卻得到救贖。事實上,若非從如此寬宏而充滿希望的...
章節試閱
費城和禧年
一九二五
海蒂說,她想幫雙胞胎取這兩個名字,奧古斯特聽了便喊:「費城和禧年!嬰兒怎麼能叫那麼怪的名字!」
要是海蒂的媽媽還在,她應該會同意奧古斯特的看法。她會說,海蒂選了鄉下人才會想到的名字,「低級、愛現」。不過她已經去世了,海蒂認為,給孩子取的名字最好尚未刻上喬治亞州家族墓園的石碑,所以她選了費城和禧年,代表承諾與希望,向前走,不要回頭看。
六月,在海蒂和奧古斯特結為夫妻後的第一個夏天,雙胞胎誕生了。他們在韋恩街租了一棟房子——很小,不過環境不錯,而且,奧古斯特說,這只是暫時的住所。「等到我們買自己的房子吧,」海蒂說。「等到我們在合約上簽名,」奧古斯特附和著。
到了六月底,知更鳥攻占了韋恩街的樹木和屋頂,整個街坊鳥鳴啁啾。鳥叫聲催眠了雙胞胎,帶他們進入夢鄉,海蒂神采飛揚,不時對著自己傻笑。每天早上都會下雨,但下午總是晴空萬里,海蒂和奧古斯特那片小小的草地就如世界初創時那麼翠綠。附近的太太小姐們習慣一早就烘焙糕點,還不到中午就把草莓蛋糕放在窗檯上待涼,滿街都是蛋糕的香氣。海蒂和雙胞胎母子三人在門廊上陰涼的地方打起了瞌睡。等到下一個夏季,費城和禧年就會走路了,像可愛笨拙的老人,繞著門廊蹣跚學步。
海蒂‧薛珀低頭看看提籃裡的兩個孩子。雙胞胎七個月大了,直直坐著的時候呼吸比較順暢,所以她用小枕頭把他們墊高。鬧了一整夜,現在終於安靜下來。肺炎可以治得好,盡管不容易治,總比得腮腺炎、流感跟胸膜炎好。與其染上霍亂或猩紅熱,不如得肺炎。海蒂坐在浴室的地板上,靠著馬桶,伸長了兩條腿。沾滿蒸氣的窗戶變得不透明,小小的水滴凝聚,順著玻璃流下來,流過白色的窗框,流到馬桶後面比較凹陷的磁磚上,聚成一個小水灘。熱水已經流了好幾個鐘頭。奧古斯特半個晚上沒睡,都在地下室幫熱水器添煤炭。他不想去上班,不想留下海蒂跟寶寶。唉,但是……上一天工、拿一天的工資,煤炭也快用完了。海蒂要他安心:天亮了,寶寶會好起來。
醫生昨天來過,建議用蒸氣治療。他也開了低劑量的吐根,勸告他們不要用鄉下人落後的偏方,比方說敷芥末調成的熱糊,但可以用薄荷膏。他用清澈的油狀液體稀釋了吐根,給海蒂兩根小小的滴管,教她怎麼用手指按住寶寶的舌頭,好讓藥劑可以流到喉嚨裡。奧古斯特付了三塊錢的看診費,醫生前腳剛踏出門,他後腳就開始調芥末糊。這可是肺炎呀。
附近傳來尖銳的警笛聲,響到就跟在家門前一樣。海蒂費了一番功夫才從地上爬起來,在浴室沾滿蒸氣的窗戶上擦了一圈。沒什麼特別的,只看到對街一排白色的房子,如牙齒般緊緊排在一起,人行道上結冰的地方已經變成灰色,樹苗在分配到的一小方凍土中奄奄一息。有幾戶人家樓上的窗戶還亮著燈──這一區的男性居民有的跟奧古斯特一樣在碼頭工作,有人負責送牛奶或送信;也有學校老師,還有許多海蒂根本不認識的人。在費城,大家都在天寒地凍的時候起床,為地下室裡的暖氣爐加柴火。儘管不認識,也同甘共苦。
披著一層薄霧的黎明從天空的盡頭緩緩升起。海蒂閉上眼睛,回憶兒時看過的日出——這些景象總揪著她的心;在費城每多住一天,想念喬治亞的感覺就更加迫切。還沒結婚前,每天早上天空剛發藍,工作的號角便響起,傳遍田野和住家以及黑紫樹林。海蒂躺在床上,看著農人從她家前面拖著腳走過去。第一聲號角響過,才會看到落後的人:孕婦、病人、跛子、老到不能幫忙採收的人、把嬰兒綁在背上的人。號角跟鞭子一樣,催促他們向前。他們的表情如道路一般嚴肅;裂開的白色田地正在等待,採棉花的人如蝗蟲般散落到田野中。
海蒂的孩子朝著她眨眨眼,十分虛弱;她撓撓他們的下巴。快到更換芥末糊的時間了。蒸氣從浴缸裡的熱水滾滾噴出。她又加了一把尤加利葉。在喬治亞,海蒂家對面的樹林裡就有一棵尤加利樹,但在費城,到了冬季,根本找不到這種植物。
三天前,兩個孩子咳得更厲害了。海蒂匆匆穿上外套,去費城水果雜貨店問老闆哪裡可以找到尤加利葉。他們指點她再走幾個街區就可以找到。海蒂第一次來德國鎮,馬上就在擁擠的街道中迷失了方向。找到目的地的時候,臉都凍腫了,她付了五十美分,買來一袋在喬治亞州不需耗費分文的葉子。「啊,妳還小呢!」賣尤加利葉的女人說。「小女孩,妳幾歲啦?」海蒂一聽她這麼問,立刻全身都繃緊了,但她還是告訴女人,她十七歲,又補充說,她已經結婚,丈夫正在學習電工技能,他們才剛搬到韋恩街的房子裡,免得被當成剛從南方移居過來的倒楣鬼。「喔,很好呀,親愛的。妳家人在哪裡?」海蒂趕忙眨了幾下眼睛,用力吞了口口水,說:「太太,他們在喬治亞。」
「妳在這裡沒有親人嗎?」
「我妹妹也在。」一年前,海蒂仍有孕在身,母親便去世了,但她沒說出來。母親死亡的打擊,在北方是孤兒,又是外地人,迫使海蒂的妹妹珍珠跑回喬治亞去。她姊姊瑪莉詠也走了,不過她說,等孩子生下來,冬天過了,她就會回來。海蒂不知道姊姊會不會回來。女人細細打量海蒂。「我現在跟妳回家,看看妳的小孩子怎麼樣,」她說。海蒂婉拒了。她很蠢,她就是這麼傻,高傲到不肯承認她要人照看。她抓緊那包尤加利葉,自己一個人回家了。
冬天的空氣就像團火般包圍著她,把她燒得一乾二淨,但燒不掉她想要孩子病好的願望。緊抓褐色紙袋袋口的手指凍成了爪子的樣子。她衝進韋恩街的房子,心中一片澄明。她覺得她能看進寶寶的身體,看穿他們的皮膚和血肉,深入胸腔,深入他們疲勞的肺臟。
海蒂把費城和禧年移到更靠近浴缸的地方。剛加的那把尤加利葉太多了——薄荷味的霧氣讓嬰孩們閉緊了雙眼。禧年握起拳頭、舉起手臂,似乎想揉揉被熏出眼淚的眼睛;但她太虛弱了,手又掉回身體旁邊。海蒂跪下來,親親她的小拳頭。她抬起女兒軟弱無力的手臂——就跟鳥兒的骨頭一樣輕——用她的手擦掉眼淚。如果禧年現在有力氣,她就會自己揉眼睛。
「妳看,」海蒂說,「妳看,妳好棒。」禧年抬眼看看母親,微微一笑。海蒂把禧年的手舉到她矇矓的眼睛前。嬰孩以為母親要玩躲貓貓,臉上浮現薄弱的微笑;笑聲很輕、有點刺耳,似乎卡了痰,但她還是笑了。海蒂也笑了,因為她的小女兒好勇敢、脾氣好溫厚——病得這麼重,仍像朵罌粟花一樣明亮燦爛。她有一顆酒窩,費城則有兩顆。雙胞胎一點也不像。禧年的頭髮跟奧古斯特一樣是黑色,費城則像海蒂,膚色淡得像牛奶,頭髮則是黃棕色。
費城的呼吸急促起來。海蒂把他從提籃裡抱出來,讓他坐在浴缸邊緣蒸氣最濃的地方。抱在懷裡的費城像袋麵粉,垂著頭,手臂軟軟地掛在身體兩側。海蒂輕輕搖了他幾下,把他喚醒。從昨天晚上,他就沒吃東西——雙胞胎晚上一直劇烈咳嗽,把海蒂好不容易餵進去的一點點蔬菜高湯都吐了出來。她用手指推開兒子的眼皮,他的眼睛翻白。海蒂不知道他是暈了,還是睡著了,如果他暈過去,或許沒辦法……或許沒辦法……
她又推推他的眼皮。這次他睜開了眼睛——我的兒子真棒!——他撇撇嘴,好像海蒂要餵他吃豆子泥,或聞到了他不喜歡的味道。他就是喜歡小題大作。
明亮的浴室令人無所適從:白色的浴缸、白色的牆壁、白色的磁磚。費城咳嗽了,長長地吐出一口氣,身體跟著搖晃。海蒂拿起暖氣上的那罐熱芥末,在他胸口上厚厚抹了一層。手指所及之處,摸到的淨是樹枝般的肋骨;只要輕輕壓一下,肋骨就會斷裂,落入他的胸腔裡。安然無恙時,他本來很胖,兩個孩子都很胖。費城抬了抬頭,但他提不起力氣,頭又垂了下來;他的下巴撞上了海蒂的肩膀,就跟剛生出來的時候一樣,還在學怎麼把頭抬起來。
海蒂在狹小的浴室時繞著圈走路,摩擦費城肩胛骨中間的地方。氣喘吁吁的時候,他的腳縮起來,踢到她的腹部;正常呼吸的時候,腳就放鬆了。地板滑滑的。她唱起歌來,歌詞都是單音節,沒有意義——嗒嗒嗒、噔噔、嗒嗒。什麼歌詞她都不記得了。
水從窗戶和水龍頭上滴下來,沿著牆流到電燈開關旁邊的板子上。整間浴室就像暴風雨後的喬治亞森林,水滴個不停。有東西發出嗡嗡聲,然後牆壁裡嘶的一聲,天花板上的電燈滅了。滿是煙霧的浴室裡一片幽藍。我的天啊,海蒂心想,居然會發生這種事。她把頭靠在門把上、閉上眼睛;她已經三天不曾闔眼。回憶湧入腦海,帶來一陣暈眩:黎明時分,海蒂和母親姊妹們走在樹林裡。媽媽走在最前面,手裡兩個大旅行袋,三個女孩跟在後面,揹著能裝下全副身家財產的大包包。穿過清晨的薄霧和矮樹叢,她們往城裡走去,裙襬不時被樹枝絆住。她們跟竊賊一樣偷偷摸摸地穿過樹林,去搭離開喬治亞的早班火車。海蒂的父親過世還不到兩天,他一死白人就把鐵匠鋪門上的名牌取下、換上他們自己的。「可憐可憐我們吧,」田野中的第一聲號角響起時,母親這麼說。
費城的腳踢進海蒂的肚臍,她驚醒過來,回到浴室裡,和兩個孩子在一起,除了驚嚇,她也氣自己居然神遊到忘了孩子。雙胞胎同時放聲大哭,一起抽噎顫抖。疾病發動攻勢,一個孩子先得了,另一個孩子也無法倖免,然後,彷彿在等待掉到谷底的時機,宛若雙叉的閃電同時攻擊。慈悲,主啊。可憐我們。
海蒂的雙胞胎發起燒來:體溫直線上升,雙腿不自然地彎曲,臉頰紅若太陽。他們咳得太厲害,什麼也吞不下——藥劑從嘴角滴出來。海蒂幫孩子擦擦臉,再餵了一次吐根,按摩他們起伏的胸膛。她的雙手靈巧地做完一件又一件工作。就算邊哭著祈禱,海蒂的雙手依然能幹敏捷。
孩子們好火燙!他們的求生意志好強!海蒂沒有別的想法,她只能想到,孩子的靈魂宛若煙霧做成的頂針;好纖細,好難抓住。她只是個年輕女孩——在這個世界上只比她的孩子早來了十七年。海蒂知道,孩子擴大了她的生命,她愛孩子,因為他們是她生的,因為他們不能保護自己,因為他們需要她;但她看看懷裡的嬰兒,看到他們的生命力好強韌好偉大,不肯從他們的身體裡被驅離。「加油,」海蒂鼓勵他們。「就像這樣,」她把空氣吸入肺裡,然後呼出來,和他們一起呼吸,要讓他們知道能做得到。「就像這樣,」她又重複了一次。
海蒂盤腿坐在地板上,禧年放在膝蓋彎曲的地方,費城則在另一條腿上。她幫他們拍背,把痰拍出來。嬰兒的雙腳疊在海蒂腿中間那塊三角形上——他們無精打采地靠著她的大腿。如果她要活到一百歲,海蒂仍會看到現在的景象,清清楚楚看見她的寶貝就在她面前倒下;她父親倒在鐵匠鋪的角落裡,鎮上來的那兩個白人走出他的店鋪,甚至不會羞愧到加快腳步或藏起他們的槍支。海蒂看到了,永遠無法消除的回憶。
在喬治亞,牧師說北方是新的耶路撒冷。會眾說他背叛了南方黑人的理想。第二天,牧師就搭火車去了芝加哥。其他人也走了,在店面或田地裡都看不到他們的身影;星期天做禮拜的時候,他們在教堂裡的座位換別人坐,到了星期三的禱告會,座位再度空出。那些逃離了南方的人,就在此刻,正在北方的城市裡度過惡劣的冬天,心中充滿了希望,臉上容光煥發。海蒂知道寶寶一定能度過難關。雖然他們很小、掙扎得很辛苦,費城和禧年也屬於那群充滿希望的人,已經動手建立新的國度。
海蒂和母親姊妹穿過喬治亞的森林,來到火車站。車程是三十二個鐘頭,在喧鬧的黑人車廂硬梆梆的座位上坐了三十二個鐘頭後,海蒂迷迷糊糊睡著了,列車長大喝一聲,又把她嚇醒來:「費城,寬街車站!」海蒂艱難地下了車,裙襬仍沾著喬治亞的泥土。費城的夢想好圓滿,像含在口中的彈珠,而對費城的恐懼則像插入胸口的細針。海蒂、媽媽、珍珠和瑪莉詠從火車月臺爬上了樓梯,進入車站大廳。雖然是晴天的正午時分,仍有點陰暗,半球型的屋頂高高拱起,鴿子在屋椽上咕咕叫。海蒂那時才十五歲,苗條得像根指頭。她和母親姊妹站在人群的外緣,四個人等待人流出現缺口,好移向車站另一頭的雙扇門。海蒂走入人群。媽媽喊:「回來!這麼多人妳會不見的;妳會迷路!」海蒂驚慌地回頭;她以為母親就在身後。人群密到她無法轉身,只能跟著人潮的方向走。她到了雙扇門,被推到外面跟車站一樣長的人行道上。
大街上塞滿了人,海蒂一輩子也沒看過這麼稠密的人潮。太陽當空高掛,空氣中除了聞得到汽車的廢氣,還有剛鋪好的柏油路發出的瀝青味,腐爛的垃圾也傳來令人作嘔的臭氣;車輪轆轆行駛在鋪路的石頭上、引擎高速旋轉,賣報紙的男孩高聲喊出今天的頭條;對街有個渾身髒兮兮的男人站在街角,雙手放在身體兩側、掌心朝上,用哀號的聲音唱歌。海蒂想摀住耳朵,堵住城市裡熙攘的聲音,但她忍住了。樹木不見蹤影,而海蒂不用看就知道了,因為她的鼻子聞得到。費城什麼都比較大——真的——什麼都比較多,太多了。但在這喧鬧中,她看不見應許之地。她覺得,費城就是亞特蘭大的放大版。就算她自認很適合城市生活,裙子下的雙膝仍不斷打顫,背上也沁出了汗珠。站到外面才這麼一下子,眼前就通過了上百個人,而她沒看到母親,也沒看到姊姊妹妹。不斷審視來往路人的面孔,海蒂覺得眼睛都發痛了。
人行道那頭的推車吸引了她的目光。海蒂還是第一次看到賣花的推車。一名白人坐在凳子上,襯衫袖子高高捲起,帽緣向前壓下來遮住陽光。海蒂把背包放在人行道上,往裙子揩了揩汗濕的掌心。黑人婦女走近推車,示意她要一束花。白人站起身——毫不猶豫,也不扭曲身體做出威脅的姿態——從水桶裡取出花束:先輕輕甩掉莖上的水滴,再用紙包好。黑人婦女把錢遞過去;他們的手似乎輕輕擦了一下?
女人拿了找零,放進皮包裡,卻打翻了三盆插好的花。花瓶和花朵從推車上滾下來,落到人行道上。海蒂全身僵硬:一定會大鬧一場。她料想,其他黑人會退開、遠離那即將承受暴力對待的女人;她臆測,等一下要遮住眼睛,讓自己看不到那女人,看不到可怕的場面。賣花人彎下腰,開始收拾混亂。黑人婦女用手勢表達歉意,又把手伸進皮包裡,看來想付錢賠償她造成的損害。不到兩分鐘,風平浪靜,女人往街道的另一頭走去,鼻子埋在包成圓錐樣的花束裡,彷彿什麼都沒發生。
海蒂細看人行道上的群眾。黑人不會靠邊踩進排水溝裡好讓白人通過,也不會固執地低著頭,目光只放在自己的腳上。四名黑人少女走過,跟海蒂一樣才十幾歲,嘰嘰喳喳講個不停。就是女孩聊天的樣子,咯咯傻笑、一派輕鬆,但在喬治亞,只有白人女孩才會這樣走在路上講話。海蒂把身子往前傾,一路盯著她們的背影。母親和姊妹終於走出車站,站到她身邊。「媽媽,」海蒂說:「我不回去了,絕對不回去。」
費城往前一倒,額頭靠在禧年肩膀上,海蒂沒來得及抓住他。他發出尖嘯的呼吸聲,聽得出來有很多痰;雙手攤開垂下來。海蒂搖搖他;他跟布娃娃一樣軟軟倒下。禧年也愈發虛弱了。她還抬得起頭來,但目光渙散。海蒂把兩個嬰兒都抱在懷裡,笨拙地伸手撲向吐根的藥瓶。費城低聲哽咽了一下,抬起頭來看看母親,表情很困惑。「對不起,」她說:「我也不明白。我會想辦法。我真的很抱歉。」吐根從她手裡滑落,在磁磚上砸碎。海蒂蹲到浴缸旁,一手抱著費城,讓禧年靠在大腿上。她轉開水龍頭,等熱水流出來。禧年用盡全身的力氣咳嗽,盡力把空氣吸到身體裡。海蒂用指尖碰碰水流,冷冽如冰。
沒時間去地下室的暖氣爐裡添煤,也沒時間等水燒熱。費城無精打采,無意間踢了一下海蒂的肚子;靠在她肩膀上的頭感覺很沉重。海蒂走出浴室。她踩到了破瓶子的碎片,割傷了腳;血跡留在白色的磁磚和走廊的木質地板上。她走進臥室,從床上拉起被子,把兩個孩子包在裡面。她迅速走下樓梯,站在小小的玄關裡穿鞋。腳上的玻璃碎片扎得更深。她出了門,走下門廊的階梯。沾濕的家居服和裸露的手臂上冒出一絲絲凝結的霧氣,消失在寒冷清澈的空氣中。太陽已經完全升起。
海蒂用力猛敲鄰居的門。「幫幫我!」她對開門的女人說。海蒂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進了屋裡,鄰居拉開被子,看到靠在母親胸膛上、軟弱無力的禧年和費城。「親愛的耶穌啊。噢,親愛的主啊,」她說。客廳裡走進來一名小男孩,是鄰居的兒子。「去叫醫生來!」女人對著他喊。她從海蒂手裡接過費城,抱著他跑上樓梯。海蒂跟在後面,懷裡抱著軟綿綿的禧年。
「他還在呼吸,」女人說。「只要還有呼吸就好。」
進了浴室,她把浴缸塞住。海蒂站在門口,輕輕搖著禧年,看到女人把熱水開到最大,她又失去了希望。
「我用過熱水了!」海蒂哭喊:「沒有其他的辦法嗎?」
女人把費城送回海蒂懷裡,在放藥的櫃子裡翻了翻。她拿出一罐樟腦膏、旋開蓋子,像用嗅鹽般在嬰兒的鼻子前晃了幾下。只有禧年對那氣味有反應,猛然轉開了頭。海蒂不知道該怎麼辦,一切都徒勞無功——她這麼努力,想救活她的孩子,結果只到了另一間一模一樣的浴室,鄰居跟她一樣,對孩子的病也無可奈何。
「我該怎麼辦?」海蒂透過蒸氣看那女人的臉。「告訴我,我該怎麼辦。」
鄰居找來一根玻璃管,一頭是球形;她用玻璃罐從嬰兒的口鼻吸出黏液。她跪在海蒂前面,淚水盈眶。「親愛的主啊。求求祢,親愛的主,幫幫我們。」女人邊吸邊祈禱。
兩名嬰兒的眼皮都又紅又腫,微血管破裂了。他們的呼吸微弱。胸口起伏的速度太快了。海蒂不知道費城跟禧年怕不怕,不知道他們明不明白自己怎麼了。她不知道該怎麼安慰他們,但她希望他們臨終前耳朵裡聽到的是她的聲音,眼睛裡看到的是她的面孔。海蒂親親嬰兒的額頭和臉頰。他們的頭往後倒,靠在她的手臂上。在呼吸之間,他們睜大了眼睛,表情驚恐。她聽到嬰兒的胸腔深處發出汨汨的水聲。他們要淹死了。海蒂不忍他們受苦,但她希望他們能走得平靜,所以她壓住自己的尖叫聲。她叫孩子們寶貝,她說他們是光,是承諾和雲朵。鄰居不斷低聲禱告。她的手一直放在海蒂的膝蓋上,就連海蒂想摔開她的手,她也不肯放開。幫不上忙,她只希望能幫這女孩承擔一點痛苦。
禧年奮鬥的時間最長。她虛弱地伸出手,想抓住費城,但她連伸直手臂的力氣也沒有。海蒂把費城的手放到禧年的掌心裡。她抱緊了孩子,輕輕搖晃他們。她把臉頰貼在孩子的頭頂上。噢,他們的皮膚跟絲絨一樣。孩子要死了,她的身體也跟著撕裂了。
海蒂的孩子按著出生的順序過世了:先是費城,然後禧年。
費城和禧年
一九二五
海蒂說,她想幫雙胞胎取這兩個名字,奧古斯特聽了便喊:「費城和禧年!嬰兒怎麼能叫那麼怪的名字!」
要是海蒂的媽媽還在,她應該會同意奧古斯特的看法。她會說,海蒂選了鄉下人才會想到的名字,「低級、愛現」。不過她已經去世了,海蒂認為,給孩子取的名字最好尚未刻上喬治亞州家族墓園的石碑,所以她選了費城和禧年,代表承諾與希望,向前走,不要回頭看。
六月,在海蒂和奧古斯特結為夫妻後的第一個夏天,雙胞胎誕生了。他們在韋恩街租了一棟房子——很小,不過環境不錯,而且,奧古斯特說,這只是暫時的...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