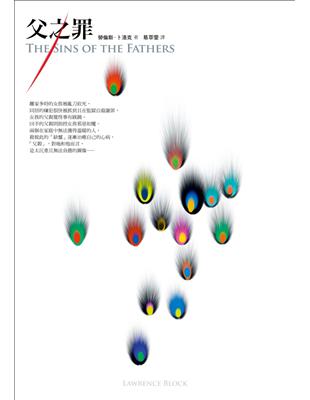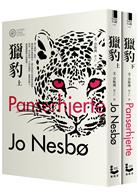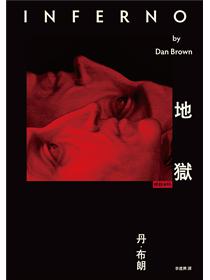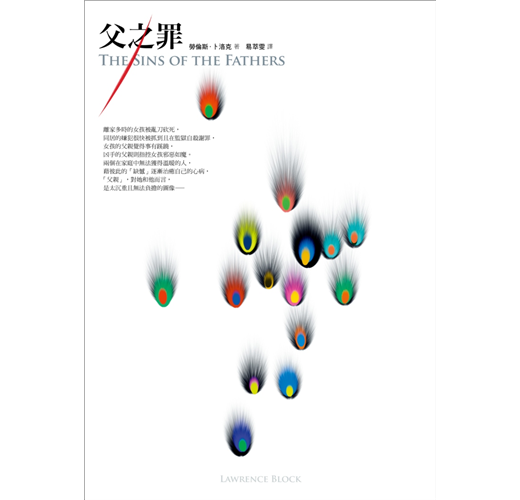名人推薦:
關於這一版……傅月庵
向一名作家致敬的最好方法是什麼?買本書追隨請他簽名,這不錯。如其因緣湊巧,能為他效勞,編一套書,那更好!
認識卜洛克是一九九七年的事。
那年,初入編輯這一行,工作壓力不大,看書成了最大福利,天經地義。恰巧「推理傳教士」詹宏志加上「臉譜」總編輯唐諾,聯兩手之力把原本冷門的「歐美推理」硬是加溫炒熱了起來,讓向來浸淫「日本推理」,只識「本格派」、「社會派」的台灣讀者,得見世界之奇,滄海之闊,慢慢竟都轉向西顧了。我是其中之一。
於是,《八百萬種死法》甫登陸台灣,便即邀來一晤,一見傾心,驚為天人。此後十多年時間裡,但凡「馬修.史卡德系列」中文新書出版,總要在第一時間購入,無暝無日讀完始休。若說我是那些年「馬修.史卡德現象」(開口閉口:「我今晚只聽不說」、「我一天戒一次」、「大多時候我是容易收買的,但你不能收買我」……)參與製造者,一點不為過。更多時候,家裡所買的卜洛克新書,一如朱天心她家一樣,總是被拿走,總要再補。
甚至讀著讀著,竟把他與王國維等量齊觀了:
「嗚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過,即以生活之苦痛罰之。此即宇宙之永遠的正義也。自犯罪,自加罰,自懺悔,自解脫。」,四月裡,斷斷續續,我一直在重讀卜洛克的馬修.史卡德探案。原因是偶然看到王國維〈紅樓夢評論〉這幾句話,忽然隱約理解一些「生命自持」的線索,因而更想靠近卜洛克,貼近馬修.史卡德。有些書,你不論何時讀,總會讀出一些道理。有些書,時候不到,你很難理解。人間無理可推,無謎可解。我所等待的四月的雨,最終還是沒有落下來,但我還有五月可以等。我一次等一天……。
奇怪的是,儘管日後卜洛克其他系列一一被引入,我也嘗試找來一讀,卻都不甚入港,從「雅賊」到「殺手」,就是有「隔」,進得去,耽溺不了。這事,跟小說行不行關係不大,純然緣分作怪,緣淺還能說什麼?有位朋友,他是「雅賊迷」,愛跟我鬥嘴,老說柏尼.羅登拔如何如何機智迷人,怎樣怎樣淵博難說,「真正愛書人都該喜歡他!」對此,我想了想,總冷冷一句回嗆:「不會老的不是人,角色而已,喜歡個什麼勁兒?」
誠然,「馬修.史卡德」與其他類型小說最大的不同是,馬修肉體會衰老,意志會動搖,道德會踰矩,辦案會潛行由徑,人家給錢他通常都收下,轉個身卻又丟一些到教堂捐獻箱。案件向來不是他的困擾,女人也不是,真正困擾他的,無非紅塵滾滾,該如何照著自己的那一套存活下去,或說存活出來自己的那一套。而幾乎有大半的時間(至少從一九七六到一九八二年,整整六年時間裡,他終於明白且面對「我是酒鬼」這一事實),他都是在跟酒瓶奮戰,To be or not to be?說穿了,馬修既不「冷」也不「硬」,與我們人人都一樣,他心中也有一個哈姆雷特。
至於辦案方式,也奇了,他似乎沒多少小小的灰色腦細胞,也沒有角落或輪椅,鐵拳或好大一把槍。接了案子,他只能不停打電話,不斷上街晃盪詢問,「有時候我們知道一些事情,卻不知道我們知道」、「去他的,東西全在那兒,只是我看的方法不對。」要想知道,要看對,只有一個方法:GOYAKOD,Get Off Your Ass and Knock on Doors,抬起屁股敲門去!天道酬勤,也許就對了。但「其實百分之九十八的調查工作皆毫無意義,你只能把想到的事都做好。你不知道哪件有用。你就像在煤礦堆裡找尋一隻不存在的黑貓,但除此之外我不曉得還能怎麼做。」——這不就是人生嗎?「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人一切的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有什麼益處呢?」幾千年前,傳道者早已論定。你我人等孜孜不倦所打拚之事,有哪幾件不是徒然、枉費的呢?
然而,他還是一旦咬住了就不鬆口,就是要從百分之九十八的徒然裡,找出那百分之二的存在意義。
於是,推理一點不重要,破不破案也不是重點了。有人從馬修身上讀到了堂吉訶德,有人看到了卡拉馬助夫兄弟;有人說他是班雅明筆下「複製時代的抒情詩人」、「步行者」;有人則相信他是推著石頭上山的現代薛西佛斯……。凡此種種,無非說明了一件事:馬修.史卡德像鏡子,人人都可在他身上照見到自己,照見到比敘事更多的其他東西。而這,大約就是「經典」的本質了。
一口咬定「馬修.史卡德系列」已成「經典」,未免說得快了,畢竟最近一本《烈酒一滴》出版於二○一一年,還待時間考驗汰擇;但若說,這套從一九七六年創作迄今,歷時三十多年,前後十七冊的小說,已然具備「推理名人堂」候選資格,相信絕不會有什麼人有意見的。
也因此,當「臉譜出版」期望為此系列再出一個新版本,邀請我參與其事時,我欣然同意。畢竟,人生能有幾次機會為自己所仰慕的作家編一套書呢!?
此次新版修訂作業,大體分為兩部分,內容與裝幀都有許多變動。
內容方面,由於出版時間跨越十多個年頭,執行編輯屢經更迭,譯者多有,許多人名、地名或專有名詞未見統一,前後冊常見扞格,趁此機會一一修訂,讓讀者閱讀時,得以一氣呵成,疑惑不生;譯文方面,盡量保持譯者多元風格,但若確定錯譯、漏譯,經徵詢後,都予修正。甚至連書名,只要有問題,也都盡量求取確定答案。譬如讀者曾質疑,《每個人都死了》(Evebody Dies)中譯書名若為《每個人都會死》,當更精準。為此,我們特別親詢卜洛克,經他回答:「都可以!書名應該保持某種曖昧,讓讀者有更多想像空間。」遂決意維持原名不動。
至於實有發微抉幽之功的「唐諾導讀」,早已成為此系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基本維持不動,僅於涉及時事處,加以註解,方便讀者掌握行文來龍去脈,了解敘事理路;系列編號則按照英文出版,重新依序排列,讓這套書最大特色的「時間感」,得以凸顯。閱讀過程裡,讀者更能感受馬修在時間之河裡奮力泅泳,逐漸老去,終而得以迎向隧道最後那一線光芒的微妙心境轉折。
裝幀設計上,特別邀請著名平面設計工作者楊雅棠擔綱,除了提供一般讀者的「平裝版」之外,更設計一款附有松木書箱,亦得為書架的「珍藏版」,限量五百套,用饗重度發燒友,以便傳家。此版封面,楊雅棠以「一抹紅」表達了這一套書「懸疑、危險、溫暖」本質,簡潔明亮的設計出「很不傳統、很不一樣」的成組推理封面,讓人耳目一新,心湖大大為之一蕩。
相對於此,平裝版封面幾乎每一個都獨立表達一個抽象的詞彙,譬如「背叛」之於《酒店關門之後》,「執念」之於《到墳場的車票》,「情慾」之於《屠宰場之舞》……等等。整體則維持他一貫素雅細緻的風格,並與時俱進,添加更多「現代」元素,希望跳脫窠臼,吸引更多新世代年輕讀者,親近這套「非常不推理的推理經典」。
「馬修.史卡德系列」全套十七冊,數逾五千頁,共二百餘萬言。短短半年不到的時間裡,要完成浩大的「改建重裝」工程,其艱難可知,疏漏必然不免,還望四方讀者不吝予以指教。「校書如掃落葉,旋掃旋生」,編書當亦如是,只能盡力,無從滿意。而這一份「永遠追求更好」之心,實即一名編輯所能奉獻給作家與讀者的最大溫情與敬意了。
〈推薦序〉
不養貓的偵探:鑑賞勞倫斯.卜洛克與馬修.史卡德\史蒂芬.金
1
替一本好的類型小說(深受讀者歡迎、歷經時間考驗)進行導讀,就有點像是在婚禮上擔任伴郎一樣,唯一的差別是:要當個成功的伴郎,只要別在典禮上昏倒或是大放響屁,然後在對的時間點遞上戒指就行。做為一名導讀者,是不用擔心會把戒指弄丟,不過卻得發表點意見,還得要能讓那位被他介紹的主角(唯一一個保證會看這篇導讀的人)覺得有趣才行。
當你介紹的是一本了不得的通俗文學時,想說些機智有趣的話有時還真是難如登天。相信我,我替好幾本書寫過序,大部分都疑似是一千二到三千字不等的廣告文宣。這項任務之所以會這麼艱難,一言以蔽之,原因就出在「引起共鳴」這件事上。一本好的通俗小說得具備許多要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否引起讀者共鳴」。大部分文學導讀在本質上都屬於內容解析,然而對於真正能「引起共鳴」的文章(也就是以易於理解的文筆,使閱讀成為一件愉快享受的事),內容解析便顯得冗長而多餘。
平易近人的文筆,不過是勞倫斯.卜洛克身為作家的美德之一,卻也無疑是他最棒的天賦。他的小說(已有二、三十本)結合了簡潔、平實、真誠以及生動等特色,帶來流暢痛快的閱讀經驗;讀者從未感覺到作者絞盡腦汁、千辛萬苦像縴夫拉船那樣吃力的讓小說成型,反倒是故事忽地浮現眼前,有如高明的魔術師一張手,就有鴿子冒出來那般自然。
這點對於讀者與觀眾來說當然是件好事。那麼,對於文學的儐相(在這裡的任務就是對典禮上的主角所成就的美妙事蹟,提出一些精闢的見解)而言,又有什麼好說的呢?追本溯源或許是個辦法;在這裡大概就是以幾千字來敘述偵探故事那精采華麗的光榮過往,然後以那可歌可泣的漫長歷險所造就的傑出終端產物——卜洛克先生—來作結。不幸的是,偵探小說的歷史並不長(古典派的說法始於愛倫坡,理論派的說法則始於漢密特),也不為人所推崇(許多評論家仍然認為偵探小說不過就是在文學的按摩殿堂幫人「打手槍」的角色罷了),況且比起我的許多讀者,我對推理小說也只能說是略懂而已,所以這招沒用。
摒除了分析法則與歷史回顧,就剩下作者軼聞可以考慮了,好比說些關於作者的低級笑話之類的;再想不出來的話,就講些溫暖勵志的心路歷程等等(雖說低級笑話總是比較好,不過溫馨小品也無傷大雅就是)。不過我運氣不好,連這點都做不到。我跟老卜並不算熟,只有幾面之緣,所以我連他走溫馨勵志風還是低級搞笑風都說不上來。我只知道他跟唐諾.威斯雷克還有布萊恩.加菲爾德〔譯註:Donald E. Westlake(1933——2008),知名犯罪小說家,得過多座愛倫坡獎。Brain Garfield(1939——),小說家、劇作家,曾於一九七六年得到愛倫坡最佳小說獎〕交好(看來這表示他比較偏向低級搞笑的類型)。既然我說不準,那麼作者軼聞這部分也只得作罷。
好吧,那還剩什麼?以社交準則來評論暢銷小說?算了吧。以心理分析層面來探討暢銷小說?這更慘,簡直令人作嘔。看來只剩下老套的宣傳手法了——天曉得這套我可是在行得很。不過在此我還是想更體面的卸下這項重責大任,理由很簡單:卜洛克的小說(尤其是馬修.史卡德系列)對我而言實在太重要了。可以的話,我希望自己不要只是在那兒不知所云的說得天花亂墜。
要是那票評論家聽到有人將暢銷小說視為人生中重要的元素,肯定會嘴角上揚,但這主要是由於那些缺乏幽默感的小人、卑微的傢伙,對高尚的人格以及簡潔易懂的小品抱持了戒心與不信任感。不管這些傢伙怎麼想,好的暢銷小說確實至為重要,其珍罕的程度遠超過那些自詡為「文學評論家」的人或是所謂「學者」所能想像。將小說視為主要消遣的男男女女都很清楚,像是老卜跟馬修.史卡德這樣的存在,在世上可說是永遠不嫌多。
因此,若是連小手段跟狗皮膏藥都消去,還剩下什麼可以介紹?親愛的華生,答案再清楚不過了。
那當然就是——故事裡沒有貓〔譯註:史蒂芬.金在此將小說中的花招、噱頭等取巧手段比喻為貓〕。
2
馬克.吐溫曾說過:「這本書裡面沒有關於天氣的描寫;這是為了要寫出一個沒有天氣變化的故事所做的嘗試。」在第一本以馬修.史卡德為主角的小說《父之罪》(首刷平裝版於一九七六年出版)中,老卜便試著寫出一本連一隻他媽的貓都沒有的私探小說,而且還成功了。我認為,這在在展現了他掌握到作家應有的那種淺顯易懂的文字功力,以及他自成一格的特質。
這下你大概會認定我是在搞怪;是的話,那你就錯了——我可是非常認真的,而且我認為我有表達自己想法的權利。告訴你,我這兩年來可是閱推理、懸疑以及私探小說無數(我曾於一九九○年,擔任美國推理作家協會最佳新人獎的評審之一,所以應該不用多做解釋了),我敢說那些養貓的私探(那些貓往往一身癩痢,有著一對大卵蛋還有一隻被咬爛的耳朵),就像開著BMW的雅痞一樣滿街都是。
記得有某位評論家還是誰,對羅斯.麥唐諾〔譯註:Ross Macdonald(1915——1985),開展冷硬派小說新局的重要推理作家,曾獲英國推理作家協會的金、銀匕首獎,以及美國推理作家協會的大師獎〕筆下的陸.亞傑系列小說的整體風格,有著如下描述——「一個男人就算噙著淚水也得走下去的險惡大街」,而這樣子的風氣直至今日都未曾有什麼顯著的改變,頂多是近年來那些胸有柔情的夢幻硬漢終於歷經滄桑回到家的時候,肯定有隻掛著兩顆大蛋蛋又少了一邊耳朵的公貓來迎接他。一個私家偵探養隻貓有什麼不對?老實說,還真的不對。首先,忽然之間所有人都一窩蜂這麼搞,給自己的貓取名為米奇、史格魯葛斯、莫里亞提的偵探,就跟那些穿著亮粉短褲在鬧街路旁溜直排輪的白痴一樣多。其次,貓是種偷吃步的手段、一種情感層面的速成法,是不懂得寫作的作家寫給不懂得閱讀的讀者看的手法,其字裡行間所散發出來的驕矜自喜,就像是作者在說:「嘿!我筆下這號人物相當與眾不同喔,因為他養了隻貓!真是個好心善感之人啊。但他只能在自己於某個孤寂深夜,從暗巷撿來的流浪貓跟前,表露他充滿柔情的一面!這他媽的不算經典還算什麼?」
在我看來,真正的答案就是那個「還算什麼」,不過問題根本不在貓,而是在開頭的那段宣言:「嘿!我筆下這號人物相當與眾不同喔,因為……」
……因為他是個同性戀的高中老師,在愛人(一位在兩屆世界大賽中都投出無安打紀錄的大聯盟投手)的協助下破案。
……因為他是個侏儒。
……因為他是個俄籍猶太人。
……因為他方當壯年時在洛杉磯工作,因而認識了好萊塢鼎盛時期的各式名人。
……因為他在拿槍跟那些壞人對幹的閒暇之餘,喜歡隨性弄些藍帶水準的餐點。
……因為他是個專攻受創兒童問題的心理治療師。
……因為他是黑人。
……因為他通靈。
……因為他實際上是個女的。
……因為她是個女同性戀。
在你叫我閉上鳥嘴滾邊去之前,先讓我向你保證我絕無詆毀之意。這類小說我可迷得很,還非常喜歡上述某些角色——比如莎拉.派瑞斯基〔譯註:Sara Paretsky(1947-),鑽石匕首獎得主,其筆下角色曾獲美國推理作家協會票選最受歡迎女偵探的前三名〕筆下的維艾.華沙斯基,我簡直哈到不行;也老迫不及待要看亞力士.達拉威系列新作;還有史賓塞、哈利.史東納也是。我想表達的重點只不過是:自山姆.史貝德與菲力普.馬羅獨自走在那些險惡街頭(而且與其說是噙淚浪蕩街頭,這兩個寶貝還比較像是在街頭狂嘯而去)以來,那些私探小說裡與案件無直接利害關係、卻緊咬線索不放的局外人偵探,其地位在歷經漫漫長路之後早已變得無可撼動;因此要打造出一個具有足夠獨創性、能夠鶴立雞群的角色可說是艱難無比。結果,許多作家轉而投入標新立異的角色設定,因此少了真實細膩的人格塑造。換個說法就是:他們借助了貓的力量——許多不同樣貌、顏色的貓……不過可惜的是,他們在暗處看起來全都灰蒙蒙的。
3
正如先前所述,馬修.史卡德系列小說中並沒有「貓」的存在。舉凡美食家的料理、侏儒(儘管確實有個嗜喝伏特加的白子患者,以提供小道消息的配角身分出現在稍後的幾本作品中)、通靈人士,一概沒有。簡言之,書裡並沒有花俏的噱頭。我會說,在近二十年中只出現過三位「純」私家偵探,除了史卡德,另外兩位便是羅倫.艾索門〔譯註:Loren D. Estleman(1952-),推理小說家,他的長、短篇小說曾多次獲得夏姆斯獎肯定〕的阿默思.沃克,以及喬納森.瓦林〔譯註:Jonathan Valin(1947-),推理小說家、樂評人,曾獲夏姆斯獎最佳小說〕的哈利.史東納。
在我看來,史東納比沃克稍微成功一點,而馬修.史卡德則居三者之冠。他的成功並不在於有什麼特別之處,反而是因為他的平凡;若是你在紐約街頭遇到他,多半不會多看一眼便與他擦身而過。他之所以真,是因為整個塑造出來的環境都是真實的;而環境之所以真,是由於卜洛克的文筆將馬修.史卡德所處的紐約描繪得極為出色。超絕的營造手法,時而令人感到驚喜,卻絕不用那種「嘿,老媽!看看我,我在寫作呢!」的方式來刻意賣弄。他對位於紐約州的通勤市鎮——馬馬羅內克的卡里奧卡這間華麗卻又不起眼的酒吧式餐廳的描述,恰恰詮釋了我的觀點:「這個房間裝飾過度,混雜了一大堆紅、黑,以及冰藍色調,似乎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在力求表現,以達到某人想呈現的佛朗明哥風格。」
分析這段簡短的形容詞句就不必了,不過我認為用這句話來點出「這裡沒有貓」是很重要的;沒有依樣畫葫蘆的手法,也沒有跳火圈的花樣——就是一個我們大家都曾去過的地方。像卡里奧卡這樣的地方到處都是,這點卜洛克清楚得很。
或許有些人會爭辯說,馬修.史卡德有養貓啊,還是隻傷痕累累的凶惡老貓呢。在早期的史卡德系列中,他是個「酒鬼偵探」,在稍後的作品中則成了「逐漸復原的酒鬼偵探」——這行唯一一個「右手拿槍、左手捧戒酒大書走在險惡大街上」的警察。他確實是個酒鬼,這點毋庸置疑;在《父之罪》中這個問題還算輕微(如同《聖經.列王紀》中所描述,是「一朵不過如手掌般大的烏雲」),而這個問題則隨著後來的故事每下愈況。這個現象造成了兩大高潮(還是跟史卡德自己辦的案子沒什麼瓜葛的高潮)——其一為「承認自己是個酒鬼」(在《八百萬種死法》結尾,史卡德終於承認了自己這個問題),其二為「確認自己是個酒鬼」(在《到墳場的車票》中,他買了瓶酒、差點喝了,但最後還是拿到水槽倒了個精光)。從一開始的《父之罪》便追隨這個系列直到最近一本《屠宰場之舞》的讀者,莫不始終好奇(說不定還有點期待著)是否會有第三個高潮——重拾酒杯的史卡德。
讀者或許盼得到,或許盼不到(當然了,盼不盼得到這個問題,也就是一本好的類型小說能否成功吸引讀者的關鍵之一)。這點連我自己都很好奇;不過這個問題對這篇小短文的訴求倒是無足輕重就是。重要的是,史卡德的酗酒問題根本就不算是在取巧。我認為這不是個仿效他人的噱頭,而是相當聰明(其實「高竿」才是第一個浮現我腦海的字眼)的、針對自始就成形的這位私家偵探人格面的冥思。你可知道,這現象真是打從一開始就存在,連夏洛克.福爾摩斯(從現代的觀點來看,他實在是一位格調高雅的偷窺狂)都是條毒蟲,而且他可不只是用鼻子吸吸,還是用注射的,甚至搞不好會趁四下無人的時候狂嗑毒品。說到注射,我也想都不用想,就知道他的針筒是打哪兒來的——太簡單了,我親愛的華生。
我們大可爭論這些被迫窺探別人生活的藥物濫用者,到底能否算是與案件本質無關的局外人,或是探討在這樣的工作壓力下(那些有能力的私探幾乎總是在這份工作中看到人性最醜惡的一面),他們是否最終都會墮入瓶中或針筒中。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私家偵探與某種癮頭可說是打從一開始就焦孟不離、同根而生。無論是在舞台上、銀幕中、書本裡,任何一個自重的私探都肯定會放個一瓶什麼在身邊;大多數這類的男主角,都會在車子的置物箱以及(或是)褲子口袋裡藏個一瓶,以備不時之需。在偵探界很少見到酒鬼女主角,或是看她們把藥丸當糖果吞,不過菸槍倒是所在多有——老是看到他們隨時隨地隨手就塞一根菸到嘴裡,唰一下點燃的畫面(「我用拇指指甲擦了一根火柴,燃著了菸草」,羅倫.艾索門筆下的阿默思.沃克總如是說)。
史卡德與沃克,或說史卡德與馬羅的不同,就在於馬修.史卡德少打了傳說中的「真人免疫血清」——讓私家偵探喝一整晚的酒,隔天還能一早打起精神去吃培根蛋早餐的仙藥。事實上,馬修.史卡德一直有喝酒的習慣,早從我們一開始在史卡德最愛的酒吧「阿姆斯壯」遇見他的時候,就見他啜著摻了波本的黑咖啡。他為間歇性的陽痿所苦(又是少了「真人免疫血清」的缺陷),而他那位身為應召女郎的朋友——伊蓮——則認為說不定原因出在酗酒,而史卡德也承認有此可能—然後又繼續出門買醉去。在《酒店關門之後》(在我心中屬於「醉醺醺」的史卡德小說中的最後一本)結尾,卜洛克筆下的這位主角簡直活在地獄之中——在這個令人頭暈目眩的瘋狂世界中,每個人都在地下酒吧喝個通霄,為的就是隔天帶著全身無力的宿醉醒來,然後用阿斯匹靈配一杯回魂酒吞下肚,好繼續下一個循環。大夥兒不吃不睡(喝到醉倒就取代了睡眠)、不玩樂也不幹正事。史卡德在這個都市場景的噩夢中艱苦掙扎(這點在《父之罪》中只能略窺一二),除了下一杯酒,什麼也不想;除了痛苦,什麼也感受不到。
這幾本早期的小說——從《父之罪》到《酒店關門之後》——極其精妙的描繪出這個酒精成癮的殘缺心靈在生鏽的軌道上,一路向著命中注定的唯一死胡同暴衝的畫面。卜洛克從深層的背景到呼之欲出的前景、無所不為的挑撥史卡德核心問題,他所採取的方法實在超乎尋常。史卡德的酗酒根本稱不上是噱頭,這是個原創的設定,是卜洛克用來將酒量驚人的偵探帶回現實層面的手法。若論此類型小說的浪漫元素,卜洛克筆下這位獨行俠倒是忠於基本設定,不過也只是像查維斯.麥基〔譯註:麥唐諾筆下的私家偵探。〕一樣,很道林.格雷〔譯註:王爾德筆下一個極其自戀的人物。〕罷了。卜洛克以某種極為可信的東西取代那些老套又神話的部分,結果成就了一系列可以糅合成一本書的作品(一本都市酒鬼版的《天路歷程》),以及一個青出於藍更勝於藍的私探角色。
4
那些參加A A(戒酒無名會)的「清醒酒鬼」從不說自己「好了」,只會說他們「正在復原」。無論如何,一旦他們不把酒吞下肚,酒精就漸漸不再是個日復一日、無限循環的問題。史卡德亦如是。在最新的一本小說中,這個問題再次成為當初《父之罪》中,那片「如掌心大小的烏雲」。有次我曾聽老卜承認說,連他自己也不曉得要是史卡德戒酒了,故事還能否進行下去;就在史卡德正視自己的問題之後,接下來的那本《酒店關門之後》便反過頭來回顧他過去最醉的那段時光,而這麼做似乎更凸顯了作者對於該如何進行下去——甚或是該不該繼續寫下去—的游移不定。
最後,將史卡德從作者創作瓶頸這團五里霧(業界通常將之定名為「接下來該他媽的怎麼辦」症)中拯救出來的,正是最初創造了他的那種精神——一雙洞見澄澈的雙眼、調和適中的現實主義與犬儒主義,以及隱約透露馬修.史卡德身陷在一個無法脫逃的坑洞中、又不斷徘徊於瘋狂與迷亂之間的那種駭人絕望與失落。
「你這樣就太不上道了」,他對一個不肯收區區幾元情報費的年輕警察這麼說,而當那名警察露出不敢苟同的神色時,史卡德用他獨一無二的方式解釋了一番:「這不算賄賂,這錢乾淨得很;你幫了人家一個忙,拿個幾塊錢當作回報也是理所當然。你想想—要是有人把錢塞給你的時候你不肯拿,那就會讓很多人都緊張起來,你得用他們給你的牌來玩遊戲才行。收下吧。」
「我的老天,」那個孩子嚥了嚥口水……然後就把錢收下來了。
這簡直是個表現冷硬哲學的完美實例。不過一旦由史卡德(這位總是將十分之一所得捐給教堂的不可知論者)做出來,就顯得有種陰魂不散的模糊曖昧在裡頭。這不是勞倫斯.卜洛克在效法前人,也絕對不是什麼花招噱頭——它無疑就是一種絕妙的寫作手法。
姑且不論其他貢獻,《父之罪》至少能引領新的讀者聽聽美國小說中不同凡響的聲音、認識這位使自身所屬文類的價值獲得肯定的人物,更別說這個作品本身就具有無上的價值,而它當然值得擁有能夠流傳久遠的精裝本〔譯註:本文是史蒂芬.金於一九九二年為《父之罪》精裝版所寫的導讀〕。對了,要是你像我一樣享受反覆閱讀此書的話,別忘了——這只是馬修.史卡德那段時而痛苦,卻饒富興味的漫長旅程的開端。(劉人鳳/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