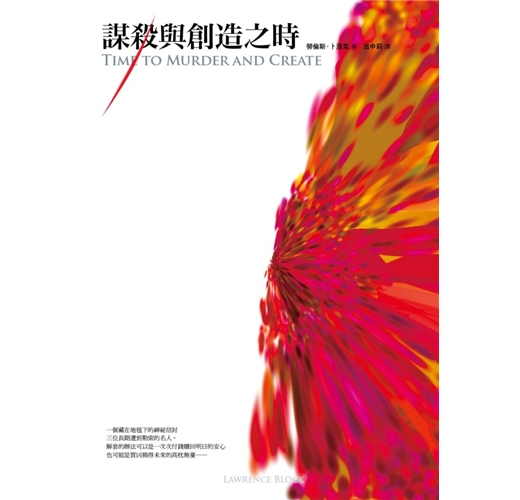名人推薦:
名人推薦
勞倫斯.卜洛克可謂犯罪小說大師……馬修.史卡德系列則可謂本世紀最棒的推理小說之一。──強納森.凱勒曼,亞力士心理探案系列作者
當代最棒最優質的小說家之一……卜洛克的私探小說創新、令人激賞。──華爾街日報
卜洛克寫得真是好,他筆下的對白活像是在紐約街頭會偷聽到的片段一樣生動精采。──華盛頓郵報
他的世界處處斷垣殘壁、夢想傾頹,處處瀰漫著絕望的氣息;然而這位都會私探即便在其中載浮載沉,卻仍然維持一貫風格,剛強與溫柔並存,絲毫不為所動。──亞特蘭大立憲報
清洌的文字,下筆犀利見骨的散文體風格,這個風格從達許漢密特、詹姆斯凱恩到勞倫斯卜洛克,一脈相承。沒錯,他就是寫得這麼好。──馬丁.克魯茲.史密斯,《高爾基公園》作者
推薦序
關於這一版……傅月庵
向一名作家致敬的最好方法是什麼?買本書追隨請他簽名,這不錯。如其因緣湊巧,能為他效勞,編一套書,那更好!
認識卜洛克是一九九七年的事。
那年,初入編輯這一行,工作壓力不大,看書成了最大福利,天經地義。恰巧「推理傳教士」詹宏志加上「臉譜」總編輯唐諾,聯兩手之力把原本冷門的「歐美推理」硬是加溫炒熱了起來,讓向來浸淫「日本推理」,只識「本格派」、「社會派」的台灣讀者,得見世界之奇,滄海之闊,慢慢竟都轉向西顧了。我是其中之一。
於是,《八百萬種死法》甫登陸台灣,便即邀來一晤,一見傾心,驚為天人。此後十多年時間裡,但凡「馬修.史卡德系列」中文新書出版,總要在第一時間購入,無暝無日讀完始休。若說我是那些年「馬修.史卡德現象」(開口閉口:「我今晚只聽不說」、「我一天戒一次」、「大多時候我是容易收買的,但你不能收買我」……)參與製造者,一點不為過。更多時候,家裡所買的卜洛克新書,一如朱天心她家一樣,總是被拿走,總要再補。
甚至讀著讀著,竟把他與王國維等量齊觀了:
「嗚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過,即以生活之苦痛罰之。此即宇宙之永遠的正義也。自犯罪,自加罰,自懺悔,自解脫。」,四月裡,斷斷續續,我一直在重讀卜洛克的馬修.史卡德探案。原因是偶然看到王國維〈紅樓夢評論〉這幾句話,忽然隱約理解一些「生命自持」的線索,因而更想靠近卜洛克,貼近馬修.史卡德。有些書,你不論何時讀,總會讀出一些道理。有些書,時候不到,你很難理解。人間無理可推,無謎可解。我所等待的四月的雨,最終還是沒有落下來,但我還有五月可以等。我一次等一天……。
奇怪的是,儘管日後卜洛克其他系列一一被引入,我也嘗試找來一讀,卻都不甚入港,從「雅賊」到「殺手」,就是有「隔」,進得去,耽溺不了。這事,跟小說行不行關係不大,純然緣分作怪,緣淺還能說什麼?有位朋友,他是「雅賊迷」,愛跟我鬥嘴,老說柏尼.羅登拔如何如何機智迷人,怎樣怎樣淵博難說,「真正愛書人都該喜歡他!」對此,我想了想,總冷冷一句回嗆:「不會老的不是人,角色而已,喜歡個什麼勁兒?」
誠然,「馬修.史卡德」與其他類型小說最大的不同是,馬修肉體會衰老,意志會動搖,道德會踰矩,辦案會潛行由徑,人家給錢他通常都收下,轉個身卻又丟一些到教堂捐獻箱。案件向來不是他的困擾,女人也不是,真正困擾他的,無非紅塵滾滾,該如何照著自己的那一套存活下去,或說存活出來自己的那一套。而幾乎有大半的時間(至少從一九七六到一九八二年,整整六年時間裡,他終於明白且面對「我是酒鬼」這一事實),他都是在跟酒瓶奮戰,To be or not to be?說穿了,馬修既不「冷」也不「硬」,與我們人人都一樣,他心中也有一個哈姆雷特。
至於辦案方式,也奇了,他似乎沒多少小小的灰色腦細胞,也沒有角落或輪椅,鐵拳或好大一把槍。接了案子,他只能不停打電話,不斷上街晃盪詢問,「有時候我們知道一些事情,卻不知道我們知道」、「去他的,東西全在那兒,只是我看的方法不對。」要想知道,要看對,只有一個方法:GOYAKOD,Get Off Your Ass and Knock on Doors,抬起屁股敲門去!天道酬勤,也許就對了。但「其實百分之九十八的調查工作皆毫無意義,你只能把想到的事都做好。你不知道哪件有用。你就像在煤礦堆裡找尋一隻不存在的黑貓,但除此之外我不曉得還能怎麼做。」——這不就是人生嗎?「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人一切的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有什麼益處呢?」幾千年前,傳道者早已論定。你我人等孜孜不倦所打拚之事,有哪幾件不是徒然、枉費的呢?
然而,他還是一旦咬住了就不鬆口,就是要從百分之九十八的徒然裡,找出那百分之二的存在意義。
於是,推理一點不重要,破不破案也不是重點了。有人從馬修身上讀到了堂吉訶德,有人看到了卡拉馬助夫兄弟;有人說他是班雅明筆下「複製時代的抒情詩人」、「步行者」;有人則相信他是推著石頭上山的現代薛西佛斯……。凡此種種,無非說明了一件事:馬修.史卡德像鏡子,人人都可在他身上照見到自己,照見到比敘事更多的其他東西。而這,大約就是「經典」的本質了。
一口咬定「馬修.史卡德系列」已成「經典」,未免說得快了,畢竟最近一本《烈酒一滴》出版於二○一一年,還待時間考驗汰擇;但若說,這套從一九七六年創作迄今,歷時三十多年,前後十七冊的小說,已然具備「推理名人堂」候選資格,相信絕不會有什麼人有意見的。
也因此,當「臉譜出版」期望為此系列再出一個新版本,邀請我參與其事時,我欣然同意。畢竟,人生能有幾次機會為自己所仰慕的作家編一套書呢!?
此次新版修訂作業,大體分為兩部分,內容與裝幀都有許多變動。
內容方面,由於出版時間跨越十多個年頭,執行編輯屢經更迭,譯者多有,許多人名、地名或專有名詞未見統一,前後冊常見扞格,趁此機會一一修訂,讓讀者閱讀時,得以一氣呵成,疑惑不生;譯文方面,盡量保持譯者多元風格,但若確定錯譯、漏譯,經徵詢後,都予修正。甚至連書名,只要有問題,也都盡量求取確定答案。譬如讀者曾質疑,《每個人都死了》(Evebody Dies)中譯書名若為《每個人都會死》,當更精準。為此,我們特別親詢卜洛克,經他回答:「都可以!書名應該保持某種曖昧,讓讀者有更多想像空間。」遂決意維持原名不動。
至於實有發微抉幽之功的「唐諾導讀」,早已成為此系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基本維持不動,僅於涉及時事處,加以註解,方便讀者掌握行文來龍去脈,了解敘事理路;系列編號則按照英文出版,重新依序排列,讓這套書最大特色的「時間感」,得以凸顯。閱讀過程裡,讀者更能感受馬修在時間之河裡奮力泅泳,逐漸老去,終而得以迎向隧道最後那一線光芒的微妙心境轉折。
裝幀設計上,特別邀請著名平面設計工作者楊雅棠擔綱,除了提供一般讀者的「平裝版」之外,更設計一款附有松木書箱,亦得為書架的「珍藏版」,限量五百套,用饗重度發燒友,以便傳家。此版封面,楊雅棠以「一抹紅」表達了這一套書「懸疑、危險、溫暖」本質,簡潔明亮的設計出「很不傳統、很不一樣」的成組推理封面,讓人耳目一新,心湖大大為之一蕩。
相對於此,平裝版封面幾乎每一個都獨立表達一個抽象的詞彙,譬如「背叛」之於《酒店關門之後》,「執念」之於《到墳場的車票》,「情慾」之於《屠宰場之舞》……等等。整體則維持他一貫素雅細緻的風格,並與時俱進,添加更多「現代」元素,希望跳脫窠臼,吸引更多新世代年輕讀者,親近這套「非常不推理的推理經典」。
「馬修.史卡德系列」全套十七冊,數逾五千頁,共二百餘萬言。短短半年不到的時間裡,要完成浩大的「改建重裝」工程,其艱難可知,疏漏必然不免,還望四方讀者不吝予以指教。「校書如掃落葉,旋掃旋生」,編書當亦如是,只能盡力,無從滿意。而這一份「永遠追求更好」之心,實即一名編輯所能奉獻給作家與讀者的最大溫情與敬意了。
〈導讀〉
向困難處去
唐諾
同時,我們覺得,重要的是信念本身是否誠實和有意義……至於結果,那便取決於際遇了。只有際遇才能指明,我們是在同幻影還是同真正的敵人作戰。
——屠格涅夫,〈哈姆雷特與唐吉訶德〉
最近,有一份甫上市就傾售一空的新理財雜誌用了類似的slogan:「有知識,才有財富;有財富,才有自由。」這兩句擲地如金石的漂亮誓言,震撼了我個人和身旁一干手頭並不寬裕的朋友,把我們從「安貧樂道」這個自我陶醉的保護藉口中打回原形,原來這麼多年下來,我們不但一直活在某種集權鐵幕之中,而且活該被罵「沒知識」。
因為還是不太甘心被罵,我們遂由此發展了一堆更加無賴的玩笑,包括,月初發薪日開始跟老闆抱怨:「最近全亞洲自由都貶值了,能不能多給點自由?」包括,我們進一步讓自由成為貨幣計量單位,「你這件新衣服很好看。」「很便宜啊,一件才二百五十個台灣自由。」包括,我們覺得終於懂了,三重幫大財閥林榮三所辦的報紙,明明每事以層峯馬首是瞻,為什麼好意思取名《自由時報》;包括,我們還自認解開了「不自由,毋寧死」這句歷史格言的真正意義:沒有自由,反正早晚得痛苦餓死,倒不如自己早做了斷云云。
自由自由,果然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但說正經的,人家這兩句話也不能說完全不對,事實上,不論就歷史經驗,或從理論推演,財富的累積的確有助於人類的解放,比方說,人類早期文明的創造,不來自終日不得喘息的勞動者,而來自占有財富的遊手好閒者,這個「有閒階級創造論」就連馬克思本人都同意,亦早已成為定論了;又比方說,二十世紀中有相當的自由主義者一度相信,人類自由的最後障礙是經濟問題,就像百貨公司中琳琅滿目的商品,依法律,上自王公貴族下至販夫走卒誰都能自由購買——障礙是,你沒有錢。
只是,財富和自由不是連體嬰,不會永遠如此甜蜜的亦步亦趨下去。當財富的追逐和堆積到某個臨界點時,它之於自由的邊際效益不僅可能會降低為零,甚至會呈現負值,這階段,財富就不再是偉大的自由解放者了,反而成為枷鎖。這個效應,特別在資本高度發達、財富大量累積的社會普遍得近乎常識,我們眼前的台灣也差不多走到這樣的階段了,有一句話「胃潰瘍是事業成功者的象徵」,說的就是這麼回事。
解開這枷鎖的方式理論上不難,從邊際效益的角度追下去思考,我們只要通過理性計算、懂得在財富的邊際效益下滑到「不划算」的某一點時停止追逐不就行了。但事實很難這樣,因為金錢不是透明沉默的交換工具,它會直接成為目的本身:當追逐並累積財富直接成為自身的目的,便和理性的、實質的效用脫離,成為抽象的數字增長,成為停不下來、不可能完成、終身實踐的準宗教了,所以我們會看到,蔡萬霖還要賺更多錢,辜振甫就連自己票一齣爛戲也要申請國家「區區幾百萬」的補助,連戰搞個意在選總統的基金會也要行政院撥款上億元——這些人老早就擁有幾百幾千輩子用不完的財富了,多出來這些巧取豪奪的金錢從邊際效益來看頂多是零,但絲毫阻擋不了他們「寧可拿錯,不可放過」的金錢本色。
了解這樣的台灣現況,我們便知道,賺錢這檔子事雖不必有何罪過,但它自身動力十足,實在不待我們再去搧風激勵,為它買贖罪券,更不必飾以知識之美名,奉上自由之冠冕(把這個榮譽保留給另一些孜孜於換不了錢信念的人不好嗎?),要賺,就請大家不必客氣不必慚愧去賺吧!
說到這個,就令人份外想念我們這位沒錢沒車沒房子、卻瀟灑自由的紐約好朋友馬修.史卡德先生了。
《謀殺與創造之時》,這部小說有知識有自由,但它不教你如何賺錢,反而會告訴你該停下來了。
◆浪費與冒險之時
《謀殺與創造之時》,純就偵探類型小說而言,卜洛克這樣子寫這本書,不僅浪費,而且還冒了險——小說中,史卡德這次的委託人「陀螺」是一名自知不保、也果然一開始就被宰的勒索者,此人手中握著三件醜聞,因此,凶手極可能便出自於這三者之中。
之所以說浪費,意思是,卜洛克身為一個靠寫書賣錢的類型小說家,題材即金錢,較合理的方式是,他應該想辦法把這三件罪案分別寫成三本書(甚至三本以上),賣三次錢,而不是這麼慷慨一本書全用掉。
至於冒險,指的是,卜洛克讓史卡德不負死去之人的付託,矢志要逮出凶手,然而,在破案同時,另外兩樁醜聞很難避免也得跟著曝光。我們知道,醜聞的發生,有時純是當事人的罪惡所造成,但也往往來自當事人的不幸與無奈,對這樣不幸而且又沒殺人、且長期飽受醜聞和勒索所折磨的人,揭開他來公平嗎?符合正義和人情嗎?史卡德便得如此時時行走在信念和良心的刀鋒上頭,在慷慨破案和傷及無辜中痛苦的抉擇。
傷及無辜,這會違反類型讀者對實質正義的簡單期待,違反讀者的期待超過某個臨界點,懲罰便伴隨而來——類型讀者的懲罰簡單有效而且很容易辦到,那就是不買你寫的書了,這對類型小說家而言,肯定是致命一擊。
於是,我們便了解了,類型小說的意識形態和情節內容為什麼總是簡單且保守——他們不能沒事冒險,不能「試驗他們的主」讀者,小說家要保有寫作的自由,便得承受損失財富的危險。
只是,方便的路走慣了,人會變懶;容易的事做多了,人會變笨:想的寫的盡是簡單保守的東西,作品會變壞變無趣,因此,也就難怪類型小說家最好的作品往往出現在他前三本書之中,甚至就是第一本。
◆兩名小說家的兩個有趣例子
在財富和作品水平做二選一,固然,大多數的類型作家可能並不那麼在乎自己的東西是否愈寫愈壞,但人世間畢竟不全然這麼灰黯,還是有些人在乎的,卜洛克顯然便是其中一個。
熟讀馬修.史卡德系列的人都不難發現,卜洛克總不肯「聰明」的避開難題,援引類型小說所允許且慣用的「破案=正義」的簡易公式進行,他總忍不住昂首往困難或甚至泥淖深處走去,問一些看來徒勞無功、他自己也無力回答的問題,包括生死的問題,包括終極正義的問題,包括人的種種處境問題云云。
在《刀鋒之先》一書之中,卜洛克寫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對話大致如此:當時,史卡德的查案陷入泥淖,他有一種拿人錢財卻無力替人消災的懊惱,他那本書裡的女友前共產黨員薇拉安慰他:「你做了工作了。」( You've done your work.)卜洛克用了work這個字的雙關語來回答,work,物理學上我們稱之為「功」,公式是力量和距離的乘積,比方說一物重二十磅,你往前推了六呎,你就等於做了一百二十呎磅的「功」。史卡德說,而他所做的卻像是推一堵牆,推了一整天也沒能讓它移動分毫,因此,儘管你是拚盡了全力,你就是沒有做成任何的「功」。
這讓我想到另一位了不起的小說家格雷安.葛林在他小說《輸家全拿》(Loser Takes All,或譯《賭城緣遇》)中一個有趣的發想:書中的主人翁流落到賭城,偶爾從一個老頭手中得到一個必然贏錢的賭法,但這個最後必然大贏的賭法非常詭異磨人,它必須先挨過一定階段的輸錢,只能輸不能贏,而且明知是輸亦一步也不能省——我記得寫小說也是葛林迷的朱天心引用過這個例子,據說她在新小說能順利開筆之前總要經過同樣短則數日長則數星期的枯坐思索(在小說題材業已鎖定的狀況下),明知一無所獲仍得每天帶著書、草稿本和筆到寫作的咖啡館報到,她的口頭禪便是:「去輸錢。」
這兩個有趣小說家的有趣例子,其中有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解決困境的階段性不均勻,它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式的每投一分心力就有一分進展,相反的,在過程中你像整個人浸泡在彷彿無際無垠的困境之中,除了困惑和徒勞之外什麼也沒有,然後忽然有一天牆開始動了,賭錢的輪盤開始跳出你押的數字來。
兩個例子不同點在於,葛林讓我們看到辛苦長路末端的光明終點,你挨夠了輸錢便能瞬間大贏,卜洛克則不給我們任何確切的答案,你推的極可能就是一堵根本不會動的牆。
◆被丟棄的困境
困境這種過程的絕對不均勻和結果的高度不確定,使它很難被管理,被做成有效的評估和有步驟的計畫,換句話說,極容易和我們的「合理化」要求牴觸。
美國已故星座名家古德曼老太太在談射手座的高遠之志時曾說:「……瞄準天上沒人看得到——或說稍有理性的人都不當它存在——的目標。」事事講求合理的人,不會明知山有虎卻一定要走這條路,他會繞道;不會像昔日的梵谷一樣把自己給曝晒在法國南方的烈日和貧窮之中,瘋子一般畫下自己眼中心中的圖像,他會放棄;也不會花三年五年時間去辛苦經營一部賣不了兩個錢或甚至連出版都不能的長篇小說,他會轉業或乾脆到意識形態廣告公司去謀職賺容易的錢……
所以說,困境之難,還不在於難以承受和克服,而是它總是「聰明」的被忽視被棄置,「策略性」「技術性」的被繞過。
當然,對一個社會絕大多數的人來說,懂得如此避開應該算好事,生活夠艱難的了,每個社會也都備有相當的機制包括宗教、心理諮詢、自由經濟市場等等直接間接引領我們躲開這種泥淖困境,好讓人生活得開心一些,然而,如若整個社會所有人都這麼聰明,那就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或很遺憾了,這樣的社會很容易變懶,失去思省的厚度和深度,拓展不開心靈的邊界和視野,亦容易喪失應有的想像力。
因此,我們遂不得不對某些個聰明才智之士,尤其是從事某種「拓展思維和心靈疆界」志業的人,有著較嚴厲點的期盼,希望他們矢志不回,不躲不避。
◆向自討苦吃的人致敬
如果還能更嚴厲一點,我們不光希望他們不閃躲,而且更主動一些哪裡有困難往哪裡去——台灣的名導演侯孝賢在一次談拍片經驗時,曾說過「給自己出狀況」,意思是,他往往會在拍片進行到順利如流水的時刻,提醒自己緩下來停下來,甚至主動丟幾個障礙給自己,嘗試一些較困難的角度和手法,他的創作經驗告訴他,太滑太沒阻力的進行往往會讓作品的幅單調而薄,等剪片時會發現宛如單行道一般再沒其他的可能和彈性了。
要人家如此自討苦吃,我們在這裡似乎便有責任做些必要而乏味的提醒了——在創作所關注的人文思維領域之中,就像卜洛克所一問再問的正義問題、生死問題、人的種種處境問題,往往並不伴隨一個妥善的終極答覆,它既不像葛林的方子所應允的必然贏錢結果,倒也不盡如卜洛克的牆那般悲壯的動也不動,毋寧,它更像個古老無趣的比方:地平線。你可能察覺自己的推動工作有所進展,但吊詭的是,你和終極答案的距離關係似乎一無變化,這是數學最基本的無限概念。
所以說,「只重過程不問結果」是不是?不,當然不是這麼虛矯甜美的氛圍,相反的,你必須去問結果,想盡辦法去逼近結果,即使面對的是不可逾越的堅城,而你手中所有的,不過是一匹瘦馬、一支生銹的長矛和一具拼拼湊湊的鎧甲,你仍得奮力攻打,如此,它的過程才是壯麗的、也充滿啟示的。
對這樣自討苦吃的人,我們無以為謝,就讓我們為他脫帽致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