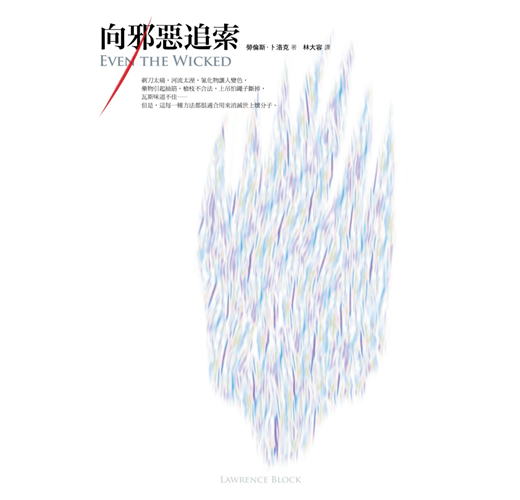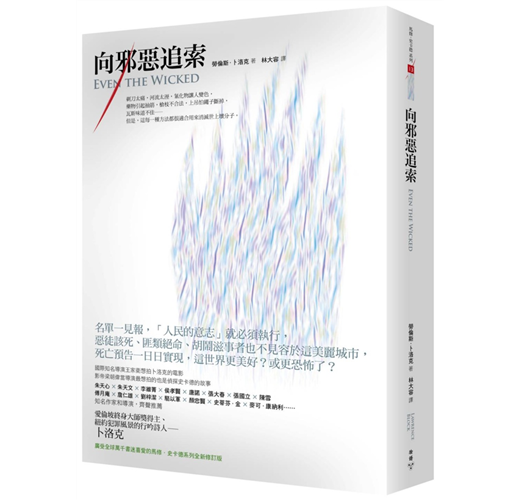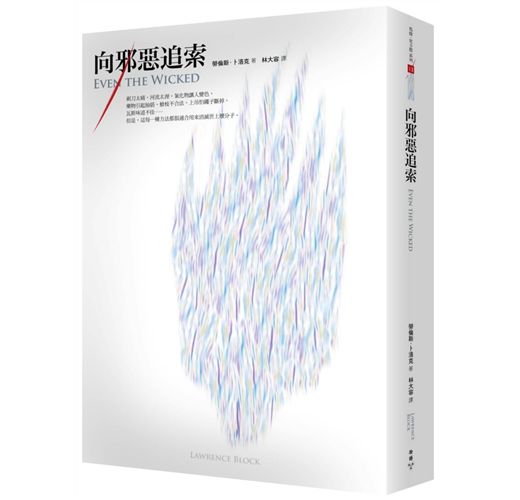剃刀太痛,河流太溼,氰化物讓人變色,
藥物引起抽筋,槍枝不合法,上吊怕繩子斷掉,
瓦斯味道不佳——
但是,這每一種方法都很適合用來消滅世上壞份子。
國際知名導演王家衛想拍卜洛克的電影
影帝梁朝偉當導演最想拍的也是偵探史卡德的故事
朱天心x朱天文x李維菁x侯孝賢x唐諾x張大春x張國立x陳雪
傅月庵x詹仁雄x劉梓潔x駱以軍x顏忠賢x史蒂芬.金x麥可.康納利……
知名作家和導演,齊聲推薦
愛倫坡終身大師獎得主、紐約犯罪風景的行吟詩人——卜洛克
廣受全球萬千書迷喜愛的馬修.史卡德系列全新修訂版
一旦你的名字出現在死亡名單上,
每一口呼吸,都要珍惜!
自稱代表「人民的意志」的威爾投書,藉著馬提.麥葛羅《每日新聞》上的專欄公告他預定的死亡名單。之後,一連串的凶殺案,戲劇性登場。
首先,殘酷連續虐童殺人犯理查.佛莫,拜辯護律師艾卓恩.懷菲德所賜,得以無罪釋放,但過不久,威爾把殺人犯吊死在當初受害人陳屍處附近;接著,紐約黑手黨、五大幫派家族之一的頭子帕奇.薩勒諾,在警察對他束手無策時,被人發現躺臥在餐廳的廁所地板上,一根兩呎長的鋼琴絃繞住了他的脖子;能言善道的反墮胎行動領導人羅斯偉.貝利,在一次次挑起支持者的暴力行動後,威爾決定一刀讓他斃命,並在他的頸子上纏了一個衣架;而朱里安‧若許德,煽動種族仇恨的黑人種族優越論者,則是在威爾還來不及動手之前,就被他的屬下以一把賽努佛族的斧頭,終結他的生命。
「威爾旋風」被媒體大肆渲染,市民無一不關注下一個人選究竟是誰。而此刻馬修.史卡德得到了答案──艾卓恩.懷菲德來電,委託他保護自己。
為了阻止威爾再度犯案,並保護列入死亡名單的委託人,史卡德縝密布局,二十四小時輪班貼身保鏢,隨時監控懷菲德周遭。可是,懷菲德卻仍在保鏢眼前倒下,中毒身亡!
完美的凶殺,任務的挫敗,逼得史卡德使出渾身解數,遍尋一切細節。而就在威爾身分呼之欲出的時刻,一封死亡指定名單的信件,刊登在《每日新聞》上!
下一位該死的,是誰?腐敗政客?淫蕩名流?
恐怖的幕後藏鏡人,何在?完美密室謀殺案真正隱藏的是哪些骯髒的秘密?
威爾的出現,又是基於什麼動機?正義?名利?或是一切只為have fun?
「過去多年有些什麼始終糾纏著我,現在都不見了。只不過它們偶爾還會回來,尤其往往發生在十一月底。白晝愈來愈短,陽光愈來愈淡,我也開始憶起我沒買的每一件禮物,吵過的每一次架,講過的每一句刻薄話,還有我找藉口留在紐約而不肯拖著疲倦的身軀回長島西歐榭的那些夜晚。」——史卡德
作者簡介:
勞倫斯.卜洛克 Lawrence Block
1938年出生於紐約水牛城。除了極少時間之外,卜洛克幾乎都定居於紐約市內,並以該城為主要背景,從事推理文學創作,成為全球知名推理小說家,因而獲得「紐約犯罪風景的行吟詩人」美譽。
卜洛克的推理寫作,從「冷硬派」出發而予人以人性溫暖;屬「類型書寫」卻不拘一格,常見出格筆路。他的文思敏捷又勤於筆耕,自1957年正式出道以來,已出版超過50本小說,並寫出短篇小說逾百。遂將漢密特、錢徳勒所締建的美國犯罪小說傳統,推向另一個引人矚目的高度。
卜洛克一生獲獎無數。他曾七度榮獲愛倫坡獎、十次夏姆斯獎、四次安東尼獎、兩次馬爾他之鷹獎、2004年英國犯罪作家協會鑽石匕首獎,以及法、德、日等國所頒發推理大獎。2002年,繼1994年愛倫坡獎當局頒發終身大師獎之後,他也獲得夏姆斯終身成就獎。2005年,知名線上雜誌Mystery Ink警察獎(Gumshoe Award)同樣以「終身成就獎」表彰他對犯罪推理小說的貢獻。
「馬修.史卡徳」是卜洛克最受歡迎的系列。透過一名無牌私家偵探的戒酒歷程,寫盡紐約的豐饒、蒼涼和深沉。此系列從一九七○年代一路寫到新世紀,在線性時間流淌聲裡,顯現人性的複雜明暗,以及人間命運交叉的種種因緣起滅。論者以為其勝處已超越犯罪小說範疇,而達於文學經典地位。
相關著作
《一長串的死者》
《八百萬種死法》
《刀鋒之先》
《到墳場的車票》
《在死亡之中》
《屠宰場之舞》
《惡魔預知死亡》
《死亡的渴望》
《每個人都死了》
《烈酒一滴》
《父之罪》
《繁花將盡》
《行過死蔭之地【《鐵血神探》電影原著小說】》
《謀殺與創造之時》
《酒店關門之後》
《黑名單》
《黑暗之刺》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勞倫斯.卜洛克可謂犯罪小說大師……馬修.史卡德系列則可謂本世紀最棒的推理小說之一。──強納森.凱勒曼,亞力士心理探案系列作者
當代最棒最優質的小說家之一……卜洛克的私探小說創新、令人激賞。──華爾街日報
卜洛克寫得真是好,他筆下的對白活像是在紐約街頭會偷聽到的片段一樣生動精采。──華盛頓郵報
他的世界處處斷垣殘壁、夢想傾頹,處處瀰漫著絕望的氣息;然而這位都會私探即便在其中載浮載沉,卻仍然維持一貫風格,剛強與溫柔並存,絲毫不為所動。──亞特蘭大立憲報
清洌的文字,下筆犀利見骨的散文體風格,這個風格從達許漢密特、詹姆斯凱恩到勞倫斯卜洛克,一脈相承。沒錯,他就是寫得這麼好。──馬丁.克魯茲.史密斯,《高爾基公園》作者
名人推薦:勞倫斯.卜洛克可謂犯罪小說大師……馬修.史卡德系列則可謂本世紀最棒的推理小說之一。──強納森.凱勒曼,亞力士心理探案系列作者
當代最棒最優質的小說家之一……卜洛克的私探小說創新、令人激賞。──華爾街日報
卜洛克寫得真是好,他筆下的對白活像是在紐約街頭會偷聽到的片段一樣生動精采。──華盛頓郵報
他的世界處處斷垣殘壁、夢想傾頹,處處瀰漫著絕望的氣息;然而這位都會私探即便在其中載浮載沉,卻仍然維持一貫風格,剛強與溫柔並存,絲毫不為所動。──亞特蘭大立憲報
清洌的文字,下筆犀利見骨的散...
章節試閱
艾卓恩.懷菲德是一顆崛起中的明星。身為一名刑事辯護律師,過去幾年中,他接了許多引起爭議的案件,同時也累積了同等的媒體注意力。光是這個夏天,我就在電視上看過他三次,羅傑.愛樂斯的談話秀,邀他討論陪審團系統的觀念已過時且應予以更新的問題。(他的立場是在民事訴訟可以試驗性實施,但刑事訴訟則否。)然後他上了CNN的賴瑞.金現場扣應節目兩次,第一次是談洛杉磯的明星謀殺案,然後是討論死刑的優點。(他明確反對死刑。)最近的一
次,則是他和雷蒙.古魯留去參加查理.羅斯的節目,嚴肅的談論律師名人話題。「硬漢雷蒙」提出許多歷史上的例子來談這個話題,說了許多厄爾.羅傑斯和比爾.費龍以及克萊倫斯.達若的故事。
在雷蒙.古魯留的推薦下,我曾幫懷菲德做過一些工作,替他查證一些證人和陪審團可能人選的背景,我還算喜歡他,希望能多跟他合作。現在打電話找我談公事有點太晚,不過偵探工作的性質,就是你隨時都可能接到電話。我不介意打擾,尤其這意味著有生意上門。到目前為止,這個夏天步調緩慢。當然不見得完全是壞事,伊蓮和我有機會利用週末長假去鄉下玩了幾趟,只不過我開始有點閒得發慌了。徵兆就是我早上看報紙時,對本地的犯罪新聞特別著迷,渴望自己能夠參與辦案。
我拿起廚房的電話說,「馬修.史卡德,」表明自己的身分,以防電話可能是由別人代撥的。
不過這通電話是他自己打的。「馬修,」他說。「我是艾卓恩.懷菲德。希望沒有打擾你。」
「我正在看拳擊賽轉播,」我說。「不論我或那兩個拳手都不怎麼投入。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嗎?」
「好問題。麻煩你老實告訴我好嗎?我的聲音聽起來如何?」
「你的聲音?」
「我的聲音沒發抖吧?」
「沒有。」
「我想也是,」他說,「可是應該發抖的。剛剛我接到一通電話。」
「嗯?」
「是一個《每日新聞》的白癡打來的,不過或許我不該這麼說他,據我所知,他是你的一個朋友。」
《每日新聞》的人,我認得的沒幾個。「誰?」
「馬提.麥葛羅。」
「不太算是朋友,」我說。「我見過他一兩次,不過沒什麼機會讓彼此留下印象。我懷疑他是否還記得我,而我會記得他的唯一原因是,我每個星期會看兩次他登在報上的專欄,已經不曉得看多少年了。」
「不是一星期三次嗎?」
「嗯,星期天我很少看《每日新聞》。」
「我猜是因為你的手指被《紐約時報》占滿了。」〔譯註:《紐約時報》平常厚度約一百頁,週日版則厚達三四百頁〕
「通常占滿我手指的是油墨。」
「可不是嗎?讓人覺得他們是他媽的故意把報紙印成那樣,好讓字句留在你手上。」
「如果人類都可以登上月球……」
「沒錯,你相信大中央車站有個報攤,販售用後即丟的白色手套,讓你用來翻閱那些他媽的報紙嗎?」他吸了口氣。「馬修,我一直在逃避重點,我猜你已經曉得重點是什麼了。」
我已經想到了。「我想麥葛羅收到了另外一封信,威爾寄的。」
「是威爾寄的,沒錯。猜猜信裡的主題是什麼?」
「一定是有關你某個當事人的,」我說,「不過我不想花力氣去猜是哪一個。」
「因為他們都是值得尊敬的人物嗎?」
「我只是完全沒線索,」我說。「我沒太注意你接的案子,除了我參與過的那幾個。而且我反正不知道威爾幹嘛會關心那些案子。」
「噢,那是一種很有趣的關心方式,我必須說,相當有用,對於我正在進行的案子絕對有用的。」他暫停了一下,再開口前的那一剎那,我明白他接下來要講什麼了。「他寫的跟我的當事人無關,而是跟我有關。」
「他說了什麼?」
「唔,很多事情,」他說。「我可以唸給你聽。」
「你拿到那封信了?」
「是副本,麥葛羅傳真給我的。他找警方之前,先打電話給我,然後把信傳真過來。他實在很周到,我不應該叫他混蛋的。」
「你沒有。」
「第一次提到他名字時,我說—」
「你叫他白癡。」
「你說對了。噢,我想他不是白癡也不是混蛋,就算是,他也是白癡或混蛋類裡做事周到的一個模範。你剛剛問威爾說什麼。〈給艾卓恩.懷菲德的一封公開信〉。我們來看看。『你畢生致力於讓有罪的人逃過牢獄之災。』這一點他錯了。在被證明有罪之前,他們都是無辜的。而只要他們有罪的證據能讓陪審團相信,我那些當事人就得進監牢。除非我能上訴並獲得改判,否則他們就得待在牢裡。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想,當然,威爾的說法相當正確。我大部分的當事人都犯過他們被控告的罪名,我想這就足以讓威爾認為他們有罪了。」
「他對你到底有什麼不滿?他不認為那些被告也有找律師辯護的權利嗎?」
「這個嘛,我不想把整封信唸給你聽,」他說,「他的意見也很難精確描述,不過可以說,他對於我善於做好自己工作的這個事實,非常不以為然。」
「就這樣?」
「真好笑,」他說。「他甚至沒提到理查.佛莫,可是他會對我不以為然,就是從這個案子開始的。」
「沒錯,因為你是佛莫的辯護律師。」
「的確,而且他逃過法律制裁時,我也收到了不少充滿恨意的信件,可是威爾的信裡沒提到我讓他脫罪所扮演的角色。我們來看看他怎麼說。他說我讓警察在法庭上被審判,這又不是我一個人而已。我們共同的朋友古魯留一向把警方拿來審判。對於弱勢的被告來說,這通常是最佳策略。他還說我把被害人也拿來審判。我想他指的是娜歐蜜.塔洛芙。」
「或許吧。」
「你可能會很驚訝,我常回頭去想這個案子。不過不是當時也不是現在。我盡全力替那個姓厄思渥斯的年輕人辯護,但即使如此,也還是沒能幫他脫罪。陪審團認定那個狗娘養的有罪。他現在正在州立監獄服十五到二十五年的徒刑,不過這樣的判決,並不能影響我們的朋友威爾。他說他要殺了我。」
我說:「想必麥葛羅直接去找警方了。」
「報警之前,他先匆匆的打了個電話給我,然後把信傳真過來。事實上,他是先影印了才傳真。他不想把正本放進傳真機,以免毀損任何有形的證據。然後他打電話給警方,接著警方就來找我了。有兩個警探來我這裡待了一個小時,我可以叫他們白癡而不必擔心他們可能是你的朋友。我有任何敵人嗎?有任何當事人對我的工作成果懷恨嗎?老天在上,我所碰過會恨我的當事人,現在全關在大牢裡,根本不用擔心他們,至少我自己完全不必擔心。」
「這些問題警方還是得問的。」
「我想是吧,」他說。「不過這個人跟我沒有私人恩怨,不是很明顯了嗎?他已經殺了四個人,他殺第一個人是因為馬提.麥葛羅叫他這麼做。我不懂我為什麼會列在他的名單上,但肯定不會是因為我幫他逃過牢獄之災又收費太高的緣故。」
「警方有保護你嗎?」
「他們提過要在我辦公室外頭布置一個警衛。我看不出這樣有什麼好處。」
「也不會有壞處。」
「對,可是也幫不上太大的忙。馬修,我得知道該怎麼做。我對這種事沒經驗,從來沒有人想殺我。最接近的一次是五六年前,一個叫保羅.梅斯倫的傢伙對著我的鼻子揮了一拳。」
「是不滿的當事人嗎?」
「不,是一個喝醉的股票經紀人。他說我搞他老婆。耶穌啊,我是西康乃迪克州少數幾個沒搞過他老婆的男人之一。」
「結果呢?」
「他拳頭揮過來,沒打中,然後幾個人抓住他的手臂,我罵了幾句見鬼就回家了。後來再碰到他,我們兩人都假裝沒事發生過似的。也許他不是裝的,因為那天晚上他醉得很厲害。有可能他什麼都記不得。你看我應該把這事情告訴那兩個警探嗎?」
「如果你覺得那封信是他寫的話,那就說吧。」
「那就太神了,」他說,「因為那個可憐的混蛋已經死了一年半了。中風還是心臟病,我忘了,反正是那種暴死的病。那狗娘養的還搞不清自己是怎麼死的。不像我們的朋友威爾。他真是條操他媽的響尾蛇,不是嗎?事先警告你,讓你知道大難臨頭了。馬修,告訴我該怎麼做。」
「你該怎麼做?你應該離開這個國家。」
「你不是認真的,對吧?就算你是認真的,我也不可能出國。」
我並不驚訝。我說:「你現在人在哪裡?辦公室嗎?」
「不,我一擺脫警方就離開了。我現在回到我的公寓,你沒來過,對吧?我們一向在市中心碰面。我住在……老天,我剛剛還猶豫該不該在電話裡告訴你呢。可是如果他想竊聽我的電話,就得先知道我住在哪兒,你說是不是?」
稍早他問過我。他的聲音聽起來是不是在發抖。當時沒有,現在也沒有,可是隨著他的談話愈來愈顛三倒四,他的焦慮是很明顯的。
他告訴我地址,我抄了下來。
「哪裡都別去,」我說。「打電話給門口的警衛,告訴他你在等一個名叫馬修.史卡德的訪客,除非看到我附相片的身分證件才能讓我上去。另外告訴他,我是你唯一在等的訪客,別讓其他人上去,包括警方都不行。」
「好。」
「把電話答錄機打開,替你過濾電話。除非你認得打電話來的人是誰,否則別接電話。我馬上趕過去。」
***
整件事情是從一個報紙專欄開始的。
當然,是馬提.麥葛羅的專欄,而這件事出現在六月初某個星期四的《每日新聞》上。麥葛羅的專欄「答客問」,每週二、週四,還有週日會見報。這已經是過去至少十幾年來紐約小報的一個固定專欄,專欄名稱都一樣,不過見報日不見得一樣,也不見得是在同一份報紙上。麥葛羅過去幾年跳槽過幾次,從《每日新聞》跳到《郵報》,然後又跳回來,中間還待過《新聞日報》。
「給理查.佛莫的一封公開信」,是這篇專欄文章的標題,內容也是如此。佛莫是紐約州首府阿爾巴尼人,四十出頭,有一大串攻擊輕罪的被捕前科。幾年前他因為侵犯兒童而入獄,心理治療過程中表現良好,諮詢顧問寫了一封對他很有利的報告給假釋庭,佛莫就重獲自由,發誓他從此會循規蹈矩,而且將奉獻他的餘生幫助他人。
他在獄中曾和一個外頭的女人通信。她是看了徵友廣告和他成為筆友。我不明白什麼樣的女人會想跟一個囚犯通信,但上帝似乎製造了很多這種女人。伊蓮說她們融合了低度自尊和救世主情結;此外,她說,這對她們來說,有一種不必煞車的吸引力,因為男的關在牢裡,根本沒什麼好擔心的。
總之,法蘭妮.倪格麗的筆友出獄了,他不想回阿爾巴尼,於是就到紐約市找她。法蘭妮是個三十來歲的護士,自從母親過世後,就獨自住在華盛頓高地的港口大道。她每天走路到哥倫比亞長老會醫院上班,替教會服務和社區組織基金籌募行動當義工,養了三隻貓,同時寫情書給理查.佛莫這類良善公民。
佛莫搬去跟她一起住之後,她就沒再寫信了,他堅持要當她生命中唯一的罪犯。她很快就沒什麼時間替教堂或社區組織當義工,不過還是有好好照顧三隻小貓。理查喜歡那些貓,三隻貓也非常喜歡他。法蘭妮一個同事常警告她別跟前科犯交朋友,法蘭妮也不只一次的回答。「你知道貓咪是什麼樣的,」她嬌滴滴的說,「而且貓很會判斷人的性格。牠們絕對愛死他了。」
法蘭妮在判斷人的性格上,本領也跟她的貓咪一樣。奇怪的是,監獄裡的心理治療並沒有改變她愛人的性行為傾向,他又回到誘姦孩童的老路上。一開始他勾引十來歲的男孩到港口大道公寓裡,把法蘭妮的裸體拍立得照片給那些男孩看,保證法蘭妮會跟他們上床。(除了肩膀很垮以及五官看起來有點像牛之外,她的大胸脯和飽滿的臀部,都讓她成為一個不無吸引力的女人。)
無論再怎麼心不甘情不願,她依照理查的承諾給了那些男孩該給的東西。她的某些訪客很樂於讓理查加入這個狂歡派對並雞姦他們。其他人則否,只是,他們又能怎樣?理查是個孔武有力的大塊頭男人,體力上可以予取予求,於是那些男孩只能就範,成為這個過程中第一階段的熱心參與者。
情況愈演愈烈。法蘭妮花光存款買了一輛旅行車。鄰居愈來愈習慣理查在公寓前面的街上洗車擦車的情景,他顯然對他的新玩具很自豪。鄰居們沒看到他如何裝飾車子內部,裡頭放了張床墊,車子邊的欄杆上還有些綁縛的工具。他們會開著車在市區轉,到了適當地區時,就由法蘭妮開車,理查躲在後車廂。然後法蘭妮會找個小男孩(或小女孩,無所謂),說服他們進入旅行車。
完事後,他們會放那些小孩走。直到有一天,有個小女孩一直哭個不停。理查找到讓她停止哭泣的方法,然後把屍體丟在內林丘公園裡一個樹木茂密的地方。
「那是最棒的一次,」他告訴她。「使一切更加圓滿,就像餐後來份甜點一樣。我們應該把他們都解決掉的。」
「好吧,從現在開始。」她說。
「想想最後她眼中的神情,」他說。「耶穌啊。」
「可憐的孩子。」
「是啊,可憐的孩子。你知道我希望怎樣?我希望她還活著,好讓我們從頭再來一遍。」
夠了。他們是禽獸—這是我們給他們貼上的標籤,奇怪的是,這個說法是用在一些我們的同類身上,而他們的行為在其他較低等動物身上其實很難以想像。他們找到了第二個被害者,這回是個男孩,然後把他的屍體丟在離第一具屍體半哩處,接下來就被逮了。
毫無疑問,他們有罪,這個案子本來應該十拿九穩的,可是後來卻一片接一片的崩潰掉了。由於法官提出種種理由拒絕,有一大堆陪審團無法看到的證據和無法聽到的證詞。這應該也無所謂,因為法蘭妮已經認罪,並且做了對理查不利的證詞—他們沒有結婚,所以也沒任何特殊保密的藉口可以阻止她這麼做。
結果她一自殺,一切就都完了。
理查的案子依然在陪審團面前被起訴,但沒什麼大用,而且理查的律師艾卓恩.懷菲德是個好律師,有辦法找出種種破綻讓理查過關。結果法官的求刑輕得幾近於無罪釋放,而陪審團花了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就回到法庭,做成無罪的決議。
「真可怕,」一名陪審團員告訴某記者,「因為我們都十分確定是他犯了那些罪,但檢方無法證明。我們必須判他無罪,但無論如何,應該找個方法把他關起來。這種人怎麼可以放掉他,讓他重返社會呢?」
這也是馬提.麥葛羅所不解的。「在法律的眼中,你或許是無罪的,」他威脅道,「但在我、我所認識的每一個人的眼中,你就像原罪一樣有罪。只有那十二個受限於司法系統而必須像司法女神一般盲目的陪審團員除外……
「有太多人像你一樣,」他繼續寫道,「鑽司法的漏洞而讓這個世界更不宜居住。我必須告訴你,我希望上帝有個方法能擺脫你,動用私刑是個壞方法,只有.瓜才會想回到無政府的民兵時代。但你是一個強而有力的論據。我們無法動你一根汗毛,而且我們只能讓你生活在我們周遭,就像個趕不走的病毒。你不會改變,也不會去尋求心理治療,而且反正你這種人已經沒藥醫了。你會玩弄心理治療師、心理顧問和假釋委員會於股掌之間,然後溜回我們城市的街道,回頭去獵食我們的孩子。
「我想親手殺了你,但那不是我的作風,我也沒有那個勇氣。也許你會走下人行道被巴士撞死。若是如此,我會很高興捐錢給那位巴土司機當辯護基金,如果司法系統發瘋非讓這個司機得到一些報應不可,那麼應該頒發一枚獎章給他—我也很願意捐錢贊助,而且心甘情願。
「又或者,在你可怕一生中,曾有那麼一瞬間,你願意當個頂天立地的人,為所應為。那麼你可以學習法蘭妮的做法,消除眾人的痛苦。我不認為你有那個膽子,但或許你會鼓起勇氣,或有人會幫助你。因為無論聖伊格內修斯教會的修女們如何教導過我,我就是沒辦法:我非常非常希望見到你頸上繞著繩子,掛在一根樹枝上,在風中,緩緩的,緩緩的旋轉。」
這是麥葛羅的典型作品,這類文章正足以說明為什麼那些小報會出破天荒的價碼挖角他。正如某人所說的,他的專欄正是構成真正紐約的一部分。
多年來,他一直插手別人的工作,而且不無成效。這些年他出了幾本非小說類的書,雖然都不是什麼暢銷書,但都頗受重視。幾年前他在一個本地的有線電視頻道主持脫口秀節目,播了六個月,後來因為跟電視台管理階層不合而喊停。之前不久,他寫過一個劇本,而且曾在百老匯上演過。
但讓他成為紐約不可或缺一部分的,是他的專欄。他用一種通曉清晰的方式宣洩讀者的憤怒和不耐,用字遺詞又比率直的表達藍領憤怒要來得高明。我記得自己讀過他談理查.佛莫的那篇專欄,也記得自己多少同意他的說法。我不怎麼在乎司法制度,不過有幾度,我覺得沒有這個制度好像還比較好。我痛恨看到動用私刑的民眾湧上街頭,不過若他們停在理查.佛莫家的門前,我也不會跑去試圖勸他們離開。
艾卓恩.懷菲德是一顆崛起中的明星。身為一名刑事辯護律師,過去幾年中,他接了許多引起爭議的案件,同時也累積了同等的媒體注意力。光是這個夏天,我就在電視上看過他三次,羅傑.愛樂斯的談話秀,邀他討論陪審團系統的觀念已過時且應予以更新的問題。(他的立場是在民事訴訟可以試驗性實施,但刑事訴訟則否。)然後他上了CNN的賴瑞.金現場扣應節目兩次,第一次是談洛杉磯的明星謀殺案,然後是討論死刑的優點。(他明確反對死刑。)最近的一
次,則是他和雷蒙.古魯留去參加查理.羅斯的節目,嚴肅的談論律師名人話題。「硬漢雷蒙」...
推薦序
序/關於這一版……傅月庵
向一名作家致敬的最好方法是什麼?買本書追隨請他簽名,這不錯。如其因緣湊巧,能為他效勞,編一套書,那更好!
認識卜洛克是一九九七年的事。
那年,初入編輯這一行,工作壓力不大,看書成了最大福利,天經地義。恰巧「推理傳教士」詹宏志加上「臉譜」總編輯唐諾,聯兩手之力把原本冷門的「歐美推理」硬是加溫炒熱了起來,讓向來浸淫「日本推理」,只識「本格派」、「社會派」的台灣讀者,得見世界之奇,滄海之闊,慢慢竟都轉向西顧了。我是其中之一。
於是,《八百萬種死法》甫登陸台灣,便即邀來一晤,一見傾心,驚為天人。此後十多年時間裡,但凡「馬修.史卡德系列」中文新書出版,總要在第一時間購入,無暝無日讀完始休。若說我是那些年「馬修.史卡德現象」(開口閉口:「我今晚只聽不說」、「我一天戒一次」、「大多時候我是容易收買的,但你不能收買我」……)參與製造者,一點不為過。更多時候,家裡所買的卜洛克新書,一如朱天心她家一樣,總是被拿走,總要再補。
甚至讀著讀著,竟把他與王國維等量齊觀了:
「嗚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過,即以生活之苦痛罰之。此即宇宙之永遠的正義也。自犯罪,自加罰,自懺悔,自解脫。」,四月裡,斷斷續續,我一直在重讀卜洛克的馬修.史卡德探案。原因是偶然看到王國維〈紅樓夢評論〉這幾句話,忽然隱約理解一些「生命自持」的線索,因而更想靠近卜洛克,貼近馬修.史卡德。有些書,你不論何時讀,總會讀出一些道理。有些書,時候不到,你很難理解。人間無理可推,無謎可解。我所等待的四月的雨,最終還是沒有落下來,但我還有五月可以等。我一次等一天……。
奇怪的是,儘管日後卜洛克其他系列一一被引入,我也嘗試找來一讀,卻都不甚入港,從「雅賊」到「殺手」,就是有「隔」,進得去,耽溺不了。這事,跟小說行不行關係不大,純然緣分作怪,緣淺還能說什麼?有位朋友,他是「雅賊迷」,愛跟我鬥嘴,老說柏尼.羅登拔如何如何機智迷人,怎樣怎樣淵博難說,「真正愛書人都該喜歡他!」對此,我想了想,總冷冷一句回嗆:「不會老的不是人,角色而已,喜歡個什麼勁兒?」
誠然,「馬修.史卡德」與其他類型小說最大的不同是,馬修肉體會衰老,意志會動搖,道德會踰矩,辦案會潛行由徑,人家給錢他通常都收下,轉個身卻又丟一些到教堂捐獻箱。案件向來不是他的困擾,女人也不是,真正困擾他的,無非紅塵滾滾,該如何照著自己的那一套存活下去,或說存活出來自己的那一套。而幾乎有大半的時間(至少從一九七六到一九八二年,整整六年時間裡,他終於明白且面對「我是酒鬼」這一事實),他都是在跟酒瓶奮戰,To be or not to be?說穿了,馬修既不「冷」也不「硬」,與我們人人都一樣,他心中也有一個哈姆雷特。
至於辦案方式,也奇了,他似乎沒多少小小的灰色腦細胞,也沒有角落或輪椅,鐵拳或好大一把槍。接了案子,他只能不停打電話,不斷上街晃盪詢問,「有時候我們知道一些事情,卻不知道我們知道」、「去他的,東西全在那兒,只是我看的方法不對。」要想知道,要看對,只有一個方法:GOYAKOD,Get Off Your Ass and Knock on Doors,抬起屁股敲門去!天道酬勤,也許就對了。但「其實百分之九十八的調查工作皆毫無意義,你只能把想到的事都做好。你不知道哪件有用。你就像在煤礦堆裡找尋一隻不存在的黑貓,但除此之外我不曉得還能怎麼做。」——這不就是人生嗎?「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人一切的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有什麼益處呢?」幾千年前,傳道者早已論定。你我人等孜孜不倦所打拚之事,有哪幾件不是徒然、枉費的呢?
然而,他還是一旦咬住了就不鬆口,就是要從百分之九十八的徒然裡,找出那百分之二的存在意義。
於是,推理一點不重要,破不破案也不是重點了。有人從馬修身上讀到了堂吉訶德,有人看到了卡拉馬助夫兄弟;有人說他是班雅明筆下「複製時代的抒情詩人」、「步行者」;有人則相信他是推著石頭上山的現代薛西佛斯……。凡此種種,無非說明了一件事:馬修.史卡德像鏡子,人人都可在他身上照見到自己,照見到比敘事更多的其他東西。而這,大約就是「經典」的本質了。
一口咬定「馬修.史卡德系列」已成「經典」,未免說得快了,畢竟最近一本《烈酒一滴》出版於二○一一年,還待時間考驗汰擇;但若說,這套從一九七六年創作迄今,歷時三十多年,前後十七冊的小說,已然具備「推理名人堂」候選資格,相信絕不會有什麼人有意見的。
也因此,當「臉譜出版」期望為此系列再出一個新版本,邀請我參與其事時,我欣然同意。畢竟,人生能有幾次機會為自己所仰慕的作家編一套書呢!?
此次新版修訂作業,大體分為兩部分,內容與裝幀都有許多變動。
內容方面,由於出版時間跨越十多個年頭,執行編輯屢經更迭,譯者多有,許多人名、地名或專有名詞未見統一,前後冊常見扞格,趁此機會一一修訂,讓讀者閱讀時,得以一氣呵成,疑惑不生;譯文方面,盡量保持譯者多元風格,但若確定錯譯、漏譯,經徵詢後,都予修正。甚至連書名,只要有問題,也都盡量求取確定答案。譬如讀者曾質疑,《每個人都死了》(Evebody Dies)中譯書名若為《每個人都會死》,當更精準。為此,我們特別親詢卜洛克,經他回答:「都可以!書名應該保持某種曖昧,讓讀者有更多想像空間。」遂決意維持原名不動。
至於實有發微抉幽之功的「唐諾導讀」,早已成為此系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基本維持不動,僅於涉及時事處,加以註解,方便讀者掌握行文來龍去脈,了解敘事理路;系列編號則按照英文出版,重新依序排列,讓這套書最大特色的「時間感」,得以凸顯。閱讀過程裡,讀者更能感受馬修在時間之河裡奮力泅泳,逐漸老去,終而得以迎向隧道最後那一線光芒的微妙心境轉折。
裝幀設計上,特別邀請著名平面設計工作者楊雅棠擔綱,除了提供一般讀者的「平裝版」之外,更設計一款附有松木書箱,亦得為書架的「珍藏版」,限量五百套,用饗重度發燒友,以便傳家。此版封面,楊雅棠以「一抹紅」表達了這一套書「懸疑、危險、溫暖」本質,簡潔明亮的設計出「很不傳統、很不一樣」的成組推理封面,讓人耳目一新,心湖大大為之一蕩。
相對於此,平裝版封面幾乎每一個都獨立表達一個抽象的詞彙,譬如「背叛」之於《酒店關門之後》,「執念」之於《到墳場的車票》,「情慾」之於《屠宰場之舞》……等等。整體則維持他一貫素雅細緻的風格,並與時俱進,添加更多「現代」元素,希望跳脫窠臼,吸引更多新世代年輕讀者,親近這套「非常不推理的推理經典」。
「馬修.史卡德系列」全套十七冊,數逾五千頁,共二百餘萬言。短短半年不到的時間裡,要完成浩大的「改建重裝」工程,其艱難可知,疏漏必然不免,還望四方讀者不吝予以指教。「校書如掃落葉,旋掃旋生」,編書當亦如是,只能盡力,無從滿意。而這一份「永遠追求更好」之心,實即一名編輯所能奉獻給作家與讀者的最大溫情與敬意了。
〈導讀〉
鑑赏卜洛克
◎唐諾
剃刀太痛,
河流太溼,
氰化物讓人變色
而藥物則引起抽筋;
槍枝不合法,
上吊怕繩子斷掉,
瓦斯味道不佳——
所以你還是活著好了。
——桃樂希.帕克
卡西勒(Ernst Cassier)一直是我個人相當尊敬的一名學者,他過世於一九四五年的美國,但他一九四一年才從瑞典出來,這意思是,和其他不少位歐陸出身的了不起心靈一樣,幸與不幸都在於他們沒辦法一輩子和平安穩的做學問,而是得浸泡在近代史裡最動盪也最令人迷惘的劇烈變動暨殺戮時代,包括兩次世界大戰,包括極左布爾什維克和極右法西斯的可怖人類實驗——人類歷史來到那一代,忽然集體瘋掉了。
這樣經歷之下的學問若還能做得好,通常是最動人的。卡西勒不能算是爆炸力十足的學者,他的動人之處,我個人以為是沉穩、誠實、視野遼濶,但極審慎的把人當人看,是很好的知識分子。
說起「知識分子」這個詞,在近些年來的臺灣總令人百味雜陳,我記得朱天文曾引述過她電影同業吳念真的說法,「哼,知識分子!?」這種問號加驚歎號的命名方式當然有難以言喻的輕蔑成分在,這裡,我們並不打算為臺灣這些東倒西歪,某種程度來說被問號加驚歎號也並不過分的知識分子辯護,但我仍願意為「知識分子」這個詞或這份志業辯護。借用以撒.柏林的典型說法是,我相信,當這個訶變成純粹的髒名詞時,我們的損失遠比想像的要巨大得多,無可彌補得多。
我個人真正最擔心的是,在如此輕蔑而且輕鬆的指責底下,往往有意的隱藏著或無意的滋生著一種退卻、軟弱和愉悅的偷懶。「知識」永遠有著艱難、孤單、不易為世人所知所接受的這一面本質,而且很多時候在我們現行的市場經濟機制之中並不受到鼓勵,因此,它之於個人常常並不合理,毋寧更接近某種信念。但我們得依靠它來抵抗龐大的世俗權勢,以及更龐大的,世俗裡永遠流竄的那些刻板的、虛假的、懶怠的、存在即真理式的三唇墨,當它缺席時,我們便不得不被某種無知無識的民粹所統治。
我們可不可以這麼講,當知識分子並不好時,我們不是去打倒他或取消他,而是用好的知識分子來解決。
什麼是好的知識分子?其實非常多,像說出「只有少數人依然有足夠能力抗拒、打擊刻板印象和真正活生生事物的逝去,而獨立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正屬於這群人。」並認真奉行不懈的米爾斯;或像「道德自由不是事實,而是假設,不是天賦,而是工作,是人給自己的一項最艱鉅的工作,它是一項要求,一個道德命令。」的哲學家康德——非常多,只怕我們不去找尋,不會有尋而不獲這種事。
卡西勒當然也是名單中的一個。
這裡我們好像把話講遠了,也講激動了,我們其實只是想引用卡西勒的一段話,這是出自於他《國家的神話》一書之中,卡西勒在回溯歷史檢查幾千年來國家神話的形成及演變之後,說,「摧毀政治神話,非哲學所能勝任。在某種意義下,神話是無法破壞的,理性的議論無法穿透它,三段論無法駁斥它,但是哲學為我們做了另外的重要工作:它使我們了解我們的對手。」
我以為這樣的結論並不黯然,只是對事實一種堅毅的認知。議論幫助我們思索、說服和揭示,但理性有時而窮,最終一步的「證明」它往往無能為力,它讓可以信的人豐盈,卻不能讓不信的人相信——這不僅僅是面對政治神話而已。
◆Long Time No See
好久不見了,馬修.史卡德先生。
的確是相當一段時日了,距離上一部的《謀殺與創造之時》已整整超過了半年,對為數儘管不夠多但心志極其堅定的史卡德迷而書,這真是有些難受。我所知道的是,在這期間出版社本身接到過相當一些禮貌程度不一、用詞強弱不一的各色詢問,其中最坦白無隱的一份此刻就放我手邊,這是五月七日下午五時四十分傳輸進來的一紙FAX,用紙是TVBS,署名「完全不能接受這種局面的憤怒讀者」,此處一字不易來函照登於此:「為什麼完全停擺了?近半年以上?非常令人不平衡……」
很奇怪的,有時人家對你破口大罵,反而有某種天涯若比鄰的溫暖之感。
為了稍事補償,這裡我們超前一步,先引述一段下一部、也是截至目前為止最新一部史卡德探案《每個人都死了》書中一小段文字,是命案後史卡德瞪視著死去的被害人所看到所想到的:
他向前趴倒,没事的那半邊臉直接壓著桌上攤開的雜誌,血順流他的臉頰而下,最終在雜誌上汪了一小灘,但不是太多,通常,人真死了血也就很快跟著停了,因此,早在殺手奪門而出之前他就死了,甚至更早在那把小槍掉落在地上之前。
他年紀多大了?六十一,還六十二?差不多就這年歲,一名中老年男子,身穿紅馬球衫和卡其長褲,外披敝著拉鍊的黃褐擋風外套。他的頭髮並没掉多少,儘管他把前額這一部分頭髮往後梳,頂上因此顯得稀薄了些許。他早上才刮過鬍子,下巴那裡有輕微的割傷,割傷的地方這會兒並看不到,我是稍早前注意到的,在我進盥洗室之前,他常這樣,刮鬍子時弄傷自己,經常會。
艾克,艾克與麥克中的艾克。
我站在那兒,身旁的人嗡嗡講著話,其中有些話可能還是跟我講的,但什麼也没被我腦子接收進來,我眼睛一直停在那篇家庭式學校文章的某一個句子,但一樣的,我腦子也没將它接收進來。我只是站在那兒,當然,我也聽到了警笛聲音,我曉得警方趕來了。
◆卜洛克比較好
美國NBA一位名球評家會這樣子講過籃球之神麥可.喬丹,「每回我看其他明星球員打球,覺得他們也一樣厲害,一樣好啊,但我把眼光移回喬丹身上,不,沒有這回事,沒人打得比他好,絕對沒有。」
卜洛克比較好,但為什麼比較好呢?
麥可,喬丹比較好,我們當然可以用數字來「說明」他,但他了不起的攻防數字,比之「其他也很厲害的明星球員」,也只是好出一步之遙而已,沒有必然的道理說這有限的差距,正正好是人和神判然二分的界線。他比較好,來自我們長年看球一種難以書喻的整體感受,這真要辯論起來很容易被譏為是某種偏見或甚至神祕主義,但它不是,每個走過八○、九○年代的像回事N B A迷都知道,這種感受是堆積出來的,除了不能證明,它絕對是確實無誤的,我們花過無數夜晚的孤獨不寐時光,貪婪的看了數百數千場球,煉劍一般最終化為一句素樸而且好像不該用數字脂粉污顏色、但卻怎麼也說服不了自家老婆的一句話:他真的比較好。
這我們可暫時稱之為「鑑賞力」。
卜洛克比較好,我們也可以耐著性子試圖說明為什麼(事實上,從《八百萬種死法》出版開始,我們每一次書前不厭其煩的引介文字不都在這樣子做嗎?),比方說,前面那一段史卡德看著死去之人的樸實文字,我們會說,你看它多不像刻板的制式推理文字,而是個完整的人的完整感受:我們會說,你看馬修.史卡德的心思多麼哀傷也多麼溫柔,他是看著一個生命的當下終結,是卡爾維諾所說那種「喪失了所有可能性」的駭然死亡,而不是數學課堂上難解的一道聯立方程式;我們會說,你看卜洛克多認真在努力捕捉那種流動著的、且雪花般稱停就消融無蹤的恍惚感受,他正如同書中的史卡德一樣,努力的凝視著這個當下,拚命不讓喧囂的既存推理現實(整整一百五十年的強大書寫記憶)拉走他的一絲注意力,這次死亡,儘管只是他口中大紐約市八百萬種死亡的其中一次,沒必然特別,但因著死者和你所存在的不可替代關係,存在著之前沒有之後也沒有的特殊聯繫,這次死亡途成為獨特的、唯一的一次死亡;我們會說,你看——
只要在說的同時,我們腦中仍存留著一張不信的臉孔,我們往往會氣急敗壞的繼續說下去,直到我們音量放大、口不擇言到甚至把一個極真的感受講成一個極誇張、極附會、而且愈聽愈假的說法。
只因為我們滿懷好意要別人也相信,我們太認真想通過「證明」來完成不可證明的那最後一步,而那恰好是鑑賞力統治的領域。
◆同類的召喚
我記得小時候學數學時看過一個神奇的證明:證明1+1=2。這是個耗用書本整整兩頁長、極其複雜且不易懂(就小時候我的腦子而言)的證明過程。對老早就相信1加l的確等於2的我個人而言,只是一種被打開視野的新奇感受而已,原來這麼簡單的事我們也可以不當它理所當然,還可以煞有介事再去懷疑它追問它,我並不因此更深信1+1=2終身不渝(這一點我三歲左右就不渝了),它只是成長中眾多引導我看到思維廣濶深邃世界其中一條驚喜且印象深刻的路而已,換句話說,我沒有「被證明」,我的收穫是在別處。
這很像緊接著文藝復興、理性最樂觀最步伐昂揚、笛卡爾、萊布尼茲乃至於洛克他們那個時代,他們認真相信,上帝可以而且會被他們證明存在,而歷史告訴我們,他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他們成功打開了人類理性思維的道路,但不僅沒能取代古老勸人信神的途徑,反而把更多人引到相信人類理性不信神的反向道路去了。
所以我總以為,這種數學式的「證明」,其實終歸還只是演繹。演繹是我們理智一種小心謹慣的漫遊,其中躲藏著某種觸類旁通,躲藏著某種冒險的、會不小心找到新發見的本質,而往往不是封閉在已知世界裡直線前進並最終一定回到你設定的原點,它是航海船或蓬車隊,而不是自家後園子裡丈量你買的土地有幾坪大。
而這個演繹的揭示,與其說是「證明」,毋寧稱之為「召喚」——它不是和仇家對決的好用銳利武器,而是一種有著基本善意基礎的對話,它試圖在廣漠喧嚷的世界中呼喚尋求同類,讓彼此覺得溫暖不孤單,從而較堅定的往下想下去,就像傑克.倫敦《野性的呼喚》裡那隻一步一步走回他自己世界的聰明大狼白克,在阿拉斯加的雪地裡,他聽見了,彷彿叫醒了他生命本能深處的某種悸動,令他血液加速起來,他想跟著那些熟悉的聲音去一看究竟。
◆集義而養氣
但鑑賞力之於我們,不會像白克那麼好命,白克是生命本能的,鑑賞力卻不是內建的,而是後來才灌進去的——就像看球夠久讓我們鑑賞得出喬丹一般,對美好事物的鑑賞,總是來自觀看、經驗、閱讀等等多元的材料吸收過程,並經過我們有意識的思考整理和無意識的自然發酵,從而得到的一種不進則退的判斷力、理解力和感受力,它的確也有著「流汗辛苦的人必歡呼收割」的艱難一面。
理解它的來之不易,它建立的艱難,我們是不是也該珍惜它、守護它並再滋養它,而不是因為它某種程度的無用(說服不了不信的人)而棄如敝屣?
孟子當年夸夸其言的說「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其實是有意思的話,他說這話同時其實是謹慎的,因為他深知這個所謂的浩然之氣可長也可消,而他的解答是「集義養氣」——白話翻譯是持續做對的事、做好的事情,才能讓它沛然不衰退。閱讀鑑賞力的維持也是這樣,你得持續看好的書並不厭其煩去細膩的分辨它,如時時磨利寶劍的鋒刃一般,否則它仍會不知不覺離你而去,就像我們的眼看臺灣有多少創作者多少讀書人,沒兩年下來,不僅再沒創造力,就連簡單的好壞良窳也再認不出來。
如此,我想我們就部分解答了一個始終存在的問題了:閱讀消遺用的推理類型小說,難道不可以是一種休息?何苦要如此時時勤砥礪到小題大作的地步呢?
我不反對休息(儘管我所理解心智的休息其實並不像肉體疲憊後的休息,它不是一種關閉式的不思不想,方式更接近飲食滋養而不是睡眠不動,因此看好的書、聽好的音樂、想好的事其實是心智的最好休息方式),更不反對只取一瓢飲的只滿足於某種聰明的設計與橋段云云,但在此同時,我更相信的是,當更好的東西出現時,你的鑑賞力不待你辛苦發動自然會起著作用,它不僅不會妨礙你的休息,反而會在比方說你清楚感受到卜洛克和艾勒里.昆恩是如此不同的情況下,有著更多的滿足和幸福之感。
這不就是我們從看《八百萬種死法》以來一直就有的感受嗎?
序/關於這一版……傅月庵
向一名作家致敬的最好方法是什麼?買本書追隨請他簽名,這不錯。如其因緣湊巧,能為他效勞,編一套書,那更好!
認識卜洛克是一九九七年的事。
那年,初入編輯這一行,工作壓力不大,看書成了最大福利,天經地義。恰巧「推理傳教士」詹宏志加上「臉譜」總編輯唐諾,聯兩手之力把原本冷門的「歐美推理」硬是加溫炒熱了起來,讓向來浸淫「日本推理」,只識「本格派」、「社會派」的台灣讀者,得見世界之奇,滄海之闊,慢慢竟都轉向西顧了。我是其中之一。
於是,《八百萬種死法》甫登...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