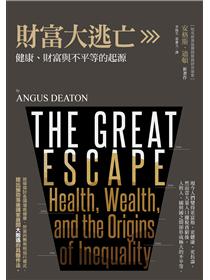一段異國之戀,甜蜜的愛情、幸福的婚姻,卻因丹麥籍丈夫罹患了ALS絕症——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妻子照顧、陪伴丈夫走完人生最後的一段旅程。有關失落、有關命運、有關勇氣的故事——面對殘酷的病痛及死亡的勇氣。
本書深刻描繪「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LS,俗稱漸凍人症)的猙獰面目,但作者描寫的僅是其所經歷的一面。罹患此病之人,病情發展皆不同,各有其恐怖的獨特處。作者相信這個被神祕黑幕遮掩的病症一定會許多不同的可怕面目;同時穿插了一些第六感的玄虛離奇情節。
作者藉由本書,欲激起世人對此病症的注意,並期望將來醫學界能揭開這怪異病症的神祕黑幕,讓世人知道,如此稀有、殘酷的絕症從何而來?讓世人明白,它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讓世人曉得,怎麼去對抗它?……
作者簡介:
池元蓮(Elsa Chi Karlsmark)
籍貫廣東,生於香港。台灣大學外文系學士,德國政府獎學金留學慕尼黑研讀德國文學,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碩士。與丹麥人結婚,長居丹麥。能說流利的國語、廣東話、英語、丹麥語及德語。
先從事英文寫作,一九九○年代回歸華文寫作,出版有《歐洲另類風情——北歐五國》、《北歐繽紛》、《兩性風暴》、《性革命的新浪潮——北歐性現狀記實》等中、英文著作十餘種。
基於其文學創作的成就,被《華人世界》與其他十幾位美歐華裔女科學家、作家、運動家、影視界名人(包括鞏俐和章子怡)等一起遴選為「文化先鋒」。
章節試閱
海上的邂逅
我曾有過一個很好的丹麥丈夫。他的名字叫做奧維•嘉士麥(Ove Karlsmark)。
因為他,我才會來到北歐丹麥這個被海洋環繞著的小國,一個國泰民安的國度,一個富有童話色彩的地方,也就是美人魚與安徒生的故鄉。奧維與我在這片有點像遠離世界的土地上悉心地耕耘出一個美好的中西婚姻花園。一眨眼,四十年的光陰過去了。
但,在婚姻的最後幾年,我們的花園被連根拔起地毀滅了。毀滅這個花園的是世界上最稀奇、最殘忍、最恐怖的病魔。全世界的醫生都不知道此病從哪裡來,也不知道怎樣去醫治它。
猙獰的病魔像北歐海洋的大漩渦那樣把奧維捲入病痛的旋流,我也跟著投入漩渦,想方設法要把他拉回來。可是,在漩渦裡,我們僅是兩顆渺小的豆子,被猛烈無比的旋流帶著往下轉,翻翻滾滾地落到漩渦的漆黑深底,然後又被旋流翻翻滾滾地往上旋轉回去。當漩渦把我們拋擲回陸地的時候,奧維失去了生命,我卻摔了一跤終於倖免於難。
在漩渦的深底,我面對面地見到命運。我以前拒絕承認它的存在;現在我從死亡裡回來,不但承認它的存在,而且完全接納它的取與給。當年,命運讓奧維與我在海上的一艘義大利郵輪上邂逅,多年後又讓我們在海上道永別。奧維與我的異族婚姻是一個命運的故事。命運要我做生還者,猜想是要我把這故事寫出來。
這個命運的故事是從海開始的。
一九六四年,奧維和我只不過二十出頭。那年夏天,命運彷彿在冥冥中引領著他和我,從不同的地方向義大利奔去,讓我們在那裡相遇。那時,奧維剛完成了他在哥本哈根大學的企業管理學業,從哥本哈根坐火車南下,準備到義大利的熱那亞(Genova)乘郵輪到印度去度假;她的姐姐嫁了一個經營咖啡種植園的印度人,住在印度南部。我自己則剛結束了在德國慕尼黑的留學生涯,從慕尼黑乘火車到熱那亞,將搭乘郵輪回香港與我的父母親重聚。
一九六○年代是義大利遠洋郵輪的黃金時代。當年的義大利郵輪公司 Lloyd Triestino 擁有七艘華貴的郵輪,分別航行到澳洲、美洲和亞洲。定期往返於歐洲和亞洲之間的有兩艘:「亞洲(Asia)」和「維多利亞(Victoria)」。郵輪從位於義大利北部的熱那亞港開航,經那不勒斯(Napoli)、埃及、葉門、巴基斯坦、印度、新加坡,以香港為終點站,全程為時一個月。
那年,奧維和我乘坐的是「亞洲」郵輪。
「亞洲」並不是一個龐然大物。她身長五百二十英尺,體重十一•六九三噸,線條優美,全身雪白,可載客五百人。在汪洋大海上,她好像一條輕盈的美人魚,飄逸地破浪前進。那個時代的義大利遠洋郵輪具有一種悠閒的羅曼蒂克氣氛;而今日載客數千、娛樂設備過剩的豪華大郵輪上,這種氣氛已不再存在。
開船後的第二天,郵輪到達義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港,船客們紛紛下船到岸上去參觀那曾被維蘇威火山灰埋沒了千多年的龐貝(Pompeii)古城遺跡。我一登上遊覽車,立刻在車門旁的第一排椅子上坐下來,拐頭一看,旁邊的位子坐著一個年輕男士,正向我微笑著。我對他的第一個印象:「這個男的很斯文,衣服穿得講究。」這位男士就是奧維。
在遊覽車上,我們很自然地交談起來。事後,奧維告訴我,當船在熱那亞開航的時候,他在甲板上故意站到我的後面,很想跟我說話,但我沒注意到他。看到我上遊覽車的那一剎那,他的心怦怦地跳著:「希望她會坐到我的身旁!」
……
兩個星期之後,船停孟買港(Bombay),是奧維和我分手的地方。他的姐夫已經在那裡等著接人。那次分別,我們沒有灑眼淚,只道再見,答應互通音信。「亞洲」郵輪再度朝大海駛去,站在岸上不斷揮手的奧維在我的眼中逐漸變小,終於完全消失在地平線上。
船上羅曼史很美是一回事,但卻是很脆弱的愛情,往往宛如一個七彩的泡沫,在空氣中飄飄然的時候很美,一旦落到現實的陸地上便化為零。當年「亞洲」船上幾對情侶的結局如何,我沒法得知。但,奇妙的是奧維與我的一段海上羅曼史竟然落地生根了。
孟買分手後,我倆各奔前程。奧維在印度假期結束返回丹麥,繼續進修企業管理碩士。不久,我提著一個皮箱,從香港飛到美國加州,進入柏克萊校園去修碩士學位。
奧維和我雖然已經遠隔重洋,但我們沒有忘記彼此,有恆地通信,每年相約在世界某一角落相會一次。命運像放風箏那樣,讓奧維和我各自飛著,它在遠方拉著愛的繩索。等到一定的時間,命運便把它手中的繩索收緊,把奧維和我這兩只風箏又拉回到同一個地方。
經過五年的考驗,我終於認為奧維是最適合做我丈夫的男人。於是,一九六九年的一個寒冬日,我從美國來到當時冰天雪地的丹麥,在聳立冰海旁的古堡裡面與奧維結成夫妻,開始共同的婚姻生活。
中西文化結合
當年,我決定在丹麥與奧維結婚,母親不贊成,父親則完全贊同。他們兩人的贊成和不贊成都是從文化的觀點出發。
我的母親在生活習慣、語言、思想各方面都是典型的中國化。她不吃洋餐,不講外國話,最怕跟外國人打交道。她從自己的文化角度來瞻望女兒在丹麥的前途:好恐怖!朝夕與外國人相處同居,終年活在陌生的習俗中,天天吃味道稀奇古怪的洋食!那樣的婚姻怎麼會長久!
我的父親曾在德國和奧地利留學八年,都是住在外國人的家裡。而且,他曾有一個漂亮的維也納女朋友,兩人相戀兩年。父親回國後向他的父親表示,他有意娶那個奧地利女子為妻,受到極大的反對。八年後,父親重返歐洲旅遊,途經維也納,還特別到往昔戀人的故居去叩門,女友的母親尚住在那裡,但愛人已嫁,隨夫遷往捷克。次年,父親便與母親結婚。由於他自己年輕時代的經驗,父親絕對不反對我跟外國人結婚。而且,父親瞭解我的性格,知道他的這個女兒適合在外國生活。
在丹麥結婚的時候,我清楚意識到與奧維的結合也是一種文化結合,而且有了做文化適應的心理準備,因為是我自願到丹麥生活,而不是奧維遷到中國去過活。
對我來說,文化的結合有實際性和精神性的兩大重點。實際性是日常的吃食習慣;精神性是思想的交融。
我到丹麥的時候,對西洋飲食已經不是個陌生人。我從小在家裡便有吃外國乾乳酪、喝咖啡、吃烤麵包等的習慣。在香港的時候,父親常帶我們小孩子到西式餐館去吃西餐。後來,我自己在德國和美國念書,住的是國際學生宿舍,如同旅館,一天三頓都吃洋餐。但,在丹麥結婚後,是我人生第一次進廚房燒菜。幸運的是,我有一位很會做菜的公公。於是,我跟他學做丹麥菜,在家裡也一直以吃丹麥菜為主。
丹麥人的飲食傳統跟德國人相似,一天兩頓的主食:一頓冷的,一頓熱的;但次序倒過來。德國人的傳統是中午吃一頓豐富的熱餐,晚餐則簡簡單單的吃黑麵包、乳酪、冷香腸等。當年我在德國時,總認為晚上那樣吃是跟肚子過不去,冬天寒夜更有飢寒交迫的難受感。所以,我很高興,丹麥人習慣中午吃冷的開口三明治(Smørrebrød),晚上吃熱餐。
開口三明治是丹麥人的名菜,與英國人、美國人的三明治迥然不同。原則是在一片黑麵包的上面放肉、香腸、魚、蝦等肉品,然後按肉類的不同加上不同的配菜,上面不再放麵包片,故有「開口」之稱,吃的時候使用刀叉。講究起來,開口三明治是一門相當複雜的藝術烹飪,有過百種不同的配合款式和規矩。黑麵包是由裸麥做成,口感比白麵包硬,帶酸味。丹麥人吃這種黑麵包已經有一千年的歷史;他們從小至大每天都吃黑麵包,離家遠行,最想念的家鄉菜也就是它。
丹麥人是一個吃豬肉的民族,日常的菜餚大都以豬肉為主料,做法各式各樣,搭配著馬鈴薯來吃(有的丹麥人是連米飯都吃不來的)。丹麥菜最優美的一點是,每頓的主菜餚必有一盤濃度適中、味道精美的熱肉汁。肉汁由肉的原汁加上奶油、麵粉、調味品、配色料等慢火煮成,淋在肉上。
丹麥人的傳統是,聖誕節吃烤豬肉(flæskesteg)或烤鴨,除夕吃鱈魚。
若要我選一個最值得一試的丹麥菜,我會選烤豬肉。這個丹麥菜餚,我也擔保,中國人會喜歡吃。它的做法其實也滿簡單。烤豬肉的原肉在丹麥的超級市場都可以買得到,原裝包好,每包的重量約為一公斤。肉是豬里肌,帶著豬皮。皮上已預先割好了一條、一條的裂紋。祕訣是:整塊豬肉皮朝上肉在下放在水裡,水只蓋住皮,水裡放數顆甜的黑棗(準備做肉汁之用),在烤爐中烤二十分鐘,拿出來在煮軟了的豬皮上抹上粗鹽,放回烤爐裡繼續烤,一個半鐘頭之後,豬皮會鬆爆起來,呈金黃色,質鬆脆。此時,肉已烤好,取出靜置二十分鐘便可切片進食。配菜是味甜的紅捲心菜。如果把已經煮熟的馬鈴薯用糖與黃油再煎一下,更好吃。當然,一盤熱的肉汁是不可或缺的。
奧維和我也吃中國菜,大約每星期一次。我的丹麥菜做得不錯,中國菜則平平;可是,奧維偏愛吃我做的變相中國菜。
奧維跟著我第一次返港探親,多次被邀請到大酒樓去吃酒席菜。十幾道菜分開上,一道吃幾口。事後,奧維坦白地對我說:「這樣的菜我吃不來,光是肉,味道濃,沒有飯,沒有汁!還是妳做的中國菜好吃。」
我笑著答:「中國人才不會喜歡吃我的中國菜。」
我曾嘗試用麻油、蠔油、五香等調味品做菜給奧維吃,他都不喜歡。可是,他卻跟我學會了吃辣椒,越辣越好。我們在家裡吃中國菜必有辣椒醬作陪。
丹麥人素來喜歡在家裡請客,認為那才意義隆重。新婚時期我遵守這傳統,被別人請過了,便在家裡自己做中國菜回敬。但我只做咕嚕肉、炒飯、青椒炒雞丁這幾道菜,再預先到附近的中國餐館去買些春捲回來助陣。這幾道簡單的菜最適合丹麥人的口味,所以很討好。我竟然在奧維的朋友圈子裡面得了「好廚子」的名聲。
後來,我偶然發現,在一個湖邊開了一家很特別的中國餐館。它的室內布置別開生面,帶有法國氣氛,牆壁上掛的均是抽象派的西洋油畫。我非常欣賞這家中國餐館。從此以後,請客都到那裡去,預先跟老闆訂好菜單,準備好優美的葡萄酒,但中餐西吃,使用長方型桌子,擺放洋餐具,不用碗筷。
……
病魔悄悄來了
一切從二○○六年的夏天開始。奇怪的病魔悄悄地踏入我們的平靜生活。
北歐的夏夜特別長,到了子夜天空仍然澄清明亮,宛如透明的瓷器。北歐的黃昏更是金光絢麗。
那個夏日的黃昏,奧維和我坐在屋子二樓後面的陽台上吃晚餐。晚霞在天際嬌嬈多色、變幻無窮;屋外濃蔭的大樹、後花園裡盛開的野玫瑰、遠處迤邐的海水都安祥地沐浴在嫵媚的夕陽下,散發著享受生命的喜悅氣象。
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晚餐吃的是奧維最喜愛的肉食—煎牛排。我們兩人都不是燒菜能手,做晚餐大都是兩人合作,各盡所能。牛排是奧維煎的,煎得生熟恰到好處;烤馬鈴薯和生菜沙拉是我做的。丹麥人習慣把現成的沙拉醬倒在菜蔬上,硬生生的吃;奧維向來不吃這種沙拉,我是能吃但不熱愛。於是,我打破西方成規,別出心裁,自創把沙拉中的各種菜蔬先用糖、醋、油、鹽等配料拌起來,約等十五分鐘,讓菜蔬稍微變軟和入味後才吃。想不到,奧維對我這有點像中西合併的特製生菜沙拉情有獨鍾,愛吃萬分。
吃著、吃著,我忽然聽到「咕咚」一聲,從桌子對面傳過來。我吃驚地抬頭凝視對坐的奧維。
「咕咚!」奧維剛吞了一口肉。聲音果然是從他那裡來的。
「你的喉嚨為什麼會發出這樣奇怪的聲音?」我問。
「哦!哦!」他微笑地看著我,一臉不好意思的表情,猶疑了一陣子,終於把問題說出來:「我吞東西有困難。」
「不能吞東西是很嚴重的事情!」我緊張起來。腦子裡立刻閃了一下紅燈:哦,可能是喉嚨生癌!「你要趕快去看醫生呀!」
結婚數十年以來,奧維很少病痛,就是有病痛,他也不訴苦,把兩道嘴唇閉緊,照樣做事情,不願意我看到他生病。我相信,他這次的喉嚨問題一定已經蘊釀了一段時間,只是他盡量避免被我發現而已。
到了醫生那裡,醫生的第一個懷疑當然是癌症。
奧維告訴我:「翰莫醫生用了好長的時間摸我的頸子。他說沒摸到什麼。現在他替我約好時間,去食道和胃的專科醫生那裡做檢查。」
……
奧維檢查食道和胃的那一天到了。我和他手牽手走路前往,那個地方就在我們常去的郵局後面,離家只不過三、五分鐘的步行路程,開車子反而麻煩。
奧維自己走進檢驗室,約二十分鐘後女護士扶著他出來,原來梳得整整齊齊的頭髮蓬亂了,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在人前蓬頭亂髮而不自知,但看來他是神志完全清醒。
「我們可以走路回家嗎?」我問那位跟著出來的醫生。「我們住得離這裡很近。」
「不行、不行!」醫生回答:「你們坐車子回去。回家後讓他在床上睡一個鐘頭。」
回家後,我把他帶到床邊,說:「醫生吩咐你要睡一個鐘頭。」他一躺下便睡覺了。我不打擾他,靜靜地在家裡做別的事情。
一個鐘頭之後,奧維忽然站在我的跟前,莫名奇妙地問:「發生了什麼事情?為什麼我會躺在床上睡覺?」
「你自己還不知道!」我笑著跟他做報告:「我們坐計程車回家的時候,你在車上還跟司機談了一下今天的天氣。下車的時候,計程車司機好有心,把你一直扶到大門前。樓梯是你自己上的。睡覺前,你還自己先把夾克、褲子脫了,摺疊好才躺上床去。」
奧維對這一切完全沒有記憶。他說,醫生替他插管進喉嚨前,給他打了一針,還半開玩笑地說:「你放心!打了這一針,你什麼都不會感覺到。唯一的危險是,你可能會把你內心深處的祕密說出來。」
過了幾天,我們回到翰莫醫生那裡聽取檢驗結果。
不是癌症!喉嚨、食道和胃都正常,奧維的吞食困難很可能是一種肌肉病症的開端,要到醫院去做肌肉檢驗。
聽了翰莫醫生的宣布,我們四目相投,多日來的緊張心情稍微鬆懈了。我心裡頓時感到一陣安慰:「奧維還可以活很多年!」
回家後,奧維對我說:「為什麼總是我到醫生處做檢查?妳也應該到翰莫那裡檢查一下妳的血壓。」
「哈,我的身體好得很!」我頗為自負的回答:「我唯一的毛病是敏感症,但我的敏感可以用藥來控制。那種藥在藥房隨時買得到,連醫生處方都不需要。」
「唉,說起妳的敏感!」奧維的眼睛笑著,幽默來了:「如果妳是一頭豬的話,妳早就給宰掉了!」
「不對!不對!」我也模仿丹麥幽默的形式來個自我誇讚:「如果安徒生再世的話,他可要把我用來做模特兒,重寫『豌豆公主』的故事。你看,我對香菸、灰塵、香水、蚊子叮、跳蚤咬樣樣都敏感,那不是比『豌豆公主』的敏感棒多了嗎?」
「還有,」奧維加一句:「你對你的丈夫也敏感!」
可見,我們當時的心境並不壞,還有開玩笑的心情。
奧維首先到我們本城的奧本羅醫院去做過兩次肌肉檢查,沒有結果。於是,翰莫醫生又寫信到松德堡(Sønderborg)醫院的腦科部,叫奧維到那裡去繼續做檢查。奧本羅城的人口連兩萬都不到,城市醫院沒有腦科部。松德堡城算是個大城,跟我們所住的奧本羅城有三十分鐘的車程距離,該城的醫院是丹麥南部設備最完善的大醫院,設有腦科部。
這期間,奧維的吃食狀態有了顯著的改變。他本來很注意餐桌禮貌,但現在,我發覺他用餐時總是把頭仰起來,兩眼朝著天花板,慢慢地吃。
「你為什麼那麼奇怪,仰著頭吃東西?」我忍不住問他。
「醫生跟我解釋,正常人是把食物從食道吞下去,」他詳細地說:「我的食道肌肉不能再做吞食的動作,我只好仰起頭來,讓食物流下去。食物流下去之前,我要把食物咬得很爛,流下去的時候,我要集中精神。一不小心,食物就會流到氣管去,那可恐怖!」
那個夏天,一切恐怖的開始;只是我們還沒洞悉真情,滿懷信心地祈望,醫生終會找出奧維的病因,對症下藥。等奧維的病醫好以後,我們可以依照原來的計畫,過我們的退休生涯。這一年奧維六十四歲。
海上的邂逅
我曾有過一個很好的丹麥丈夫。他的名字叫做奧維•嘉士麥(Ove Karlsmark)。
因為他,我才會來到北歐丹麥這個被海洋環繞著的小國,一個國泰民安的國度,一個富有童話色彩的地方,也就是美人魚與安徒生的故鄉。奧維與我在這片有點像遠離世界的土地上悉心地耕耘出一個美好的中西婚姻花園。一眨眼,四十年的光陰過去了。
但,在婚姻的最後幾年,我們的花園被連根拔起地毀滅了。毀滅這個花園的是世界上最稀奇、最殘忍、最恐怖的病魔。全世界的醫生都不知道此病從哪裡來,也不知道怎樣去醫治它。
猙獰的病魔像北歐海洋的大漩渦那樣把...
目錄
海上的邂逅
奧維的家鄉
奧維這個人
最早西化的家庭
對我最有影響力的人
做飛鳥的願望
中西文化結合
反映婚姻的搬家史
家住灰色兄弟廣場
西班牙月夜的啟示
聖喬治湖畔的融入與回歸
與美人魚做鄰居
為了旅遊南遷
病魔悄悄來了
等待
丹麥的醫療制度
第六感的警告
最後的審判
對死亡的看法
安樂死在丹麥不合法
非搬家不可
雪中送炭的新居
最後一次搬家
家裡變成一間醫院
在順境、在逆境
成功的婚姻是個花園
冤魂附身
向信仰治療師求助
信仰治療師培訓學校
不人道的痛苦
半夜的電話鈴聲
遺憾與安慰
最後的願望
誰把我推下樓梯?
他真的回來看我
等待、等待、再等待
隨海而去
後記
海上的邂逅
奧維的家鄉
奧維這個人
最早西化的家庭
對我最有影響力的人
做飛鳥的願望
中西文化結合
反映婚姻的搬家史
家住灰色兄弟廣場
西班牙月夜的啟示
聖喬治湖畔的融入與回歸
與美人魚做鄰居
為了旅遊南遷
病魔悄悄來了
等待
丹麥的醫療制度
第六感的警告
最後的審判
對死亡的看法
安樂死在丹麥不合法
非搬家不可
雪中送炭的新居
最後一次搬家
家裡變成一間醫院
在順境、在逆境
成功的婚姻是個花園
冤魂附身
向信仰治療師求助
信仰治療師培訓學校
不人道的痛苦
半夜的電話鈴聲
遺憾與安慰
最後的願望
誰把我推下樓梯?
他...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5收藏
5收藏

 1二手徵求有驚喜
1二手徵求有驚喜



 5收藏
5收藏

 1二手徵求有驚喜
1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