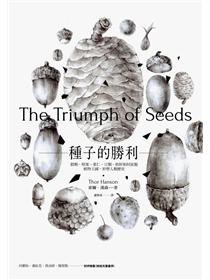現實是有縫隙的,虛構可以再生,過往與未來共舞。陳又津倒身進入記憶廢墟,撿拾無用垃圾,逆光剪影,恣意拼貼,無常也不過如常。令人期待的新二代溯源書寫,已然越過堤防,漫溢肆流。——顧玉玲
十九歲那年,父親過世了。認識父親的時候,他已經是個老人。
是退守到台灣的老榮民,是做餅人,同時也是收藏破爛的拾荒者。
如果要我的母親有什麼夢想,就是給我們家後面的空地砌上一圈水泥拿來種花、買一台新的冰箱、找一個工時不太長的工作、明天洗床單的時候不要下雨……
我在書桌前,一步一步,像父親推著腳踏車那樣收集紙箱和鐵罐,
敲擊鍵盤記錄我們曾有的回憶,打撈父母那一代準台北人的故事……
新銳小說家陳又津,繼《少女忽必烈》之後,一洗華麗文風,以抒情之筆寫一段最深層的記憶,照亮少話的退伍老兵、買單程機票的南洋女子、誤會自己是混血兒的移民小孩,贖回人世的恬淡與寬諒。
★文末收錄多篇書寫二代移民的故事:
「我對她完全一無所知。她的本名,從哪裡來,過去怎麼樣都不知道。」——趙素芬,河南榮民爸爸╳泰國媽媽
「不能怪外勞沒有敞開心胸,因為我們的媽媽還真的欺負他們!」——初傑克,山東榮民爸爸╳印尼華僑媽媽
「浮現我媽的樣子,她本來是個對自己很有自信,把生活過得很好的女性,可是她沒有經營出她想要的關係與婚姻。但她應該像我同學那麼開心。」——廖宜盈,台灣客家爸爸╳越南華僑媽媽
「我爸在泰國曼谷長大,來台灣以後認識媽媽。我自己從來沒問過他們怎麼認識、結婚,多半是聽長輩講的。」——鄒駿濠,泰國華僑爸爸╳台灣媽媽
作者簡介:
陳又津
1986年出生於台北三重,專職寫作。台灣大學戲劇學研究所劇本創作組碩士。27歲時以風格鮮明的《少女忽必烈》登上《印刻文學生活誌》封面人物。美國佛蒙特藝術中心駐村作家。
2010年起,陸續獲得角川華文輕小說決選入圍(《寂之聲》)、香港青年文學獎小說組冠軍(〈長假〉)、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劇本佳作(《甜蜜的房間》)、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跨界通訊〉)、文化部藝術新秀創作發表補助、國家藝術基金會長篇小說補助。入選《九歌103年度小說選》。
BLog∣少女忽必烈
Email∣hubilieh@gmail.com
章節試閱
長假
十九歲那年,父親過世了。
我認識父親的時候,他已經是個老人了。
高血壓、重聽、頭髮稀疏、吐痰的時候發出很大的聲音、上完廁所不沖水、假牙泡在漱口杯裡、每天用一些來路不明的藥酒擦腳……父親身上常常發出一種混合了紅花油、髮油和藥酒的氣味。這十九年間,他多次進出病房又安然歸來,正以為他會一直頑強地繼續下去,沒想到這次他真的離開了。
那年夏天,他放了一個長長的暑假。因為他碰上了農曆七月,後面又是閏七月,天天都有他生前捨不得開的冷氣可吹。──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長的假期。
父親又生病了。
這次不是痛風、不是車禍,他倒在自己的床下。
一早看到他頭下腳上的姿勢有點不太對勁,連話都說不出來,母親叫我打電話叫救護車,因為我的國語對方比較能夠聽懂。之前有過叫車的經驗,知道不能急,他會一個一個問你問題,這樣才是最快的方式。不要哭訴你受到怎樣的驚嚇,把話講清楚,最重要的是地址,你現在人在哪裡,否則車子無法開來。
救護人員說,這是中風。
當父親從加護病房被推進開刀房,醫生跟我說:「情況很危急,因為病患年紀大了,要裝心導管有一定的風險,需要直系親屬簽署手術同意書。」
這不是平常在電視劇聽到的台詞嗎,竟然從醫師口中一字不差聽到,有點奇妙的感覺。我很認真地看切結書,雖然每個字都懂,但實際能做到的只有檢查錯字的程度,總不能讓醫師這樣站著一直等我吧,但也不能簽太快,那樣好像有點隨便。然後我把簽好的同意書交給護士。同時瞭解一些本來就知道的事:
父親在這世上的直系親屬,除了我之外沒有別人。
在這塊土地之上,我們這個家族尚且沒有親人埋在這裡。
不知不覺之間,父親已經七十二歲了。
母親和我坐在外面等,醫院很安靜,開刀的時間不知道是怎麼過去的,但我只記得加護病房很專業,就算在醫院混了這麼久,我還是第一次看到床頭有這麼多儀器,它們發出的聲音像協奏曲此起彼落。
裝好了心臟導管,父親很快地從加護病房轉到普通病房,辦理出院手續。
父親以驚人的速度恢復健康,他開始走路,握筆寫出來的字跡讓人看不出來他曾經是中風的人。他繼續從街口撿垃圾回家,但身邊沒有野狗的身影。他回到家裡,一樣很少對這個世界發表意見或抱怨,只是多了一些時間看電視。他早起看華視的平劇,皮黃腔拉長的音調也許可以讓他回到以前的時代。
我們好不容易趁他住院丟掉的垃圾,又漸漸地多了起來。
這老人終究還是垮了。
他第二次中風送進醫院,急診室、加護病房、開刀房、普通病房,當病房也不能繼續住下去了,我們只好把父親移往安養院。
這次父親再也搬不動任何垃圾,甚至也無法舉起他自己的手。
他住進一個沒有窗戶的房間,室內瀰漫著食糜的甜膩氣味,他躺在跟別人一樣的鐵床上,跟別人理了一樣的平頭。
這時候,我才第一次看見父親的白髮,
雖然我認識父親時他已經是個老人,但沒想到他還可以更老。
他的頭髮由灰色褪至銀白,在父親病倒以前,我從來沒看過他的白髮,因為他總是在浴室裡擺上染髮劑和細細的尺梳,對著鏡子,一點一點,把髮根染黑。出門以前,還要用髮油抹上稀疏的頭髮,維持旁分的造型。
現在打開廁所,髮油那種刺鼻的氣味不見了,
沒人會替他染黑頭髮,家裡還剩好幾罐沒開過的紅花油。
這樣一個在意儀容的男人,靜靜躺在安養院的床上
每次見他,他都問現在幾點了,好像這是一個固定的問候,比吃飯還重要。
「現在幾點了?」
「六點。」
「是早上還是晚上?」
「晚上。」
母親把這個回答的機會給我,讓我跟他說兩句話也好。
雖然他床頭擺著一個從家裡帶來的時鐘,就跟我們以前住院的時候一樣。
但他似乎連放在他床頭的時鐘都無法轉頭看見了。──那是安養院裡面唯一一個屬於他的東西。他的西裝、領帶都不能帶來,也都用不上了。假牙放在床頭,但每天從喉嚨灌食沒有戴假牙的必要,不知道哪天開始連他的假牙都消失了。當然他撿的那些家具雜物都不能帶來,有空的時候我們就一天丟一點,一天丟一點。
父親和來看他的人關於時間的對話通常到此為止。
這時他會微微轉頭,看向白色的牆壁。
表示談話已經結束。
然後我就回家。
但他如果繼續說話,老實說我也聽不太懂。
話語從那凹陷的嘴,咿咿嗚嗚,我必須透過母親的翻譯,才能知道他在問些什麼。某次他問了一個從未問過的問題,我不懂,母親也不懂,我們猜了很久,結果是──「讀書讀得好不好?」
好,當然好,好得不能再好。更具體地說是PR99的好,但父親可能不懂,就是一百人取一人的意思。
後來他終於搞清楚我考上大學,不知道母親是怎麼跟他溝通,他竟然下了一個勞師動眾的決定──要去郵局領錢給我,他要親手簽下提款單,當然是我填數字他簽名,因為他的手一直抖,沒辦法把數字填進格子裡面。
早知道應該留下那張提款單不去領錢才對。
後來他又問了同樣的問題,他大概忘了我已經考上大學,我說很好。
這時候他連瞳孔都變成銀色的了。
我看見眼前這個枯瘦的老人,一路從老家福建退守到三和夜市,從店鋪退守到家裡,最後撤退進自己的身體。
他從來不說自己吃過什麼苦,也沒有告訴他的孩子關於他的故事,他的父母、他的兄弟,還有他怎麼學會做餅。
父親的緘默使我無法想像他的身世,重建他所參與的戰役、硝煙的氣息,還有他身為一個人的處境。我能做的僅僅是,像母親說的「就看看人家怎麼寫吧」,在更廣大的歷史之中定位父親所在的座標。
無論這樣的測量有多麼浮動不穩定,而且常常是錯誤的。至少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他必然和他同時代的人一樣,有著平凡的願望,希望戰爭結束、平安回家,還有成家立業。
只是當他想到要成為一個父親時,比其他人晚了二三十年。
第一次的婚姻,被大時代沖散。第二次婚姻,他無法跨越族群或教養的隔閡。第三次婚姻,他終於有了一個孩子。如此一來,他的人生才不算是繳了白卷。
「家」對父親而言,很可能是複數的概念。一個是新的,一個是舊的。一個是現代性的核心家庭,另一個是農村社會的古老家族。當他離開田地,踏上甲板的那一瞬間,他所呼吸到的,很可能是王朝崩解之後,前所未有的自由空氣。
從此,他不曾再拿起鋤頭和鐮刀,在海上展開全新的生活。
那時他才二十一歲,對未來充滿希望,他必須比那些在舊大陸已掌握權勢的人更快找到自己在現實的位置。父親毫不留戀,獨立於眷村和國宅之外,和建設公司交涉,絕口不提自己的過去,重新開始。
這個穿上西裝的賭徒,在青年時代就贏得了一間自己的房子。
也許他還太過年輕,不願意像其他比較老的人那樣承認對現實失望,他相信自己絕對不會跟他們一樣。就算他失望了,他也輕描淡寫。
他一直都是那個不服輸的少年,因為他的青春從二十一歲才開始,自此不曾改變。即使中風多年,他都不曾講過想死,儘管他的求生意志正在黯淡,他就像他這幾十年做的一樣,不說。
不說是他唯一的抵抗。
硬漢從不說自己的事,硬漢的孩子也都懂得不問的溫柔。
等我要拔管的時候,那管子和針尖輕易地像是從液體中拿出來,他沒有留下任何一句話,可是他已經盡責維持心臟的跳動,因為他的胸口都是燒焦的痕跡。
他沒有留下任何一句話。
不痛、不怕,心無罣礙,無所恐怖。
禮儀師替他蓋上金黃色的誦經被,打開袖珍型唸佛機,經文不斷地從揚聲器流淌而出,不知道是誰推著父親的床頭,忽然間整個加護病房動了起來,只要是病床所到之處,全都刷─刷─刷刷拉起綠色的簾幕。
父親的故事落幕了。
三重埔
隔著淡水河與艋舺相望的新莊,在清代是第一個出現的平原,人們稱之為頭前埔。第二個,稱為二重埔。第三個,就命名為三重埔。
為了越過河川,這裡不斷興建更大更寬的橋,而四通八達的橋樑是河川的遺跡,住在三重,你幾乎不可能有一天沒看到橋。
念幼稚園的時候,母親牽著我的手去上學,每天都要經過藍色的天橋,某天下樓我忽然心血來潮,想比賽誰比較快,她還來不及阻止,我就滾下去了。有頂的天橋無法避雨,雨絲會隨著風斜斜地吹進來。如果下的是太陽雨,又急又快,機車騎士紛紛停下車來在路邊穿雨衣,但等他們穿好,雨又沒了。橋下有五條道路交會,其中一條叫做重新路,總計五段,是貫穿三重的主要道路。
中學的我搭公車上下學,每天都要穿越重新路,因為這裡的安全島很長,簡直到了藐視人權的地步,天橋只有十二歲以下的兒童在走,不管是拖菜籃車的阿桑還是白髮蒼蒼的阿公,都在奔騰的車流之間來去自如。
就算安全島上豎起紅色的告示牌,「請勿跨越,違者罰鍰新台幣三百元」,大夥仍前仆後繼、不捨晝夜;即使安全島中央圍起欄杆,自有勇士把鐵條敲彎,只見六十老叟提起退化之膝蓋怡然跨越,垂髫幼兒亦能彎腰通過,他媽媽在後方扛著嬰兒車呢。
陸橋、浮橋、高架橋、快速道路,通往各種地方。
這些橋全有一個勵志但虛幻的名稱,像是忠孝橋、中興橋、中山橋、重新橋……
重新橋墩下有個流浪漢提著好幾個塑膠袋在那躺著,不受風吹雨打;還有人在橋側刻字,大大的「~椎名林檎~」在乘客還沒清醒的眼簾中一閃而過。忠孝橋側接近住宅的隔音板下,也有鴿子和好幾個保力達B的瓶子並立,那瓶子也許是某個駕駛在塞車的陰鬱時光中累積的小小樂趣,或是幾名從未會面的司機一個順手的默契。從台北橋一下來,就能看見熱鬧的三和夜市,也是父親工作了大半輩子的地方,儘管對面是已荒廢的天台廣場,但夜市始終不曾沒落。
黃昏的時候,可以看見鴿群盤旋在城市上空,養鴿人嗶嗶吹響回家的哨音,紅旗飄舞在屋頂鐵皮之下。
就地理位置來說,三重左擁蘆洲、新莊、五股,右望萬華至士林一帶,中間的橋樑不可勝數,每個要從西部縣市進台北城的人們都會經過三重,但很少人會記得這個地方,也許是因為這裡沒有大學也沒有像樣的車站,沒有公共建設,也沒有一個明顯的商業地標,雖然景氣好時曾有外商投資的大型商場,但現在都成了養蚊子的地方。當我說我住在三重的時候,通常要附加「西門町往成都路再下去」、「從台北車站過忠孝橋」這類說明。
這裡的房子多是兩層樓的透天厝和四層樓的公寓,地板是磨石子,深藍色的鐵捲門裡面裝落地窗,講究些的就用毛玻璃,每天早上家家戶戶開鐵門都劈哩啪啦,像過年放鞭炮。房屋的格局狹長,外側是客廳兼公媽廳,靠牆擺放刻囍字和不知名的神獸的木椅,還上了亮光漆,後面是廚房。遮雨棚下面的車庫,是拿來堆雜物的,通常可以看到水果紙箱、剛拆封的家電包裝、學步車、小孩子用的腳踏車,輔助輪已經拆了、啤酒罐、空了的米酒瓶等,林林總總記錄了這戶人家住過的歷史。
入夜之後,有些住戶透出不尋常的光亮,隔著紗門看進去,幾個穿白背心的男人站在大桌子前燙衣服,他們舉起鐵製的大熨斗,額頭不斷地滲出汗來;另一戶人家,戴厚手套操作沾滿黑油的機械,裡面放了好幾台工業用電扇,門口還能聞到淡淡的機油味;也有門戶大開的木材行,走進去就是里長的辦公室……。母親亦曾在這些家庭工廠之中,踩著縫衣機,嘎噠嘎噠,賺取我的奶粉錢。
在這塊沖積平原之上,也住了許多外鄉的神明。
我家前面和後面兩條街加起來就有六間廟,這些還不是主要幹道,拜令府千歲、天上聖母、降龍師父、有應公……什麼都有,有的廟在路頭與銀行大樓各霸一方,有的設在大樓轉角講經,透明的大玻璃讓講堂看起來像個魚缸,有的開在公園旁邊大伙搖扇子談天,也有神神祕祕藏在公寓二樓,窗口掛個紅燈籠的。所以我上學的路上三步一壇、五步一廟,一年到頭都有神明出巡,保佑孩子們平安長大。
這些墊高了兩三階的房屋,一間就是一個櫥窗,像一個生活的舞台。
但它們墊高卻不是為了讓路人方便觀看,而是因為三重地勢低平容易淹水。一遇到大雨或颱風,平常弄丟的東西就浮了出來,雖然我很喜歡水涼涼浸到小腿肚的感覺,但小時候的我被交代要待在椅子上不要亂跑,只能呆呆看著漂浮在周圍的臉盆、塑膠袋、口香糖紙和蟑螂屍體……我們家向來不買沙發、不買漂亮的櫥櫃,因為泡過水的家具沒幾季就要丟掉。
二樓住著一對夫婦和兩個女兒,我常去他們家玩,陽台上種了九重葛,鐵窗上的木板用立可白工整寫著,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
三樓有一對兄妹跟著外婆住,哥哥已經上明志國中,不會跟我們這些小鬼頭湊成一塊,理著平頭背大書包,後來在都更協調會再見,反而覺得他很年輕,還像個十幾歲的少年,一頭棕髮。他外婆四點就起床到提防運動,作為養女的母親在他們國小時自殺,父親做泥水匠離婚後不知何處。妹妹是我扮家家酒的玩伴,我們摘水溝蓋從接縫長出來的蒲公英葉當菜,毛茸茸的種子是調味料。他們母親死後,曾經搬去八里,又回到三重。但我和那妹妹從此成兩個世界的人。上了國中以後,她非常瘦,穿著細肩帶露出刺青,總是坐在機車上等人。
住四樓與頂樓加蓋的三兄弟,小弟跟我同年,在軍中欠下一屁股債,忽然就變乖了,兄弟聯合起來賣薑母鴨。過去我們的公寓是不關樓梯間的,但常常在電錶前面發現塑膠袋,可能是有人吸膠。除了開店,還有賭場、神壇、掛小吃店招牌的卡拉OK店。
鄰居們有多久沒有回故鄉了呢?還是大家都已經忘了故鄉的樣子。那樣的話,也沒有什麼好難過的,反正房子很快就要拆了。以前的照片都放在電腦裡,我們把照片洗出來,在嶄新的牆面上釘釘子,反正都要拆了,不如提醒自己曾經在這裡活過。
為了不讓父親泡水,撿骨的時候變得像濾網上的菜渣,我們沒將父親葬在他熟悉的三重,而是選了一個比較北邊的墓地,雖然沒能跟他的父母親族葬在一起,至少當海上的雲霧散開,他說不定能夠遠遠地看見他的家鄉。
其實三重已經不淹水了,我記得的事卻像河水一樣地流走了。
長長的安全島被圍起燈泡,彷彿扮起永恆的慶典,行人再也過不去。
公園的樹被上次的颱風吹斷,廟台前面的布袋戲也沒有人看,舞台上的戲偶被筷子插著不動,笑臉迎著這忽晴忽雨的天氣,旁邊賣米粉的攤子也關上鐵門。
大雨、新的店鋪淹沒了我的印象。
附近有很多我不認識的大樓,那些家庭工廠早變成一個一個單純的住家,門口用磚塊填起來,鐵捲門換成了棋盤格的白鐵門。
遠方的河岸亮起燈來,水邊也可以蓋豪宅了。
有時候橋被封鎖,因為這個城市要放煙火慶祝。
慶祝什麼不知道,但在夜市裡討生活的都知道這天的生意特別好,儘管互相屏擋的遮雨棚讓他們看不見頭頂的煙火,那段時間客人全都被煙火吸走,街上就像淨空了一樣,但小販還是站在自己的攤位,喜孜孜地等待即將暴湧而來的人潮,抓住客人手中遞來白花花的零錢或鈔票。
白天的時候三和夜市是個菜市場,到了下午就準備收攤,柏油路上滿是被行人踩爛的菜葉和清洗的痕跡,這時屬於夜市的攤販才拖著推車從騎樓下走出來,在天空將暗之際點亮黃色的燈泡。
我從來沒偏離過夜市的主幹道,突然覺得應該要假裝住戶,走進回字形的走廊。該是樓梯間的地方,似乎是套房增建,整棟建築物像生物一樣,每一層樓都有不同形狀。
至於我就讀的幼稚園,後來幾經轉手,曾經關閉過一陣子,現在又掛上新的名字。連街道的名稱都變了,從福音街換成捷運路。
站在橋上,看生命中大多數的事物被沖刷而去,像河裡的石頭。死亡連接這些石頭,搭起一座便橋,我踩著棧板在無光的夜中行進,天空中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不知道前面有些什麼,只有河水潺潺的聲音可以確定時間正在流動,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會走到哪去,直到我看見橋的盡頭,是通往夜市的路。
每次父親收攤回家,遇到雨天總是穿著後背有反光條的黑色雨衣,我記得他騎腳踏車的背影,還有腳底下水融融的車燈光線,拉得長長的。
他是這樣沉默地走過世間,所以他的背影消失時,也沒有任何人注意,甚至當我想起來的時候,他已經離開了。
而我很可能是那個時代最後的見證者。
那年我十九歲,他七十七歲。未來我三十歲,他還是七十七歲──今後這個距離只會縮短不會延長,最重要的是他曾經二十一歲。但隨著時日增長,我可以一點一滴,追上老人的步伐。
我想,追回這個距離是有可能的。
長假
十九歲那年,父親過世了。
我認識父親的時候,他已經是個老人了。
高血壓、重聽、頭髮稀疏、吐痰的時候發出很大的聲音、上完廁所不沖水、假牙泡在漱口杯裡、每天用一些來路不明的藥酒擦腳……父親身上常常發出一種混合了紅花油、髮油和藥酒的氣味。這十九年間,他多次進出病房又安然歸來,正以為他會一直頑強地繼續下去,沒想到這次他真的離開了。
那年夏天,他放了一個長長的暑假。因為他碰上了農曆七月,後面又是閏七月,天天都有他生前捨不得開的冷氣可吹。──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長的假期。
父親又生病了。
這次不是痛風...
目錄
鹹光餅的假期
甜蜜蜜
附錄
海風:書寫新二代與新二代書寫
致謝
鹹光餅的假期
甜蜜蜜
附錄
海風:書寫新二代與新二代書寫
致謝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36收藏
36收藏

 34二手徵求有驚喜
34二手徵求有驚喜



 36收藏
36收藏

 34二手徵求有驚喜
34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