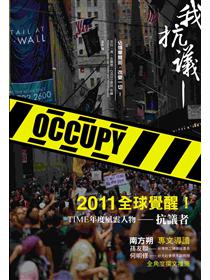關鍵特色
★2014年英國卡內基文學獎決選入圍
★2015年英國格蘭平兒童圖書獎決選入圍
★2015英國讀寫學會青少年小說獎入圍
★2015年英國聖海倫圖書獎入圍
★英國兒童文學桂冠作家傾力佳作
★英國重量級青少年文學家,正面面對家暴議題與自我療癒的誠懇力量!
媒體推薦
「一位從來直言不諱的作家,一部力道十足的作品。」——《獨立報》
「閱讀范恩的作品永遠兼具挑戰與樂趣。她就像每每在家族聚會中戳破不堪真相的難搞親戚,但總能以機智無比的妙語折服人心,全身而退。」——《衛報》
「范恩再度以這本危險而黑暗的新作,證明她何以能持續寫出優秀作品……情感強烈、構思優美、令人身歷其境。」——書評網站We Love This Book
四歲的艾迪與母親被囚禁在暗無天日的屋子裡,直到七歲那天……
那可憐的孩子把臉平貼在窗口,我偶爾會注意到報紙的邊角有動靜,那孩子可能想把臉湊上去往外看,說不定那空隙只容得下他用一隻眼睛朝外頭瞥。結果有一天,連報紙的邊角都用膠帶全貼死了。
我第一封信寫得很小心。後來什麼事也沒有。我整天都在擔心那個孩子,所以我又試了一次。然而他們還是沒有反應。我第三封信就強硬多了。我說,如果社福單位再不立刻派人查看,那麼若孩子死了,社福單位必須負起全部責任。
他們還是花了十一天才有反應。兩個人帶著孩子的媽走出來,這女人幾乎站不住,她的頭禿了好幾塊。接下來,我看到男孩走出來,彷彿受驚的小馬。
寄養家庭先收留了艾迪,他就像個新生兒一樣什麼都不懂,他只知道要靜靜地蹲在牆邊,不能發出一點聲音惹怒殘暴酗酒的哈里斯。接著艾迪必須開始上學,做孩子該做的事,但他不知道要怎麼融入群體,永遠與大家格格不入,只能靠著從前偷看的兒童節目,構築出一個既虛幻又真實的情感避風港。
經過一番永無止境、僵化冰冷的社福程序煎熬後,艾迪從寄養家庭搬入領養家庭,他必須努力再努力才能跟上同齡孩子的腳步,學習其他人看似輕易簡單的社交溝通,學校的廢棄廁所成了他最常窩的校園角落。
經過多年的磨練及成長,艾迪的人生逐漸步上正軌,但一切都在他偶然看到一張照片後,開始走調,野獸哈里斯的臉再度出現眼前,過往的噩夢從未遠離。
作者簡介:
安.范恩(Anne Fine)
1947年生,為英國當代最重要、最受歡迎的兒童文學作家之一,曾獲選為2001-2003年英國兒童文學桂冠作家(Children’s Laureate),擔負鼓勵兒童閱讀、激發孩子閱讀興趣的推廣工作。
累積著作超過五十部,獲獎無數,包括卡內基獎、惠特布雷獎、衛報獎,擅長以或幽默或銳利的筆調探討複雜的人際互動、家庭與社會議題,作品已譯成四十幾種語言在全球發行。
2003年成為英國皇家文學學會院士(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並獲頒大英帝國官佐勳銜(OBE)。
譯者簡介:
蘇瑩文
輔仁大學法文系畢業,曾任職外國駐華機構及外商公司十餘年,現為英、法文自由譯者。譯有《當愛遠行》、《鄰人》、《魔鬼遊戲》、《凡妮莎的妻子》、《說故事的人》、《離別時刻》、《禁錮男孩》(以上皆由臺灣商務出版)、《騙過死神的女孩》、《娃娃屋》等書。
章節試閱
艾迪
戶外的一切重重地打著我的臉,像是一巴掌落在我的皮膚上。我已經忘了外頭的世界。而且,那味道──喔,我不知該怎麼說,應該是有些銳利吧。幾乎可以用粗糙來形容,像多角的水晶一樣。我覺得空氣比光線讓人驚訝,有一、兩次我經過游泳池,聞到氯氣的味道,又回想起羅勃打開樓下大門那個奇特的時刻。
我忘不了自己搭上警車,好像走進了又大又寬廣的世界。我們經過公園時,我只想到從前念的幼稚園,因為園裡也有一塊綠地。我彷彿看見了逐漸遺忘的景象。當然了,電視裡也有樹木和草地,但看到左右兩側各有半座公園,那種感覺又不一樣了。我感覺像是在綠意中游泳。
另外就是天空。我們住在公寓的尾端,即使在哈里斯封住窗戶之前,我也得扭著脖子歪著頭才看得到一小片天空。車窗是關上的,但如果我靠上去往上看,還是能看到大片藍天。
景象飛快地往後退,到處都好明亮。
因為這是輛警車,所以我以為我們要去警察局。(柏金斯先生帶我們去過警察局。)車停好後,羅勃.瑞德說:「我們到了。」看我沒動,他靠過來推開車門。他讓我在車外站了一會兒,才說:「來吧,艾迪。以後還有很多時間看。」
這次我動作快多了,因為我知道他在對我說話。(我認得他喊那個名字的聲音,聽起來,好像我和磚塊一樣厚。但哈里斯通常只喊我「廢物」或「蠢才」,媽媽在還能說話的時候會喊我「甜心」,所以我幾乎忘了自己的名字是艾德華。)
羅勃.瑞德帶我穿過玻璃門,最讓我驚訝的是他連碰都沒碰,門就自己打開了。門後的人比我這輩子見過的所有人加起來還多,而且沒有任何一個看著我。
「來,艾迪,」羅勃.瑞德說:「我們往這邊走。」
他帶我穿過長長的走廊,我以為我們不可能有走到盡頭的一天。
露絲.馬契特(安妮女王醫院醫師)
我驚訝地發現那男孩狀況並不差,真的。走進診療室之前,我已經聽說那孩子好幾年沒離開過公寓,我記得自己心想:「這孩子一定缺乏維生素,很可能生長遲緩,精神狀況耗弱,應該會是弱智。」
他的小腿有幾處輕微瘀青,踢他的人似乎沒辦法把腳抬得太高,要不,就是不把他當一回事。(我聽說他母親受到的待遇就不同了,被踢得慘不忍睹,而且慘到失去語言能力。)沒想到孩子只受了皮肉傷。沒錯,他身上有一、兩道傷疤,但我沒找到足以確認是香菸燙傷之類的痂。我看過更糟的案例。的確,來這裡的孩子多半比美式足球賽後的球員還要慘。
他不太說話,但還算願意回應,這表示他的頭腦還能運作。他大多透過搖頭或點頭來回應,但碰到不得不開口回答時──例如我問他:「你能不能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他會立刻看向他的守護者,也就是叫作羅勃的矮胖、半禿老好人,然後正確地說出:「艾迪。」
我打量他身上的衣服,襯衫太大,而且也該洗了。但我連他下半身穿的是什麼都看不出來,因為那塊布太破、太舊。於是我說:「艾迪,我們現在可能要脫下你這件襯衫。」
羅勃嘟囔地說:「這沒什麼好捨不得的。」從他譏諷的語氣聽來,我猜這件襯衫的主人應該是被警方逮捕的布萊斯.哈里斯。
我脫下艾迪的衣服。我以為那時自己總該能看到真正的傷處了。動手家暴的人通常很狡猾,傷痕全集中在別人看不到的部位。但這孩子的胸膛和臀部都沒有傷痕。羅勃.瑞德拍了拍孩子的頭,這時,我要進行的是所有孩子都厭惡的檢查了──特別是那些知道接下來會如何發展的孩子。艾迪果然在我的觸摸下瑟縮了一下,但我覺得那單純是害羞。我必須說,我在他身上看不出任何足以讓我判斷他受過類似侵害的證據。
他身上連虱子都沒有。
儘管我看不出照片在法庭上能發揮什麼作用,但我們還是拍下了照片。
「我猜他沒有身分資料,對吧?」逐項檢查過後,我問他:「沒有醫療保險卡、家庭醫師的名字之類的資料?」
「機會不大,」羅勃說:「他們明天會派人過去仔細搜查,但是我沒抱太大希望。那地方又小又亂。」
「如果什麼都找不到,那麼我們得開始幫他安排預防注射。」我寫下筆記。「在他媽媽遭虐前,他可能打過一些疫苗。」我直接問孩子:「艾迪,你記得嗎,有沒有醫生或護士幫你打過針?把針頭刺進你的手臂,告訴你痛一下就沒事了?」
要不是他聽不懂,就是不想回答,光是自顧自地瞪著擦得光亮的地板看。於是我說:「沒關係,」我脫下醫療手套,「我們先到此為止好了。」
我幫他穿上醫院毛茸茸的兒童袍,讓他能趁志工幫他找乾淨衣服時先去吃點東西洗個澡。他們走到門邊,羅勃打探似地回頭看著我;我聳聳肩。我們不想在這些孩子面前談這種事,那像是把他們當作死了或失去知覺。但羅勃是好人,而且認真看待自己的工作,於是我想讓他知道,就我所知,我看得到的他也看得出來。幾處從前的瘀傷,就這樣而已。我只希望這可憐傢伙所帶過來的孩子全都能這麼幸運。
但我要說句話,我的工作不在於檢查這可憐孩子的心智或自我價值有沒有受到傷害。
這種傷害通常無法痊癒。
艾迪
我們再次走出來時,陽光依然閃亮刺眼,我不停地眨眼。羅勃.瑞德注意到我的表情。(他什麼都不會放過。)「如果繼續這樣,」他說:「我們得馬上帶你去檢查眼睛。」
這似乎讓他想到別的事。「到公園裡休息十分鐘怎麼樣?」他咧嘴笑,「乾脆好好把握曬太陽的時光好了。」
他停下車。「別動,」這話讓我意外,因為我連想都沒想過要動,「我繞過來幫你開門,讓你從另一邊下車。」我知道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因為外頭行駛中的車子咻咻掠過,速度快到讓我頭暈。
他牽著我穿越高低不平的草地。「坐下來,面向這邊。」他要我背對太陽坐下。我感覺到後腦和脖子越來越熱,我想,那是因為幫我洗澡剪指甲──包括腳趾甲──的護士在洗我頭髮時可能也做了什麼奇怪的事。當時我什麼都不懂,要不就老是猜錯!
但有件事我很確定。「我不是該抹點防曬乳嗎?」
羅勃揚起一邊的眉毛──就微揚而已,但若要說我懂什麼,那就是察言觀色了。我低頭去拔草。
一會兒後,他才說:「你覺得你應該要抹防曬乳嗎?」
我脫口說出:「柏金斯先生說一定不能忘記抹防曬乳。」
「柏金斯先生是誰?」
我認得這種刻意裝成漫不經心的語氣。看到我媽和哈里斯的相處情形,我知道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可以引發怒火,最後連她自己都覺得活該遭到踢打。於是,我什麼也沒說,希望這句話就這麼過去。但是他繼續追問:「柏金斯先生是誰,艾迪?」
嗯,現在我知道他可能怎麼想了。但當初我答得緊張,如今想來都好笑。「你知道的,電視上的那個柏金斯先生。」
「電視上?」
「對呀,他的節目。」
「我從來沒看過。」
他當然沒看過。那些影帶是三十年前的東西了。我不知道是誰把影帶留在櫃子裡,但東西就堆在沒標記的盒子中。在我還很小的時候,媽媽和我放了第一卷影帶來看。哈里斯因為搬家的事不高興,還在氣頭上,立刻關掉放映機。媽媽看哈里斯的吼叫嚇到了我,還煮了杯熱可可給我喝。「說不定那只是電影。」她說。
但影帶裡有柏金斯先生,全是從前的電視節目。他出場會先唱歌,因為嶄新的一天讓他心情大好,我們有好多事可以一起做。
「快樂的日子,快樂的方式,
「我希望你們知道
「今天看到你們能和我在一起,我有多麼高興,
「我們會玩得很開心。」
他邊唱歌邊脫外套,影片一開始一定是這樣。接著他會開始煮水,把貓食倒進碟子裡。(「小黑炭,吃飯嘍!你餓壞了吧!」)接下來,他開始展示自己怎麼用膠水、紙張、繩子或舊花瓶之類的東西來裝飾放捲筒衛生紙的架子。任何東西只要到他手上都有用處。之後,我們要跟著他開始參觀。每集節目都不同,但主題都很有趣。柏金斯先生會帶我們去看消防隊、農場或披薩餐廳。(「出發嘍,和我一起跳上巴士。」)我們拜訪過釘馬蹄鐵的女士和動漫畫家,看到裝了機械手臂的機具怎麼摘柳橙,還參觀過醫院,去工廠看通心麵的生產過程。有時候,我真擔心這個世界上的人和地方太少,我們很快就沒有拜訪對象或再也沒地方可去,還好這只是白操心。柏金斯先生每帶我們去一個地方,就會提出一百個問題。「為什麼要用那種方式?」「你不害怕嗎?從來都不會?」「會不會很難?」「你會不會不小心燙傷自己?」「煮這食材要花多久時間?」
他的問題永遠問不完。有時候,他會問我們:「你會不會幫忙下廚?」「你有沒有曬傷的經驗?」(我就是從這裡學到塗抹防曬乳的事。)我每次都會回答,就算嘴裡塞滿派餅或起士也一樣。到了節目尾聲,我們會和當天拜訪的人揮手道別,讓他帶我們回到他家。最後他會唱另一首歌,內容是我們長大以後什麼都能做,想做什麼就能做什麼,只要我們真的很想做就可以。
「因為你的內心堅強又勇敢,
「但最重要的,當然是因為你很想要,
「想要,想要,
「因為你的內心堅強又勇敢,
「而且真的想要去做。」
我們第一次看影帶時,媽媽在節目結束後擦掉臉上的淚水,按下按鍵退出影帶,收回盒子裡。「這樣吧,我們把這些影帶好好藏在櫃子裡,改天再看,好嗎?」
我覺得自己在當年就懂了,她的意思是:「別讓布萊斯看到。」(她喊他布萊斯。那是從前的事了,後來幾乎每天都有人來敲門,在外頭喊「哈里斯在哪裡?」「哈里斯,你這個混球!快開門!欠債還錢!」「我知道你在裡面,哈里斯!」後來媽媽越來越害怕,腦袋也出了問題,逐漸就不說話了,而我也忘了他從前叫作布萊斯。)
我把影帶放回盒子裡。我每次都記得哪面該朝上,放好後再蓋上塑膠盒蓋。媽媽把盒子放在櫃子最深處,還會用她的襯衫蓋住。我猜,她認為哈里斯若發現影帶,一定會拿去錄自己的東西,蓋掉原來的影像。就算在哈里斯帶了一臺能播放DVD的全新電視回家後,我仍然小心地保留影帶,趁他出門時看。哈里斯應該不會想到他用來堆啤酒罐的機器還能用。如果你是那種狗死了幾星期後還懶得把屍體拿出去的人,你怎麼會注意到角落有個沾滿灰塵的舊機器?
艾迪
羅勃雖然在講電話,但眼睛仍然盯著我看。他走回來時說:「可以走了嗎?」
我們又坐進他的車裡。我記得當時自己很驚訝,因為這段路很顛簸。一開始我以為是路面有坑洞,隨後才聽到他嘀咕:「可惡的減速丘!」
他把車子停在另一棟建築外,這棟樓和醫院一樣,都有玻璃門。羅勃朝接待桌後的人點點頭,帶我穿過推門來到走廊。多數和我們反方向擦身而過的人都點頭致意,但沒有人停下腳步說話。他試了幾扇門,敲過門後馬上推開,但最後都低聲說:「抱歉。」才又關上門。
最後他終於找到一間空房,我們這才走進去。這個房間鋪著磚紅色地毯,裡頭有扶手椅和矮桌,桌上有些玩具,但角落還有更大一堆。羅勃輕推著我經過整面鏡牆,走到房間裡坐在椅子上,我覺得好像有另一個男孩和我們走在一起。我沒認出那是我自己的影像。
羅勃拿起桌上的電話,按下幾個號碼。我不明白他和對方說了什麼,但隨後立刻有人走進來,坐在我們兩人中間的椅子上。
「艾迪,」羅勃說:「這位是蘇,她是警察,也是我的好朋友。她要旁聽我們說話。她可能會有一、兩個問題,或許會想要我幫她問。她還會用這個小機器錄下我們的對話。」
我本來沒注意到那個機器,我以為桌上那個漂亮的銀色小盒子是香菸盒。
「這樣我們才能記住一些事情,好嗎?」蘇說。
我怎麼會知道這樣做好不好?我沒看她,只顧直挺挺地坐好。
接下來是一堆問題,問不完的問題。我覺得最怪的是他們很多事明明知道,卻仍然問個不停。他們似乎知道不少哈里斯的事,對我媽的認識也比我更多。羅勃表示他聽說我媽曾經在禮服店工作,問我有沒有聽她提起過。(現在回想,他們當時應該希望我能記得店名,好追查她離職的時間。但我沒幫上忙。)
他們問我誰負責採買東西,誰下廚,帳單誰處理。我恐怕只能茫然地面對每一個問題。我是說,我知道媽媽從前得去買東西,可是自從她那次從牆上跌下去後,哈里斯就算冷靜下來也沒辦法讓她站起來,所以只好由他自己採買。他會用箱子裝自己喜歡的東西帶回來,扔在桌子上。有時他會吃,但他多半出門去吃東西,也經常帶著滿身咖哩或披薩的味道回來。我沒辦法知道他會不會想吃箱子裡的東西,所以為了安全起見,我大都不會去動。不過,我倒是知道哈里斯不喜歡吃什麼,所以在媽媽還能自己握住湯匙,不至於把食物灑出來之前,我會拿那些東西餵她。我怎麼可能知道他們想要什麼答案呢?誰採買誰下廚?一切都亂成一團了。
然而我還是盡力。一會兒後,有人端了盤薯條進來,熱騰騰的酥脆薯條,盤子上還有番茄醬。蘇和羅勃互相開玩笑,說他們邀了大野狼一起午茶,應該點雙份才對。儘管如此,他們仍然繼續發問。有些問題連我聽來都頗有道理,有些聽來則是非常奇怪,比如我記不記得小潔是怎麼死的,拖了多久時間。(我又沒計算日子,怎麼會曉得,我只記得哈里斯興致一來就踢踢牠僵直的斷腿,嘴裡不停地說:「喂,幫個忙,趕快站起來。」)
他們問的全是這種問題,我倒也不介意。他們要我坐在一張塞滿靠枕的大椅子上,羅勃.瑞德也在場,他當時就說得很清楚:除非我想要,否則我再也不會看到哈里斯。這句話讓我度過這輩子最美好的一天。
「你記得自己上過學嗎?」
「媽媽說我上過學,我好像還記得。學校裡有紅色和黃色的小車,但大家都喜歡玩紅色的車。」
蘇問道:「是踩踏板前進的小車嗎,艾迪?」
我回想了一下。「不是,是用腳踩地往前滑的。」
蘇轉頭看羅勃,說:「這麼說,是幼稚園了?要不就是托兒所。」
羅勃問我:「之後就沒別的印象了嗎?」
「他不喜歡,」我告訴他們:「他告訴媽媽,我進進出出的會引人好奇。他說他喜歡把家人留在身邊,喜歡隱私,而且別人管不著我的事。」
「家人?」羅勃往前靠。「艾迪,你記不記得你媽媽帶著你和其他人一起生活?比如從前有沒有見過不同的爸爸?」
我搖搖頭。
「你媽媽從來沒提過?」
我不想講出媽媽不會說話了,只好低頭看著他們給我的球鞋。我真的很喜歡這雙鞋,公寓附近那些男孩騎腳踏車時都穿這種鞋。
「喔,沒關係,」他說:「他們一定能找出答案的。」他看看手錶。「時間差不多了,還是說,你有什麼問題想問?」
我只有一個問題。「我媽媽在哪裡?」
「她還在看醫生。」羅勃.瑞德說。
我突然好驚慌。「她生病了嗎?」
「拜託!」他責備我。「看看那些瘀傷,而且她的頭一定很痛。我們覺得她得花幾天時間才能療傷,才能恢復原來的狀況,到時候你就能和她見面了。」
「她在那個醫院裡嗎?你帶我去的那個醫院?」
「不是,不在同一個地方,是在另一個醫院。她很安全,離哈里斯遠遠的。」
有人推開了門。我看不到對方的臉,我只聽到她說:「嗨,羅勃。今天可以結束了嗎?這可憐的孩子頂多七歲。」
羅勃.瑞德問了最後一個問題。「是這樣嗎?」
現在回想起來,我發現這麼講真的很奇怪。但是那天他們提出的所有問題,以及在接下來的日子裡,那是唯一我沒有嘗試去回答的問題。
我一點概念也沒有。
艾迪
戶外的一切重重地打著我的臉,像是一巴掌落在我的皮膚上。我已經忘了外頭的世界。而且,那味道──喔,我不知該怎麼說,應該是有些銳利吧。幾乎可以用粗糙來形容,像多角的水晶一樣。我覺得空氣比光線讓人驚訝,有一、兩次我經過游泳池,聞到氯氣的味道,又回想起羅勃打開樓下大門那個奇特的時刻。
我忘不了自己搭上警車,好像走進了又大又寬廣的世界。我們經過公園時,我只想到從前念的幼稚園,因為園裡也有一塊綠地。我彷彿看見了逐漸遺忘的景象。當然了,電視裡也有樹木和草地,但看到左右兩側各有半座公園,那種感覺又不一樣...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6收藏
6收藏

 2二手徵求有驚喜
2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