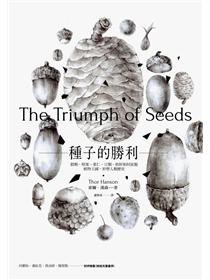最痛的人所給的安慰往往都是最溫柔的
賴香吟短篇創作的十年釀藏,精煉如永生之華
穿越魔幻時刻之後的自由
——如今文青當然不是個乾淨字,消費流行與裝腔作態使它討人厭,這本書回收此字,不是擁護,不在批判,而是想理一理文青這個字曾經乾淨的成分。是的,曾經,意味今已不存,初心已改,所以文青已老,已死——這些年,觀看同輩甚至較我年輕世代之文青變形記,不免有此感嘆,可我又偏偏不想放棄。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然而,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就莫再多煩憂;揮別脆弱惶惑的自我,然後,懷抱著那麼一點乾淨,繼續向前走吧。
〈在幕間:一則偽評論或偽小說〉
命運的手掌重重地朝他們新生的身軀狠打了幾下,放聲啼哭,一股新鮮空氣倏地湧進胸口,他幸福但悲傷的知道,他與久別的妮亞重聚了,可是,眼前這一生,他想在妮亞的身軀裡,取得愛情,恐怕將走得比前生更為辛苦。
〈暮色將至〉
他發現,病魔和他們以前反抗的霸權異曲同工,全是蠶食鯨吞,橫取豪奪,毫不手軟,過去還是看得見的政黨、敵人、殺手,現在一刻一刻啃蝕過來的卻是誰也看不見的病變、命運、死神,難怪阿君要沉默了——
〈靜到突然〉
塵埃細細,色壞形空,過去無數淡水寫生所描繪過的藍天、白雲、綠樹、紅瓦、黃貓、黑狗、灰色的人,已隨光陰流向大海,二十一世紀人類正在匆忙趕赴最後的夕陽。一念之間的愛情。靜到突然。
〈天竺鼠〉
我們搭起一棟房子,我們工作,購物,踏青,探望父母,出入作息正常,假裝這個家庭就算稱不上幸福美滿,也是平靜安穩。愛是可以模仿的嗎?愛是危險的問題,避開這個危險我們可以模仿成真地生活嗎?
〈約會〉
他抱住她,先是安慰,然後生出了點激情,開了那無數難以分辨的痛與苦的閘門,嘆息如浪生湧,接而帶來平靜,讓人不願意分開。這樣的擁抱是太長了,他感覺到她一如少女,然而,人生終點就要來了,他們要一起走到終點嗎?
〈日正當中〉
她靜靜坐著,懸著頸,如有巨斧隨時可能落下,在如此的美好裡。戶外明豔,室內陰涼,哪裡傳來哪戶人家午睡醒了扭開收音機,咿咿嗚嗚,她支著頸子,感覺自己如一艘擱淺的船,停泊在荒廢的小漁港裡……
〈遷徙〉
高樓夜風冷,他拉拉被子,十二樓,這輩子沒想過住這樣高的所在,鳥兒似的,人講落葉歸根,他與妻子到頭來卻選了這麼高的枝頭,靜靜地棲息。
〈小原〉
他瞪著她,狐疑且孤獨,她果真不在乎自己了。他忽然生氣起來。她不知道這是因為她嗎?自從他愛過了小原,他便成為一隻夜半不眠奇怪的獸。
〈文青之死:A Fond Farewell〉
輸掉的拳擊手。愛我,別走。我的抒情,我的怪胎,我的Sunrise & Sunset。千禧年,我二十七歲,搖滾樂裡有該死的27Clubs,但我從來沒想過要死,我甚至想要重新開始。
作者簡介:
賴香吟
台南市人,畢業於台灣大學、日本東京大學。一九八七年發表第一篇小說,之後散文、評論、小說散見報章雜誌。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吳濁流文藝獎、九歌年度小說獎、台灣文學金典獎。著有《其後それから》、《史前生活》、《霧中風景》、《島》、《散步到他方》等書。
章節試閱
暮色將至
年底,初冬,寒氣教人還不太習慣,所以感到分外地冷。外頭天色陰沉沉的,林桑從衣箱裡找出厚外套,這是今年第一次穿它,但衣服是早已穿舊了。在國外那幾年,冬溫低得嚇人,即便多麼窮學生,也得常備幾件厚衣。此刻上身這件,猶記是在星期天的跳蚤市場買來的,那時他和阿君,簡單娛樂就是去逛跳蚤市場,少少錢換一整天樂趣。阿君挑東西眼光不知該說怪還是獨特,總能從一堆不起眼貨裡翻找出特別東西,且那價格通常低廉得很,彷彿除了阿君沒有人會去爭搶。那些奇奇怪怪的小配件、布料、提包,他不能同意多麼好看,但等阿君把它們裝飾在屋裡或在身上穿搭起來,卻又有了一股不俗味道,阿君向來有她自己鮮明的風格,那經常是對比突兀而不講章法的,但愛上的人就會很愛,好些朋友就說阿君光憑這跳蚤市場的撈貨技巧,就足以回台灣開家二手精品店轉手賺錢,餓不死的。
餓不死,這的確是阿君的本事,阿君也常不在乎調侃自己是草根命 ,丟到哪裡長哪裡,怎麼樣的環境都可以活下去,不像他,阿舍命 ,嘴上說要吃苦畢竟是挺不住的。林桑對著鏡子,把外套釦子一顆一顆扣好,舊衣服舊歲月,過往的經濟生活,好像從來沒有光彩過,國外那些年更是克難得緊,然而問題也許並不在窮,這點小事根本打倒不了阿君,她是那種只有百元日幣也可以把日子過下去的人,真正使她投降是他的心。他總想從與阿君的共同生活裡逃離,然而,眼前生活不盡滿意,推翻又要怎麼辦呢?他嘴巴上說得好聽,認為自己就算隨便捲幾個紙箱過流浪漢生活也是可以的,事實上,他從來沒能真正跨出那一步。他惱恨自己,偏偏人對自己的惱恨是最難以承認的,於是便把氣全推到阿君身上,認為這麼多年就是阿君絆住了他,而他從來沒有愛過阿君。
他對阿君從來沒有承認過,若非出國需要,他們之間恐怕是連結婚登記也不會去做的。在一起那麼多年,阿君沒要過什麼,他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對或愧疚。阿君唯一有過的念頭只是小孩,然而那些年他的心已經跑得那樣遠,時不時總在準備哪一刻就要跟阿君提分手,怎麼可能再有小孩。泥淖般的婚姻生活,他以為自己欠缺的是真正的愛情,以及,一顆夠殘忍的心,如此才能讓他有所動力來處理與阿君的關係。外遇就是這樣來的。誰知一次、兩次他還是拖拖拉拉、吞吞吐吐,阿君也不復往日理性,兩人要嘛完全裝死不談,要嘛鬧到歇斯底里,搥胸頓足追不回重點在哪裡。他們在這樣的關係裡猛然覺悟彼此竟然已經變得這樣多,不再是當年那對率性的革命情侶,而是面對輸贏放不開手、眼望人生殘局也難免感到悔恨與恐懼的中年百姓。
最後兩人真正簽字離婚,已經不干任何第三者的事。在好幾次鬧到大打出手,彼此無比憤恨、計較之後,婚姻的屋簷下一片混亂與寂靜,他看阿君背影,知道她要放了,兩人畢竟走不下去了。不久之後,阿君便回台灣,他以為兩人情分終於到了盡頭,他安慰自己,盡頭是好的,在此分道揚鑣,各自新的人生。
沒想到,事情完全不是那樣。
他從山坡居處走下來,穿過捷運地下道,來到鐵軌對岸的醫院。這一帶,出國前他熟得很,但捷運通車後很多地景都改變了。他在醫院入口處按了消毒劑,抹淨了手,進入一個與外頭兩相隔離、截然不同的世界。大廳有人圍聚說話,說不多久便哭起來,然後是止不住的激動吶喊。路過的林桑偷偷瞄了幾眼,生老病死,他以前總盡可能避開,總推給阿君代為處理,除了幾個不得不露臉的告別式,對於人生盡頭的淒涼,醫院裡疾病折磨的場景,他能逃則逃,現在,他逃不掉了。
電梯上到六樓,一開門便見阿君請的看護正在走廊上和人聊天。他輕手輕腳走進病房,阿君睡著,她體力一天比一天差。床邊小桌擱著寫字板,上頭阿君字跡記滿她提過的朋友名單。即便已到這地步,阿君還是什麼都堅持自己來,毫不避諱交代身後事,細節諸如保險金錢事務可找誰,誰來幫忙清空房子,其中健身器材、家電分送給誰,遺孤愛貓又託誰續養,若不就範可找附近哪家動物醫院來打麻醉針等等。
寫字板上頭沒有他的名字,阿君對他的交代只是口頭,安撫他說諸事都已經安排妥當,就差時候到了得有個人來打電話通知大家,而他,就是那個負責通知的人。
他有過抗拒,好像一個責任又從天而降罩在他頭上。他不是已經和阿君離婚了嗎?為什麼是他?實在作夢也沒想到,甚少鬧病的阿君一病就這麼重。當阿君透過電郵初次告訴他的時候,他不以為意,他早習慣了阿君自己料理自己,待至後來回台,見阿君頭髮掉光,才不免具體驚惶起來,慌慌張張問了病事。那一次,阿君已動完大刀,化療也告一段落,坐在週末的咖啡廳裡,看得出來特意打扮,紮了條花色大膽的頭巾,身上披披掛掛,頹廢嬉皮風。她老在他面前故作無事,一整個下午淨是口氣樂觀,說自己怎樣抗癌,吃喝多講究,誰慷慨大方給她送來許多營養品,一生時光大約現在最是悠閒奢侈云云;阿君相信意志力,說自己現在感覺不壞,再休養一兩個月,便要回去上班。
後來果真這樣過了一段日子。其間,他從日本回來,一兩次沒地方住,借住阿君家也是有的。她領著他拐進藏於巷弄之間的傳統菜市,有說有笑跟商販打招呼,然後進了一間家庭美髮,上得二樓,租來的兩間房布置得色彩繽紛,熱呼呼堆滿什物。他很意外,和阿君在一起那麼多年,從沒想過阿君生活竟也需要這麼多東西。以前他們屋子裡堆的淨是他的書與收藏,阿君個人擁有不過簡單幾疊衣物,現在,放眼望去,除了那些砸下重金的抗癌設備:鹼性水過濾器、空氣濾淨機、健身器材之外,就連花草、彩繪、瓶瓶罐罐、絨毛玩偶等擺飾亦不缺少。窩在以前他們侷促家居絕不可能出現的懶骨頭裡,他想,阿君是在過另一種生活了,憑她的本事,她很容易可以過得很好,如果她不生病的話;阿君應該會覺得跟他離婚也是好的,因為她要精采人生並不難,如果她不生病的話……
可是,現在,她病了。一兩回合的相處,阿君的話裡偶爾會洩漏一些怨哀,想要依靠,使他不知所措。他忽然發現,他沒有太多照顧阿君的經驗,癌或死,這些字眼他感覺負擔不了,他想逃,他跟阿君坦白:我不知道怎麼處理。阿君看他幾眼,默默收話不再講下去。總是如此,他不知道怎麼辦便兩手一攤說實話,阿君總會放過他,原諒他。
後來,他回台灣便改找弟弟找朋友,沒再住過阿君那裡,幾通電話只是簡單問問病情。真正搬遷回台,工作又沒他想像得容易,只好靠著以前朋友關係,這裡接接計畫,那裡做做顧問,看似風光,頭銜好聽,但總沒個定數。他多少體會到了幾分流浪漢的滋味,原來根本不是自由與浪漫。然而,他跟阿君畢竟離婚了,各走各的吧。若非阿君情況後來惡化,他是沒準備要和阿君再次恢復成這種關係的。
夏天,阿君的癌往腹部、肝臟擴散。秋天再度入院,這回不開刀了,阿君託人捎來消息,簡短、明白地說:時日不多,希望見個面。
這消息不能說有多意外,彷彿一盤棋局擱久了,最後幾步終要點名到他。他想逃,卻無所遁逃。他說不出口這不關他的事,也不能耍賴說這不是他的局。呆呆地進了醫院,他期待阿君會告訴他怎麼辦,孰料阿君跟他一樣無所遁逃地垮下去了。她躺在病床上,平靜,冷淡,看不出想些什麼,惟在朋友來訪,談及生死後事種種,才洩漏那麼幾絲情緒。前兩天跟他一起來的汪明才,以前留學時代的朋友,要離開的時候,從口袋掏出紅包往阿君手裡塞。
「我不需要錢。」阿君推回去:「你倒說說看,錢現在對我有什麼用處?」
她說得平靜,沒有怒氣,也沒有怨意,只是苦笑說出了事實,讓人不禁要為自己的舉動慚愧起來。汪明才靦腆應答幾句,沒再硬推,嘆口氣,對阿君說:「妳要想開點。」
「我是想開了,總歸早晚要走的路。倒是你們也要想得開,你們想得開,我才好走得開。」
他聽出一絲哽咽,抬頭看阿君,心裡跳了幾下:她要走了?她準備好了,那他呢?垂頭繼續看報紙,心內陌生得彷彿有扇打不開的門,有時候,他真不明白自己是準備好了?還是根本沒進入狀況?眼前情景彷若阿君只是生了小病,而他不過來演一場探病的情景;如果他不轉頭看阿君病瘦的臉,坐在這個房間好像只是跟阿君在過家常生活,報紙裡那些消息很快可以引他讀得興味盎然:總統大選倒數不到百日,隨處可見他熟悉的名字與言論,那是他們過去黨外歲月的成果,也是阿君和他的共同回憶,是的,如果他與阿君還能站在同一陣線說點什麼興致勃勃的往事,大約就是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如今成為政治主角之點點滴滴,那些他與阿君一起走過的患難青春……
阿君在他沉溺於回憶的此刻張開眼睛。他收起報紙,問問身體情況,說點外頭天氣,兩人之間其實沒什麼話。他把看護沒關上的電視調回正常音量,像以前那樣假裝自己自在得很,時不時還對選舉加上幾句評論。新聞正在回顧黨與派系的成立經緯,他轉頭以為能和阿君交談點什麼,但她低垂著眼,一種他不敢去猜測她在想些什麼的枯萎神情。他只能自己回味螢幕裡那些舊照片,如今已成政治大老的大象,十幾年前的臉龐看起來簡直就像個文藝青年,在一幕稍縱即逝的靜坐畫面中,他甚至從人群縫隙裡看到了青春的阿君……
阿君生病消息一傳開,多位朋友包括大象二話不說就開了支票讓人送來,這是交情,但又有點令人感慨。前幾天阿君幽幽說:「大象明年要送阿平去美國念書了。」阿平是他和阿君看著長大的小男孩,阿君對待阿平甚至有幾分情人的意味。這個臉色細白、敏感、而又甜蜜的孩子,當年無論抗議、演講、行軍各類活動,跟著爸媽無役不與,在那些充斥憤怒與委屈的場合裡,阿平的童言童語若非教人開心就是讓人心碎。如今,阿平十六歲了,和他們這些大人漸漸生疏起來,就連他們大人之間,也因為身分、權力的變化,難免有些不同了。以前沒錢,現在有錢;以前有空,現在沒空;以前做什麼都一票人夥在一起,現在阿君形單影隻進出醫院,大家都忙,沒空來看她,花倒是送了一堆;以前沒沒無聞的朋友,現在人盡皆知,病房裡的花卡,上頭署名經常搞得護士和看護工都緊張起來,那天老胡匆匆來探,還吸引了醫護人員和隔壁房的家屬來要簽名,搞得看護也虛榮了,逢人就要講兩句。
聯繫他與阿君的過去,很容易可以畫出一張現今執政圈的人際關係圖,其中有些與他仍是好朋友,有些則不然了。偶爾他也有所憤恨,感嘆人心冷暖,聽他們發表政論,有些依然敲痛心中角落,但有些話已經不對勁了。他痛心於以前努力爭取來的如今濫用糟蹋至此,且竟有那麼些不知哪裡冒出來的小角色,牆頭草,見風轉舵者,以及令他難以置信之聰明伶俐、敢吃敢拿的政治金童。不同派別各自表述,彼此不問是非,就是反對到底。他不知道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開放所帶來的,竟然不是愈來愈多的選項,而是幾近沒有選項,衝突非但沒有化解,且是更草莽地對立。
緊接著一場決戰即將再來,他們會不會再勝?他看著新聞,不知道自己應該怎麼抉擇。他依舊不認為自己過往那些相信是錯的,他也知道自己不免還是會基於舊情誼而替老朋友找藉口;無論如何,他不希望他們輸,但他們贏他似乎也不感到多麼高興。他看著枯萎的阿君,現在的她很少評論什麼,依她的時間演算法,這一場政治,輸或贏,皆影響不了她,因為,她是不可能活到答案揭曉的。
就在阿君昏沉沉即將入睡之際,門口有人探臉,竟是多年不見的安。國外那幾年,安在他家搭飯過一陣子,算是很熟悉他與阿君的人,但他簡短打個招呼便讓身出去,他猜安應該也沒多大興趣看他,這陣子,他被阿君一幫女朋友罵到怕,在她們的審判下,阿君的病全是他這負心的丈夫害的。沒想安很快從病房出來,邀他去樓下咖啡吧坐坐。安一開口便問他現在做些什麼之類的樣板問題,他隨便講點兼課的事,跳過那些積在心裡其實非常想要傾倒出來的埋怨與求援,這些年,他學會了,不要隨便說出真心話,有時這是一種禮貌,簡單方便的應酬,最好,對方也不要莫名其妙說起真心話來。
眼前的安看起來氣色不錯,臉上微笑穩定,不虛偽,但也沒說真心話。這很好,她是怎麼辦到的?她曾是那麼迷惘的一個小女生,叨叨絮絮和他在電車裡、在餐桌上說個沒完,真心表露自己對於人生舉棋不定。見他意興闌珊熬著學位,安勸他不如換跑道重新開始,他當她小孩子說大話,他畢竟不是安的年紀,且他當初帶著阿君來日本,何嘗不是以為自己正要轉換跑道重新開始?他酸溜溜地說:「重新開始談何容易,妳有後援又年輕,當然可以重新開始,我可是形勢已定,頭都洗一半了 ,不弄完能如何?」
這類口氣的話,安通常是接不下去的。這是他的本事,他很知道怎麼以退為進。安臉上每每浮現尷尬抱歉的神情。然而,事實上,他想跟她表示,其實他是感謝她的,至少她那麼煞有介事跟他談論他的人生。那時候,他以為安和他一樣是不穩定的人,是那種能夠理解不穩定之必要與無奈的人 。可現在,連她這樣的人也過得很好了。他應該為她高興,但有另一種不可理喻的懊惱騷擾著他,他想,隔了這麼多年,如果安膽敢再跟他提到「重新開始」,他就要使出這陣子堵人封口的撒手鐧:「重新開始?妳瞧瞧我,這年紀,連當大樓警衛都有問題吧。」
結果,安沒提,什麼也沒提。約莫半個鐘點的談話,安僅僅止乎禮說:局勢大不如前,暫時這樣也很好,再等等機會之類。然後,他們談到阿君,安感嘆阿君命薄,堅強抗癌至此,卻還是得宣告失敗。安說,你知道阿君一點都不把自己當病人,她興致勃勃跟人玩電腦,重拾畫筆,還說要去學義大利文……
聽起來安一點都不怕,她甚至陪阿君度過一段親密的抗癌生活,包括SARS期間陪阿君上醫院,看剛跳樓的張國榮拍的鬼片,枕頭貼著枕頭睡覺。為什麼安可以不怕?自己又為什麼想逃?他低下頭,感覺自己心肉如蝸牛般蜷縮起來,叫不動,就是叫不動。巨大而無情的死亡,他是敗兵一名。寂靜黃昏,安沒為阿君抱怨什麼,沒像阿君其他女朋友責備他薄情寡義,惟小心翼翼結論:「現在,有你陪她,應該是最好的結局了。」
兩人站起來告別。不過是剛結束下午茶的時間,外頭天色卻陰鬱得好似夜晚已然降臨。他站在醫院門口,望著安的背影漸行漸遠。「最好的結局」?這小女生當真知道人生的滋味?否則為什麼老要裝成熟地跟他說關鍵詞。「最好的結局」?他與阿君的結局,難道不應該是在辦好離婚登記走出戶政事務所的那一刻嗎?夫妻一場,斷不乾淨也就算了,誰還想出這種結局來整他,不只是關係的結局,還是生命的結局!
他回到病房,正來了護士在幫阿君做排毒處理,阿君的消化器官幾已作廢,不僅沒辦法吃,就連排出來都沒辦法。護理過後,阿君僅僅叮嚀明天父親和律師要來確認遺產與安葬的事情,便似氣力盡虛。他讓她睡下,離開病房。幾年不見阿君父親,沒想再見就此情景。阿君有記憶以來沒見過母親,父親也四處飄泊,可說是阿嬤一手養大的。這回病,她寧可讓阿嬤望穿秋水,佯裝人在國外而不敢頂著光頭病容回去看八十好幾的老阿嬤。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哀,怎麼說也只能讓那畸零人般的父親來承受。
阿君跟他在一起那麼多年,結不結婚,去不去日本,請不請客,這個父親從沒說過什麼,對他這女婿既沒表示過贊同也沒表示過反對,他甚至不確定這父親是否知道他與阿君已經離婚。明天,明天相見該以什麼心情呢?這父親想必不會安慰人,但應該也不至於落淚吧?這父親只是被動地走進病房來,跟他一樣,是的,跟他一樣,飄浮、猶豫、逃避,阿君從來不指望他們,可是,最後一關,阿君終究還是只有他們,他們逃不掉了,父親與丈夫將在這裡相會,為女兒,為妻子,為一個他們從來沒有負責過的關係收場,送行。(未完)
暮色將至
年底,初冬,寒氣教人還不太習慣,所以感到分外地冷。外頭天色陰沉沉的,林桑從衣箱裡找出厚外套,這是今年第一次穿它,但衣服是早已穿舊了。在國外那幾年,冬溫低得嚇人,即便多麼窮學生,也得常備幾件厚衣。此刻上身這件,猶記是在星期天的跳蚤市場買來的,那時他和阿君,簡單娛樂就是去逛跳蚤市場,少少錢換一整天樂趣。阿君挑東西眼光不知該說怪還是獨特,總能從一堆不起眼貨裡翻找出特別東西,且那價格通常低廉得很,彷彿除了阿君沒有人會去爭搶。那些奇奇怪怪的小配件、布料、提包,他不能同意多麼好看,但等阿君把它們裝...
作者序
(後記)
時差
寫作是件有「時差」的事,從經驗演化到寫到書,階段之間,時光從未稍停,人生變成一本書呈現讀者眼前,作者已經遠遠離開了那本書。「後記」這種東西,大約是個調節時差的救濟之舉,給作品排個時序,或給創作背景做個解說,不過,有些書時差實在太大,要做解說也難,這本書,原是這樣的性質,本無後記之心。
是在本書進入編輯作業的二○一五年末,偶然一天我路過華山光點,看見 Amy Winehouse。雖然在小說〈文青之死〉提過這個女孩,可現實生活裡,我很少在台灣聽聞她的動靜。出於一種祕密的熟悉,我更改當下行程,鑽進影院裡去看這部紀錄片。
27 Clubs,Amy 的一生,螢幕縮編為兩個小時,不過,愈短愈清楚,生命至難不在毒癮,不在酒精,而是世間好矛盾,既要人真心,然而,過分真心又讓人活不下去。現實之於牛皮之人不算什麼,厚著臉皮鐵著心腸便能無傷度日,然而,對某些靈敏之心,與現實卻一觸即碎。或有人要反問,靈敏何用?是的,無用,日常生活,靈敏驚險的生命使人頭痛,但在藝術,我們消費似地朝靈敏之心挖寶,享用其精神的纖細與劇烈……
藝術有其奢華,也有殘酷,身處其中,各憑其命。Amy Winehouse 之死,物傷其類者想必聽得懂老前輩 Tony Bennett 在片末說的話:Slow down, life teaches you how to live it if you live long enough.
二○○○年出版《島》之後,我沒有再出版短篇小說集。其間斷續寫些評論、散文、雜文,中長篇小說,至於短篇小說,一期一會,不那麼特意求寫,等到積足字數,竟然也就十來年過去。
倘若沿用前文所謂 Slow down,這本書,以時期言,可能就是我的 Slow down,或以我自己的語言,是減法。這本書裡的故事,寫得慢,離得遠,與其有我,毋寧無我,與其言愛,多為不愛,是現實人生凌駕靈敏之心;我們得先學會活得夠久,才能等看生命要教給我們什麼。
回顧來看,我不能說這是完全正確之法,但之於我是一段打回學徒的苦修之路,在重重限制下琢磨自我,在反覆練習裡推敲「出師」的可能。這一段小說路,是嚴苛,是 Slow down,是減速,是消極,然而,奇妙的是,關於小說領悟,有其命運默默生長,十來年,我多少也領受魔幻時刻,逐漸感到輕,感到自由,可以加速,可以飛,甚而我寫出了 Fight 這個字。
書中各篇,曾初刊於報紙期刊(索引如後),不過,成書之際,字詞多所修訂,篇名亦有異動。至於書名,猶豫許久,以近作「文青之死」定名,乍看之下似無連結,想想又覺可通:九則故事,儘管角色、情節有異,但大抵是內在生命與現實相互牽制或漠視的故事,症狀表現為錯誤的情感,志業的彷徨——多數文青人生正是在這兩者病去了大半。
如今文青當然不是個乾淨字,消費流行與裝腔作態使它討人厭,這本書回收此字,不是擁護,不在批判,而是想理一理文青這個字曾經乾淨的成分。是的,曾經,意味今已不存,初心已改,所以文青已老,已死——這些年,觀看同輩甚至較我年輕世代之文青變形記,不免有此感嘆,可我又偏偏不想放棄。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然而,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就莫再多煩憂;文青成為一個死字無妨,餘下來初心不改就請揮別脆弱惶惑的自我,然後,懷抱著那麼一點乾淨,繼續向前走吧。
回到 Amy Winehouse,可以說是 Amy 觸動我後記之心,我總對這樣的生命有著靈敏度,雖然我未必表現為同樣的生命,面對他/她們的夭折,除了心生不忍,我亦擔憂餘生活成一張牛皮,幸而,如今我還寫著,依然明白那些靈敏坦率之心,依然被他/她們所打動,在比往昔更深的內心。
這個更深是生命一層而又一層演化所將抵達之處,人生果實的可能,然而,在那之前,道阻且長,時代愈來愈顯奇幻,後浪前浪,新人舊人,從不間斷沖刷上岸許許多多受傷的真心,對那些飽受激擾,忍不住衝撞、叫喊的,我想說:Slow down;對那些被打擊、信心薄弱的,我想說:Get stronger.
道阻且長,讓我們一起繼續。
二○一六年一月十日
(後記)
時差
寫作是件有「時差」的事,從經驗演化到寫到書,階段之間,時光從未稍停,人生變成一本書呈現讀者眼前,作者已經遠遠離開了那本書。「後記」這種東西,大約是個調節時差的救濟之舉,給作品排個時序,或給創作背景做個解說,不過,有些書時差實在太大,要做解說也難,這本書,原是這樣的性質,本無後記之心。
是在本書進入編輯作業的二○一五年末,偶然一天我路過華山光點,看見 Amy Winehouse。雖然在小說〈文青之死〉提過這個女孩,可現實生活裡,我很少在台灣聽聞她的動靜。出於一種祕密的熟悉,我更改當下行程,鑽進影...
目錄
在幕間:一則偽評論或偽小說
暮色將至
靜到突然
天竺鼠
約會
日正當中
遷徙
小原
文青之死:A Fond Farewell
(後記)時差
在幕間:一則偽評論或偽小說
暮色將至
靜到突然
天竺鼠
約會
日正當中
遷徙
小原
文青之死:A Fond Farewell
(後記)時差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40收藏
40收藏

 60二手徵求有驚喜
60二手徵求有驚喜



 40收藏
40收藏

 60二手徵求有驚喜
60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