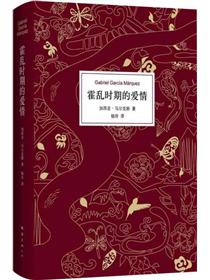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風流手記 / 執行主編 蔡逸君
一直無法忘懷寫〈公寓導遊〉,寫〈四喜憂國〉,寫〈將軍碑〉的張大春。更讓人無法釋疑的是,那個把當代小說技藝擴展演繹得無遠弗屆,引領一番時潮流風的小說家張大春,究竟要將小說書寫撥轉到哪個方向去?從很久以前,他流連在一個我們看不起眼的角落,獨自個在那處推衍摹生另一形款、恐怕連評論家都無以名之的文學創作。張大春如願了,他終於讓所有人止住了嘴巴,不知該如何看待他的「不與時人彈同調」,以史以筆記以說部為棋子,布亂了當代小說成規的局面。他清明自覺,謹慎地在小說棋盤上落下「中國流」的布局,古雅典麗的手著,讓之前爭先爭勢的「現代流」諸子,不知如何對應。這一手回到傳統的「指導棋」,其實把讀者、甚至編輯嚇得心驚驚兼頭暈暈,不知他葫蘆裡賣的什麼藥。幸虧,終於,精采,張大春自己出來說話了(他真要不說,也沒人敢問)。這些年雖然他一個下午半在電台裡說書,但說的是別人,而這回他說自己,說自己在幹些什麼新鮮好樣。「十年磨一劍,水到終渠成」讀者終於可以明白,一個創作者如何掙脫出自身極難解放的自我束縛與框架,最後自信自由隨地流淌,這是在繁華顯耀之際,足以惕勵與提升創作的高貴路徑和尊嚴展現。當然,以他說書的口白來說,就「廢話不必多說看嘛即是」,以他的律句而言,恁是「島渚十方無對人」,不如丹黃爛然「荒煙聊伴注書痕」!這樣隨手風流的張大春,看倌,您怎能不看?
要數風流,本期另一個傳奇人物《狼圖騰》的作者姜戎,也是。
三年多前當《狼》書一出,蒙古草原上的荒野狼魂從曠古裡縱躍顯現,不知震懾了多少中原柔弱的「羊群」,除了詫異,更多的是驚嘆。《狼》書封面摺口作者介紹極其簡單,說「作者不拍照、不談身世、基本拒絕媒體採訪」,這「三不」今日終於一次突破,由莊新眉採訪撰文的對話並取得同意曝光的作者身影,均是獨家披露,錯過就可惜了。
另外本期開始刊出陳家毅執筆的【新藝錄】,首篇由近年來以「爆破」美學風靡全球的蔡國強開場,介紹藝術家在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和「古根漢博物館」展出的裝置藝術;讀者雖不能親臨現場,但由攝影照片所透出來的力量,足以感受其震撼之勁道。
八月底由文建會指導,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印刻文學生活誌》共同主辦的「2008全國台灣文學營」將在清華大學展開,也是兩岸三地文學交流的匯集,誠摯邀請對藝文有興趣的各界人士一起來參與,一起歌吟且創造今朝文學的風流!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風流手記 / 執行主編 蔡逸君
一直無法忘懷寫〈公寓導遊〉,寫〈四喜憂國〉,寫〈將軍碑〉的張大春。更讓人無法釋疑的是,那個把當代小說技藝擴展演繹得無遠弗屆,引領一番時潮流風的小說家張大春,究竟要將小說書寫撥轉到哪個方向去?從很久以前,他流連在一個我們看不起眼的角落,獨自個在那處推衍摹生另一形款、恐怕連評論家都無以名之的文學創作。張大春如願了,他終於讓所有人止住了嘴巴,不知該如何看待他的「不與時人彈同調」,以史以筆記以說部為棋子,布亂了當代小說成規的局面。他清明自覺,謹慎地在小說...
章節試閱
【專輯】我所繼承的中國小說傳統 /張大春
我是一個從遠方來的客人。每一回來到內地,不論是哪一個城市,面對的是我的朋友,或者是陌生的人,尤其是連媒體記者在街上碰到都跟我握手,聽到南腔北調,我都有一種莫名的興奮。因為語言豐富的土地,方言多樣的土地,一定會有比較多元的、比較複雜的,也可能會有比較激烈振盪的語言活力。這種活力在一個開放性較強的社會,或者流通性較大的社會,當然會伴隨著大大小小的生活衝突而形成對這生活的觀察和反省。
我就是依賴這種活力討生活的一個人。今天就從近代中國一次巨大的語言活力萌生的背景上說起。
我們知道在民國初年,有一次非常大規模,而起碼在歷史影響上,我們自己覺得非常深遠的一次運動,一個「五四」愛國運動。也因為這個愛國運動,稍早已經萌芽的白話文運動甚至還侵奪了「五四」這個符號,而為我們今天所從事的文字工作奠定了新的基礎。白話文運動的細節,不容我在這裡野人獻曝。我這樣一個「依賴語言活力討生活的人」今天能夠稍微談談的,則是在白話文運動──或稱「新文學運動」之後,在現、當代文學本質上帶來的一個揮之不去的重大影響。
到今天為止,包括在座有我尊敬的作家李銳、包括我自己,我們所寫的是甚麼呢?大體而言,是小說。是甚麼樣的小說呢?一方面,從語言最表面的特徵上看,我們以為我們寫的是「現代小說」,這是有別於印象中六朝志怪、唐人傳奇,也不同於歷代文人於公牘私啟之餘撰寫而成的筆記故事。這些老古董,至少在膚廓上是用舊式語符連綴而成的,是用文言文寫的。
撇開文、白差異不說,從另一方面看,即使是宋元話本乃至於連篇成套的明、清章回故事,大致已經是語體之作了,似乎也和今天我們所寫的、而且稱之為小說的東西迥然不同。形式、情感、主題、結構,但凡是有關敘事的一切質素,兩者都不一樣。
我──還有今天也在現場的李銳、蔣韻,以及千千萬萬不在現場的華文作家──過去近百年來究竟在作甚麼呢?請容我提出一個根本的疑問:我們是不是都在用漢字寫西方小說呢?
或許,當我們在使用白話文、語體文的同時,已經自動接收了正好就是在新文學運動同時大量輸入中國的西方敘事傳統。「現代性」這個詞的意義,可能更大程度地在我們的小說之中,成為一個被辨認、被理解、被認同,以及被模仿而傳承的特質。
為什麼我說是用漢字寫的西方小說呢?首先請看:我們都是個別的作家,而個別作家擁有他個別作品的創作權。光是這一句話裡的兩個元素──我的作品是出自「我」的「創作」,這就是一個現代性的概念,而且是純粹西方輸入的概念。當然,所謂「特質」還不只如此,更多可以解析的,譬如說:在我們慣常書寫的作品之中,往往會出現大量心理的描述,用以「深化」、「支撐」、「體現」我們在過去傳統小說裡常看到的動作性的細節,作品不再滿足於戲劇性的張力或者是離奇的遇合,取而代之的是作品中的主人翁幾經人生的轉折(或許儘管相當平淡)之後,對自己的處境、命運、性格或者是情感,有著非常大的轉捩。一般我們稱這樣具有啟蒙色彩的轉捩為「神悟」、「頓悟」,一個詞epiphany。往往在故事接近尾聲之處,我們會看到一次主人翁特別的發現──這種發現當然不是動作的,不是外在的,不是殺了仇家、娶了愛人、打敗了敵人、獲得了官誥而已,而是往往跟隨著作者自己想要提出,或者是想要呼應的某種思想息息相關。
如果從這個書寫上的異變看起,也就是從將近一百年間輸入並成形的這個傳統往回看,大概它和西方近五百年來整個小說的工業的發展,以及它的終極關懷是密切不可分割的──我暫時不提它,祇在這裡稍微點明一下。對我而言,我更關心的是,過去三十多年以來,我所從事的工作,是否根本上是一個誤會呢?姑且不細論在台灣,或者其他華人地區,有多少人讀過我的作品,或者是聽過張大春這個名字,他們是不是也誤會了?大家說我是台灣小說家,中文小說家,是嗎?還是應該還我一個本來面目:我不過是一個用漢字寫西方小說,而出生在台灣的中國人呢。這是為什麼會有今天這個講題──「我所繼承的中國小說傳統」──的緣起。
在大概四歲左右罷?我的父親把我放在膝蓋上,他是一個六尺高的大漢,總在把我安置好了以後說:「咱們來說個故事吧!」一說從我四歲、五歲、六歲,說到我小學二年級,說的不是一般的故事,說的是《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等等大部頭的章回,一路說下來。我記得上小學第一天的時候,我的父親跟我說:「你已經是小學生了,今天慶祝你上小學,給你講兩回罷!」我永遠不會忘記:他講的是《水滸傳》開篇的兩回。那天聽故事的興奮遠超過我成為小學生的興奮。
當這樣的一個經驗,從四歲左右開始慢慢地進入我的生活之後,我發現有的時候我幾乎沒有辦法分辨,我今天聽到的故事跟上個月聽到的故事,甚至我今天早上和昨天下午的生活,說直了,就是那些故事會帶來種種微小的騷動,形成某些輕盈的擾亂。故事的情節應該是源出於狹小不及七、八平方米的起居室裡,夢幻的場景卻可以推拓到無限江山之外;而千古風流與萬里刀兵卻可以長驅而入,侵入我們眷村那一整排鼓盪著蟲鳥之聲的紗窗。
也許為了要理清這個錯亂,我會刻意在回憶自己生活的時候,把現實摻和到小說裡。梁山泊下朱貴放哨箭的水亭在遼寧街巷口的五洲麵包店,而大水寨就在幾百公尺以外的長春市場。似乎是為了不讓自己感覺自己在聽故事以後,跟自己的現實生活錯亂的這個動機之下,我讓它定位得更清楚──其實卻錯亂得更厲害。從這個錯亂的起點上,讓我們進入今天所要講的「我所繼承的中國小說傳統」中的第一個傳統。
第一個我要談的是「史傳」。過去大家都知道,它幾乎是研究古代文獻也好,或者是考古材料、器物的材料,只要回到古代,我們總習慣性先回到被書面語記載的史傳,它是真的嗎?我一直以為是。
在我念大學的時候,進入中文系,我的第一堂課就是《史記》,老師從本紀往下講,第一篇是〈項羽本紀〉。我的老師李毓善先生十分仔細地分析著項羽的身世、性格和種種遭際得失,以及他與劉邦的比較,闡釋了作為一個悲劇英雄的諸般特質。可是在那一堂課上,我卻受到了一個大震撼,原來我們一向以為足以相信、憑靠的史料,和我四歲、五歲的時候,那種混雜著想像、虛構和現實材料的故事情境並無二致。
《史記》如此記載:項羽被困於垓下的時候,身邊祇剩下二十八個騎士,這時他留下了那句流傳百世的名言:「天亡我,非戰之罪也!」為了表現他的善戰,還高聲說:「你們看!我一定要連勝漢軍三陣,為了你們,我要突破重圍,斬漢將、搴漢旗!」而漢軍則在三個不同的地方發動合圍,項羽的確做到了他所說的斬將搴旗,但是,之後再輾轉退到烏江西岸,在殺了百數十人之後,項羽終於在絕望中自刎了。
接下來項王幾乎是被分屍的。可是這一段經常讓我納悶。因為現場從高坡之上下來,到他整個軍隊被殲滅,他自己被分屍,這一整個兒的過程是在哪一個原始的材料上有記載呢?在漢武帝那個時代,司馬遷靠著什麼樣的現場材料得知項羽說過那些話,做過那些動作,當時沒有錄音筆,沒有攝影機,它是哪來的?我的老師說,這就是史家「操縱之筆」,這個對我來說是太不可思議的,司馬遷跟我們這一行的人說來實在太像了。然而,這個〈項羽本紀〉絕對不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次「操縱之筆」。我甚至覺得當一個史家在描述歷史現場諸般細節的時候,根本不需要實證,以「國史」如此慎重的載記,仍然允許史官運用各種材料,以及技法,來發動一個具有現場感、臨即感的故事。所以我們的史傳從最基礎的表現上,就認同一個自我悖反的努力:以虛擬之筆還原現實。不管《史記》或者日後的史傳裡,到底有多少內容看似無根底、無來歷,可疑,至少大約可以這樣去判斷,中國的史傳是容許摻雜著史傳作者的虛擬之筆的。
第二個對我來講也一樣構成震撼,而且有強烈影響的,來自於「說部」。不管從長篇章回,或者是筆記小品,包括《客窗閒話》、《子不語》到《三言二拍》、《聊齋誌異》這一類的作品,不論是來自曲藝,或者是來自連伴奏樂器都沒有的東西,說部它大概都分享著一種奇特的氛圍,我特別想強調的就是我的老師叫作高陽,是寫歷史小說的一位作家。
高陽有一天喝了酒,喝得差不多了,就跟我說:「你知道嗎?我們現在寫小說,比不上人家講書的,也比不上搞說唱的那些人。表面上看起來,我們讀了些書,能夠掌握史料,工夫深的還能作些小考證;可是,我們實在不能跟『人家』比。」不能比說書人?這種話突然出在高陽嘴裡是不可思議的,對他而言,當代還有誰能跟他談歷史小說的表現藝術呢?他本來是在吹牛的,吹著吹著,居然說起我們比不上說書人來了,接著他又說起揚州出了一個說書人。
他說那位揚州人有一天說書了,說的是〈武十回〉,就是《水滸傳》裡以武松為主角的故事。而且這個說書人特別有名的段子就是「獅子樓」──獅子橋前酒樓的一個簡稱。說書人把它簡稱為獅子樓。這就回到《水滸傳》的文本,在文本裡,武松殺嫂,為兄報仇,這一整個段落並不長。換言之,一個定本的《水滸傳》,按照一字不漏地說,兩三段說完。但是說書人有自己的門道,高陽所說的揚州的說書人,有一天坐在書場裡,說:「今天說到這兒,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他說到了武松一抬腿,要進獅子橋前酒樓,見西門慶,他能殺得西門慶嗎?各位去翻一翻《水滸傳》,這一次說書人沒停在回目分隔之處,他停在準備要錢的地方,就這樣,今天不說了,要聽明天再來。
說書人一回頭到後台,來了個人,先拱手捧上一包銀子,說我是你的粉絲,特別喜歡聽你的武松打西門慶,可是我是個商人,我今天要趕到杭州去做生意,我去一天回一天,辦一天事,共三天。你好不好給拖一拖,三天以後我回來了,如果能讓我聽到了武松殺西門慶,我再給你原樣的一包銀子。
據高陽說,三天以後那說書人驚堂木一拍,開場講了,商人也回來坐在那兒──「話說武松登登登就上樓了!」這中間有三天的時間。高陽跟我說,你知道他怎麼辦到的?我說我不知道。我說你知道嗎?他說我也不知道。高陽告訴我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沒有另外一個說書人,能知道這說書人是怎麼拖過那三天的──也許我們還可以想像,但凡現場有其必要,某個說書人甚至可以丟本子拖過十天。可是無論如何這個說書人的活兒,不會有第二個人知道。我就幻想,說不定說書人一回頭到第二天一拍驚堂木,要上樓的時候,突然一抬腿,後面有人喊了一聲「武二哥!」
我在一本小說論《小說稗類》裡面,曾經以李逵獨劈羅真人的例子,宋江派李逵陪著戴宗下山,中間就發生了枝枝節節的事,李逵去管閒事。我就納悶為什麼中間會冒出跟正文無關的段子,我回頭想,這個羅真人,很有可能就是現在在我們台灣很流行的大法會主講人。一場法會要開講了,有各種奇詭的設計,會讓現場觀眾產生類似法力幻覺的布置。比方說:活佛一進場,偌大一個體育館頓時涼爽起來,沒有人計較這是忽然把冷氣開大的效果,還以為是活佛帶來了滿室清涼。這種大法會讓我想起來:也許羅真人這個段子的來歷或靈感,就是千年以前的某個說書人,對他周遭所發生的這種場面的一個小小的嘲弄,我們讀到羅真人如何施展法術的時候,說不定就已經遁入《水滸傳》的作者在第一度的生活經驗裡面所接觸到的實務,而產生了一種同理可證之感。後世的讀者只知道李逵脾氣火爆,遷怒要劈羅真人,而真正的羅真人到底是什麼背景?早就已經失去了。
我之所以這樣說,回到了說書人的身上去討論一個敘事,我想特別強調一點,也就是跟剛才的史傳略有不同的,是我認為中國的小說還有一個特色,就是它不是一個單一的作者,運用一個單一的文本,形成一個單一的創作所有權,甚至它跟個人創造這幾個形而上的概念,個性創造這幾個概念是無關的。它是你用,我也可以用,武林、江湖、門派、寶劍以及技擊之術,通通是各代作者、講者彼此分享的。
說部的作者一向不以為自己擁有或獨斷了作品的內容,也不以他人運用了自己的「創作」元素為忤,同時也不認為自己借用了前人或同行的文本作為材料就是甚麼抄襲剽竊。在這個我們姑且可以泛稱之為「民間」的敘事場域裡面,情節、人物、道具通通是可以相互流通而無礙的。
相互流通而無礙的作品是不講究創作權的,「創作」祇是個人融入一個巨大敘事傳統的小小步伐。那麼,會有人不甘心嗎?會有人覺得:創作活動裡的那個「我」,更應該被認識嗎?也許,在不同身世、背景、價值觀的書寫者身上,我們能夠看到不一樣的關切。
這就引起我們注意到了第三個傳統。中國小說或者中國的敘事傳統裡,還有一個我認為,多年以來沒有被大家注意──也許注意到了,但也不把它當做是一個顯著重要的領域:「筆記」。我所知道的台灣的史學界,在過去十年間,很多學者付出相當多個別的努力,不約而同地注意到歷代流傳的「邊際材料」──筆記。
當我們打開那些筆記,一定會感受撲鼻而來的酸味。說句不同於化學家定義的話:筆記基本上是「酸性」的產物。為什麼酸呢?我們注意到寫筆記的人,大部分筆記作者,我所讀到的,要不就都是考場不得進取的讀書人,要不就是公餘賦閒的佐吏,要不就是退休致仕的官僚。他們能「文」,也就是有書寫的能力。但是,在劉勰所謂「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文心雕龍‧宗經第三》)以外,應該還有經書以外的內容,具有「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這樣的性質。
筆記的作者可以議論時事,發表公共言論,不過,他們更可能處身於大歷史的角落之中,擷取些「大敘事」(grand narrative)所無暇顧及的瑣碎。我曾經在一篇討論筆記小說的文字裡如此寫道:「中國古典之中的筆記何啻萬千?述史者有之,論文者有之,研經者有之,記實者有之。異方殊俗之珍聞軼事者,輒筆而記之;騷人墨客之趣言妙行者,輒筆而記之;某山某水有奇石怪木者,某詩某曲有另字旁腔者,亦不得不筆而記之。王公貴族、是不免要入筆記的,販夫走卒、妖僧俠丐也往往廁身其間,點綴著一則又一則動人心弦的人間燈火。筆記之龐雜、浩瀚,之琳瑯滿目、鉅細靡遺,連『百科全書』一詞皆不足以名狀。總的看來,筆記可以說就是一套歷代中國知識分子眼中的生活總志。」
然而之所以酸,乃在於這種生活總志與廟堂經典的旨趣不能相容──它是「野」的,也是「在野」的。這些寫筆記的人都有兩個基本心態,第一個要傳。即使不能赴會於廟堂經典,然而一旦成為文字,就有流傳的機會,就有「為後世所見」的機會。
清人筆記裡有這麼一則,說的是康熙朝在京師有一群詩友,經常做文酒之會,他們是查夏重、姜西溟、唐東江、湯西崖、宮恕堂、史蕉飲等人。這些人聚在一起,常相互期勉:「吾輩將來人各有集,傳不傳?未可知;惟彼此牽綴姓氏於集中,百年之後,一人傳而接傳矣!」這不僅僅是好名而已,恐怕正道出了藉由書寫而得以與史傳主流分庭抗禮的一種期許。這和前面所說的民間說部,恰恰是兩種不同的創作態度。撰寫筆記的作者,往往希望藉由筆下所記的故實,而得以名其人。然而,筆記作者還可能有不止於揚一己之名聲於後世者的寫作動機。我所謂另一個基本心態就是他們在「史外立史」甚至於「史外造史」的企圖。
我們知道在南宋,這個國度是很怪的,從康王渡江以後,準備定鼎南京,然而不到一年,就被揈到臨安去。南宋在杭州有根據地,在溫州也有根據地,在金人無暇同理管轄的許多小城市都還保有統治權,但到底它有多少領土,幾乎可以說是不明確的。質言之:南宋是一個不知道自己擁有多少國土的國家。可是北方呢?金朝的統治者立國以後,就開始打一個算盤,他們認為要統治漢人,得用漢人那一套。所以金人大量起用沒有南遷的士人,而且發展儒學,那一套儒學因為漢人歷史正統的關係,所以到現在還必須依靠非常少數的考古材料去建構。
南宋既然是這樣一個偏安的局面──老實說,說偏安都有點慚愧,應該說是「碎安」──可是卻出現了許多筆記,在討論、追憶、補述北宋神宗、宋哲宗的時候,就是北宋中期,文化活動最劇烈的時期,有一個現象很有意思,我稱之為「人人爭說蘇東坡」。蘇東坡在他自己的時代,並沒有為自己打造任何神話,反而是在他過世之後,他的弟子,他的弟子的弟子,以及渡江之後,南宋的諸賢不斷地複製出來的一個具有輝煌、鼎盛的光環的偉大文教時代,有人也因此而發明亦發揚了一套「正統論」。
在我看來,甚至不乏像司馬遷寫項羽那種筆法的,安插一些情節,讓這些情節歸屬於某一個偉大的人物。在此,讓我們想起蘇東坡……
【特稿】穿越曠古之《狼圖騰》姜戎專訪 /上海‧莊新眉‧採訪撰文
開始注意到《狼圖騰》這本小說還是因為每回進入書店它總在最顯眼的位置,不論在上海還是北京,一概成落的堆著,胸有成足地展示它熱銷的身分。可我幾回經過總提不起特別的興趣,畢竟我是一個看慣張愛玲、三毛和王安憶的女子,《狼圖騰》這樣的名字和書封面那雙綠瑩瑩的狼眼睛,對我來說,顯得太野太遙遠。
也是偶然,我在幾份英美和中國的報章上讀到幾篇《狼圖騰》的書評,又在網上看網民們激情地討論,就這麼打翻成見被引著讀起 。
姜戎顯然是個好說書人,狼和草原的內涵遠比我以為的野蠻爭奪強悍來得豐富(雖然我無可避免地對於暴力血腥的捕獵殺敵一目十行飛過),但越讀下去我越發覺《狼圖騰》說的其實不是遙遠的蒙古族故事,而是每一針都扎在皮肉裡一樣息息相關的我的故事,也是這樣心中被打出了一竿子疑問和情緒。
幾經周折,終於取得訪談姜戎的機會,感謝北大中文系陳曉明教授的協助。
那天北京的風沙刮得不小,姜戎和我們約見的地點在鳥巢斜對角一家四星酒店裡的茶館。在茶館門口,姜戎親切地和我們握手招呼,他穿著斯文保守的襯衫西褲,臉色略顯蒼白疲憊,但還是遮蓋不住他的一雙眼睛,那是一雙像狼一樣的眼睛,細長而精神。我感覺到,眼前這個人既非道貌岸然也沒有故弄玄虛,卻有一種高深莫測的氣質。
他像個熟客招待我們進了茶館,包廂垂著珠簾隔開了紛擾沙塵,起初姜戎還有幾分拘謹,隨著問題接力賽似的被丟出,他漸漸行雲流水滔滔不絕,像個習慣給人傳道授業解惑的老師,也像《狼圖騰》裡那個能說會辯的陳陣,我的問題就像一個個擲向水壩的炸彈,不斷地引起了洩洪似的反應,說到興頭上,姜戎就像個飲起酒來欲罷不能的蒙古大漢。待我們都感到言無不盡了,才驚覺已經日落三竿,知道了餓,便邀姜戎一起晚餐,他說:「那,我和我太太問一聲。」拿起手機撥通,他的語調甚是溫柔恩愛,和先前氣霸山河的模樣真不能聯想。掛上電話,姜戎帶上棒球帽,領我們到一家簡單的韓國餐館,飯後,才在夜色中道別。
寫完訪談的同時,我再度拿起《狼圖騰》翻看,內心仍有強烈的矛盾。中華文化的各個角落仍不乏順從服眾的漢羊,他們習慣了被人以家畜性的方式對待,往往越是在社會底層的人,越是沒有意識地接受,也越沒有自保的能力,教人恨不得立馬灌輸他們多分自主自強,不這麼恭敬地被驅使欺侮;然而,另一方面,在中國的大城小村不時可見宣傳大有為政府的標語旗幟,在北京奧運臨近的當下,更是充斥著表揚民族精神愛我大中國的宣傳,這要人不禁憂心,如若中國人都像狼學習,中國會不會據此名正言順地擴張霸道呢?人們真的能在學習狼圖騰的同時不沾一絲狼的野性嗎?我背脊發涼地在心中打下疑問……(未完,全文請見60期《印刻文學生活誌》)
【專輯】我所繼承的中國小說傳統 /張大春
我是一個從遠方來的客人。每一回來到內地,不論是哪一個城市,面對的是我的朋友,或者是陌生的人,尤其是連媒體記者在街上碰到都跟我握手,聽到南腔北調,我都有一種莫名的興奮。因為語言豐富的土地,方言多樣的土地,一定會有比較多元的、比較複雜的,也可能會有比較激烈振盪的語言活力。這種活力在一個開放性較強的社會,或者流通性較大的社會,當然會伴隨著大大小小的生活衝突而形成對這生活的觀察和反省。
我就是依賴這種活力討生活的一個人。今天就從近代中國一次巨大的語言活力萌生的背...
目錄
【專輯】我所繼承的中國小說傳統 /張大春
我是一個從遠方來的客人。每一回來到內地,不論是哪一個城市,面對的是我的朋友,或者是陌生的人,尤其是連媒體記者在街上碰到都跟我握手,聽到南腔北調,我都有一種莫名的興奮。因為語言豐富的土地,方言多樣的土地,一定會有比較多元的、比較複雜的,也可能會有比較激烈振盪的語言活力。這種活力在一個開放性較強的社會,或者流通性較大的社會,當然會伴隨著大大小小的生活衝突而形成對這生活的觀察和反省。
我就是依賴這種活力討生活的一個人。今天就從近代中國一次巨大的語言活力萌生的背景上說起。
我們知道在民國初年,有一次非常大規模,而起碼在歷史影響上,我們自己覺得非常深遠的一次運動,一個「五四」愛國運動。也因為這個愛國運動,稍早已經萌芽的白話文運動甚至還侵奪了「五四」這個符號,而為我們今天所從事的文字工作奠定了新的基礎。白話文運動的細節,不容我在這裡野人獻曝。我這樣一個「依賴語言活力討生活的人」今天能夠稍微談談的,則是在白話文運動──或稱「新文學運動」之後,在現、當代文學本質上帶來的一個揮之不去的重大影響。
到今天為止,包括在座有我尊敬的作家李銳、包括我自己,我們所寫的是甚麼呢?大體而言,是小說。是甚麼樣的小說呢?一方面,從語言最表面的特徵上看,我們以為我們寫的是「現代小說」,這是有別於印象中六朝志怪、唐人傳奇,也不同於歷代文人於公牘私啟之餘撰寫而成的筆記故事。這些老古董,至少在膚廓上是用舊式語符連綴而成的,是用文言文寫的。
撇開文、白差異不說,從另一方面看,即使是宋元話本乃至於連篇成套的明、清章回故事,大致已經是語體之作了,似乎也和今天我們所寫的、而且稱之為小說的東西迥然不同。形式、情感、主題、結構,但凡是有關敘事的一切質素,兩者都不一樣。
我──還有今天也在現場的李銳、蔣韻,以及千千萬萬不在現場的華文作家──過去近百年來究竟在作甚麼呢?請容我提出一個根本的疑問:我們是不是都在用漢字寫西方小說呢?
或許,當我們在使用白話文、語體文的同時,已經自動接收了正好就是在新文學運動同時大量輸入中國的西方敘事傳統。「現代性」這個詞的意義,可能更大程度地在我們的小說之中,成為一個被辨認、被理解、被認同,以及被模仿而傳承的特質。
為什麼我說是用漢字寫的西方小說呢?首先請看:我們都是個別的作家,而個別作家擁有他個別作品的創作權。光是這一句話裡的兩個元素──我的作品是出自「我」的「創作」,這就是一個現代性的概念,而且是純粹西方輸入的概念。當然,所謂「特質」還不只如此,更多可以解析的,譬如說:在我們慣常書寫的作品之中,往往會出現大量心理的描述,用以「深化」、「支撐」、「體現」我們在過去傳統小說裡常看到的動作性的細節,作品不再滿足於戲劇性的張力或者是離奇的遇合,取而代之的是作品中的主人翁幾經人生的轉折(或許儘管相當平淡)之後,對自己的處境、命運、性格或者是情感,有著非常大的轉捩。一般我們稱這樣具有啟蒙色彩的轉捩為「神悟」、「頓悟」,一個詞epiphany。往往在故事接近尾聲之處,我們會看到一次主人翁特別的發現──這種發現當然不是動作的,不是外在的,不是殺了仇家、娶了愛人、打敗了敵人、獲得了官誥而已,而是往往跟隨著作者自己想要提出,或者是想要呼應的某種思想息息相關。
如果從這個書寫上的異變看起,也就是從將近一百年間輸入並成形的這個傳統往回看,大概它和西方近五百年來整個小說的工業的發展,以及它的終極關懷是密切不可分割的──我暫時不提它,祇在這裡稍微點明一下。對我而言,我更關心的是,過去三十多年以來,我所從事的工作,是否根本上是一個誤會呢?姑且不細論在台灣,或者其他華人地區,有多少人讀過我的作品,或者是聽過張大春這個名字,他們是不是也誤會了?大家說我是台灣小說家,中文小說家,是嗎?還是應該還我一個本來面目:我不過是一個用漢字寫西方小說,而出生在台灣的中國人呢。這是為什麼會有今天這個講題──「我所繼承的中國小說傳統」──的緣起。
在大概四歲左右罷?我的父親把我放在膝蓋上,他是一個六尺高的大漢,總在把我安置好了以後說:「咱們來說個故事吧!」一說從我四歲、五歲、六歲,說到我小學二年級,說的不是一般的故事,說的是《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等等大部頭的章回,一路說下來。我記得上小學第一天的時候,我的父親跟我說:「你已經是小學生了,今天慶祝你上小學,給你講兩回罷!」我永遠不會忘記:他講的是《水滸傳》開篇的兩回。那天聽故事的興奮遠超過我成為小學生的興奮。
當這樣的一個經驗,從四歲左右開始慢慢地進入我的生活之後,我發現有的時候我幾乎沒有辦法分辨,我今天聽到的故事跟上個月聽到的故事,甚至我今天早上和昨天下午的生活,說直了,就是那些故事會帶來種種微小的騷動,形成某些輕盈的擾亂。故事的情節應該是源出於狹小不及七、八平方米的起居室裡,夢幻的場景卻可以推拓到無限江山之外;而千古風流與萬里刀兵卻可以長驅而入,侵入我們眷村那一整排鼓盪著蟲鳥之聲的紗窗。
也許為了要理清這個錯亂,我會刻意在回憶自己生活的時候,把現實摻和到小說裡。梁山泊下朱貴放哨箭的水亭在遼寧街巷口的五洲麵包店,而大水寨就在幾百公尺以外的長春市場。似乎是為了不讓自己感覺自己在聽故事以後,跟自己的現實生活錯亂的這個動機之下,我讓它定位得更清楚──其實卻錯亂得更厲害。從這個錯亂的起點上,讓我們進入今天所要講的「我所繼承的中國小說傳統」中的第一個傳統。
第一個我要談的是「史傳」。過去大家都知道,它幾乎是研究古代文獻也好,或者是考古材料、器物的材料,只要回到古代,我們總習慣性先回到被書面語記載的史傳,它是真的嗎?我一直以為是。
在我念大學的時候,進入中文系,我的第一堂課就是《史記》,老師從本紀往下講,第一篇是〈項羽本紀〉。我的老師李毓善先生十分仔細地分析著項羽的身世、性格和種種遭際得失,以及他與劉邦的比較,闡釋了作為一個悲劇英雄的諸般特質。可是在那一堂課上,我卻受到了一個大震撼,原來我們一向以為足以相信、憑靠的史料,和我四歲、五歲的時候,那種混雜著想像、虛構和現實材料的故事情境並無二致。
《史記》如此記載:項羽被困於垓下的時候,身邊祇剩下二十八個騎士,這時他留下了那句流傳百世的名言:「天亡我,非戰之罪也!」為了表現他的善戰,還高聲說:「你們看!我一定要連勝漢軍三陣,為了你們,我要突破重圍,斬漢將、搴漢旗!」而漢軍則在三個不同的地方發動合圍,項羽的確做到了他所說的斬將搴旗,但是,之後再輾轉退到烏江西岸,在殺了百數十人之後,項羽終於在絕望中自刎了。
接下來項王幾乎是被分屍的。可是這一段經常讓我納悶。因為現場從高坡之上下來,到他整個軍隊被殲滅,他自己被分屍,這一整個兒的過程是在哪一個原始的材料上有記載呢?在漢武帝那個時代,司馬遷靠著什麼樣的現場材料得知項羽說過那些話,做過那些動作,當時沒有錄音筆,沒有攝影機,它是哪來的?我的老師說,這就是史家「操縱之筆」,這個對我來說是太不可思議的,司馬遷跟我們這一行的人說來實在太像了。然而,這個〈項羽本紀〉絕對不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次「操縱之筆」。我甚至覺得當一個史家在描述歷史現場諸般細節的時候,根本不需要實證,以「國史」如此慎重的載記,仍然允許史官運用各種材料,以及技法,來發動一個具有現場感、臨即感的故事。所以我們的史傳從最基礎的表現上,就認同一個自我悖反的努力:以虛擬之筆還原現實。不管《史記》或者日後的史傳裡,到底有多少內容看似無根底、無來歷,可疑,至少大約可以這樣去判斷,中國的史傳是容許摻雜著史傳作者的虛擬之筆的。
第二個對我來講也一樣構成震撼,而且有強烈影響的,來自於「說部」。不管從長篇章回,或者是筆記小品,包括《客窗閒話》、《子不語》到《三言二拍》、《聊齋誌異》這一類的作品,不論是來自曲藝,或者是來自連伴奏樂器都沒有的東西,說部它大概都分享著一種奇特的氛圍,我特別想強調的就是我的老師叫作高陽,是寫歷史小說的一位作家。
高陽有一天喝了酒,喝得差不多了,就跟我說:「你知道嗎?我們現在寫小說,比不上人家講書的,也比不上搞說唱的那些人。表面上看起來,我們讀了些書,能夠掌握史料,工夫深的還能作些小考證;可是,我們實在不能跟『人家』比。」不能比說書人?這種話突然出在高陽嘴裡是不可思議的,對他而言,當代還有誰能跟他談歷史小說的表現藝術呢?他本來是在吹牛的,吹著吹著,居然說起我們比不上說書人來了,接著他又說起揚州出了一個說書人。
他說那位揚州人有一天說書了,說的是〈武十回〉,就是《水滸傳》裡以武松為主角的故事。而且這個說書人特別有名的段子就是「獅子樓」──獅子橋前酒樓的一個簡稱。說書人把它簡稱為獅子樓。這就回到《水滸傳》的文本,在文本裡,武松殺嫂,為兄報仇,這一整個段落並不長。換言之,一個定本的《水滸傳》,按照一字不漏地說,兩三段說完。但是說書人有自己的門道,高陽所說的揚州的說書人,有一天坐在書場裡,說:「今天說到這兒,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他說到了武松一抬腿,要進獅子橋前酒樓,見西門慶,他能殺得西門慶嗎?各位去翻一翻《水滸傳》,這一次說書人沒停在回目分隔之處,他停在準備要錢的地方,就這樣,今天不說了,要聽明天再來。
說書人一回頭到後台,來了個人,先拱手捧上一包銀子,說我是你的粉絲,特別喜歡聽你的武松打西門慶,可是我是個商人,我今天要趕到杭州去做生意,我去一天回一天,辦一天事,共三天。你好不好給拖一拖,三天以後我回來了,如果能讓我聽到了武松殺西門慶,我再給你原樣的一包銀子。
據高陽說,三天以後那說書人驚堂木一拍,開場講了,商人也回來坐在那兒──「話說武松登登登就上樓了!」這中間有三天的時間。高陽跟我說,你知道他怎麼辦到的?我說我不知道。我說你知道嗎?他說我也不知道。高陽告訴我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沒有另外一個說書人,能知道這說書人是怎麼拖過那三天的──也許我們還可以想像,但凡現場有其必要,某個說書人甚至可以丟本子拖過十天。可是無論如何這個說書人的活兒,不會有第二個人知道。我就幻想,說不定說書人一回頭到第二天一拍驚堂木,要上樓的時候,突然一抬腿,後面有人喊了一聲「武二哥!」
我在一本小說論《小說稗類》裡面,曾經以李逵獨劈羅真人的例子,宋江派李逵陪著戴宗下山,中間就發生了枝枝節節的事,李逵去管閒事。我就納悶為什麼中間會冒出跟正文無關的段子,我回頭想,這個羅真人,很有可能就是現在在我們台灣很流行的大法會主講人。一場法會要開講了,有各種奇詭的設計,會讓現場觀眾產生類似法力幻覺的布置。比方說:活佛一進場,偌大一個體育館頓時涼爽起來,沒有人計較這是忽然把冷氣開大的效果,還以為是活佛帶來了滿室清涼。這種大法會讓我想起來:也許羅真人這個段子的來歷或靈感,就是千年以前的某個說書人,對他周遭所發生的這種場面的一個小小的嘲弄,我們讀到羅真人如何施展法術的時候,說不定就已經遁入《水滸傳》的作者在第一度的生活經驗裡面所接觸到的實務,而產生了一種同理可證之感。後世的讀者只知道李逵脾氣火爆,遷怒要劈羅真人,而真正的羅真人到底是什麼背景?早就已經失去了。
我之所以這樣說,回到了說書人的身上去討論一個敘事,我想特別強調一點,也就是跟剛才的史傳略有不同的,是我認為中國的小說還有一個特色,就是它不是一個單一的作者,運用一個單一的文本,形成一個單一的創作所有權,甚至它跟個人創造這幾個形而上的概念,個性創造這幾個概念是無關的。它是你用,我也可以用,武林、江湖、門派、寶劍以及技擊之術,通通是各代作者、講者彼此分享的。
說部的作者一向不以為自己擁有或獨斷了作品的內容,也不以他人運用了自己的「創作」元素為忤,同時也不認為自己借用了前人或同行的文本作為材料就是甚麼抄襲剽竊。在這個我們姑且可以泛稱之為「民間」的敘事場域裡面,情節、人物、道具通通是可以相互流通而無礙的。
相互流通而無礙的作品是不講究創作權的,「創作」祇是個人融入一個巨大敘事傳統的小小步伐。那麼,會有人不甘心嗎?會有人覺得:創作活動裡的那個「我」,更應該被認識嗎?也許,在不同身世、背景、價值觀的書寫者身上,我們能夠看到不一樣的關切。
這就引起我們注意到了第三個傳統。中國小說或者中國的敘事傳統裡,還有一個我認為,多年以來沒有被大家注意──也許注意到了,但也不把它當做是一個顯著重要的領域:「筆記」。我所知道的台灣的史學界,在過去十年間,很多學者付出相當多個別的努力,不約而同地注意到歷代流傳的「邊際材料」──筆記。
當我們打開那些筆記,一定會感受撲鼻而來的酸味。說句不同於化學家定義的話:筆記基本上是「酸性」的產物。為什麼酸呢?我們注意到寫筆記的人,大部分筆記作者,我所讀到的,要不就都是考場不得進取的讀書人,要不就是公餘賦閒的佐吏,要不就是退休致仕的官僚。他們能「文」,也就是有書寫的能力。但是,在劉勰所謂「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文心雕龍‧宗經第三》)以外,應該還有經書以外的內容,具有「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這樣的性質。
筆記的作者可以議論時事,發表公共言論,不過,他們更可能處身於大歷史的角落之中,擷取些「大敘事」(grand narrative)所無暇顧及的瑣碎。我曾經在一篇討論筆記小說的文字裡如此寫道:「中國古典之中的筆記何啻萬千?述史者有之,論文者有之,研經者有之,記實者有之。異方殊俗之珍聞軼事者,輒筆而記之;騷人墨客之趣言妙行者,輒筆而記之;某山某水有奇石怪木者,某詩某曲有另字旁腔者,亦不得不筆而記之。王公貴族、是不免要入筆記的,販夫走卒、妖僧俠丐也往往廁身其間,點綴著一則又一則動人心弦的人間燈火。筆記之龐雜、浩瀚,之琳瑯滿目、鉅細靡遺,連『百科全書』一詞皆不足以名狀。總的看來,筆記可以說就是一套歷代中國知識分子眼中的生活總志。」
然而之所以酸,乃在於這種生活總志與廟堂經典的旨趣不能相容──它是「野」的,也是「在野」的。這些寫筆記的人都有兩個基本心態,第一個要傳。即使不能赴會於廟堂經典,然而一旦成為文字,就有流傳的機會,就有「為後世所見」的機會。
清人筆記裡有這麼一則,說的是康熙朝在京師有一群詩友,經常做文酒之會,他們是查夏重、姜西溟、唐東江、湯西崖、宮恕堂、史蕉飲等人。這些人聚在一起,常相互期勉:「吾輩將來人各有集,傳不傳?未可知;惟彼此牽綴姓氏於集中,百年之後,一人傳而接傳矣!」這不僅僅是好名而已,恐怕正道出了藉由書寫而得以與史傳主流分庭抗禮的一種期許。這和前面所說的民間說部,恰恰是兩種不同的創作態度。撰寫筆記的作者,往往希望藉由筆下所記的故實,而得以名其人。然而,筆記作者還可能有不止於揚一己之名聲於後世者的寫作動機。我所謂另一個基本心態就是他們在「史外立史」甚至於「史外造史」的企圖。
我們知道在南宋,這個國度是很怪的,從康王渡江以後,準備定鼎南京,然而不到一年,就被揈到臨安去。南宋在杭州有根據地,在溫州也有根據地,在金人無暇同理管轄的許多小城市都還保有統治權,但到底它有多少領土,幾乎可以說是不明確的。質言之:南宋是一個不知道自己擁有多少國土的國家。可是北方呢?金朝的統治者立國以後,就開始打一個算盤,他們認為要統治漢人,得用漢人那一套。所以金人大量起用沒有南遷的士人,而且發展儒學,那一套儒學因為漢人歷史正統的關係,所以到現在還必須依靠非常少數的考古材料去建構。
南宋既然是這樣一個偏安的局面──老實說,說偏安都有點慚愧,應該說是「碎安」──可是卻出現了許多筆記,在討論、追憶、補述北宋神宗、宋哲宗的時候,就是北宋中期,文化活動最劇烈的時期,有一個現象很有意思,我稱之為「人人爭說蘇東坡」。蘇東坡在他自己的時代,並沒有為自己打造任何神話,反而是在他過世之後,他的弟子,他的弟子的弟子,以及渡江之後,南宋的諸賢不斷地複製出來的一個具有輝煌、鼎盛的光環的偉大文教時代,有人也因此而發明亦發揚了一套「正統論」。
在我看來,甚至不乏像司馬遷寫項羽那種筆法的,安插一些情節,讓這些情節歸屬於某一個偉大的人物。在此,讓我們想起蘇東坡……
【特稿】穿越曠古之《狼圖騰》姜戎專訪 /上海‧莊新眉‧採訪撰文
開始注意到《狼圖騰》這本小說還是因為每回進入書店它總在最顯眼的位置,不論在上海還是北京,一概成落的堆著,胸有成足地展示它熱銷的身分。可我幾回經過總提不起特別的興趣,畢竟我是一個看慣張愛玲、三毛和王安憶的女子,《狼圖騰》這樣的名字和書封面那雙綠瑩瑩的狼眼睛,對我來說,顯得太野太遙遠。
也是偶然,我在幾份英美和中國的報章上讀到幾篇《狼圖騰》的書評,又在網上看網民們激情地討論,就這麼打翻成見被引著讀起 。
姜戎顯然是個好說書人,狼和草原的內涵遠比我以為的野蠻爭奪強悍來得豐富(雖然我無可避免地對於暴力血腥的捕獵殺敵一目十行飛過),但越讀下去我越發覺《狼圖騰》說的其實不是遙遠的蒙古族故事,而是每一針都扎在皮肉裡一樣息息相關的我的故事,也是這樣心中被打出了一竿子疑問和情緒。
幾經周折,終於取得訪談姜戎的機會,感謝北大中文系陳曉明教授的協助。
那天北京的風沙刮得不小,姜戎和我們約見的地點在鳥巢斜對角一家四星酒店裡的茶館。在茶館門口,姜戎親切地和我們握手招呼,他穿著斯文保守的襯衫西褲,臉色略顯蒼白疲憊,但還是遮蓋不住他的一雙眼睛,那是一雙像狼一樣的眼睛,細長而精神。我感覺到,眼前這個人既非道貌岸然也沒有故弄玄虛,卻有一種高深莫測的氣質。
他像個熟客招待我們進了茶館,包廂垂著珠簾隔開了紛擾沙塵,起初姜戎還有幾分拘謹,隨著問題接力賽似的被丟出,他漸漸行雲流水滔滔不絕,像個習慣給人傳道授業解惑的老師,也像《狼圖騰》裡那個能說會辯的陳陣,我的問題就像一個個擲向水壩的炸彈,不斷地引起了洩洪似的反應,說到興頭上,姜戎就像個飲起酒來欲罷不能的蒙古大漢。待我們都感到言無不盡了,才驚覺已經日落三竿,知道了餓,便邀姜戎一起晚餐,他說:「那,我和我太太問一聲。」拿起手機撥通,他的語調甚是溫柔恩愛,和先前氣霸山河的模樣真不能聯想。掛上電話,姜戎帶上棒球帽,領我們到一家簡單的韓國餐館,飯後,才在夜色中道別。
寫完訪談的同時,我再度拿起《狼圖騰》翻看,內心仍有強烈的矛盾。中華文化的各個角落仍不乏順從服眾的漢羊,他們習慣了被人以家畜性的方式對待,往往越是在社會底層的人,越是沒有意識地接受,也越沒有自保的能力,教人恨不得立馬灌輸他們多分自主自強,不這麼恭敬地被驅使欺侮;然而,另一方面,在中國的大城小村不時可見宣傳大有為政府的標語旗幟,在北京奧運臨近的當下,更是充斥著表揚民族精神愛我大中國的宣傳,這要人不禁憂心,如若中國人都像狼學習,中國會不會據此名正言順地擴張霸道呢?人們真的能在學習狼圖騰的同時不沾一絲狼的野性嗎?我背脊發涼地在心中打下疑問……(未完,全文請見60期《印刻文學生活誌》)
【專輯】我所繼承的中國小說傳統 /張大春
我是一個從遠方來的客人。每一回來到內地,不論是哪一個城市,面對的是我的朋友,或者是陌生的人,尤其是連媒體記者在街上碰到都跟我握手,聽到南腔北調,我都有一種莫名的興奮。因為語言豐富的土地,方言多樣的土地,一定會有比較多元的、比較複雜的,也可能會有比較激烈振盪的語言活力。這種活力在一個開放性較強的社會,或者流通性較大的社會,當然會伴隨著大大小小的生活衝突而形成對這生活的觀察和反省。
我就是依賴這種活力討生活的一個人。今天就從近代中國一次巨大的語言活力萌生的背...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雜誌商品,恕不提供10天猶豫期退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