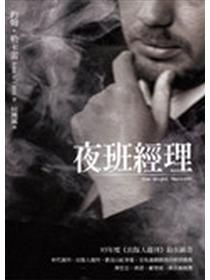簡單之人
成英姝
「沒風就好,趕上天不好,風就像刀子似的。上禮拜就趕上三、四級風,滑起來感覺有點涼,還行,颳風挺討厭的。明天就天晴了,沒有霾……」
「國內的雪我操,就前幾天滑他媽那個萬龍,盡是冰面兒,速度快點兒就收不住,那雪要鬆厚,雪板稍微一刺乎,腿不用那麼使勁兒,這冰殼子你橫著過來,就往下蹴溜……」
兩個男人坐在深夜的北太平橋下食攤上,喝著啤酒吃著炒菜,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天寒地凍,一張嘴便吐出白霧。這會兒都凌晨一點了,周遭很安靜,一個穿著毛呢大衣的女人,懷裡抱著個花瓶,搖搖晃晃地朝這兒走來,他兩目光自然地停留在她身上,畢竟這種大半夜,會來到這食攤上的,多半是些夜班計程車司機、喝完酒的醉鬼、下夜班的底層工人。
女人穿著厚呢大衣,那種落肩的,很有復古的風味,但她只是圖它的寬大,裡頭可以多穿幾件刷毛衣。她這裝束像隻胖熊,整天到處走下來,一會兒汗流浹背,一會兒又凍得簌簌顫抖,向來她應付的最低溫度也不過攝氏十度,這會兒都零下了。踱著那雙為了多穿兩雙厚毛襪而買大兩號的雪靴,網路上買的,她生得一雙大腳,女人的鞋她穿不下,買的是男人的鞋,同樣的尺碼卻要大上一些,像左右駛兩艘船,跑起來路都走不穩。
雖是寒天,一會兒室內一會兒室外,外帶上樓下樓的,東奔西走,弄得腋下汗濕的,頭皮也是汗濕的,鼻尖卻是冰凍的,腳指和腳掌也是冰凍的,半夜沒車又迷路,忘了帶酒店的電話,越走越清冷僻靜,起先是店都歇了,燈都滅了,走著走著店面都少了,人影沒蹤跡了,晃到這橋下,雨落後濕漉漉的地面,似有若無的悉悉索索人聲,漆夜裡微黃黯淡的光,沁靜空氣裡飄渺的白煙,給人鬼影幢幢的荒涼離世之感。
她坐下問道:「你們都是活人吧?」
那圓臉的男人把炒豆芽夾進嘴裡,很乾脆地答:「不是。」
她瞪了那圓臉的男人一眼,隨即慢條斯理地轉過臉,望向麵攤老闆,那是個四十出頭的男人,高高的額頭,一對劍拔弩張的濃眉,五官倒是溫文爾雅,搭上漫不經心的表情和一雙裝作收斂的銳利眼睛。
「你相信有鬼麼?」她說。
老闆笑了笑說道:「我對鬼的存在沒什麼概念,反正我是沒見過,有也可以沒有也可以,和我似乎沒啥關係。」
女人把花瓶往桌上慎重地一擱。
她想起父親生前是不信鬼的,他崇尚科學,老說只相信眼見為憑,孩子小的時候他也同他們說過聖誕老人或者狐仙那類超自然的故事的,可畢竟無傷大雅,只要孩子稍微大一些就能毫無困難地把這種便宜行事的哄弄給糾正過來。子不語怪力亂神,他既不喜歡有人在他面前提到鬼,他也不信,可他死後卻變成鬼了,他不覺得這很諷刺嗎?
父親臥病了一年,死得很突然,她信他那套科學性的講法的,人死後什麼都沒有的,那些為了死人擺弄的名堂毫無意義,為了省租冰櫃的錢,她是將他的遺體馬上火化的,告別式也擱著,再說吧!可幾天後,她下班回到家,鑰匙往玄關的櫃子上一扔,電燈一開,父親就坐在搖椅上。他有半年時間沒坐過客廳了,剛臥床的時候還能把他抱到沙發上,後來也不行了,至於這搖椅,好些年他都不坐了,怕暈,怕跌倒。
父親一直想成為作家。他是個生活很貧乏的人,大半輩子在中學裡教國文,沒有朋友,沒有什麼戲劇化的人生,不曾冒過險,也不追求什麼超乎常人的經歷,保守,一板一眼,對自己以外的事漠不關心,不知什麼原因卻以為自己通曉了人世深奧的哲理,他老在書房裡寫東西,幻想著出版一本驚世之作,可他從沒寫完,他在摸索一種繁複艱深、炫惑詭譎、難以一眼看穿的文字,把一些極其淺薄的,諸如孤獨的本質,某種能救贖一切的恢弘的美(但那究竟是什麼?),萬物通往善良的法則之類的……寫得裡頭很有一番玄虛。這是什麼道理?千方百計地把一點貧薄簡單的東西弄得繁碩複雜,再叫人百轉千迴地鬥智還原那空洞的原貌?或者這是無法還原的,只會使人掉進一個鑲滿鏡子無數岔路的迷宮,永遠看不清它本質上的粗陋。簡單的說,那就像一條平凡的下水道,關鍵不過就是牆壁上用了多高級的鑲金磁磚。
他沒能成功,他自始至終都沒能找到一種符合他理想的文字,他不是一個天才,要命的是他並不知道,他甚至沒發現他不夠努力。
可她了解他的心,他整個平庸又恥辱的人生,配不上他複雜又深邃的靈魂。
老闆把韭菜雞蛋、醬爆肉絲、包子和炒飯遞上來,她咕嘟嚥了一下口水,先前有一陣子她真餓得眼冒金星了,白天她只喝了幾杯咖啡,腦勺痛得。寒凍弄得她手心和腳底發癢,尤其是腳底,好似千百條蠕動的小蟲用牠們細尖的毛在她的腳心扭搓,可穿著幾層厚襪子和靴子不好脫下來搔,她真想哭,走了一天即使是穿平底鞋子,蹠骨也疼得要命。餓得胃裡躁攪的時候找不著吃的,難受,也莫可奈何,餓上半個鐘頭,也就過去了,不覺得對食物那麼渴望,這會兒夜深人靜了,吃食的香氣和熱氣滿臉撲上來,喚起一種淒涼的匱乏感,她連鼻子也酸了。
桌面很小,杯盤碗碟擁擠地擱在一起,胳臂都縮著不敢敞開,尤其身上一層層厚衣服肉粽一般裹著,動作與知覺格外笨拙不靈光,一個不留神磕碰了,就把那花瓶撞得搖搖晃晃,差點推倒,老闆見了,問她是不是讓他先給收起來,免得跌壞了。她婉拒了,說這是她父親生前最喜愛的一個花瓶。
也就一個極其普通的長弧形陶瓶,形狀和顏色都相當粗陋,不均勻又稀薄的綠釉彩上得隨興,面上糙礪而不光滑,倒有種豪放的味道。她說大學的時候她修了陶藝課,他父親對陶瓷藝品是相當鍾愛的,因之十分欣喜,她隨口就承諾了會親手做一個陶瓶送給他。可她向來是沒有耐性在細活上琢磨的,也從無意要去練就這一門手藝,她修這門課只是勉為其難地從必修的通識課裡挑了一個沒那麼無趣的,可也不至於有趣到生出心思去下功夫。她試過一次手拉胚就放棄了,令她震驚的慘敗,徹底控制不了那技巧和力道,弄得一塌糊塗,把胚土往上拉時一瞬間崩毀的那種充滿破壞性的衝擊感實在太糟了,很難忍受。低年級生將自己的素胚作品留在教室,高年級生會在老師的指導下替這些作品上釉,放進窯裡燒,燒好的作品就陳列在走廊的地面上,讓學生們自行回來領取。她用陶土隨意捏了一隻小馬,但看起來毋寧說更像一隻小狗。她沒領回她的小馬,而是鬼鬼祟祟地竊取了不知是誰做的花瓶。
對於偷取那個花瓶她是一點罪惡感都沒有的,放眼望去,堆在走廊上的一整堆破爛,全是些歪鼻扭嘴不像樣的垃圾,就不信有誰真當作心血寶貝,哪個不是同她一樣敷衍打發出來的?當中幾個勉強像樣的,若有本事做出這樣的東西,再重新做幾個也無妨吧?有什麼關係呢?倘使有人想偷她的小馬,她就大方地完全不介意。
她把那花瓶送給父親,他十分歡喜,愛不釋手,每見他對這花瓶充滿感情地珍愛,她多少有些心虛愧疚,她不是老練於說謊欺騙的人。
她滔滔不絕地說著,也沒想那老闆和那圓臉的男人,和另一個單眼皮的男人有沒有在聽。可她話語一歇,他們又恢復滑雪的話題了。
「我現在速度一快,控制就費勁了。那天在纜車下來靠左邊那條道,有幾個滑得好的,不行,跟不上,跟上速度就控制不了。」
「因為你腳底沒勁兒。速度起來那每個彎是給你減速的,奔下一軋雪,速度就下來了,腿上有勁的速度快了,兩下大一點彎,速度鏗地就下來了。我第一天滑,沒勁了到後來,直他媽哆嗦,加上那黑道的坡又特陡,真有點下不去。」
「下去以後重心轉不過來,感覺重心下得大,身子好像還是有點往後,壓不下去。」
「我瞧你屁股好像有點兒後坐,重心如果靠後會壓著雪板尾部,下陡坡會影響轉向,容易摔。越陡的坡重心應該比較前面,擱在腳掌上,你腿要知道怎麼使勁,使在什麼地方。」
「我現在還在腿肚子疼,雙板的技巧複雜,使的勁兒跟單板不一樣。」
她插不上話,來北京前她連雪都沒見過。她是冬天生的,因此特別喜愛冬天,可她又很怕冷,只不過,更討厭太陽。
那老闆不發一語,抽著菸,臉上有種似有若無的淡然笑容。這種天還在外頭開食攤,她覺得他也是個奇怪的人,她問他不討厭冬天麼?
「是不喜歡,」他咧嘴笑著說:「女孩兒穿得太多了。」
圓臉的男人問老闆什麼時候同他們一起去滑雪,「也該運動一下,練練腿,你不說是現在每天最大的鍛鍊就洗澡?」
「我開玩笑你還真信。」老闆笑著說。
「冬天我都不洗澡的。」單眼皮的男人說。
她聽著他們說話,是感覺其中有一種趣味的,不在內容上,是裡頭又粗礪又柔軟的起伏情調。這會兒她吃飽了,喝了點酒,身子熱起來了,腿也沒那麼痠了,腦袋不那麼轟轟作響了,她情願把煩人的事都忘了。其實她一逕這麼幹的,她面對不了、處理不來的,她就逃避去想,就像她小時候得了蛀牙,看了一回牙醫,把她嚇破膽,抵死再不去,可不看牙醫,她的蛀牙又該怎麼辦?擔心得她在棉被裡哭,覺都沒辦法睡,可她還不是過來了?蛀牙也沒讓她死,日子你不推它它也是規規矩矩望前走,一分鐘也不落下的,走到她不知不覺大了,能挺胸走進牙科,啥都不怕了,打麻醉針也好,抽神經也好,開刀、拔牙,樣樣來過。回頭看容易,可你在當中的時候,那是千難萬難的。
父親過世的事,她瞞著在美國的弟弟。但紙包不住火,她收到他的電子郵件,說要從美國回來,他沒趕上父親臨終,沒趕上父親的告別式,沒趕上父親安葬,他總要來奠祭,怎麼說他是他的親兒子。其實這些都是她自己想的,他的信她只草草瞄了幾眼,老天!因為那是一封英文信啊,一看英文她就暈。弟弟是八歲時去美國的,那個歲數明明說寫中文的能力已經跟他用了一輩子差不多了,偏偏要以電腦無法打中文為由,總是寄英文信來。說「總是」,其實二十多年來總共也只寫過六、七封。當年父母怕這個兒子受不了台灣的升學壓力,把他送到國外去。或許他們把男孩子看得重,寵愛他遠勝過對她,但無所謂,她一直把這件事想成全歸咎於他特別的笨,以他的智能,只能同老外那些傻子一起學習,國內這種對腦容量需求較高的教育他是應付不過來的。縱使他們在美國有幾個親戚,還有幾個善良的朋友,他們也不能放他一個那麼小的孩子沒有父親或母親陪在身邊,因此她的母親也一同過去,從那以後他母親便與父親漸行漸遠,一次也沒有回台灣過。她倒沒去猜測過母親是否在那兒有了別的男人,她弟弟是傻得沒有能力通風報信過的,可那重要嗎?母親是不是愛了別的男人,重要嗎?從多早開始她就不愛她的丈夫了,這說來很殘酷,卻很稀鬆平常。她估計她愛過別人,可後來也不愛了。也就這麼一回事。
她趕在弟弟回國前溜了,她不想跟他打照面。她不再是孩子,不再是年輕人,不再有力氣去往臉上堆虛假的溫情與傷感,去裝作一個通情答禮、重義又和藹的人了。
她沒回過父親出生的舊居,她父親本人也沒有,現在回來,自然是找不著原住處,那地方早都不存在,他活著的時候就很清楚。他那個時候,還叫做北平,不叫北京呢!
她回過神,聽見老闆的說話聲。「其實我挺喜歡運動的,只是不喜歡刻意的鍛煉,健身房什麼的覺得沒樂趣,我年輕時也算正經學過跳高,踢足球,還有電影學院的形體訓練,壓腿、踢腿、劈叉、大小跳啊的,強度很大的,練到下台階時後腿撐不住,只能倒著下樓梯……」
「真看不出來。」她咂了咂嘴說。
老闆呵呵笑,「歲數大了,都還給老師了。現在還是懶了,運動談不上,玩兒還行。」
「老闆表現出來的模樣你不能信,」圓臉的男人說,「他是演員出身的,他都在跟你演戲。」
「真的?他最擅長演什麼?」她興致勃勃地問圓臉的男人。
「噢,莫測高深的樣子罷!」圓臉的男人吃著花生米說。
她笑起來,轉臉問老闆:「那麼你最不想演的角色是什麼?」
老闆故作正色,一臉實在地答道:「專業的職業教育告訴我,作為一個演員應該有塑造不同角色的能力,無論什麼樣的人應該都可以勝任……但是,我想我完全理解不了的角色,沒法嘗試吧!」
「所以那是什麼?」她追問。
「女人。」老闆笑著說。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