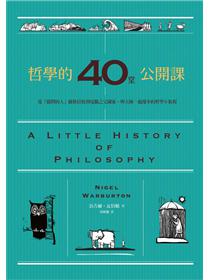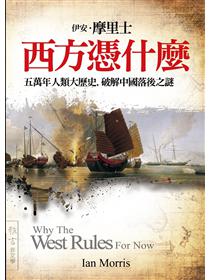我在德國看敘利亞難民 2015年6月26日,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同性伴侶有在美國任何地方結婚的權利。27日週六,我的臉書被台灣友人的彩虹旗洗版了,同一天,整個歐洲(土耳其與突尼西亞)發生了三起恐怖攻擊,身在柏林的我,因為隨機的恐怖攻擊感覺很害怕,看著臉書上歡欣的彩虹旗,我第一次覺得自己離台灣那麼遠。
敘利亞和德國並沒有那麼近,德國至今也尚未發生過恐怖攻擊,那一天是我第一次由衷地對這些不停發生的恐怖攻擊感到害怕,在難民潮佔滿媒體所有篇幅之前,我真的沒想過,原來有一塊土地,上面有一群跟你我一樣的老百姓,必須天天面對恐怖攻擊,天天都在經歷自己或親人的倖存或死亡或重傷。
我的德國房東老太太,今年八十三歲,聊天時常常開頭語是帶著詼諧口氣的:「你知道德國在二戰中戰敗了,事實上德國輸了每場戰爭…」,以及「我要有來世,一定選當永遠的不沾鍋瑞士人。」我很喜歡和她聊天聽她講那個戰爭中與戰敗的德國的歷史——她的童年與學生階段。她並不為德國辯解,卻在講到無辜的人民時總是含著眼淚。在這樣的聊天中我漸漸明白了「戰爭」——戰爭,從來不只是兩個黨派的事,在那樣的歷史洪流中,每個人都只能主動或被動被捲進去,無人能全身而退。
敘利亞的內戰,從2011年3月到現在已經四年半了,2014年隨著敘利亞反對派壯大,敘利亞人必須離開家園,在那個昔日的家園中,不論是政府軍或反對派皆四處燒殺、擄掠、虐殺、暴行、謀殺、法外處決、酷刑……,若你是個成人,你能不奮力一搏帶著你摯愛的父母、伴侶與孩童離開那樣的人間地獄嗎?
在柏林報(Berliner Zeitung)上,我讀到一篇難民的採訪,難民亞拉(Yara, 為了保護還在敘利亞的父親她不願意提供姓氏與照片)來自敘利亞西南的小城Dera,亞拉的家庭在敘利亞屬於中產家庭——父親為經濟學者,母親為教師。亞拉自己原就讀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的大學大眾傳播與教育學系,一直到了2014年5月22日亞拉家裡最小的成員——十四歲的弟弟在家門口被炸彈擊中身亡後,他們家才決定逃亡;逃亡由她的哥哥開始,現在,她的哥哥已經被安頓在雷根斯堡(德國),今年的夏天他們家終於籌到了六千美金足以讓她和母親共同逃亡,而他們的父親卻因為沒有足夠的經費只能先留在敘利亞。亞拉和她母親的逃亡歷時兩周,先由敘利亞到黎巴嫩,再乘坐超載的船抵達土耳其,到達土耳其後,他們一路從希臘─馬其頓─塞爾維亞─匈牙利─奧地利至最終的目的地德國。亞拉說,一路上他們皆受到友善的對待,除了在布達佩斯(匈牙利)時店家不願意賣水給他們。
2015年至今,已有超過四百萬敘利亞人離開自己的家園。
德國在二戰的歷史中,有機會重新思考自己。德國和他的鄰國不大相同,他們的民族性嚴謹、一絲不苟,有時也缺少一些衝動與幽默感,但是他們凡事都是認真的。德國作為歐盟的領導國家之一,它無法西裝革履地對敘利亞難民的悲劇置身事外。
當梅克爾今年六、七月對著難民的小孩說道: 「孩子,我很抱歉,德國無法讓全部的難民留下」,小孩應聲哭泣時,德國的媒體意指梅可爾太傷小孩的心了,我們看到了德國總理理性的一面。接下來她在八月打開了大門,願意承擔更多難民的責任,我們又看到了她感性的一面。
英國政治學家Anthony Glees指稱「德國就像掉了腦袋,以往德國是最嚴謹遵守規定的國家,現在德國的做法卻像只跟著自己感覺走的嬉皮」,以及「德國若自己現在不遵守規矩,整個歐盟可能要四分五裂」,我卻看到了德國在冷眼旁觀這悲劇的歐洲鄰國中,試圖給難民最實質、最大的幫助。梅克爾帶著堅定的眼神與口氣在國會說:「這(難民潮)並非德國無法勝任的工作,德國在五、六十年代處理過自己國家難民的經驗,正是用在這時候。」台下國會議員們給予熱烈的掌聲。
十年前剛到德國時,聽著日本朋友許的生日願望是世界和平,我笑他請認真許願,他正色說他是認真的,世界上還有那麼多戰爭! 我羞愧並啞口無言,因為我愚蠢到以為只有一戰或二戰才算戰爭,認為戰爭這名詞已走入歷史了。
這次的難民潮,就像戰爭的影子,蔓延到了歐洲的大門口,挑戰的是歐洲的人道精神。
梅克爾說,若我們不接納難民,我們就不是我們想像中的歐洲了。
德國預估2015年敘利亞難民申請總數可達八十萬人,是去年的四倍,德國媒體上出現了「伊斯蘭化的德國」、「德國將因此改變」這樣的標題。也聽到了梅克爾告訴人民,如果自己不上教堂不讀聖經,怎麼可以怪這些有堅貞信仰的穆斯林影響了自己的信仰?德國人是否有擔憂、有害怕?當然有,但是在社會應付不了這樣的變化之前,我遇到的德國人都堅信這是德國現在無法選擇且必須做的事。
九月初,德國的超市裡已經出現了聖誕節點心,天氣也變冷了! 希望在寒冬降臨前難民們可以有個堅固並溫暖的庇蔭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