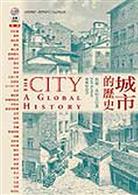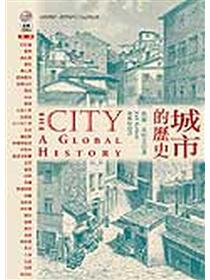一趟從奧勒岡,穿越大西部,前往南加州的絕命追殺令
沿途重重危機,遭遇各色人等……殺人的意義,為金錢,還是為兄弟?◆ 榮獲2011年加拿大總督文學獎
◆ 加拿大羅傑斯作家基金會小說獎
◆ 入圍曼布克獎、加拿大吉勒文學獎決選名單
◆ 亞馬遜網路書點編輯年度十大文學選書之一
◆ 已售出30國語言 電影盛大籌拍中
渥爾姆,你死定了!
他為什麼必須死?
有錢能使鬼推磨!
江湖上聞風喪膽的殺手希斯特兄弟,接下准將的必殺令
「你們要殺的人就是赫曼.渥爾姆!」
這個人小命不保了,但是,渥爾姆到底是誰?
顛覆硬派西部經典文學
不正經描述手足俠義的年度風雲小說荒誕滑稽、既暴力又傷感;金沙碧血,小說魅力無法擋!
「赫曼.渥爾姆死期到了!」別名「准將」的老大哥決定買兇殺人,交辦「殺人零失手」的雙槍殺手希斯特兄弟取他小命。從奧勒岡一路追殺到沙加緬度,漫漫長路惹得弟弟伊萊希斯特莫名惆悵,不禁自問「為何渥爾姆必須死?」
不像哥哥查理嗜殺成性又貪杯,儼然性情中人的伊萊,質疑自己的維生之道,也質疑他效忠的對象。伊萊自覺與查理拆夥、分道揚鑣的時候到了。就在狹路相逢時,渥爾姆聲稱他握有舉世無雙的淘金祕方。黃沙碧血的淘金場上,在准將與渥爾姆之間,向來心直手快的希斯特兄弟,上演一場逆轉命運的終極對決……
作者派崔克‧德威特以《淘金殺手》一書向經典拓荒文學致意,卻顛覆地透過弟弟伊萊主述,以惆悵省思卻反而不正經的語調書寫,在滿腹委屈的殺手眼前,不只是英雄鏢客,還有窩囊廢,有騙徒,更不乏三教九流的痞子。藉由一對血脈相連、出生入死、手足情深的殺手兄弟,一段腥風血雨、物慾橫流的旅程,令人時而辛酸,時而會心一笑。
本書風格突破,入圍曼布克獎決選外,並榮獲加拿大最高榮譽總督文學獎肯定。出版後大受讀者歡迎,至今已售出30國語言版權。
作者簡介:
派崔克‧德威特(PaickdeWitt):
著有佳評如潮的小說《洗禮》(Ablutions: Notes for a Novel)。
1975年生於加拿大卑詩省溫哥華島,曾旅居加州與華盛頓州,目前與妻兒定居奧勒岡州。曾經做過工人、店員、洗碗工和酒保等工作。
譯者簡介:
宋瑛堂
台大外文系學士,台大新聞所碩士,波特蘭大學專業文件碩士,曾任China Post記者、副採訪主任、Student Post主編等職。譯作眾多,包括《幸福的抉擇》、《大騙局》、《數位密碼》、《斷背山》…… 等。
各界推薦
媒體推薦:
好評推薦:小說家高翊峰
《淘金殺手》這部小說的敘事,有一種奇異的潔癖乾淨。共鳴情感出來的速度很直接,文字也充滿視感畫面。我不會懷疑,它可以直接改編成電影,因為角色人物立體鮮明得就像是為影像而生的,彷彿是年輕的海明威為現代好萊塢寫了一個西部拓荒的美國夢,而這故事竟然還可以幽默。
推薦序:極盡kuso能事,徒然令人噴飯
名作家馮光遠
希斯特兄弟受雇於「准將」,前往加州的淘金場處理一個叫渥爾姆的傢伙,時間在十九世紀中。聽起來好像是一部典型的拓荒時期小說,可是如果你這麼想,就大錯特錯。
因為除了場景為讀者熟悉之外,所有拓荒文學應有的元素,在派崔克‧德威特這本小說裡全被顛覆了。
個性迥異的兩兄弟,在接近目標的過程中,展現出來的殺手形象叫人傻眼,交往的各個角色也有點讓人摸不著頭腦,雙槍客在作者虛構出的美國西部底層社會討生活,過的哪是殺手「應該」過的日子,是啦,暴力層出不窮,可是盡是些無從說起、漫畫般地於情節中竄出的暴力,毫無血腥,徒然令人噴飯。
從來沒有見過西部小說是這麼處理的,在行文中,作者似乎根本不在乎殺手將如何達成任務,他寧願讓讀者與希斯特兄弟一同經歷他們每天的日子,尋常到不行的日子,兩個人對牙膏口味的爭論可以寫一大篇,可是誰說殺手不會在乎牙膏的口味。
弟弟伊萊是故事的主述者,講著講著就會逸出主題,跳進其他無關的場景,或者出現一些完全多餘的解釋,把讀者帶到一個超現實的西部拓荒故事裡。這讓我想到在諸多正統007號情報員的電影裡頭,就是有那麼一部由大衛‧尼文主演的《皇家夜總會》(Casino Royale),跳tone的程度,有如《淘金殺手》之於傳統西部開拓小說。
這是一本極盡kuso能事的小說,不論情節,光是形式的設計,就讓我這個也算搞笑的人甘拜下風。
媒體推薦:好評推薦:小說家高翊峰
《淘金殺手》這部小說的敘事,有一種奇異的潔癖乾淨。共鳴情感出來的速度很直接,文字也充滿視感畫面。我不會懷疑,它可以直接改編成電影,因為角色人物立體鮮明得就像是為影像而生的,彷彿是年輕的海明威為現代好萊塢寫了一個西部拓荒的美國夢,而這故事竟然還可以幽默。
推薦序:極盡kuso能事,徒然令人噴飯
名作家馮光遠
希斯特兄弟受雇於「准將」,前往加州的淘金場處理一個叫渥爾姆的傢伙,時間在十九世紀中。聽起來好像是一部典型的拓荒時期小說,可是如果你這麼想,就大...
章節試閱
奧勒岡城,一八五一年
第一部
我坐在准將公館外,我哥查理在裡面商談任務的細節,我等著他出來。白雪呼之欲降,我好冷,沒事找事做,開始端詳查理的新馬敏步。我的新馬名叫躂步。我們沒有替座騎取名的習慣。這兩匹是上回任務酬勞的一部分,牽過來時已經取名了,我們只能接受。我們以前的兩匹無名馬浴火而死,這兩匹馬來得正是時候,然而我認為准將應該支付現金酬勞,好讓我們自行去物色個人中意的馬匹,自行挑選無羈絆、無惡習的良駒,無須喊牠們聽慣了的名字。我非常喜歡以前的那一匹,最近常夢見他慘死火舌中的景象,見到著火的馬腿頻頻猛踹,眼珠子被燒得蹦出眼窩。他一天能跑六十哩,迅捷如狂風。我從不動手打他,對他動手的時候只有輕撫他或替他洗澡。我盡量不去回想他命喪穀倉火場的模樣,奈何當時的情景經常不請自來,我是防不勝防。躂步尚屬健壯,但他比較適合野心較小的馬主騎乘。他的身形偏肥、凹背,一天的腳程不超過五十哩,常逼得我對他抽鞭子。有些人把打馬當成家常便飯,有些人甚至不打不開心,但我不喜歡打馬。何況,鞭子一抽下去,躂步會認定我生性殘酷,會暗暗惆悵著﹕此生可嘆,此生可嘆。
有人盯著我看,被我察覺到了。原本看著敏步的我抬頭,瞧見查理正從樓上的窗戶向下凝視,對我豎起五根手指。見我沒反應,他歪一歪臉皮,想逗我笑。見我不笑,他垮下鬼臉,向後退出我的視線。他剛看見我在打量他的馬,我知道。昨天上午,我提議賣掉躂步,各出資一半另覓新馬。他原本認為很公平,但午餐席間他卻反悔,推說換馬的事該等新任務完成後再議。這不合道理,因為我擔心的是躂步無法勝任新任務,最好還是在出任務之前換馬吧?查理的八字鬍沾了一點午餐的油漬,開口說:「伊萊,最好等任務結束再說。」他對敏步毫無怨言。敏步和他先前那匹無名馬大致差不多,甚至更好。先挑馬的人是他,因為那天我身負任務期間受的腿傷,無法下床。我不喜歡躂步,但我哥對敏步感到滿意。這是隨馬而來的難題。
查理登上敏步,我們一同前往豬玀王酒館。才兩個月沒光臨奧勒岡城,大街上多了五家店面,而且新商家的生意看起來很興隆。「人類確實是腦力充沛的物種,」我對查理說,他沒有回應。來到豬玀王,我們在靠後牆的地方找張桌子坐下來,侍者端來一瓶我們常喝的酒和兩只酒杯。平常我們各倒各的,今天查理卻替我斟酒,因此在他開口時我已有接受壞消息的心理準備。
查理說:「這次任務由我擔任頭子,伊萊。」
「誰規定的?」
「准將說了就算數。」
我淺酌一口白蘭地。「這話什麼意思?」
「意思是,任務由我來指揮。」
「錢呢?」
「我的份比較多。」
「我問的是我拿的錢。和以前一樣嗎?」
「你的份比較少。」
「沒道理吧。」
「准將說,上次任務假如事先規定誰當頭子,就不會出差池。」
「沒道理。」
「有啊,怎麼沒道理?」
他再幫我斟一杯,我端起來喝。我以自言自語的口吻對查理說,「他想給頭子多一點錢,那也無所謂,只不過,虧待部屬是不厚道的行為。為了效勞他,我的腿破了一個大洞,馬也被活活燒死。」
「我的馬也被燒死了。他給了我們兩匹馬。」
「不厚道就是不厚道。甭幫我添酒了。把我當成殘障人士不成?」我搶走酒瓶,詢問新任務的細節。准將吩咐我們南下加州,去找一個名叫赫曼‧科密特‧渥爾姆的淘金客,然後要他的命。查理從夾克口袋摸出一封信,執筆人是准將的偵察兵亨利‧墨里斯。墨里斯是個講究衣著品味的人,常在我們出動之前先去蒐集情報。信上寫著:「已觀察渥爾姆多日,得知其習性與個性如下。他慣於獨來獨往,但經常流連舊金山的酒館,在酒館裡閱讀他帶在身上的科學與數學書籍,常在空白部分畫圖。他把這些書綁起來提著,模樣酷似學童,常因而遭人譏嘲。他的身材矮小,因此加倍滑稽,但請留意,他不喜歡被人嘲笑身高。我見過他多次與人打鬥,儘管他幾乎是每打必輸,我認為他的對手可不希望再和他對打,原因之一是他不惜咬人。他的頭頂童山濯濯,紅毛鬍雜亂無章,手臂瘦長,肚腩凸出如孕婦。他不常洗澡,以大地為床,舉凡穀倉、門口都可以睡,必要時更可以睡在路邊。與人交談時,他的態度粗鄙而冷峻。他隨身攜帶一把龍騎兵小左輪,插在纏腰帶上。他不常飲酒,但酒瓶一舉起來必定是爛醉方休。他以未加工的金屑付帳。金屑放在一只小皮袋裡,藏進一層又一層的衣物中,以繩圈揹著。自從我抵達此地,他不曾離城過一次。我不知道他是否有意返回他的地盤。他的地盤位於沙加緬度以東大約十哩(隨信附地圖)。昨天在酒館裡,他向我討火柴,口氣禮貌,直呼我的名字。他似乎始終沒有注意到被我跟蹤,我不知他為何認識我。我問他如何得知我的身分,他變得口不擇言,我只好離開。我不欣賞他,但有些人卻認為,他的心智異常堅強。他和平常人不太一樣,這一點我能認同,但我能褒他的言辭或許僅止於此。」
在渥爾姆的地盤地圖旁邊,墨里斯附上素描一幅,奈何他的畫工太差勁,而且塗改得至為模糊,即使渥爾姆站在我身旁,我也認不出人。我對查理說這件事,他說:「墨里斯正在舊金山的一間旅店等我們。他會幫我們指認渥爾姆,方便我們辦事。聽說舊金山是個殺人的好地方。舊金山人不是忙著放火燒光整座城,就是忙著重建,忙個沒完。」
「墨里斯為什麼不直接殺他?」
「你老是問這問題,我老是這樣回答﹕這任務是我們的,不是他的。」
「這太沒頭腦了。准將扣我酬勞,卻幫這條糊塗蟲支付開銷,給他薪水,結果打草驚蛇,讓渥爾姆發現自己被人盯上了。」
「老弟,你不能罵墨里斯是糊塗蟲。這是他頭一次失誤,而且他慨然認錯。我認為墨里斯之所以穿幫,與其怪他糊塗,倒不如怪渥爾姆太精了。」
「可是,他不是說,渥爾姆露宿街頭嗎?何不乾脆趁渥爾姆睡覺時槍斃他?」
「墨里斯不是殺手的話,怎麼狠得下心?」
「那何必派他去?一個月前,准將何不派我們直接動手?」
「一個月前,我們在忙另一項任務。你別忘了,准將的利害關係很多,一次只能關照一件事。他常說,生意欲速則不達。只要看看他的成就,就能瞭解這話的真諦。」
聽他以仰慕之情來引述准將之語,我覺得反胃。我說:「加州離這裡挺遠的,趕路幾個禮拜才能到。沒必要去的話,我們何必去呢?」
誰說沒必要去﹖我們的任務就是去加州。」
「如果渥爾姆不在加州呢﹖」
「他會在。」
「假如人不在加州呢﹖」
「可惡,他一定會在。」
結帳時,我指向查理。「頭子請客。」由於我們通常五五分帳,他聽了這話不高興。我哥得自老爸的真傳,吝嗇成性。
「只請這一頓,」他說。
「領頭子薪水的頭子。」
「你從來就不欣賞準將,而他也從來就不欣賞你。」
「我是愈來愈不欣賞他了,」我說。
「如果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你想當面告訴他,我也不攔你。」
「如果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查理,你會知道的。你會知道,準將也會。」
我不願繼續拌嘴下去,所以丟下他,自行回酒館對面的旅店歇息。我不喜歡吵架,尤其不喜歡和查理爭辯,因為他一吵起架來,唇舌異常刻薄。當晚夜半時分,我聽見他在街頭和一群人交談。我拉長耳朵傾聽,以確定他有無危險。他很安全—那群人只是問他叫什麼名字,聽他回答之後就走開。但只要他有危險,我勢必捨身救人。其實,我靴子還沒穿好,那群人就已經解散。我聽見查理上樓的聲響,趕緊跳上床,假裝熟睡。他探頭進我房間,喊我的名字,我不吭聲。他把我的房門關好,走向他自己的房間,我則靜躺暗室裡,想著親人難為,想著有些至親世系的事跡多麼顛狂,多麼歪曲。
隨後,一陣忽強忽弱的寒意從脛骨往上爬昇,冷若冰霜。我說,「那隻小動物可真帶勁呵,老哥。」未久,一股高燒襲捲而來,我不得不躺下。查理見我面色蒼白,不禁擔憂﹔我發現自己講不出話時,他把火生得旺一些,騎馬去最近的城鎮找大夫。醫生來的時候,我已墜入一團迷霧,茫茫之中聽見他趁查理走開時咒罵一通,想必他是來得半依半就,或者是被查理強押過來看診。大夫給我一帖藥或抗毒素,其中有一種成分讓我飄飄欲仙,宛如酒醉,使我淨想著原諒所有人,不計較過往,也想抽菸抽個不停。不久後,我睡著了,昏睡得不省人事,整天整夜始終意識不明。直至隔天早晨,我醒來時看見查理仍守在營火旁。他朝我望過來,展露笑容。
「你剛才夢到什麼,還記不記得?」他問。
「只記得我動彈不得,」我說。
「你一直說,『我在帳篷裡﹗我在帳篷裡﹗』」
「我不記得了。」
「『我在帳篷裡﹗』」
「扶我站起來。」
他過來攙扶我。頃刻後,我踩著麻木的雙腳,繞著營地兜圈子。我微微想吐,卻照樣大啖培根、咖啡、烤餅,沒有嘔出來。我自認恢復得差不多了,可以上路,所以兄弟倆跳上馬,信步前進四、五個鐘頭,然後再歇腳。查理反覆關心我的身體狀況,我屢次含糊以對,其實自己是壓根兒不清楚。我總覺得魂不附體似的,作祟的不知是蜘蛛毒液,或是神色慌張的大夫給的抗毒素。這晚,我徹夜發燒,時睡時醒。隔天,我聽見查理對我喊早安,轉頭想回話,他看我一眼,駭然驚叫。我問他,怎麼了?他找來一個錫盤,叫我照鏡子。
「什麼鬼東西?」我問。
「那是你的頭啊,老弟。」他原地向後傾身,吹一聲口哨。
我的左臉浮腫得面目猙獰,從頭頂一路腫到頸子,下至肩膀才逐漸輕微,左眼只剩一道細縫。查理恢復揶揄他人的本性,說我腫成了半人半狗,還拋擲一根樹枝看我會不會去撿。我查出臉腫的根源是牙齒和牙齦,伸一指進嘴裡,按一按左下排的牙齒,一陣劇痛從頭竄至腳丫,然後回竄,嗡嗡痛徹全身。
「一定漏了一加侖的血水,在腦殼裡面蕩來蕩去,」查理說。
「昨天那個大夫是你哪裡找來的?我們應該回頭去找他,請他幫我戳一戳。」
查理搖搖頭。「最好別主動去[找]他。費用的事情和他鬧得不太愉快。他如果看見我,一定會很高興,不過他大概不肯進一步協助我們。他提過,從這裡往南走幾哩另外有個部落,可能是我倆最明智的辦法,如果你自認走得動的話。」
「由不得我吧。」
「是啊,人生確實有很多由不得人的事情。」
……
我提出自己的一套理論,認為牙疼若非源自蜘蛛螫傷,就是抗毒素在搞鬼,但瓦茨說沒有醫學證據能佐證我的猜測。他告訴我,「人體是不折不扣的奇蹟啊。誰能解剖驗證奇蹟呢?病因有可能是蜘蛛,沒錯,也有可能是那位大夫所謂的抗毒素產生的反應,但也有可能兩者皆非。話說回來,病都生了,原因何在,有啥差別呢?我沒說錯吧?」
我說,大概吧。查理說,「大夫,我剛對伊萊說,我敢打賭,他的腦袋裡一定有一加侖的血水涮來涮去。」
瓦茨抽出一支擦拭得雪亮的銀色柳葉刀,臀部向後挪,審視著我的頭,視之為一尊惡獸塑像。「戳下去就知道,」他說。
翌日早晨,我在地板上醒來,查理已不在身旁。我的身後傳來一腳落地的聲音,轉頭發現查理站在敞開的門口,向外凝望著小屋前的原野。這天出了個大太陽,兩匹馬站在遠處,旁邊有個樹木的殘樁被挖出地表,樹根朝天,馬繩就綁在樹根上。草地蒙上一層霜,敏步嗅著草,想啃草來嚼一嚼﹔躂步則發著抖,不知盯著什麼東西。「老太婆走了,」查理說。
「走了最好,」我邊回應邊站起來。屋裡混合著灰燼味和煤炭味,我的眼珠乾澀、灼痛。不燒開水不行,於是我走向門口,不料卻被查理攔阻。他的面容憔悴疲憊。「她走是走掉了,」他說,「卻留住我們,把我們當成紀念品。」他比劃著,我朝他手指的方向望去。老婦人徹夜串珠子,成品在門框圍了一圈。[我大致會走,]我記得她說過—大致上是走掉了,卻沒有走得乾乾淨淨。
「我想聽聽你的想法,」我說。
查理說,「不可能是裝飾品。」
「我們可以拆掉,」我邊說邊伸手去搆。
他抓住我的手。「別碰,伊萊。」
我們向後退一步,衡量對策。馬兒聽見我們講話的聲音,正從野地裡望著我們。「不能從門口走出去,」查理說。「唯一的辦法是破窗而出。」我的腹圍向來寬廣,這時我拍拍肚子說,窗口那麼小,我大概鑽不出去。查理說,不試試看怎知。然而,如果鑽到一半卻被卡住,滿臉通紅卻縮不回去,那種情景絕不讓我想要一試。所以我說我不想鑽。
「那我自己先出去,」查理說,「幫你找工具回來,把窗口擴大一些。」他把老嫗的椅子拉過來,站上搖搖晃晃的椅子,以左輪的槍柄敲掉玻璃,叫我支撐他爬窗戶出去。隨後他掉頭走來前門,和我隔著門口對看。他面帶微笑,但我板著臉。「鑽出來了,」他說著拍掉肚子上的碎玻璃。
我說,「我不喜歡你這套計劃。荒郊野外的,哪裡去找好心人?誰願意出借工具呢?到時候你會騎著馬,漫無目的走來走去,留我一個人在這棟茅屋裡瞎耗。如果老太婆回來了,我怎麼應付?」
「她留下毒咒來對付我們,沒有理由再回來。」
「你說得倒輕鬆。」
「我相信她鐵定不會回來了。不然我能怎麼辦?你如果想得出辦法,趕快提出來討論討論。」
但我想不出法子。糧食袋放在馬兒身邊,我叫他去幫我拿些東西過來,看著他走向繫馬處。「別忘了拿鍋子(pan),」我呼喚。「什麼男人(man)?」他問。「鍋子﹗鍋子﹗」我比劃著以鍋子煮食的動作,他點頭會意。他帶東西回來,從窗外送進屋裡,祝我早餐愉快,然後躍上敏步,騎行而去。他們漸行漸遠,一股悲慘的情緒滋生我心中﹔我呆望著他們遁入的樹林開口,心生不祥的預兆,擔憂他們將一去不回。
我鼓起蓄積心中備用的興致,決定暫時以小屋為家。屋內沒有柴薪或火種,所幸煤灰仍有餘燼,於是我抓起老太婆的椅子,對著地板使勁擊打,然後收拾殘破的椅腳、椅座、椅背,在壁爐裡堆積成倒V字形,澆淋燈油。不一會兒,碎椅轟然起火。火光與香味令我心情開朗。椅子的材料是硬質橡木,很容易燃燒。我母親常在這種時候說「小小的勝利」,而我這時也自言自語說出來。
我在門口佇立幾分鐘,向外望著世界。晴空是萬里無雲,藍得發紫的蒼穹顯得比平常更高、更深邃。融雪從屋頂串串流下,我舉起錫杯去窗口接水,手中的杯子變得冰涼,透明的冰雪小島漂浮水面,我舉杯喝時感覺嘴唇刺麻麻。我嘴裡殘餘昨天的死血,有陰森的棺味,冰水一入口,沖散了血腥,舒坦了我的心情。我把冷水含在嘴裡,漱洗傷口,沒想到這麼一沖刷,我赫然發現嘴裡有固體的東西鬆動了,在水中流動。我以為是漱掉了一塊皮肉,趕緊吐在地上。啪的落地聲,聽起來令我反胃。我彎腰去近看,見到一條圓柱形的黑色物體,心臟砰然加速﹕難道瓦茨大夫瞞著我,在我嘴裡塞進一條水蛭?我以拇指去戳撥,那東西散開來,我才想起牙醫曾在牙齦邊塞棉花。止血棉被我扔進爐火,順著燃燒的椅腳往下滑,開始冒泡、生煙,流下一道血液與唾液的痕跡。
蒸氣從野地浮昇,我凝視著屋外,回想起近日發生一連串的禍害,先是蜘蛛,後是頭腫,現在又被下咒,幸好是一一化解,我不禁雀躍。我吸了滿滿一肺臟的冷空氣,胸腔漲到極限。「躂步﹗」我對著野地高呼。「惡毒的吉普賽巫婆對我下咒,把我困在這間小屋了﹗」躂步抬頭,嚼著一嘴硬梆梆的青草。「躂步﹗主子遭逢急難,快來救人﹗」
我為自己煮了一小頓早餐,有培根、粗燕麥粥、咖啡。一塊軟骨卡進拔牙後的傷口,我硬是挑不出來,傷口因此又流血。我想起大夫給我的牙刷,從背心口袋拿出來,連同牙粉,整齊排列在杯旁的桌上。該不該等傷口完全癒合才刷牙呢?大夫並沒有說,但我考慮刷刷看,謹慎一點應該無礙。我弄濕刷毛,搖出一丁點牙粉,嘴裡覆誦著大夫吩咐的「上下刷,左右刷。」薄荷味的泡沫在我嘴裡形成,我也把舌頭刷得火紅。我攀著窗沿,引體向上,對著泥土和雪地吐掉血水。我的口氣變得清新涼爽,嘴裡有麻麻癢癢的感覺,深得我心。我決定今後將每日使用牙刷。我以刷柄敲著鼻樑,寥無心事,或者同時想著幾件模糊的事物,這時看見一隻熊拖著笨重的身軀走出樹林,走向躂步。
我們敲墨里斯的旅店房門,無人應答。查理撬開門鎖,我們入內後發現他的許多盥洗用品、香水、蠟油,堆疊在門口旁邊的地板上,除此之外別無墨里斯的蹤影,沒有衣物或行李,床鋪整理過,窗戶全數緊閉﹔我的直覺是,墨里斯幾天前就已經離開。他不告而別讓查理和我警覺起來,近乎焦躁不安,因為儘管我們確實是遲到,但失約不合乎墨里斯的作風。我提議向旅店人員詢問他是否留言,查理贊成我去調查。我正要走向房門,這時留意到,床邊的牆壁上嵌著一個黑色的大號角,裡面有個擦亮的銅鈴,號角下方掛著一個招牌﹕{搖鈴找服務人員。}我依照指示搖鈴,鈴聲響徹房間,令查理嚇一跳﹔他引頸看個究竟。「你在幹什麼?」
「我聽說東岸的旅店有這種裝置。」
「哪種裝置?」
「你等著看。」片刻之後,旅店內部傳來女聲,聲音皺縮而遙遠。
「喂?墨里斯先生?」
查理整個人轉過來。「她躲在牆壁裡面?聲音是從哪裡來的?」
「喂?」女聲又問,「您是不是搖鈴找服務人員?」
「你快講話啊,」查理催我,但我莫名其妙羞澀起來,示意他去對答。他遠遠對著號角喊,「妳在裡面聽得見我嗎?」
「聽得見,不過您的聲音微弱,請湊近號角說話。」
查理玩出興致了,起床走過來,整張臉探進號角去。「怎樣?比較清楚了嗎?」
「比較清楚了,」女聲說。「墨里斯先生,今天有何指教?您回來了,真好。您跟著那位大鬍子的矮冬瓜怪人走掉,我們好擔心。」查理與我互看一眼。他再對號角說,「小姐,我不是墨里斯。我剛從奧勒岡準州南下來拜訪他。他和我在同一家商號服務。」
女聲愣住。「墨里斯先生去哪裡了?」
「我不知道。」
奧勒岡城,一八五一年
第一部
我坐在准將公館外,我哥查理在裡面商談任務的細節,我等著他出來。白雪呼之欲降,我好冷,沒事找事做,開始端詳查理的新馬敏步。我的新馬名叫躂步。我們沒有替座騎取名的習慣。這兩匹是上回任務酬勞的一部分,牽過來時已經取名了,我們只能接受。我們以前的兩匹無名馬浴火而死,這兩匹馬來得正是時候,然而我認為准將應該支付現金酬勞,好讓我們自行去物色個人中意的馬匹,自行挑選無羈絆、無惡習的良駒,無須喊牠們聽慣了的名字。我非常喜歡以前的那一匹,最近常夢見他慘死火舌中的景象,見到著火...
作者序
派崔克‧德威特簽書會側寫
宋瑛堂 二○一二年二月
機運是《淘金殺手》故事的主軸,兩兄弟在南下過程中,誤打誤撞,好運連連來,作者派崔克‧德威特的經歷何嘗不是如此﹖德威特創作本書的機緣始於一本舊書。家住波特蘭東北區的他,有一天散步路過一場住家舊物出清的拍賣會,無意間翻到一本名為《The Forty-Niners》的舊書,內容不是美式足球的舊金山四九人隊,而是一八四九年蜂擁而至西岸的淘金客,以圖文詳述當年的人事地物,兩毛五美金俗俗賣,替他為本書的故事搭起場景,只等他捏出幾個玩偶進駐。
曼布克文學獎已有四十三年的歷史,二○一一年的入圍書單首度出現以美西拓荒為背景的小說。由於曼布克獎僅限大英國協公民參加,以黑色幽默來書寫十九世紀美西槍俠的佳作更難能可貴。加拿大的三大文學獎當中,本書更囊括總督獎和羅傑斯獎,譯者於二○一一年十二月造訪溫哥華時,隨處可見本書以黑紅色為主調的封面,大小書店無不以最醒目的位置為本書加持。由於本書的主要場景設在奧勒岡州,因此在作者第二家鄉的各大年度好書榜上也是常客。
令人意外的是,德威特的成名並非純屬運氣。小時候的他稱不上作文課的奇葩。德威特是加拿大公民,一九七五年出生於溫哥華島上的席德尼,幼年隨父母遷居南加州,中學老師讀了他的文章頻搖頭,還勸他打消專職創作的志願。他在其他科目的表現同樣遜色,篤定被留級時,他毅然輟學。他半開玩笑說,「幸好我後來從事的工作對學歷要求不高,我可以騙老闆說我中學畢業,對方也不會叫我拿文憑出來。」
在南加州期間,德威特曾在好萊塢的夜店工作長達六年,從徒手洗杯盤做起,後來昇任酒保助理,期間看遍酒池的人生百態。辭職之後,他根據這段經歷,以第二人稱的角度發表首部小說《洗禮》(Ablutions),佳評如潮但銷路平平。但在處女作問世之前,他屢次投稿《紐約客》雜誌卻吃足了閉門羹,灰心卻從不喪志,堅持走自己的路,最後終於開闢出屬於自己的園地。
這些往事,德威特在簽書會上娓娓道來,態度大方自然,與他酷酷的外表不太相符。簽書會於二○一二年二月十九日在波特蘭名勝的鮑爾(Powell)書店舉行,預定七點半開始,但七點不到就座無虛席,承辦人凱文和馬克只好再推著折疊椅出來加位,連講席兩側的小三角形空地也不放過。在書店的這一隅,或坐或站的書迷人數破百,圍觀的人群也是愈來愈厚密,等候他出場。甫譯完《淘金殺手》的我也慕名而來。在他進場前,馬克把我介紹給德威特,問我們要不要來一張合照,德威特二話不說就把我拉過去。
他瘦長的身材接近一百九十公分,戴著厚厚的黑框眼鏡,身穿褐灰相間的格子衫,向觀眾介紹個人生平之後開始朗讀本書中的墨里斯日記,隨後向在座觀眾說明,他的父親是愛書人,有時晚餐開飯了,他仍在一旁捧書猛啃,不肯上桌。書讀完了,父親會把書扔給兒子,所以少年德威特接觸到的全是針對成人寫作的書,這些大人書催熟了他的文學心,更加堅定他日後的志向。成年後,他開始勤跑圖書館,捧一大疊好書回家,但大部份的書只看前幾段就合起來放著,準備退還給圖書館。
開放觀眾發問時,現場冷了一陣,凱文和馬克有點著急,德威特連問了兩次才有人怯生生地舉手。這位讀者稱讚他,雖然他用英文寫作,主題是美國西部,字裡行間卻有俄國文豪的風格。他說,他從圖書館裡借出來的書當中,最後送還的總是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
接下來的發問是一發不可收拾,有人想知道他的寫作習慣(陪兒子走路上學後才回家動筆),有人問他是否先擬好劇情架構才開始動筆(是的),更有一位熟年女士對於他的求學辛酸產生共鳴。《淘金殺手》出版時,他已經著手撰寫第三本小說,但礙於本書的熱潮洶湧,打亂了他的寫作紀律,目前只完成一百頁左右,寫寫停停。可以透露內容嗎﹖新書的靈感同樣始於因緣際會。有天他在曼哈頓街頭,走著走著,撞見記者圍剿梅道夫(Madoff,在金融風波前騙財無數。)的場面。當時梅道夫事件剛爆發,他不認得這人的臉,只在心頭嘀咕,這老頭犯了什麼滔天大罪,怎會遭人踐踏到這種程度﹖他開始構思一個本性不壞﹑個性討喜﹑卻作惡多端的人。
最後,承辦人凱文在觀眾席後對他猛招手,意猶未盡的他才歇口走向簽名桌。
住過卑詩省﹑加州﹑華盛頓州,他最後在書香之城波特蘭落腳生根,婚後育有一子,太太萊絲理以創作劇本為業,他也應邀寫過一部獨立製片的劇本,片名是《Terri》,敘述一個心思細膩的小胖弟求學的辛苦,由電影《芝加哥》的男配角約翰‧萊里(John C. Reilly)擔綱,而他也已買下《淘金殺手》的製片權,開拍日期未定。
德威特在家中排行老二,當年決定輟學時,他認為反正一家三兄弟的成績一樣菜,哥哥比他更早失學,弟弟最後也只勉強拿到中學畢業證書,他不覺得丟臉。他說希斯特兄弟的互動靈感源於自己家的三兄弟。哥哥弟弟是什麼樣的人﹖該不會是在夜店門口耍槍的保鏢吧﹖其實三兄弟都是愛樂青年,偏愛黑膠唱片。老大麥克自創一間專門出版限量發行黑膠唱片的公司,老三尼克是他旗下的樂手,演奏的曲風揉合民俗搖滾和沖浪音樂。幼年時期,飽受哥哥欺壓的他常對弟弟出氣,因此寫作本書時援引手足情誼是信手拈來,以親身經歷寫盡了查理霸道的暴虐和伊萊的陰柔豪情,家有兄弟的讀者在神遊淘金潮時代的西岸時,或許也能對兄弟倆勾心鬥角卻不忘互相照應的情節會心一笑。
派崔克‧德威特簽書會側寫
宋瑛堂 二○一二年二月
機運是《淘金殺手》故事的主軸,兩兄弟在南下過程中,誤打誤撞,好運連連來,作者派崔克‧德威特的經歷何嘗不是如此﹖德威特創作本書的機緣始於一本舊書。家住波特蘭東北區的他,有一天散步路過一場住家舊物出清的拍賣會,無意間翻到一本名為《The Forty-Niners》的舊書,內容不是美式足球的舊金山四九人隊,而是一八四九年蜂擁而至西岸的淘金客,以圖文詳述當年的人事地物,兩毛五美金俗俗賣,替他為本書的故事搭起場景,只等他捏出幾個玩偶進駐。
曼布克文學獎已有四十三...
目錄
推薦序 極盡kuso能事,徒然令人噴飯 名作家 馮光遠
第一部 馬之難題
第二部 加州
插曲
第三部赫曼‧科密特‧渥爾姆
插曲之二
終曲
派崔克‧德威特簽書會側寫 宋瑛堂
推薦序 極盡kuso能事,徒然令人噴飯 名作家 馮光遠
第一部 馬之難題
第二部 加州
插曲
第三部赫曼‧科密特‧渥爾姆
插曲之二
終曲
派崔克‧德威特簽書會側寫 宋瑛堂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