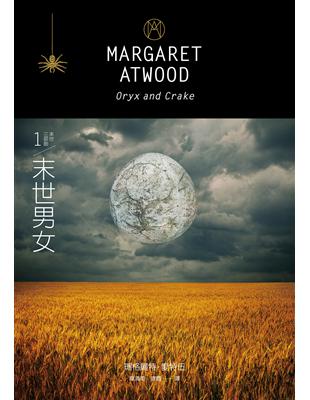★瑪格麗特‧愛特伍「末世三部曲」第一部《末世男女》。
★英國布克獎《盲眼刺客》作者,亦是諾貝爾文學獎呼聲最高的作家瑪格麗特.愛特伍,繼《使女的故事》之後再度挑釁讀者的神經,描述人類遭受病毒感染、基因改造後的廢墟世界。
★HBO與《黑天鵝》導演戴倫•艾洛諾夫斯基合作,即將改編《瘋狂亞當》迷你影集,現正拍攝中
未來文明極度發展,人類以近乎造物者之姿,改造基因創造無數異種,甚至理想中的新人類--克雷科人。然而,一場預謀的瘟疫--無水之洪--幾乎毀掉地球上所有的人類,一處處廢墟重新為植物覆蓋,新種生物恣意橫行。
劫難後的荒涼世界裡,倖存的人類雪人吉米,帶領克雷科人,躲避凶殘的生物,漫無目的的活著。沒有未來,只有回憶與疑問:他的伙伴克雷科與情人奧麗克絲,如何操控這場災難,以生物科技和病毒變種造成人類浩劫?背後的理由又是什麼?
瑪格麗特‧愛特伍以詩人敏銳的筆調書寫人性;《末世男女》故事令人毛骨悚然、怵目驚心,瀰漫著悽涼的美學。
作者簡介:
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
一九三九年出生於渥太華,加拿大最傑出的小說家、詩人,同時也寫短篇故事、評論、劇本以及創作兒童文學。她已發表四十多部作品,翻譯超過三十五種語言,其中小說《盲眼刺客》獲頒二○○○年布克獎,《雙面葛蕾斯》獲頒加拿大季勒文學獎,並獲義大利最負盛名的蒙德羅文學獎(Premio Mondello)。二○○五年,她獲頒愛丁堡圖書節啟蒙獎(Edinburgh Book Festival Enlightenment),得獎理由是對世界文學與思想的傑出貢獻。二○○八年,瑪格麗特‧愛特伍獲頒西班牙艾斯杜里亞斯親王文學獎(Prince of Asturias Prize for Literature)。她目前住在多倫多。最新作品是《THE HEART GOES LAST》(二○一四)。
譯者簡介:
韋清琦
一九七二年生於中國南京市,一九九八年畢業於南京師範大學英語語言文學碩士班,為北京語言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的博士候選人。
袁霞
一九七三年生於中國蘇州,一九九八年畢業於南京師範大學英語語言文學碩士班,為大學教授。
各界推薦
得獎紀錄:
★二○○三年布克獎、二○○三年英國柑橘文學獎提名
★二○○四年《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
★亞馬遜網路書店評鑑五顆星
名人推薦:
《末世男女》乃是多重喻義的科幻寓言。它具有性別抗議、社會批判、探討文明和記憶脆弱等意義,可以說是第三波傑出著作。一九八五年愛特伍發表她首部「科技反烏托邦」小說《使女的故事》對科技社會做了悲傷的預言,而今繼《使女的故事》之後寫《末世男女》,我們不仿將這兩部作品相互參照比較。──南方朔
媒體推薦:
一部科幻小說的里程碑之作,可媲美《發條橘子》、《美麗新世界》……愛特伍也超越了她自己。──《柯克斯書評》
壯闊而大膽……愛特伍超越歐威爾了!──《紐約客》
一部爆出火花的作品……愛特伍是我們這個時代中最具野心的作家。──《衛報》
強而有力的視野……非常值得一讀。──《紐約時報書評》
一連串冷面、黑色、嘲諷的笑聲……年度最讓人驚異的小說。──《經濟學人》
得獎紀錄:★二○○三年布克獎、二○○三年英國柑橘文學獎提名
★二○○四年《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
★亞馬遜網路書店評鑑五顆星
名人推薦:《末世男女》乃是多重喻義的科幻寓言。它具有性別抗議、社會批判、探討文明和記憶脆弱等意義,可以說是第三波傑出著作。一九八五年愛特伍發表她首部「科技反烏托邦」小說《使女的故事》對科技社會做了悲傷的預言,而今繼《使女的故事》之後寫《末世男女》,我們不仿將這兩部作品相互參照比較。──南方朔媒體推薦:一部科幻小說的里程碑之作,可媲美《發條橘子》、《美麗新世界》……愛特伍也...
章節試閱
1.
芒 果 雪人在天亮前醒來。他靜靜地躺著,傾聽潮汐湧向岸邊,浪一波接著一波拍打著各種障礙物,呼啦嘩啦,呼啦嘩啦,節奏猶如心跳。他寧願自己仍在睡夢中。 東邊地平線上有團被一道刺眼玫瑰色光芒照耀的灰霧。但奇怪的是,色澤仍然那麼柔和。在晨曦的輝映下,近海處的瞭望台現出黑色輪廓,彷彿矗立在粉紅與淡藍色的珊瑚礁中。築巢的鳥兒發出銳叫聲,夾雜著近處海浪拍打著由生鏽的汽車零件及破磚瓦組成的人工礁石聲,聽起來就像是假日的車潮。 他出於習慣地看了看錶——雖然已經不走動,但不鏽鋼外殼並磨過的鋁製錶帶仍閃閃發亮。他把這當作具有神奇魔力的護身符。對他展示出一張空白的面孔:零時。沒有公認的時間使他不寒而慄。不論何時何地,沒有人知道現在幾點。 「冷靜下來。」他對自己說。他做了幾次深呼吸,抓了抓被蟲咬過的地方——周只抓圍,且不觸及最癢處——小心地不碰觸結痂;他可不想讓毒素跑進血液中。接著他掃視地面看看有沒有什麼野獸:一切都很安靜,沒有鱗片,沒有尾巴。左手、右腳、右手、左腳,他順著樹爬下來。他撣掉樹枝、樹皮,然後將髒兮兮的床單像件袍子般裹在身上。因為怕那頂仿紅襪隊棒球帽被偷走,整晚他都把它掛在樹枝上;他檢查了帽子裡面,趕走一隻蜘蛛後才戴上。 他往左走了幾步,對著灌木叢撒尿。「抬起頭,」他對受到突如其來衝擊而匆忙逃散的蚱蜢說。然後他走到樹的另一頭,遠離小便處,開始在儲藏櫃裡翻找。櫃子是他用幾根水泥條拼湊出來的,用紗網蒙住以防鼠輩。他在裡面存放了些芒果,捆紮在塑膠袋裡的還有一罐斯維爾塔那無肉合成香腸,半瓶寶貴的蘇格蘭威士忌——剩不到三分之一——以及一塊從休旅車營地裡翻出來並用錫箔紙包著的快融化、巧克力口味的高熱量餅乾。現在還不能吃,這也許是他能找到的最後一塊了。他還藏了一把開罐刀、沒有特別理由而留下的碎冰錐,以及為了懷舊和貯存清水的六個空啤酒瓶。還有他的太陽眼鏡;他戴了起來。已經缺了一個鏡片,但總比什麼都沒有好。 他解開塑膠袋,只剩一顆芒果了。奇怪,他記得應該還有一些的。雖然他盡可能地綁緊了,但還是有螞蟻鑽進去。黑蟻和凶殘的黃色小螞蟻現在爬上他的手臂了。他很訝異牠們竟能造成那麼大的刺痛感,特別是黃色那種。他揮手撢掉。 「嚴格遵守日常規定才能保持良好的精神和健全的心智,」他大聲說。他覺得自己正在引用書裡的話,某種過時、為幫助歐洲殖民者經營莊園之類的生計而立下的古板規矩。他記不起有沒有讀過這種東西,但這已沒有意義了。在他殘餘的腦中有很多空白,而這應該是記憶所在的位置。橡膠園,咖啡園,黃麻種植園(黃麻是什麼?)。他們被教導要戴遮陽帽,進餐時衣著要穿齊整,不可強姦當地土著。不可能用「強姦」這個字眼。不可與女性原住民親熱。或換種說法…… 他打賭他們沒遵守,十有八九。 「出於從輕發落的考量,」他說。他發現自己站在那兒張著嘴,努力想回憶起接下去的句子。他坐到地上吃起芒果。
漂 流 一群孩子走在白色的沙灘,上面散布著被沖刷上岸的珊瑚,以及破碎的骨頭。他們渾身閃耀著濕亮的水光,一定剛游過泳。他們應該小心一點,誰知道珊瑚礁中藏了什麼;但他們並不擔心;他們不像雪人——即使在夜晚陽光照不到他的時候,他也不會把腳伸進海裡。更正:特別是在夜晚。 他羨慕地注視著他們,抑或是懷舊?不可能,他兒時從沒在海裡游過泳,也沒有赤裸裸地在海灘上到處跑。孩子們掃了一眼周圍的地形,彎腰揀起沖到岸上的漂浮殘骸;接著他們商量,留下一些東西,扔掉其餘的;他們把揀出的寶貝裝進一只破口袋。遲早——他確定——他們會找到他,發現因陽光毒辣而裹著破床單坐在地上、抱著小腿躲在樹蔭下吸吮芒果的他。對那些有著抗紫外線厚實皮膚的孩子們而言,他是活在陰霾的昏暗裡。 現在他們過來了。「雪人,哦雪人,」他們像唱歌似的反覆喊道。他們從不會離他太近。是出於尊敬,他比較願意這樣想;還是因為他散發著臭味? (他的確散發著臭味,他知道得很清楚。臭烘烘的帶著膻氣,跟海象一樣油膩、鹹腥。他沒有真的聞過這種動物,但他看過圖片。) 孩子們打開口袋齊聲喊道,「哦雪人,看我們找到了什麼?」他們拿出那些東西,高舉著像是在兜售:輪軸蓋、鋼琴鍵、被海水沖得很光滑的淡綠色汽水瓶玻璃片、一罐「喜福多」塑膠瓶,一個奧那賓斯雞塊桶,也是空的。一個電腦滑鼠,或說是它的殘餘部分有著一根長長的電線尾巴。 雪人想哭。他能告訴他們什麼?根本無法向他們解釋這些古怪東西是什麼,或曾經是什麼。但他們已經猜到他會說什麼,因為他總這樣說。 「這都是過去的東西。」他使自己的聲音保持和善而疏離;應該就是混合著老師、占卜者和仁慈叔叔的語氣。 「會對我們有害嗎?」有時他們能找到幾罐機油、腐蝕性溶劑以及塑膠瓶裝的漂白劑。以前的害人玩意兒。他被當作了專家,擅長處理突發事故:能灼傷皮膚的液體、致病煙霧、有毒粉塵。各種奇怪的病痛。 「不會,」他說。「很安全。」他們聽到這個便沒了興趣,拿著袋子晃蕩著。可他們不走開,他們站在那,盯著他看。撿沙灘上的東西來只是藉口,其實他們只想看他,因為他和他們多麼不同啊。他們常常要他摘掉太陽眼鏡再戴上,他們要看看他是不是真有兩隻眼睛,或是三隻。 「雪人,哦雪人,」他們唱著,有種玩笑方式而非叫他。對他們而言,他的名字只不過是兩個符號。他們不明白雪人是什麼,他們從沒見過雪。 克雷科的規矩中有一項:選名字一定要有具體形象——哪怕是標本,哪怕只是骨架——能夠得到證實的。不能是傳說中的獨角獸、獅身鷹首獸、人面獅身蠍尾獸或蛇怪。不過這些規矩不再適用了,雪人為自己取了這個含糊的稱呼,也給了他一種苦澀的快感。喜馬拉雅山雪人——存在的和不存在的,在暴風雪中時隱時現,像猿一般的人或像人一般的猿,神出鬼沒,只限於傳言和那遺留的腳印。據說山裡的部落曾追蹤到牠,並乘機捕殺。據說他們將牠煮了、烤了,舉行了特別的盛筵;簡直是同類相食嘛,他推想,這更刺激了。 考慮現今的狀況,他縮短了名字,只叫雪人。只有他知道前面還有「討厭的」這個詞,他把祕密藏在心中。 猶豫片刻後,孩子們圍成半圓跪了下來,男孩和女孩都是。有幾個年紀小一點的還嚼著早餐,綠色果汁流到下巴。在沒有鏡子的情況下,每個人都很邋遢,這讓他感到沮喪。不過他們仍然漂亮得讓人吃驚,這些孩子——每一個都赤身露體,每一個都很完美,每一個都有不同的膚色——巧克力色、玫瑰色、茶色、黃油色、乳白色、蜜色——但每人都有著綠眼睛。克雷科的審美觀。 他們充滿期待地看著雪人。他們希望他會跟他們說話,可是他今天沒興致。頂多讓他們看看他的太陽眼鏡,或是他那閃亮卻停擺的手錶,或是他的棒球帽。他們喜歡這頂帽子,但不懂他為什麼需要這樣東西——像是活動的頭髮但又不算是頭髮——他還沒有找到說法。 他們安靜了一會兒,盯著他看並反覆琢磨著,不過接著其中年齡最大的一個說話了。「哦雪人,請告訴我們——從你臉上長的那些青苔是什麼?」其他人也附和起來。「請告訴我們,請告訴我們吧!」不是起鬨,不是嬉鬧,是很認真地詢問。 「羽毛。」他說。 每周他們至少問一次,他都給相同的答案。才過了這麼短的時間——兩個月,還是三個月?他數不清了——他們積累了許多有關他的說法和臆測:雪人原本是隻鳥,但他忘記怎麼飛了;他其餘的羽毛也脫落了,所以他感到冷,需要第二層皮膚把自己裹起來。不,他會冷應該是他吃魚,而魚是冷的。不,他把自己裹住是因為他弄丟了男人的東西,他不想讓我們看見。這就是他為什麼不去游泳。雪人有皺紋是因為他以前住在水裡,皮膚就變皺了。雪人很悲傷是因為像他那樣的人都飛過大海去了,現在就只有他一人。 「我也要羽毛,」最年幼的孩子說。一個實現不了的希望:在這些克雷科的孩子們裡,男人不長鬍子。克雷科覺得鬍子不合理的,每天都得刮鬍子讓他覺得很不耐煩,所以他取消了這一項。不過對雪人當然沒輒:太遲了。 現在他們齊聲喊起來。「哦雪人,哦雪人,我們也能長羽毛嗎?拜託。」 「不行。」他說。 「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行嘛?」最小的兩個孩子撒嬌道。 「等一下,我來問問克雷科。」他把手錶舉到空中,將手腕轉了一圈,然後貼近耳朵作出正在傾聽的樣子。他們著迷地盯著他的每個動作。「不行,」他說。「克雷科說不行,你們不會有羽毛的。好了,快滾開吧(piss off)。」 「滾開?滾開?」他們面面相覷後又看著他。他用錯詞了,這是個無法向他們解釋的字眼,尿(piss)這個字並不會讓他們覺得受辱。「什麼叫滾開?」 「走開!」他揮舞著床單,他們一哄而散,沿著沙灘跑走。他們仍然不確定是不是該怕他,或者有多麼怕他。沒聽說他傷害過小孩子,但還不了解他的本性。誰也不知道他會做出什麼事來。
聲 音 「現在我獨自一人了,」他大聲說。「完完全全地一個人,獨自傍著寬闊的海。」燃燒中的剪貼簿的片段又飛進腦中。 更正:海岸。 他需要聽到人的聲音——真正的人聲,就像他的聲音。有時他笑得像隻鬣狗,或是吼得像隻獅子——他所知道的鬣狗,他所知道的獅子。小時候他曾在老DVD片子裡看過那些動物:動物紀錄片,展現牠們的交配、咆哮,牠們的隱密生活,以及母獸舔著幼崽的鏡頭。為什麼在當時給了他莫大的安慰呢? 他要不像那些器官豬(pigoon)般地嘓嘓尖叫著,或是像狗狼(wolvog)般地嚎叫著:「嗷嗚!嗷嗚!」有時候天色微暗他就會在沙地上跑來跑去,把石頭扔進海裡並大吼著:「他媽的,他媽的,他媽的,他媽的,他媽的,他媽的!」然後他會覺得好過些。 他站起身伸展雙臂,床單掉了下來。他低頭懊惱地看著自己的身體:蟲叮蚊咬過的骯髒皮膚,一簇簇黑白相間的體毛,日益增厚的黃色腳趾甲。像剛出生那天一樣赤裸,並不是他記得這些;有許多重大的事件悄悄地在發生著,在他們無法注意的時候:比方說出生與死亡時,還有做愛時的那種忘我。 「想都別想。」他告訴自己。性就像是喝酒,一大早滿腦子就想到這事是很糟糕的。 他以前維持得很好,跑步、在健身房裡鍛鍊;現在他可以看見自己的肋骨了,他正日益消瘦。動物性蛋白質攝取不足。一個女聲在他耳邊溫柔地說,「好漂亮的屁股!」不是奧麗克絲,是別的女人;奧麗克絲不再喜歡說話了。 「說話吧,」他懇求她。她聽得見他,他需要相信這一點,可是她只給了沉默。「我能做些什麼?」他問她。「你知道我……」 「哦,好棒的腹肌!」耳語又打斷了他的話。「寶貝,躺著就好。」是誰?某個他找來的妓女。更正,職業性技專家。高空鞦韆表演者,附著在她身上的塑膠尖刺,還有亮晶晶如魚鱗般的裝飾。他痛恨這些回音。以前的聖徒也曾聽到過,他們都是些瘋瘋癲癲、滿身蝨子的隱士,住在山洞和沙漠裡。很快地,他就會看見妖冶的魔鬼向他招手,舔著唇,露出火辣辣的乳頭,伸吐著粉紅的舌頭。美人魚將越過水裡那些搖搖欲墜的塔樓踏浪而來,他會聽見她們嫵媚的歌聲,然後游向她們,再被鯊魚吃掉。長著女人腦袋和胸脯及鷹爪的動物將從天而降,他會敞開胸懷去迎接,而那就完蛋了。魂飛魄散。 或者更糟糕的是,某個他知道或認識的女孩將會穿過樹林款款走向他,她會很高興見到他,但她卻是空氣做的。即便如此他也歡迎,有人作伴吧。 他用有鏡片的那隻眼睛掃視了一下地平線:空空如也。大海像一塊灼熱的金屬,天空是那種漂白過的淺藍色,此外只有太陽在上面燙出的一個洞。一切都那麼空盪盪的。水,沙灘,天空,樹林,流逝的時光碎片。沒有人聽得到他。 「克雷科!」他嚎叫道。「混蛋!滿腦子都是屎!」 他傾聽著。鹹鹹的水又沿著臉頰流下來,他永遠不知道這何時會發生也無法阻止。他喘著大氣地呼吸,彷彿一隻巨掌攫住了他的胸口——抓住,放開,抓住。蠢人自擾。 「都是你害的!」他朝著大海吼叫。 沒有回答。這並不奇怪,只有波濤拍岸,呼啦嘩啦,呼啦嘩啦。他握著拳頭擦臉,擦著灰土、淚水、鼻涕、落魄者留的那種落腮鬍以及黏稠的芒果汁液。「雪人,雪人,」他說。「找回生活啊!」 2 火 堆 從前從前,雪人不叫雪人,他叫做吉米。那時他是個乖孩子。 吉米最早的完整記憶是一大片火。他應該有五歲了,也許六歲。他穿著紅雨鞋,兩隻鞋尖都畫有鴨子的笑臉;他記得的原因是因為看過火燒之後他得穿著雨鞋走過消毒池。他們說消毒劑有毒,別弄得水花四濺。於是他就擔心毒素會鑽進鴨子的眼睛弄痛它們。他們說那些鴨子只是圖案,不是真的,所以沒有感覺,但他不太相信。 那麼就當是五歲半吧,雪人想。大概沒錯。 那時可能是十月,或者十一月;樹葉仍然在變換著顏色,橘紅色和紅色。腳踩著泥濘——他一定是站在泥土地上——還下著毛毛雨。被燒的是一大堆牛、羊、豬,腿還僵直地伸出來,已經澆上了汽油;火焰沖天而起,黃色、白色、紅色和橘紅色,一股焦肉味瀰漫在空氣中。有點像他爸爸在後院烤肉的味道,但更濃些,並夾雜著汽油味以及毛髮燒焦的味道。 吉米知道毛髮燒焦的味道。因為他曾用指甲剪剪下自己的頭髮,用媽媽抽菸的打火機去燒。那些頭髮卷起來,扭動地像一團細小的黑蟲。他又剪了些頭髮來燒。被發現時他前額的頭髮已剪得像狗啃的,被罵時他說那是一項實驗。 他爸爸笑了,而媽媽卻沒有。(爸爸說)至少吉米還懂得把頭髮剪下來之後再燒;媽媽說他沒把屋子燒了已是萬幸。然後他們又為了那只打火機爭執起來,(爸爸說)要是媽媽不抽菸打火機就不會在那兒了。媽媽說所有小孩根本都是縱火狂,就算沒有打火機也會用火柴。 他們開始爭吵,吉米就如釋重負,因為他知道不會受到懲罰。他所要做的就是閉上嘴,很快他們便會忘記當初為什麼吵起來。但他也感到內疚,都是他的緣故。他知道吵架將會以摔門結束。他越來越蜷縮在椅子裡,爭吵聲在他頭上颼颼地飛來飛去,最後門重重地關上了——這次是他媽媽——隨之而來的是一股風。摔門時總會有一股風,「噗」的一聲,就在他耳邊。 「沒關係,小夥子,」他爸爸說。「女人總愛氣得臉紅脖子粗3,她會冷靜下來的。我們來吃點冰淇淋。」於是他們用畫有紅色、藍色鳥的吃玉米穀片的大碗吃覆盆子冰淇淋,大碗是墨西哥的手工製品所以不能用洗碗機洗。吉米吃光了他的那份,讓爸爸知道一切都沒問題。 女人,以及她們衣領內的事情。她們的羅衫之下是帶著奇異的麝香味道的錦繡國度,那兒天氣多變,忽冷忽熱——神祕、珍貴、難以控制。這就是他爸爸的理解。可是他從來沒有研究過男人的體溫;他小的時候爸爸也沒提過這個,只會說,「別太熱衷了。」為什麼沒說過呢?為什麼對男人衣領內的火氣就隻字不提呢?那些光滑而線條分明的領子及硬挺的深褐色襯裡。他原本可說出一番道理來的。 第二天他爸爸帶他去櫥窗貼有一位噘著嘴穿著一邊快滑下肩膀的黑色T恤漂亮女孩照片的地方剪頭髮,那女孩瞪著一雙炭黑色的眼睛,迷離又害羞,頭髮像刺蝟。屋裡瓷磚地上到處都是頭髮,成綹成綹地;店裡的人正用長柄闊掃帚將頭髮掃起來。吉米先是被罩上了黑色披肩,但看起來比較像是圍兜。吉米不想披著,因為像是小娃娃用的。理髮師笑著說這不是圍兜,因為哪個小孩會用黑圍兜?所以就沒問題了。接著吉米整頭頭髮都被剪短了,為了和那狗啃地方一樣齊,這可能正是他當初所想要的一頭短髮。理髮師從罐子裡挖了點什麼撥弄成豎直的髮型,聞起來像橘子皮。他朝鏡子裡的自己笑笑,接著又怒目而視,推擠著眉毛。 「硬漢,」理髮師向吉米爸爸點點頭說。「好一隻老虎。」他把吉米剪下來的頭髮撣到地上與其餘的頭髮一起,然後用誇張的動作解開黑披肩,將吉米放下來。 吉米在火堆旁很為那些動物著急,因為牠們正被燒烤著而那一定會使牠們受傷。不會的,爸爸告訴他,動物已經死了。牠們就和牛排、香腸一樣,只不過還帶著皮而已。 牠們有頭,吉米想,牛排沒有頭。有頭就不同了。他想他能看見動物們透過燃燒著的眼睛責備地看著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所有這些火堆、燒焦味,但最重要的是這些被燒著的、正在受罪的動物都是他的錯,因為他沒做任何能挽救牠們的事。那時他發現火堆很漂亮,閃閃發光像棵聖誕樹,不過是棵著了火的聖誕樹。他希望會有爆炸聲,就像電視上那樣。 吉米的爸爸在他身邊,一直牽著他的手。「把我舉起來,」吉米說。他爸爸以為他想更舒服些,將他抱起來。吉米的確是想更舒服些,但也為了看得更清楚。 「就這麼結束了。」吉米爸爸說,他不是對吉米說,而是對和他們站一起的一個男人說。吉米的爸爸語氣裡帶著惱怒,那個男人回答時也如此。 「據說是有人故意帶進來的。」 「我不會覺得奇怪。」吉米爸爸說。 「我可以拿一隻牛角嗎?」吉米說。他覺得不留起來很可惜。他想要兩隻,但可能會被罵。 「不可以,」他爸爸說。「這次不行,小夥子。」他拍拍吉米的腿。 「哄抬肉價,好狠賺一筆,他們會這麼做。」那個男的說。 「是賺了一筆,」吉米爸爸帶著厭惡的口吻說。「但也可能是哪個瘋子幹的,邪教分子,誰知道呢。」 「為什麼不行?」吉米說。別人都不想拿牛角,這次他爸爸沒理他。 「問題是,他們怎麼做的?」他說。「我本來就認為我們的人把我們蒙在鼓裡。」 「我也這麼想。我們付的錢夠多了,那些傢伙是幹什麼吃的?養他們不是讓他們睡大覺的。」 「也許被買通了,」吉米的爸爸說。「他們會去查銀行轉帳,不過把這種錢一直留在銀行裡那也是蠢到家了。不管怎麼說,有人人頭要落地了。」 「仔細調查就是了,我可不願意跟他們一樣,」那個男子說。「哪些人是從外面進來的?」 「修理工,還有那些開廂型貨車送貨的。」 「他們應該讓自己的人來做這些事。」 「我聽說計畫是這樣的,」他爸爸說。「這種病毒是新的,我們已在顯微鏡下拍到了。」 「那種遊戲可以有兩個人玩。」男子說。 「多少人玩都行。」吉米的爸爸說。 「為什麼要燒那些牛羊?」吉米第二天問爸爸。他們正在吃早餐,他們三個都在,所以那應該是星期天。那是他爸媽會同時在早餐時出現的時候。 吉米的爸爸正在喝第二杯咖啡。他邊喝邊在一張滿是數字的紙上寫著。「牠們必須燒掉,」他說,「防止擴散。」沒有抬頭。他隨意撥弄著袖珍計算機,用鉛筆快速寫著。 「防止什麼擴散?」 「疾病。」 「什麼叫疾病?」 「比如你咳嗽了,就是一種病。」他媽媽說。 「要是我咳嗽了,會把我燒了嗎?」 「很有可能。」他爸爸說著翻過那頁紙。 吉米很害怕,因為一周前他咳嗽過,隨時可能會再咳的;他的喉嚨好像卡著東西。他能想見自己的頭髮著火了,不是像盤子裡的一兩簇,而是所有長在他頭上的。他不想被和牛啊豬啊什麼的堆在一起。他哭了起來。 「跟你說過多少次了?」他媽媽說。「他還小。」 「爹地是壞蛋,」吉米的爸爸說。「開個玩笑嘛,小傢伙。你知道的——玩笑。哈哈。」 「他不懂這種玩笑。」 「他當然懂,對吧,吉米?」 「對。」吉米抽抽噎噎地說。 「別吵爹地,」他媽媽說。「爹地正在思考,那是他的工作。他現在沒時間陪你。」 他爸爸把鉛筆一扔。「哎呀,你就不能等會兒再抽嗎?」 他媽媽把香菸丟進喝了一半的咖啡裡。「來,吉米,我們去散步。」她抓住吉米的手腕拉他起來,異常小心地輕帶上後門。兩人甚至沒穿外套;沒外套,沒帽子,她只穿著睡衣和拖鞋。 天空是灰色的,風很冷;她低著頭走著,頭髮被風吹起。他們繞著房子轉,越過濕潤的草坪,手拉手快步走著。吉米感覺自己被有鐵爪的東西在深水裡拖著。他覺得像是挨了一頓打,好像一切都被弄散了捲走了。同時他又覺得精神振奮,他看到媽媽的拖鞋上面沾了潮濕的泥土。如果他的拖鞋也這樣,他就糟糕了。 他們放慢了腳步,然後停住。她媽媽用電視裡女老師那種輕柔好聽的聲音對他說話,這種聲音意味著她在生氣。病菌是看不見的,她說,因為它太小了。它能在空氣中飛或躲進水裡,或沾在小男孩的髒手指上,這就是為什麼你不能用手挖鼻孔或放進嘴裡,為什麼你上廁所後總得洗手,為什麼你不能擦…… 「我知道,」吉米說。「我可以進去了嗎?我很冷。」 他媽媽似乎沒聽見他的話。她繼續用那種平靜的、拖長了的聲音說:「病菌鑽進你體內,改變了裡面的東西。把你的細胞一個個重新排列,這樣細胞就生病了。你是由極小的細胞所構成的,它們一起工作使你保持著活力,而如果生病的細胞到了一定的數目,那你就……」 「我就會咳嗽,」吉米說。「我會咳嗽的,現在就會!」他發出了咳嗽的聲音。 「哦,沒關係。」他媽媽說。她經常想向他解釋,又感到很灰心。那是最難受的時刻,對兩人都是。他會反抗,即便懂也裝不懂,裝出愚蠢的樣子,但他也不願讓她放棄。他要她勇敢,盡可能地對他好,要她推倒他築在他們之間的那堵牆,並與他一同前進。 「我要聽聽那些小細胞的事,」他放肆地嚷道。「我要嘛!」 「今天不行,」她說。「我們進去吧。」
1.
芒 果 雪人在天亮前醒來。他靜靜地躺著,傾聽潮汐湧向岸邊,浪一波接著一波拍打著各種障礙物,呼啦嘩啦,呼啦嘩啦,節奏猶如心跳。他寧願自己仍在睡夢中。 東邊地平線上有團被一道刺眼玫瑰色光芒照耀的灰霧。但奇怪的是,色澤仍然那麼柔和。在晨曦的輝映下,近海處的瞭望台現出黑色輪廓,彷彿矗立在粉紅與淡藍色的珊瑚礁中。築巢的鳥兒發出銳叫聲,夾雜著近處海浪拍打著由生鏽的汽車零件及破磚瓦組成的人工礁石聲,聽起來就像是假日的車潮。 他出於習慣地看了看錶——雖然已經不走動,但不鏽鋼外殼並磨過的鋁製錶帶仍閃閃發亮。他把這...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