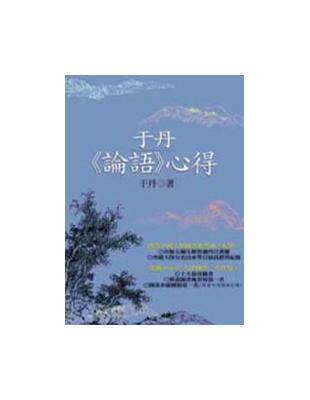天地人之道
宋代開國宰相趙普曾經標榜說,自己以半部《論語》治天下。
可見《論語》在古代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發揮的巨大作用以及古人對《論語》的推崇。
這部曾被譽為治國之本的《論語》,對於我們現代社會,現代人的生活,還有什麼實際意義嗎?
大家別以為,孔夫子的《論語》高不可及,現在我們必須得仰望它。
這個世界上的真理,永遠都是樸素的,就好像太陽每天從東邊升起一樣;就好像春天要播種,秋天要收穫一樣。
《論語》告訴大家的東西,永遠是最簡單的。《論語》的真諦,就是告訴大家,怎麼樣才能過上我們心靈所需要的那種快樂的生活。 說白了,《論語》就是教給我們如何在現代生活中獲取心靈快樂,適應日常秩序,找到個人坐標。
它就是這麼一本語錄。
兩千五百多年前,孔子教學和生活中的點點滴滴,被學生片片斷斷記錄下來。這些以課堂筆記為主的紀錄由他的學生彙集編纂,後來就成了《論語》。
我們會覺得,《論語》好像沒有很嚴密的邏輯性,很多是就事論事,裡面也很少有長篇大論的文字,幾乎每一則語錄都很簡短。
其實,無言也是一種教育。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孔子對他的學生說,你看,蒼天在上,靜穆無言,而四季輪轉,萬物滋生。蒼天還需要說話嗎?
《論語》終極傳遞的是一種態度,是一種樸素的、溫暖的生活態度。孔夫子正是以此來影響他的弟子。
大家知道,孔子弟子三千,其中有七十二賢人。他們每個人都是一粒種子,把那種生活的態度、生活的智慧廣為傳播。
我們說孔夫子是聖人,聖人就是在他生活的這片土地上最有行動能力,最有人格魅力的人。神聖神聖,神基本上是接近天空的,是像李白那樣的人;而聖是接近土地的,是像杜甫那樣的人。
孔聖人帶給我們的是一種在大地上生長的信念,他這樣的人一定是從我們的生活裡面自然生長脫胎出來,而不是從天而降的。
中國的創世神話是盤古開天闢地,但這個開闢不是像西方神話講的那種突變,比如說拿一把大斧子,啪,劈開,然後金光四射出現一個什麼樣的天地萬物,這不是中國人的敘事情感。
中國人習慣的敘事是像《三五曆紀》裡面描述的那樣,是一個從容、和緩而值得憧憬的漫長過程:
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
它說開始時「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在裡面待了一萬八千年。後來天地分開了,但它不是作為一個固體「啪」地從中間斷裂,而是兩股氣逐漸分開,陽清之氣上升為天,陰濁之氣下降為地。
這並不是天地開闢的完成,這種成長才剛剛開始。
中國人是講究變化的。你看,盤古在天地之間「一日九變」,像一個新生的嬰兒,每天都在微妙地變化著。
這種變化最終達到了一個境界,叫做「神於天,聖於地。」
這六個字其實是中國人的人格理想:既有一片理想主義的天空,可以自由翱翔,而不妥協於現實世界上很多的規則與障礙;又有腳踏實地的能力,能夠在這個大地上去進行他行為的拓展。
只有理想而沒有土地的人,是夢想主義者不是理想主義者;只有土地而沒有天空的人,是務實主義者不是現實主義者。
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就是我們的天和地。
盤古的變化還在繼續,這個故事還要接著講:天地開闢之後,天每天升高一丈,地每天加厚一丈,盤古也「日長一丈」,跟著天地一塊兒長。如此又過了一萬八千年,最後是「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人的意義跟天和地是一樣的,天地人並稱為「三才」。所以,在孔子看來,人是值得敬重的,人又是應該自重的。
讀《論語》我們會發現,孔夫子教育學生時很少疾言厲色,他通常是用和緩的,因循誘導的,跟人商榷的口氣。這是孔夫子教學的態度,也是儒家的一種態度。
我們見到一些老師聲色俱厲,經常指責他的學生不該如何如何。那是這個老師沒有到境界,真正好的老師會像孔夫子這樣,平和地跟學生商量著把這種天地人三才共榮共生的關係講透。這樣一種從容不迫的氣度,這樣一種謙抑的態度,其實正是中國人的人格理想。
與西方不同,中國哲學崇尚的是一種莊嚴、理性和溫柔敦厚之美。《論語》中孔夫子的形象,就是這樣一種審美理想的化身。
在孔夫子這個形象身上,凝聚著他內心傳導出來的一種飽和的力量。這種力量就是後來孟子所說的「浩然之氣」。
只有當天地之氣凝聚在一個人心中的時候,它才能夠如此的強大。
《論語》的思想精髓就在於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精華融入人的內心,使天、地、人成為一個完美的整體,人的力量因而無比強大。 我們今天也常會說,天時、地利、人和是國家興旺、事業成功的基礎,這是《論語》對我們現代人的啟發。
我們永遠也不要忘記天地給予我們的力量。什麼叫天人合一?就是人在自然中的和諧。
我們努力創建和諧社會,而真正的和諧是什麼?
它絕不僅僅是一個小區鄰里間的和諧,也不僅僅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還一定包括大地上萬物和諧而快樂地共同成長;人對自然萬物,有一種敬畏,有一種順應,有一種默契。
這是一種力量,我們如果學會了提取鍛造這種力量,我們就能夠獲得孔夫子那樣的心胸。
我們看到,孔夫子的態度非常平和,而他的內心卻十分莊嚴。因為其中有一種強大的力量,那是信念的力量。孔夫子是一個特別講究信念的人。
他的學生子貢問,一個國家要想安定,政治平穩,需要哪幾條呢?這個故事在《論語》裡叫做「子貢問政」。
孔子的回答很簡單,只有三條:足兵,足食,民信之矣。第一,國家機器要強大,必須得有足夠的兵力做保障。第二,要有足夠的糧食,老百姓能夠豐衣足食。第三,老百姓要對國家有信仰。
這個學生矯情,說三條太多了。如果必須去掉一條,您說先去什麼? 孔夫子說:「去兵。」咱就不要這種武力保障了。
子貢又問,如果還要去掉一個,您說要去掉哪個? 孔夫子非常認真地告訴他:「去食。」我們寧肯不吃飯了。
接著他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沒有糧食無非就是一死,從古而今誰不死啊?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國民對這個國家失去信仰以後的崩潰和渙散。物質意義上的幸福生活,它僅僅是一個指標;而真正從內心感到安定和對於政權的認可,則來自於信仰。
這就是孔夫子的一種政治理念,他認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個國家凝聚起來。
現在有一種說法,說二十一世紀評估各個國家人民生活得好與不好,已經不是過去簡簡單單GNP(國民生產總值)一個標準,還要看GNH,就是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國民幸福指數。
也就是說,評估一個國家是不是真正富強,不能單純看國民生產總值的絕對量和增長速度,更要看每一個老百姓內心的感受││他覺得安全嗎?他快樂嗎?他對他的生活真正有認同嗎?
中國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曾經參加過一次國際調查,資料顯示,當時國民的幸福指數只有百分之六十四左右。一九九一年再次參加調查,這個幸福指數提升了,到了百分之七十三左右。這得益於物質生活條件的提升和很多改革措施的實施。
但等到一九九六年再參加調查時,發現這個指數下跌到了百分之六十八。 這是一件很令人困惑的事情。它說明,即使一個社會物質文明極大繁榮,享受著這種文明成果的現代人仍然有可能存在極為複雜的心靈困惑。
讓我們回到兩千五百多年以前,看看就在那樣一個物質匱乏的時代,那些聖賢是什麼樣子。
孔夫子最喜歡的一個學生叫顏回,他曾經誇獎這個學生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
就是說,顏回家裡很窮,缺衣少食,住在非常破爛的小巷子裡。這麼艱苦的生活對別人來說簡直難以忍受,而顏回卻能夠自得其樂。
也許很多人會說,生活就是這樣,窮日子富日子都得過,那有什麼辦法? 顏回真正令人敬佩的,並不是他能夠忍受這麼艱苦的生活境遇,而是他的生活態度。在所有人都以這種生活為苦,哀歎抱怨的時候,顏回卻不改變他樂觀的態度。
只有真正的賢者,才能不被物質生活所累,才能始終保持心境的那份恬淡和安寧。誠然,誰都不願意過苦日子,但是單純依靠物質的極大豐富同樣不能解決心靈的問題。
我們的物質生活顯然在提高,但是許多人卻越來越不滿了。因為他看到周圍總還有乍富的階層,總還有讓自己不平衡的事物。
其實,一個人的視力本有兩種功能:一個是向外去,無限寬廣地拓展世界;另一個是向內來,無限深刻地去發現內心。我們的眼睛,總是看外界太多,看心靈太少。
孔夫子能夠教給我們的快樂秘訣,就是如何去找到你內心的安寧。
人人都希望過上幸福快樂的生活,而幸福快樂只是一種感覺,與貧富無關,同內心相連。在《論語》中,孔夫子告訴他的學生應該如何去尋找生活中的快樂。這種思想傳承下來,對歷史上許多著名的文士詩人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子貢曾經問老師:「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假如一個人很貧賤,但他不向富人諂媚;一個人很富貴,但他不傲氣凌人。這怎麼樣? 老師說,這很不錯。但還不夠。還有一個更高的境界,叫做「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更高的境界是,一個人不僅安於貧賤,不僅不諂媚求人,而且他的內心有一種清亮的歡樂。這種歡樂,不會被貧困的生活所剝奪,他也不會因為富貴而驕奢,他依然是內心快樂富足、彬彬有禮的君子。
這是多高的驕傲啊!一個人能夠不被富足的生活蠱惑,又能在貧賤中保持著做人的尊嚴和內心的快樂。
這樣一種儒家思想傳承下來,使我們歷史上又出現了很多內心富足的君子。東晉大詩人陶淵明就是其中之一。
陶淵明曾經當過八十三天的彭澤令,那是一個很小的官。而一件小事,便讓他棄官回家。有人告訴他,上級派人檢查工作,您應當「束帶見之」。就如同今天,你要穿正裝,繫領帶,恭敬地去見主管。
陶淵明說,我不能為五斗米向鄉里小兒折腰。就是說,他不願意為了保住這點做官的「薪水」而向人低三下四。於是把佩印留下,自己回家了。回家的時候,他把自己的心情寫進了〈歸去來兮辭〉。 他說,「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我的心靈已經成了身體的奴僕,無非是為了吃得好一點,住得好一點,就不得不向人低三下四、阿諛奉承,我的心靈受了多大委屈啊! 他不願意過這樣的生活,「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於是就回歸到自己的田園。
陶淵明的意義,不在於在詩中構置了一個虛擬的田園,更重要的是,他讓每一個人心裡都開出了一片樂土。
安貧樂道,在現代人眼中頗有些不思進取的味道。在如此激烈的競爭面前,每個人都在努力發展著自己的事業,收入多少、職位高低,似乎成了一個人成功與否的標誌。
但越是競爭激烈,越是需要調整心態,並且調整與他人的關係。那麼,在現代社會,我們應該如何為人呢?
又是子貢,問了老師一個非常大的問題,他說:「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您能告訴我一個字,使我可以終身實踐,並且永久受益嗎?
老師以商量的口氣對他說:「其恕乎!」如果有這麼個字,那大概就是「恕」字吧。什麼叫「恕」呢?老師又加了八個字的解釋,叫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你自個兒不想幹的事,你就不要強迫別人幹。人一輩子做到這一點就夠了。
什麼叫「半部《論語》治天下」?有時候學一個字兩個字,就夠用一輩子了。這才是真正的聖人,他不會讓你記住那麼多,有時候記住一個字就夠了。孔子的學生曾子也曾經說過:「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說我老師這一輩子學問的精華,就是「忠恕」這兩個字了。簡單地說,就是要做好自己,同時要想到別人。
拓展一點說,「恕」字是講你不要強人所難,不要給別人造成傷害。言外之意是假如他人給你造成了傷害,你也應該盡量寬容。
但是,真正做到寬容談何容易。有很多時候,一個事情本來已經過去了,而我們還是老在那兒想,這麼可惡的事,我怎麼能原諒它呢?然後就在不斷的自我咀嚼中,一次一次再受傷害。
佛家有一個有意思的小故事: 小和尚跟老和尚下山化緣,走到河邊,見一個姑娘正發愁沒法過河。老和尚對姑娘說,我把你背過去吧。於是就把姑娘背過了河。
小和尚驚得瞠目結舌,又不敢問。這樣又走了二十里路,實在忍不住了,就問老和尚說,師父啊,我們是出家人,你怎麼能背著那個姑娘過河呢? 老和尚就淡淡地告訴他,你看我把她背過河就放下了,你怎麼背了二十里地還沒放下?
這個故事的道理其實和孔夫子教給大家的一樣,該放下時且放下,你寬容別人,其實是給自己留下來一片海闊天空。
所以什麼叫「仁者不憂」呢?就是讓你的胸懷無限大,很多事情自然就小了。
在生活中,每個人都有可能遭遇失業、婚變、朋友背叛、親人離去等等這些事情,它對你是大事還是小事,沒有客觀標準。
這就如同劃個一寸長的口子,算大傷還是小傷?如果是一個嬌滴滴的小姑娘,她能邪乎一星期;如果是一個粗粗拉拉的大小夥子,他可能從受傷到這個傷好,一直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的內心究竟是做一個嬌滴滴的「小姑娘」,還是一個粗粗拉拉的「大小夥子」,完全可以由自己決定。
其實,《論語》告訴我們的,不僅遇事要拿得起放得下,還應該盡自己的能力去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所謂「予人玫瑰,手有餘香」,給予比獲取更能使我們心中充滿幸福感。
大家知道,儒家理論的核心和最最精髓的東西,除了「恕」字以外,還有一個是「仁」字。
孔子的學生樊遲曾經畢恭畢敬地去問老師什麼叫仁?老師只告訴他兩個字:「愛人」。愛別人就叫仁。 樊遲又問什麼叫智?老師說:「知人。」了解別人就叫智慧。
關愛別人,就是仁;了解別人,就是智。就這麼簡單。
那麼,怎樣做一個有仁愛之心的人呢? 孔子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也》) 你自己想有所樹立,馬上就想到也要讓別人有所樹立;你自己想實現理想,馬上就會想到也要幫助別人實現理想。能夠從身邊小事做起,推己及人,這就是實踐仁義的方法。
我記得大學英語課本上,有一則西方哲人寫的小寓言,說有一個國王每天都在思考三個最最終極的哲學問題:在這個世界上,什麼人最重要?什麼事最重要?什麼時間做事最重要?
就這三個問題,舉朝大臣,沒人能夠回答得出來。他很苦悶。後來有一天,出去微服私訪,走到一個很偏遠的地方,投宿到一個陌生的老漢家。 半夜裡,他被一陣喧鬧聲驚醒,發現一個渾身是血的人闖進老漢家。那個人說,後面有人追我。老漢說,那你就在我這兒避一避吧。就把他藏起來了。
國王嚇得不敢睡,一會兒看見追兵來了。追兵問老漢,有沒有看到一個人跑過來?老頭說,不知道,我家裡沒有別人。
後來追兵走了,那個被追捕的人說了一些感激的話也走了。老漢關上門繼續睡覺。第二天國王問老漢說,你為什麼敢收留那個人?你就不怕惹上殺身之禍?而且你就那麼放他走了,你怎麼不問他是誰呢?
老漢淡淡地跟他說,在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就是眼下需要你幫助的人,最重要的事就是馬上去做,最重要的時間就是當下,一點不能拖延。 那個國王恍然大悟,他那三個久思不解的哲學問題,一下都解決了。
這個故事,又可以做《論語》的注腳。 實際上,孔子也罷,莊子也罷,陶淵明、蘇東坡直至泰戈爾,古今中外聖賢的意義是什麼呢?就是用他們對生活的體驗,總結出一些對我們每個人都有用的道理。
這些道理不是那些磚頭一樣的典籍,讓你要拿著放大鏡,翻著《辭海》去讀,非常吃力地去參悟一輩子。真正的聖賢不會端起架子、板著面孔說話。他們把活潑潑的人生經驗,穿越滄桑,傳遞到今天,讓我們仍然覺得溫暖;而他們在千古之前,緘默地微笑著、注視著,看我們仍然在他們的言論中受益而已。
子曰:「予欲無言。」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論語.陽貨》
子貢問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論語•顏淵》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
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論語•學而》
我們的眼睛, 看外界太多,看心靈太少。 ──于丹心語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論語•衛靈公》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曾子曰:「唯。」
子出。
門人問曰:「何謂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論語•里仁》
你寬容一點, 其實給自己留下來一片海闊天空。 ──于丹心語
樊遲問仁。
子曰:「愛人。」
問知。
子曰:「知人。」
樊遲未達。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 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論語•顏淵》
關愛別人,就是仁慈; 了解別人,就是智慧。 ──于丹心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