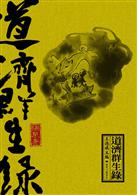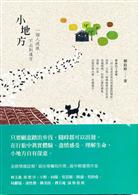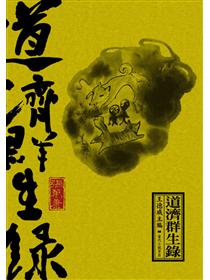一
與其說是攝影,不如說是男孩以單眼相機這樣的昂貴設備做為面具,一方面遮掩色慾,一方面替窺視的雙眼打開一扇窗。
當梅雨的氣味終於浸透了象山,女孩也來到他門前。
她穿著粉紅色背心與牛仔短褲,帶著一個抽煙的男孩,站在他的工作室門口,問他可否借地方拍照。
「我們攝影師說這裡有很多木雕佛像,氣氛很特別。」她兩手合掌頂在下巴,拜託他:「我們只拍一個下午就好。」
他無意回答,拿起雕刻刀,修飾檯燈下的木雕觀音。
女孩靠近他,彎下腰,兩隻套著紅色碎花拖鞋的腳掌踏進燈下,他不悅地抬頭,正面迎上女孩的笑臉,女孩耳際的幾撮細髮垂落下來,散在他額頭,說:「拜託,這是學校作業。」
他之所以答應,並非源於女孩的美貌,事實上,女孩的外貌並不出色,除去胸與臀,膚色偏黃,嘴唇太薄,鼻子不挺,兒童一般的輪廓,缺乏女性的魅力。但是女孩的眼尾有著一顆小小的黑痣,配上那張童稚的臉,令他想起早夭的女兒。
擔任攝影師的男孩說保證不會影響他工作,但事實並非如此。女孩旁若無人地在他的工作室裡褪去衣服,換上過小的白色上衣,以及黑色百褶短裙。攝影師男孩叫女孩靠在、躺在、趴在他尚未完成或已完成正待取件的作品上,幾次他正要下刀之際,閃光燈啪一聲亮起,令他瞬間目盲。他收起雕刻刀,轉過身想請他們離開,卻看見女孩跪坐在牆角,短裙拉至膝蓋上方,攝影師換上長鏡頭,也跟著蹲低。
他發現,每當攝影師放下相機,目光都是落在女孩大腿間的陰影,他不再多說什麼,轉而將自己當作一個觀眾,站在一旁觀察兩人的互動。
學生時期他修過攝影課,也曾開過幾次個人攝影展,他看得出男孩只有九流的技術與三流的光線概念,僅有器材是一流的。與其說是攝影,不如說是男孩以單眼相機這樣的昂貴設備做為面具,一方面遮掩色慾,一方面替窺視的雙眼打開一扇窗。
年輕人的色慾,他在心裡如此嘲笑。就他看來,這個男孩終其一生都必須靠著掩飾或工具,才能滿足自我。在這具年輕的軀體裡面,除了體力,沒有其他能使色慾圓熟至爆發的可能。男孩命令女孩張腿、抬腿、蹲下、起立,擺出各種姿勢,然後透過照相機的鏡頭,把自己投入觀景窗中的某個位置,以此演繹各種體位,但何必如此?那些行為看似來自內在情感的表現,實則不過是偽裝,人們為了引誘他人而擺弄出各種姿態與行為,並非是為了表達內在情感,而是要將之扭曲,以符合他人的美好想像。
那都是外在的雜質罷了。
以他多年的雕刻及嫖妓經驗,他知道如何蛻去雜質,直取核心。就像從木頭中挖掘出一尊觀音像,那並不是他將木頭刻成觀音,而是觀音本來就在木頭裡,他只是藉由雕刻,除去雜質,讓觀音從中顯露。他觀察女孩的外在,眼神如愛撫落在女孩身上每一處,將女孩視為一塊木材,以藝術家的眼光直視女孩在面露羞澀的同時眼尾藏笑,女孩在攝影師男孩的要求下擺出幾個姿勢,轉頭望向站在男孩背後的他,羞怯地摀著臉說真不好意思。
他突然心底湧起一股惡意,看出女孩正同時勾引著兩個男人,好其想知道這個女孩是什麼滋味,與他經歷且傷害過的那些女人有什麼不同,究竟該怎麼做,女孩才真會打從心裡感到羞怯甚至是羞恥。
但當他又看見女孩眼尾那顆黑痣,原本打算施加在女孩身上的羞恥感便突然回到他身上。對一個未成年且一臉童稚的女孩起這種念頭,他感到這是情場浪子與禽獸的差別。他搖搖頭,走出工作室,撐起一把傘,走向外頭的山路,在細雨中點起一根煙。
一口比霧氣還濃比春雨還輕淡的煙隨著他的嘆氣飄遠,尼古丁稍微軟化他緊繃的肩膀,他撥開偶爾擋住他去路的竹枝,努力將注意力從肩頸交接處的疼痛轉移到對作品的思考。
自從受傷後,他整天有一半以上的時間受困於激烈的疼痛中,他看過許多醫生卻沒有改善,有時甚至手麻而難以工作。醫生說是受傷的頸椎壓迫到神經,需要做進一步的核磁共振,或許還需要開刀,但妻子過世後,他便沒有完成新的作品,也沒有新的收入,開刀手術風險過高,也許會斷絕他的創作生涯,他無法如此冒險。
手上的煙燒到盡頭,他想將煙蒂丟進男孩車裡,卻發現外面道路上沒有停放汽車或機車,他猜想女孩與男孩可能是從捷運站下車後,沿路閒逛,也許是看見四獸山頭雲霧繚繞,而跟著登山客的路線走向都市邊緣的山區,一路走向半山腰,來到他的工作室。
他的工作室位置並不高,只是特殊的地形與氣候使然,較為潮濕的日子裡,四周便被山嵐所籠罩,有時眼前的台北盆地只是一片蒼白,交錯縱橫的都市建築猶如毛玻璃上的細紋,在雲霧中僅剩輪廓,僅有城市中心的超高大樓像一根針,直直地插在盆地上,有時,令他覺得整個城市有如一個不斷抗拒改變方向的陀螺儀,忙碌地原地旋轉,那棟超高層大樓是軸心,而象山在城市邊緣拔地而起,便是一個置身事外的觀測點。
由於附近地勢突如其來變得陡峭,往來的車輛大多選擇不穿越這座山丘,到了雨天,人車更少,雨聲掩蓋風聲蟲鳴,遠方山下的車流靜靜地劃過一條條光痕,奔馳而去,在夜裡,這裡只被浪一般的雨聲所佔據。
他丟掉第三根煙,並往回走,正好看見女孩與男孩從他的工作室走出來,女孩已經換回原本的衣服,走到他身邊跟他道謝,男孩則是低頭整理背包裡的攝影器材,沒有與他交談。
他們兩人撐著雨傘,路燈打在濕滑的柏油路上,更顯出山路的陡峭,他們緊抓著路邊的欄杆,側著身體往下走,沒多久身影便隱沒不見。他沒有打算告訴他們,山裡的夜黑得很快,他們恐怕找不到下山的路。畢竟他們粗魯地打擾了他,且他向來不是一個溫柔和善的人。
入夜之後,他的門鈴響起,女孩與男孩又來到他門前。一樣是男孩默不作聲站在女孩身後,女孩以天真無辜的表情告訴他找不到下山的路,求他讓他們借宿一晚。
「當然,這裡是都市邊緣。」他說。
可能是淋了雨,女孩的頭髮與衣服都濕透了,他很願意站在窗邊看著他們被拒絕後沿路下山不知所措的樣子,也許還會發現周遭起伏的草叢全是墳墓而感到驚恐,但他卻違背了自己的意志,開門讓他們進來。
他在他們分別進入浴室洗澡後在工作室的地板上鋪上一層床墊,將沙發上的長抱枕擺在上面充當枕頭,囑咐他們不可亂動工作室的木材與雕刻,也不可以在工作室抽煙,便獨自走回樓上房間。
他們並不知道,為了防盜,他的工作室裡裝了數台針孔攝影機,在他上樓後,躺在床墊上的男孩將女孩拉往懷中,女孩枕在男孩手臂上,雙手高舉著單眼數位相機,逐格看著男孩所拍的照片,男孩側身以另一隻手握住女孩胸部,膝蓋上提放在女孩小腹上,以腳指夾住女孩內褲褲頭往下拉。
他無意偷窺他們,只是想確認男孩沒有在工作室裡抽煙,在男孩褪下女孩內褲時就打算關掉監視器,但當他看見男孩將頭埋在女孩跨下,而女孩笑著起身將鏡頭對準男孩,說要拍下男孩舌頭進入她體內的一瞬間,他感到突如其來心跳加速。
這是妻子過世後他第一次感到性衝動,來自一個肉體上並不吸引他的女孩。是因為禁慾太久?還是他已不再為妻子的死而感到悲傷?他不曉得確切的原因。
他一直覺得所有女人做愛的神情都很像,妻子也好,他嫖妓的對象也罷,只要適度地讓對方進入狀況,最後都是五官擠在一起哀嚎,與被他傷害後的痛苦神情一樣。
但是女孩不同。
男孩翻身躺下後,女孩起身跨坐在男孩身上,調整姿勢的過程中,她一度彎腰喀喀笑,接著便閉起眼睛,滿足地在男孩身上搖晃起來。此時他才發現,他從未與一個真正喜歡性愛的女性上過床。妻子與妓女,前者冷感後者職業,無法抱著享受的心情迎接他,雖然在累積許多經驗後,他開始懂得要領,懂得如何溫暖她們冰冷的身體,讓她們感到炙熱,讓她們在激烈的浪潮中載浮載沈,然後呼喊,顫抖,痙攣。
但沒有一個像搔癢,像遊戲,像夏日傍晚蹲坐在庭院吃一塊西瓜那麼輕鬆愉快怡然自得。
強烈的空虛感蔓延至他全身,彷彿他從未被女性熱切地包容過。他關掉監視器,走出房間走下樓,繞過樓梯打開後門。外面的雨已停,取而代之的是沿著山坡翻滾而下的山嵐,他走到門外,在濃重的霧氣中點起一根煙,水氣混入煙草中,點燃沒多久便熄滅。他再次點火,將煙靠在火苗上,用力吸了幾口,煙草沾濕後煙味變得較為苦辣。
夜風一路吹向這座陡峭的山丘,把整山的水氣全數往下刮,那些在路燈照映下一圈圈地往下翻滾的嵐霧像是漂流的靈魂,一個一個落入山下的小鎮。
他很慶幸自己搬來這裡,身在都市之中卻又不參與其中,四獸山像是尚未被都市降服的野獸,居住其上便是身處化外之地,若是他依舊住在鹿港,聽著那些被外界視為藝術家的木雕師父盡在名與利上打轉的言語,他也許更早之前便放棄了這門技藝。
他不喜歡鹿港,那是一個被外界特地標示為「傳統」且只能活在傳統中的城市,給予他許多創作上的限制。他認為傳統唯一存在的意義便是要被打破,尤其鎮上的耆老說他們家出了吊死鬼,依據習俗,必須「送肉粽」,將他魂魄驅離至海邊,他勃然大怒揪著耆老的衣領,說不是意外死亡,是窗簾的拉繩意外纏住脖子,不是上吊,不是自殺,不需要「送肉粽」。
當天晚上,不等耆老們的討論做出結論,他便收拾行李離開鹿港。會來到象山,並非出於計畫,他在某個週末下午越過半個台灣西部,跨過台北市中心,準備往東台灣前進,卻在市中心之後的地景中看見不遠處藏身於雲霧之間的象山。他的童年時期與母親一起在南港度過,他的印象中盡是灰濛濛的天空與化工廠排放的滿溝七彩污水,此刻他環顧四周,卻看不見任何一個熟悉的地標,只有象山依舊是象山。他只是為了前往山上的觀音廟祈求保佑,之後無意識地走上廟旁陡峭的山路,直到他感到精疲力竭而回頭一望,赫然發現整個台北的夜景正在他背後點點繁茂地燃燒著,在他茫然不知何去何從之際,這景象像一個天啟,他便決定回到故鄉定居下來。
他有意離群索居,刻意不與昔日友人來往,且這棟位於陡峭山腰上的小房子過於落寞,陰濕黯淡,昔日老友也總來探望他一次後便極少出現,他花了一段時間才適應這裡,一開始,在太安靜的夜裡,他不安地發出一些聲響來確定自己並沒耳聾,室內的光無法傳到遠方,只隱約照出窗外近景的輪廓,草木陰影交錯,向光面與背光面被切割出明與暗的不同面貌,再往外是無盡的黑。無風的夜,空氣沈滯,天上星光顆粒分明,彷彿近在眼前。他關掉燈,便看見林間流洩而出的螢火蟲,在原住民的傳說中,螢火蟲是死人的指甲,他相信這個說法,因為在流動的螢光中,他常聞到各種混雜的、悶悶的腥臭味,也許是某種動物在樹林草叢中腐爛,也許是公墓底下屍體的分解,到了仲夏的夜裡,潮濕悶熱之下,不知從何而來的腥味像極了下水湯的溫熱內臟味,彷彿某個看不見的巨人,正對著山呼出一口又一口溫熱的空氣。
房子裡只有妻子與女兒的牌位陪著他,他希望在此為他們刻一尊觀音,一尊慈悲寬容,會理解並原諒他們三人所有痛苦的觀音神像。
女孩走到他身後時,他正閉眼想像觀音神像的其中一個手勢。女孩的腳步聲驚動他,一轉頭只見女孩僅在上半身套一件寬大的T-Shirt,也許是覺得有點冷,雙手環抱在胸前,看著他。
他起身走近女孩,看不出女孩下半身是否有穿內褲或短褲。
女孩對著他笑,說:「老闆!謝謝你今天收留我們,你真是大好人。」
女孩的身型與五官被濃霧抹淡,只剩一個隱約的外型,他想起剛剛目睹的性愛,衝動地站到女孩身邊,搭著她的肩,說:「小事一件,別客氣。」
他的手掌順勢滑過女孩的後背直到臀部,確認女孩在寬大的衣服下確實是一絲不掛,才收手轉身,走回屋內。
女孩並未受到驚嚇,反而緊緊跟在他身後,在他即將上樓梯時拉住他的手,向前一步,貼著他的臉頰,問:「你願不願意跟我們一起?」
「一起?」
「攝影師說,如果你願意的話,可以一起……」
不等女孩說完,他便推開女孩的手,急速上樓走回房間,坐在床沿發呆。過了一會,他又打開針孔攝影機的監視器。男孩與女孩繼續未完的遊戲,在周遭已完成的、未完成的神像眼神的凝視下,男孩趴在女孩身上蠕動。
他全神貫注地看著畫面中央女孩臉上的紅暈與露齒的微笑,沒有發現畫面角落,有一個不屬於木雕神像或家具的黑影,從門口蔓延至工作室角落堆放廢棄木材的牆角,潛伏在女孩腳邊,安靜,且耐心地,等待某一種時機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