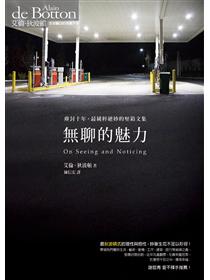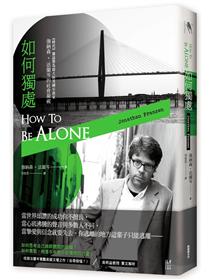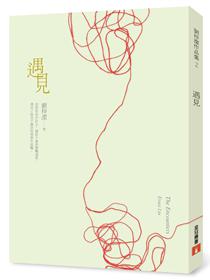永劫回歸的鯤島夢境,等候與背離的擇選之路
現代職場生存百態,你我無可迴避的隔板圈寓言
我回想自己因為駑鈍順從一般人生的進程加入然而不算長的職場生涯,時時心不在焉,陷在那其實絲毫不可笑的生活保障感與明知自己所要卻踟躕不前的困局,惱怒自己的不能當下徹底,痛恨自己的遲緩,然而儘管牛步地與時間、自己的時間並轡且戰且走,現在回頭張望並儘可能忠實寫下這一系列,雖然不得不反芻那些厭憎可鄙同可悲可愛的,才了解那是無可迴避、不可揀擇的必經過程。——林俊頴
輯一:蜂巢
「我們存活其中的這部現代巨獸機器,究竟有什麼是一開始便是敗壞殘廢的呢?」
描繪現代職場中各色工作者樣態,落置於隔板圈如蜂巢空間中,作為一個人的意義與抉擇,波士、馬內夾、上進白領、老人、畸人、打工者,或者是「長了翅膀的蛇」、「野地的獸」及所謂失敗者。幽暗不明的人事爭鬥與曖昧耳語,考驗膽識與貪婪之心的賽局,亢奮而短暫的繁華,瞬間煙消人散的幻滅,以及如常的美好、如夢的虛無。他,一個叛逃者(或臥底者?),像透過放大鏡看病理切片的觀看一切。
輯二:夏天的合音
「我們四周是那個經濟起飛的時代,除了熱風與創造數字成長的意志,一切單調、粗陋、乾旱,然而他們夫妻倆就在那裡。」
脫農入商的父祖輩矢志努力打拚的上進之路,以及盡頭。祖父生意失敗,被譏為「笨蛋老實人」,成為家族夙怨。總是身穿白襯衫的父親一生警醒著不能步上祖父後塵,卻難逃經商一路的挫敗。民國五〇年代末、六〇年代初的夏天,南風猛烈,掀動如巨浪,許多物事再也回不來了。
輯三:大城小鎮
「日與夜移位,我努力不讓我的虛空之屋就這樣虛擲,挪到窗邊搶收最後的天光,希望像燧石點燃書上的字。」
在世界之城,逐夢的異鄉人匯聚之處,如人類學者的探勘觀視,走過現代、後現代商辦高樓,曾經氣派後遭毀滅、現成紀念之所的世貿遺址,在「社會的遊戲、夢幻以及幻想」的地圖上,作為一個旁觀者,思索其間的闖蕩與飄零。
作者簡介:
林俊頴
一九六○年生,彰化人。政治大學中文系畢業,紐約市立大學Queens College大眾傳播碩士。曾任職報社、電視台、廣告公司。著有小說《我不可告人的鄉愁》、《鏡花園》、《善女人》、《玫瑰阿修羅》、《大暑》、《是誰在唱歌》、《焚燒創世紀》、《夏夜微笑》等,散文集《日出在遠方》。
章節試閱
佛滅之日
「路是為了回頭而鋪的,沒有一個人走到終點。」黃皙瑛《悠悠家園》
白領工蟻十三年後,中央空調的辦公大樓依然沒有寒暑感,那一天如同之前無數個工作日,又是一個只有例行工序消磨時間的平淡日子。
我通常是第一批早到的鳥兒,入口感應器讀了員工卡,很久很久以前覺得是阿里巴巴的寶藏祕門、玻璃門打開,空氣陰涼,睡了一晚的機器、文具、影印紙、盆栽、化纖地毯,確實如同古墓的殉葬品,恍惚有靈,而隔板規劃出一格一格的工作空間,又像是訓練白老鼠的迷宮。我無恥地妄想過中子戰後的末日早晨,遊魂歸來,一人得以霸佔整層空間,騎獨輪車,放風箏,充滿了無人的喜悅;落地窗下眺一長排雲龍般美麗的樟、欒樹樹冠,自南徂北。
兩個月前,我桀傲的工作搭檔嗅出已經沒有轉機了,機伶遞上辭呈,那時我還不瞭解「專業者只有自行轉換跑道,沒有留下來被砍頭的」與「革命者只有被殺,沒有自殺的」兩者的差別。整整一年了,辦公室瀰漫著一股窒悶,顯得死氣沉沉,所謂總監的位子懸缺很久了,舊客戶不送新案子,新客戶引不進來。從口水有血絲到吐出一隻鵝的謠言每個月進展,劇本一,雖然是老字號的跨國公司,但總部大頭們見了區域財務報表連續幾年營收溜滑梯,心裡動搖了,唯一時還找不到買主也還不能決定拋售的價碼。劇本二,水流濕,火就燥,對岸兩地正興旺,商人無祖國的決策,果然準備遷往冒險家大樂園去,正在京滬港進行評估、前置作業,樹遷猢猻散的日子不遠了。劇本三、四、五…,我們的生產力與創意有了出口。
我父親彼輩近乎道德潔癖的工作倫理是一日不作,一日不薪,不作而領薪是為賊。他總以日語「泥棒」強化語氣。我與工作搭檔那段時日正是兩條快樂的泥棒,沒有工作不是我們的錯,兩人遂尋寶般吃遍了周圍每一家商業午餐,飯後長長漫遊,自以為是兩塊大磁鐵吸收了沿途這城市的靈光鐵片零件,收藏以待來日大用。
但突然一聲霹靂,掉下了新任總監。搭檔火速打了幾通電話摸清了她的底,找出一本年鑒,指著新總監的代表作,一張修圖的大水管平均對分,一半水流一半嘩嘩啦錢幣,不屑哼道,這老梗也叫創意,憑那半世紀前的埃及艷后髮型來監督指導我嗎?幹。在那傾軋之必要、批鬥之必要、競爭之必要,因此互相鄙視仇視之必要、一點點暴力與羞辱之必要的鋼骨水泥叢林,他或想點醒我的律條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辦公室沒有不可被取代的職位,關係決定一切,我們既然在她的人際網絡最外沿,不是舊識或心腹,要存活下去的兩條路,附勢上去表態效忠,或者自行滾蛋讓出位子避免受辱,走向自己的光明。
一切,蝸角蚊睫的可憐又可恥的鬥爭。我們甚至比不上梭羅於華爾騰湖旁紀錄了紅黑兩隻螞蟻大軍的決死之戰,無論死傷,光明磊落。
「與其給我愛、金錢或名譽,不如給我真理。」真理是,白領工蟻十三年,我平均不到兩年便移支別棲一次,視職場的遊戲規則如糞土,自然被反視為糞土的機率逐年增加。因為土象星座作祟,當我還猶豫著是否也再次遞辭呈,還庸人自擾著工作、薪水的意義是什麼?那早晨我在走道遇見埃及艷后頭皮笑肉不笑的向我打招呼,班雅明的書名變形如一尾響尾蛇昂首咬了我一口,「資本主義發達時代的人啊」。下午,我接到了生平第一道資遣令。
解放之日
借用陳映真《萬商帝君》的譏刺諧音,那昏沉的下午,總「馬內夾」(經理)電召我到他方位採光絕佳的辦公室,有一套設計名師線條簡潔的桌椅陳設,最宜觀賞夏日雷雨。據說他才去了太平洋觀光小島玩海底攝影度假歸來,正值壯年的總馬內夾是張愛玲形容佟振保的,即便衣服肘彎的皺紋也「皺得像笑紋」,卻不願或不敢抬頭直視我,只說了句:「我覺得你還是不適合。」文明地取代了「你被解雇了。」
我不反駁,不爭辯,即使最起碼的為什麼也不問,自然也沒有『推銷員之死』老威利之戲劇化悲憤,「你不能吃了橘子就扔了皮,人可不是水果。」我心底冷笑,「一年了,你才認為我不適合?」
前後不超過兩分鐘,我起身要走,總馬內夾才也起身與我慣性的握手。我去洗了手,隨即新任總監埃及艷后頭扮白臉上場,她的辦公室面積小多了,風格走親和路線;一交手她便知道了我沒有潑硫酸或拿槍掃射的威脅性,虛張聲勢的開心朗聲:「你早說嘛。」
回到我蜂巢般的工作隔間,著手收拾自己的私人物件,所幸只有一個馬克杯、幾本書、一把牙刷一管牙膏、一件抗冷氣的外套是真正屬於我的私產,其餘因為工作衍生且累積的文件資料都可以資源回收處理,一扔了事。十幾年的好習慣,我始終將辦公桌與下班後私領域的交集保持在最低限度,我喜歡好萊塢電影常見的來去辦公室皆一硬紙箱的簡便無罣礙。我欽佩女同事以小盆栽乾燥花、印度織布靠枕、填充布偶、化妝品零食、偶像海報親人照片將一幾隔板空間裝置得一如居家。
人與現代生產組織的關係,我服膺如此邏輯,生滅的是人,恆在的是位子;淘汰流動不是悲歡離合,體制的健康(永生?)大於個人的感傷(必死?),秩序必定是美德。或者,至今依然令我玩味也莞爾的還是陳映真不免天真嫌疑的句子:「上班,是一個多大的騙局,一點點可笑的生活的保障感折殺多少才人志士啊。」因為只消替換幾個關鍵字,馬上逆轉成為正面表述,「造就多少才人志士啊」。
為什麼得上班?或者我應該徹底反省的是,有此一問者究竟間在想什麼?職場十幾年我老是間歇發作如同瘧疾的發寒熱。我就是那刻舟求劍的愚人吧?十九世紀中葉,廿八歲的亨利梭羅在華爾騰湖邊蓋自己的房子,總計材料費花了二十七點九四美元,之後他更結論一年只需工作六週就足以得到生活所需,支撐他以自由、獨立的狀態從事一己志業。亦即心智澄淨的梭羅確實執行了生活與物質的減法至最低限度,得以拒絕做為謀生與薪水的工奴,大不了吃吃土撥鼠肉。
那麼,心不在焉的職場「泥棒」如我終於被解雇,豈不是合理、正當的嗎?天行健般的體制機器豈容許一個只願一年工作六週、「食碗內,看碗外」的無忠誠者?
最後一次的下班時刻,等電梯時遇到公司的包打聽,幸災樂禍對著我奸笑得如一頭卡通貓,我木木看著他卻說不出口,你才是這職場的蛆!然而步出那「每個上班族心中都有一座華盛頓大樓」,眼前林蔭大道如層積雲,其上是城市的光害才開始,如同脫了網的魚,我感到那沛然的自由大海令我一下子有些茫然。
兩個父親的台北城
民國六〇年代初期,父親在台北城居留、奮鬥了四年,做了幾樁生意之後,終告黯然敗走,一人先行轉去中部。他消失之前的某個深夜還是清早,我在睡夢中聽見九妗婆借酒意上門大聲理論,代替九舅公來向父親索討一筆原本是合資然而蝕本了就成了借債。
那或是台北水城的最後時光,我們租屋在興建中的佳佳保齡球館對面巷弄,巷底一窪死水塘,還有幾株姑婆芋。它原本可能接著是一窪大水塘或水田填死了變為荒地,每天黃昏極目有毛絨絨的紅黃落日,蕭條蒼涼。父親掏出紙鈔要我去幫他買啤酒,對門一排即將完工卻突然停工的兩層樓連棟住屋黑沈沈足以吞噬人。他壯年增生的、我無從了解的鬱悶與夜裡盲人按摩悽愴慌空的笛音重疊,每天晚飯佐一瓶台灣啤酒是他「心涼脾肚開」的豪奢享受吧。有一週祖父母突然來了,寄住在同一條巷子二樓的大姑家,母女一大早裝扮整齊前去八里拜一座據說非常靈驗的廟寺(義賊廖添丁?),祈求財運。父親非常厭憎如此作為,他一生信念,錢財是血汗拚搏來的,向一座柴頭偶也燒香磕頭便可求得,荒謬,無骨氣。
一覺醒來,搬了家,而父親不在了,接手來的是外祖父一家、五叔公一家,更有延伸的戚誼若干,一掛一掛粽子般來去,混居在不到三十坪的公寓租屋,兩層鐵床如通舖,圍上草履蟲圖案的布簾,床前一堆拖鞋,睡前他們不改鄉居在三合院埕內大嗓門開講的習慣,彷彿一班隆隆響著、不知開往何處的時代夜行列車。
是技術與生財器械方便在姻親關係中轉移吧,外祖父也開了一家麵包店,形同貨櫃的烤爐便是鄉下家裡的那一座,睹物思人,我想像龐然大物的它是如何從小鎮搬運上台北城,懷念短暫的冬天裡它散發的熱力。沒多久,麵包店轉型為小吃店,賣魯肉飯、湯麵、餛飩、肉粽,父親每隔一段時日匆匆回來,似乎我還來不及與他說話,早晨醒來他又離去了。
生意既定,親戚四散各尋生路,母親隨外祖父一家租了菜市場旁的兩層樓木造違建,二樓其實是不及成人高的閣樓,樓梯外不知為何有個如武俠片的暗道。那時的台北城違建蔓延如黴菌,菜市場嗝出蔬果腐味、魚腥、雞鴨屎臭,火燒似的黃昏有鴿子啪啪群飛。
印象中父親與外祖父交談比起與我深深思念的祖父更為契合、更有一份男性的情誼。同理,我懷疑外祖父對他是否比對舅舅更包容、更有疼惜之心,共同商量過什麼賺錢大計,然而時也命也終究無成。
我小心地與外祖父母保持距離,始終無法親近,必然在我意識裡有一條簡單公式,親近他們就是背叛、削減了對家鄉祖父母的感情。我用著外來者的眼睛看外祖父,漫長的暑天下午,他打開大冰櫥,取出一塊豆腐,淋上醬油,灑上柴魚片花,烏唇大嘴一大匙吃將起來。他懂得享樂,肯花錢,愛美食與時新器物,假日帶著一群孫兒女去松山機場看飛機、遊草山,轉到北投洗溫泉,大頭大眼,身量若銅錘,講話重低音,不怒自威。他更是極有權威的一家之長,有他在,即使已經五個兒女的舅舅也隱逸無光。他嫌自己唯一的男孫過於軟弱,亦從不假以慈色。
我其實怕他。我相信當年從中部率領一家遷居台北城從頭開始是外祖父一人的決定。
一如當年決定北上一闖,不相信「人兩腳,錢四腳」而相信有一番事業美夢在前方的是父親一人的決定。
小吃店的共同點永遠是工時長、瑣事繁,打烊後的準備事項更多更雜,週而復始。我與舅舅的兒女們假日以剝一大鋁盆的白煮蛋蛋殼為樂,偶爾被叫喚支援洗碗,各自想法逃遁。那個盛夏,我童年的終結,台北城炎熱得柏油路軟綿綿,黏住塑膠拖鞋,我們的探險疆界無法再推得更遠了,局限於建國南北路的荒地,周遭的眷村在拆除,堆棧著水泥與木材廢料、野草廢土,有一處資源回收場,讓我們發狂於撿拾破銅爛鐵換取幾個硬幣。潦草且漫長的黃昏,我望向地平線,幼稚地發誓有一天要去到那裡。
父親又一次匆匆回來,我們火速搬到對街的樓房(那兩年搬遷範圍始終在方圓幾百公尺內,因為預算、時間上的經濟),對於一直奮鬥著要擺脫貧窮的他必定惱怒我們租屋住在違建。我第一次大膽要求他買一本辭典,他臉上不豫,還是帶我上一家磨石子地光亮的文具店買了,我每逐頁翻著自學生字,心中總浮現他的難色。
大同水上樂園開張前,外祖父得知,嗅出商機,立決兵分二路與一親戚合夥在樂園大門對面再開一家餐飲店。大人期期以為一條金光大道就此展開了,畢竟疲累奔波兩地,蒙昧的第三代只會興奮有了絕佳新天地可玩耍。
前去樂園得在萬華轉車,客運、公車的烏煙裡,擁擠者太多的人、過度的貨物與太吵雜的聲音、太明豔的色彩,我懷念祖母的美感,能簡能減能斂才能骨秀、神秀。據說有著全台第一座人造波浪泳池的樂園所在,有機會先來探險一段時日的表弟妹發現圍牆一處傍著一棵龍眼樹,正好攀爬免費入園。太陽下,滿滿來玩樂消費的遊人。牆邊是農家老厝與泥土路徑,更有大片簡陋砌建的屋舍簇群,非常粗糙不文的異鄉,唯有夠堅韌夠強悍者得以存活。新小吃店生意興旺,午餐尖峰時段人潮如浪潮湧進,我手捧一碗熱湯,遭客人一擠碰,燙傷一整手掌。母親也在隔了十年後再懷孕,我看著她肚子大了起來,感覺異樣陌生。在中部山區,父親轉業似乎有了不錯的開始,聖誕節長假,他特地帶我們全家南下一遊溪頭,他工作地旁一條冬天荒枯遍河床的累累石頭,走近水邊才發現僅剩的河水猶然湍急。
秋冬某日,表姊慌張地跑來叫醒還在睡覺的母親,「阿公死了!」我記得母親下床時尖挺的腹肚,西曬的窗戶明亮。據說外祖父那一早如常起來開店門,喝了幾口的牛奶瓶放在桌上,心肌梗塞遽然將他擊斃,他用以打拚、奮鬥的店正面對著樂園。
我木木的看著母親獨自哭泣,外祖父出殯她因是孕婦或其他我不了解的理由,並沒有返回家鄉參加。我暗自想,合乎情理嗎?黃昏之後,城市巷弄上空還是有它的光亮。
外祖父的死亡其實宣告的是兩個父親、兩個一家之長、兩個供養者闖赴一個新興城市自求生計的結束,多年後我臆測,父親應是拒絕了外祖父賣吃食賣勞力的合夥提議,無關行業貴賤,那不是父親所擅長,在他盛年的時間,他還有餘裕可以揀擇,那是他的傲骨與硬頸。
那個七月的早晨,父親領著兩輛貨車裝載著我們全部家當,我幫忙提著一支水銀膽熱水壺給初生的小弟路上泡牛奶用,車輪轉動,告別了那年代的台北城。
飄零
T約我西七十二街中央公園入口處會合,對岸路口是那巨人城堡般華麗非凡的The Dakota豪宅,當然住戶皆是唐諾在《世間的名字》形容的「金色皮膚的富翁」與演藝名人(「大鼻子情聖」法國演員不是才為了抗逃富人稅入籍俄國?),約翰藍儂一九八零年在門口遭一精障者槍殺。因而此地順理成章是觀光熱點,遊覽巴士蜈蚣來蜈蚣去,導遊持播音器有口無心地介紹,入園處一大陣的人力三輪車,歐洲人種的車夫(移民?移工?難民?背包客?遊學生?)短衣短褲彷彿是駕馭馬車的阿波羅。
T改不掉遲到的老毛病,燦亮日光裡一現身,臉團團如泰迪熊,髮色夾大量灰白的平頭(宋襄公軍令,「不殺二毛」),氣色是好的。他是我第一份上班族工作的同事,前電腦化時代的職場,畫一手可愛風格的好圖,上下班打卡朝九晚五的每一日罕見他開口說句話,我校對著有他畫插圖的家電目錄,故意激他,每個人神態都像你。他冷冷瞪我一眼,翌日給我一張筆觸狂放的彩圖。我們一同討厭那日文流利但用起敬語極噁心、待員工苛吝的蟾蜍眼老總,解嚴前口頭鼎力支持黨外運動,卻也是第一批快馬去朝拜兩岸紅頂商人。很久遠以前的某段天空非常藍的秋日,我跟著他假日四處拍照,他說拍得上品的攝影是一筆業外收入,也跟我解密,蟾蜍眼看不上眼的生意就是他的「阿魯拜兜」,一個起碼抵一個月薪水。最好的復仇就是比你的敵人活得更好。
九七後T開始積極計畫離開島國,毫無章法的問過我關於留學美國的事,音訊斷絕了一年多之後,我聽說他已賣掉了台北市的公寓,定居曼哈了。我想到他蒐藏一整面牆櫃的古典音樂CD,好幾件稀奇古怪的骨董,確實是風象星座人的行事,他底氣有著藝術創作者的膽識,藐視規範的野性,甚至強力的自我表現吧。我無從理解他在我看來近似自我流放的移民,畢竟「五月畫會」或謝德慶行為藝術家的時代遠矣,那不是我們這一代需索的活化酵素。或者他愛戀的只是異國他鄉的浮根自由,一如他年輕時的寡言獨行,「都不要來煩我!」。
多年後重新聯絡上,T說九一一發生時他住在下城,在頂樓照了一整天的浩劫真相。他說得平淡,令我想到那個親見災難而時時回望並以其所長的形式記下過程的比喻。走到碧絲達噴泉前的林蔭道,不知是來自歐洲或南美洲或雜牌混合的四人樂團演奏著,我們聽了一會,發現他們得到的賞錢滿好。他也巧遇了他在游泳池常見的一男子擁著波浪捲髮的女友。他咯咯笑說曾將一間小空房出租給一個平時當餐館服務生等待機會的劇場演員,兩個月後付不出房租而悄悄落跑,留下一包來不及帶走(或故佈疑陣)的舊衣褲。
他突然眼睛放光,問我要不要去那邊的兒童動物園走走?日光充滿,我只覺些微淒涼。
晚上在燈光溫暖的公寓裡,P感嘆並判斷T恐怕至今身份問題並沒解決,遑論找一份起碼有醫療保險的工作,「這樣的人紐約好多好多。」弱怯者輕易成為被剝削的俎上肉。我對著P快手做出的美食突然沒了胃口,P與T這大城的兩個陌生人當然不是「同是天涯淪落人」,顯然與唐君毅當年的花果飄零之巨大感嘆也完全無關。隔街的消防車又嗚哩呱啦銳叫了起來。
佛滅之日
「路是為了回頭而鋪的,沒有一個人走到終點。」黃皙瑛《悠悠家園》
白領工蟻十三年後,中央空調的辦公大樓依然沒有寒暑感,那一天如同之前無數個工作日,又是一個只有例行工序消磨時間的平淡日子。
我通常是第一批早到的鳥兒,入口感應器讀了員工卡,很久很久以前覺得是阿里巴巴的寶藏祕門、玻璃門打開,空氣陰涼,睡了一晚的機器、文具、影印紙、盆栽、化纖地毯,確實如同古墓的殉葬品,恍惚有靈,而隔板規劃出一格一格的工作空間,又像是訓練白老鼠的迷宮。我無恥地妄想過中子戰後的末日早晨,遊魂歸來,一人得以霸佔整...
目錄
I.蜂巢
佛滅之日
解放之日
有窗景的辦公室
理想的波士
惡女的條件
頂尖對決
Y的悲劇
宵待草
星散
鬥
恍惚的人
小蝦米的故事
大倉庫追憶錄
傷害
春風戀情
波士家的晚宴
癡人方舟
秋日和
往昔的黃磚路
滾石不生苔
野地的獸
敵人
兒子
畸人
老人
長了翅膀的蛇
天使
美麗新世界
II.夏天的合音
條直之人
笨蛋老實人
大街上的餅店
餅店之夏
家春秋
軟飯與神寵
父親的白襯衫
兩個父親的台北城
遙遠的長夏
阿姨
舊厝歲月
衣棄
III.大城小鎮
門房
公園大道
星沉地底
西城故事
中央公園
一粟上班族
發達盛
飄零
美夢
高馬美人
華盛頓廣場
夢中的書房
原子人與他的虛空
散步大武
美麗的天空下
I.蜂巢
佛滅之日
解放之日
有窗景的辦公室
理想的波士
惡女的條件
頂尖對決
Y的悲劇
宵待草
星散
鬥
恍惚的人
小蝦米的故事
大倉庫追憶錄
傷害
春風戀情
波士家的晚宴
癡人方舟
秋日和
往昔的黃磚路
滾石不生苔
野地的獸
敵人
兒子
畸人
老人
長了翅膀的蛇
天使
美麗新世界
II.夏天的合音
條直之人
笨蛋老實人
大街上的餅店
餅店之夏
家春秋
軟飯與神寵
父親的白襯衫
兩個父親的台北城
遙遠的長夏
阿姨
舊厝歲月
衣棄
III.大城小鎮
門房
公園大道
星沉地底
西城故事
中央公...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4收藏
14收藏

 10二手徵求有驚喜
10二手徵求有驚喜



 14收藏
14收藏

 10二手徵求有驚喜
10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