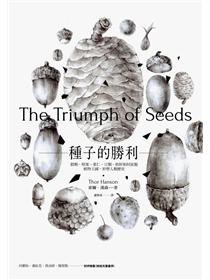首屆 台積電文學賞得主 連明偉 中篇小說集
黃錦樹、童偉格 專序推薦
最新一代書寫異域的作家!
以簡潔複誦的敘事,構築出「遷徙家族」必然遭遇的景況。
「多年以後的連明偉,因遠赴他鄉而有了新的際遇,已非當日『吳下阿蒙』。『番茄街』不產番茄,但它緊鄰番茄醬;《番茄街游擊戰》沒有柳丁,也沒有嚴格意義的巷戰,也許這部小說本身即是連明偉的『番茄街游擊戰』」。——黃錦樹
「在每次變奏中,連明偉所動用的敘事模組如何耗盡動力,自那古老時光脫離,宣告自身的終結?是在這裡,連明偉以《番茄街游擊戰》,示現他作為小說家,最內鑠如詩的識見。」——童偉格
我一個人走在番茄街上,望著陽光柔軟成一條亮晃晃的神祕河流,流過整條街道,流過哭泣的孩子,我忽然覺得自己變成一艘不知要划去哪裡的小舟。
三則容或各異的故事,描寫彷彿流浪於異鄉的孩子們,在各自遊蕩的長夏,嬉戲、困惑並且成長。簡潔複誦的敘事,隱然浮現等待命名的憂傷與躁動,構築出「遷徙家族」必然遭遇的景況,諸多認同命題無不指向自我,並指向存在本身,關於疼痛、失落與神祕的愛。
作者簡介:
連明偉
1983年生,畢業於暨南大學中文系、東華大學創英所。曾任職菲律賓尚愛中學華文教師。作品曾獲得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篇小說首獎、台積電文學賞、中國時報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獎等。〈番茄街游擊戰〉為首屆台積電文學賞得獎作品。
章節試閱
第一部 番茄街游擊戰
名字
我的名字叫作Dela Cruz,Albert Bradford T。
我住在連街番茄街的一條小巷內。每天早上,番茄街都會被吉普尼車塞得滿滿的,排出烏煙瘴氣的廢氣,把整條街道的天空噴得很黑。我每次都在想,人那麼多,車那麼多,再擠下去總有一天真的會擠出番茄汁來。
番茄街在Dalayan村莊北側,西南方向可以通到Manila,報紙都把馬尼拉寫成大岷區,東邊通往Munous,一個不大不小的市鎮集散地,小偷和強盜特別多,我叫那地方摸奶子。靠近東邊還有一個小小的市集Frisco,我叫它活力似寇。我討厭記這些拉七雜八的英文,尤其番仔島很多用語都來自西班牙文,捲舌彈舌,連在一起的字母像是饒舌的Rap,我真搞不懂這些番仔怎麼可以記得那麼輕鬆。剛從台灣來到番茄街過日子時,非常很不習慣,語言不通,街道又亂得讓人迷路,我只好替附近的地名都取了中文諧音,這樣子才好記。
番茄街並不產番茄。
為什麼要叫番茄街呢?承善這個大胖子曾經問我。愛芮莎和彼得對我使了個眼色,表示他們知道。是啊,只要住在番仔島的人都知道,村子外的街名叫作Delmonte,剛好是著名的番茄醬名稱,所以這條街就變成了番茄街。只有承善這種傻傻胖胖來番仔島讀書的韓國人才不知道。
白天熱烘烘的,沒事可做,我會跑到番茄街,或者跑進達拉癢村莊找樂子,我就讀的學校就在這。我們的學校叫作Philadelphia School,可是中文名稱卻是尚愛中學。剛來這裡讀書時,我就覺得奇怪,學校為什麼要用一個美國城市的名字呢?更奇怪的是,中文竟然不叫費城中學,而是一個毫無關連的名稱──「尚愛中學」。我們是華僑學校,收費比普通公立學校貴很多,教英文、塔加洛語(Tagalog)之外,還教中文。說是中學也有些奇怪,學校收的學生從幼稚園、小學直到中學,整間學校熱熱鬧鬧像個大雜燴,什麼年級的學生都有。我的小六同學有一大部分是混過番仔血統的中國華僑,也有一小部分是南韓人和被來自甘肅的中文老師稱為純種的番仔。
我從彼得那邊得知學校的名稱來自《聖經新約》中的〈啟示錄〉,節錄自第三章第七節,跟美國派軍駐紮過菲律賓一點關係都沒有。彼得之所以會知道,是因為他參加由校長主持的讀經班。老太婆解釋學校的名稱來自兩個希臘字,Phileo代表愛,Adelphos則代表教友間的兄弟姊妹之情。我搞不懂彼得為什麼要參加老太婆主持的讀經班,除了上完早課可以吃廉價的餅乾、喝泡粉果汁之外,根本就沒有什麼好處。更何況,要吃東西就爬上樹幹摘青芒果和牛奶果就好了啊。
彼得皺著眉說:「是媽媽逼我參加的。」
我不討厭彼得的媽媽張欣,她挺有趣。張阿姨的肉很白,頭髮燙得蓬蓬捲捲,喜歡穿非常短的緊身牛仔褲,將大屁股包得很緊,腳上穿著磕磕響的高跟鞋,身上始終有著淡淡的人工玫瑰花香,每次聞了我都會頭暈。張阿姨不太會說中文,每次見到我都跟我說福建話,那種福建話跟台語不同,我只能聽懂一半,後來猜得累了,索性說起英文溝通。張阿姨不喜歡說英文,她繼續用難以理解的福建話同我交談。我去找彼得時,張阿姨都會拿出台灣的旺旺仙貝、人參糖與乖乖餅乾請我吃。這些餅乾在番仔島很貴,普通的雜貨店沒有賣,一定要到中國城的某些國際商店才買得到。張阿姨還會請我喝立頓奶茶、義美奶茶和黑松汽水,說東西都是從台灣進口的,味道可不一樣。張阿姨得意地拿出甜點,覺得食物來自台灣就很了不起。我喜歡去彼得家,張阿姨很香,家裡的擺飾很漂亮,整間屋子都鋪著白色磁磚,有兩個可以供叫喚差遣的啞啞,張阿姨還會拿出很多在台灣生產的食物,這會讓我想起以前的日子。
這個夏天,我、承善、彼得和愛芮莎約好要去一條神祕的溪流划船。
愛芮莎說那條溪流離奎松不遠,往南坐車大約只要一個小時。愛芮莎說她是和媽媽一起去遊河時發現的。河邊有許多依河捕魚的住家,整條溪流綠油油水漾漾,一張網撒下去就會抓到十幾條大魚,更上游還有兩個大瀑布。愛芮莎說他們都有船,住在水上,整天晃來晃去還以為是在坐海盜船。愛芮莎說夏天一到,我們可以跟爸爸媽媽說要參加三天兩夜的營隊,拿兩千披索當旅費,這樣就可以離開骯髒吵鬧的奎松,去河邊探險,划船,看星星,吃烤魚。
我們需要一條小舟,愛芮莎異想天開地說。
愛芮莎說我們可以從上游往下自由漂流,或者從下游往上游用力划行。我、承善和彼得都睜得大大的眼睛望著綁起頭髮的愛芮莎,彷彿她是一個從天而降的外星人。愛芮莎說不用擔心,因為叢林裡不會有老虎,也不會有其他的怪獸或是獵人頭的原住民,頂多出現一、兩條鱷魚或是蟒蛇。愛芮莎笑呵呵,看準我們會害怕,接著她又跟往常一樣,望來調皮的眼神,似乎是在說,我就知道你們不敢,這群小孬孬。我覺得這個提議不錯,立即附和,說要造一條小舟,說這樣子才是夏天。
夏天還沒有到,我們已經決定好要一起造舟。
校長和中國來的嚴平老師
這個學期,學校來了兩個新面孔,一個擔任空缺已久的中文部主任,另一個則是從中國大陸請來的自願者嚴平老師。中文部主任來自台灣,五十幾歲,圓肚,肥下巴,說話很粗魯,遠遠聽起來還會以為是獅子亂吼,聽說主任的老婆是個番仔婆。嚴平老師是從甘肅來的年輕老師,皮膚黝黑,扁平的臉孔沒有特色,雖然穿著體面的學校制服,看起來還是像個農夫。嚴平老師是校長特地從中國大陸找來的華文教師,受過專業師資培訓等等亂七八糟的訓練課程,有著一張又一張的鬼屁證書。
嚴平老師擔任五、六年級的中文老師。剛開始,嚴平老師很有活力,每次上課都想盡辦法想讓同學們集中注意力,但是沒有用,同學一會兒就在課堂打起瞌睡,上完廁所就溜去福利社買餅乾,或者目中無人、光明正大做起別科作業。嚴平老師不太會說英文,也不會說福建話,每次上課都是雞同鴨講,鬧哄哄一片,他說他的,我們做我們的。嚴平老師總叫我做翻譯,要我把中文翻成英文和番仔話給同學聽,我不喜歡這樣,因為我好像變成專討老師喜歡的要命小老師,那種人最不要臉了。我每次在上課前喊起立、立正與敬禮時,同學都不理我,我可不想自討沒趣。嚴平老師的國語很不標準,不是捲舌捲得厲害的北京腔,也不是軟綿的南方腔,而是中國內陸含著魯蛋、嚼著風沙的中文。嚴平老師說話很快,彷彿是機關槍掃射,沒多久全班同學就集體陣亡了。
我和彼得都認為嚴平老師是個傻子,說話都說不清楚是要怎麼教中文呢?
一天下午,中文課,校長無緣無故氣匆匆跑了上來,甩開門,眼神掃射同學一圈,點了吉祥,噼哩啪啦用中文問你家有幾個人?你今年幾歲?你喜歡什麼顏色?你晚上幾點睡覺?你是男生還是女生?校長的問題雖然很基本,但是聽起來卻相當變態。在台灣,我不會這樣問我的朋友你是男生還是女生?這些詭異的問題只會讓我感到噁心。我和愛芮莎互瞄了一眼,知道又有許多人要遭殃了。果然,校長點了幾位同學後,輪到縮在角落的承善,承善支支吾吾肥老鼠啃食般說我家有五個人。老太婆問有哪五個人。承善說有我、爸爸、媽媽、妹妹──
怎麼才四個?校長瞪著承善,張開大嘴辱罵嚴平老師。怎麼教的?為什麼學生連基本會話都不會?校長轉過身,氣沖沖走了出去。
主任縮在校長身後,繃著一臉你們倒大楣的模樣跟著下樓。
中文課真是愈來愈不好混啊。
放學後,我和愛芮莎、彼得擠在中文辦公室外,偷偷打開門縫,想知道同學們受了什麼懲罰。嚴平老師、吉祥和承善等人站在主任辦公桌前,低著頭,皺著眉,臉上被抹了牛大便般。承善被趕出來時,嚴平老師還待在原地挨罵。我塞給承善一顆從達拉癢村莊摘來的牛奶果,試著安撫他,說校長這個老太婆一定是因為停經才得了憂鬱症。承善沉著一張臉,兩道眉毛擠在一起,單眼皮的細長眼睛幾乎要被縫了起來。我和愛芮莎拉著承善到學校籃球場,問主任到底說了些什麼。承善扒開牛奶果,舔著白色汁液,一口一口吃了起來。承善說這個週末以前,他一定要學會二十句華文自我介紹,不然六日要留下來補習。彼得拿來四枝牛奶冰淇淋。承善一看見冰淇淋便笑了。我們一邊吃冰淇淋,一邊替承善惡補中文,我們可不希望建造小舟的重大工程被這種芝麻小事給耽擱了。五點半,承善家的司機查爾依舊西裝筆挺站在學校門口,輕聲喚著:「少爺,該回家了。」我從書包掏出巧克力餅乾遞給承善,愛芮莎從口袋掏出兩顆芒果糖,我們都要承善不要擔心,不過是二十句沒有意義的華語自我介紹罷了。
愛芮莎的叫賣聲
承善、彼得和我走路去活力似寇市集。從達拉癢村莊出來之後,接上筆直的番茄街,往東,過了髒兮兮的San Francisco River,再往Frisco Place走去,途經斜陡的黑色柏油路上坡,左側停滿一排等著載客的三輪車,司機們慵懶地躺在座椅上打呵欠,昏昏欲睡,右側有好幾條小路可以通往Damayan和San Francisco Del Monte村莊。這兩個區域屬於活力似寇,但是算不上正式的村莊,沒有完整的圍牆,也沒有二十四小時輪流看守的警衛,四處都是垃圾。彼得的媽媽一直告誡他不要來這兒,說這裡是貧民窟,很危險,容易被搶。
我領頭,承善和彼得怯怯懦懦尾隨,一同繞進右側小路。活力似寇並不是貧民窟,只是住著比較多的番仔。番仔都將路面與房子搞得十分骯髒,隨意丟著垃圾,胡亂大小便。白天熱,番仔男人裸著上身,只穿一件短內褲。番仔女人含蓄得多,不過也是短衣短褲,露出粗壯的大腿。小孩不是穿一件破內褲,就是光著屁股到處跑。愈靠近活力似寇,吉普尼開始少了,四處載客的三輪車與人群逐漸多了起來。街道邊,老人擁著一堆新鮮椰子在電線桿下睡覺,另一群老人推著載滿香蕉的三輪車躲在陰暗處,開雜貨店的婦人悠閒地對著電風扇乘涼,肥滋滋的油煙從烤肉串攤位飄了出來,讓空氣充滿了肉香。
「好熱喔,休息一下好不好。」承善紅著臉頰,滲著滿身汗水。
「我就說你該減肥了,還不承認,走這麼一點路就累,真沒用。」
我們選了一家有冷氣的網咖,靠近門縫吹著冷氣。
「彼得,你幫我去買冰啦,就在對面。」
「那麼近還要我幫你買,你這樣下去會變成豬公喔。」
「我快要中暑了,都是你們找我出來的,我就說我要待在家裡打電動。」承善放大聲量,賭氣地坐在門縫,不讓人出去,也不讓人進去。
「好啦,錢拿來,你這個豬公。」彼得拿了一張二十圓披索,往對街的冰店走去。
彼得在冰櫃前看了許久。
「沒有賣嗎?」我大喊。
「你們要吃什麼口味?」
「我要巧克力,有核桃和碎碎的餅乾那種。」承善大喊。
「笨蛋,什麼口味都可以。」我罵著彼得。
我們在網咖前吃起冰淇淋。
人潮愈來愈多,我掏了掏口袋內的零錢,跑到冰店買了牛奶冰淇淋要給愛芮莎。我們離開網咖,繞進市場,即使來了那麼多次,我還是摸不透分岔的小巷到底會通向哪裡。市場用破爛的隔板遮蔽,攤位互相連接,賣著雞蛋、魚、水果、蔬菜和過季衣褲。愛芮莎曾經說過,市場賣的二手衣服很便宜,不過買的時候要仔細挑選,很多都是從墳墓堆死人身上挖出來的。愛芮莎認真的表情有點好笑,讓我不知道該不該認真回應她。愛芮莎還說雖然她的衣服都在市場買,但是她都有仔細挑選,全都是有錢人家不要的衣服,只穿了一兩次而已。自從愛芮莎跟我說過這件事,每次看到她,我都覺得她穿著死人的衣服,身上瀰漫腐爛的味道。愛芮莎最常出現在活力似寇,有時候在擁擠的巷道旁擺攤,有時候在排排相連的攤位前叫賣。
愛芮莎叫賣得很有魄力,她的叫賣聲可是市集裡的活招牌。
有一次,我到市集幫奶奶買雞蛋時,看到愛芮莎綁起頭髮,白毛巾綑成一圈繞住額頭,左手插腰,右手拿著蒼蠅拍在剁魚的板子上敲打,我還以為來到台灣的年貨迪化街。市集裡沒有人這樣賣東西,一堆人圍著看,大家的眼睛都睜得大大的。愛芮莎敲打的歌曲都是快節奏,容易帶動氣氛。還有一次,我看到愛芮莎站在一家賣手機殼的店外,隨著店內震天價響的搖滾樂起舞,歌手是番仔最愛的Bruno Mars,歌曲是〈Just The Way You are〉。愛芮莎擺動小小的身體,搖著臀,扭著腰,嘴裡跟著唱:「When I see your face, there's not a thing that I would change. Cause you're amazing, just the way you are. And when you smile, the whole world stops and stares for a while. Cause girl you're amazing, just the way you are. 在看妳的臉時,我一點也不想改變它,因為妳好棒──就是妳現在的模樣。而當妳微笑時,整個世界都暫時停了下來,只為了凝視妳,因為女孩妳好棒──就是妳現在的模樣。」愛芮莎還在市集賣過很多商品,從商店的奶油麵包、巧克力麵包和蛋黃麵包,到小攤販售的青芒果、黃芒果、肥香蕉、切好的小鳳梨、牛奶果、椰子汁,或者是為賣菜攤販推售小番茄、小紅蘿蔔、四季豆、涼薯、小苦瓜、大黃瓜等等。愛芮莎總是用令人出乎意料的方式推銷青菜、水果和雜貨。我曾經問過愛芮莎為什麼一天到晚都在賣東西,開玩笑地說總有一天她會賣掉自己。愛芮莎說:「我沒有錢。」說的時候,愛芮莎還是微笑著,我聽不出話中是否帶著悲傷。
我們找到愛芮莎時都累了,早已忘記了危險。彼得在路邊找起海賊王與鋼彈的盜版光碟,承善跑到飲料攤買豆花吃。這次,愛芮莎賣起鴨仔蛋,番仔稱「Balot」,很便宜,一顆鴨仔蛋不到二十披索。
我把融化的牛奶冰淇淋送給愛芮莎吃。
愛芮莎分別塞了一顆鴨仔蛋給我和彼得。
「不公平,我也要吃,為什麼我沒有。」承善說。
「你不能再吃下去了,再吃下去你會變成一隻長翅膀的大象。」
「為什麼大象會有翅膀?」
「因為肥死了,只好升天啊。」
我們都笑翻了。
鴨仔蛋放在竹簍中保溫,竹簍底下墊了木頭椅子,客人不需要彎腰挑選。
我將鴨仔蛋放進口袋。
「趕快吃啊,冷了就不好吃了。」
我面有難色看著愛芮莎,隨意找了理由搪塞。「我我──我想要帶回家給奶奶吃。」
「鴨仔蛋很好吃的。」彼得說。
「台灣是不是沒有鴨仔蛋,你不會是不敢吃吧?」愛芮莎問。
「哪有,台灣什麼都有,不像這裡那麼落後,每天放學,我都在學校附近的雜貨店買一顆鴨仔蛋吃。」
「熱熱的很好吃。」彼得剝開殼,蛋中露出半個鴨頭。
我感覺有些噁心。
彼得嘟起嘴巴,吸湯汁,加鹽巴,咬下絨毛鴨頭。「媽媽說很營養。」
承善也要吃,和彼得搶了起來。
「不要搶了。」愛芮莎笑著拿出另一顆鴨仔蛋。
要吃下鴨仔蛋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不過,如果我不吃,是會被彼得和承善取笑的。我試著保持鎮定,拿著鴨仔蛋敲擊竹簍,撥開殼,學著承善加鹽巴,咬一口,趕緊吞進肚子。我要表現得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樣子,不過是一顆鴨仔蛋罷了。我加了鹽,一口一口吞了進去,盡量不去想像自己正吞下一隻可憐的小鴨。
「我就說沒有什麼好怕的。」我的嘴中都是腥味。
「你的臉都白了。」愛芮莎說。
「我才不怕,在台灣,我們還會吃鴨血、吃豬血、吃酸掉的豆腐,還會吃雞的睪丸和腸子。」我露出不服氣的表情。
「不跟你吵了,等一下你們要去哪裡?」愛芮莎問。
我們面面相覷,沒有人有計劃。
承善蹲在地上說想回家,彼得說想去找盜版光碟。
「你們要不要去找木頭?」愛芮莎說。「你們從Dalayan來的時候沒有看見嗎?接近Savemore商店那個出口砍了兩棵木棉樹,聽說要蓋一間工寮,以後出入口都會有警衛守著。反正木棉樹也沒有要做什麼,頂多拿來燒,趕趕蚊子,你們去問可不可以拿走。」
我望著彼得,彼得望著蹲在地上抱著肚子的承善,承善用無辜的單眼皮眼神看著大家。
我們決定把樹拖回家。
警衛將砍下的木頭堆在鐵柵欄邊,割下枝幹,一壠一壠堆著當柴,一根斧頭砍在堅硬的樹幹上。
黃昏,警衛用細柴升火,燒出灰煙。
「這些柴有用嗎?」我試探性地問。
警衛用嚴厲的眼神對我們上上下下審視了一遍,考慮了很久才說沒有。「有問題嗎?」
「我們只是隨便問問。」
警衛丟了一些乾枝葉,雙手往耳旁揮趕蚊子,火忽然大了起來。
承善和彼得拉著我的手想離開,我走了幾步就停了下來,不自覺走向成堆樹幹,想著如何才能當個稱職的小偷。
警衛遲疑地看著我們。「你們是村裡的人嗎?」
我們立即將彼得推向前。
彼得怯怯懦懦說出自己的地址後,警衛的口氣就變得和善了。
離開鐵柵欄時,天色已經黑了,還沒抵達彼得家,獅子狗托比忽然大叫了起來。
「明天下課後,一起去偷木頭吧。」我說。
第一部 番茄街游擊戰
名字
我的名字叫作Dela Cruz,Albert Bradford T。
我住在連街番茄街的一條小巷內。每天早上,番茄街都會被吉普尼車塞得滿滿的,排出烏煙瘴氣的廢氣,把整條街道的天空噴得很黑。我每次都在想,人那麼多,車那麼多,再擠下去總有一天真的會擠出番茄汁來。
番茄街在Dalayan村莊北側,西南方向可以通到Manila,報紙都把馬尼拉寫成大岷區,東邊通往Munous,一個不大不小的市鎮集散地,小偷和強盜特別多,我叫那地方摸奶子。靠近東邊還有一個小小的市集Frisco,我叫它活力似寇。我討厭記這些拉七雜八的英文,尤其番...
推薦序
推薦序
柳丁與番茄/黃錦樹
有好幾年[似乎是我沒寫小說的那些年]進出系辦時,常會看到系辦對面牆上的佈告欄「榮譽榜」三個彩色大字下,大大的寫著「連明偉」三個字,名字下是文學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篇小說獎首獎、中國時報文學獎、台積電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等的剪報。我沒仔細看,那些年已不太留意文學獎,對新崛起的整個世代也沒怎麼注意,我也忘了自己在忙甚麼,安靜的活在自己的時間裡。但「連明偉」這名字我是記得的,那年吳曉青過世時,他們那一屆好像特別悲傷,我曾陸續讀到過幾篇淚漣漣的悼文。年輕未婚的吳曉青大概像兄長那樣陪伴著他們,一起打球、一塊游泳,談心事,因而情誼格外深厚。但我一貫採取刺猬策略,對我的老師輩、同事、學生都一樣,刺越長的離越遠,以免來日碰傷費事。他或許修過我的小說課,但我也不記得了,就像我不記得我上課時說了哪些話。教書都為稻梁謀,也從不敢鼓勵學生以寫作維生。此路難行,我認識的寫作的朋友都過得很清苦--如果沒有別的正職可以維持生活的話。
東華創作所成立後,彷彿是台灣的愛荷華寫作工作坊,好多對寫作懷抱夢想的年輕人[包括大馬青年]都會翻山越嶺繞到那裡,泡幾年山風海雨,連明偉也不例外。但之後他和同代台灣文青走了一條不同的路,到比外島更遠[心理距離,實際距離未必]的異國菲律賓去當替代役,到那裡的學校教中文。那段時間的「人類學考察」的成果就是這本《番茄街游擊戰》。
這本小說包含了三個中篇,每一篇的篇幅都比我曾經寫過的小說都來得長。我沒到過菲律賓,雖同屬東南亞,但曾受西班牙、美國殖民的天主教國家菲律賓,與曾被英國殖民的、以伊斯蘭教立國的馬來西亞大異其趣。我只知道從華人移民史的角度來看,這些東南亞區域[印菲泰馬]在民族國家建立前有一些共同的要素--譬如方言群/宗親會館、華文中小學,華文報,甚至華文文學。移民史一樣深受中國內部動亂影響,一樣有創造新文學史的南來文人,一樣有認同問題[中國認同/在地認同],從維新保皇/革命之爭到國共內戰,都深深的影響了華人社群[有趣的是,老是被迫在我們華文課本裡與妻訣別的林覺民,他弟林健民就是移居菲律賓的「南來文人」,和施穎洲等同為菲律賓華文新文學的創始世代(1)]。在美援的五六○年代,台灣也有過菲律賓僑生;菲華作家和台灣的「民國文壇」也多有交流。但我對菲律賓華文文學並不瞭解,以為它在一九七六年菲化法案後早就漸趨沒落了,但有的資料說它持續發展得頗有規模(2),楊宗翰告訴我其實已出現嚴重的斷層危機(3)。
但連明偉這些小說多半不會被當成菲華文學。它是台灣本土文學的一種有趣延伸。如果目前普遍認可的台灣本土文學是山/海,是台灣的農村與小鎮,那連明偉這些小說就確切是台灣的熱帶文學--熱帶台灣文學是幾年前我為了藉用這裡的資源把馬華文學偷渡進日語,而胡謅的。但虛擬的延伸也可能變成現實。台灣的替代役可以藉由僑委會的管道到菲律賓教中文,如果不是殘存的中華民國的民族主義,就是和旅菲台商子女的權益有關(4)。簡言之,這樣的文學題材之所以出現,還是和民國——台灣視域的合理延伸,但只怕台灣在地的讀者對它會產生一種直覺性的抗拒,就像面對在台的馬華文學。《番茄街游擊戰》的位置也許接近在台馬華文學。大膽一點說,它似乎介於在台菲律賓文學與在菲台灣文學之間(5)。這是連明偉小說得面對的風險,但也反襯出他初試啼聲的勇氣--走向域外,或異域。而台灣文學的異域面一直沒有真正被打開。不論是沿著當年民國孤軍棄子[泰緬][本土論者不會覺得那是「我方的歷史」]、非洲農技團的蹤跡,還是台商一個公事包走天下的旅程,都還屬於台灣文學的暗影地帶。
《番茄街游擊戰》一書收錄三篇作品〈番茄街游擊戰〉、〈我的黃皮膚哥哥〉和〈情人們〉,說實話,我讀得蠻吃力的。陌生的背景並不是最關鍵的,而是這幾篇小說的節奏和速度都異常緩慢,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第三世界的、前現代的時間感[一如我的故鄉],濃稠粘滯的細節,青少年的語調和視角,陌生的雜語。誠如梁文道在評審意見中指出,〈番茄街游擊戰〉讀起來有點像《頑童歷險記》(6),不同階級出身而被家裡忽略的孩子,因為同學而得以相互取暖。作者刻劃了幾個不同出身的孩子﹝我,彼得,愛芮莎,承善﹞,那樣悲涼的背景,也許是力圖突顯一個典型環境及那環境裡的典型人物;以漫遊體,讓讀者得以跟隨主人公的腳步,仔細看看貧民窟的悲慘狀況;藉由泛舟,得以一窺那條河的髒臭。在那散發著臭味的絕望的底層,少年們相濡以沫的情誼彷彿是最後的微光。
「番茄街」不產番茄,但華人喜好蔑稱異族為「番」則是舉東南亞皆然,華人的種族優越感,即便文化出現嚴重危機時也不例外。
這三篇都以「我的名字」為開端,都有自我介紹,也都採取了小說敘事最古老的形式之一的青少年成長小說類型,以在地青少年的視角,寫他們的同儕情感、家庭裡的矛盾、隔代教養的疏離、乏味的上課的點點滴滴、文化與身份認同問題等等,也涉及菲律賓華文教學的種種問題(7)。我們都知道,這些小說的經驗參照來自連明偉一年多的菲律賓替代役中文教學(8);因此也清楚知道,作者在小說裡的位置並不是故事的核心,而是在邊緣的暗影地帶,他為自己在那裡找到一個有距離的觀察位置[也是個倫理位置]。這些作品展現了作者瞭解他者的誠意,就這點而言,一個可能的閱讀參照是顧玉玲寫在台東南亞移工處境的《我們》。因此即便〈我的黃皮膚哥哥〉那樣的小說,也不是「我」的故事,而是「他們」的故事。這篇小說裡的主人公是有著純正土著血統的買來的養子,有錢父親一直換漂亮的新媽媽,好像那是甚麼可以輕易更替的商品[有錢老爸換女人的情節一樣出現在〈番茄街游擊戰〉]。那樣的父親,當然無暇關心青春期兒子的成長,更別說是更為微妙的文化認同。中文在那樣的世界裡,連標記自己的名字都是個難題。「難以用中文表述自己」[小說中用的日常形式是「以中文自我介紹」]是這幾篇小說共同的基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菲律賓新一代華人的文化認同危機--或者說,從這些小說再現的華文境遇多少也可瞭解為什麼菲華文學會陷入斷層危機。已經沒甚麼華語語境了,比馬來西亞新經濟政策、馬來化的教育更為嚴酷的「菲化法案」[1976]施行三十多年後,菲律賓政府已有效的讓華文書寫的日常根基徹底崩塌[如同印尼、泰國]。可以做菲華文學讀的《番茄街游擊戰》會是消失中的菲華文學的一個悲慘的見證嗎?
純就小說言,三篇中最具野心的應是〈情人們〉。與七旬奶奶相依為命的「我」男性,中學畢業,奶奶經營特種行業,他就打滾於諸老妓與眾老恩客之間。小說寫的是個衰敗的老華人殘花敗柳的風月世界,未成年的「我」從小泡在那「湯婆婆」的世界裡,學會像成年人那樣爭寵,扮裝,化身雌性以引誘奶奶的情人,春爺爺,驢子爺爺,虎牙--性別越界。在那衰老淫猥的成人世界裡,小丑巴奇似的春爺爺的恐怖劇場是箇中高潮,最終他把自己變為骨灰罈。這一篇的情色展演、淫佚奇觀,也是最接近連明偉的東華老師李永平《大河盡頭》中《海東青》似的情色巴洛克的。這會不會是菲華文化日暮途窮的一則隱喻?
多年前在暨大文學獎的評審過程中,駱以軍獨具隻眼的為一篇極盡唬爛之能事的小說辯護,我被他說服了。那小說標題是〈一顆柳丁〉,作者是連明偉。小說寫甚麼我一點都不記得了,唯一的印象是,那年輕的寫手似乎在試圖窮盡一切的可能在榨出那顆柳丁的意義。多年以後的連明偉,因遠赴他鄉而有了新的際遇,已非當日「吳下阿蒙」。「番茄街」不產番茄,但它緊鄰番茄醬;《番茄街游擊戰》沒有柳丁,也沒有嚴格意義的巷戰,也許這部小說本身即是連明偉的「番茄街游擊戰」。他們這一代有志於文學者幾乎都過著清苦日子,需要更大的韌性來迎接民國的日落。
謹致祝福。
民國一○四年六月十日
1. 方鵬程,《南国惊艳: 新加坡与菲律宾》台灣:商務印書館,2006:254。
2. 雲鶴,〈路漫漫其修遠兮--菲華文學八十年發展淺錄〉[2008]http://blog.udn.com/yunhe/1999518
3. 我就這問題請教了楊宗翰,他曾受僑委會「委派赴菲律賓馬尼拉兩年,擔任尚愛中學(Philadelphia High School, Metro Manila)華語教師暨教務主任,掌管校內從幼稚園到高中各年級師生的華語課程及行政工作,亦承擔過招收學生及與菲國家長協調等任務。」,返台後「為秀威資訊策劃過『菲律賓‧華文風』書系,並擔任書系主編。這套書從2009年起在台北印行,共有21冊,作者包括月曲了、和權、謝馨、雲鶴、千島詩社等,應屬菲華文學在台灣最大規模的一次集體展示。」[都引自宗翰給我的信,2015/6/8]他直言,「最大的問題還是作者年齡『斷層』,40歲以下幾乎無人可接棒。現在還在報刊發表作品的中堅世代,大約60-70歲之間。」關於菲律賓華文文學的狀況,參《文訊》284期,2009年6月號的「椰子樹下的低語--『菲華文學』風雲路」。連明偉也說詩以外的那些當代作品都「難以卒讀」。
4. 「學生大都是當地華人,若以五十人的班級而言,菲籍華人的比例可能佔三十五人,另外五個是韓國人,另外五個是當地菲人,另外五個可能是陸商子女。台商子女的比例很低,大部分都是陸商子女(大陸至菲經商,把孩子順道帶過來,或者是祖輩經商,留菲,成為菲籍華僑)。不過這比例也因各校而不同。」連明偉致筆者函,2015/6/9電郵。
5. 類似的例子不只連明偉,「至菲擔任替代役者,有些許人從事文學相關創作。例如楊宗翰從事編輯與詩評,何俊穆詩集《幻肢》,何立翔詩集《無心之人》,以及陳柏青散文<內褲旅行中〉(2014年時報文學散文首獎)。」連明偉致筆者函,2015/6/9電郵。
6. 《印刻文學生活誌》四卷四期,總100期,2011/12,頁223。
7. 相關討論見楊宗翰,〈菲律賓華文學校的四大病灶〉《中原華語文學報》第5期(2010年4月),頁57-69。感謝作者提供。關於菲律賓華校的狀況[都是私校吧?都是教會學校?用甚麼教學媒介語?],我也問了連明偉,他說:「大多為教會學校(又分基督教和天主教)沒錯,也有佛教學校,例如『佛教能仁中學』,甚至是道觀學校(一貫道),例如『丹轆建德』。都是私立學校,非公立學校。除華文科外,其他學科使用兩種語言教科書,分別是英文和當地語言Tagalog。Tagalog也是用英文拼音。」2015/6/9日電郵。
8. 連明偉給我的答覆:「我是擔任九十九年僑委會教育替代役(此為專業替代役,類似外交替代役派遣新兵去非洲耕作,只是負責的單位不同),時間是2010.03.29-2011.04.28,開始在成功嶺受訓三禮拜,接至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受訓約一個多禮拜,後直接分派至菲律賓奎松尚愛中學,在菲任教約一年。」2015/6/9日電郵。本文的私函引用都經當事人同意。
推薦序
「我們不必擔心明早的文明,不必為自己寫碑」/童偉格
就初步分析,我們可將《番茄街游擊戰》裡的三個中篇,視作同一則成長小說的三種變奏:三篇小說,情節安排容或各異,但它們基本上,都是一則關於小說裡的年輕主人翁,在經歷特定事件後,以如何的新狀態,「永遠」地,成為一名成年人的故事。意即:就敘事模式論,《番茄街游擊戰》重複演習的,是人類學家范杰納(Van Gennep)在《過渡儀式》中指出,且經常被學者借用以定義「成長小說」之為物的,由「分離」,「轉換」與「整合」等三個敘事階段,所依序合組的基本故事型。這故事型的指向,總是關於主人翁如何獨自察覺所謂「世界」,是一個與己對立的廣大「異鄉」(分離),因之而迷亂(轉換),最後,終於重新確知在世界裡,自己是誰,或可以是誰(整合),這樣的故事。
指認「異鄉」,對這故事型是重要的。因無論故事型的衍異,是如童話與寓言常見的,主人翁發覺自己變形、成怪了(通常配以詛咒),必須學習以新肉身重新感知世界,奮力求生,或就騎上飛鵝去歷險了;無論是如現代小說常見的,主角因巨大變故(父喪母離等),或不致命打擊(種種被侮辱與受損害;甚至可能,只是如遭誣偷了同學橡皮擦,這樣一種由細故推動的骨牌效應),而發現自己偏離熟習生活常軌,從此,需得像受困異星的太空人,在渾沌中積累足夠「常識」,以能放心預期,明天太陽將自何方昇起。無論如何,在詛咒解除,或明日安然以前;在主人翁返家、或再次融入世界,從而故事也就該結束以前,「異鄉」以壓倒性篇幅,成為這故事型主要書寫範疇。最簡單的斷言因此是:這故事型寫的,就是「異鄉」。
以此觀察,則連明偉的《番茄街游擊戰》有其獨特的直截:運用台灣青年創作者書寫中,常見的成長敘事模組,連明偉疊印上述「異鄉」明喻,以大部分台灣創作者絕無關注、遑論書寫的,我們真實的近鄰與「異鄉」,菲律賓。連明偉或許著力探觸的,是如巴赫金(M. M. Bakhtin)重理西方小說時空體時,所提出的核心判準或疑問——「小說如何把握真實的歷史時間和歷史的人」——而盡求觀照深廣卻修辭簡白地,涵蓋這真實「異鄉」的多重地層。這可能,即是《番茄街游擊戰》裡的三個準長篇,以同一基本故事型,去演繹變奏的原因之一。
三篇小說,一致由各自的年輕主人翁,「我」,以什麼姓名指稱自己,開始後續敘事。命名直接啟動的,是關於「異鄉」中的階級、族群與性別等,所有這些事關認同的命題。在命題交錯的語境裡,連明偉建構起他所謂「遷徙家族」的原型系譜:在中國戰亂時,被迫或自主流徙,跳島向南的曾祖或祖父一代,他們攜帶原鄉義理與話語,在「異鄉」,自守一個微型舊世界;忙於生計或生意,也因日常所需,而初步「本土化」的父親一代;以及最後,在既定語境裡,勉力開啟自我敘事的,年輕的「我」輩。
這系譜由三篇小說一體沿用,而連明偉書寫的特殊性,毋寧是父執一輩的恆常缺席,或存在感低落。這使如上所述的,初步「本土化」的徵兆或景況,在「我」的敘事裡,總以嘉年華式的倒錯,非日常地閃現;而或許更重要的是:這使「我」對「我是誰」或「可以是誰」,這敘事模組之終極指向的揣摩與思索,洞穿父執一輩,而上觸祖父一代,與那力求自保為「純粹」的古老時光,有了直接對證的可能。對「我」而言,這是天地更寬的自由,代價是線性時程的進一步塌陷。就敘事模組論,這是將「轉換」無限前擴,而使「分離」極限縮小:幾乎就在敘事之初,年輕主人翁指稱自己名姓時,分離過程已然發生並結束,角色已經就在一個真實「異鄉」裡游蕩。那個「異鄉」,就像剛與祖輩的南漂船接觸那般真實。
於是三篇小說裡的三位「我」,有了一段各自游蕩的長夏(那幾乎是熱帶「異鄉」裡,惟一可能的季節),無論那是在父輩安置缺席的豪宅,或平民街區。而既然「與自己置身的世界對立」這事,像是一種直證自祖輩的徵狀,敘事模組中,那標誌階段的所謂「特定事件」,其戲劇性也就相應減到最低,或碎散成一系列相鄰事件,支應那個像是在「我」出生前即在,之後也將持續漫漶的「異鄉」長夏:「我」惟能感知與表述的時空場域。這是《番茄街游擊戰》的特殊結構原則,有趣的是,連明偉似乎正是以此,與他所沿用的成長小說基本故事型,展開具破壞性的反向辯證。
因表面上,《番茄街游擊戰》所濃縮複現的,是成長小說的必然進路:如前所述,在「整合」落實,永久阻斷敘事動力以成就故事結局以前,這故事型著重衍異的,是主觀認知或客觀條件上的,種種形式的「異鄉」,對它們各自的主人翁,所提出的系列自主訓練課程。這大概是大部分有意識創作成長小說的作者,普遍共用的結構原則:透過主人翁面對「異鄉」的種種試誤與挫折,頓悟與理解,他們企圖「整合」的,是某種投向讀者的,以造就持恆狀態為目標的情感教育——即便表面上情感疏離,如村上春樹的《海邊的卡夫卡》,我們依舊能從話語裂隙,明確讀出作者正透過主人翁的「異鄉」遊歷,熱切教誨他的讀者,如何可能,「你永遠要在你自己的圖書館裡活下去」。是的,「永遠」。
即便作者並無教育訴求,這故事型所能深層鎸刻的,依舊是讀者的情感認同:它指認「異鄉」,賦與敘事動力所能容許的、逼近篇幅極限的關注,其中的年輕主人翁,無論其性格——如巴赫金用以對西方成長小說再作分類的——是情節安排的常數,抑或是變數,其用以遊歷「異鄉」的一段時程,是每位讀者已歷,或正在經歷的「不成熟狀態」(康德,〈答「何謂啟蒙?」之問題〉)。對成長小說真正的教育對象,年輕讀者而言,種種「異鄉」遊歷,或許主要是一種同步而親切的導引。對成年讀者而言,成長小說卻可能是一種另類深情的類型小說:它以最大專注力,描述一段注定將由自身敘事動力所耗盡、宣告為與「永遠」危顫對立,且也是每位讀者均已無可重蹈的過往時程。
另類深情:似乎,連明偉正是在以其特殊結構原則,及其所成就的簡潔變奏,確保上述「過往時程」的一再複現。於是,簡單說來,這其實是一組摧毀成長小說之普遍目的論的成長小說:它們讓每個事關「整合」的啟蒙時刻,變得似乎無關宏旨,至少,不能動搖那正漫漶著的古老時光。然而,「整合」如何發生,或者說:在每次變奏中,連明偉所動用的敘事模組如何耗盡動力,自那古老時光脫離,宣告自身的終結?是在這裡,連明偉以《番茄街游擊戰》,示現他作為小說家,最內鑠如詩的識見:如何終結?直到最後一點來自原初的情感記憶,與話語義理,在「我」猶存活的當下耗盡為止。無論那是童真的友誼(〈番茄街游擊戰〉),遺贈自過往、錯嫁如實的親情(〈我的黃皮膚哥哥〉);或者,其實就是所有先於「我」、造就「我」的生命期程(〈情人們〉)。
這時,所有這些「我」,就永遠是嶄新的成年人了。
推薦序
柳丁與番茄/黃錦樹
有好幾年[似乎是我沒寫小說的那些年]進出系辦時,常會看到系辦對面牆上的佈告欄「榮譽榜」三個彩色大字下,大大的寫著「連明偉」三個字,名字下是文學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篇小說獎首獎、中國時報文學獎、台積電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等的剪報。我沒仔細看,那些年已不太留意文學獎,對新崛起的整個世代也沒怎麼注意,我也忘了自己在忙甚麼,安靜的活在自己的時間裡。但「連明偉」這名字我是記得的,那年吳曉青過世時,他們那一屆好像特別悲傷,我曾陸續讀到過幾篇淚漣漣的悼文。年輕未婚的吳曉青大概像...
目錄
推薦序:
柳丁與番茄/黃錦樹
我們不必擔心明早的文明,不必為自己寫碑/童偉格
番茄街游擊戰
我的黃皮膚哥哥
情人們
推薦序:
柳丁與番茄/黃錦樹
我們不必擔心明早的文明,不必為自己寫碑/童偉格
番茄街游擊戰
我的黃皮膚哥哥
情人們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3收藏
13收藏

 23二手徵求有驚喜
23二手徵求有驚喜




 13收藏
13收藏

 23二手徵求有驚喜
23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