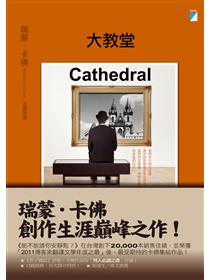周芬伶歷時二十年完成的文學史傳
作者從發想、修改到出版,整整歷時二十年。透過訪談龍瑛宗次子劉知甫,以及長子劉文甫的修訂,源源本本記錄龍瑛宗以寫作與工作為重心的一生,及其對台灣文學發展的貢獻。
一九一一年(民國前一年),出生於日治台灣的龍瑛宗,是個客家孩子,沒學過漢文,所以他精通的是日文和客家話。龍瑛宗最精彩的生活是在戰前,二十七歲以日文作品〈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榮獲日本《改造》雜誌第九屆懸賞小說佳作獎,開始受到台日文學界的矚目。然而,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台灣的統治者換成了彼岸的國民政府,三十五歲的龍瑛宗喪失了發聲的舞台,面對陌生的中文和福佬話,他只能選擇靜默。戰後的生活平淡加上停筆,有四十幾年的生活空白。
龍瑛宗婚姻生活不幸福是他的悲劇之一,中文書寫與日文書寫水準相去懸殊是悲劇之二,他的生不逢時是悲劇之三……,他的一生過於安靜,就像他的人一樣。
身為文學家的他越是無法書寫,心緒就越是苦悶,妻子的強勢和難以契合的思想,令龍瑛宗簡直無所容於天地間,這段期間閱讀日文書是他逃避現世、遁入心靈的唯一途徑。困頓中的龍瑛宗勉力自學中文,五十多歲後才能慢慢以中文寫作,也重新受到世人的注意。
開始以喜愛閱讀的龍瑛宗,年輕時為了省錢常站在書店看書拉開序幕,接著從頭細數發生在劉家的家族悲劇如何影響龍的一生、文壇上大放異彩的歷程,與張文環、吳濁流、呂赫若、王白淵等文人的互動、參與編輯工作、學習國語以中文寫作的艱辛、各處旅行的回顧、最後在病榻上回憶的前塵往事……
作者簡介:
周芬伶
政大中文系畢業,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現任教於東海大學中文系。曾獲吳濁流小說獎、中國文協散文類文藝獎章、中山文藝散文獎、吳魯芹散文獎、台灣文學獎散文金典獎。跨足多種創作形式,著有散文《紫蓮之歌》、《母系銀河》、《汝色》、《花房之歌》、《雜種》、《蘭花辭》、《北印度書簡》等,小說《影子情人》、《浪子駭女》等,以及少年小說、文學論著等多種,另編有散文、小說選本。
章節試閱
序曲—愛看站書的年輕行員
一九三○年代,在台北市的書店街,即重慶南路與衡陽路,這一帶在日據時代稱為「本町」,衡陽路為「榮町」。本町與榮町的路口,正好位於新公園西入口出來的第一個十字路口,是當年本町通與榮町通兩條繁華街道的交會點,是所謂的黃金路段。這個十字路口也成為日據時期台北街道風景明信片最經常出現的街景之一,這裡有台北最高建築物菊元百貨店,還有三軒書店、新高堂、文明堂與杉田書店。緊臨著總督府的台灣銀行,高大的巴洛可建築走出一個行員,每天他幾乎都到附近的書店街中報到,這個瘦小青年常流連在這裡立讀,最常光顧的是新高堂,其次是杉田書店,站書看久了,他摸出一個要領,只要小心不要弄髒新書刊,那麼老闆就不在意;因此他翻書的動作非常小心,以撫摸輕觸的方式進行。他的臉孔瘦而外凸,有小暴牙,身高約一六○左右,體重也才四十多,在日本人中不算矮小,在本島人中算是小的,因此常被誤為日本人。
他看書的時間極長而且非常專注,常常把一本小說讀完才捨得離開,這種站讀習慣從他來台北讀書即開始,一直到老還不罷休。書籍對他來說是寶庫,也是心靈的寄託所。除了讀,他更想寫,他對自己的寫作極有自信,在工商學校念書時的國文老師,常讚美他的日文寫作比日本人好,還常在課堂上念給同學聽,讓他感到得意又害羞。三十歲,他把時間定在三十歲,那時一定要在文壇上佔有一席之地。一邊想著,拚命翻動書冊的他,眼睛閃著精光,他的內心有著如黑夜般的伏流湧動著。
有個晚上到西門町散步,在路邊買到一些二手舊雜誌,如《中央公論》、《改造》、《新潮》、《文藝春秋》等,回家仔細翻閱,看到《改造》舉辦懸賞小說活動。當時張文環已以《父親的臉面》入選過新人賞,選外佳作,也就是說台灣人有機會得獎,還沒真正入選。
那是一九三六年,他已二十六歲,距離三十歲很近了,這令他有點焦急。有一天他翻著新出的《改造》雜誌,讀到朝鮮作家張赫宙的作品〈餓鬼道〉入選懸賞,這對他來說無疑是一道曙光,原來殖民地的作家也是可以跟日本人相比肩,他心想著:「朝鮮人既已進出日本文壇,台灣人怎麼不可以呢?」當時《改造》雜誌與《中央公論》、《文藝春秋》並稱為日本三大雜誌,它們對政治經濟有一定的影響力,尤其是在文藝上的表現可謂百花齊放,其中《中央公論》的立場是中間偏左:《改造》是較為激進的左派;《文藝春秋》則是十分保守的右派。《改造》的文藝獎精神是為底層的階級伸張,有時與殖民政策站在相反的立場,這次入選的張赫宙,一九○五年生於韓國慶尚北道。以〈餓鬼道〉一作進入日本文壇,作品被評為「對日本帝國主義之榨取殖民地韓國農民之正面告發的憤怒文學」,成名之後前往東京定居,後提倡「內鮮一體」之論,戰後的一九五二年,娶日本人為妻改名野口赫宙,歸化日本籍。張赫宙與另一位韓國作家金史良被認為「在日韓國人文學」的嚆矢。
張赫宙的成功,讓龍瑛宗十分振奮,小商家出身的他,靠著優異的成績,得以在日本人銀行中佔有一席之地,但作為殖民地的子民,他懷著抑鬱不得志與不滿,雖然在令人歆羨的金融機構台灣銀行工作,薪水只有三十圓,與日本人相差甚多,他的職務是辦理儲金、匯兌、日台翻譯。由於他是客家人,不懂閩南語,故常受日人斥責。前幾年還被發配到南投分行,那個中部山區小鎮,那被上司與同事欺壓,有志難伸的痛苦令他難以忘懷。連祖母死亡也不能奔喪,唯一談得來的女友兵藤晴子,也被分行副理干涉警告。南投那四年,不僅毀了他的情夢,還讓他的文學夢延宕四年。要寫就寫那個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那充滿水果腐朽氣息的空間,他對空間與景物具有異常的靈敏感覺,能將它化為小說氛圍與象徵。
午後,陳有三來到這小鎮。
雖說是九月底,但還是很熱。被製糖會社經營的五分仔車搖晃了將近兩個小時,步出小車站,便被赫赫的陽光刺得眼睛都要發痛似地暈眩。街道靜悄悄地,不見人影。
走在乾裂的馬路上,汗水熱熱地爬在臉上。
街道汙穢而陰暗,亭仔腳﹝騎廊﹞的柱子燻得黑黑,被白蟻蛀蝕得即將傾倒。為了遮蔽強烈的日曬,每間房子都張著上面書寫粗大店號─—老合成、金泰和—─的布篷。
走進巷裡,並排的房子更顯得髒兮兮地,因風雨而剝落的土角牆壁,狹窄地壓迫胸口;小路似乎因為曬不到太陽,濕濕地,孩子們隨處大小便的臭氣,與蒸發的熱氣,混合而升起。
通過街道,馬上就看到M製糖會社。一片青青而高高的甘蔗園,動也不動;高聳著煙囪的工廠的巨體,閃閃映著白色。
一下筆幾乎不能自休,從一九三六年八月開始,每天利用上班前短短的一兩個鐘頭寫一兩頁,持續四個月。那時銀行工作很忙,忙到許多人得肺癆喪生,晚上還得加班,加完班夜色已深,也只有早起偷寫一點算一點。如此四個月寫出〈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年底將一百多頁稿子寄到東京,他想如果今年不入選,明年再參加,一直投到三十歲,如果失敗,就斷絕文學之路。
一九三七年四月這篇小說得到《改造》雜誌懸賞小說「佳作推薦」,獎金五百圓,是筆大數目。按「佳作推薦」在一九三五年的第八回懸賞創作入選發表以前,沒有用過這個名目或獎項。一九三六年曾停辦,一九三七年的第九回懸賞創作入選發表以後,才用這個新名詞。當時好像夠水準的作品相對地減少,因此沒達到一等以及二等的作品就用新詞「佳作推薦」。
文章刊出時,龍氏的得獎引起一些討論,大家都好奇這是哪號人物?
當時的徵文比賽,共有八百多篇參加,沒有入選作品,只取佳作兩篇。龍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及渡邊 涉君的〈晨霧〉,佳作推薦不記名次,但先刊登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他的作品發表於一九三七年四月號、渡邊的作品發表於一九三七年七月號。當時之所以沒取入選,也許正如三輪健太郎所言:「從現在文壇的水準來看〈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雖然不是難看,但一點也不屬於優異的作品」,但是本島人「龍君的出現確實也給我國現代文學增加了另一個領土吧」,因此他被視為台灣的張赫宙,三輪也是《改造》的得獎作家,說的話也許過激,但也顯示主編者與日人的優越感與偏見。這個消息也讓日人引起討論,慶應大學出身的作家持質疑的態度,早稻田大學的作家則十分激賞,早大是日本自然主義的大本營,對他富於風土人情的書寫自然投以好感。文藝評論家杉山平助於《朝日新聞》,評論他的小說,並打八十分,以日本嚴苛的標準,算是高的。作家葉山嘉樹評曰:「這不是唱著台灣人的悲哀,是唱著這個地球上被虐待階級的悲哀。這種精神共通於普希金,共通於高爾基,共通於魯迅,也共通於日本的普羅作家。這篇小說作為充分具體地內含了最高文學精神的作品,我在此推崇其入獎。」也有質疑其創作態度的「把黑暗當作黑暗予以某種程度上肯定著的作者態度,在質樸中奇妙地意識著小說的構成之點,含著叫人難以贊成的因素。透過題材存在於其背後的作者之眼並不十分澄澈,是比什麼都讓人對這位作為一個現實主義的新進作家今後之成長感到擔心」。更有譏嘲其「文章拙劣」、「描寫笨拙,人物的說明也不夠」;「沒有賣弄小聰明這點是很好的,但這位作家令人覺得他在說謊」;這其中較為中肯的意見當屬出生於台北的中山侑:
可是開頭那種拙劣的文筆,後來描寫故事中心「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內部,以及描寫居住在那兒「受教育的年輕本島青年」的煩惱時,就渾然達到靈魂與肉體一致的境地,會很快吸引讀者,在這裡處理的題材十分強烈,這一點要給予較高的評價吧!……
而且在這個小鎮(島)上,煩悶不僅是常見的社會憂悶,而是在每一個人所依靠的家庭生活上,這才是真正受台灣家族制度的折磨,他們都無法避免有雙重的痛苦。受到社會和家庭雙重的壓迫,他們才真正是世紀的精神上的孤兒了。不必聽到戴秋湖、蘇德芳的體驗,聘金制度帶給本島青年的煩惱,就切切實實打動我們的心。作者龍瑛宗氏是把「受過教育的本島青年」知識分子的悲哀,以及舊家族制度的幽靈,在〈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裡,以寫實的筆致,切實描繪下來。而且現在加上某種偏見,苛酷地投給他們三重痛苦(這或許他不懂,他才沒有寫)。
這不僅限定於一個部落的情形而已,也不是一個部落普遍有的情形。
從這一點來,我才對這一篇作品,給予較高的評價。
中山侑是活躍於台灣文壇的作家,作品追求現代主義精神,有詩〈招待至熱帶〉、小說〈透視鼓浪嶼〉,也許從台灣人的眼光更能透視作品的深層內涵。也許是巧合,這篇文章說明了作者對自己嚴苛的反省,及對作品嚴酷的要求,這幾乎是他一生的縮影。他一生受到三重痛苦,社會的、家庭的、自己的。也就是對於殖民地青年的心靈分裂、身分分裂的高度自省。其中,描寫最著力的是經濟問題,薪水、階級、聘金皆緊扣著「金錢」,這裡有一個學商行員的現實觀察。很顯然的,裡面的地景與人物跟他在南投四年的「下鄉」觀察有關。
得了這個獎意味著他已正式踏入文壇,為了買書,也為了踏入那夢想中的現代與文學之都,他決定前往東京,一九三七年六月向銀行請假一個月,第一次遠度重洋,對一切事物都感到十分新鮮,六月六日他抵達神戶港,搭「燕」號快車到東京,可惜經過富士山已暮色蒼茫,讓他沒達成眺望富士山的願望。他對東京的第一個印象,是「街上的霓虹燈裝飾,像孔雀展出絢爛的翅膀那麼美麗」;六月七日,午後訪問改造社,他與多位文藝界人士見面,包括作家阿部知二、評論家青野季吉等知名人士。在上野的喫茶店,會晤《改造》編輯水島治男(水島治男著有《改造社的時代〈戰前編〉》以及《改造社的時代〈戰中編〉》,兩本都在一九七六年,由日本的圖書出版社出版)。明治大學的教授與作家阿部知二(一九○三─一九七三,岡山縣人,東京帝國大學英文學科畢業,小說家、英文學者、翻譯家)也來信希望能晤談,他到阿部家訪問,阿部聊著中國故都的風光如何美好,空氣非常乾燥,不像日本濕氣太重,兩人相談十分愉快,阿部的代表作品《冬天客棧》於一九三六年問世,名震一時。龍氏也拜訪了文藝評論家青野季吉,他談了一些文學問題,讓龍氏覺得獲益匪淺;在鬧區新宿有名的中村屋附近,一家鮮果店裡,會晤作家芹澤光良,他也是《改造》入選作家,龍向他請教許多文學問題。
《改造》第一屆入選者保高德藏(一八八九─一九七一,大阪人,早稻田大學英文科畢業,小說家),對他關懷備至,保高也是早大畢業,並主編《文藝首都》雜誌,邀龍氏成為《文藝首都》(一九三三年創刊)的會員。他拜訪《改造》雜誌那天,保高以溫柔的態度請他入內,然後對他說:「原本預定和張赫宙聚會後再和你見,但那之前你能夠來拜訪我,真令我高興。」
龍看了這個他想像已久的編輯部,放置了許多讀者的來稿,桌上攤著丹羽文雄的信,以及宇野浩二的原稿,跟他想像的差不多,如果他也能做同樣的工作多好!編輯工作對他來說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他既能看到許多稿子,也能發揮文學的影響力,尤其在二三○年代,文學刊物的讀者眾多,文學雜誌編輯通常是資深作家,像保高,長期為文學效命,默默耕耘,在龍的腦海裡烙下深刻的印象,保高是他夢想的引領者,他的心跟手因興奮而顫抖,久久說不出話來,還好住過台北的社長山本實彥先生助理頻頻問他台北的情形,令他原本緊張的情緒放鬆下來。
他們走出辦公大樓,穿過芝公園來到增上寺,一路談論文學:直木三十五、坪田讓治、宇野浩二等幾位作家的事,搭上計程車來到銀座,巧遇石川達三、高見順、田村泰次郎,都是當紅的作家。高見正為興建「日本近代文學館」努力(位於東京目黑區駒場,一九六七年開館),石川寫《活著兵隊》(一九三八年發表,描寫日軍在中國戰場的自由創作性小說)。龍當時對那乾枯的噪音與狂躁所籠罩的銀座暮色,印象十分深刻。
保高可說是他的文學知音,他在《改造》第一回懸賞中以〈孤獨結婚〉(一九三六年)入選而成為作家。沉寂一段時間,再以長篇《勝者敗者》(一九三九年)轟動文壇。對於他的作品風格,川端康成評曰:「受到自然主義形式甚多的影響,作品予人略微陰暗的印象。但是,就傳統日本小說於人物的描寫而論,畢竟有新進作家無法企及之處。」保高對於拔擢新人十分用力,幾乎把時間都傾注在《文藝首都》上,他與龍的文風相近,有英雄惜英雄之感。
六月十一日,龍逛淺草電影街,看了一場電影《騰空的戀》,是沒什麼內容的娛樂片,感到失落極了。走過各條街道,蒼白的丸之內、沒特別興趣的銀座、充滿新興活氣的新宿、後街的咖啡館,感覺東京樹木很多,相較之下,台北比較具有都市體系。當時的龍認為台北比東京更具都市體系,令人驚訝,細想之下,也許台北因日本殖民政府當作美麗新世界來改造,在三四○年呈現異樣的繁華,從研究老台北歷史的資料來看,無論建築、都市規劃都比我們想像好,而關東大地震之後與戰爭前夕的東京蕭條一些是正常的,那是都市的外在,在內涵而言,具有科學與知性的優越感,文學活動相當活躍;六月十三日,看東寶劇場,對他來說是鮮豔的刺激,票價也很昂貴,對輕鬆歌舞劇一向不喜歡的他,只眩惑於絢爛的衣裳,還有女明星的反串表演;六月十九日,逛神田舊書店,買了一些書,對於買書他一向最捨得花錢,就貧窮的讀書人來說,東京的書相對多樣而便宜,台北人口三十萬,書店只有三家,他為十錢買到《德田秋聲集》感到憤怒,應該說是寂寞,一生的寶貴著作,用這麼少錢就可買到?六月二十日,到橫濱,是個西洋風味很重的港口,港口白色的外國船隻彷彿燃燒著鄉愁,沿著山坡有許多美國殖民時期的建築,也有外國人墓地,碼頭的汽笛聲聲聲催促,浪漫的港口曾被許多作家寫入作品中,這裡充滿異國風味,有洋人當眾親吻,還有穿黃袍的阿拉伯人或印度人,而南京街的中國戲曲正要上演;六月二十一日寫〈東京的烏鴉〉隨筆,因為烏鴉的聲音太突兀,可說是對東京最強烈的印象,東京為什麼那麼多烏鴉?他寫著:「我堆積著滿滿的旅愁來到東京,卻為了烏鴉的啼叫聲而感到煩惱.走在被梅雨淋濕的東京的人行道,或倚靠在旅社的窗邊時,突然,烏鴉發出惡魔性的叫聲,飛過挾在屋頂與屋頂中間的樹木上而去。那個時候,我就會被封閉在非常悲哀的鄉愁裡了。」在鄉下,人們相信烏鴉啼就會有人死,那是個凶兆,他的心因此充滿不安;六月二十三日,逛日本橋兜町交易所與濱園町貧民窟,貧與富的對比,讓他思考經濟的問題,這也算是業務考察;六月二十五日,在咖啡館思索著東京之所以偉大,是富於科學性精神的知性造就的。日本在世界史上能完成驚人的發展,根據的是科學主義吧?
東京經驗對他而言是精神的沖刷,這些過程他以鄉巴佬的自謙寫成〈東京鄉下佬〉、〈東京的烏鴉〉刊於八月號的《文藝首都》,描寫在東京的街頭突然聽到烏鴉發出惡魔般的叫聲,讓人封閉在濃濃的鄉愁裡。在知性的科學精神之都,他靈敏的直覺卻讓他感到不吉與不安。
序曲—愛看站書的年輕行員
一九三○年代,在台北市的書店街,即重慶南路與衡陽路,這一帶在日據時代稱為「本町」,衡陽路為「榮町」。本町與榮町的路口,正好位於新公園西入口出來的第一個十字路口,是當年本町通與榮町通兩條繁華街道的交會點,是所謂的黃金路段。這個十字路口也成為日據時期台北街道風景明信片最經常出現的街景之一,這裡有台北最高建築物菊元百貨店,還有三軒書店、新高堂、文明堂與杉田書店。緊臨著總督府的台灣銀行,高大的巴洛可建築走出一個行員,每天他幾乎都到附近的書店街中報到,這個瘦小青年常流連在這裡立讀...
推薦序
政大台文所講座教授 陳芳明 推薦
夢見愛與死——《龍瑛宗傳》序
未完的愛,未遂的死,貫穿龍瑛宗的一生。青春時期所夢想的初戀,即使未曾開花結果,卻永恆地保留在靈魂深處。結婚後的龍瑛宗過著不快樂的日子,一直到六十歲之前,他常常有著自殺的意念。求愛未成,求死不得,構成了龍瑛宗文學最迷人之處。生命的完成總是以殘缺的形式呈現,他有許多話想說,卻從來沒有完整表達的機會;他有許多願望想要實現,卻都最後找不到破土的機會。他的一生,就是一首未完成的長詩。跨越兩個時代,他從未輝煌過,就像詩那樣充滿了象徵、隱喻、暗示,具體的內容卻都隱藏起來。
周芬伶的《龍瑛宗傳》,把跨越兩個時代的台灣作家,相當生動地描寫出來。到目前為止,似乎沒有一本精彩的作家傳記,可以寫得如此動人。她寫了二十年,斷斷續續,終於沒有擱筆。在漫長的歲月裡,周芬伶的散文與小說日益精進,卻從來沒有忘懷她要為龍瑛宗立傳。這部作品如果完成於十年前,恐怕無法臻於完美的形式。遲到與延宕的書寫,本身就是一種折磨,但也是一種等待。二十年後,周芬伶的散文技藝已經到了不容失誤的地步,只要她一出手,就是令人擊節讚嘆的文字。恰恰就是她在文學最成熟的階段,她適時完成這部傳記的書寫,果然就是出手不凡。從第一章描寫劉家從唐山渡台的故事,便緊緊扣住讀者的心。劉氏家族的傳承,經歷太多的夭折與死亡,那樣坎坷的命運竟然孕育了一個傑出的文學靈魂,簡直是近乎傳奇。
龍瑛宗最精彩的文學生涯,其實相當短暫。一九三七年,他所發表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讓他獲得日本《改造》雜誌的文學獎。那年他二十六歲,這個獎項燃燒了他的生命。身為銀行的職員,總是在數字裡討生活,他卻在文字中找到心靈的寄託。經歷太平洋戰爭,他慢慢覺悟文學並不是純粹的藝術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受到政治權力的干涉。如此早熟的台灣作家,也預告了他日後早夭的文學生命。他從未預知舊的時代很快就要消失,新的時代則又匆匆到來。在兩個時代交錯而過之際,並不僅僅是政治權力的轉移而已,其中還有相當惱人的語言轉換。
《龍瑛宗傳》無論就結構或文字而言,都可視為周芬伶書寫的高峰。書中所承載的藝術價值,完全不亞於她的小說與散文。或者更確切而言,如果沒有小說與散文的藝術造詣,也許不可能使這本傳記到達一定的高度。開篇的序曲,出手就頗不尋常。她優先從青年龍瑛宗的愛書歲月寫起,然後分成兩頭敘述,追蹤劉家祖先如何渡台、開拓,並且也開始建構獲獎之後龍瑛宗的文學生涯。她穩定掌控著作家的生命節奏,探索戰爭時代的文學心靈,如何被當時各種不明的政治挑戰所覆蓋。
全書的序曲「愛看站書的年輕行員」,便是描述一九三○年代初入銀行的年輕人,如何在當時台北銀座的書店站著看書。彷彿是一場黑白影片的開端,顏色恰到好處,準確掌握了那個時代的光與影。這位年輕人不僅僅是看書而已,內心裡還暗藏著一個文學夢。這位殖民地青年,對於遠在東京的中央文壇懷抱著一定的願望,希望有一天他的作品能夠被看見。一九三七年,他寫出〈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雖然是推薦佳作,卻是在八百餘位投稿的作者中脫穎而出。在日本雜誌入圍,等於也宣告一個殖民地作家的誕生,他的生活與思考從此有了巨大的改變。但是他自己不知道,身為作家,其實比同時代的知識分子還要受到矚目。這樣的身分帶來的不是祝福,而是詛咒。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國民政府來台接收。龍瑛宗以為一個更為美好的時代就要到來,他甚至南下去擔任《中華日報》日文版的編輯,以為可以延續他年少的未遂之夢。他未曾預料,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宣布,從此禁用日文。作家所能憑藉的思考武器,無非就是語言。當日文使用受到禁止時,對他而言,中文反而是一種折磨。在傳記中,周芬伶對語言問題的描述用功甚深,從而也反襯了龍瑛宗所承受失語症的痛苦。龍瑛宗在日語禁用的前夕,寫了一篇〈台北的表情〉,深深感嘆為什麼戰爭結束之初,台北市民的笑容處處可見,一年之後,所有的表情都化為苦悶。龍瑛宗寫的是城市的表情,無疑也是在寫他自己的心情。殖民地知識分子的悲哀,莫此為甚。
這本傳記最為精彩之處,便是觸及龍瑛宗的文學過從。她寫戰爭時期的文壇時,以「這些與那些文人們」為題,點出龍瑛宗分別與日本作家、台籍作家的往來經過。這是書中最迷人的一章,藉由龍瑛宗所處的位置,可以窺探當時活躍文壇的作家身影。在考察友情時,周芬伶特別彰顯龍瑛宗與台籍作家呂赫若、張文環是如何親近,對日籍作家西川滿、濱田隼雄是何等厭惡。在檢查作家之間的親與疏,周芬伶還特別閱讀雙方的文字記載。凡是熟悉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史者,都知道台籍、日籍作家之間的緊張關係,表面是虛與委蛇,背後則是頗多微詞。很少有人如此生動寫出作家之間的感情升降,周芬伶為我們鋪陳了一個較為完整的面貌。雖然描寫的是友情問題,卻也精確掌握了戰爭時期文壇的生態。
這樣的筆法,也延伸到戰後時期。戰後新時代的誕生,竟是以悲劇的二二八事件作為歷史的開幕。龍瑛宗目睹自己的朋輩一個一個開始停筆,強烈感受恐怖氣氛從四面籠罩起來。一九五○年代初期,他聽聞呂赫若死亡,楊逵、葉石濤入獄,終於不能不承認他所期盼的和平時代,永遠不再到來。但是更為痛苦的是,他無法使用流利的中文,而且也見證了許多文友一個一個開始封筆。他年少時期的文學夢,終於宣告破滅。他能夠寫出日文作品的機會甚少,只有在向日本發行《今日之中國》的宣傳刊物上,能夠發表幾篇短文,除此之外,龍瑛宗徹底變成一個被遺忘的名字。
書中有一段非常生動的畫面,便是龍瑛宗在合作金庫工作時,參加了棒球隊的活動。其中有一段敘述,重建了台灣的棒球史,從嘉農隊參加日本甲子園的比賽寫起,一直到戰後棒球成為台灣體育史上的主流,都有著相當生動的記載。棒球是殖民地時期遺留下來的體育活動,這可能也暗示了龍瑛宗在心靈上的某種寄託。身為銀行員,他一直沒有放棄追逐文學的夢想,他與吳濁流、張我軍、郭水潭、楊雲萍、王白淵、王詩琅、吳新榮始終保持密切的聯繫,在內心他非常羨慕鍾肇政能夠以中文書寫小說,那是他永遠無法企及的夢。
周芬伶在傳記裡,對於龍瑛宗的家庭生活描述得尤為清晰。龍瑛宗與他的妻子李耐,一直處在緊張的狀態,往往為了瑣事細故而造成語言上的衝突。曾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龍瑛宗常常想要自殺,那種死亡的陰影甚至他的兒子也能感受。正因如此,他常常想念初戀的日本情人兵藤晴子。這位女性是他永恆的嚮往,沒有完成的戀愛總是完整而美好地保留在心靈深處。懷抱著這份感情,他反而在現實的家庭生活中感到殘缺。周芬伶曾經出版過一冊《憤怒的白鴿》,其中第一篇便是〈作家的妻子:李耐的婚姻故事〉,寫的正是龍瑛宗的婚姻生活。這篇記錄並沒有直接描寫龍瑛宗,卻讓他的妻子李耐、他的媳婦郭淑惠、他的兒子劉知甫發出聲音。這篇文字是一種反白式的紀錄,也就是作家本人沒有發言,卻由他的家族成員從旁描述,終於浮現了作家的生命歷程。這篇訪談的篇幅甚短,卻相當深刻描述了龍瑛宗不為人知的生活。
二十年前,周芬伶便已發願要寫出一部《龍瑛宗傳》,當時我也答應要寫《楊逵傳》。經過這麼多年之後,她始終沒有放棄,反而意志更加堅強。能夠使傳記順利完成,應該歸功於《龍瑛宗全集》的出版。而更重要的是,龍瑛宗的兒子劉文甫與劉知甫都樂於接受訪談,他們都說出不為人知的龍瑛宗。置身於龐雜的史料、作品、訪談之間,周芬伶可以有條不紊理出一條記憶的線索,那樣清楚,又那樣起落有致。我曾經去拜訪過龍瑛宗,那時他已經無法言語,整個晚上我與這位可敬的老人對坐,整個客廳特別安靜,只見到他不停微笑頷首,那是我僅有的一次見面,也是最後一次見面。如今捧讀《龍瑛宗傳》時,他的影像宛然在眼前,反而特別生動,其中所表達出來的感情,更是強烈衝擊著我。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日 政大台文所
政大台文所講座教授 陳芳明 推薦
夢見愛與死——《龍瑛宗傳》序
未完的愛,未遂的死,貫穿龍瑛宗的一生。青春時期所夢想的初戀,即使未曾開花結果,卻永恆地保留在靈魂深處。結婚後的龍瑛宗過著不快樂的日子,一直到六十歲之前,他常常有著自殺的意念。求愛未成,求死不得,構成了龍瑛宗文學最迷人之處。生命的完成總是以殘缺的形式呈現,他有許多話想說,卻從來沒有完整表達的機會;他有許多願望想要實現,卻都最後找不到破土的機會。他的一生,就是一首未完成的長詩。跨越兩個時代,他從未輝煌過,就像詩那樣充滿了象徵、隱喻、暗...
目錄
夢見愛與死——《龍瑛宗傳》序 陳芳明
序曲 愛看站書的年輕行員
第一章 劉家的家族悲劇
第二章 站上舞台的文學新星
第三章 這些與那些文人們——戰爭時期的文壇
第四章 華麗與非華麗——歌頌南方的評論家
第五章 合庫與棒球
第六章 戰後初期的搏鬥
第七章 與語文搏鬥
第八章 在死亡的邊緣——中文寫作的苦戀
第九章 重要的轉折
第十章 旅行與歷史的回眸
第十一章 病榻
第十二章 尾聲
後記
附錄 龍瑛宗年表
夢見愛與死——《龍瑛宗傳》序 陳芳明
序曲 愛看站書的年輕行員
第一章 劉家的家族悲劇
第二章 站上舞台的文學新星
第三章 這些與那些文人們——戰爭時期的文壇
第四章 華麗與非華麗——歌頌南方的評論家
第五章 合庫與棒球
第六章 戰後初期的搏鬥
第七章 與語文搏鬥
第八章 在死亡的邊緣——中文寫作的苦戀
第九章 重要的轉折
第十章 旅行與歷史的回眸
第十一章 病榻
第十二章 尾聲
後記
附錄 龍瑛宗年表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8收藏
8收藏

 13二手徵求有驚喜
13二手徵求有驚喜



 8收藏
8收藏

 13二手徵求有驚喜
13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