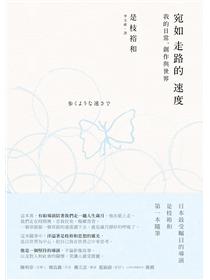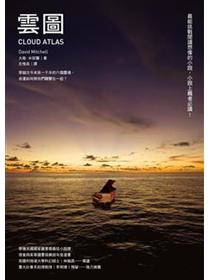名人推薦:
侯孝賢
我感覺,有時候拍片你不能想太多,是憑直覺的。因為你一直接觸,其實最重要的還是『客觀實體』,就是人,或這個環境,這個很重要。因為這個東西永遠是你眼見的、寫實的;你在再造的過程裡,這就是你所面對的真實、現實;你面對這個現實、真實,你才能穿越;穿越了電影,你就不會有別人電影的影子;因為你一直在面對你眼前的這個時代,存在於你眼前的這些人,你在電影裡表達的是你對他們的一種感覺,或是你自己的感覺藉助這些人表達出來。」
吳念真
「在自己的生命過程裡,曾經參與過這樣的一個工作,其實它真的沒什麼特別,比較起生命中很多起起伏伏的大事,我覺得,它已經不算什麼了,許多事都可以取代它,在你自己的生命中,譬如誰的過世,那個太大了;這個對我來講,已是小事了。甚至我常常忘記我寫過哪些劇本,有時候晚上看電視,好熟啊,才發現,這個劇本是我寫的。沒什麼特別。」
邱復生
「一部作品,你要怎麼去平衡到既有藝術價值、同時又有觀眾,究竟能夠調整到哪一個程度,讓它產生經濟價值?這就是技術。這些,沒有幾個人能做得到。一個一個時代看下來,我覺得,現在的電影越來越困難,也越來越簡單,就看你往哪條路走會越簡單,往哪條路就越困難。」
陳國富
「我當年會走進電影製作這條路,跟孝賢有絕對的關係。我記得以前我剛開始寫評論時,有人問我,你會不會想,自己有一天也當導演?我說,不可能,因為電影太難了,我也不是科班的,我也沒有從場記、副導演開始幹起;對我來說,電影完全是一個遙不可及的事情。但是我當時是碰到了孝賢、楊德昌、張華坤這些人,他們讓我覺得是可能的,只要你敢想像、願意試,都是可能的。 其實我這幾年在大陸的經驗並沒有脫離這樣的軌跡,我希望我還是堅持這種直覺及情感取向,繼續走下去。」
朱天文
「你如果是電影裡頭拍電影,那會非常窄;電影縱深下來,看了這麼多電影,如果只是在這裡頭拍電影,就會有他的瓶頸。要還能走下去,其實很多地方要從非電影處來的。……如果你用很多電影的模式或知道的電影知識,當然那些要學、要看、要知道,但是最終你還是活在當代,你活在這裡,那你不去看看你的當代?其實這也是你的責任。此身不生生何生,你已經生在這個時代了,這是你的優勢,因為下一代人也看不到你的現在,你以前的人也不知道你的現在。」
新電影發展軌跡上最重要的一個句號
黃建業(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及電影創作研究所專任副教授、資深影評人)
藝術作品經歷過時間的考驗,淘去每一個時代特定流行的價值觀,有時會變得越發清晰明亮,台灣新電影代表作《悲情城市》歷經二十多年,再作回眸,就像一面重新被擦拭的鏡子,撥去塵埃後,更能顯露出它獨特的時代風華。某些對經典作品重新檢視的行為,不單讓作品在新時代新感性的碰撞中,體認到它強韌的原創意義,有些時候更能迸發新的火花,在時代的行進中,激勵出全新的文化啟示。
《悲情城市》似乎是新電影發展軌跡上最重要的句號,就像某些文章結尾時,特別標示出一行作為結論,鏗鏘有力地為台灣新電影鑄刻著藝術成就及人文關懷的印記。一九八九年《悲情城市》的出現,似乎是台灣新電影踏入一九九○年代前,對自已作出最具野心的總結。《悲情城市》不單標示出代表侯孝賢電影美學從《風櫃來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戀戀風塵》後,越來越大膽成熟的客觀寫實美學的重大成就。它更代表了臺灣新電影在本土歷史探索和社會性揭露的最終突破。當然本片獲得威尼斯金獅獎的加冕,確實為新電影於八○年代末在保守現實與尖銳批評的波瀾中,尋找到最有力的支撐和發展定調,有著極重要的意義。
很多專家學者在近二十多年間,己經對《悲情城市》發表了相當可觀的探討和研究;在在都證明《悲情城市》不論在社會歷史及藝術美學意涵上,均有其豐富且多面向的成就,作為臺灣新電影的歷史發展而言,《悲情城市》也代表了某一重要歷史階段的任務完成。其經典的位置,有著越來越呈現不可動搖的意義。先從其社會歷史面向來談,《悲情城市》超越時代的禁忌命題,直接表現最大的政治禁忌「二二八事件」,這也是《悲情城市》在當時備受執政和反對黨重視和施加壓力的原因。《悲情城市》在歷史詮釋觀點上,完全未曾刻意依附於兩黨的既定意識形態。在當時堪稱兩面不討好,但因為先獲得威尼斯影展的藝術冠冕,政治的批評與干擾也變得微妙和收歛得多。如今看來《悲情城市》隱晦的觀點顯得明朗,侯孝賢的客觀歷史態度,反而不會掉入非黑即白的二元扁平角度。侯孝賢真正關注的無疑是那些在族群利益糾葛中,善良甚至沉默地犧牲的人民與質樸的生活感情和夢想。這就不難瞭解為何《悲情城市》中出現那麼複雜的族群爭鬥,還有那位無法言語的照相藝術家及一群鮮少發言的女性。《悲情城市》本身的史詩格局,並不是因為它以歷史為背景,而是因為侯孝賢在片中,揮灑出一份沉澱渾厚的歷史掌握與關懷。這甚至可能出現在不同的國家、城市及不同的族群,也使《悲情城市》不至於變成一個地方角頭家族的沒落史。政治的污濁和黑暗,如此微妙地建立在利益與黨同伐異的鬥爭之中,失聲的藝術與人性的溫善,瘖啞無語。
今日回看《悲情城市》的藝術問題,它一方面有力地推展侯孝賢前面作品,逐漸洗練的寫實感和客觀性,它另一面是侯孝賢電影美學在《童年往事》及《戀戀風塵》後,進一步渾厚地呈現詩化影像及文學元素的傑作。Kent Jones盛讚本片在陳松勇被殺身亡後,蒼蒼天地間孤鳥低翔的鏡頭,正是這個原因。如同在《童年往事》中貼在玻璃上滴水的郵票,及《戀戀風塵》一塊浮雲掠過山際平原,侯孝賢的詩化影像,直接在現實細節中滲漏著承接前段文理,所產生的複雜曖昧性。
侯孝賢的電影美學,到了《悲情城市》真可謂穿越眼前的真實,透露客觀鏡語下的文學詩情。在一九八○年代整個新電影的發展中,在鏡頭內蘊的豐富性上,無人能及。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告投降,昏昧未明的八斗子作開始,《悲情城市》中侯孝賢也試驗著他從未出現過如此複雜的取材及敘事手法,他將故事佈局推向鮮有的不同社群及龐大的敘事架構。當時有不少國人一直懷疑國際影人如何能瞭解如此龐大而人物眾多且方言混雜的電影。甚至認為就像一九五一年《羅生門》獲獎一樣,推斷應是對東方文化的誤解,才是其得獎原因。本片的敘事企圖,事實上也開始了侯孝賢往後越見大膽的敘事及取材試驗,從一九九三年的《戲夢人生》開始,到《好男好女》、《南國再見,南國》、《海上花》、《千禧曼波》、《咖啡時光》、《最好的時光》、《紅汽球》都證明了侯導演,踏入一九九○年代後,各種教人咋舌的大膽嘗試,都是向不同元素的藝術冒險。《悲情城市》像一個結論,也像一個開始。它在其藝術上的渾厚和準確,也標誌著台灣八○年代末,社會、政治、藝術眾聲喧嘩下,最令人懷想的一個特別的時空。
讓台灣影史不再悲情的《悲情城市》
聞天祥(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執行長、知名影評人)
《悲情城市》在台灣電影史上的重要地位,早已無庸置疑。
一九八九年,當它奪下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金獅獎,成為第一部在三大影展獲得首獎的台灣電影後,對政府政策、電影工業、媒體與觀眾,都產生了不可輕忽的影響。再者,影片描述到日本戰敗撤離、以及國民黨掌權時期的「二二八事件」,這些在過去不可討論的政治、歷史禁忌,注定要碰撞當時電檢的敏感神經,也成了另一個足以引爆台灣各界爭論的要素。
果然,《悲情城市》推出後,「載譽歸國」加上「二二八」,吸引了無數民眾爭賭,創下當時台灣電影史上的最高票房紀錄(根據一九九○年中華民國電影年鑑公布的資料,《悲情城市》的台北票房「約」是六千六百萬台幣,全台票房通常加倍計算)。且影響力無遠弗屆:以文學為例,編劇朱天文、吳念真寫的《悲情城市》電影書(包含劇本與拍攝記錄)躍登暢銷書排行榜冠軍;戲劇界則有「屏風表演班」向觀眾徵求年度十大新聞事件以編演新戲《民國七十八年備忘錄》,其中「《悲情城市》獲得金獅獎」也赫然在列;同年,「社會大學文教基金會」評選「年度十大企劃案」,《悲情城市》也被選入。更有甚者,是《悲情城市》成了當年選舉最常出現的文宣用語,例如分屬對立政黨的台北市議員候選人周柏雅和陳學聖都用「悲情城市」這個名字作文宣;在高雄甚至有將反對黨聞人余登發的屍首照片印製成「一九八九悲情城市」傳單挨家挨戶散發而引起爭議;台東縣立委候選人陳清泉乾脆在政見發表會場架起銀幕請民眾免費看《悲情城市》;都是當年引人側目的政治、社會新聞。就連它的拍攝地點——九份、金瓜石,也從原本蕭條過氣的小鎮,搖身變成熱門的觀光勝地。
既然在社會各界引發了如此強大的效應,對於《悲情城市》的為文探討,也理所當然「百家爭鳴」,除了以電影美學理論來閱讀外,援用結構、解構、馬克斯主義、女性主義、新殖民論述等批評理論來檢視《悲情城市》的,也大有人在。亦即《悲情城市》的問世,也刺激了台灣評論方法、論述戰場的多元與轉移。
雖然《悲情城市》贏得威尼斯金獅獎,也為侯孝賢掙得第一座金馬獎最佳導演,但當年關錦鵬導演的《三個女人的故事》(港名:《人在紐約》)卻在金馬獎頒獎典禮上贏得八項大獎,遠勝《悲情城市》的兩座;就連《悲情城市》這兩座最佳導演與最佳男主角(陳松勇)也只是「險勝」過關。同樣,由品味向來較為保守的「中國影評人協會」票選的「年度十大國片」,也是《三個女人的故事》名列《悲情城市》之前。有趣的是,關錦鵬卻在金馬獎過後,於輔仁大學舉辦的座談會出人意表地認為《悲情城市》的成就遠高過《三個女人的故事》,當他在頒獎典禮看著工作夥伴接連上去領獎時,心中頗覺不安。當年金馬影展也舉辦了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國際競賽,當時應邀來台的幾位國際影評人或策展人,也對《悲情城市》在金馬獎的落敗提出不滿及批評的意見。
儘管如此,《悲情城市》對台灣電影無論在國內或在國際的影響都是史無前例的。它開啟了台灣電影界對台灣歷史、尤其「白色恐怖」回顧與反省的序幕(之後陸續有王童《香蕉天堂》、楊德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萬仁《超級大國民》、徐小明《去年冬天》、林正盛《天馬茶房》面世),也吸引了國際影壇對台灣電影更多的注目,讓台灣電影在九○年代成為國際影展的寵兒(李安的《喜宴》獲一九九三年柏林影展金熊獎、蔡明亮的《愛情萬歲》獲一九九四年威尼斯影展金獅獎)。而鮮為人知的是侯孝賢在本片大獲成功後,自掏腰包讓杜篤之等主要技術人員增購器材與培養人才,對台灣電影技術升級(尤其是同步錄音技術),貢獻厥偉。
即使回到電影藝術層面,《悲情城市》的不同凡響,也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它選擇了一個獨特的歷史敘事觀點,男主角(梁朝偉飾)是個啞巴,旁敘者則是女性(辛樹芬飾),它既然跟英雄史詩劃清了界限,遂從一個家庭不同成員的命運變遷,反映人在歷史洪流裡的掙扎。影片彷彿是從混亂的現實抽取出零碎的片段,然而這些片段透過有力的掌控,讓場景、人物和構圖空間,建立起複雜的意涵。譬如片頭這個家庭的大哥文雄(陳松勇飾)燒香拜拜時,收音機傳來日本戰敗撤退的消息,同時他的私生子誕生了,房間裡原本未亮的燈泡也在此時因供電而發光。亦即這雖然是電影的開場,卻非故事的開端,我們在這場戲完成時,除了瞭解到這個男人在家庭的地位、時代的背景外,也悠悠讀出台灣相較於大陸如同庶子般的地位,以及未來的希望也在明滅之間,埋下了伏筆。到了影片結尾,這個家庭只剩年老的、失能的(瘋癲的三子)和還沒長大的小孩一塊吃飯,表面上侯孝賢對台灣近代最悲愴的一段時間好像無動於衷,其實透過景框裡侷迫的構圖與沈寥的環境,便能感受到歷史施展在這個家庭身上的沈重力道。而他著名的長鏡頭美學,更在主角夫婦餵食嬰兒、無意收到兄長等社會主義青年被就地正法的通知,利用成人的愕然,對比尚不懂世事的嬰孩無知玩鬧,形成內在情緒壯闊波瀾的起伏。片中的珠機華采,俯拾皆是。
在台灣,為一部電影出書,通常是配合影片上映的同步宣傳。本書卻在《悲情城市》問世二十年後才付梓,既肯定了影片的影史地位,也標示了寫作企圖的高度。張靚蓓不僅具備豐富的媒體經驗,還是當年親赴威尼斯報導的歷史見證者,但更難得的是她具備的電影知識與熱情,這在訪談李安的《十年一覺電影夢》和《不見不散:蔡明亮與李康生》,皆可得見。《悲情城市》雖然只是一部電影,但要找齊早已各分東西的眾人,並且讓他們願意開誠布公,若非張靚蓓的專業和誠懇,恐怕都只是空中樓閣。這段漫長的採訪之旅,結果必定是日後影史研究的重要資料。對關心台灣電影的讀者而言,每個受訪者的精彩,以及他們在觀點上的異同,則交織出多元的層次,而不再只是一家之言。記憶的滌選,在此形成許多彎道,在《悲情城市》為台灣影史立下重要里程碑的主流上,增添了新航道,再看風景感受也大異於往。
當年《悲情城市》上映時,我是個大一準備升大二的學生,頂多是個影迷。所以當「田園城市」和張靚蓓邀我為本書作序時,立刻謙卑地婉拒,畢竟比我有資格發言的前輩大有人在。現在同意厚著臉皮提筆,除了盛情難卻,主要是他們再度說服我的理由之一,是這本書呈現的多是二十年前參與本片的影人們的口述記憶,而前面寫的這些拉拉雜雜的文字,應該可以作為一個外圍影迷深受《悲情城市》以及這些影人們啟發、影響的證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