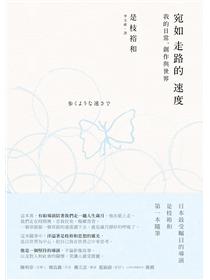名人推薦:
一座碎裂 暗影 瘋狂 鬼魂與春宮 家族藤蔓之巨塔 的孤獨建築史
駱以軍
離開長壽街的我後來的一生好像是沒有未來的,一如我也沒有家而只有旅館的命,被老家族放逐之後就注定只能飄泊在這種永遠羅漢腳式絕子絕孫的身世裡,從一個爛旅館換到另一個更爛的旅館地活下去。從過去回到更過去,而未來始終沒有來。—〈寶島部。尾篇。清明。〉
我想最有耐性的讀者,也很難不被這龐大小說的洪荒漫漶、幻夢亂竄的維度擊垮─如比太陽系大一萬倍的古老星系瞬脹又塌縮的,整團灰塵雲,閃爆後向無垠黑幕噴散而去的粒子幽靈,一種妖魔之子不僅要陳述「我這一族瑰怖駭麗的死亡史詩」,而是要演繹「死亡」這件事在文字佈展這件事的吞噬性與黑洞意象。每一串字鍊如此充滿顏色、強光暗影、腥臭芬芳,在書頁噴吐而出時,又形成一條往昔之街、古老廳堂、家族老人不同面孔陳說自己古怪悲慘滑稽身世的嘴角特寫……。但又在下一個敘事團塊,下一個妖怪夢境,夢境中再開啟的另一個夢中夢,或敘事者轉述另一個不在場角色之身世時,這不在場人物又轉述了另一個無關之人的大段獨白……這一切從故事核心不斷翻湧、不斷暴脹而出撐破並吞食原本故事母胎之子宮的「妖怪孩子」(或某種編印永劫回歸之基因密碼之,故事的病毒?)像一場超乎想像的時空規模的,「不存在裝置藝術」。
他想把我們正活在其中的這個世界,佈置成一個巨大的「鬼故事」?
一個在疲憊、色慾淌流、刻舟求劍的城市街道漫遊記憶,電影情節轉述,像布魯諾‧舒茲〈肉桂色鋪子〉裡那些燈泡暗影下蠟白臉孔老掌櫃們龐大話術回憶的舊昔歷史碎骸……在這小說家偏執又繁華簇放的手指撥轉的,一個魔術方塊。像卡爾維諾《命運交織的旅館》那由一副塔羅牌任意搓洗、疊蓋、亂陣……而形成的故事網羅故事迷陣,對小說家言,不同時代(中世紀、文藝復興、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的小說話語,決定了這些牌陣的複雜輪廓、維度,甚至立體離開一個平面的幻覺,「故事」(在二十一世紀的此刻,百感交集要鋪展開的,「關於寶島」的一個夢裡尋夢,百年孤寂,在父輩幻想啟程往繁華文明意義上,牛奶與蜂蜜之迦南地,而終破滅,成為鬼域的故事)的暴脹、灑豆成兵、漫天仙佛羅剎,夢境互相吞食,掘祖墳拾骨卻幻變成滿臉淫慾的日本美少女,或尤里西斯的隻身大冒險卻走著走著走進北野武的公路電影景框裡了。這個《寶島大旅社》的故事,大到、漫漫無盡頭到,像杜子春的一生(很多人的很多生)那樣過完了,所有的恐怖、親人惡死、被遺棄、所有的痛都被硬撐開眼皮經驗過了,最終只是爐塌丹毀,胸腔像破洞風琴張動嘴巴,不為了號哭、吁嘆、古典悲劇的恐怖與哀憫,而是為了「如何」,如何全面啟動的說這個「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一部小說家的願力想將一切顛倒夢想、一切有情無情同圓種智、一切劫毀與生滅全吞納其中的故事「大爆炸」。那是意圖將「寶島」帶進二十一世紀世界景觀的「摩訶婆羅多」化的說故事欲力,那樣大的時空圖景,那樣天河撩亂的家族怪物詩篇,那樣嘈嘈繁錯的怨念耳語,那像宮崎駿《風之谷》裡的超級巨怪機器人,巍然站起,同時各部位崩塌著、融化著,但同時又筋肉骨架繼續在這毀滅煙塵中恐怖的增長著。
那恰像是台灣,這個島國的,「現代文明繁華夢」的一個隱喻。
這或許是個祕密:作為同代人,然我是所謂「一九四九年集體大遷移至台灣所謂外省人」之第二代;作為遷移者的兒子,「遷移」的故事就是父親他一個人的故事。「多桑的客廳」(楊澤在為石黑一雄《浮世畫家》一書之序文所說)─作為童濛渾沌將來要開展爆炸成對整個人世之體驗的,最初模型(教養或傷害的黑盒子),我在慢慢成人的過程,難免遇到像顏忠賢這樣的「有身世的本省哥們」:而欣羨而嫉妒。
譬如說:顏的父親,是台灣當年「太子龍企業」的家族老大(也就是說,我那個年代全台灣的小學生中學生,都是穿他們家作的制服衣褲),他家當年在彰化市中心有一家獨棟戲院,有一間「寶島大旅社」。這絕對可以寫一個「台灣布商在台中彰化地區興衰史」的專書,或他們的「文明小史」:日劇時期或國民政府時期,他們殷厚的實力(如他在〈長壽街〉一章所描寫),第二代男的栽培成醫生或建築師,女的或赴歐洲學音樂或赴日本學家政,儲備當醫生娘。這樣的家族網絡,追時髦玩車(或重機車)養狗、養鳥,玩房子,聽古典樂,收集真品武士刀,讀日本書吸收科學新知或玩女人;女人家則將家清一色佈置成「委托行」淘貨的日式洋裝、皮包、盥洗劑、電器。這後面的政商風暴和前景浮世繪般的「栩栩如生」的「文明夢」,一種從小活在比王複雜十倍百倍的家族人際結構裡,拜祖先牌位,喪葬的習俗,甚至顏從小學就像日本小學生會到大街最大的文具店,著迷觀看某支他想收藏的西華或派克牌鋼筆(在我可能還偷爸媽錢到永和柑仔店買蘆筍汁或五角抽那些垃圾塑膠玩具的同齡時光)。那是一個台灣布商的《百年孤寂》或《天香》的大故事資產。像建立在台灣彰化版本的《陶庵夢憶》,充滿物質史的可以追問老輩人的《追憶逝水年華》。他不像陳雪的夜市擺攤場景仔瘋狂愛戀的窮困少女時光;也不像胡淑雯的「泊車老爸」因此成為城市混跡但直面畸零人、瘋子、妓女、變性人、性成癮症女孩、嗑藥少年的一個憎恨「不義政權」的「女兒」。或童偉格的死靈魂充滿,父無法言說的枯荒北海岸。
顏忠賢的父親,在「多桑的客廳」,給予這個孩子的「電影排場」,是一個對島外「更現代、更文明」國度(日本、美國、歐洲)豔異且朝上想學習、進入、變成大江所謂的「新人類」。
當然在這個故事裡,如所有的「後來」(《紅樓夢》後四十回,顏本人真正的身世遭遇,或整個八○年代泡沫化後至今的台灣)那一切都像最恐怖驚悚的噩夢,一瞬間被吸進某個暗翳突梯像開玩笑的荒誕漏水孔,一瞬間樓塌了,眼前繁華蒸發消失了,家破人亡了。它變成一部「非要動員像好萊塢製作那樣規格,大批專業人員,不可能製造出這等效果」的,鬼電影。
《寶島大旅社》作為一個關於「建構」的巨觀,似乎必須放在一宇宙空間維度,才得任其四面八方爆脹,即被「我」像卡爾維諾在《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中,最後一章〈繁〉,所舉例:譬如福婁拜晚年最後一部想容納「全部知識」的瘋狂「圖書館抄寫員小說」:《鮑華與貝庫歇》,不斷繁殖,如地毯線織,層層錯縫的一個,駭異的「家族史詛咒的言說」─是的,到後來作為讀者,你未必有辦法像閱讀《百年孤寂》這樣的「邦迪亞家族樹枝串的死亡百科全書」;那樣建立一個「家族史幻覺」(或如《紅樓夢》)─但你會被那「宛若家族史的言說」:低迴、追憶、亂倫的暗影、孩童視角一知半解不確定曾見到的「家族裡說的祕密」,毀滅的遺傳、《基度山恩仇記》式的那個與生殖、與祖先、與典型大家族各房親屬鏈糾葛的仇讎、勢利、耳語八卦、屈辱……所有這一切聲音與憤怒、哭泣與耳語,像無數的太空垃圾,或闖入某一水域數十萬隻足以致命的透明毒水母包圍─一種「家族史故事言說」的「癌」景觀,如果用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癌」,因為突變而基因序列被竄改,使編碼的蛋白質產生畸變。《寶島大旅社》的「家族史故事」,似乎是一種關於這樣的「長恨歌」的刻意突變,腫瘤化、怪物化(像我們那個年代的科幻經典《異形》系列),它變成一種「預期來聽某一個家族故事者,空出來的聽故事房間」被那竄長、暴脹、失控的「神燈巨人」般,或如「地獄變」那壓擠在一起掙扎扭動的各種哀愁怨悔的祖輩鬼魂的核分裂颶風烈焰給撐爆炸碎。
我自己閱讀時,至少第一瞬腦海就調度幾本不同的長篇:
1.魯西迪的《摩爾人最後的嘆息》
2.奧爾嘉‧朵卡萩的《收集夢的剪貼簿》
3.帕慕克的《純真博物館》
4.薩拉馬戈的《修道院紀事》
這是幾種完全不同的長篇小說建築形式。有藤蔓根莖狀的家族史故事幻術;有將夢境筆記小說化然逼近某一離散(或創傷)民族潛意識與民間神話的祕密下水道靈魂髒汙之濾鬚;有以舊昔之物,作為一種「偽時光擺設」,巴洛克式地所有傷逝蜿蛻之物,作為一種班雅明「過去之街櫥窗景觀」的藻井曼陀羅佈陣;另有真正硬底子,知識考古學重現某一歷史時期(中世紀,或十八世紀,或如顏這書中蓋寶島大旅社的日據時期台灣),帝國文明妄夢,在小說中「真正蓋一座夢幻建築」的當時建築學的「專家話語」;知識考掘學;泉漳不同頂尖師傅的風格揉雜或傳說禁忌;或日本帝國的天才建築師在這「國境之南」實驗夢幻中的「瞻仰歐洲」的脫亞入歐的「建築史博物館實驗室」。
這部分我作為讀者,確實被他那卡卡西老師式的「萬花筒寫輪眼」的「建築師瘋狂之夢」─一座台灣二十世紀心靈史的巴別塔通天塔,從各處輔臂、塔樓、肋拱、鑲嵌影玻璃花窗、柱頭,無一處細節不下了這種「寫輪眼咒術」,一種奇異的「瞳孔收束」(因為要專注的這個家族的崩壞和哀慟太巨大了)同時又擴散(因為說故事的這個聲音漫灑出太紛繁絢麗的,「漫天紛飛的銀杏葉片」,一種孤獨個體和這幅畫面中其他所有同時旋轉、墜落的葉片,之間的「命運交織」:獨語、旁白、夢境、一個空間的繁殖─不論是旅館裡的一台電視中正播出A片的劇場素描;一條班雅明式街景的佈置;日本的寺院庭園或色情秀場的明暗、濃淡、光陰、過度飽滿或初意枯荒的視覺強迫症;身世的纏藤淹漫;神鬼邊境的幽森漫遊;對一場性愛進入微物之神、感官如科幻太空艙儀表板閃爍潦亂……);因之顏展示的敘事肌肉,是充滿這種「水電工暴力」,他同時從卷軸中魔術般無止境展出那他正構蓋著的鋼骨、水泥、牆磚、玻璃、電線水管、大理石地磚……然同時用巨鎚在砸碎這個「也許就差一點點就蓋好的」,骷髏檀城,或數百隻墮落天使的擠壓肉浮屠、像芥川小說中那個畫師只差將自己最後一個寫真繪入的百鬼圖〈地獄變〉。他砸碎它,或一邊在搭蓋時一邊就悲傷的讓它炸裂。像那一幕最森冷恐怖的,這群失父失母的孤兒們,信了基督教,於是如夢遊般請了人按教會儀式,來到家中神廳,拆除砸毀那些一支一支木籤一個一個祖先名字依次進駐的神主牌,那一刻,這一支族人的命運,在這樣建築「我父祖們已在說不出為什麼的陰鬱、怪物中死光光,留下一座『寶島大旅社』、一座昔日電影院」的強大意志;和用巨鎚敲毀「這座故事的鬼魂不該只是被禁錮在顏麗子和森山,依『日月龍蛇鍾地理』,依森山(日本人)那折衷樣式與現代主義的『他人的夢境棲所』、神明廳、舊花園、裝了『現代』機械又科學的鐘、那些層層纍聚的,失落的文明夢」的瘋狂力量─這樣互扭、悖倫、衝擊、建與拆、懷念與怨恨、古老的招魂與現在所在的(更大的「繁華夢」中百鬼夜行)對兩列火車的對撞……到達暴力的最高潮。
關於所謂卡卡西老師的〈萬花筒寫輪眼〉,舉例隨證之。譬如在「旅館部」裡,這個「我」的視覺,同時網羅至少幾個元素:
1.那個篇章裡作為像科幻片場景的性愛閉室劇場的某一間現代旅館(或汽車旅館)像遊樂園般的佈置、設計。
2.那次的男主角和那個像「鶴妻」(其實是不倫敗德的「人妻」)的A片式昆蟲學式照相寫實技法的性愛奇觀。
3.這段「寄宿於旅館」的時光(或女主角離去後)男主角作的鬼魅怪異之夢。
4.如蒙太奇跳閃在以上不同聲軌之敘事元素之間的,男女主角像《雅克和他的主人》那樣漫無主題的漫聊:童年的傷害、吸毒的經驗、某一次異國旅行的安哲羅普洛斯影片風格的孤寂運鏡回憶,或是因年齡差而這其實還是年輕女孩的「人妻」說起她的青春玩伴那朝生暮死蜉蝣聚落般的、朱天文〈世紀末的華麗〉裡,米亞的後四、五代的新小妖人種的城市人類學式生命輕悲歌。
5.穿插在前四種元素之間的,恰好這旅館房間內那台電視,隨意按鍵跳選不同頻道的某部好萊塢電影或影集(譬如《超異能英雄》、《怪醫豪斯》、《CSI》)或中國大陸電影(譬如《七劍》)。像故障播放器,以一種白痴式記錄片方式紀錄那斬頭去尾的電影情節或時空規則因這樣亂跳而變得時光重瞳、紊亂的一個「當代」。
6.這一章節這間隨機選擇之旅館,周邊的台北街區之地誌學、街道興衰史,或「我」的不同時期城市的記憶沉積化石,而到了「寶島部」,則是像卷軸畫,慢慢工筆素描一個「彰化」、「大佛」、「長壽街」、「曾發生的大水」、「布商興衰史」……
這部分,或是要處理一藤蔓盤錯、樹枝狀家族史故事必然要像照相館;或像一條「另一張清代─日據─國民政府不同時期繪製的地圖」而從祖先之鬼魂中重建的「栩栩如生」的昔日之街─馬奎斯的「馬康多」;《陶庵夢憶》;〈清明上河圖〉;最後,由這些姑婆、姑姑們、死去的父親、母親、姊姊、家庭其他的親戚們的「從不斷累聚之陰影向下望」,像馬賽克小瓷磚拼貼的各人的亂倫、背德、負棄、被詛咒的中邪、惡死、怪病或由盛而驟衰,一小片一小片拼組成一座卡爾維諾的《看不見的城市》。
它其實是艾可的《昨日之島》的魔術,透過一種錯誤的執念,以透鏡折射出一塊時光中或許不曾在的「被隱蔽的存在」,一種敘事的魔術從夢中塌毀之泥爛廢墟裡,硬生生蓋起的「倒影鏡城」,說話的全是鬼,但說話的同時將家族史的金字塔(「人肉浮屠」)全疊塔在這家族最後一個子孫(「我」)身上。像魯佛的《佩德羅‧巴拉莫》。一種鬼之哀歌的巴洛克、壇城、唐卡、亂針刺繡。
至於小說家如何「惡童」那樣將「祖先之歌」變成鬼故事的幻術,也是摺藏暗佈。譬如:在老去的姑姑家,曾經豪奢繁華而如今像鬼宅的時間之屋裡,某個媳婦中魔般瘋狂瞎拚的奢侈名牌:那些GUCCI、LV、香奈兒、昂貴的洋裝、絲質湘繡襯衫、手工緹花長裙、別著蕾絲羽毛的各種淑女圓帽……堆在那死角,「嚴重發霉到鱷魚皮或小羊皮手袋,已然歪歪扭扭地皺如乾菜而塞滿擁擠得不像話的衣裳」……「快轉的成住壞空快轉的人世盛衰的令人難料的極其荒謬」……
譬如:家族所有的人都瘋了,都有難以言喻的罪(曾把神佛吃掉了?),又譬如說,在「寶島部」尾篇〈清明〉裡,夢中一家人一起掃完祖墳回來,「女人們去燒點線香,安放一大堆蒼蠅在拜的時候圍繞來一起吃的牲禮供品,小孩們去壓又黃又紅的一疊疊成行成列的粗糙冥紙墓紙,男人們開始砍雜草甚至長出的樹根樹頭,拜祖先也拜后土,」而後便是在老家天井中吃潤餅:「太多瓷盤中近數十樣的各色講究的顏色鮮豔繁複的菜色:高麗菜、胡蘿蔔、豆芽菜、荷蘭豆、韭菜、芹菜、香菜、青蔥、小蔥、皇帝豆、滸苔、豆乾絲、肉絲、蝦仁、香菇、蛋絲、扁魚酥,還有我從小就最愛的菜市場老店的花生粉」,這時,這個我,突然陷入:
「小時候我都拿捏不住包餅的竅門,要不包太大把餅皮撐破了要不包太小就沒有豐盛的感覺,怎麼包都包不好的沮喪。」
過多繁華眩目的細節,或因「我」,這個家族最後一個回憶者「不會包」,可能歪扭、爆破、塌癟的恐懼,那成為這個巨大「鬼故事」像絲襪裂縫冰涼竄上的「惘惘的威脅」,災疫震搖、尖叫的在夢中不知自己已死的父系母系先祖鬼魂們,被甩出破裂的祖屋,我這時卻正拿著老式相機替這一切塌毀之家族鬼魂們拍大合照。
然後是唐卡佩古畫中鬼王對阿難臨死前的恐嚇,那些「成群半枯骨半腐肉的餓鬼團團圍住了阿難和佛陀」;然後是一部叫《1408》的鬼電影,牆的裂縫滲血出來了,直看大有人從每一個陽台跳下去,這人被自己失愛的往日憾悔所崇纏,最後問:
「那旅館到底想要我的什麼?」
即使在這一章趨近尾聲,把祖先鬼魂的靜置時光,哭泣與耳語,像潤餅薄皮爆裂露出鮮豔駭麗的「妖怪化」恐怖片大場景。作為收煞、鎮魂、儀式的引渡或安慰,這些台灣古老儀式的如禮巡行,卻仍被這個「妖怪小孩」從夢境的換日線,移形換影到迷路的現代性機場出境大廳,新宿車站JR線入口處,日本(是的,「寶島」最核心塌落的「現代文明春夢」,那終究只是轉生不了成不了人形的「鬼電影」之夢綺地),老孤兒一路踟躕流浪在兩年伎町、未來科幻感的膠囊式旅館,這個將祖先牌位砸碎,從祖先殘恨遺憾夢境廢墟重起高樓蓋出「寶島大旅社」,卻一梁一柱、長廊房間照著設計圖蓋成了一塊域中、亡魂渡舟的「台灣文明春夢」的尤里西斯,通往那夢中國度的浮橋棧道:
「醒來之後,離開之前整理桌前,所以仔細看看那經理給的古怪小籃子裡,有一個保險套和一個手淫用內在濕海綿的紙圓筒,美少女整群穿學生服,一張護貝的使用者,寫著:『本人確定,始未了!』安心,環境,守各樣之會員登錄,必要。東京都條例之知。全黑垃圾桶很素,像工業用的,很大正方形的口正下方,寫著Would u like to review what your life should be?」
最後,在濕紙巾上我第一次注意到旁邊有二十四的數字而印著的店名很大很明顯的出現,在正中央就出現了這兩個字「寶島」。
我覺得他的《寶島大旅社》讓我的《西夏旅館》變成一種夢境的過渡型態,這不是自謙,同樣用這種旅館的概念、想像,我覺得遷移者後裔、暗喻,我可能是一種外省第二代,他其實是一條暴漲的溪河,他是一個流放串逃的運動感。可是這一塊台灣一直都沒有,包括揚澤曾經講過父親輩的故事,或是聽楊凱麟說的一些本省籍的長輩他們父親的那一輩,這種難以言喻的彆扭凹槽,就是它有一種很奇怪的視野,你會覺得人類文明的泛泛光芒好像一間鬼屋一樣,像是賣火柴的小女孩把那三根火柴點亮,好像台灣的歷史只給這批台灣曾經的士紳階級或是比較上層,或是比較有創造性的,或是知識菁英,好像只給他們三根火柴的機會,可是當這火柴熄滅後,一切只能是〈迷失於歡樂屋〉裡的踟躕和夢遊了。這在長篇小說本來就牽動著他表述的形式。《寶島大旅社》恰好是把一種文明的過渡,過熟,糜爛的沉澱物,有很多種可以描述的裝置。包括裡面有很多可能都是不可靠的語言,包括他想要去玩恐怖分子式的爆炸。他有能力去把這種過熟的文明,你會覺得台灣老一輩鬼影幢幢的惱人夜裡的密室裡面,他又可以用他的書寫去建構一個靜止的繁複的鑿井建築的,好像是腸子裡的絨毛那樣的一個祖先的驚嚇之夢。他把整個祖先之夢或是家族史,命運交織的祖先的祖靈之屋,他把它布置成一部恐怖片、鬼電影、春宮秀,這是一本非常暴力書寫的驅動。我前面講說他在性的操作上,他進不了城,進不了愛,進不了他人的妻的子宮,在城市的地誌學上,他是躲在浮光掠影假的標的建築這些汽車旅館裡面,就像他之前在印刻出過的一本《殘念》,很奇怪的一種色情小說的書寫的一個昆蟲學式,或是機械年代的一種偏執在寫性,那種性其實是沒感情的,是一次一次的進入性,他在他這本「台北色情故事」的旅館裡,每一個章節是他跟這個美少女在台北不同的motel,台北的motel在這個空間劇場裡來說,本身都是魔幻的,都是童話城堡也可能是一個鬼屋,陳雪之前也寫過這方面的考察。而顏忠賢本身就是學建築的,他在這本「台北色情故事」裡有一個非常奇怪的,很像一個A片教學影片,就是這個「我」本身是一個性猛男、性皇帝,每次約會帶著這個充氣娃娃般的下一代女孩,這是不倫的,到這個台北建築裡是多餘出來的不存在的空間,描述的一個即興的約定的色情場所,然後他鉅細靡遺寫這些motel裡面的裝潢,很low的很山寨的,每次約會都是一個老師對徒弟的教學,就是他在對這個少女性啟蒙,他說今天我們的主題是網襪,是口交,或是邊看著旅館裡的A片,這是一個色情技術的展示,這在台灣的小說書寫裡,就是舞鶴和陳雪,陳雪是女性寫性已經寫到非常妖魔非常恐怖,另一個舞鶴是寫性的教父,但我覺得顏忠賢是另開出一個他自己的路線。後來他把人妻、旅館這塊,變成一種很奇怪的,做為一種顏忠賢時代幻滅掉的,台灣彰化布商的,寶島大旅社的,太子龍的這樣一個曾經的貴族滅掉了。滅掉了以後,做為一個已經失去線索的後裔,他如何要去追尋那個某一種精神性的,台灣人曾經在那個年代那個時間點跟白先勇、跟王文興、跟朱天文朱天心、跟張大春想要的不一樣的跨過換日線進入到現代進入到高度文明,從日本人這邊對歐洲的欣羨,一個帝國夢,一個華麗的未來科幻場面。但這個小說當它有了「少女」這一塊布置在裡面的時候,這一塊變成一個非常恐怖悲傷的隱喻。第一個女孩是亂倫的,是他人的,她是永遠不能著床的空的子宮;第二個,在尬這個女孩的場合,這些汽車旅館全都是台灣人自己做出來對世界錯誤想像的滑稽可笑的山寨版歐洲、山寨版義大利、山寨版羅浮宮,或是山寨版的日本和室、山寨版的中國唐風,他在這樣一個偽空間裡面尬這個不倫的別人的女人,因為永遠不可能著床,所以他變成一種德希達所說當這個詞的符號、話語的、形上的永遠的核心的指射被抽空掉以後,它永遠只是一些符號表面的狂歡亂舞,化裝舞會。這就是顏忠賢技術的祕密,就是性變成了他小說裡一種強迫症式的、科幻小說式的一種A片,一種有點怪異的,這東西其實我們都有在看日本的《全員逃走中》,或是那種誰都不准笑的,非常奇怪、很變態的,控制力非常強的大規格製作,可是他其實只是把一些人類本來古典的行為變成一個科幻化。這部分是這大小說其中反覆出現的一塊,好,他又繼續長,開始挖墳墓,去講那個一層一層的暗影下去挖的家族故事,這一塊其實是典型的家族式書寫,這是另外一本。你看這裡面我現在已經講了這本,還有那個家族史的「紅樓夢」,有色情的虛空,科幻的霧濛,可是問題是他又在這一棟一棟不同的台北的這些motel旅館再把章節加上去,變成一種朱天心的《古都》,變成色情版本,他把《古都》色情化,這些旅館可能有些在圓山、在大稻埕、在南京西路、兄弟大飯店、中山北路,不同的區,變成區中之區,刻舟求劍的一個基地,色情的場所,發展他的台北地誌學。
小說如果做為一種理解世界的方法論,本來就是各種不同層次的知識跟話語像編織地毯那樣編在一起,可是我覺得顏忠賢不是這樣,也有,可是他比較像是一種海德格的,存在的繁(煩),就是會一直暴脹,根本就是個妖怪了,他的查克拉一直湧出來根本就是噩夢,然後你必須很耐心再看第二遍第三遍才會發現,比起我跟陳雪寫小說的,他更是建築師,是搞裝置的,每一個層疊建築像是《越獄風雲》裡那個刺青在自己身體上的建築管線,所有的空間都是他設計的。
他造出一個非常恐怖的,你以為這個人瘋掉了,失控了,核爆炸,像癌細胞一樣不斷繁殖擴散,他的這些看起來規格過大的核燃料般的怨念,性的書寫,瘋癲,他很多時候的描述方式不像是《紅樓夢》那樣古典的場域在演,也不是張愛玲式的勾心鬥角,他全部是姑婆講了什麼姊姊講了什麼,你記不記得當時講了什麼,可是他回憶的大的段落裡面又會接著出現大量電影,然後這些電影本身都是科幻片。我覺得現在投注在台灣純文學小說的評論話語,其實像是一個歲月靜好的封閉的話語世界,這個話語世界其實有一個很龐大的脈絡,比如從五四過來,比如台灣這幾年是從台灣的家族史,從女性書寫,同志書寫,情慾書寫,城市空間書寫,大概就這些。但這些年以我們這群朋友來說,可能我跟陳雪是比較純質的附著在小說語言地表上在寫小說的人,可是顏忠賢跟成英姝是各自在三十幾歲時候有在權力的世界泅泳過,又完全撤退變廢了的。他們不是想像的。陳雪說我們很會寫個人生命史、個人的瘋狂,聚焦在某一個父親的瘋狂,母親的妖怪,我被遺棄時刻,我們比較會處理這種比較聚焦的運動裡。可是顏忠賢們曾同時有在大的權力世界打過滾,然後他們有對當代大的、最流行最時尚的不管服裝還是影評裝置藝術,他是用這樣未來學或是科幻材質來偽造這個棧道進入到《寶島大旅社》。顏忠賢是一個在書寫上更奇怪暴力的恐怖組織,他假裝成這個通往感傷的、被遺棄的,其實全部都在這個繁,那個癌細胞分裂把你的閱讀之眼撐爆,我自己在看的時候也常覺得受不了了,可不可以不要看(笑)。但其實在裡面有一些在台灣已經關閉起來的,可是在西方是非常羅蘭‧巴特式的浮游聚落,對於感官跟表象快速的朝生暮死,關於美學關於裝置藝術的,一種奇怪的狀態。他說他在紐約遇到中國大陸十幾年前的藝術家,用貨櫃去買大陸一胎化時偷打掉的幾百個或是上千個嬰孩的屍體,變成他的一種裝置藝術。在這個世界上可能我們各自有各自的妖術幻術在文體上的講究,但他很奇怪,我覺得他在閱讀的時候很容易會讓讀者產生一種很痛苦的核汙染的傷害性,又有一種疾病的隱喻的癌細胞式的凶猛串長,但他又帶有這種好萊塢最新最時尚最奇怪的空間概念全部在他布置出來的空間。
在他想描述祖先發生的《紅樓夢》故事的時候,他是透過夢境,當他最後一路在找尋文明的起點的時候,不管是傷害的起點還是宇宙大爆炸的起點,最初的那個啟動原始碼,最開始的時刻是什麼?他透過這個纏線交錯的情結,最後追逐到日本東京,我們最後看到的是一場非常可怕華麗的色情秀,一場非常漂亮的煙火。他一方面寫祖先的肉身浮屠,另一方面也寫極限的女體的高度的未來感高度的科幻變化高度的現代性技術進去控制的色情的一場春宮秀。所以這一本書其實可以當作一個非常奇怪的,像我以前寫《我未來次子關於我的回憶》的時間上的謬論,這是一本寫給未來的東京夢華錄,或是寫給未來的滅絕史。他好像是直接進入到鬼片的遊樂園,一定要彈一下手指才會進入到一個散會的語言,這個語言的城堡才會忽然變成一個嚴密的祕密之陣,但如果你不願意去彈一下手指……就像那部講魔術師的極致的《出神入化》,它就是把幾種魔術的概念瞬間擠在一起,可是那個魔術是你得要願意去承受就像對性的想像,奇觀妄想,對於台北在我們現在已知的台北城之上,還可以忍受再蓋一百座不存在的城市,對歷史也是對夢境也是,就是你願意讓你詞的敏感帶去開發爆炸,你進入到顏忠賢這本小說就會整個全面啟動。
降靈會
陳雪
看了一輩子的電影,卻從來沒離開過電影院。如今那電影院倒掉了,一如我那敗掉了的家……我也才開始切身式地切入我人生真正的要害。我的小時候的線索再怎麼用力地找,也還沒足以完成這個家的故事的血肉。因為……那畢竟只是引信。甚至,一如,祭品拜光,天葬場屍骨都切得更碎讓兀鷹吃得更乾淨……
有一兩年的時間,我們這群小說家朋友的酒吧夜談話題總圍繞著「父親」,圍繞著家族祕密,那像是吹熄蠟燭前最後光影搖晃的醉夜時刻,有人咒語般低訴著生命裡某一段「納悶」的時光,以像是傾訴祕密,又像是提出疑惑般的聲調低語著,「我的父親如何如何」,某一段遺落的「傷害」或「困惑」的時刻,凝固在意識底層直到這些如層層剝洋蔥的說故事之夜,杯中的酒精或咖啡已經喝完,腦子都被故事餵得飽足酣暢,顏忠賢以一貫低沉的嗓音說著:「我們家族在彰化是做布的,以前學生制服的太子龍有沒有,就是我們做的……家族事業很龐大,我父親開了一家戲院……我們親戚開了一家『寶島大旅社』……」
那是二○○八年。
這些年他一直在寫,難以想像八十萬字的長篇小說顏忠賢是靠著iPad與iPhone點點滴滴完成的。一般人拿來玩臉書,傳Line,自拍打卡哈拉交友的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卻成為他完成古老工匠技藝的修煉場,他真的以手指在手機的觸控螢幕上一有空就寫筆記,待有更完整時間時,在平板電腦上大塊大塊剪貼,修改,進行結構的整理,幾千個檔案如磚石瓦片一塊塊建構他的《寶島大旅社》。
在我們最初相識時,他總是用紙筆寫筆記,寫日記,會用相機拍下筆記本的內容以電子郵件傳給我們,非常不可思議的照片,一張一張都是草稿,他的信寫來也特別長,詩一樣的文字,都是文章等級的內容。那時他的小說完稿得先請打字行幫忙整理稿子,再列印出來細修,既不是完全靠手稿寫作,也非我這種很早就開始用電腦寫作的人,我在本文開頭即點明他的書寫方式之進程,是因為對我而言,工具與形式都是改變顏忠賢的小說結構與內容的重要關鍵。
他的小說是龐大又傾頹的現代建築,是在遼闊的廢墟建構起來的「裝置藝術」,是有著最先進外殼卻又裝備著千年幽靈的「夢中之夢」。
他總是在寫,我可以想像,也親眼見識過,他幾乎無時無刻,無分場所(等公車,計程車上,電影院裡,剛拔罐完,瑜伽教室結束倒立出門,百貨公司美食街,咖啡館,二十四小時泡沫紅茶,無所不在的,無處不書寫),他醒來就寫,一有空就寫,這些點滴細碎的書寫曠日廢時,甚至已經滲透進他的夢境,寶島大旅社啟動的另一個「駭人書寫」是在夢境裡推演的,小說家的自動書寫,強迫書寫,進入下意識的夢境裡,使他大量作夢,我猜想,起初是為記錄下夢的內容,而夢境卻改變了小說,也改變了家族史,那些已經逝去,已然傾頹,已經消失的親人、建築、事業,那些「亡魂」、「冤親債主」,那些念茲在茲卻無從對證的「當時」,在他用強大的小說意志改造過的心靈攝像中,產生了「恐怖的力量」─夢。夢成為除了虛構文字以外另一層虛構的方式,他在夢裡追尋,追問,與死者對話,與亡靈共舞,他夢了再夢,將夢境翻譯成小說語言時,夢又改變了現實,每一層的推進都更進逼到這個家族隱密不為人知,無法證實的祕密核心。
大多數的小說家「寫夢」,而顏忠賢卻是用夢來寫小說,我不確知那要經過什麼樣繁複的手續,或者練習,要使自己處在怎樣的狀態裡,才能一直大量地作夢,越進入書寫《寶島大旅社》的後期,小說裡盤根錯節的夢境,對夢境鉅細靡遺的描述,盤據了整個小說的肌理,那非常近似一種起乩,或「降靈術」,顏忠賢讓自己像波赫士短篇小說〈環墟〉那個作夢者,齋戒沐浴,全心全意,像要誕生一個孩子那樣去夢,更有甚者,他將生命大多數時光與夢置換,醒著的時光裡,他旅行,教書,練瑜伽,到處去看病,而做著這些事的同時,他無時無刻不在記錄著他那關於家族的「夢」,就像我們寫長篇小說時那樣,只是我們靠的是虛構,而他則是「造夢」。
關於夢境的描述吞吃了想像中應該存在的「家族史」,因為夢的結構使得這部描述百年家族的小說,充滿了瘋狂、難以控制、層層疊疊、彎曲迴繞的夢之迷宮,彷彿他越是努力想要告訴我們這個家族發生了什麼事,小說的路徑就會更加迂迴地進入「與現實相抗的夢境」,好像他努力挖掘的不是已經發生的「家族歷史」,而是可以改變的「家族命運」,真實藏身於層層疊疊的夢境裡,呼之欲出,卻又不得說破,顏忠賢羅列、或架設一座巨大的迷宮,為的不是找出「我為什麼變成這樣子」的真相,而是要讓自己永遠停留在「我們都已經變成這樣子了」的噩夢裡。
用荒誕的噩夢來對抗真實的荒謬,用比可以想像得還要虛幻的恐怖,來對抗已經是既成事實的恐怖,「我是這樣的存在」,「那是一個如此的家族」,曾經輝煌的,燦爛的,未來,全都提早凋萎成一個搖搖欲墜的廢墟,如夢幻泡影,一戳即破。
然而寫作是更大的虛妄,必須用更繁複厚實的文字築起長城,排列出陣行,讓他日日夜夜隨時可以進入,可以隨身攜帶,可以隨時改寫。小說或人生亦然。
閱讀《寶島大旅社》的過程猶如參加一場連續七天七夜的降靈會,是那種一旦進入會使你猶如「中魔」般染上他的文字腔調,會使你頻頻作夢,甚至可能噩夢連連地夢出你這生最瑰麗多彩,也最魔幻怪誕的夢,甚或者你無法分清這是你的夢,或者你只是進入了「顏忠賢的夢」,你無法分辨這是生者之言,或是死者之聲,他的小說擺出的陣是你可能進入不了,但一旦進入也難以脫逃的。
在閱讀寶島,或寶島誕生之前,作為顏忠賢的好友與寫作同輩的我,對於他此前的創作,無論是小說,或他的各種最前衛的裝置藝術,印象總是有揮之不去的「鬼影幢幢」,總像是刻意要「召喚」、「勾引」、「沾染」邪靈,總是瀰漫死亡與陰間氣息,我一直納悶他這種與「死者糾纏」的美學所從何來,直到《寶島大旅社》的轟然問世。直到我進入了他的「陣式」。
為何這般「自暴自棄」、「跟自己過不去」甚至「找事」地哪有問題偏往哪處去,總是在跟危險挑釁,總是與禁忌共舞,穿得像個彩衣僧侶,活得像個魔術師,顏忠賢是我所見過的人最不忌諱,甚至刻意召喚所謂的「出事」、「卡到」、「壞掉了」等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陰森」、「黑暗」、「古怪」,但在這些看似陰暗,怪異,恐怖,逆倫的外殼下,他又是我見過青壯年一輩禮數最周到,待人最溫柔的,他甚至是拘謹地,某種必須要用力衝撞才能撞破的「教養」、「人格養成」早在他童年時或許已經建立,這些也都是我在他蓋寶島大旅社的過程裡發現的。
從下筆至今,四、五年過去,顏忠賢真的把寶島大旅社蓋起來了。八十萬字的長篇,是他做過最大型的「裝置藝術」。
但我總覺得其實更早,早在他以老天使的姿態,以紐約MOMA美術館駐館藝術家、耶路撒冷駐市藝術家的身分,以他的軟建築,明信片,廢墟畫老虎,海邊燒王船,勾毛線大展覽,他的作品一直瀰漫著未來感,帶著宇宙觀,像失去動力的人造衛星,像被外星人遺棄的高科技建物,其驅動程式卻時常是有某種「最古老的」記憶與技藝,我想,他早早就在為了建造寶島大旅社而做準備了,那些貌似瀆神、不信邪,或是「問邪」的舉動,有著最哀傷與動人的企圖,如一次西藏之旅他與朋友刻意長途跋涉去尋找一處天葬場,那種越深入越毛卻害怕就越走進的旅行方式,正如他的生活(或其實沒有生活,人生已經被作品盤根錯節地占據),華麗而充滿自找的麻煩,孤寂卻又非如此不可的擁擠,這些「壞掉人生」,我本以為顏忠賢會以一本大長篇從曾曾祖問起:「我們這個家族是怎麼了?」使我們成為這樣子的核心災難是什麼?但最後他並不是觀落陰把整個故事說出來,而是讓這個家族故事以一層跌進一層的夢,用瘋狂,賦格,變奏,使之從過去被移植到現在,甚至是未來,一次一次地「再生」,讓這些老人們在事情尚未發生之初,在「生命崩壞之前」,以一千零一夜的夢,繼續活著。
《寶島大旅社》寫的不是救贖,亦不是再現,他創造了一個因為虛幻而再也不會消失的建物,讓那些鬼魂無法離開,災難雖然沒有停止,幸福卻可能再來,他曾執拗逃開,卻又時時企圖使之團聚的親族,降靈會裡,那些已經成為亡靈的,以及背負著遺憾之痛苦的生者,在還會一直進行下去的夢中,生者不滅,死者永生,他們終於聚集在一起了。
寶島形上學與旅社的時間綿延
楊凱麟
寶島大旅社同時是過去、現在與未來,它已經無可挽回地傾頹煙滅崩為齎粉、它即將一瓦一柱如影片倒帶筋脈逆轉地飛旋落成、它正在淫邪綺麗剎那即永恆的夢中夢洶洶翻滾而出。寶島大旅社同時是時間中的一切,是六道眾生因果生死的永恆輪迴。在此,真實比夢更迷幻,夢比真實更逼真。
寶島大旅社正在/即將/已經是台灣三代人的微縮膠捲與亂針刺繡,在這個八十萬字的碎形文字幾何中,書寫成為究極時間動態中的追焦與平移,繁複的語言構成觀看時間的特異之眼。一目重瞳,時間在zoom-in與zoom-out的反覆撥動中以夢的無限形式出現。僅只目光一霎之間,寶島即將滅亡正在滅亡且已經滅亡。但這並不是因果業報,它只是一座促使無數夢境生滅輪轉的旅社,然而旅社同時也是台灣的夢與一百年的孤寂。
寶島其實什麼都不是也哪裡都不在,但小說裡卻到處都是寶島。寶島是我們生養蟄居之地,是顏忠賢對於建築、性與死亡的耽溺痴迷與殘酷美學,亦是由綿密文字所全面啟動的小說存有本身。小說書寫就如同一座宇宙等級的自然史博物館,各種奇花異卉飛禽走獸珍饈寶饌以人類學的視野層層疊疊地放進不同時間的疊影之中。已逝的時光宛如剖開的考古學岩盤,在花紋妍麗層次緊緻的「過去層」中,小說家既謹慎又放縱地從事時間飛梭調校與空間軸心挪移的文字學。
書寫首先成為時間的唯物誌異與空間的唯心考古。小說裡有收藏癖的堂姊夫提到牛津人類學博物館的古羅馬梳子展時說:「那博物館在展的是他們的視野,他們對人類學式的人類的更尖銳的收集,用他們收集的從中世紀,文藝復興,巴洛克,到現代來種種在羅馬長出的不同文明不同時代找來的更多對梳子想像的夢幻,和某種因之探究的人類那種種更瘋狂的投入與著迷。」而「梳子,就一如這瘋狂的標本,是一個故事的開始,因為標本被收集的原因,教我們更多為什麼人類這樣想像與理解自己。」在一個又一個如山水卷軸連環展現的夢境中,《寶島大旅社》最終展現的是十八世紀以來的自然史之夢,是逆溯時間之河窮盡個體肉身經驗的當代台灣心靈《小獵犬號之旅》。
這是何以《寶島大旅社》形上學式地迥異於《西夏旅館》。對駱以軍而言,故事職人決戰於故事已發未發間的瞬息萬變,致使一切故事起源創生的宇宙大爆炸變成故事斷死續生的一線生機,小說家必須不斷回返這個原始場景,以文字精確調控的明暗快慢反覆遠眺近觀甚至定格倒帶,以便思考事件的真正意義(而近代小說裡的唯一事件,或許竟是「小說之死」);然而顏忠賢則蒐羅獺祭一切「人類學樣本」作為小說的唯物實證性,書寫最終造就了一切博物館的博物館,小說家因深情於已逝的美好與災難而勉力泅泳於時間風暴中,成為以倒走替代前行的「新天使」(Angelus Novus)。
五年之內,創世紀者駱以軍與啟示錄者顏忠賢皆以過客逆旅的姿態提出長篇小說(《西夏旅館》五十萬字,《寶島大旅社》八十萬字),一個意圖以書寫回返所有開始之前的不可能清明,另一則希冀語言能在一切結束之後總合判教。關鍵字是:旅館/旅社。這或許不只是單純的巧合。
僅存在(或僅消失)於小說裡的長壽街、彰化大佛、八七水災、太子龍學生服、天成飯店、北投溫泉旅館……構成《寶島大旅社》的古老質地,這是小說的唯物實證性或考古學檔案,「一種對『末代』太過眷戀的想念」;顏忠賢並未輕易讓這些元素成為鄉愁與懷舊的藉口,亦未理所當然地敷衍成鄉土文學,寶島大旅社裡的那些「末代」物件、角色與稱謂,那些至今仍光影閃爍著某一獨特時地認識條件的詞與物,就如同林明弘的花布般被注入當代創作的思維,以一種光鮮且不無殘酷的方式在小說中影影綽綽。
主要是,主導《寶島大旅社》的並不是歷時與線性的時間,那些從幽暗生命中汩汩翻滾而出的無數夢境漫漶了時間中原本緊密封印的關係,時間脫節了!不再乖順地由過去經現在進入未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無人稱與虛擬的巨大過去,其不斷地以夢的形式(我的夢、姊姊的夢、朋友的夢、情人的夢、家族的夢……)實現虛構的威力。這或許是隱含在顏忠賢(以及包括駱以軍在內許多當代小說家)作品中最深沉的柏格森主義。
夢的生命衝動(lan vital)與旅社的時間綿延(dure)如同構成小說生命的DNA雙螺旋分子鏈結,在此,過去從不是單純不變的「已逝的現在」,未來亦不僅是依序進場的「還沒來的現在」,「我」成為過去與未來衝擊對撞的重力曲扭之場,「我還沒開始的人生找上門來」而「老家族不可思議地全部都出現」,生命被無政府主義地動員並開始流變為飽含詩意的各種時間切片,崇高與淫猥共同以夢的語言重現。
在《寶島大旅社》中,夢是生命的最終形式,而時間則是在不同時代與不同肉身中連環羽化的夢。或者不如說,夢是比生命更激進的形式,它是生命的赤裸狀態亦是小說的裸命。因為在小說中「你只是在找一個夢中的替身,一個特技演員來演你過去所不敢進入的一如夢或電影裡那極限運動式的極限。」小說述說著夢的語言,因為夢成為大寫時間的最純粹狀態,是存有的極限形式。《寶島大旅社》不僅是夢的極限形式更是極限形式之夢,這就是顏忠賢所實踐的小說技藝。如果對駱以軍而言,故事的入口成為一切故事被述說之前最重要的考究,對顏忠賢來說,夢的入口或界面不是問題,怎麼留在夢裡才是小說的關鍵。
夢之小說或小說之夢宛若巨大的百合花綻放,世界成為共時性的疊影,寶島同時既指涉台灣亦是某一旅社的名字,而旅社則既是小說中一再出現的各種場所又是小說本身。寶島/大旅社所輻湊交織的心靈原點,是一顆孤獨、哀痛、棄絕與不合時宜的心靈:我。
我是夢的巢城,但接踵而至的每一個夢卻都在邊界透露著「潰敗的先兆」。書寫或許很難不成為張愛玲式的「哀愁的預感」,然而在這惘惘的威脅中,小說家迫現於文字的卻首先是其強悍的書寫意志,是如何動員記憶的材料與感性創造一整座個人的繁複宇宙。
八卦山是文字所幻化的魔山,而彰化則成為顏忠賢的馬康多,描寫一整個家族夢境般興盛與衰敗的《寶島大旅社》卻不無怪異地處處呈顯出《二○○一太空漫遊》般謎樣的尤里西斯時間之旅。這是一個指向未知與未來的神祕旅程,但同時也是從一開始便自我封印沒有出口的巨大靈魂密室。「這房子沒有大廳,沒有樓梯,沒有窗口,甚至,像個單向甬道所形成的巨大陣列或迷宮或就只是個放大的充滿走道卻看不到出口的密室。」
一整座巴洛克迷宮,萊布尼茲花園中的花園,然而所有巴洛克藝術的重點並不只在於究極而言營造了何等交疊曲折的複式空間(不論這個空間是由木石、樂聲或語言所給予),因為更為重要的,在於這個極度褶曲凹陷的空間中必須完整而獨特地映射整個宇宙。這便是單子構成宇宙、宇宙映射於單子的萊布尼茲式交互含攝。一部小說是構建宇宙的基本單子,但同時卻又是呈顯宇宙獨一無二意義的觀點。小說述說了一個世界,但這個世界裡住居著小說家。由強虛構所迫出的套套邏輯與惡性循環封印著當代小說:我寫了寶島大旅社,但寶島大旅社亦徹底改變了我。然而,顏忠賢一直是個末世論的巴洛克小說家與創作者,因此我們在這個將一整個巨大宇宙內縮吞噬並不斷再從內部蔓生枝椏根系的小說單子中看到的,是「摺疊無限回皺摺的『末代』營造法式的終極版本」,一個由系列夢境綿延滋長直到世界末日的「重新尋獲的時光」。
在小說的終篇裡我們讀到顏忠賢所有夢境的黯然核心,隱藏在他一切書寫背後的蒼涼手勢:「一如我找尋我的老家族,找尋旅社,都很雷同地陷入了這種盲目找尋的用力之中。但是,我卻一定要找回老家,找回過去,找回寶島。這些都已經過去了,以後也只就是這樣,不會再怎樣了。」似乎從第一頁起書裡的一切便早已經灰飛煙滅地結束,絢美的誕生不過是為了最終的覆滅,啟示錄般的寶島大旅社注定「在我的開始是我的結束」。書裡每一個被寫下的字都是為了重新找回「寶島」,為了重新豎立古老迷幻的寶島大旅社也為了再次讓其絢爛崇高地崩裂消失。整整三代人長達一百年的糾葛繾綣,他們的孤寂與歡愉、哀愁與榮耀,容許我在最後引用賈西亞‧馬奎斯,「書上寫的一切從遠古到將來……永遠不會重演,因為被判定孤寂百年的部族在地球上是沒有第二次機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