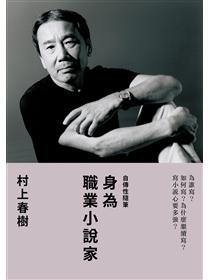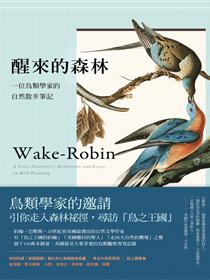「三三」成為歷史,《三十三年夢》從「三三」的灰燼中升起,紀錄了一個人如何忠實、忠誠地穿過多變的時代,穿過不變的京都地景,尋找並看守自我靈魂「自由」的過程。——楊照
我清楚記得他們的身影,他們的笑語。
我第一次來京都至今,櫻花已開過三十三次了。
儘管昨天傍晚才來過,我走在通常無人、但它不管濃蔭的夏天或蕭索的冬日都同樣泛著青光的石板路(只路邊灌木叢中終年有一家子貓),總是心內既波動又安定,彷彿從沒離開過。
寧寧道上人影幢幢,我看到在愁煩心事、在想著自己進行中的小說的三十出頭那時以為自己好老人生已走到盡頭現在看去多麼年輕的自己,
我看到牽著女兒、彎下身子與大頭妹說話的唐諾,
我看到二十二歲時穿著長襖打兩條及胸辮子、出神出世的天文,
我看到因疾走而長袍角揚起的胡蘭成爺爺,
我看到盛年時的父母,我看到宏志宣一倆牽著阿朴的背影,大春美瑤和兩歲的張容,丁亞民盧非易杜至偉黃宗應這些少年友人,老焦焦雄屏的比我還愛進玻璃小店,一僧一道也似的吳繼文和黃錦樹,當時的好友蕭維政老蕭,當時我最喜歡的以軍鄭穎,正益小鄭一家,麗文乃菁馬各,最能走最會看的俊頴,侯子……,更別說坐在嬰兒推車裡專注兩眼不言不笑的盟盟。
我清楚記得他們的身影,他們的笑語。
我第一次來京都(一九七九)至今,櫻花已開過三十三次了。
一九七九年開始,二○一三年重回京都故地,幾次盤桓漫遊京都時空中。京都,說是故地,其實早已自初履後幾次再臨流連,再加諸回憶與情感的重量,對它的熟悉已僅次於居住的台北。
那裡的街道、佛寺神社、一叢叢櫻花與嫩芽、迎面的相識臉孔,如同另一個故里。這個他方,經由朱天心自身的疊覆揉合,被她漸次回想梳理收進。回望三十三年,從中再看過往歲月,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物,幾番出入,這才發現,記憶深刻、情感強烈執拗,不因時間而流損。
作者簡介:
朱天心
山東臨胊人,一九五八年生於高雄鳳山。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曾主編《三三集刊》,並多次榮獲時報文學獎及聯合報小說獎,現專事寫作。著有《方舟上的日子》、《擊壤歌》、《昨日當我年輕時》、《未了》、《時移事往》、《我記得……》、《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小說家的政治周記》、《學飛的盟盟》、《古都》、《漫遊者》、《二十二歲之前》、《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獵人們》等書。
章節試閱
二○一三年二月七日早上八點半、京都、攝氏四度。
時間還夠,我和唐諾穿八坂神社側門出,再走一次京都所有寺廟參道中我最喜歡的東大祖谷廟,它右首有圓山公園,左有通往二年坂的寧寧道,在遊人「哇哇」驚歎四顧中極易被忽略。
儘管昨天傍晚才來過,我走在通常無人、但它不管濃蔭的夏天或蕭索的冬日都同樣泛著青光的石板路(只路邊灌木叢中終年有一家子貓),總是心內既波動又安定,彷彿從沒離開過。
我們是約定好九點到高台寺會合女兒盟盟,今天是她隨侯孝賢《聶隱娘》劇組在京都拍片一個月的最後一天,清晨六點通告,從不出借外景的寺方因日人的侯迷甚夥,便破例出借(如此的尚有東福寺、大覺寺、清涼寺、平安神宮……),唯拍攝工作必須在九點開放遊人入園前結束。
侯子(我們都叫他侯子)籌拍《聶隱娘》六年,光劇本就數十易稿(原《唐傳奇》中的聶隱娘不到千字),參與初期劇本工作的包括阿城和阿運,三年多前,編劇天文拉盟盟幫忙,盟盟從純粹的文書記錄整理工作到一起討論到提供知識背景(她念民族學,熟稔唐朝的少數民族,唐官制又巧是她的私人嗜好),亞斯柏格人的她對細節雜知的執迷和驚人記憶能力讓侯子覺得彷彿帶了筆電在身可隨時google,所以此戲開拍她從頭到尾皆參與劇組拍片,包括一○年秋的奈良、京都,一二年秋冬的武當山、大九湖、棲蘭山,她尚得負責交出電影小說和拍片扎記二書。
她已不跟我說話近三年,儘管我們朝夕共宿一室,從她出生到現在,沒有須臾分離過(是這原因嗎?所以她必須以如此方式斬斷臍帶?)。
看見長滿苔蘚的茸皮簷的菊乃井家告示板右行,就是寧寧道了(若不右轉、反向的往坡上前行,是一大片墓地,我們仨有一年不進寺廟而逛墓地,吃驚這個作家那個近代史人物就長眠於此。這片墓地我們曾想看它到底幅員多廣,一路走到知恩院的上方咧)。
早晨和黃昏的寧寧道從不叫人失望,通常只有穿著美麗圍裙匆匆出來遛狗的鄰婦和蔴黃袈裟也成為風景一部分的僧人。
洛匠咖啡當然尚未營業,隔著木柵門可窺見庭園池裡的錦鯉,我一無例外的一定湊上去看一眼,以為可以看到那從小就不隨我們進咖啡店內,只趴在池邊屁股朝天執意摸某隻她熟識的錦鯉的三歲、四歲、五歲……乃至好大一隻了的女兒盟盟。
我好害怕,也期待看到工作中的盟盟,我不知她會不會因為在這裡,這個我們留下太多記憶的地方,她會自然的接續上那些潮水湧動樣的記憶,對我自然的一笑(她那獨特的目光不與人接觸,顯得酷酷的笑容),那我每每忍不住拐進手工玻璃小店時她無可奈何又容忍我的一揮手「去吧」的笑容,她通常都在對面的櫻樹下研究樹洞的蟲子、收集樹幹上泌著的樹膠(喏,送你琥珀),地上的櫻籽……,不分哪樣的年紀。
寂靜清冷的寧寧道,第一次感覺像是走在洶湧淘淘排面而來的激冷河水裡,心底響起的音樂是電影《新天堂樂園》男主角回到童年小城的老戲院裡,看著老放映師把當年所有電影剪掉的片段(當然都是各種情人甜蜜熱情的擁吻)集成時,潮水一樣湧動的配樂。
因此寧寧道上人影幢幢,我看到在愁煩心事、在想著自己進行中的小說的三十出頭那時以為自己好老人生已走到盡頭現在看去多麼年輕的自己,我看到牽著女兒、彎下身子與大頭妹說話的唐諾,我看到二十二歲時穿著長襖打兩條及胸辮子、出神出世的天文,我看到因疾走而長袍角揚起的胡蘭成爺爺,我看到盛年時的父母,我看到宏志宣一倆牽著阿朴的背影,大春美瑤和兩歲的張容,丁亞民盧非易杜至偉黃宗應這些少年友人,老焦焦雄屏的比我還愛進玻璃小店,一僧一道也似的吳繼文和黃錦樹,當時的好友蕭維政老蕭,當時我最喜歡的以軍鄭穎,正益小鄭一家,麗文乃菁馬各,最能走最會看的俊頴,侯子……,更別說坐在嬰兒推車裡專注兩眼不言不笑的盟盟。
我清楚記得他們的身影,他們的笑語。
我第一次來京都(一九七九)至今,櫻花已開過三十三次了。
至於第一次來還是坐在推車裡的盟盟,無論醒醒睡睡,總不鬆脫離手那捏了一星期她在大阪御堂筋拾得的一片銀杏葉(唉那時若知曉有所謂亞斯柏格人便不足為怪了),如今在京都工作近月,每晚傳簡訊給天文「在四條大橋邊,吃Fauchon麵包,好幸福。」她隨劇組住五條崛川的東急飯店,每日通告前兩小時四下狂走,有一天清晨走到高台寺再疾返飯店會合劇組,劇組車出發,下了車,竟又是高台寺。
我和唐諾拾級而上高台寺參道(亦是一條靜靜美透了的小參道),我因酷寒因氣喘,走走停停,心臟忐忑突跳,除了怕黑怕鬼怕死什麼都不怕的我,竟然膽怯起來,延捱著,喘著,不敢前往。
我不知道,盟盟會不會對我一笑,於是,斷線珠子似的讓我們瞬間串起這所有的三十三年?
一九七九年五月,京都。
同行人:胡蘭成爺爺、仙枝、天文
匯率日幣:台幣/1:0.166
來晚了,雖然這是我第一次出國。
來晚,指的是櫻花季已過,因為這一年初的台灣,才剛剛開放出國觀光旅遊,之前的任何國外旅遊都得託旅行社以商務之名申請(包括我那在小鎮行醫一甲子、已經跑遍地球一圈的外公外婆)。自胡爺被以漢奸之名查禁著作,怕繼續連累我們而在七六年底《三三集刊》開辦前夕返日,至今始終與胡爺爺通信不斷且勤學日語的他學生仙枝和姊姊天文,便在開放觀光的第一天著手辦申請赴日手續。
不知手續困難何在(現猜想,可能是年輕女子單獨未跟團赴日且長達一個月,不是賣春是什麼?),拖拖拉拉幾乎胡爺每日一信,快來快來櫻花不等人。
我從未見過櫻花,不覺得錯過有何要緊,而且畢竟我還在念大三,蹺一個月的體育課有些麻煩,那一兩年,根本我和唐諾念的是建築,天天在淡水與丁亞民阿丁擠一間校外的學生宿舍,讀他的教科書、幫他連夜趕圖做模型、一起練歌練舞,開口閉口說的是路易斯康、漢(寶德)……,回台北時都為了唯一得點名的體育課,所以每有人問起我在哪兒念書,爸媽異口同聲答:「台大體育系。」
我對赴日一遊或見兩年沒見的胡爺意興闌珊,被動的該備什麼證件該去入出境管理局就去。
胡爺要我們只管機票就好,其他無需準備,但我仍將所有存款換了約十萬日幣(按當時匯率約只需不到台幣一萬七),儘管當時我的《擊壤歌》賣得像印鈔機,但深知集刊和出版社財務窘迫,便要求記帳至日後獲利了再結算(這一「再算」,一直到十年後出版社結束營業、我結婚後三年、台灣泡沫經濟始才拿到,已啥事都做不了了)。
結果我們弄到四月下旬才上路,胡爺獨自一人親來成田機場接機,一路先搭京成線到上野並換山手線,山手新宿站換青梅線往立川,立川再換車到福生的家。
當時胡爺七十三歲,大多老舊的月台並無電扶梯,他一襲長袍在我們從未見識過的擁擠人潮中快手快手腳幫我們將那鬆垮龐大、比他二戰時逃難中的行李差不多少的行李袋扛上扛下月台讓人忘了他年紀,當然更不可能預料那是他人生的倒數二年。
胡爺爺,儘管多年後的現在,我已能習慣與王德威黃錦樹陳子善陳丹青小寶……談及時可自若的連名帶姓說他,彷彿他只是個書裡尋常的歷史人物,但在記憶中、獨處中、與舊時友人言談中,是永遠的胡爺爺。後來我也才發現我可能是他這一輩子認得的眾女子中唯一喊他爺爺的,而他似也首次覺得這身分這關係很新鮮有趣,卯起來當爺爺管我這管我那管個不停,包括不老實吃正餐吃太多巧克力(像蘇曼殊),包括別戴隱形眼鏡太傷眼(人家張愛玲也不戴呀),包括別再抱狗抱貓,更不用說那長長一列書單,教文盲教阿難般的耐心。
京成線上,他每指那窗外一閃即逝的新綠說「那些原先都是櫻花的呀」隨即講起他最喜歡的桃山時代和開此時代的豐臣秀吉。天文仙枝如常認真的聽著課,我立即被窗外那些各色各式的小房子吸引,還有大量深淺濃淡不一的綠、出了台北才看得到的水田、車內各種香、愛乾淨的人體匯集的冷冽清鹼的香、空調內的後來永遠釘在我腦頁某一褶縫的一種上品的京香。
胡爺爺胡奶奶(沒錯就是《今生今世》裡的佘愛珍)和女兒咪咪、咪咪的八歲兒子一清住在福生駅前不遠、現西友百貨與麥當勞後所夾角象限處,在新宿若運氣好坐到青梅快速、不須在立川換月台至福生駅,也得四十幾分鐘(正好不多不少一堂課時間:古文明源起、四書五經、經濟學、唐詩、日本史、能樂、茶道、花道、書法、圍碁、當前國際局勢……十足像多年後盧貝松的電影《第五元素》中那守護人類安危存續祕密苦等天人降臨的老教士,為那如同白紙〔白癡?〕的天人在短短數小時內將地球/人類的所有知識和歷史灌注於她)。
福生市以市東為美軍橫田基地為人知,胡奶奶五○年代在此開酒吧,房子先租後買即現下我們住的同一幢,屋舍數十年來沒變動吧,乍看與一般日人家屋無異,平房木造建築、庭院環繞(只有屋後臨胡爺書桌一叢竹是胡奶奶認真照顧的,其餘任野花野草茂生,不似日本人家再小的院子一花一草的皆有安排),大而寬敞的客廳連餐廳,木頭地板須脫鞋入內但無榻榻米日式氣味。洗手間緊鄰有二間、別男女,是當年酒吧形制清楚的遺跡。
夫妻年紀大了似乎都回到一人狀態不願再勉強適應任何人哪怕是終身伴侶,胡爺胡奶似也別寢,他們將書房連臥室的單人床讓仙枝睡,胡奶奶堆滿什物的雙人床我和天文,她自己在廚房隔壁的雜物間搭了臨時行軍床,那年她已七十九歲,每早跟我們自誇睡相好,都不曾滾下床。胡爺爺則似在咪咪一清房打地鋪,只怪那時我們太開心太粗心,竟至疏忽了因我們三人的闖入他們是如何大亂了生活作息的。
例如胡奶奶,一兩天就摸清我們愛吃什麼,每天早餐我們邊吃早餐邊聽課時,她已超市回來,開始準備講究的上海菜,那些雞胗必須剔其筋、一隻隻蝦仁挑泥腸、剝豆莢、一莖莖的掐去頭尾的豆芽……的活兒,原來是上海菜炫耀(我家有手腳麻利的女傭們)的構成部分,現都她一人獨挑。
她且看我們進出門兩手空空很怪,例如我,薄薄十張日幣萬元鈔塞牛仔褲屁股口袋好平整,無需梳妝的年紀,出門連梳子都不用,更不用說如今已像包包內建必有的護手霜護唇膏防晒乳目葯水維他命薄披巾環保筷木糖醇口香糖(三C……)這些不帶個包簡直無法出門的現下。胡奶奶立即在駅前的西友百貨幫我們一人買了一個肩包,我們才從此脫離身無長物的年代。
她且見我們並無真正可應付北地四月天候的衣著,便夥著咪咪翻出那些保管如新的咪咪舊衣中的薄大衣外套風衣給我們,我和咪咪等身量,走時咪咪索性將她收理好多年的衣服全給了我們,所以大學畢業循例校園拍照時穿的及膝旗袍就是咪咪的。
咪咪並非胡爺胡奶親生,是戰後在獄中待審漢奸罪時、同房一日本女間諜中島成子獄中所生,後胡奶奶先出獄,便受託帶出並一輩子視如己出。
他們仨平日交談都用上海話(連只會說日語的一清也全聽得懂),吵嘴叮對時也是,但咪咪和我們說的是可當播音員的標準普通話,胡奶奶是上海腔普通話,胡爺爺是濃濃的紹興口音(但他的日語聲腔可多像小津電影中的笠智眾啊),以致我屢屢電車上問他那好看極了的行道綠樹叫什麼名字呀,怎麼聽他答的皆是「銀行樹」,因太怪了,便追問四五次,他認真一字一字咬清楚:「銀、行、樹。」我便寫信給唐諾說我好愛一種美透了的叫「銀行樹」,還夾了一片新綠的、小扇子一樣的,欸,後來知道就是銀杏樹的美麗葉子。
從到東京的第一天,胡爺爺就再再預告就要去京都了、下星期去、下個月去、梅雨前去、葵祭前去免得到處是遊客……,對此,我不像耽美的天文充滿期待,因我覺得這裡就好透了呀,不進城的日子,每天清早六點多就陪胡爺去多摩川邊打拳,從胡爺家快走到堤邊「二子玉川像」的水上公園那裡約需半小時,自從遭我們仨尾隨後,總要拖拉成一小時,終歸我和天文太貪看一家家的庭院了,大戶人家的大樹名花不需多描述,連小家小戶只一坪大的院子也精心植滿花木,四月底,芍藥已備好苞蕾,牡丹已微微綻露,還有那從未見過在水溝邊、田坎邊、野林隙地……的異國溫帶野花,每天看得心醉神馳。
胡爺川邊打拳的時候,我們就放野牛羊四處遊蕩,這塊有著「二子玉川」兄弟紀念像的疏水道區,多年來害我都一直誤會是太宰治最終跳水自殺成功的玉川上水,也衷心以為是大雄和小叮噹走入地下龍騎士王國的那入口。
二○一三年二月七日早上八點半、京都、攝氏四度。
時間還夠,我和唐諾穿八坂神社側門出,再走一次京都所有寺廟參道中我最喜歡的東大祖谷廟,它右首有圓山公園,左有通往二年坂的寧寧道,在遊人「哇哇」驚歎四顧中極易被忽略。
儘管昨天傍晚才來過,我走在通常無人、但它不管濃蔭的夏天或蕭索的冬日都同樣泛著青光的石板路(只路邊灌木叢中終年有一家子貓),總是心內既波動又安定,彷彿從沒離開過。
我們是約定好九點到高台寺會合女兒盟盟,今天是她隨侯孝賢《聶隱娘》劇組在京都拍片一個月的最後一天,清晨六點通告,從不出借外景的寺...
推薦序
【推薦】
說吧,追求「自由」的記憶!
──讀朱天心的《三十三年夢》
楊照
1
那是個如夢般的情景,我和天心走在敦化南路的巷弄中,隨著兩個北京國際學校的學生及其家長,找尋著應該在附近的一家商業攝影棚。《三十三年夢》在《印刻文學生活誌》上連載好幾個月了,我好奇問起這本書的寫作進度,天心臉上露出了典型的羞赧笑容,承認了我早就猜到的情況──書絕對不會像和蔡逸君對話問答時所說的,以十六萬字的規模收場,也因而她正掙扎著是否要以原來的方式繼續寫下去,還是應該調整,寫得節制些、精簡些?
毫不思索地,我衝口說出:「就寫吧!別想那麼多,先全都寫下來再說。」會有此話,並不是因為我覺得自己有資格、有權力建議天心怎麼寫,而是因為在那一瞬間,我的腦中同時浮現起兩個影像。一個影像,是小說《羅莉塔》作者納博科夫的照片,在一本書的封面上,那本書,叫做『說吧,記憶!』
說吧,記憶!事實是,記憶並不是一個靜態的倉庫,存放了過往的聲音、影像與情緒,等著我們愛怎麼去搬弄就怎麼搬弄。我早已知道:記憶真的不屬我們主觀意志的控制領域。要讓自己記得甚麼,和讓自己忘記甚麼,都永遠艱難且不成功。而且,和一般想像不同,我的經驗是要記得雖難,要遺忘其實更難。
人或許還能刻意壓抑某些記憶,封在潛意識裡,然而一旦記憶啟動了,我們哪有辦法決定記得甚麼、想起甚麼?先記得甚麼、後記得甚麼?只要記得甚麼、不要記得甚麼?
完全不在我主觀控制中,和天心並肩走著,我腦中出現的第二個影像,是三十年前的淡水重建街,窄小曲折的巷道,前前後後錯落走著天心、材俊、丁亞民、鍾信仁、盧非易、杜志偉、游明達,以及好幾個霎時竟然全都記起名字的「小三三」女生們──高菁穗、吳怡蕙、林仲全、杜嘉琪……
還記起了我自己身上穿著一件那年突然紅起來的成衣廠牌「WE」的藍色套頭平領麻紗上衣,風吹來,又薄又輕又寬大的衣服在身上飄,就在心上背誦白居易的詩:「二月二日新雨晴,草牙菜甲一時生。輕衫細馬春年少,十字津頭一字行。」我們,就像是那帶點豪氣、帶點囂張,橫排一字走在津頭的少年們。
然後還想起了在淡水街頭上,十七歲的自己惦記著手上寫的小說,訂了個叫「春雨三月」的標題,但心中始終不舒服,更想取作「年少春衫薄」,但這五個字,已經被三姊先拿去用在她的小說上,我能說服她把「年少春衫薄」讓給我嗎?……
記憶停不住,記憶有自己的動力與方向,很多時候,我們只能兩手一攤,無奈卻又多少有些耽溺地模仿納博科夫:「說吧,記憶!」
2
以京都為主要場景,紀錄三十年來一次又一次到京都漫遊行走的旅程,《三十三年夢》如此啟動了朱天心的記憶。她的主觀打開了記憶之門,寫作之初,她或許想像自己如同走入了一座龐大如宜家家具的庫房,必要時動用堆高機將存放在高高低低架上的人與事與情景與情緒,下架、搬出。
然而幾萬字之後,我們已經能夠察覺如此形象比擬逐漸不適用了。貨架上的東西飄浮起來,有的輕輕飄到天花板上,堆高機升到最高也無從將之下架;有的則沉重地直落在堆高機上堅持要被帶出去,甚至進而不理會開堆高機的人,自主操控著離開了記憶庫房,自主成形為一行一行的文字,出現在《三十三年夢》書中。
仍然是關於京都的回憶,但記憶要說的,重點不在遊記、不在旅情、甚至也不在或喜或悲的懷舊。記憶說的,毋寧接續了當年《擊壤歌》中的「莫名的大志」。
經過了三十多年,穿越《三十三年夢》,我們現在可以更認真、更準確些理解那份「莫名的大志」。那不只是朱天心少年時期浪漫、口齒不清的隨手修辭,竟然早早含藏了她終究的人生與文學核心。
容我強作解人,朱天心的「大志」,近乎於傳統所說的「詩言志」,換成現代的語言說法,「志」就是價值、是非,文學作品必須有強烈的價值、是非為其基礎,文學作品的重點,也在於傳遞強烈的價值、是非判斷。
和她的外表截然相反,朱天心個性剛烈;和她早期作品表面呈現的截然相反,朱天心的文學,灌注了濃厚的價值判斷。
《三十三年夢》中,對於親人、友朋,乃至對於「胡爺」胡蘭成的回憶,都必須穿過朱天心的價值、是非判斷。大異於許多人的印象,就算對胡蘭成,朱天心都不可能抱持著徹底、簡單的全盤接受態。從第一次去日本、去京都時,她就已經在自己的腦中、心中,和胡蘭成、和胡蘭成所教誨的道理辯論,並沒有因為那是來自「胡爺」的知識,便理所當然視之為真理。
如此我們也就不會意外,即便是一起長大的姊妹、即便是曾經論交二十年的朋友,也無法單純以親情或交情讓朱天心改變看待、評斷他們的價值與是非標準。
朱天心認真、堅持看待自己的信念,不輕易動搖。她的信念中,最稀有難得的,應該是「自由」吧!三十多年的時間中,她的「自由」信念,在社會領域中,甚至推擴到了「不認同的自由」;在創作的領域中,則推到了讓每一個創作者都不得不為之動容的「不書寫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不在正面的選擇──可以選擇自己是甚麼人、認同哪個國家哪個文化;可以選擇自己要寫甚麼──而在負面的拒絕,舉世滔滔狂潮中,「自由」地拒絕任何標準答案。
更稀有、更令人動容的,是這三十多年間,朱天心(加上唐諾)為了保有這份「自由」所做的種種準備、種種決定。說吧,記憶──記憶說出了一個人如何盡量減卻世間依賴、減卻有所待的享受,以便讓自己繼續保有這樣的一份「自由」。
在京都漫長、彷彿沒有沒了的步行,因而取得了一種現實以外的根本意義,正常旅人、甚至正常的生活者無法體會的意義──只靠自己,不依賴任何操之在人、操之在財富的工具與機制,走路時,她是獨立且自由的。
3
天心記憶力驚人,能將三十多年來的眾多細節全都存藏著。在書中,她甚至幫我記住了我自己都忘了的事。讀著讀著,我想起來了,高中二年級吧,的確曾經被主任教官找去,鄭重其事地警告──高中生不得參與校外社團,如被發現,會被記過,還有可能送調查。我當然知道教官說的「校外社團」,指的就是「三三」。我沒把警告當一回事,警告後仍然繼續參加「三三」的活動,繼續出入景美朱家。
並不是因為我特別英勇,而是因為在那時候,對我而言,這不過就是和教官打交道時,一定要被斥責、警告中的其中一樁而已。我並未知覺這後面的政治意涵,更沒有聰明到理解這原來是政治迫害的一種形式,一種最低階的形式。
連帶地,我記起了,就在這種不斷被叫喚到訓導處、教官室的情境中,我也有了自己的「大志」,我立意堅決追求,一定要做個「自由」的人。是的,我也認為「自由」是最重要的,不受任何權威掌控、支使,為自己做決定,同時為自己的決定負責。
「自由」的前提,當時我了解的,是不依賴,不依賴家人、不依賴單位、不依賴老闆,而要不依賴,最好的辦法是孔子說的「多能鄙事」,讓自己身上多些不同的本事本領,就多點機會可以在這個社會上不依賴地活著。
當時,我努力開發的一項「鄙事」工夫,就是做美工、貼完稿。事實上,這也就是當年有一段時間我經常出入景美朱家的理由,《三三集刊》停刊後,只剩下報紙型的「書訊」在發行,「書訊」的編務由盧非易負責,我是跟在他旁邊幫忙做美工、貼完稿的人。
我記得有一次完稿後,盧非易特別請我去中華路「徐州啥鍋」吃飯。我記得有一次「書訊」出刊後,在朱家的飯桌上大家七嘴八舌檢討,好幾個人覺得美工做得花俏了些。聽著,少年的我臉紅了,口中沒有說出甚麼,但心裡畢竟是不服氣的。
回頭想想,這中間有著一份深刻的反諷,反諷的深刻。奇異的時代,泊湊的機緣,讓一群都想望「自由」的人,在那個客廳裡集結為一個團體。那個團體,因不自由的時代環境而生,沒多久,解散各分東西,也就不意外了。
「三三」成為歷史,《三十三年夢》從「三三」的灰燼中升起,紀錄了一個人如何忠實、忠誠地穿過多變的時代,穿過不變的京都地景,尋找並看守自我靈魂「自由」的過程。
【推薦】
說吧,追求「自由」的記憶!
──讀朱天心的《三十三年夢》
楊照
1
那是個如夢般的情景,我和天心走在敦化南路的巷弄中,隨著兩個北京國際學校的學生及其家長,找尋著應該在附近的一家商業攝影棚。《三十三年夢》在《印刻文學生活誌》上連載好幾個月了,我好奇問起這本書的寫作進度,天心臉上露出了典型的羞赧笑容,承認了我早就猜到的情況──書絕對不會像和蔡逸君對話問答時所說的,以十六萬字的規模收場,也因而她正掙扎著是否要以原來的方式繼續寫下去,還是應該調整,寫得節制些、精簡些?
毫不思索地,我衝口說出...
目錄
【推薦】
說吧,追求「自由」的記憶!
──讀朱天心的《三十三年夢》/楊照
三十三年夢
文學答問信/朱天心、蔡逸君
【推薦】
說吧,追求「自由」的記憶!
──讀朱天心的《三十三年夢》/楊照
三十三年夢
文學答問信/朱天心、蔡逸君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42收藏
42收藏

 39二手徵求有驚喜
39二手徵求有驚喜




 42收藏
42收藏

 39二手徵求有驚喜
39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