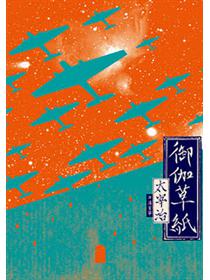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以愛總結:我是切‧格瓦拉 /執行主編蔡逸君
切‧格瓦拉不屬於誰,他屬於每個人。
不分國籍,沒有種族之別,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幾乎所有的人第一次知道或接觸切‧格瓦拉相關事物──包括他的傳奇事蹟、肖像、書本、T-shirt等等所有從他身上衍生出來的一切,即莫名為他那張深刻的臉所吸引。接著,不管你是否繼續熱愛他所代表的信念,不管你是否贊同他所有的作為,你已經無法忘卻他了。在切身上有某種無法言說的魅力,混合了愛與革命的氣息,混合了詩人與領袖的特質,他總是在路上,他總是哮喘著兼思索著,他總是站在弱者的那邊。切‧格瓦拉是浪漫精神至極的代表,他的演說和文字書寫,總透露出那樣懇切熱望的理想,完全的人的高貴意志展現,他說:
一個真實的革命者是被偉大的愛所指引。╱ 讓我們面對現實,讓我們忠於理想。╱ 哪裡有貧困,哪裡就有我!╱ 堅強起來才不會喪失溫柔!╱ 我怎能在別人的苦難面前轉過臉去。╱ 在革命中,一個人或者贏得勝利,或者死去。╱ 我並不在意死亡,只要有人能撿起我的槍繼續戰鬥。
切的確像他所言那樣──如果說我們是浪漫主義者,是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分子,我們想的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那麼,我們將一千次的地回答說,是的,我們就是這樣的人──他直到死亡降臨時都不悔其志。沒有人可以像切那樣,雖然全世界都知道他的慘敗結局,但大多數人依然由衷地向他致敬,不減損其一絲一毫的英雄形象。理解切的人,總是相信他並未真正失敗,他的勝利會在未來的某一天到來。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英雄,若是少了像切這樣標竿式的人物,時代也只是無聊的歷史堆疊罷了。標竿人物給出方向和信念,他有一雙熒熒目光看向遠方,他的思索緊扣著當代謀劃著未來,他孤單卻獨力支撐起了時代的高峰。本期還有三個人物,他們所代表的面向雖大相逕庭,但其面對時代所展現的不屈的意志卻是那樣的接近,吳思漢,法農,高信疆,他們是我們時代的標竿,典範在夙昔。
我們不會忘記這些臉孔,他們為歷史刻劃塗抹鮮豔的顏彩,指出路來讓大家走,那樣不平凡的人,也正是最平凡的一張臉。看著他們,我們終於明白,當一個人可以平靜的面對自己的良心,可以無愧地不需閃躲自己,他便能從容的面對最困境、最險惡、最可怖之時代。
「我是切‧格瓦拉。」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被捕時,切平靜的說。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以愛總結:我是切‧格瓦拉 /執行主編蔡逸君
切‧格瓦拉不屬於誰,他屬於每個人。
不分國籍,沒有種族之別,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幾乎所有的人第一次知道或接觸切‧格瓦拉相關事物──包括他的傳奇事蹟、肖像、書本、T-shirt等等所有從他身上衍生出來的一切,即莫名為他那張深刻的臉所吸引。接著,不管你是否繼續熱愛他所代表的信念,不管你是否贊同他所有的作為,你已經無法忘卻他了。在切身上有某種無法言說的魅力,混合了愛與革命的氣息,混合了詩人與領袖的特質,他總是在路上,他總是哮喘著兼思索著,他總是站在...
章節試閱
繼續上路★不斷革命 ──廖偉棠VS.張鐵志對談切‧格瓦拉
這場對談很有意思,從發生到進行到結束,似乎就如「革命」般,充滿不確定因素。找廖偉棠(人在義大利)跟張鐵志(人在台北)談切‧格瓦拉,是因為這二位作家的特質相當迷人,而且對切都有深入的理解,某種相同的質素將這三個心靈互相拉扯住,在網路上以mail進行對話。編輯負責搖旗吶喊,發出mail提出第一個問題暖場:「第一次知道切是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初次的印象如何?」(台北時間pm4:28)為了真實的呈現,我們把時間也標示出來,這是非常即時的反應,打字速度先不說,要能夠在這樣的時間內寫出如此深刻的話語,不禁讓身為旁觀者編輯的我大為驚嘆!只有切有這麼大的魅力吧,他所影響的一代一代人,將他的信念繼續燃燒、延伸。(編者)
廖偉棠(以下簡稱「廖」):
可能很早就在某些影像上看到切的頭像,但不知道是什麼,還有在美國樂團「憤怒反抗機器」(Rage Against the Machine;另譯討伐體制樂團)的專輯上也見到過。但真正認識到切,是在一九九七年,我從香港到廣州買書,回來的巴士上我在最新一期《讀書》雜誌上看到大陸的拉美研究學者索颯寫的關於切的紀念文章,當時我在巴士上讀得淚流滿面,沒想到當代還有這麼偉大、無私的人。回到香港,馬上買到大塊出版的《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看了,很快又買到香港一家托派出版社在七○年代出版的《古巴革命戰爭回憶錄》,以及大陸七○年代出版的蘇聯人寫的切的傳記,於是對切有了基本的瞭解。對他的初次印象就是:那是一個可以信任、可堪追隨的人。(台北時間pm 4:36)
張鐵志(以下簡稱「張」):
我記得,應該是九○年代前期的大學時期讀到格瓦拉。彼時終日投身於學生運動,搞讀書會、上街頭、在學校發傳單,手持麥克風在少少的人群前演講。尤其,除了專注於現下的台灣社會矛盾,我也很著迷歷史上的青年革命,不論是台灣從日治時期開始的學生運動,或者六○年代的全球學生反抗。然後,不記得在什麼書上,讀到了切的故事。那樣典型的革命者的故事,決絕的姿態。結合了勇氣與悲劇,獻身與犧牲。在那個我們正急切於尋找反抗典範的過程中,他當然是成為無可取代的典型。(台北時間pm4:54)
廖:
你提到勇氣和悲劇、獻身與犧牲,我想這是吸引我們的最初動機,其實這幾種特質在宗教殉教的聖徒(比如說聖塞巴斯蒂安)身上都具有,我們早年對革命的嚮往中也是混雜著宗教情感的。而你提到的決絕才是我們更進一步認識切的道路,他有別於其他共產主義當權者的一點是他對自身也非常決絕,具有苦修精神——當然這又讓人想到宗教,如聖方濟各(San Francesco,1182-1226)。但同時他對普遍的人類情感並不冷酷,他的革命是飽含了愛、愛恨分明的革命,如果只有愛不講恨那就和宗教無異,只講恨不講愛——那是極端左派如日本聯合赤軍那樣的。切是一個心懷大愛的戰士,他身上也有很多屬於人類的弱點,正是這樣的一個人才不至於淪為神話符號吧。如沒記錯,我是在他的《論游擊戰》的序上讀到他談論革命中的「愛」的見解的,深為折服,你看到過嗎?(台北時間pm5:09)
張:
你說的真好,且我正好在思考這一點。關於革命與愛。
我在我的書《反叛的凝視》寫切的文章時,引用了他的一句話:「一個真實的革命者是被偉大的愛所指引」。誠如你說的,他的革命是愛恨分明的革命。但我想,應該是以愛,對於被壓迫者的愛,對正義、和平的價值的愛為底蘊,然後才會出現對那些壓迫與支配者的恨。所以愛是指引。
回首歷史,太多的革命者以正義之名,但最後都是以醜惡的面孔出現。尤其作為一個革命者,是處在高密度思想和肉體鬥爭的處境,他的愛與善很難在與惡的鬥爭過程中不被一步步侵蝕。於是,許多革命者最初對人民的愛,很容易後來只淪為對權力的愛。
這就是格瓦拉最吸引人的部分。我在想,或許因為他是醫生,所以可以保持那樣的愛,如同我們在《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和《玻利維亞日記》中所看到的,對同胞與同志的愛。
格瓦拉還有什麼特質吸引你呢?
或者說,他對你相信的信念來說,還有什麼樣的意義呢?(台北時間pm5:18)
廖:
對,我在《論游擊戰》序言中注意到的也正是這句:「一個真實的革命者是被偉大的愛所指引」。很多革命者(在當代也存在這樣的人)在鬥爭中,很容易忘記了最初的革命動機,而對權力和榮譽的迷戀導致出一種變態的潔癖——認為其他所有人都不如自己革命,繼而以此為藉口來清洗革命隊伍,把恨放諸那些應該去愛的人身上,這些人也許是不夠自己「革命」的同志,也許是「革命覺悟」不高的人民,但無論如何,他們不應成為恨的對象。
切能避開這一點,除了因為他是個醫生,更因為他是個詩人——我是這樣理解的。他身上的詩人氣質,他的憂鬱都是吸引我的,也許他寫的詩滿一般的,但他的行為本身就是一首詩。至於說到他現在對我的意義,我和他不同的地方是我比他虛無一些,但正是他不斷提醒我在理想主義行為中存在的積極意義,讓我從不對理想主義絕望。他的行為告訴我們,那些被譏為空想的行為,竟然是可以實行的。他令我堅持了行動主義的信念,革命絕對應該坐言起行。
但畢竟不是全世界都是當年的古巴或今天的查巴達,那麼我們如何行動下去?我想聽聽你對切的鬥爭方式的理解,還有你覺得如何轉化為我們現今在城市中的鬥爭?(台北時間pm5:35)
張:
哈哈,你果然是詩人之眼讀到了切的詩意。是的,他的行動就是一首詩,抒情而意義飽滿。
回答你的問題。我覺得切的游擊鬥爭有幾層啟示:
第一,他對社會不平等、對弱勢的關切是這個時代最迫切的問題。當然,在資本主義體制中,這個階級矛盾的問題從來沒有消失。只是,隨著過去二、三十年的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國與國之間,以及一國之內的社會不平等增加了,且非洲大陸、南亞等地區人民的貧窮並未改變。改造資本主義的迫切從來沒有一刻停止過。而且,這個鬥爭不是正在進行嗎?從一九九九年西雅圖反WTO的抗爭,左翼、環保主義、青年安那其們,他們許多人身上穿著切的T-shirt,秉持著他的火炬,用身體去抵擋新自由主義的暴力巨輪。(那一年在香港,你不是也在抗爭現場嗎?我想起你那首我摯愛的〈灣仔情歌〉)
而這些格瓦拉的子民們某程度上是取得成就的:血汗工廠減少了,世界貿易談判的議程轉變了(更強調第三世界的發展,雖然還在談判中),公平貿易的概念越來越深入人心。然後,去年,新自由主義的資本邏輯吞噬了自己,造成內爆。當然,鬥爭還是要繼續。
第二,我想他的游擊戰對我們來說,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理解。亦即文化的游擊戰。面對資本主義的強大力量,除了與其正面對抗,除了用街頭的公民不服從取代切的山中武裝游擊,我覺得也有必要展開文化的游擊戰。透過各種文化的形式,音樂、詩歌、劇場等,去暴露體制的暴力與壓迫,去展現抵抗的可能。
我其實在想,切如此愛寫日記,他一定是很重視文字所能展現的力量。
你說呢?切對於你的文化行動主義有產生影響嗎?(台北時間pm6:00)
廖:
切對文字力量的注重這點你發現得好。其實他很敏感與現代鬥爭的新形式,比如當法國人德布萊(Jules Regis Debray)被捕後,切並不感到害怕,反而高興於這樣一來會有傳媒、繼而是大眾知道和關注游擊隊的存在;而之前他在非洲給周恩來寫信要求支援大功率的發射電台,也是出於同樣考慮。如果切身處如今這網絡時代,他將會和馬訶士(S. Marcos)一樣如魚得水。我想這也是他對我們現在的文化行動的啟發,盡可能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傳播資源,把要求變革的思想傳達到任何可能、渴望接觸它的人眼中。所以我毫不避諱在社會運動中寫作和朗誦、傳播詩歌,我始終認為詩歌是可以有實際影響力和提供反思能力的(當然我也認為沒有上述兩者的詩歌也可以是好詩歌)。切的信念是能影響一個人就是一個,所以他在臨刑前夕還會對士官們「說教」。我的詩歌觀也如是,正如我曾經在一個訪談裡說的:詩歌對現實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無能為力,但我偏就不放棄那百分之零點一,我的憤怒只對我的良知負責,如果有人傾聽或和應的話,就能賺一個是一個。
你對切的文字和著作最感興趣的是哪本?我最喜歡的,還是《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但最震撼我的是《玻利維亞日記》,我以它為藍本寫了一部詩劇《玻利維亞地獄記》。(台北時間pm6:20)
張:
和你一樣,最喜歡《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主要還是因為相對於其他幾本書是比較細瑣地談游擊戰過程,摩托車日記更有血肉,有對土地傷痕、人民苦難的描寫,也讓我們看到一個青年理想主義者的成形,讀到那些青春的純粹熱情。
你對詩的看法也正如我對音樂的看法,我深信音樂或其他文化形式的力量,對人們意識的衝擊與塑造的力量。所以我特別有興趣於文化和社會運動的接合。兩者都是在抵抗。文化創作是要抵抗既有的價值、意識形態與霸權,是要創造另一種想像可能。社會運動則是改造壓迫性的政經、社會結構。兩條路線的行動者可能是分開的,但當他們結合時,就會產生巨大的力量。當然,我這幾年都是在以搖滾作為文化的切入,去挖掘搖滾的激進主義及其限制。
我也是這樣期待自己的文字:希望文字書寫成為我的文化實踐之一。我寫的題材乍看比較雜,但其實都是一貫的:去揭露、批判資本主義或威權政治的壓迫,或者比較抒情地去書寫那些反抗行動,不論是搖滾人的社會介入,或是如《反叛的凝視》一書中所討論的各種行動者,這是因為我自己被他們深深感動或是inspired。
當然,文字,或者文化行動,還是必須植基於書房外的行動中,這樣的文化實踐才是有機的,也才能讓我們不斷地反省文化實踐的可能虛弱,起碼我是常常覺得自己的不足。(台北時間pm6:38)
網上筆談兩小時倏忽而過,一點也不冷場,竟比看動作電影還刺激。幾乎一字不改的原文刊載,除了發現作家的思路脈絡,也可見文字比言說似乎多了一層清澈的質感,直入人心。可畢竟是打字,兩個鐘頭共合寫了約三千二百字,已經是驚人。意猶未盡之餘(寫的人跟即時監看的編輯都是),遂相約隔日同一時間再戰兩小時。(編者)
廖:
午安!鐵志、逸君。我們繼續我們的游擊吧。鐵志你終於看到足本的電影《切‧格瓦拉》(註)上下集了嗎?我是上個月在香港電影節上看的,當我看到下集切‧格瓦拉的遊擊隊在猶羅峽谷中最後一戰時,耳邊是淒慘得如來自另一世界的零星鳥啼、加上那一兩個長度不超過十秒的主觀蹣跚的鏡頭,一下子糾結起前面三個多小時的壓抑,轉換成泰山欲傾的巨力向我壓下來。那一刻我突然感到渾身戰慄,不覺間竟然淚流滿面——那完全是他一個人求索的地獄,我覺得Steven Soderbergh對《玻利維亞日記》裡那種彷彿被命運控制的氣氛理解得很好,成功轉換為影像,他用目不暇給的鏡頭切換配合明亮環境下的淺景深,成功地營造出游擊戰中充滿不可知因素的噩夢氛圍,我們不時看到焦點外的世界如幽靈一樣向鏡頭飄來,迅即又落回實處,這種一張一弛的節奏也像極了切在《玻利維亞日記》裡記載的戰爭,還有隱藏得更深的切‧格瓦拉的內心:孤絕的意志在痛苦中咬牙、衝突。
這部電影不迴避殘酷,我覺得比《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拍得好,《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把現實的矛盾簡單化和淡化了,變成了一部青春成長小說式的電影,過於突出溫情和夢幻,而忽略了現實是夢魘。
我在這部電影中感受最痛苦的是:那出賣游擊隊的農民羅哈斯臉上現出的一個最平凡、最正常的、人的表情,這一張臉,和不久面對死亡的切‧格瓦拉的那一張臉,竟然都屬於人類之臉。人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動物,是否還存在救贖的可能?我們面對背叛和不理解的時候,都忍不住自問,我們為之付出的努力是否有意義?但切更無私,超越了這種質疑,他完全相信意義就存在於尋找意義的行為本身之中。
張:
我還沒有機會看到Soderbergh這部片,但我知道台灣在這個夏天會上演,很期待。
電影作為一種大眾文化的力量,確實影響力深遠,我可以想像,這部片在台灣上演時,必然又會捲起一股格瓦拉熱潮。但這也正觸及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格瓦拉現象的核心矛盾:切的商業化,以及革命的庸俗化。
我們該如何看待他無所不在的頭像,尤其是各種商品上的英挺頭像?而這部新的電影除了讓我們對切有如你所論及的理解外,可以讓新世代更理解切真正代表的革命精神嗎?
切的商品化現象在古巴也一樣。我前兩年去哈瓦那時,就發現切已經是他們最大觀光商品,氾濫到讓人幾乎都不想買。如果我們對於卡斯楚的矛盾情結是,他是一個後來成為政治獨裁者的革命者;對於格瓦拉的矛盾情結則是,他是一個後來成為商品化偶像的革命者。
不過,某方面來說,我對於這個現象倒不是完全批判。因為人們總是需要令人感動的故事與啟發。切成為一個大眾的英雄並不是壞事。畢竟,如我前面所說的,還是有許多對全球化的反抗青年把切的頭像穿在身上。他們並沒有忘記切的真正精神。而且,還好他的形象不是屬於某企業的智慧財產權,而是可以被不斷複製、再造。你可以在任何國家的地攤、夜市看到。這不也是一種對當前資本主義私有財產邏輯的顛覆?
當然,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去介入對於切的詮釋權,如何讓他成為不只是商業機器的搖錢樹,而是在他已然被大眾化、流行化的既有事實下,去讓那些只以為這個頭像很酷的年輕人,對於切,對於左翼歷史,對於切的精神在現實的實踐,有更多的理解。
廖:
這點我和你觀點很接近,不吐不快,所以剛才我已經也在同時寫,剛剛寫好就看到你的信,真是一拍即合!
切的影像和事蹟的傳播,的確有被流行商業文化利用的嫌疑。但是反過來說,也可以是切的幽靈對商業傳播的利用,我常這樣說:假如一千個人因為迷戀切的頭像之帥和酷而購買相關的產品,其中或許有十個人對這個帥哥頭像背後的思想產生好奇,然後去尋找關於他的文字、去了解他的意義;而其中有一個人被他觸動、感召,繼而想行動起來做點什麼去改變這個需要變革的世界,那麼這被利用也是值得的。
我看過紀錄片《暗殺卡斯楚的638種方法》,當被問及為什麼不怕暗殺的時候,卡斯楚說:「我有道德防彈衣!」而在一九九七年紀念切的遺骸運回古巴時,卡斯楚的講話中說:「我也把切當成道德力與日倍增的巨人,他的形象、力量與影響澤被全世界。」道德正義正是切無敵的武器,卡斯楚用之武裝著自己也武裝了古巴,即使他在一次次的講話中也有利用切的偶像號召力之嫌,但是毫無疑問他也幫助切‧格瓦拉實現了一個理想:讓殉道者的精神成為抗爭者的意志、動力。他一九六七年、六八年大量「輸出」切的影像、開放切的著作的版權讓各國翻譯出版,這都是好事。所以我們看見當今世界各地的抗爭街頭上,飄揚的都是切‧格瓦拉的頭像作為旗幟,而不是來自好萊塢造夢工廠生產的任何一個英雄人物。
不過,切和卡斯楚相比,分野最大的還是切毫不戀棧權力;最近在美國的古巴流亡作家紛紛撰文批評切‧格瓦拉,說他在獨裁和對暴力的迷戀中不遜於卡斯楚,我看了一些翻譯過來的文章,覺得極像是捏造的。你怎麼看...(未完,更多精采內容請見《印刻文學生活誌》2009‧六月號:他的行動就是詩──CHE 切‧格瓦拉)
註:美國導演史蒂芬‧索德柏(Steven Soderbergh)拍攝切‧格瓦拉的史詩電影,《CHE》總長四小時三十分鐘,分成上、下兩集接續上映。台灣版則分別以《切:28歲的革命》、《切:39歲的告別信》預備上映。
廖偉棠
一九七五年出生於廣東,後移居香港,現為自由作家、攝影師。曾獲中文文學獎,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等。曾出版詩集《苦天使》、《少年游》、《黑雨將至》、《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遊》等,攝影及雜文集《波希米亞中國》(合著)、《我們從此撤離,只留下光》,攝影集《孤獨的中國》、《巴黎無題劇照》等。
張鐵志
深信文化想像、思想論述和組織抗爭三面向,都是改變世界不可或缺的。書寫是他的主要文化實踐,主題從國際政經、基進政治到文化與音樂,尤其是這幾個主題間的彼此連結。二○○四年出版《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獲選為年度十大好書,並於○八年出版簡體版。二○○七年出版《反叛的凝視:他們如何改變世界》書寫當代美國的文化與政治。預計今年出版一本關於西方抗議歌手與其時代的書。現為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理事。
繼續上路★不斷革命 ──廖偉棠VS.張鐵志對談切‧格瓦拉
這場對談很有意思,從發生到進行到結束,似乎就如「革命」般,充滿不確定因素。找廖偉棠(人在義大利)跟張鐵志(人在台北)談切‧格瓦拉,是因為這二位作家的特質相當迷人,而且對切都有深入的理解,某種相同的質素將這三個心靈互相拉扯住,在網路上以mail進行對話。編輯負責搖旗吶喊,發出mail提出第一個問題暖場:「第一次知道切是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初次的印象如何?」(台北時間pm4:28)為了真實的呈現,我們把時間也標示出來,這是非常即時的反應,打字速度先不說,要能...
目錄
【編輯室報告】以愛總結:我是切‧格瓦拉 蔡逸君
【旅行關鍵詞】臉 魏瑛娟
【微塵】買名兼盜名 陳淑瑤
【波動】班傑明之歌 穀雨
【剪貼冊】我阿母買衣記 張輝誠
【封面人物】一個只受愛驅使的真正男人──切‧格瓦拉
直到邁向永遠的勝利──寫在日記之前 卡密諾‧格瓦拉
玻利維亞日記 切‧格瓦拉
玻利維亞──獻給解放者的國度 陳小雀
與切相遇在字裡行間 陳小雀
完美的人──切‧影‧語‧錄 切‧格瓦拉/著 丘德真/譯
切,一份斷想 戴錦華
繼續上路,不斷革命──廖偉棠VS.張鐵志對談切‧格瓦拉
【世間的名字】菸槍 唐諾
【特輯】跨越無涯的一則傳說──紀念高信疆先生
鷹
大地的囚徒
鷺鷥
漁歌三疊
【專欄:文學內外】在中文系,遇見王文興老師(四) 柯慶明
【專欄:虛實空間】書店與文學生產 范銘如
【專欄:河濱散記】看不見的城市 房慧真
【漫遊者】抽刀斷水(謹以此文紀念6.25韓戰五十九週年) 李黎
【那些人那些事】
尋找祖國三千里──殖民地台灣青年吳思漢的身分認同之旅(中) 藍博洲
【回聲集】
憂傷中國藍──我讀陳玉慧《China》 張瑞芬
昨日之怒──閱讀法農《大地上的受苦者》 孫大川
【場邊故事】短暫的夏日棒球女子隊 陳彧馨
【馬戲團】粉紅雀‧地球馬戲團4 Chen肯吉
【文化專刊】面對大海的進行式──尋找台灣舞蹈、戲劇的「故事力」
【超新星】
再憂鬱一點 神小風
輕質女孩的新暴力感 鍾文音
【CEO生命閱讀】向歷史藝術探索的人生遠遊──專訪皇家國際運通總經理溫業濤
田運良、林瑩華╱採訪 蘇惠昭╱文
【六月小說】擎火之人 鍾文音
【編輯室報告】以愛總結:我是切‧格瓦拉 蔡逸君
【旅行關鍵詞】臉 魏瑛娟
【微塵】買名兼盜名 陳淑瑤
【波動】班傑明之歌 穀雨
【剪貼冊】我阿母買衣記 張輝誠
【封面人物】一個只受愛驅使的真正男人──切‧格瓦拉
直到邁向永遠的勝利──寫在日記之前 卡密諾‧格瓦拉
玻利維亞日記 切‧格瓦拉
玻利維亞──獻給解放者的國度 陳小雀
與切相遇在字裡行間 陳小雀
完美的人──切‧影‧語‧錄 切‧格瓦拉/著 丘德真/譯
切,一份斷想 戴錦華
繼續上路,不斷革命──廖偉棠VS.張鐵志對談切‧格瓦拉...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雜誌商品,恕不提供10天猶豫期退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