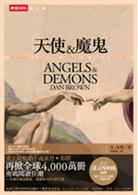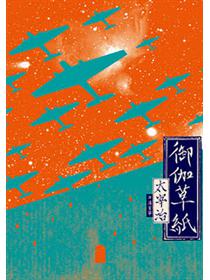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編輯室報告】邊緣者的立場──大江健三郎訪台暨創刊六週年感言 /副總編輯周昭翡
一九九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將在十月五日首度訪台。他在《小說的方法》中,引述《聖經‧約伯記》的話:「唯有我一人逃脫,來報信給你。」這正是他飽含深意的創作準則。也說明了小說家以纖細的情感,獨特的語境,檢視時代的苦惱,擔負「唯一報信人」的責任,並直率表達個人的立場。大江健三郎始終維持著邊緣者的立場。
〈日本屬於沖繩〉寫於一九六九年,《沖繩札記》的第一章。是大江三十多歲時多次前往該地,反覆思考沖繩問題的源頭。他透過沖繩歷史人物和社會運動,反映日本與沖繩間的矛盾。特別是二戰結束前,沖繩渡嘉敷島集體自殺事件。大江提出證據,認為軍方主導集體自殺,後來被軍人遺族控告其毀謗先人名譽,震撼全球,此案至今猶在最高法院審理中。
大江不曾改變立場,始終站在邊緣者的角度觀看,對日本及日本人的問題,深刻提出批判觀點。這在他與薩伊德、鈞特‧葛拉斯的書信往返中表露無遺。他們談論人類歷史的複雜性,還有戰爭帶來難以癒合的心靈創傷。
他曾在小說中描寫過洪水把一個村莊與另一個村莊分離開來的場景。他說,咆哮的洪水,或許就是少年時代所體驗到戰爭的某種象徵,洪水噴湧而洩的具體場面非常鮮明。戰爭時期糧食短缺,靠澱粉乾度日。曾經河水裡帶刺的水藻刺痛了全身,類似的記憶在身體裡延續著,最後走進大江浩瀚的文學創作中。
製作大江健三郎專輯的此時,台灣遭逢莫拉克風災肆虐,災情不斷擴大,本刊攝影主編陳建仲獨自前往災區,記錄了許多畫面,河川山水的變貌,滿目瘡痍的家園,讓我們的心情隨之起伏洶湧。即將訪台的大江健三郎,彷彿報信人般給我們帶來重要訊息。他在諾貝爾文學獎得獎演說辭中,以〈我身於曖昧的日本〉為題,說到他相信藝術不可思議的治癒力量,並「將以自己羸弱之身,以凌遲的痛苦,承受二十世紀科技與交通的畸形發展所累積的禍害。」
他立於邊緣者的立場,帶著與苦難交纏、搏鬥而充滿堅強意志的文學內涵,鼓舞著我們,在山窮水盡的絕境中繼續保持希望與勇氣。
今年九月,《印刻文學生活誌》創刊六週年,六度獲得金鼎獎最佳文學及藝術類雜誌肯定,我們將獎金捐出賑災。也要感謝這六年來各界給予的支持與鼓勵。本期增加篇幅,推出更多精采之作:甫以《西夏旅館》獲得金鼎獎最佳著作人獎的駱以軍,發表新作〈藍天使〉,讀者或可從故事中,隱約窺見這位台灣當代重要小說家接續的轉變與關注的面向;莊新眉踏尋沈從文原鄉寫作的盡頭,來到抒情文體家筆下的湘西,她以兩萬字長文再現這方邊緣之地的勞動意義和生存現實;香港作家西西「中國古代服飾熊」系列,記載自己因復健需要而縫製毛熊的因緣,她以歷史人物為主題,將背景掌故嵌入日常生活,親和力十足。
每一個文學作者,都是獨特、唯一的報信人。作為一份文學雜誌,我們期許像一座結實的橋樑,連接文學的讀者與作者,也連接文學的過去和未來。期許不斷將寫作者獨特的立場傳達出來,特別是邊緣者的立場。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編輯室報告】邊緣者的立場──大江健三郎訪台暨創刊六週年感言 /副總編輯周昭翡
一九九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將在十月五日首度訪台。他在《小說的方法》中,引述《聖經‧約伯記》的話:「唯有我一人逃脫,來報信給你。」這正是他飽含深意的創作準則。也說明了小說家以纖細的情感,獨特的語境,檢視時代的苦惱,擔負「唯一報信人」的責任,並直率表達個人的立場。大江健三郎始終維持著邊緣者的立場。
〈日本屬於沖繩〉寫於一九六九年,《沖繩札記》的第一章。是大江三十多歲時多次前往該地,反覆思考...
章節試閱
封面人物】創傷與救贖——專訪大江健三郎
吳佩珍、彭小妍、陳世昌‧專訪 唐顥芸‧整理
一九九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即將於二○○九年十月五日至九日來台訪問,並參加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北京社會科學院外文所聯合舉辦之大江健三郎研討會,擔任主題演講。文哲所研究員彭小妍、政治大學助理教授吳佩珍及《聯合報》駐東京特派員陳世昌,於四月二十七日前往大江先生在東京的住所,簽訂邀請合約。大江先生原先答應接受兩小時的採訪,見面後相談甚歡,欲罷不能談了三小時。
節錄
《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彭:
有關您二○○七年的小說《優美的安娜貝爾‧李——寒徹戰慄早逝去》,有幾個問題想請教。
大江:
請說。
彭:
剛剛也提到,您和朱天文女士的小說類似的地方是互文性,經常引用世界各國的文本。您這本書中,互文的用法非常自由、豐富,可是同時故事結構也很嚴密,所有的互文都指向於女主角的心理創傷。也就是說互文和故事性之間取得很好的平衡,形成極大的張力。互文性強的作品,有時候故事的結構容易變得散漫,可是您這部作品卻沒有這個問題。這是寫作過程自然的發展,還是原本特殊的設計?關於這點想請您談談。
大江:
這一點我也想說說。我引用的作家有很多。以我這部作品來說,比如說用了三個文本,像是德國的作家克萊斯特,美國的詩人愛倫坡,還有其他許多的文本。就像您現在說的,我在這部小說裡面,想把整體的結構弄得很緊密,然後才放入許多文本。如果這樣做,有時候小說篇幅就會拉長,比如《憂容童子》;本來是想盡量寫少一點的。所引用的文本,比如說愛倫坡的詩〈安娜貝爾‧李〉,這首詩的日文翻譯也非常有意思。
吳:
是日夏耿之介的翻譯。
大江:
對,他的翻譯。其次是德國克萊斯特的小說。我對每一個文本都有很強烈的關心。比如說愛倫坡的詩,是怎樣束縛了大江這個作家,我很清楚地寫在裡面,一方面,愛倫坡跟克萊斯特,清楚地表現出他們的不同,把他們都寫在小說裡。到了小說的最後,把大江、愛倫坡、克萊斯特轉化成電影、戲劇,各式各樣的人的詮釋,每個都是獨立的,但又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可以說彭老師所說的是非常正確的。
彭:
您這本小說也經常引用納布可夫的《羅莉塔》。
大江:
是的,納布可夫也是很重要。我想到了一件小事,我曾在美國的大學生活了半年。美國的大學的日本文學研究者是沒有什麼經費的,所以邀我去上課演講結束的時候他們給我一點點謝禮,大概一百塊美金左右,我也拿過七十塊美金的。我們就到餐廳去,每個人約有十六塊美金的預算,點十六塊美金的餐,酒是一罐啤酒,要喝第二罐就要自己付錢,然後大家聊天。那時,薩伊德這個非常棒的學者也在,他是我的好友,已經去世了。還有評論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文學系教授Masao Miyoshi,土耳其拿到諾貝爾文學獎的奧罕‧帕慕克,大概有十人左右。我們猜謎,看某個作家、人物是什麼時候出生的。有人就出題說,有人知道一九三五年出生的精采人物嗎?薩伊德就說,我知道兩個;我也說我知道兩個。薩伊德說是大江健三郎跟羅莉塔。然後我說是薩伊德跟羅莉塔。我跟薩伊德跟羅莉塔都是一九三五年出生的,如果羅莉塔還活著的話就七十四歲了。
彭:
我讀您這部小說,覺得結構的嚴謹就好像偵探小說一樣,您這部小說要解決的那個重大問題,是一點一點抽絲剝繭透露出來的,到最後才發現女主角櫻的創傷到底根源何在。這一點,想問您是不是整部小說寫的時候,目的就是在解決這個創傷?從開始寫的時候就預備這樣寫,還是說寫到後來慢慢的發展出來?
大江:
是後者。我很喜歡克萊斯特的小說,現在日本人不太讀。最初,我想如果寫克萊斯特的事,日本人會如何解讀,因此出現了將他的小說改編成為世界性電影的情節。其中我想寫一個女主角,是電影的女演員。在寫的過程中,櫻這個人物在我心裡變得越來越具體,不斷成長。然後我在思考這個人物的時候,就想到她是小時候受過心理的創傷,這是因為小時候的我也有心理的創傷。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日本戰敗,而日本侵略中國,把台灣變成殖民地,所以中國人心理的創傷是更大的,台灣人也是,韓國人也是,大家都有心理的創傷。日本人有,我也有。對我來說,本來戰爭的敵國變成來占領我們,那時我十歲。他們建了圖書館,我從十二歲到十三、四歲,就很狂熱地在那圖書館讀英文書。所以對我來說,美國,首先是和日本打仗的國家,然後是占領日本的國家,在這點上,我在從事學生運動的時候也反對美國的政治,所以是很複雜的。而同時我十三、四歲又常去美國的圖書館,在那兒讀書,像是愛倫坡等,可以說是在那兒受到教育。所以在我的心中,美國是很有吸引力的,同時又很可怕,從小時候就這樣覺得。我小時候日本與美國打仗,那之後美國和日本又有很緊密的關係,日本的政治一直在美國的國際政治的影響下一路走來,始終沒有從美國獨立出來。所以我在思考女主角如果受到心靈創傷會怎麼樣的時候,想到一起製作電影的情節,然後她的心靈創傷在拍電影的過程才逐漸被發掘出來。我並不討厭偵探小說,偵探小說家跟我們純文學作家、普通作家的寫法不一樣。偵探小說家是在一開始就知道最後的謎底,如果是一個女性發現她的心靈創傷,偵探小說家從一開始就很清楚知道這個創傷是什麼,可是讀者不知道。偵探小說一開始就告訴讀者有這個創傷,我們純文學作家想寫的則是和自己相近的真實人物,在寫的過程中,自己去發現這個女子有過心靈的創傷,最後發現這個心靈創傷是如何來的。小說裡面,在製作電影的過程中,女主角櫻自己去克服、解決這個創傷。然後我想像她從自己的心靈創傷解放出來的瞬間,是在鄉下的森林裡,一邊製作電影,然後得到解放的場景,我就是這樣去寫的。我小時候有時會看到美麗的日本少女跟美國兵走在一起,她們穿著美國送來的漂亮舊衣,而我們所穿的則是破舊的衣服,而這啟發了我的構想。
最新小說《水死》
彭:
在《優美的安娜貝爾‧李》中,女主角櫻是國際大明星,可是到最後解決她的心靈創傷的,是大江先生母親和祖母所代表的敘事傳統。這好像是大江先生您作品一貫的特色,無論您如何引用國際性的文本,到最後都回歸到您四國故鄉的敘事傳統裡面。您自己是否覺得,您寫小說也是受到這種四國女性敘事傳統的影響?
大江:
是的。我現在正在寫一本小說,叫《水死》,是我最後的小說了。本來想寫我的父親,可是在寫的過程又發現不一樣的東西。特別是我的母親,年輕的時候,她朋友跟著丈夫去上海的貿易公司工作。她的朋友在那裡生產時,一個人覺得寂寞,所以叫我在四國的母親也去。過了一年,我母親都沒有回來。後來是我父親出國去帶她回來的。那是一九三三、三四年,我是三五年出生的。如果我母親還在上海的話,就沒有我了。我本來是想寫父親、母親的故事,寫了三分之一。可是,我從小就聽說我母親有一些資料,收在紅色的行李箱裡,是她從上海帶回來的。我母親去世大概過了十年後,我妹妹本來保管那個行李箱,就給了我。我打開來看,裡面竟然什麼重要的東西也沒有。所以這部小說就寫不下去了。於是我就轉換了一下,寫一位小說家「長江」想寫一部叫《水死》的小說,回到四國跟新結識的朋友一起做戲劇。後來這部小說的重點發展成寫那做戲劇的人的痛苦經驗。現在正在寫,開始要寫後半,是關於此痛苦真相的發覺,而這才是這小說的重要部分。這正好跟《優美的安娜貝爾‧李》的形式很相近。我想將這兩部小說結合成一個作品,以二部曲形式呈現。
彭:
昨天我們去看了歌舞伎。歌舞伎裡面表演的都是男性角色,但是在您的小說裡面您母親的這個劇團,都是女性在演出,而且觀眾也都是女性,男性還不能去看。這是不是要表現一種邊緣性?也就是說,日本的歌舞劇傳統的主流是男性演員,而您這部小說裡面的劇團是女性的世界。您是不是蓄意在創造一種邊緣性,來跟主流對抗?
大江:
是的。在日本的近代史裡,女性是被歧視的弱勢,可說是社會的邊緣。可是女性確實保有一些文化,我的祖母創作了類似歌舞伎的戲劇,我的母親對此戲劇也很擅長。女性擁有日本民俗性的、民眾的記憶,所以我想描寫女性記憶形式的民眾記憶這樣的東西。大約這一百二十年來的日本近代史,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成為新的國家,接二連三地侵略亞洲。侵略亞洲這類歷史,是以男性為中心的歷史,以男性為中心的記憶。反過來看,女性到底有怎樣的記憶?當然,日本有很多女性學者已在研究。可是我以一個男性作家的身分,想要寫我自己的母親、祖母是怎樣活過近代史,如何以女性的方式去記憶。在新的小說裡也是,特別是寫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結束的時候,日本人有怎樣的反應,雖說我父親在當日便已經過世了。大致是以我的父親為主角去寫,可是在寫的過程裡,父親的歷史本來應該是以男性的歷史去寫的,卻發現那個歷史是留在母親以及祖母的記憶裡的。還有我的妹妹,站在女性的立場去思考我的父親是怎樣活過來,怎樣死去的。身為男性作家想要去發掘女性所見證的近代史,但是便會遭遇女性的記憶,女性所記憶的歷史。也因此,像我這樣年過七十歲的作家,總是一面寫,一面想著:這是最後一部了,大概不會再寫小說了吧,不久就會死了吧。我是這樣設定的。所以寫了這部小說,我想應該就不會再寫了。
吳:
《優美的安娜貝爾‧李》的寫法跟早期比較,改變了很多。
大江:
是啊,漸漸改變,也漸漸沒人要看了。
吳:
哪裡,我其實很驚訝,和早期像是《飼養》、《奇妙的工作》的作品比較,對我一個外國讀者來說,感覺變得比較容易讀了。早期的作品非常難讀。
大江:
是嗎?我可以說就是一個四國鄉下什麼也沒學過的小孩,受到自己母親、祖母的影響,然後一個人學習外國的小說,讀外國的書和詩,然後學法文。由於在美國占領下,所以不想學英美文學。到了二十歲,成為小說家,可以說是一個外行的小孩開始寫小說,然後二十二、三歲,我自己慢慢思考小說是什麼。學習如何寫小說就是我的人生,六十年來一直不間斷,一直書寫。所以,比如說日本的作家常去酒吧喝酒、玩樂、戀愛等等,我沒有什麼玩樂的記憶,成年以後就是在家裡學習、寫小說。不過,比如說憲法的問題、沖繩的問題、廣島的問題,這些有必要的事我會去做。在這之外,小說的學習就是我的人生了。這樣一點一滴寫著小說,真的是很無趣的人生。那像彭老師這樣,思考我的小說是如何寫出來的;有這樣的讀者,是我最高興的事。我一直在思考的就是小說該怎麼寫。現在日本的年輕作家,覺得小說是很容易寫的,或者是小說寫得簡單才好。連讀者也是這樣的,覺得為什麼非要讀這樣難的東西不可,就對我生氣。
彭:
您的小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虛構」跟「現實」的交錯。大江先生、夫人、孩子都是小說裡面的人物。《優美的安娜貝爾‧李》中,主要的角色像木守和櫻,他們兩個人有原型嗎?還是說,的確是有原型,但是經過改造以後,再放到小說裡?
大江:
沒有原型。我的小說是以我這樣的作家、我的妻子、我的家庭為基礎去寫的,這是我寫小說的方式。可是在這裡面又加入新的虛構去寫。日本一直有個「私小說」的類型,加藤周一很討厭這種類型,總是寫我自己個人如何如何。比如剛才說的台灣作家寫自己的歷史,寫從中國來到台灣的外省人如何在台灣生活的自傳性小說。我覺得有趣的是這種自傳性小說的特徵。而這當中,雖是自傳,但寫自傳的人,本身都像是虛構的人物,如同我們從來不認識的人般。無論是年輕的作家、男性作家或是女性作家,寫著如自己的自傳般的小說,將中國的問題、台灣的問題以及何謂人的問題,非常嶄新的表現出來;對這一點我非常感興趣。而所謂自傳,首先是要把自己當作虛構的人物去創作、去塑造。比如說鈞特‧葛拉斯,還是福克納的作品,雖然反映他們自己的生活,但是也創造出虛構的人物。我認為日本人的私小說,完全不批判自己,只是把自己怎樣生活寫出來而已,這和德國的 Ich-Roman或是美國的 I-Novel是不一樣的。戰爭時期,我還是小孩,也不知道日本正在做些什麼樣的事。然後戰爭結束,美軍來了,帶來了新的文化,我看到新的世界。我是這樣活過來的,我想寫這樣的一個人的自傳,所以開始寫小說。可是不能只停留在自己的生活,而是以自己的生活為基礎,不斷加入虛構的人物,這樣的寫法便是我小說的形式。例如《優美的安娜貝爾‧李》裡的櫻,以及目前的小說寫我死去的父親,同時也打算寫更年輕的世代。這不是明治晚期以來的「私小說」,而是透過描寫像我這樣的人物,清楚地表現出現實,同時也要不斷加入新的人們,這就是我想要寫的小說...(未完待續)
【封面人物】國際視野中的大江健三郎文學——研討會開幕致詞 /東京‧大江健三郎‧文
東京‧大江健三郎‧文 唐顥芸‧譯 吳佩珍、彭小妍‧修訂
我今天站在這裡,不僅深深地感動,還思考著接下來必須完成的重要任務。衷心感謝各位的邀請。我可以看到我想念的、敬愛的朋友們的臉龐。從中國大陸來參與會議的各位,從莫言先生──對我而言,他是中國文學的、更是世界文學的重鎮──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研究所的學者教授們,可說是我個人的老朋友了,都聚集在此。
台灣優秀作家們的作品,我已經透過翻譯,有了廣泛而深刻的認識。接下來將與這些作品的作家們面對面,是多麼令人興奮的時刻。而和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的學者教授們,則即將展開全新的交流。我滿懷期待,首先在此與大家致意。
本研討會的主題,是「國際視野中的大江健三郎文學」。被選為這種主題的作家,自己是不是適合,我沒有什麼自信。我想,如果我是村上春樹的話,不知會以怎樣輕鬆的心情,站在這兒接受各位的歡迎。即使如此,我還是提起勇氣,衷心期盼地來到台灣參加這個研討會,有以下幾個理由:
第一,最近十年,我作品的新譯本,最多的就是中文版。所以我想向將我的作品翻譯成中文的翻譯家們,表達感謝之意。
第二,我特別希望,自己的文學可以放在國際的視野中討論。當然,也包括批判在內。長期以來,我透過各式各樣大量的世界文學,塑造了自己。我在文學上的出發點,是少年時期讀過的魯迅、馬克‧吐溫、拉格洛芙(Selma Lagerlof)。除此之外,我透過日文翻譯,閱讀各種外語文學,由此建構了我的日文文體。當然,我也向日本的近現代文學的作家們學習,但他們也深受海外文學的影響。此外,我還直接透過幾種外語閱讀,嘗試確立自己的文學。此種種現在仍持續進行著。
透過「國際視野中的大江健三郎文學」會中的討論,領悟最多、最尖銳、也最深刻的,恐怕是我自己。而作為一個被研究、被批判的對象,我也會竭盡所能,回答各位的問題。
第三個理由,是我很關心華文文學在當代世界文化中所扮演的各種角色。我不是政治人物,而是從事文學的人。所以我所關心的,不是某個國家的文學,而是某個語言的文學。舉辦本會議的各位所使用的「兩岸的」這個辭彙,讓我頗受感動。因為我對「兩岸的」華文文學懷抱同等的關心。此外,對於在美國、法國持續創作華文文學的優秀作家,我也心懷尊敬和友情。
因此,對這樣具體內含「國際視野」、十分活躍的華文文學家和研究者所舉行的討論,我會特別關心,應該是很自然的。
除此之外,尤其是對我這一代日本人而言(我是為數越來越少的倖存者),「兩岸」的民眾和我們日本人之間沉重而痛苦的過去,以及仍承受著負面遺產的現在,是一種宿命。但此中也蘊含了對未來的希望,這也是一種宿命。身為日本小說家、知識分子,能夠來此參加研討會,而且被選為討論的主題,我心中感慨萬千。我想先跟各位表達這種心情,也希望我能符合各位的期待。謝謝大家。
編案:「國際視野中的大江健三郎文學」研討會將於2009年10月6日至7日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召開,並舉辦「大江健三郎特展」9月29日至10月8日假文哲所。
封面人物】創傷與救贖——專訪大江健三郎
吳佩珍、彭小妍、陳世昌‧專訪 唐顥芸‧整理
一九九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即將於二○○九年十月五日至九日來台訪問,並參加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北京社會科學院外文所聯合舉辦之大江健三郎研討會,擔任主題演講。文哲所研究員彭小妍、政治大學助理教授吳佩珍及《聯合報》駐東京特派員陳世昌,於四月二十七日前往大江先生在東京的住所,簽訂邀請合約。大江先生原先答應接受兩小時的採訪,見面後相談甚歡,欲罷不能談了三小時。
節錄
《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彭:
有關您二○○七...
目錄
【編輯室報告】邊緣者的立場──大江健三郎訪台暨創刊六週年感言 周昭翡
【語鋪子】地下鐵事件 編輯部
【旅行關鍵詞】光之三 魏瑛娟
【微塵】畫牆與燈 陳淑瑤
【封面人物】大江健三郎
我身於曖昧的日本──大江健三郎一九九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受獎紀念演講 許金龍/譯
沖繩札記 大江健三郎/文 陳言/譯
大江與愛德華‧W‧薩伊德的往返書信 楊孟芳/譯
大江與鈞特‧葛拉斯的往返書信 郭玲莉/譯
筆耕者大江健郎手稿展
創傷與救贖──專訪大江健三郎 吳佩珍、彭小妍、陳世昌/專訪
「國際視野中的大江健三郎文學」研討會開幕致詞 大江健三郎
特殊的翻譯因緣 劉慕沙
我是唯一一個報信人 莫言
小說的誓言──以「晚期風格」致大江先生 朱天文
【特選】山脈 張萬康
【世間的名字】男高音 唐諾
【專欄:理論大師的文藝情愫】阿多諾:琴鍵上的辯證法 楊小濱
【圖與話】
中國古代服飾熊 西西
婦好 鍾離春 莊子 司馬相如、卓文君 嵇康、阮咸 風塵三俠
毛熊與漢服──何福仁對談西西
【特別刊載】文學的湘西──尋沈從文筆下故土舊人的腳步而去 莊新眉
【演講】「美麗的」日本與我 朱天心
【愛說書】
緩慢的人 何致和
小城畸人 丁名慶
【八八水災】八八水災我們一起度過 陳建仲╱攝影 蔡逸君╱文
【特稿】周夢蝶──時間在身上做著夢 曾進豐
【回聲集】張愛玲的考題 周芬伶
【馬戲團】粉紅雀‧地球馬戲團7 Chen肯吉
【文化專刊】等待一封寫給記憶的情書,在遠方──尋找台灣文學的「故事力」
【那些人那些事】山東白、四川菜與台南外省麵
──記一個府城少年在昇平年代的味覺探索 鄭鴻生
【場邊故事】真正的棒球寫作 余文馨
【CEO生命閱讀】陶爸‧陶冶‧樂陶陶──專訪奇哥董事長陶傳正
田運良、林瑩華╱採訪 蘇惠昭╱文
【九月小說】藍天使 駱以軍
【編輯室報告】邊緣者的立場──大江健三郎訪台暨創刊六週年感言 周昭翡
【語鋪子】地下鐵事件 編輯部
【旅行關鍵詞】光之三 魏瑛娟
【微塵】畫牆與燈 陳淑瑤
【封面人物】大江健三郎
我身於曖昧的日本──大江健三郎一九九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受獎紀念演講 許金龍/譯
沖繩札記 大江健三郎/文 陳言/譯
大江與愛德華‧W‧薩伊德的往返書信 楊孟芳/譯
大江與鈞特‧葛拉斯的往返書信 郭玲莉/譯
筆耕者大江健郎手稿展
創傷與救贖──專訪大江健三郎 吳佩珍、彭小妍、陳世昌/專訪
「國際視野中的大江健三郎文學」研...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雜誌商品,恕不提供10天猶豫期退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