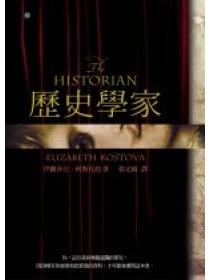榮獲法蘭西文化獎最佳外語小說
美國當代重要作家保羅‧奧斯特經典之作
版權售出三十餘國,全球長銷二十餘年
三段追索的故事,改寫了人類對存在的呼求......
《紐約三部曲》由三個人物和三件任務組成,跳離了傳統偵探小說的解謎模式,用大膽、聰明的鋪陳,使真相如萬花筒般眩目迷離,藉以探尋身分、認同和存在的難題,開創獨樹一格的小說風格。
〈玻璃之城〉這一切,都從一通打錯的電話開始。匿名小說家化身為偵探,建立多重身分,在城市中追尋等待,然而他等到的卻是……
〈鬼靈〉私家偵探「阿藍」日夜監視對街的「阿黑」,「阿黑」也從對街望向窗外。在監視者與被監視者之間,可能建立什麼樣的聯繫?
〈禁鎖的房間〉范修失蹤了,留下妻兒和作品,任由童年好友闖入他的生活,也一步步走進他謎樣的陷阱……
作者簡介:
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
1947年生於美國紐澤西州,現居布魯克林。是小說家、詩人、翻譯家和電影編劇,曾和王穎合導電影「煙」,並自編自導The Inner Life of Martin Frost。
《紐約三部曲》為其享譽國際的經典作品,另著有《月宮》、《幻影書》等十餘本小說。其他作品有《孤獨及其所創造的》、《失.意.錄》、《布魯克林的納善先生》,以及詩集、評論集等。奧斯特曾獲頒「法蘭西文化獎」、美國文學與藝術學院頒發的「莫頓.道文.薩伯獎」、法國文壇四大文學獎之一的「麥迪西獎」等,更在二○○六年榮獲有「西班牙的諾貝爾獎」之稱的「阿斯圖里亞斯王子獎」,被譽為最重要、最受歡迎的當代作家之一,作品已被譯為三十餘種語言。奧斯特的作品常探討人生的無常與無限,筆下的主角也常思考自我存在的意義、尋找自己的人生位置。他擅長實驗性的寫作風格,並在流暢的文字間,暗蘊值得再三玩味的人生哲理。文壇曾比喻他是「穿膠鞋的卡夫卡」。
章節試閱
事情的開端是一通打錯的電話,在死寂的夜裡響了三聲,話筒另一端要找的人並不是他。很久以後,他思索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種種,並下定結論:這事除了純粹的機緣巧合之外,沒有別的解釋。不過,那是很久很久以後的事了。起初,就只是單純的一個事件,與這個事件所帶來的後果,無論事情的發展是不是會有所不同,也不論這一切是否早在電話那頭的陌生人說出第一個字時就已注定,都不是問題。問題在於故事本身,至於有沒有意義,也和這個故事沒有關係。
對於昆恩這個人,我們毋須太過費心。他是誰、從哪裡來、做過什麼,都不是太重要。例如,我們知道他三十五歲。我們知道他結過婚,有過小孩,但是老婆孩子都死了。我們知道他寫書,更精確地說,我們知道他寫推理小說,用威廉.威爾森的筆名發表,平均一年寫一本,賺的錢足夠讓他在紐約的小公寓裡過上差不多的生活。他一年花在寫書的時間頂多只有五、六個月,所以其他時間想做什麼都可以。他大量閱讀,逛畫展,看電影。夏季,他看電視轉播的棒球賽;冬季,他去看歌劇。然而,他最愛的是散步,無論晴雨,不分寒暑,他幾乎每一天都出門在城裡散步。他倒也沒真的走到哪裡去,就只是隨興之所至,兩條腿帶他往哪裡去,就到哪裡去。
紐約是個取之不竭的空間,是一個走不盡的迷宮,無論走得多遠,無論對鄰里街巷有多深的了解,他始終擺脫不了迷失的感覺。不僅是在城裡迷了途,甚至也在心裡找不到自己的存在。每回散步,他彷彿拋開了自己,藉著讓自己身陷街道的車流人龍,也藉著將自己化簡成一雙窺伺的眼,他擺脫思考的義務,並藉此為自己帶來祥靜,讓內心得以放空。整個世界在他之外、在他周遭、在他面前,那不斷變化的迅捷速度,讓他不可能在任何單一事物上耽溺過久。他把一腳抬起放到另一腳前面,讓自己隨著身體四處晃蕩。動才是本質。因著漫無目標的散步,所有的地方都變得毫無二致,身在何處再也無關緊要。散步散到最盡興時,他覺得自己彷彿置身於虛無之境,而這就是他最終所追求的:置身於虛無之境。紐約就是他在自身周遭所建立的虛無之境,他明白自己再也不想離開此地了。
過去,昆恩比較有企圖心。年輕的時候,他出版了好幾本詩集,寫過劇本和文學評論,也做了不少長篇的翻譯,但是一夕之間,他突然全放棄了。他對朋友說,一部分的他已經死了,他不想讓那個自我陰魂不散。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他開始用「威廉.威爾森」這個筆名。昆恩再也不是那個能寫書的人,雖然就很多方面來說,昆恩還繼續存在,但他再也不為其他人而存在,他只為自己而活。
他繼續寫作,因為這是他覺得自己唯一能做的事。推理小說似乎是個合理的出路。推理小說所需要的迷離情節,他輕輕鬆鬆就寫得出來,而且不費吹灰之力就寫得很好。對於寫出來的東西,他並不認為自己是作者,也就不覺得負有責任,因而打從心裡就沒有挺身捍衛的動力。畢竟,威廉.威爾森是虛構出來的,儘管出自昆恩本人之手,現在卻已經擁有獨立的人生了。昆恩很敬重他,有時甚至還很羨慕,可是從沒欽羨到相信自己和威廉.威爾森是同一個人。正因如此,他始終隱身在筆名背後,未曾走到幕前。他有個經紀人,但兩人素未謀面,往來僅限於書信,昆恩還為此在郵局租了郵政信箱。出版社也一樣,支付費用、款項和版稅都透過經紀人轉交給昆恩。威廉.威爾森的作品從來不印作者的照片或生平簡介。威廉.威爾森從未列名任何作家名錄,也從未接受專訪,收到的所有信件都交由經紀人的祕書回覆。就昆恩所知,他的祕密無人知悉。起初,朋友們知道他放棄寫作時,都會問他打算如何維持生計,他總是拿同一套說詞搪塞:他繼承了妻子的信託基金。事實上,他的妻子根本就沒有錢,並且他也不再有任何朋友了。
至今五年多了,他不再那麼常想起兒子,不久之前,他把妻子的照片從牆上取了下來。每隔一段時間,他會突然有一種將三歲男孩摟在懷裡的感覺,但那不算是他心裡真正的想法,甚至也算不上是回憶。那只是一種肢體的感覺,是過往時光在身上所留下的烙印,他完全無法控制。如今,這樣的時刻不再那麼常出現了,最主要是事情似乎開始因他而改變了。他不再希望自己死去,但也不能說他很高興自己還活著,可是至少不再因為自己活著而怨天尤人。他活著,這個牢不可破的事實慢慢地讓他著迷,彷彿他已經設法活過自己的大限,過著某種近似死後的生活。他夜裡不再亮著燈睡覺,也已經好幾個月不記得自己做過的夢。
夜裡,昆恩躺在床上抽菸,傾聽雨珠打在窗上的聲音。他很想知道雨何時停,也在心中暗忖,自己早上會想散步散得長一些或短一些。有本翻開的《馬可孛羅遊記》面朝下躺在他身邊的枕頭上。自從兩個星期前寫完威廉.威爾森最新的作品之後,他就一直提不起勁來。他筆下的敘事主角私家偵探麥克斯.渥克破解了一系列精心策劃的犯罪事件,挨了不少揍,歷經數次九死一生的際遇,他的奮力而為,搞得昆恩有點筋疲力竭。幾年來,渥克變得和昆恩極其親近,對他來說,威廉.威爾森一直都只是個抽象的人物,但渥克卻有了生命。在昆恩逐漸發展出來的三重人格中,威爾森扮演了某種腹語者的角色,昆恩自己是個啞巴,而渥克則是那個表明行動意旨、栩栩如生的嗓音。如果威爾森是個幻覺,那麼他的存在就只是為了證明其他兩個人存在的合理性。如果威爾森不存在,那麼他就只是一座橋樑,讓昆恩可以透過他而走向渥克。慢慢地,渥克在昆恩生命中逐漸占有一席之地,是他精神上的兄弟,孤寂之中的同志。
昆恩拿起《馬可孛羅遊記》,重新讀第一頁:「吾人將如實記述眼所見、耳所聞,爰本書或為忠實紀錄,絕無任何虛構偽造。有閱讀本書或聽聞本書者,皆可信其為真。」正當昆恩開始思索這幾個句子的意義,在心中反覆思忖作者信誓旦旦的保證時,電話響了。很久之後,在他可以重新拼湊出當晚的原貌時,他會記得自己瞥了時鐘一眼,看見時間已過十二點,很納悶誰會在三更半夜打電話給他。他心想,最可能的是:壞消息。他從床上爬起來,光著身子走向電話,在鈴響第二聲的時候拿起話筒。
「喂?」
另一端沉默良久,有那麼一會兒,昆恩以為打來的人已經掛掉電話了。此時,話筒裡響起一個昆恩從未聽過的嗓音,彷彿從遙遠的地方傳來。那聲音既機械化又充滿情感,像耳語般低微卻又清晰可聞,而那聲調,讓昆恩分不出講話的到底是男是女。
「喂?」那聲音說。
「哪位?」昆恩問。
「喂?」那聲音又說。
「我在聽。」昆恩說:「哪位?」
「是保羅.奧斯特嗎?」那聲音問:「我要找保羅.奧斯特。」
「這裡沒這個人。」
「保羅.奧斯特,奧斯特偵探社的保羅.奧斯特。」
「對不起。」昆恩說:「你一定是打錯電話了。」
「這事很緊急。」那聲音說。
「我幫不上忙。」昆恩說:「這裡沒有保羅.奧斯特這個人。」
「你不明白。」那聲音說:「就快沒有時間了。」
「那我建議你掛掉重打。這裡不是偵探社。」
昆恩掛掉電話。他站在冰冷的地板上,低頭看著自己的腳、膝蓋,和他軟趴趴的陰莖。
有那麼一下子,他很懊悔自己對打電話來的人那麼不客氣。他想,能和那人再多周旋一會兒,一定會很有意思。說不定他能在這個案子裡找出蛛絲馬跡—或許還能幫上一點忙。「我得學會讓自己站著的時候腦筋轉快一點。」他對自己說。
昆恩和大多數人一樣,對於犯罪勾當幾乎一無所知。他沒謀害過任何人,沒偷過任何東西,也不認識任何犯過類此罪行的人。他沒進過警察局,沒見過任何私家偵探,也沒和任何罪犯講過話。他對這方面所知的一切,都是從書本、電影和報紙上看來的。然而,他並不認為這算得上是障礙。他所寫的故事讓他感興趣之處,不在於它們和這個世界的關係,而在它們和其他故事之間的關係。遠在成為威廉.威爾森之前,昆恩就已經是推理小說的愛好者。他知道大部分的推理小說都寫得很爛,禁不起最輕微的檢驗。然而,這種形式的小說就是能吸引他,只有極少數爛到無以復加的推理小說,他才會拒絕讀。儘管他對其他書籍的品味極其嚴苛,要求高到器量狹小的地步,然而他對推理小說幾乎是來者不拒。心情好的時候,一口氣讀個十本、十二本都沒有問題。饑渴的感覺緊緊攫住他,拚命渴求某種特殊的食糧,他要一直吃到再也吃不下為止。
他之所以喜歡推理小說,是喜歡書中那種豐足而簡約的感覺。好的推理小說絕不浪費筆墨,每一字每一句都有其重要性,即便目前不具重要性,未來也將會累積成某種重要性。書裡的世界活了起來,和祕密、矛盾交織著種種可能性。所見所說的每一件事,即便是最微不足道、最細瑣的事情,都和故事的發展有關係,任何細節都不容忽視。一切都變得事關重大,故事的重心會隨著推動情節的每一個事件而改變。因此,重心無所不在,在故事結束之前,根本無從畫成任何一個圓。
偵探是一個去看、去聽的角色,他穿透物體與事件所構成的迷障,推敲出想法,把所有的事情拼湊起來,釐清道理來。事實上,作者與偵探的角色可以互換。讀者透過偵探的眼睛看見世界,彷彿首次體驗到種種細節的湧現。他會察覺到周遭的事物,彷彿聽見它們對他說話,彷彿因為他此刻的注意,讓這些事物開始變得別具意義,而不只是單純的存在。「Private eye」(私家偵探),這個詞在昆恩看來有三重意義。「eye」,唸起來像字母「i」,代表了「investigator」(調查者),而大寫的「I」(我)是躲在會呼吸的自我之中那個小小的生命蓓蕾。同時,這也是作者的眼睛(eye),一隻從作者內在往外望向世界的眼睛,要求這世界在他面前展露真面目。五年來,昆恩始終活在這種雙面人生裡。
當然,他很久之前就不再認為自己是真實的了。倘若他現在還算活在世上,那也僅僅是間接地透過麥克斯.渥克這個想像人物而存在。他的偵探必須是真實的,推理小說的本質如是要求。倘若昆恩允許自己消失,退居於與世隔絕的陌生環境之中,渥克卻還是繼續存在於其他人的世界裡,而且昆恩愈是消聲匿跡,渥克在這世界上的存在似乎就愈持久。昆恩不時覺得自己格格不入,但渥克卻敢作敢為、快人快語,無論身處何地都輕鬆自在。對昆恩造成問題的一切,在渥克身上卻顯得理所當然,他在冒險歷程中應付暴力場面的漠然輕鬆,每每令創造他的人為之感佩。要說昆恩希望自己變成渥克,或是想像自己像他那樣,都不見得正確,但是在寫作的時候假裝自己是渥克,知道自己願意的話可以成為渥克(即便只在內心裡),都能讓昆恩覺得安心。
那天夜裡,終將沉沉入睡之際,昆恩試著想像渥克會對電話裡的那個陌生人怎麼說。在他後來遺忘的夢中,他發現自己獨自在房間裡,對著一堵空無一物的白牆開槍。
隔天夜裡,昆恩並沒有心理準備。他反覆思索那個意外,不認為那個陌生人會再打來。結果,他坐在浴室上大號的時候,電話又響了。時間比前一夜晚了點,大概是十二點五十或五十幾分。昆恩在狹小的浴室裡辦大事,《馬可孛羅遊記》翻開攤在膝上,才剛讀到馬可孛羅從北京到廈門的那一章。電話鈴聲格外惹人惱火,要及時接起電話,意味著他得沒擦屁股就衝出去,他可不喜歡在這種狀態下穿過公寓。另一方面,要是他按照平常的速度完事,他就無法及時接起電話。儘管如此,昆恩卻覺得自己並不想動。電話不是他喜歡的東西,他不只一次想拔掉電話。他最厭惡的是電話的專制蠻橫,不僅擁有力量違背他的意願、干擾他正在做的事,而且總是讓他不得不屈服。這一次,他決定力抗到底。但是鈴響到第三聲,他的腸子已經清空了。第四聲鈴響,他已經擦淨自己了。第五聲鈴響,他拉起褲子,走出浴室,不慌不忙地穿過公寓。第六聲鈴響時,他接起電話,但另一端沒有聲音。打電話的人掛掉電話了。
隔天夜裡,他準備妥當,伸展四肢躺在床上,仔細翻看《體育新聞》,等待那個陌生人第三次打來。每隔一會兒,開始覺得緊張的時候,他就起身在公寓裡踱步。他放了海頓的歌劇「月世界」(Il Mondo della Luna),從頭聽到尾。他等了又等,到了兩點半,他終於放棄,上床睡覺。
隔天他又等了一個晚上,再隔天也是,就在他明白自己的揣測完全沒有道理,打算放棄計畫時,電話響了。這天是五月十九日。他記得日期,因為這天是他爸媽的結婚紀念日,或者應該說如果他爸媽還在世的話,就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他媽媽有一回告訴他,他是在她的新婚之夜受孕成胎的。這件事一直很吸引他──竟然可以精確知道他從何時何刻開始存在──多年以來,他也一直偷偷在這一天慶祝他的生日。這一次,電話來得比前兩次稍早一些,還不到十一點,他伸手去接電話時,還以為是別人打來的。
「喂?」他說。
再一次,電話另一端默然無聲。昆恩馬上知道這就是那個陌生人。
「喂?」他又說:「我能幫你什麼嗎?」
「是的。」那個聲音終於說話了,用同樣機械式的低語、同樣絕望的語氣。「是的,現在就需要,不能拖延。」
「需要什麼?」
「講話,現在,現在就要講,是的。」
「你要找誰講?」
「就是那個人啊,奧斯特,說他自己叫保羅.奧斯特的那個人。」
這一回昆恩毫不遲疑。他知道自己想做什麼,既然時機來了,也就做了。
「說吧。」他說:「我就是保羅.奧斯特。」
「終於,我終於找到你了。」他聽得出來那個聲音如釋重負,似乎突然擁有了真切的平靜。
事情的開端是一通打錯的電話,在死寂的夜裡響了三聲,話筒另一端要找的人並不是他。很久以後,他思索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種種,並下定結論:這事除了純粹的機緣巧合之外,沒有別的解釋。不過,那是很久很久以後的事了。起初,就只是單純的一個事件,與這個事件所帶來的後果,無論事情的發展是不是會有所不同,也不論這一切是否早在電話那頭的陌生人說出第一個字時就已注定,都不是問題。問題在於故事本身,至於有沒有意義,也和這個故事沒有關係。
對於昆恩這個人,我們毋須太過費心。他是誰、從哪裡來、做過什麼,都不是太重要。例如,我們知...
推薦序
王寅
詩人、南方周末記者
保羅.奧斯特近身錄
紐約的四月,丁香花已經開放,但是依然春寒料峭。保羅‧奧斯特的家位於布魯克林區公園坡附近,那是一套典型的褐石公寓。
點燃細枝雪茄的奧斯特身穿黑色襯衣,梳油頭,金魚眼,臉膛微紅,聲音渾厚,頭髮已經有些花白,側面望去,臉部輪廓就像古羅馬的塑像。同為小說家的奧斯特夫人希莉‧哈斯特維特(Siri Hustevedt)買回來一大棒梅花和紫色的鬱金香,在敞開式的廚房裡修剪花枝,將花一一插入花瓶,花香瀰漫在有著一百多年歷史的建築空間裡。
一九四七年,保羅‧奧斯特出生於美國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一九六九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大學畢業之後,奧斯特漫遊歐洲,過著漂泊無定的生活,「做了各種各樣瘋瘋癲癲的事」,做過翻譯、棒球運動員、參加舞團的排練等……。
迄今為止,保羅‧奧斯特總共發表了十三部小說、五部傳記、兩本詩集,以及大量的書評和影評文章。奧斯特目前已經躋身一流作家的行列,他在西方,尤其是歐洲擁有眾多崇拜者。《華盛頓郵報》給予他高度評價:「保羅‧奧斯特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具特色而罕見的作家!」日本作家村上春樹也極其欣賞他:「能見識保羅‧奧斯特是我此生的榮幸。」
奧斯特的小說大多有著偵探、犯罪小說的外殼,有「實驗偵探小說」、「後現代偵探小說」之稱,「憑藉著對推理小說的全面翻轉,保羅‧奧斯特開創了一種全新的小說敘述方式。」(《村聲雜誌》)奧斯特的小說中,經常有一個與現實存在疏離感的孤獨偵探,這個普通人常常迷失在城市的人群中,他一直在創造屬於他自己的故事。
《紐約三部曲》之一的〈玻璃之城〉講的是偵探小說家昆恩的故事。一天,昆恩接到一個打錯的電話,電話那頭找一位原名叫保羅‧奧斯特的私人偵探,昆恩冒奧斯特之名去見了這位行為古怪的求助者,這個叫彼得‧史提曼的人是他同名父親的犧牲品,老史提曼是一位瘋狂的神學家,他把兒子長期幽禁。幸虧一場大火,小史提曼才被人救出,老史提曼被法庭認定為精神失常而收容。小史提曼擔心的是瘋子父親即將釋放,他想請偵探盯住老頭子以防再遭威脅。於是昆恩冒充保羅‧奧斯特盯梢老史提曼。有一天他醒來以後,發現老史提曼不知去向,而小史提曼也忽然聯絡不上了,於是昆恩只好轉而監視小史提曼的住所,但他從此以後再也沒有見到小史提曼的蹤影。昆恩失去了隱居的家,甚至失去了原來的容貌,成了一個一無所有的流浪漢。
「事情是從一個打錯了電話開始的,在那個死寂的夜裡,電話鈴響了三次,電話那頭要找的人不是他。」這就是〈玻璃之城〉開頭的一段文字。在回憶這部小說的創作經歷時,保羅‧奧斯特告訴記者,他寫的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在寫第一本書《孤獨及其所創造的》的時候,一天,外面來了一個電話,問奧斯特這兒是不是一個很有名的偵探社?奧斯特回答說不是,然後掛了電話。過了一段時間,又打來一個電話問是不是那個偵探社?奧斯特本能地再次說不是。把電話放下的刹那,他想應該說我就是。於是他就把這次經歷寫成了小說。後來,在寫完《紐約三部曲》之後,他又接到第三次打錯的電話,這次的巧合更為離奇,電話中問奧斯特是不是昆恩先生?
保羅‧奧斯特喜歡故事套故事,一邊是作家創作的故事,一邊是作家自己的故事。他也因此被稱之為製造迷宮的作家。其實,這只是作家包裝作品的手段,奧斯特更著迷的是虛幻的真實、現實的偶然和人生中的悲劇因素。
批評界認為奧斯特深受貝克特和博爾赫斯的師承,但奧斯特心儀的作家卻都是現實主義作家,排在第一位的是賽萬提斯,此外還有狄更斯、托爾斯泰、杜思妥耶夫斯基、霍桑、梅爾維爾和梭羅。保羅‧奧斯特在十五歲那年,讀到杜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非常震撼,那時候就立志以後也要寫這樣的小說。在後來的小說創作中,奧斯特始終試圖嘗試對生命中的重大問題提問。「我沒有解決任何重大問題,這就是我還一直堅持提問的原因。如果找到了答案,可能也不是正確的答案。我雖然沒有答案,但是還是對尋找答案有一種迷戀,所有的作家窮其一生都是一個尋問的過程,而且推動他們追尋的動力是他們所未知的東西,而不是已知的東西,一開始似乎都是潛意識的東西,然後再繼續挖掘、探索。」
在保羅‧奧斯特的不少小說中都可以看到紐約做為背景。紐約不僅是奧斯特生活的城市,更是他小說中的真實的場景,就像電影外景地一樣。荒誕情節中的細節都發生在真實的場景之中:布魯克林的街道,曼哈頓的地鐵,唐人街的車衣廠……在〈玻璃之城〉中,奧斯特這樣寫道:「我來到紐約,因為她是最迷失也最淒涼的地方,一切都很脆弱,到處紊亂不堪。你只要睜眼瞥一下,到處充斥著脆弱的人、易碎的東西、軟弱的思想,整座城市是一堆破銅爛鐵。」這些以紐約為背景的小說形成了奧斯特鮮明的創作特色。《週日泰晤士報》評價道:「透過筆下鮮明的紐約,秉承偉大的美國傳統,迸放活力四射的文學創造力。」
「我最主要的身分還是作家,主要的任務是寫小說。在寫小說之前的十年是翻譯、寫詩、寫文章,但我一直想寫小說,一直在想怎麼寫小說。一九七九年開始小說寫作之後,就一直寫到現在。」寫小說的時候,保羅‧奧斯特和每個有正常工作的人一樣,七點到九點左右起床,坐在餐廳的椅子上,喝下去一大壺茶,看完報紙,然後去住所附近不遠的一個小屋子,在那裡開始寫作。路上買個三明治,午飯時間,餓了就邊吃邊寫,下午四、五點的時候結束工作。平時不用電腦,更不會使用電子郵件。
奧斯特身分繁多:小說家、詩人、劇作家、譯者、電影導演。他與華人導演王穎合作了兩部電影――「煙」和「面有憂色」。一九九○年,《紐約時報》的編輯給保羅‧奧斯特來電話,報紙預留了耶誕節那天倒數第二版整版,請他寫一個短篇小說。奧斯特從來沒寫過短篇小說,但還是答應了。小說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王穎看到後,覺得很有趣,就打電話給奧斯特,想把小說拍成電影。奧斯特以前看過王穎描寫三藩市唐人街的電影「陳先生失蹤」,對王穎很是欣賞。後來王穎來到紐約,奧斯特帶他在布魯克林轉了轉。王穎說,我要把你的這個短篇小說做成真正的劇情片。王穎請另外一個作家把小說寫成了電影大綱,然後寄給奧斯特。奧斯特看了之後,不太滿意,和太太一起又編了一個電影腳本。王穎看了之後認可了這個版本。接下來尋找資金的過程也頗為順利,王穎去東京辦事,和一個日本製片人談起這個電影腳本。這個日本製片人正好又讀過奧斯特的作品,很喜歡。日本製片人說,你真要做的話,把作者拉進來,我提供一半的資金。王穎回來之後,在美國又碰到一個美國製片人,解決了另一半資金。找到拍攝資金之後,王穎拉著奧斯特一起物色演員、編輯、拍攝,一共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奧斯特對這段經歷念念不忘:「王穎是我的老師,教了我很多電影方面的東西。」「煙」後來獲得柏林影展銀熊獎和最佳編劇獎。後來拍第二部電影「面有憂色」,那時候王穎已經病了,大部分導演工作是奧斯特承擔的。
由於「煙」的成功,保羅‧奧斯特應邀擔任坎城電影節評委,那一屆的評委中還有鞏俐。鞏俐說的是普通話,而給她派的翻譯講廣東話,結果無法溝通,只能請鞏俐的經紀人做她的翻譯。看完電影之後,評委發言,鞏俐對參賽影片進行藝術評判,前後講了五分鐘。但是翻譯只講了一句:鞏俐喜歡這個電影,鞏俐不喜歡那個電影。就完了。令保羅‧奧斯特印象深刻的是鞏俐非常漂亮,他盡量靠近鞏俐,坐在鞏俐旁邊,「她的皮膚非常好,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好的皮膚。」
二○○七年四月,紐約
王寅
詩人、南方周末記者
保羅.奧斯特近身錄
紐約的四月,丁香花已經開放,但是依然春寒料峭。保羅‧奧斯特的家位於布魯克林區公園坡附近,那是一套典型的褐石公寓。
點燃細枝雪茄的奧斯特身穿黑色襯衣,梳油頭,金魚眼,臉膛微紅,聲音渾厚,頭髮已經有些花白,側面望去,臉部輪廓就像古羅馬的塑像。同為小說家的奧斯特夫人希莉‧哈斯特維特(Siri Hustevedt)買回來一大棒梅花和紫色的鬱金香,在敞開式的廚房裡修剪花枝,將花一一插入花瓶,花香瀰漫在有著一百多年歷史的建築空間裡。
一九四七年,保羅‧奧斯特出生於美國一個...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43收藏
43收藏

 26二手徵求有驚喜
26二手徵求有驚喜



 43收藏
43收藏

 26二手徵求有驚喜
26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