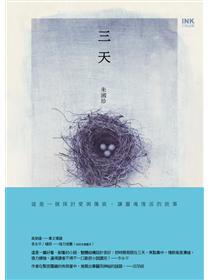陳雪與胡淑雯在最新一期的《短篇小說》裡,不約而同寫了同性戀人的愛情故事,是那麼美麗,又有些微哀傷,關乎身體、靈魂,自由與存有的想像。
〈維納斯〉摘文
陳雪
那晚初見面時,在熱鬧的酒吧裡。兩組朋友相約,十來人哄鬧,人群裡他們認出彼此,就像天生使然。冬樹完全知道鳳凰其實是男兒身,即使她那麼美,正如鳳凰也知道冬樹其實是女孩子,即使他那麼帥,在那個酒吧相遇時,他們只是遠遠看著對方,就感覺到一種「這個與我切身相關」的神祕感受,眼光始終無法離開對方,「有什麼事會在我們之間發生,必然地」,他們各自思考了許多問題,身邊共同的朋友站起來,坐下,握手,介紹,這誰那誰,誰誰誰,席間歡聲笑語,調笑調情,酒吧裡他們不是最怪的人,自覺坦然,只是忍不住想著「那個誰」像是嵌進自己心裡柔軟一角那麼合適地出現了,但都不知道接下來應該如何是好。
是冬樹先約鳳凰的,那晚所有人都互相加了臉書,交換手機號碼,立刻可以發Line,App起來,最新式的聯誼,他卻覺得那些手機上的圖案都顯得唐突,鳳凰在臉書上毫不避諱地放生活照與小文章,冬樹的臉書上卻只有每天紀錄的日出日落照片,他發簡訊跟她要了email,問了地址,正式地用紙筆寫了一封短信約她出來喝咖啡。
今天稍早在咖啡店門口碰頭,他們都二十六歲,完美的髮妝使鳳凰看來更成熟些,在店裡,鳳凰身著女裝,冬樹不完全男性化的中性模樣,使他們般配,又醒目。
他們倆從下午談到深夜,換了兩家咖啡店,最後到二十四小時營業的麥當勞待到凌晨兩點,像有一輩子的話急需與對方交談,不疾不徐,任由腳下的地景變換,喝下大量液體,像流水滑過那些建築,漫向屋內的某張椅子,爬上桌,洩落地。這家店打烊,便起身走進黑夜的街道,他們很自然地挽著彼此,幾乎像是一對中年夫妻,鳳凰說附近有個公園,他們就晃進公園裡,冬樹想起這是他大學時代苦苦等過女孩子的地方,溜滑梯前滿地的菸蒂猶如當年擲落踩熄。走累了,又進入店舖,尋找一組可以對看的桌椅,持續地把那些需要說的話逐漸變成語言說出來。
要對彼此交代自己過往人生並不困難,只是需要足夠的時間,他們人生有許多細節並不相同,甚至可說相似的地方還比較少,並沒有出現「不需言語就可以理解」的神祕感應,他們感應到的,是完全相反的情緒,是一種必須要對「這個人好好說明自己」的需要,同時地,等量地,從心裡湧出來。就這麼做了。
〈年下之男〉摘文
胡淑雯
也許是孤單,純粹的肉體孤單。 失溫太久的我,需要人的體溫。以前聽梅子說,有些踢被老婆甩怕了,被現實累壞了,會上網釣男人,找個紳士伺候自己。大概就是這種感覺吧。
除了自暴自棄,捨身離開自己,或許也出於恐懼,恐懼即將展開的荷爾蒙「治療」。於是通過男人的身體,對自己提出最後的質詢:你可以嗎?可以委身於強壯的男性,接受溫柔的豢養嗎?
也有那麼一點好奇。對這個曾經擁有曙芳的男人,感到羨慕,感覺可親。
事後,捧著宿醉的腦袋,喝著現榨的檸檬,才得知小路也有他的孤寂。他長得太好看,太成功,碰到的女人沒幾個真心,愛的都是表面風光。他說他對女人沒有信任感,還說,「正常的女人其實都不太正常。」
接著,小路將半滿的玻璃杯擱在額頭,癡癡望著天花板,眼神空空的,像是在回憶,回憶他經歷過的女人,又彷彿在思索,思索「這一晚」對他的意義、「小冠」(而非張婉宜)對他的意義,突然想通了什麼,幽幽地說,「我相信那個女人……她叫Michelle,本名李靜慧;我相信,她是真的需要那筆錢。」 我沒說話,小路也沈默了許久,直到門縫裡塞進熾熱發白的黎明,小路發出一種感冒般恍惚而低沉的聲音,對我說:
「你那樣對我,你剛剛那樣對我,是因為你太正常,還是因為你太不正常?」
我一時反應不過,隨口丟了一句:我只知道,我不是「不太正常」的那種,因為我不是「正常的女人」。
「你說什麼?」小路側過身來,將一臉的疑惑推向我。
「你自己說的呀,」我重複小路的話,「正常的女人都不太正常。」
「但是,你是我這兩年所遇到的,最好的一件事。」小路說。
小路說他從來不缺女人,再漂亮的女人他都經歷過,摸過整型的乳房,也睡過最光滑的皮膚。「但是只有小冠你,是唯一的真人。」那一刻,那一刻,我真心感覺自己得到祝福,低聲哭泣起來。我想到自己注滿化學藥劑的未來,遙遙無期實則尷尬多餘的變性手術。但小路讓我覺得自己是有資格的,有資格理直氣壯走下去的。
小路竟然墜落了,天天都想見面,真誠大膽直視我的眼睛,說出「我愛你」。我感動莫名,卻也更加確信自己沒有辦法,沒有辦法成為「男人的女人」。而小路如此美好,好得像一則標準答案,肯定不是我要的。
寧願繼續否定,並且持續寬諒,這不成體統的世界;同時心安理得,以身作則,繼續做個不成體統的人。
 8收藏
8收藏
優惠價: 9 折, NT$ 225 NT$ 250
本商品已絕版
陳雪與胡淑雯在最新一期的《短篇小說》裡,不約而同寫了同性戀人的愛情故事,是那麼美麗,又有些微哀傷,關乎身體、靈魂,自由與存有的想像。
〈維納斯〉摘文
陳雪
那晚初見面時,在熱鬧的酒吧裡。兩組朋友相約,十來人哄鬧,人群裡他們認出彼此,就像天生使然。冬樹完全知道鳳凰其實是男兒身,即使她那麼美,正如鳳凰也知道冬樹其實是女孩子,即使他那麼帥,在那個酒吧相遇時,他們只是遠遠看著對方,就感覺到一種「這個與我切身相關」的神祕感受,眼光始終無法離開對方,「有什麼事會在我們之間發生,必然地」,他們各自思考了許多問題,身邊共同的朋友站起來,坐下,握手,介紹,這誰那誰,誰誰誰,席間歡聲笑語,調笑調情,酒吧裡他們不是最怪的人,自覺坦然,只是忍不住想著「那個誰」像是嵌進自己心裡柔軟一角那麼合適地出現了,但都不知道接下來應該如何是好。
是冬樹先約鳳凰的,那晚所有人都互相加了臉書,交換手機號碼,立刻可以發Line,App起來,最新式的聯誼,他卻覺得那些手機上的圖案都顯得唐突,鳳凰在臉書上毫不避諱地放生活照與小文章,冬樹的臉書上卻只有每天紀錄的日出日落照片,他發簡訊跟她要了email,問了地址,正式地用紙筆寫了一封短信約她出來喝咖啡。
今天稍早在咖啡店門口碰頭,他們都二十六歲,完美的髮妝使鳳凰看來更成熟些,在店裡,鳳凰身著女裝,冬樹不完全男性化的中性模樣,使他們般配,又醒目。
他們倆從下午談到深夜,換了兩家咖啡店,最後到二十四小時營業的麥當勞待到凌晨兩點,像有一輩子的話急需與對方交談,不疾不徐,任由腳下的地景變換,喝下大量液體,像流水滑過那些建築,漫向屋內的某張椅子,爬上桌,洩落地。這家店打烊,便起身走進黑夜的街道,他們很自然地挽著彼此,幾乎像是一對中年夫妻,鳳凰說附近有個公園,他們就晃進公園裡,冬樹想起這是他大學時代苦苦等過女孩子的地方,溜滑梯前滿地的菸蒂猶如當年擲落踩熄。走累了,又進入店舖,尋找一組可以對看的桌椅,持續地把那些需要說的話逐漸變成語言說出來。
要對彼此交代自己過往人生並不困難,只是需要足夠的時間,他們人生有許多細節並不相同,甚至可說相似的地方還比較少,並沒有出現「不需言語就可以理解」的神祕感應,他們感應到的,是完全相反的情緒,是一種必須要對「這個人好好說明自己」的需要,同時地,等量地,從心裡湧出來。就這麼做了。
〈年下之男〉摘文
胡淑雯
也許是孤單,純粹的肉體孤單。 失溫太久的我,需要人的體溫。以前聽梅子說,有些踢被老婆甩怕了,被現實累壞了,會上網釣男人,找個紳士伺候自己。大概就是這種感覺吧。
除了自暴自棄,捨身離開自己,或許也出於恐懼,恐懼即將展開的荷爾蒙「治療」。於是通過男人的身體,對自己提出最後的質詢:你可以嗎?可以委身於強壯的男性,接受溫柔的豢養嗎?
也有那麼一點好奇。對這個曾經擁有曙芳的男人,感到羨慕,感覺可親。
事後,捧著宿醉的腦袋,喝著現榨的檸檬,才得知小路也有他的孤寂。他長得太好看,太成功,碰到的女人沒幾個真心,愛的都是表面風光。他說他對女人沒有信任感,還說,「正常的女人其實都不太正常。」
接著,小路將半滿的玻璃杯擱在額頭,癡癡望著天花板,眼神空空的,像是在回憶,回憶他經歷過的女人,又彷彿在思索,思索「這一晚」對他的意義、「小冠」(而非張婉宜)對他的意義,突然想通了什麼,幽幽地說,「我相信那個女人……她叫Michelle,本名李靜慧;我相信,她是真的需要那筆錢。」 我沒說話,小路也沈默了許久,直到門縫裡塞進熾熱發白的黎明,小路發出一種感冒般恍惚而低沉的聲音,對我說:
「你那樣對我,你剛剛那樣對我,是因為你太正常,還是因為你太不正常?」
我一時反應不過,隨口丟了一句:我只知道,我不是「不太正常」的那種,因為我不是「正常的女人」。
「你說什麼?」小路側過身來,將一臉的疑惑推向我。
「你自己說的呀,」我重複小路的話,「正常的女人都不太正常。」
「但是,你是我這兩年所遇到的,最好的一件事。」小路說。
小路說他從來不缺女人,再漂亮的女人他都經歷過,摸過整型的乳房,也睡過最光滑的皮膚。「但是只有小冠你,是唯一的真人。」那一刻,那一刻,我真心感覺自己得到祝福,低聲哭泣起來。我想到自己注滿化學藥劑的未來,遙遙無期實則尷尬多餘的變性手術。但小路讓我覺得自己是有資格的,有資格理直氣壯走下去的。
小路竟然墜落了,天天都想見面,真誠大膽直視我的眼睛,說出「我愛你」。我感動莫名,卻也更加確信自己沒有辦法,沒有辦法成為「男人的女人」。而小路如此美好,好得像一則標準答案,肯定不是我要的。
寧願繼續否定,並且持續寬諒,這不成體統的世界;同時心安理得,以身作則,繼續做個不成體統的人。

※ 二手徵求後,有綁定line通知的讀者,
該二手書結帳減5元。(減5元可累加)
請在手機上開啟Line應用程式,點選搜尋欄位旁的掃描圖示
即可掃描此ORcode
|
||||||||||||||||||
|
||||||||||||||||||
|
||||||||||||||||||